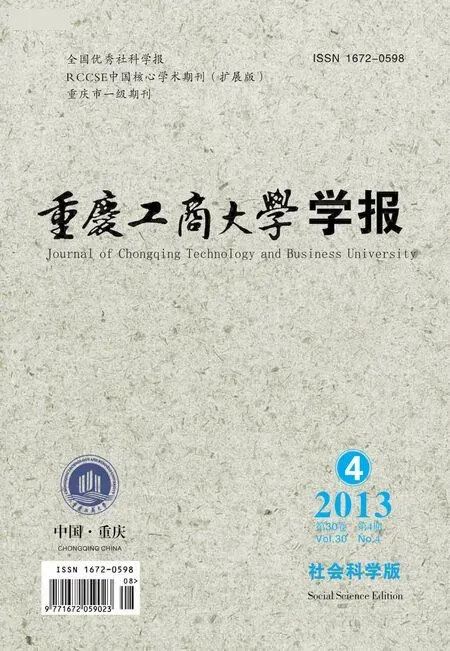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学术价值探析*
2013-03-31陈良中
陈良中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047)
袁燮(1141—1224),字和叔,鄞县人,登进士第,历官礼部侍郎,宝文阁直学士,追谥正献,学者称絜斋先生。乾道初入太学,与同里贤俊沈焕,杨简,舒璘聚于学,朝夕以道义相切磨。陆九龄为学录,亲炙之。遇陆九渊于都城,一见即指本心,公神悟心服,遂师事焉。又与乡贤吕祖谦游,自谓“屡升其堂”“有怀诲言,敢不铭刻。”[1]又从永嘉陈傅良游,由此器业日益充大。淳熙辛丑(1181)第进士。迟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宁宗嗣位,始以太学正召。伪学之禁兴,袁燮亦以论国罢。嘉定初元(1208),天子诛权臣韓侂冑,召公为宗正簿、枢密院编修官权考功郎,迁丞奉常,提举江西常平权隆兴府事。明年春迁秘书少监兼司业,及秋进祭酒,冬除秘书监,仍兼祭酒。每延见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学。九年(1216)春正月兼崇政殿说书,十一月权礼部侍郎,升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进侍讲,犹兼祭酒。明年除宝谟阁待制提举鸿庆宫,起知温州,辞。升直学士,皆奉祠如初。为人守正不阿时好,平生之节不可屈。为官孜孜献纳,有言必尽。其志以扶持世道为己责,然自始学于义利,取舍之辨甚严。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癸已薨于正寝,享年八十一。
一、袁燮《絜斋家塾书钞》概况
袁燮少而嗜书,讲道于家,以诸经《论》《孟》大义警策学者,于《书》《礼记》论说尤详,有《絜斋集》二十六卷,《后集》十二卷,亡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为二十四卷。又有《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库馆臣辑为四卷。袁燮常于“平旦集诸生及诸子危坐说《书》,夜再讲,率至二鼓。”用功颇勤。其家塾讲义由长子袁乔汇录,其子袁甫绍定四年(1231年)十月己未刊刻,其《后序》云:“是编也伯兄手钞,虽非全书,然发挥本心大旨具在。伯兄名乔,天资纯正,用志勤笃……惜未尽行所学耳。……刻是编,名曰《絜斋家塾书钞》,而纳诸象山书院,以与世世学者共之。”[2]絜斋乃袁燮斋名,“絜”本自《大学》“君子有絜矩之道”,《礼记注疏》云:“絜,犹结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谓当执而行之,动作不失之倍。”[3]谓君子行为符合法度。袁燮当取此意为斋名。然是书书名历代书目记载不一,陈振孙载为《洁斋家塾书钞》十卷,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与陈振孙同。《宋史·艺文志》载为《书钞》十卷。絜斋、洁斋之称宋世已经歧出,其子袁甫概称“絜斋”,真德秀撰袁燮《行状》作“洁斋”,合以文献,袁燮之斋名当以“絜斋”为优。
是书久已亡佚,朱彝尊作《经义考》注云“未见”、叶文庄编《菉竹堂目》“尚存”,[4]宋以来诸家说《尚书》者罕引,其传本稀少。今传本乃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采辑编次而成,止于《君奭》,厘为十二卷。其中《五子之歌》《胤征》《汤誓》《仲虺之诰》《伊训》《梓材》诸篇解全缺,而《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同为逆河,入于海”、《汤诰》“夏王灭德作威……孚佑下民,罪人黜伏”、《盘庚上》“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予亦拙谋,作乃逸”、《盘庚中》“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微子》“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我不顾行遯”、《洪范》“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康诰》“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洛诰序》《多士》“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非予罪时惟天命”等节之解有缺佚。
二、《絜斋家塾书钞》特点及体式
(一)据关键字词推衍义理
袁燮解《书》以发挥义理为准的,往往一节围绕关键字词阐说。如解《舜典序》“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云:“尧、舜二《典》之所谓聪明,即《论语》之所谓仁,仁与聪明若不相似,然其实一也。四肢偏痹谓之不仁,此心有毫厘窒碍便是不仁,便是不聪明。孔门学者急于求仁,求仁所以求聪明也,此是学问最亲切处。”[5]论“聪明”而及《论语》之“仁”,旁牵远绍,稍涉牵强。又解《舜典》“浚哲文明”之“文”云:
文,是粲然有文可观。只如这一“文”字,须是子细思索如何是文。如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如所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夫是之谓文。今人有文者能几何?纵有之而亦甚微。色相杂谓之文,《周礼》亦言青与赤谓之文。古人多说这文字,称尧曰:“焕乎其有文章。”言夫子曰:“文章可得而闻。”《记》言:“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棫朴》一诗,诗人美文王而比之以天之云汉,其诗曰:“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可见其文矣。《易》又曰:“内文明而外柔顺。”盖刚健文明之德,这个断少不得。[5]705-706
此一段文字阐释“文”之义理,至“夫是之谓文”经义已完足,接着推衍古人重“文”之义,引《诗》《书》《易》《礼记》之文敷衍阐扬以补充说明,务在言明“文”之重要性,文多枝蔓,然乃家塾讲章常态,非注疏谨严可比。这种据关键字推衍义理,一书之中皆是。如解《大禹谟》“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袁氏云:
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此两期字不可不详玩,可以见得皋陶之心。期于予治,是期使天下至于大治也。刑期于无刑,是不特苟了职事,必欲至于无刑也。犹有刑焉,是天下犹有不善之人也,天下犹有不善,是明刑之责也。人莫不有所期,如射者期中于的,所期高者其至必高,所期远者其至必远,苟无所期则亦终于卑污蹇浅而已。观期之一字,想见一夫不获,皋陶必曰:“时予之辜。”[5]733
据“期”一字衍说义理,欲以此见皋陶之心,此为袁氏解《书》宗旨。由圣贤之心推及“人莫不有所期”,旁枝逸出,虽解说寓教化,颇涉支离,带有鲜明的家塾说《书》痕迹。又解《皋陶谟》“臣哉邻哉,邻哉臣哉!”云:
邻之一字直是相亲,有师友之义。古者五比为邻,言邻取其亲也。……世尊君卑臣之说兴,人主俨然南面以祸福刑威宰制天下,古人师友群臣之义变为以尊临卑之事矣。邻之一字不可不着精神看,此等字在后世皆无了。[5]757
此一段袁燮据“邻”字发掘君臣师友之义,批评后世“尊君卑臣”、人主以祸福刑威宰制天下的专制,蕴含着理想社会的诉求。然袁氏敷衍义理稍涉泛滥,带有十分鲜明的家塾讲授性质,而缺乏注疏体式的谨严。
(二)解《书序》与尊经精神
对于文本的处理,直接反应经学家的思想。袁燮《书钞》解《书序》《逸书序》,以《书序》为孔子作。袁燮受知与朱子,而朱子废《序》解《书》之说当有所闻,这种处理方式是其尊信古经思想的反映。如解《旅獒序》“西旅献獒”云:“《书》言西旅底贡厥獒,而孔子序《书》笔之曰献。盖所谓贡者,如《禹贡》所言贡赋皆服食器用有用之物,獒岂用物乎?非用物而贡之,是远夷以此媚中国也。故圣人易贡为献,其意深矣。”[5]887辨“贡”“献”之别,对献纳之物深所警惕。袁燮深信孔子序《书》说,因此以“春秋笔法”解《序》,如解《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云:
《序》称十一年,《书》称十三年,前后之说者多矣。或以为两处必有一误,或以为观兵于十一年。要之,观兵者为是。……伐纣虽在十三年,然当其观兵之时,伐商之心盖始于此,所以孔子定为十一年,《春秋》之法也。一月戊午,此即十三年之一月,孔子书法甚严,观书一月便可见,不曰正月而曰一月,正者,正也,是时无王不得为正,故不称正而称一,其严如此。[5]854
《书序》与经文纪年不相应,袁燮谓武王伐商之心始于观兵之时,孔子序《书》定为十一年。又以“一月戊午”即“十三年之一月”,然与上文“十一年”不相照应,非是。又云:“不曰正月而曰一月,正者,正也,是时无王不得为正,故不称正而称一”,此皆以“春秋笔法”而寻经典之微言大义,钩深索隐。又解《伊训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云:“然桐宫在国都之外,臣子而摈君于远,不可以为训,故圣人笔之曰‘放’,所以著伊尹之过也。”[5]797严辨君臣大义。一书之中,袁氏皆本“春秋笔法”以论《书序》。
与信孔子序《书》相应,袁氏尊信古经,对当时疑经之说多有批评。如解《武成》一仍原始篇序,又《康诰》篇首四十八字苏轼以来诸家以为脱简,袁燮云:“其实不然。此事正与封康叔一事脉络相贯,当时虽命康叔而心在洛邑,商之民既迁于此,而吾于是乎命焉,不特告康叔,亦使商民闻之晓然知上意所在,周公之意正是如此。则作书者正当叙此一段,如何是脱简乎?”[5]900批驳苏轼脱简之说。《多士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是洛邑既成之后方迁殷民于此也。而《召诰》云:“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则是营洛之始庶殷已在洛。有学者以为《多士》之书当在《洛诰》之前,编帙淆乱耳。袁氏云:“《召诰》所谓庶殷,盖经始洛邑之时所调发从役者尔,……周既得天下,则商人皆吾役也,国家有大兴作则皆调发以从……及都邑既成,然后尽迁其民,周公营洛之次第盖如此。”[5]932此一解说是相当合理的,反对随意改变篇序。
袁燮不怀疑《尚书》古经,正如陆九渊认同《大学》古本,有鲜明学派特色。袁氏对《书序》的尊信,对“书法”的关注,这一点更多受到尊信古学的乡贤吕祖谦“《书》之《序》,《春秋》之策,其同一笔乎!”[6]思想影响。其解经思想与当时诸家疑古有间。
三、袁燮《书》学思想
(一)心学思想的发扬
1.心即天——良心善性之根源
袁燮受学象山,一本其师心学宗旨,以发扬本心为宗旨,探究人复善的可能和依据,带有经学家鲜明的淑世精神。袁燮之学源自陆九渊,象山学问之要在得其本心,袁燮遇象山于都城,一见即指本心,燮服膺而师事之。袁燮学问倡发明本心,兼综体用,以开物成务为宗旨,尝云:“见象山先生读《康诰》有所感悟,反己切责,若无所容;读《吕刑》叹曰:从肺腑中流出。”[5]695陆九渊这种读书反求诸己的方式无疑对袁燮产生深远影响,故袁氏于《尚书》一经发明本心,以圣人为职志,《书钞》中反复致意,随处发掘本心善性。如解《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云:
衷之义与中同,皆只是人心,天下之至中者,人心也。是中也,天得之而为天,人得之而为人,初非是两个。谓之降衷,则是在天者降而在民,下民之衷即上帝之衷也。以此观之,人之性如何不是善?天道降而在人,初不曾分。孟子所以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谓人之性善,只缘见得这个道理分明。成汤诞告之首发为此言,所以使万方有众咸知良心善性吾所固有,咸知吾心之衷与上帝一般,其警人也切矣。[5]793
人得“中”而具良心善性,即天赋与人善性,阐明了人的类本质性及根源。天人同得此“中”,“初非是两个”,阐明了天人具有同质性,在人心得以完全展示的时候“吾心之衷与上帝一般”,这是陆九渊“吾心即宇宙”思想的阐扬,这个与天为一的心无疑带有本体性质。袁燮在文集中有更明确的论述,《建宁府重修学记》云:“人之一心至贵至灵,超然异于群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尔。”[7]天地人同此心,心即宇宙,赋予了心本体性质。心体又呈现为道,《韶州重修学记》“上帝降衷,有自然之粹精,保而勿失,大本立矣,万善皆由是出。……天下无心外之道,安有不根于心而可以言道者乎?”[7]119-120自然之道只有通过人的认识把握才能具有现实价值,在现实世界作为一种合规律合目的的呈现,从这一点上说“天下无心外之道”是完全正确的。在对“本心”的本体追述这一点上,袁燮思想的重心在于用“本心”来阐述人心本善以及复善的可能性。
人得天地之中以为性,“中”不偏不倚,无一毫欠缺,决定了人心的纯然之善。正如《皋陶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一节,经义主要阐明如何矫正人个性的偏失,袁燮本其心学思想阐释云: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天之所以为天,中而已矣。天得此中而为天,人得此中而为人,天以此中降人,人受此中而生焉。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大本者,人心也。人心者,中也。人之本心固至中而不偏。[5]747
上天赋予人的“本心固至中而不偏”,袁氏认为人性是没有丝毫缺陷的。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对人性的同质性有相同认识,人禀天地之中而得良心善性,这是人的类本质。人“至中不偏”之本心乃现实价值之根源,是明识道理的关键。所谓“吾之本心,此所谓道心”“所谓道心,只是此心之识道理者。”[5]737又解《盘庚中》“丕从厥志”云:“大抵天下之至明者,人之本心也,……本心虽明,一时蔽于利害,则往往昧于是非之理,然其实自不可泯没。”[5]826这一“本心”是至明而“不可泯没”,是辨析是非利害的根本。道德的扩充可以与天为一“此心即上帝之心”,并且举四海九州之人“此心皆天心”,如解《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云:“咸有一德,则此心即天心也,与天为一,一物不留,是以享天下之至乐,故谓之克享。人皆有此天心而不能享之,……吾德既一,则此心即天心也。”[5]811人秉持纯一之德,无物欲之障蔽,“此心即天心”便与天为一,可以彻照万物之理。
2.气禀物欲——人性差异的原因
人的类本质是同一的,但现实的个体却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异来自何处?朱、陆二家皆以“气禀”说进行了解释。陆九渊以“良心”为人之本质,“此心本灵,此理本明”是纯然善的。但“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必以二涂总之,则宜贤者心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气必浊。”[8]人的现实差异则来自于气禀之不同,陆九渊以气之清浊解释了现实人性的差别。袁燮秉承师说,以气禀说阐释了个体之差别,如解《皋陶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一节,经义主要阐明如何矫正人个性的偏失,袁燮云:
人之本心固至中而不偏。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禀山川之气要不能无偏者。[5]747
气禀不同而导致了人性格的差异,但气禀更多的是出生环境决定的,带有与生俱来的特性,个体无法选择。气禀不同之外,“习尚所梏,俗论邪说所蔽”[8]137也会遮蔽人之善性,物欲、个人思想及所接受学说等后天因素会影响人之善恶,又云:“愚不肖者之蔽在于物欲,贤者智者之蔽在于意见,髙下污洁虽不同,其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则一也。”[8]11“物欲”“意见”等都是遮蔽人性的重要因素。袁燮《书钞》反复论述物欲之害,阐明师说。如解《说命中》“惟天聪明,惟圣时宪”云:“人之聪明有时而不聪明,天之聪明则无时而不聪明,利欲昏之,外物夺之,人固有时而不聪明矣。”[5]839袁氏认为人“本心”易被利欲外物遮蔽,这是导致不明事理的关键。又解《大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云:“正当危疑之际,所以此心皆昏蔽而不知天理之所在。”[5]896袁燮以为当时不想讨伐三监叛乱之人“此心皆昏蔽而不知天理”,从人性论角度做出了阐述。袁氏于《书钞》中凡涉不合事理之事皆以物欲、利欲之蔽“良心”为说,务在阐明现实人性之恶来自何处。
人心既有偏弊,何以复性?袁燮《书钞》多方致意,与陆九渊强调静坐不同。物欲遮蔽了人心,祛出物欲之蔽就成为复性的一大关键。如解《大禹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云:
所谓一者,有一毫之私意,有一毫之人欲,便不是一。惟精惟一,则人心必不至于危,道心亦不至于微。[5]738
以精一为复性工夫,就是要做到无“一毫之私意”、无“一毫之人欲”,精诚专一。“方其喜怒之萌,反而以道理观之,其当喜耶?不当喜耶?当怒耶?不当怒耶?方其声色之接,反而以道理观之,其当好耶?不当好耶?”[5]737以“道心”体察是非美恶,不敢有一毫懈怠,此乃圣人用功处。又强调以学问变化气质,排除私欲的干扰,所谓:
所贵乎学问者,将以克其气质之偏,约而归于中也。故未归于中也,当强力矫揉,用工日深,使得其大本可也。[5]747
袁燮重学问以变化气质,“学问者,将以克其气质之偏”,并且强调“强力矫揉”,带有强制性,这与老师陆九渊倡导“尊德性”直悟本心的修养方法有差异的,而更接近重“道问学”的朱子。袁氏认为这种复性工夫在于一生的持守,而不是一时的冲动。解《皋陶谟》“思曰赞赞襄哉”,据上文意,“襄”当训“成”[9]。张载、苏轼、薛季宣诸家均以为“曰”乃“日”之讹,经义谓皋陶思日日赞成舜治天下之功。袁氏解云:“赞,进也。襄,上也。……皋陶不自以为足,方且进进,只欲向上。古人工夫只是不住,盖此事无住时节。”[5]753袁氏阐释以修养工夫立论,强调了修养的终生性,指出复性“只是不住”,而不是刹那间的顿悟。又《大禹谟》“耄期倦于勤”,经义指勤于本职,袁氏云:“勤之一字不可轻看,《诗》称‘文王既勤止’,召公戒成王‘夙夜罔或不勤’,且君道之尊,不躬亲庶政,而所勤者果何事?学者要当思而得之。盖缘此心不可一念不存,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要须常常兢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之谓勤。勤则其德日进,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勤而已矣。”[5]732“勤”本指行为,而“此心不可一念不存”之说则重在对持存本心的论述,把行为化为心理。又解《旅獒》“夙夜罔或不勤”云:“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一个勤。《诗》言‘文王既勤止’,才不勤便有间断,才间断便有过失,古人未尝一念之不勤。”[5]888同样于“勤”字发挥出存心的义理。在袁燮的思想世界里,保持本心是一个念念不住的心理历程,此生不息,此念不息。
心学强调践履工夫,关注发明人之本心,有鲜明的现实关怀,这一点上与静坐参禅的佛教徒、打坐练气的道教徒有根本的区别。时人多批评象山学问有禅意,袁燮驳斥云“或谓先生之学如禅家者流,单传心印,此不谓知先生者。先生发明本心,昭如日月之揭,岂恍惚茫昧,自神其说者哉!”[7]99确实象山学问宗旨在发明本心,更重视学问对人生的价值导向,对溺于章句注疏而忘却人生的学问取向是一种有益的矫正,而与佛家传心印是有别的,袁燮确实抓住了老师学问宗旨的精髓。
(二)吸纳程朱理学——心学与理学的融合
陆氏后学学多与朱子后学对立,这在杨简身上是比较突出的,而袁燮深受知于朱子,其《题晦翁帖》云:“淳熙己丑之岁,四明大饥,某待次里中,晦翁贻书郡守谢侯,谓救荒之策合与某共讲之。某虽心敬晦翁,未之识也。久而吕子约为仓官,晦翁屡遗之书,未尝不拳拳于愚。不肖自念何以得此,或者过听以为可教耶?”[7]104朱子于袁燮眷眷不忘,燮解《书》吸纳程朱子思想颇多,可谓陆学私淑朱学者。袁燮不明引朱子之说,而多暗用,盖时处庆元党禁而言论当有避忌。袁燮《书钞》广取程颐之说,如解《太甲下》“唯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一节云:
敬、仁、诚此三字当仔细思索。伊川言:“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方其此心无一毫之驰散,无一毫之夹杂,既不思量此,又不思量彼,此是主一,此是无适,此所谓敬也。……才是能敬,天即亲之。盖方其致敬,此心即天心也,天安得而不亲。仁是识痛痒处,……孟子以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仁之端,自此而充之,举天下皆与吾为一体,则仁道尽矣。……诚即成也,《中庸》所谓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5]805
袁燮全用程颐观点为解,“仁是识痛痒处”乃程氏观点,程氏云:“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10]又《洪范》“敬用五事”解云:“敬用者,能敬而后能用也。貎能敬则恭,言能敬则无口过,视听能敬则不至于非理,思能敬则不至于邪思妄念,故以敬为主。……此即伊川之所谓主一者是也。”[5]872明引伊川“主敬涵养”精神为说。袁氏对朱子观点暗引亦多,如解《尧典》“安安”云:“安安者,安而又安也……仁者安仁,或安而行之,恭而安。古人多说这安字,德盛仁熟,终日周旋不出于规矩准绳之内,而无一毫辛苦勉强之意。”[5]698-699朱子云:“安安,无所勉强之貌。言其德性之美皆出于自然而非勉强,所谓性之者也。”[11]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又如解《微子之命》“殷既错天命”云:“天命,天之道理也。”[5]852朱子云:“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12]二者思想一贯。他如解经暗用程、朱之说处颇众,此乃二家相承小之小者。
《书钞》中天理人欲之心性论、道统观与程朱一脉相承,此为程朱思想之核心与关键。朱、陆对“心”的认识可以当作二家分判之界标,朱子认为“道心”即天理,是人心之本然善性。“人心”是源于人自然属性的各种生理欲望,“人心是知觉,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底,未是不好,只是危。”[13]朱子《观心说》曰:“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11]3278朱子把心分为道心、人心两个层面,意在探讨人性善恶之源,同时寻求修养方法。陆九渊强烈反对此种观点云:
《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曰惟危,自道而言则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圣,非危乎?无声无臭,无形无体,非微乎?[8]395-396
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坚决反对程朱分人心为二的观点,认为《尚书》所谓“人心”指人而言,人不念其善则“人心”放失。“道心”指道,“无声无臭,无形无体”,微妙难测。又云:“天理人欲之私论极有病。”[8]475陆九渊批评程朱学派心性之说。而袁燮解《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云:
凡是人便有这心,所谓人心。道心者,良心也。人心危而难安,道心微而难明。所谓道心,只是此心之识道理者……此正吾之本心,此所谓道心也,只是道心隐微不著。[5]737-738
袁燮以察识善恶之心为“道心”,易受外物影响之心为“人心”,这一认识与陆九渊“人心本善”之说是不一致的,而更接近朱子思想。人心为何易受物欲诱导,袁燮以为“人之一身皆是血气,血气聚而为形体,而耳目之官又不思所以,易得为物所诱而溺于逸欲。”[5]750“气聚成形”这实质是程朱以气质论人性。又《太甲上》“王未克变”经义本谓太甲不听伊尹教训改过,袁燮解云:“天理不足以胜其私欲,两者交战,欲为善乎则人欲炽盛不能尽克,欲为不善乎则闻伊尹之训如此,知善之不可不为,既不肯为不善,又未能决意为善,此所谓王未克变,正交战之时也。”[5]800-801陆氏几乎不以天理人欲说人性,以天理人欲为说,此乃程朱理学之家法。又解《咸有一德》“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云:“一是天理,二三是人欲。大抵天理自是纯一,终始能保守此一,则亦终始常如此之新。”[5]812“一”经义指道德纯粹专一,与天理人欲本不相涉。由袁燮以天理人欲思想解《书》可以看到他更多地受到了朱子思想影响。
又从道统观来看,陆九渊认为:“孔门惟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8]443所谓“颜、曾从里面出来”是指他们学问以“尊德性”为根本,也即是学问在发明本心。“外入之学”指“道问学”一途,指为学专注知识而忘却了其价值导向。所以陆九渊认为道统至孟子而绝。而袁燮《廉溪先生祠堂记》中阐述了他的道统观,云:
昔者孔氏之门,惟曾、颜最知道,颜子蚤死,夫子哭之恸,痛斯道之无托尔。幸而曾子得之,传之子思,传之孟子。皇皇乎正大之统,昭晰无疑,毫发不差。……自时厥后……道统寖微,不绝如线。寥寥至于我宋,乃始有若濂溪先生者,精思密察,窥见其真,……二程氏之学渊源于兹,遂以斯道师表后进,迄今学者趋向不迷。[7]109
袁燮以周敦颐为理学开端,这一道统观念与朱子《伊洛渊源录》《近思录》所建构的道统谱系是一致的,袁燮实深受朱子影响。这种思想上的一脉相承,方可见学术上的前后影响。
四、袁燮《书》学影响及评价
袁燮粹学伟行为时儒宗,其影响当时甚大,然《书钞》罕传于世。袁燮思想核心无疑是来自陆九渊,一书之中反复阐述“天人一心”之说,为象山之干城。但袁燮思想取境较宽,其解《书》较多地受到吕祖谦、朱子的影响。乾隆题《袁燮絜斋家塾书钞》云:“议论持醇正,兴亡鉴古今。致危惟戒逸,胜怠莫如钦。惜未联全璧,幸仍拣碎金。流斯失法度,先已获予心。”[5]696肯定了《书钞》议论醇正及书中所寄兴亡之戒,评价颇为中肯。全祖望论云:“慈湖之与絜斋,不可连类而语。慈湖泛滥夹杂,而絜斋之言有绳矩。”[14]此乃本理学宗旨为评判,“夹杂”当指杨简学问以“提醒为要”,有禅宗之习。袁燮教人倡“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此乃其入门工夫。“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14]2528尤重工夫,此乃所谓“绳矩”。袁燮《书钞》是一部有益于治道的经学著作,又是象山心学一派的《书》学要着,研究此书可见心学之思想流变,以及心学、理学之相互交流借鉴,对于了解时代思潮以及经学之本质皆有帮助。然陆氏之学仅盛于甬上,其学传播未广。而朱子门生遍布天下,由于宋理宗赏识,逐渐以伪学入正统,朱门弟子多与象山殊轨,其学不繁乃理之自然。
[1]吕祖谦.东莱集(附录卷二)[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8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464.
[2]袁甫.蒙斋集(卷十一絜斋家塾书钞序)[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470.
[3]孔颖达.礼记注疏(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74-1675.
[4]朱彝尊.经义考(卷八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8:459.
[5]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卷一)[M].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刊.四明丛书约园刊本.1994:705.
[6]时澜.增修东莱书说(卷三十五)[M].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7:149.
[7]袁燮.絜斋集(卷十建宁府重修学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18.
[8]陆九渊.陆九渊集(卷六)[M].与包祥道.北京:中华书局,1980:80.
[9]杨伯峻.左氏春秋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062.
[10]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上)[M].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33.
[1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154.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15.
[13]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668.
[14]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2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