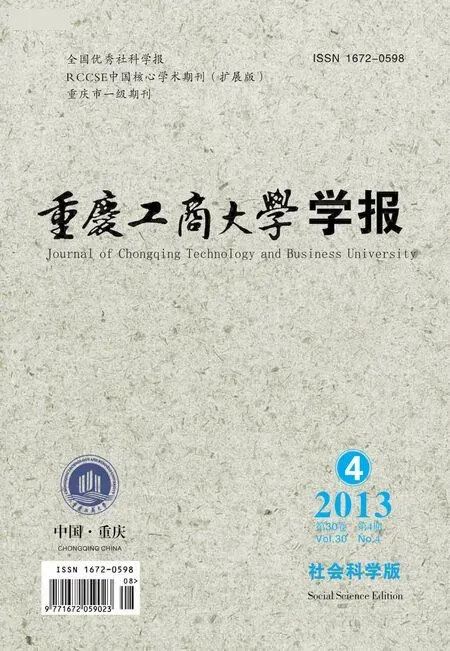步入重生的美学
——解读《山音》的老年主题*
2013-03-31冯千
冯 千
(四川外语学院 日语系,重庆400031)
一、引言
《山音》(『山の音』)是川端康成创作生涯中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其战后代表作之一,全文由十六章构成,自昭和24年(1949年)首次发表在《改造文艺》上起,先后以各章节名称发表在《群像》《新潮》《世界春秋》等杂志上,直至昭和29年(1954年)终稿,最后命名为《山音》,由筑摩书房出版发行。在日本,关于《山音》的文学批评、研究始于作品发表伊始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山音》与日本传统、《山音》中的女性形象、包括梦境、幻觉在内的信吾的各种心理活动及其象征意义等多个方面。而在众多研究者中,长谷川泉和小泽正明则明确将注意力集中在这部作品的老年主题方面。长谷川泉指出《山音》论中《山音》作为老人文学备受关注①转引自平山三男.山の音〈川端康成〉——分裂する老い.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89(4):65。,小泽正明也认为“被菊子的美所吸引的同时,层层展开的信吾老去的人生构成了该作品的主题”②转引自金惠妍.『山の音』の研究——老いの問題を中心に.新樹,2000(14)。。而在国内,早期的批评往往着眼于伦理道德层面,认为作者“把公公与儿媳间的爱慕之情写得细腻入微,幸亏作者极力加以抑制,才没有使二人的关系发展到乱伦的地步”(何乃英,1989(Z2):84)。直至近年才有学者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山音》,且提出了不少颇为中肯的见解。有学者认为,作品中“对信吾和菊子超越伦理的爱表达的十分委婉、含蓄,并没有什么出格之处”(谭晶华,1996(6):78),“该作品是作者对苍凉的人生黄昏的临终关怀”(张建华,2002(17):45)。
的确,川端康成创作《山音》时正好五十岁,这是作者的思想及艺术追求发生新的变化的时期,而《山音》则较集中而显明地体现出了这种变化。
本文拟从剖析凝聚于《山音》之中的衰老、重生情结入手阐释作品的老年主题,进而揭示川端面对生老病死这一人生无法回避的自然法则的艺术性沉思及其向倚重闲寂、悲哀的日本传统美学的回归。
二、小说的老年主题:死亡和重生
历时四年半创作出的《山音》与川端康成的其他小说一样,情节并不复杂。小说中主要登场人物包括年逾花甲的尾形信吾,年长他一岁的妻子保子、儿子修一与儿媳菊子,以及虽已出嫁却带着两个外孙女回到娘家的女儿房子。此外还有一个仅存在于信吾美丽幻想中的关键人物——保子的姐姐。
(一)死之痛
作品以尾形信吾意识到衰老和对死亡的恐惧开头:他无论如何想不起前几天刚刚回家的女佣的姓名,“无论怎样回忆,加代的形象还是没有清晰地浮现出来。脑子里如此空荡荡,不免有点焦灼,涌上几分感伤,有时心情反而变得平静。(中略)信吾似乎感到自己的人生已经逐渐消逝”①文中引用的小说译文均出自叶渭渠、唐月梅译《山音》,不再另注。;信吾在家要靠家人提醒、在公司要靠年轻女职员帮助才能恢复记忆。工作四十年,领带的系法早已烂熟于心,某日却突然忘记。信吾的衰老不仅限于日益严重的健忘,他的身体也大不如前,六十岁第一次咯血,登车站石梯觉得腿脚发软。虽然妻子保子显得年轻,但在夜里“当妻子停止打鼾的时候,干脆伸手摸摸她的身体?信吾这么一想,不由心头掠过一阵莫名的哀伤”。当信吾首次意识到死亡时,他蓦地听见了山音,“它很像远处的风声,但有一种地声般深沉的内力”,“声音停息之后,信吾陷入恐惧中。莫非它预示着死期将至?”
接着,朋友的死讯相继传来:乌山在家被妻子虐待而悲惨地死去;北本在战争时失去了工作,因为害怕衰老开始对着镜子一根根拔头上的白发,拔着拔着疯掉了,不久死在精神病院。水田带着年轻女子住进温泉旅馆,在那里猝然长逝……可以说,《山音》中,悔恨之痛、衰老之苦无处不在。这“其间对死亡逼近的预感,描写得比死亡本身更让人感到恐怖。”(吴舜立,2011:47)究其原因,这与川端的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川端两岁丧父,3岁丧母,8岁和12岁时,与他相依为伴的祖母和祖父又相继去世。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自幼形成忧郁、扭曲的性格,加之亲身经历了多年的残酷战争,亲眼见到过太多的死亡与不幸,使他感到生命的孤独和脆弱,也无形中产生出对死亡的悲伤和恐惧。而这一切,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他的创作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作品都与死亡相联系。但从总体上看,在《山音》中,死亡作为作者创作过程中的审美观照对象,凝聚着作者的审美理念和审美兴趣。作者以闲寂乃至超然的审美眼光审视衰老和死亡,以细腻、伤感而又恬淡的笔法描写死亡,从而赋予了衰老和死亡重大的审美意义。
(二)生之美
与死亡相对应的,则是对青青的向往、对性的妄想、对生命活力的崇敬。
作品中有这样的描述:信吾的人生有一处无法弥补的遗憾,他年少时憧憬过一位美丽的女性,在她离世后,信吾迎娶了她的妹妹保子。然而无论是在保子或是他们的女儿房子,甚至在房子带回来的两位外孙女身上,都丝毫找不到保子姐姐美丽的影子。数十年过去,信吾心中的保子姐姐依然青春美丽。作品中的她没有名字,始终以“美貌的姐姐”(美しい姉)出现,对永恒恋人的追忆成为信吾一生的慰藉。
同时,他不仅对儿媳菊子、女儿房子、同事英子等年轻女性观察入微,还一次又一次流连于荒淫的梦境:他触摸到一位年轻女性,但不知道对方是谁(《蝉翼》);他搂抱着一个姑娘,却感觉不出年龄的差距(《海岛之梦》);他看不清女性的模样与身体,唯有一对硕大的乳房高高悬空(《伤后》)。醒来后,他感到那些梦太无聊、太莫名其妙。如此反复多次后,又开始怀疑梦中性的对象是菊子:
“梦中的姑娘不就是菊子的化身吗?就是在梦里,道德也的的确确在起作用。难道不是借助了修一朋友的妹妹作为菊子的替身吗?而且为了隐瞒乱伦关系,也为了掩饰良心的谴责,不是又把替身的妹妹,变成比这姑娘更低下的毫无情趣的女人吗?”
“就算在梦中爱上菊子,不也是很好吗?干嘛连做梦都害怕什么、顾忌什么呢?就算在现实里悄悄爱上菊子,不也是很好吗?信吾试图重新这样思考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信吾与菊子并不曾有过乱伦的行为。儿媳菊子与“美貌的”保子姐姐有几分相似,她在信吾眼中是青春与美丽的化身,菊子唤起了信吾心中埋藏多年的单恋之情。信吾开始构筑一个虚幻的世界,其中只有他自己、保子姐姐及其化身菊子三人,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家庭琐事的烦恼,可以忘记对衰老、死亡的恐惧,肆意享受朝气蓬勃的青春。实际上,信吾对儿媳的想入非非,不过是信吾对早年恋人相思之苦的错位的情感投射,是他人生观由“暗”转“明”的矛盾过程中的产物。
除年轻女性外,全身长满胡须的男子和死去的友人也先后进入过他的梦境。在现实中,信吾从向日葵的花蕊上感觉到了自然大而凝重的力量,认为那仿佛是个巨大的男性象征。他还从黑百合花的味道中嗅出了女性的气息,几乎与慈童的面具接吻。这些,实际上是垂垂老矣时的信吾对性的幻想,是深感力不从心时对青春的眷念和对生命活力的崇敬,而其背后,则是他意识到自己已至日暮黄昏时难以化解的精神沮丧,是在潜意识中对衰老之悲及死亡之惧的排解。
(三)重生
面对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山音》展现的并非一味颓废,而是阅尽风霜雨雪后思想的顿悟和精神的超越。
小说中,当作为保子姐姐化身的菊子渐渐淡化、现实中的菊子日益独立起来时,信吾逐渐远离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山音”的世界,取而代之传来了“天音”。
小说中写到,“春天,鸢稚嫩而甜美的声音,似乎使信吾家的上空变得柔和清澄。”
“连续好几年听见的鸢的鸣声,果真都是同一只鸢发出来的吗?难道它不换代吗?会不会不知不觉间母鸢死去,子鸢悲鸣呢?今天早晨,信吾才第一次这么想。”
鸢的母子更替启发了信吾,生命并非随着自己的死亡而终结。生命将不断繁衍、无限延续。
同时,儿媳菊子的变化对信吾的思想也有不小影响。菊子作为美丽的化身曾出现在信吾的梦境之中,但菊子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当她得知丈夫修一有了外遇之后执意堕胎,而后,菊子逐渐成熟起来,不仅腰身丰盈了许多,还长了个子。此刻,她意识到植物上新生命的迹象:如银杏树发出嫩叶、枇杷树吐出新芽。可以说,从菊子嫁入尾形家起,信吾就能从菊子身上能感受到“生”的力量,而菊子意识的变化也悄然深刻影响着信吾的老年观。
终章《秋鱼》中,信吾对菊子表明“菊子是自由的”,这时,天上传来了声响。“抬头望去,原来是五六只鸽子从庭院上空低低地斜飞过去。”鸽子是自由的象征,“从‘山音'向‘天音’、从‘暗'向‘明’”,信吾生存态度的转变有力地改变了作品主题,这一听觉上的主题变换,坚实地稳住了覆盖在作品表层的信吾对儿媳菊子既危险又微妙的感情”。(今村润子,1988)
小说结尾,是尾形一家七口齐聚一堂享用晚餐。信吾将自己比喻成盘中的香鱼,“香鱼深知死将至,湍湍急流送入海,这后一句仿佛是我的写照。”信吾从最初听到“山音”,惧怕死亡,到将自己比喻成香鱼,不畏迟早到来的“死”。自此,信吾已不再期待时间停滞或回春,反而能从容地接受“衰老”和“死亡”。自此,信吾已彻悟了生命的意义——生命是超越时间的,有死亡便有新生。生与死,是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从惧怕死亡到坦然面对,标志着信吾精神境界的新的升华,而信吾生存态度的转变有力地改变了作品主题。
三、小说的老年美学:轮回转生
有学者曾将川端文学作品中的生命体验和死亡思悟归纳为三个维度:反对死亡、接受死亡、超越死亡(吴舜立,2011:160)。笔者认为,这恰好与信吾的死亡观、老年观升华的三个阶段相一致。
反对死亡。步入花甲之年的信吾,人生尚不满足却察觉到死亡将至,于是表现出对死亡的强烈排斥。出现在作品前半部分的“山音”“衰老”“死亡”皆是悲哀、痛苦而又令人恐惧的。
接受死亡。尽管困扰信吾的家庭问题直至小说结尾也未得到解决,但作为美的化身的菊子渐渐脱离信吾自身构筑的虚幻世界,回到现实中。此刻信吾耳边响起的不再是意味着“死亡”的“山音”,而是象征“永恒”的“天音”,作品的旋律从低沉转向明快。
超越死亡。信吾将老去的自己比喻为为了产卵而竭尽全力游入大海的香鱼,这表明他已化解了死亡的恐惧,主动接近未来无限循环往复的世界。迎接“重生”的死亡是美丽的,是一种“不灭的宇宙精神”。(吴舜立,2011:160)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山音》中,作者对衰老、死亡及由此衍生的悲哀和恐惧的审美观照是辩证的、动态的。信吾的精神世界及思想观念在经过不断变化后最终得到升华,他直线型的、不可逆转的时间概念也通过领悟世代更替从而转化成为循环往复的时间观。这种圆环形时间观被鸟羽徹哉命名为“万物一如轮回转生思想”(羽鸟徹哉,1979),而这种思想与川端的成长密不可分。
川端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遭遇过太多的痛苦和不幸,而佛教气氛浓厚的生长环境又使他自幼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佛教禅宗“生—灭—生”的无常思想甚至成为他排解悲苦和恐惧的精神支撑。而这些,必然会给他的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川端曾直言不讳地谈到:“这种孤儿的悲哀从我的处女作就开始在我的作品中形成了一股隐蔽的暗流”(《独影自命》,1948),“我孑然一身,在世上无依无靠,过着寂寥的生活,有时也嗅到死亡的气息”(《美的存在与发现》,1969)。但是通过佛教的“万物一如轮回转生”,却可以挣脱死亡的恐惧和痛苦。在《初秋山间空想》(1925)中,他明确表示,“总之,我虽然难以把这轮回转生之说理解为打开全宇宙奥秘的唯一钥匙,但我觉得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思想中最美的思想之一。”他相信佛教的“轮回转生”,接受了来世的观念,感觉到这是对死亡的有意识反抗、是对人类内心死亡焦虑的化解,也就是对死亡的超越。
由此可见,《山音》的美不仅体现在用优美、纤细、沉静的文字细腻地刻画大自然或女性,还在于通过灵动的笔法展现出以轮回转生的佛教思想为依托所追求的“无我”的“永恒”的境界。
四、结语
在执笔《山音》的前一年,日本刚刚经历了战败,川端怀着对社会的不安和他一贯的对美的执著开始此部作品的创作。这一年,也可说是年满五十的川端借着在恐惧与矛盾中经历了三个“死亡”阶段而获得重生的信吾这一形象而“步入了重生的第一年”。(《独影自命》,1948)
其实,川端的“重生”,既是思想境界的某种飞跃,也是艺术追求方面的新的突破。
川端康成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在他的创作中,既留下受西方文学潮流影响的印记,又表现出对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的倚重。从《山音》中的梦境描写、下意识幻想等,不难看出他对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倾情,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作品的艺术形象还是浸润于作品之中的审美情趣等方面看,都不难看出作者在回归日本传统审美理念方面的努力。
在发表于1945年11月号《新潮》上的《追悼岛木健作》一文中,川端谈到:“我现在深感自己的生涯尚未‘出发之前'就已经终结了,只有自己一人回到旧日山河中去。我业已死去,此后除日本悲哀的美之外,连一行字也不想写了。”这被认为是川端回归日本古典的宣言。在川端眼里,虚幻的想象和梦境、“无语泪双流”般的幽玄与悲戚、无助无奈下的闲寂……这些经久传续的日本传统审美意趣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川端自少年时起爱读《源氏物语》,他在《我在美丽的日本》(1968)演讲中称赞其为“自古至今,日本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可以说《山音》在思想上继承的是佛教,而文学理念则秉承了《源氏物语》的“物哀”精神,它正是作者在这种特定的审美理念支配下创作出的如此韵味深长的艺术世界。小说中,川端赋予老主人公信吾与自己同样敏锐的感性与观察力,而发生在尾信家的琐事则以信吾的视角逐一展开,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信吾的哀怨、悲愁、恐惧、无奈、潜意识的挣扎以致最终的超然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审美观照下的哀怨之美、闲寂之美也恣意流淌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因而可以说,战后日本文坛虽出现了包括唯美派大师谷崎润一郎荒诞怪异的《疯癫老人日记》(『瘋癲老人日記』1961)在内的不少塑造老年形象的小说,但是,《山音》不仅以其幽玄的美烘托出“老”在生命轮回流转中的独特意义,而它独特的审美意趣更能让读者真正领略到新的艺术洞天。
[1]何乃英.川端康成[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39.
[2]何乃英.川端康成美学思想特点探索[J]外国语言文学,1989(Z2):84.
[3]谭晶华.典型的中间小说——论川端康成《山之声》的创作[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6):78.
[4]张建华.山音主题的二十一世纪阐释[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17):45.
[5]川端康成.美的存在与发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川端康成.山音[M]叶渭渠、唐月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吴舜立.川端康成文学的自然审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8]川端康成.独影自命[M]叶渭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6.
[9]金惠妍.『山の音』の研究——老いの問題を中心に[J].新樹,2000(14).
[10]村松定孝.『山の音』と〈老い〉『風韻の相剋』[M].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79.
[11]今村潤子.川端康成研究[M].東京:審美社、1988.
[12]羽鳥徹哉.作者川端の基底[M].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79.
[13]李徳純.前書き[A].国文学解釈と鑑賞[C].1989(4):9.
[14]羽鳥徹哉.川端康成その魂の軌跡[J].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97(4):26.
[15]川端康成.後書き[Z].川端康成全集第33巻[C].東京:新潮社.1982.
[16]李鹏飞.论川端康成小说创作的“东方意识流手法”[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1(2):103.
[17]靳明全.日本近代文论主流历史扫描[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8]刘静.论日本普罗文学运动[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