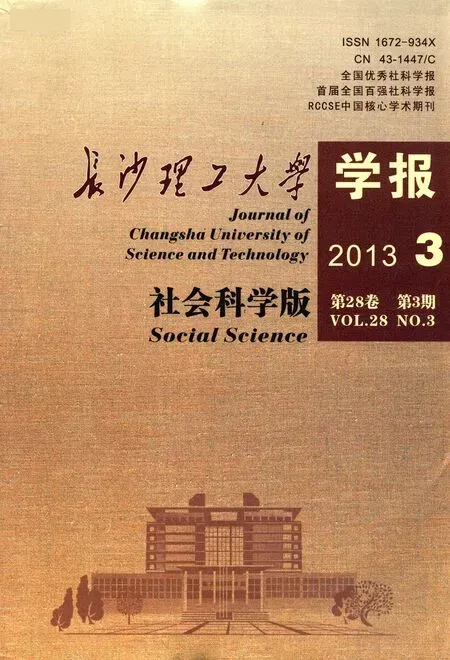中国近代以来的“技术强国”话语变迁及其统摄
2013-03-31李三虎
李三虎
(广州行政学院,广东广州 510070)
中国近代以来的“技术强国”话语变迁及其统摄
李三虎
(广州行政学院,广东广州 510070)
目前“自主创新”已成为理解中国技术发展方式的核心话语,但这一话语毕竟有其历史渊源。这种历史渊源的逻辑线路是近代以来的技术强国话语变迁:一是在殖民主义压力下经过从“道器合一”到“道器分离”再到“道器合一”的话语转换,中国最终以“器”的话语形式接纳西方现代技术并确立了技术强国理念,进入现代主义话语体系;二是中国现代主义话语经过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到技术精英治国论,将技术强国理念逐一贯穿到国防、经济、文化乃至政治过程;三是随着技术强国话语的确立和完善,中国传统主义一直被称为保守派、顽固派或玄学派,其基本诉求在于技术强国必须要适应本土生产方式或再创造;四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适应性转换,不仅在于它的中国传统因素参照,而且也在于它将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结合起来,对技术强国理念进行了创造性话语统摄。沿着这种话语变迁线路,中国技术强国理念在共和国建立后经过革命话语、改革话语和发展话语之后,逐步变成了今天的“自主创新”表达或修辞。
技术强国;道器合一;现代主义;传统主义;马克思主义
目前中国正以“自主创新”之名,按照自身的民族复兴逻辑追求独立的技术强国路线。为了思考这种追求,必须要考虑世界技术的空间发展历史。相对于西欧工业革命来说,整个世界显然存在着某种时空差异:一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均有着自身的古代技术发展路线,它们在世界文明交流中为西欧现代技术发展提供了知识资源;二是西欧现代技术兴起和发展,又反过来吸引或深刻影响着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就第一历史阶段来说,人们围绕“李约瑟难题”(即近代工业革命何以没有在中国产生)对中国技术文明做了广泛的科技史学研究。就第二历史阶段来说,人们热衷于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西方技术成就及其应用颂扬。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从技术哲学思想史角度,把握从第一、二阶段进入到目前自主创新阶段的历史进程。本文为此主要考察中国近代以来技术强国理念变迁及其统摄过程,以表明当前自主创新话语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背景。
一、殖民主义压力下的技术话语转换
1498年之前,中国与欧洲文明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地理上的空间隔绝,所谓“技术渗透”的文明交往非常缓慢。即使从1498年伽马开辟至印度海路直到1800年,中西关系仍被置于亚洲国家自身确立的框架内加以处理。在中国传统中,基本上是只有“王朝”和“天下”,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概念。只有在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面临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压力,才被迫卷入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体系,“民族-国家”意识由此不断被强化。就中国古代思想和技术文明受到以机械论为其形而上学基础的自然科学挑战来说,西方自然科学传入本身是一种殖民化行为。但从自17世纪开始的中国与西方科学的最初接触来看,这种殖民化并不明显,因为最初传播的有关“上天”(天文学)的知识(包括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天文学理论)可以弥补中国原有知识的不足。那时中国人既不是对技术强国理念的深刻理解,也就用不着考虑技术殖民主义会削弱传统信条甚至民族风格。但在1839 -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殖民者正是依靠作为现代技术产物的“船坚利炮”打开了天朝大门。鸦片战争直接输入了现代兵械、炮火、分割技术等,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天道”、“神器”不再属于清王朝。在这种文明张力中,清政府为了改变来自西方的威胁,开始了掀起一场“技术强国”运动,并通过洋务运动表现出来。这虽然并未能挽救清政府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由此进入技术话语转换中,并逐步确立起了“技术强国”理念。
第一,“中道-西器”模式:从“不藉外夷货物”到“师夷长技”。在鸦片战争前,大清帝国的君臣们认为天朝的一切应为“夷”所“师”,绝对不允许“用夷变夏”。但在鸦片战争中,英国洋枪洋炮沉重地打击了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在这种劣势状态下,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这一命题意味着从“不藉外夷货物”到“师夷长技”的技术话语基调转换,后来成了洋务派的基本句式,即使是“借法自强”也不过是魏源政策主张的另外一种表达而已。正如王善博指出,“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框架除了‘器’之外很难容纳下其他东西”,[1](P78)中国人只有把“机械”解释为可接受的“器”之后,才能接纳西方现代技术。魏源对西方现代技术采取一种工具论态度,但他毕竟不能完全离开中国传统语境。他为此采取三个步骤处理这种语境转换:一是将西方现代技术解释为“奇器”或“奇技”,以“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实现一种语义转换,因为现代“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2](P18-19)二是将“器”与“道”分离,使西方现代技术与中国传统技艺同等地变成中立于价值或“道”的手段;三是坚持“天不变,道也不变”原则,将对“天道”的关怀落实为“治事”或“治器”(学习引进技术),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2](叙)的手段-目的互利中,维持中国传统政制和儒家伦理之“天道”。魏源这种话语转换其实是一种“中道-西器”模式,认为西艺、西器和西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仅仅在于它们是有用的“术”或“器”(或手段)而不是“道”,与“天道”无涉。也就是说,学习西方现代技术不过是服务于重振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道的历史任务。魏源从“以中土人谭西洋”转向“以西人谈西事”是改变中国传统技术思维的重要创新,走出这一步显然是在外来殖民力量下进行的,以“手段-目的”二分为原则,立足中西“手段差距”或“技术鸿沟”,实现了从中国前现代技艺向西方现代技术看齐的话语转换。
第二,“中体-西用”模式:从“师夷长技”到“自造自强”。魏源的“中道-西器”思想及其政策主张,在鸦片战争后20多年中并未受到特别重视。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才在引进西方现代技术过程中对魏源思想给予不断丰富和发展。左宗棠作为魏源的思想追随者,在创办福建船政局之初曾设想出一套从“师夷长技”到“自造自强”的技术强国方案,试图以自造改变“以彼之长傲我之短,以彼之有傲我之无”的殖民与被殖民情形,进而达到“突过西人”或“驾而上之”目标。为了论证这一方案,左宗棠虽然与魏源一样保留了传统政制和伦理价值,但不再如魏源那样为传统技艺留有一席之地,而是面对传统主义(一般被称为“保守派”甚至“顽固派”)的“失体论”(即认为现代技术将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秩序),以“本末论”讨论学习、引进和超越西方现代技术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但中国在现代技术方面落人之后毕竟是事实,因此“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3](卷18)他在这里强调讲义理者也应成为执艺事者,此即“本末兼顾”或“明体达用”。这种“明体达用”思想在冯桂芬那里更为明确:“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4](P39)此后洋务派思想家于19世纪70-80年代从不同角度表述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张之洞提出“旧学力体,新学力用”,强调“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认为“正人心”是要通过“中学”或“旧学”明确“所当守”,这是自强的目的所在,“开风气”则是要通过“西学”或“新学”解决“如何守”。[5](设学第三)这实际上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其理论前提是“中不如西,学西可也”。这一模式的政治策略在于悬置中国传统文化,抛弃中国传统技艺和器物,转向全面接纳包括军工和民用在内的西方现代技术。
第三,“器体-道用”模式:从“自造自强”到“变法图强”。“中道-西器”与“中体-西用”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其不变者道而己”,矛盾在于:一是尽管可以认为引进西方现代技术为中国道统服务,但西方现代技术引进毕竟会对传统体制产生冲击;二是如果中国道统不能适应西方现代生产方式变化,就需要按照道与技艺相通的整体逻辑变革道统。这种“道器关系”的变革逻辑,直到戊戌变法时期才成为解构道统的重要方向。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的机械化力量显示出其对中国的绝对优势。面对西方现代技术的普遍化压力,中国人要在保留传统政制条件下“自造自强”的独创性道路自然成为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现代技术取得巨大成效。鉴于日本经验,中国开始从学习欧美“转而相师”日本热潮。在这种背景下,严复对“中体-西用”模式进行批判:“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列,合之则两亡。”[6](P558)严复以“牛体马用”这一隐语说明西方现代技术无法与其政制和文化价值相分离,中国传统政制和儒家价值必定会阻碍西方现代技术引入和机械论哲学传播。这种批判思路表明,必须要将“中体-西用”模式包含的“道体-器用”颠倒为“器体-道用”,以便适合维新派的变法图强思想。谭嗣同根据王夫之的道器理论证明“道器相为一也”:“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7](P390)这既表明了道器同一,又把魏源以来的“道体-器用”颠倒为“器体-道用”。不过这时不仅“器”已经变为西方现代技术,而且“道”也变成与西方现代技术相一致的“道”,因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7]391这种“器体-道用”模式表明了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派的核心变法思想,它不仅表现为变革中国前现代技艺而转求西方现代技术,而且还要变中国传统技艺之“道”为西方现代技术之“道”。正是在这种话语转换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援西入中”、“以西释中”或“化西为中”一时间成为中国思想界热潮,从而逐步使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现代主义。
二、现代主义话语的技术性操作逻辑
中国现代主义式的技术强国理念得以确立起来,它的实践逻辑是:以竞争态势进入由技术、商业和军事霸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复制资本主义的技术、资本和军事扩张的现代化途径,以便最终使中国在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中确立自身的主权地位。在技术强国的意识形态支配之下,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型“科学话语系统”建立起来,并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术语不断建构着保守/创新、传统/现代、中国(东方)/西方、落后/进步等世界时空秩序。这种科学话语系统作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社会理想和历史建构的理论框架,其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无疑是将科学知识谱系看作世界秩序变革的基本要素,而将其对世界改造具有现实作用的现代技术创新置于科学知识的应用层面。但必须要指出,科学话语系统包含的世界秩序是以现代技术的去背景化操作力量或意志来构建。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主义思想的历史进程在于,先有技术强国理念,后有科学话语系统。在这种意义上讲,技术强国作为民族-国家主权秩序建构的力量或意志,应被看作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各种现代社会思潮产生的中心路线。因此与其说中国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是通过科学话语系统构建当时中国社会和国家的理想秩序,毋宁说是技术强国理念通过科学话语系统获得了意识形态强化。
第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技术变革的进化理论表达。西方进化论思想迎合了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不仅为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接受,而且也为孙中山、章太炎、严复等革命派所抱持。孙中山用“太极”代替西方哲学的“以太”概念,认为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展示了“太极-电子-元素-物质-地球-人-人性”的世界单向进化过程。他用进化论思想解释人类社会,说明了“神权-君权-民权”的世界政治发展趋势。这意味着中国为顺应这一世界潮流,必须要实现从变“器”到变“道”的技术-政治转换,此即民主共和的政治革命诉求。但只有严复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为这种技术-政治转换提出了最为完整的现代化方案。严复曾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和斯密的《原富》等著作,其目的就是要告诫人们人类社会包含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中国人必须要自强图存。在自强意义上,严复作为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仍然保留着劝慰的传统文化风格,但问题在于这种劝慰一旦诉诸对西方现代技术何以如此发达的解释,就要转向对科学主义的主题叙事:“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两者自呈。”[7](P1248)他从强调科学之用,转向科学公理、科学方法及其程式,以便打破宋代以来的程、朱、陆、王理学思维方法束缚。严复对实验和逻辑方法推崇备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便成为一种激进的文化与政治革命话语,其比较逻辑在于:西方现代技术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乃是因为科学公理或自然规律揭示用于人类社会秩序建构。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诉诸革命去革除那些不符合与支配现代科学(技术)的自然法则相一致的西方社会公理的一切政制和价值,然后通过发展技术、经济和军事能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并不是历史延续的自然进化结果,而应是按照去背景化的技术操作秩序进行平等地物竞天择的现代化创制。
第二,科学主义:技术去背景化操作的科学话语。20世纪以来,鉴于从基础科学到技术应用的单向度关系,当时中国思想界逐步将科学推上了偶像的高台。郭颖颐将这称为“唯科学主义”或“科学主义”,包括“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科学主义”。[8](章1)所谓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科学话语,还不如说它更接近于西方资本主义技术的去背景化操作思想。吴稚晖作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的最好典型,最初是以其“无政府”概念表现其观点:人人“自范于真理公道”而无“治人与被治者”。1907-1908年期间,他一直致力于倡导“促新理新机之发明,造成世人之幸福,使世界进化者也”,要求整个中国抛弃传统文化,以完善科学工业知识,取得“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1916-1918年期间,他通过人工造物效用讨论,推出了通过机器取得“大同”的乐观主义观点:“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劳动,都归机器。”[9](号2)吴稚晖以牛顿力学为基础,坚信宇宙的机械本质,根据物质性假定和机械性预先假设,认为人与现代科学呈现出来的自然物并无不同,因此人类社会可以作为对象被纳入科学研究范围。与吴稚晖相似,陈独秀将科学或民主与进步力量相等同,必须要以西方民主与科学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以使技术发展能够在富国强兵中发挥有效作用。这一文化变革主张面对的一项重要政治事件在于:1914年2月8日,袁世凯发布了尊孔的总统文告。这一文告的意义并不在于关心儒家作为经典还是作为宗教加以信仰,而在于它代表了君主专制力量,因此实际上成了包括陈独秀、胡适等现代主义思想家发动新文化和新思想运动的重要政治线索,其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以技术的去背景化思想消解传统文化,同时突出技术强国理念的科学话语权力。
第三,技术精英治国论:技术强国理念的政治形态化。近代以来的技术强国理念,已经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话语系统,使复制资本主义技术的去背景化操作成为一种合理化意识形态:一是技术要素从特定情境中抽取出来,以科学话语形式得到广泛认同;二是将自然和社会作为改造对象简化为实用功能,以目的和结果形式得到激进和非激进赞扬。这种合理性意识形态进入中国当时现实中,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形式上以广泛实用性和高度有效性赋予科学话语体系和专业技能以自主的合法性,而且也使以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主的技术精英群体拥有在实践上推动世界技术化的“威权”地位。这种实践最初表现为科技术语审定、语言技术化,后逐步转向政治体制,从而导致1930年代的技术精英治国论盛行性。罗隆基发表的“专家政治”一文成为中国技术精英治国论宣言,提出“20世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10](号2)一是工业革命带来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工业、交通和运输迅速发展,人口向工业地区集中,垄断兴起,这些问题使行政范围和职能扩大,因此正如铁路、电报、汽车、飞机和采矿等行业需要按照科技知识进行专业管理一样,在政治上无论采取何种意识形态,行政均需进入专门领域,以专门行政知识实行专家治理,否则再好的意识形态也只是空谈;二是专家治理的最佳途径是“专家知识的吏治制度”,如聘任考试制和任期制、分级及订薪制和官吏违法舞弊法、退职养老制和吏治职业化等。这种技术精英治国论观点,受到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广泛支持。胡适转向技术精英治国论观点并非来自经验,而是来自其理论逻辑:一是以科学主义支持自由民主的广泛内在价值时,其明显的意识形态指向是技术精英的自由主义;二是从科学主义转向技术精英治国论时,受杜威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原则支配,依靠技术的“效能”维护技术精英治国意义的独裁制度,从而宁愿放弃一般民主政治价值体认。中国技术精英治国论虽然仅仅局限于行政过程的科学化或技术化实现,但它在思想上毕竟与自由主义逻辑不相符合,因为前者要求确立高效的国家或政府威权地位,后者的基本诉求则是民主化。这种思想困境与其说是中国移植西方自由主义产生的“自由-专制”、“民主-独裁”、“主义-时事”或“自由民主-民族富强”之争,不如说是中国现代主义思想发展中从科学主义到技术精英治国论面对当时抗日战争的现实矛盾反映。
三、传统主义的技术批判与文化建构
从技术强国理念的意识形态强化过程看,几乎均是基于西方科学话语系统的技术原则。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已经逐步转向这一原则的话,那么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到技术精英治国论,一路下来不过是要将这一原则复制到文化、政治、社会和生活等各个领域变革中。这种复制对传统文化秩序无疑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因此随着技术强国理念及其科学话语完善,也遭到传统主义对抗。这种对抗在晚清时期表现为坚执传统政制(人们至今还笼统地称此为“顽固派”或“保守派”),辛亥革命后逐步表现为退守社会生活方面的传统文化秩序(今天人们称之为“现代新儒家”)。传统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对西方现代技术给予了思想批判,同时又鉴于技术强国这一意识形态要求力图从传统道德话语对现代技术给予建构性阐释,由此来维护中华传统文化。
第一,西方现代技术的文化批判。资本主义诞生后,现代主义以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天文学或科学革命表明的“空间同构”为基础,确立起了通过理性使历史逐渐克服野蛮的时间之矢。但西方思想家们却从二次世界大战中看到理性的异化,看到世俗化的科技文明不过是颠覆社会和道德的理智发现和发明。这种思想变化也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获得反映。梁启超作为维新派思想家,在1898-1912年期间曾强烈主张接受西方科学和文化,但他后来赴欧洲考察,于一战结束后回国便转向了对现代主义的思想批判。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对机械论哲学及其“破坏性创造”进行了批判,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与梁启超相似,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指出中西文化差异从根本上说是作为生活动力的“精神”或“意欲”差异,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折中”。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是一种现代技术文化隐喻,它包含两种倾向:一是对外在世界的理性计算导致科学发展;二是个人私利、权利的倾力追逐导致民主扩展。梁漱溟认为这两种倾向均源自“理智”运用,这种理智一方面发展了改造自然的技术方式,增加了知识和财富,另一方面也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因为它“常常分一个目的、手段”,“若处处持这种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这样“彻底的理智把直觉、情趣斩杀得干干净净”。[11](P133-134)按照这一看法,现在是西方文化占据主流的时代,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主流的时代。
接受梁启超和梁漱溟的现代主义思想批判,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讲演,说明了中西文明传统的差异在于,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内心生活之修养”的“精神文明”,而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以人力支配自然”的“物质文明”。正是由此引起了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主义支持者的强烈反应,也吸引了陈独秀、胡适、吴稚晖、任鸿隽和唐钺等人的广泛参与。丁文江对张君劢把物质文明与科学等同起来表示不能认同,认为物质文明是科学的结果而非科学的原因,西方因战争引起的物质文明危机不能归咎于科学。这场“科玄”论战的焦点问题及其意识形态意义在于:一是西方现代技术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就是表明中国落后于西方,从而在心理层面产生了一种以精神前提评判中西文明模式标准,因为人们意识到枪炮和机器制造只是一种具有开拓精神的文明的副产品而已;二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当将中国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哲学思考时,体用范畴的传统理论已经逐渐被抛弃,中国整个思想领域甚至大众舆论倾向于吸纳西方科学话语系统,坚持科学方法万能的一派总是被认为拥有人生和宇宙的钥匙,而坚持传统文化秩序的传统主义一派则总是被认为玄学家而不受欢迎;三是科学主义派针对传统主义派所提出的技术后果往往采用工具论将科学与其负面影响分离开来,将其负面后果归于应用而保留科学的纯洁,传统主义派则一般不排斥科学,但在技术负荷价值意义上对机械论哲学给予批判,并试图以传统文化秩序给予批判和矫正。在这种意义上,传统主义不得不从技术批判转向对技术创制的本土文化解释,即在中国文化意义上对西方现代技术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合理性论证。
第二,现代技术的传统文化建构。梁漱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传统文化秩序的西化浪潮中,重又举起儒家思想大旗,力图在不完全拒绝现代科学的情况下复兴一种“孔颜乐处”的人生态度。他认为,“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取收溶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种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11](P214)与梁漱溟坚持“新心学”(或“新陆王”)把中西文化看作一种“路向”的个性差异不同,冯友兰从“新理学”(称“新程朱”)体系出发推演出中西文化的共性差异。在他看来,文化的
“理”是公共的,是各个民族或国家都有的“共相”,但具体到每个国家又表现为不同形态,即“殊相”。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均包含共同的“理世界”(如功利境界),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而已:中国文化是“生产家庭化底文化”,西方文化是“生产社会化文化”。这里一个严肃文化问题在于:如果不能避免学习西方生产社会化文化,那么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或殊相。中国文化的出路是吸取西方文化共相(工业化)而舍弃其偶然性(如私有的功利),然后将西方文化的工业化属性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如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结合起来,以避免全盘西化与全盘孔化的文化困境。冯友兰强调超越中西实际世界之上存在的基本道德是不变的“客观”或“理”,即中国传统的“五常”(仁义礼智信)、“至善”或“良知”。他指出“我们的良知,遇见事物自然而然知其至当处置之办法,我们只须顺我们的良知而行”,“所谓至当或‘天然之中’本是本然的有,不过我们良知能知之”,而“良知即我们知之智者,我们的知愈良,即我们的知愈智”。[12](P187,193)他将“仁”(良知)解释为“智”,以“理”的客观性取代“心”的主观性,借不变的、公共的、超越的“理”和“理世界”应对变化的、流动的、生动的实际世界,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以及社会变迁等。这种主张虽然与梁漱溟不同,但他以“理”论证知识、技术、工业、制度、道德、规范、标准等一切现实的合理性,赋予梁漱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命题以深刻的哲学解释。与梁漱溟和冯友兰相比,熊十力更加明确地对科学与哲学做了区分,以避免科学主义一派将“从实用出发”、“以实测为本”、“从各部分区探究”的科学方法变成哲学上的科学认识论和机械论,从而追求与理智认识(“量智”)相反的非理智认识所能达到的本体境界(“性智”)。他以“体用不二”方法表明,现象是本体的“功用”,“功用”是永恒变动、生生不息和“流行”不已,而本体就是“流行”。熊十力喜欢以“翕辟成变”为隐喻,说明本体以凝聚(翕)与开发(辟)两种动力势能处于永恒运动之中。他指出“惟有凝摄之一方面所谓翕势,乃使健以开发之辟势,有所依据、集中,以显其胜用”。[13](P67)这种“翕辟成变”既适合解释自然世界运动,也可用于说明人工世界。他指出“翕势方起,即有辟势与之俱起,健以开发乎沉坠之物,转翕而不为翕转,是故就辟之一方面而言,终未尝物化”。[13](P145)这就是说,当现代技术展现其强大力量时,必须要以“内圣”的道德价值防止“外王”的“有体无用”情形。
在以上三位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以西方机械论的理智和算账意识批判,来衬托儒家文化的“孔颜乐处”。与此不同,冯友兰无疑赋予西方现代技术(大机器)和机械论(功利意识)以合理性,以便成就“极高明而道中庸”。但冯友兰在追求“天地境界”方面,即以“内圣”之道作为根本,应对西方文化和哲学挑战,不仅与梁漱溟相同,而且与熊十力也完全一致。熊十力坚持以“体用不二”方法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以应对西方哲学(包括机械论)挑战。也就是说,可以从儒家文化中通过“内圣”开出“外王”,如科技和民主等,其意义在于将西方现代技术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借助技术强国途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秩序。
四、马克思主义的适应性表达与统摄
无论如何,当一个民族或国家普遍地认为自身技术能力低于别国时,就是对自身文化形象的一种贬抑。自鸦片战争之后,不管是现代主义还是传统主义,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多持这样一种思想假设: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意味着西方文明本身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正如阿尔法雷斯(Alvares)指出:“至迟到1949年,西方技术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它向中国人表明中国自身的落后;它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划下一道深深的伤痕:中国锐气已被‘挫败’。”[14](P186)西方现代技术的这种意识形态功能,显然伴随着当时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复杂的意识形态选择。这种选择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在不完全拒绝复制资本主义的去背景化技术操作逻辑基础上能否维护中华民族传统。以下讨论将表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有效传播,正在于其共产主义的技术价值预想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技术强国理念之间的思想同构,从而成为中国以后的意识形态方向。
第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参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的技术价值设想为使用价值享用,而非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增殖形成。这一预想无疑从古代社会传统获得启示。但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古代社会传统是否包含中国传统?在马克思那里,中国与印度一样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生产方式基础,但中国有着不同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15](P604)中国这种传统生产方式表现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能够给予资本主义大工业产品以最顽强抵抗。马克思曾高度赞扬古代人把技术看作对劳动和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改善,且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使用机器是把工人全部时间变成资本价值增殖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工具。这样亚细亚的农村公社和土地公有制,便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城邦社会和行会制度,一起成为马克思以使用价值及其享用设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参照视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技术预想渗透传统因素,绝不是对传统的简单重复,以传统道德因素对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强调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创造。马克思作为道德家和历史哲学家,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技术发展(包括机器系统和工业革命),意在表明人类技术实践和物质现实的辩证过程必然要从抽象的、单向度的生存状态发展到多向度的、具体的、丰富多彩的生存状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技术预想中,原始公社或道德共同体的传统道德因素是作为对现实的批判,同时融入新的社会理想中而发挥重要的思想建构作用。
第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转换。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给予论述,只是赋予太平天国革命以“Republique chinoise——Liberte,Egalite,Fraternite”(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之名,不过是预告了以后的“中华民国”诞生。但这与其说是“只看到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前景”,[16](P148)毋宁说是预测到中国社会主义必经的资本主义逻辑复制阶段。在这种意义上,康有为可以说是最早萌发“社会主义”理念的中国本土思想家。很难说康有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早年留学国外,归来后早于俄国十月革命,站在时代高度使用国学语言提出了诸如“去财产界限”、“大同世界”等概念,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谋而合。1920年代以后,康有为有关大同理想的社会具体化策略(实即“立宪制”或“共和制”),不仅在科学主义那里成为赞成社会主义的技术精英治国理念,而且在传统主义那里演变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技术设计”。在“科玄”论战之前,杨铨曾提出一种康有为式的科学大同叙事模式——“科学=平等=和平=大同”,当时无疑属于科学主义范畴。但与其他科学主义者的不同在于,他认为科学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信仰或道德观念。这构成了“科学=大同”的思想困境,从而使传统主义者张君劢诉诸传统文化资源进入社会主义的“技术设计”或“文明规划”。他把“人的理智自主性”看作“现代的真正动力”,而自主理智来自中国传统人心或思想的技术合理化。他依靠这种技术合理化论证方式,把中国文化作为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技术设计方案。这里一个基本逻辑是,如果资本主义及其技术逻辑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特征,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那么包含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他者”便倾向于社会主义。张君劢虽然在政治选择上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坚信“社会主义”需要“文化”资源,“文化”在资本主义情境中必须以“社会主义”为目的。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能够克服因“公道”为本产生的效率低下效应,因此会成为一种解决现代文明危机的“技术”或方法,成为一种自我创造活动,成为“国人之努力”和“国人之创造”的传统资源。[17](P86)有趣的是,丁文江作为张君劢的论敌,依着社会达尔文主义逐步进入这样一种逻辑:如果在技术强国方面无需诉诸中国传统,那也不一定非要复制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作为备选道路。丁文江本来一直主张“科学=自由=民主”这一等式,但他在1930年代救亡图存历史条件下转向技术精英治国论时,部分地参照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于1933年夏去俄国以前曾认为“自由是养活科学最重要的空气”,对苏联缺乏自由会阻碍科学发展表示担心,但到了那里看到其“地质探矿联合局”比中国地质调查所用经费多100倍,科学并未因自由丧失而受阻。他回国以后便开始赞同社会主义,从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转向技术精英治国论的救国方案。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的创造性融合。无论是传统主义还是科学主义,在思想上均基于技术强国的政治逻辑,部分地出现了社会主义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形成于国家救亡的现实主题,它一方面来自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国家政治参照,一方面来自适应时代要求的传统自我转换。李大钊作为最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便从两个方面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色:一是为避免或跳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最早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阶级希望放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二是强调社会主义的协和、友谊、互助和博爱以及尊重劳动等伦理道德特征,作为“阶级斗争”的社会文化补充,具有道德主义倾向。与这一思想一致,梁漱溟作为传统主义者倡导“地方自治”和“乡村自治”,其宏大目标是建立一种新型中国文化和社会,使中国既受惠于现代科技成果,又在中国传统智慧和组织框架中避免西方之恶。这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相互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要求提供了文化启示。毛泽东与梁漱溟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就中国农村和智力改进问题将中国道德倾向同政治、经济和军事成功结合在一起,把美好社会实现系于连续的社会精神改造。但他们的不同在于,对梁漱溟来说牺牲本身是目的而非手段,对毛泽东来说道德上的自我牺牲是为了民族或国家。在传统意义上,这可以说是“道体”的象征性表达,但作为手段的“体用”又必定是为了集体生存。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将中国革命融于传统生产方式和现代技术的紧密结合中,也试图将技术强国理念贯穿于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目标设想中。在战争压力下,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分科原则上模仿了苏联技术体制,但从一开始就将技术问题与边区小农生产方式结合起来推动以“半自给”为导向的技术政策,其目标是促进边区生产和保障度过难关。当然,毛泽东针对社会主义未来,并不限于小农生产方式,而是追求小农生产方式的高级化发展。毛泽东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将“物质生产过程”、“阶级斗争过程”和“科学实践过程”看作社会实践三个组成部分,1940年强调“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1944年开始,毛泽东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理论,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是“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8](P237,239)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P1081)1949年3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里从“农业国”到“工业国”(或说工业化)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包含了从“手工”到“机器”的技术变革逻辑,其整个政治陈述不过是将技术强国理念转换为革命话语。但问题在于,这种革命话语在以后发展中完全超越“农业国”的国情和条件,因此经历了有关技术与政治的各种意识形态纠葛和曲折。即使是在今天,技术强国理念自近代以来,从参照英国、日本到参照美国、前苏联再到参照欧美,经历革命话语、改革话语、发展话语之后,最终以“自主创新”获得最新表达。但如果考虑到国际智力鸿沟的全球背景以及国内脑体分工的本土背景和其他各种因素,“自主创新”作为中华文明复兴的技术强国策略仍需经历很长的历史。我们既不能因强调自主创新的“独立创造”而忘记向别国学习最前沿科技成果,也不能因强调学习而丧失本土创造的民族-国家意识。
[1]王善博.追求科学精神——中西科学比较与融通的哲学透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2]魏源.海国图志(卷2)[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张之洞.劝学篇(外篇)[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6]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上海:三联书店,1954.
[8]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9]吴稚晖.机器促进大同说[J].新青年,1918(5).
[10]罗隆基.专家政治[J].新月,1929(2).
[1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
[12]冯友兰.新事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1937.
[13]熊十力.新唯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4]Alvares,Claude.Decolonizing History: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India,China and the West 1492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The Apex Press,and Goa:the Other India Bookstore,1991(1970/1980).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6]徐长福.马克思与康有为对中国社会进程的预见[J].河北学刊,2008(6).
[17]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人生观之论战(郭梦良编)[M].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
[18]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刘范弟]
The Vicissitudes of Discourse and Dominion of"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echnology"in Modern China
LI San-hu
(Guangzhou Administration 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 510070,China)
At present,"independent innovation"has become the core discours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of Chinese technology.However,such discourse has its historical origin,the logical route of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discours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echnology.First,under the pressure of colonialism,China has undergone the vicissitudes of discourse from"unity of theory and technology"to"separation of theory and technology"and then to"unity of theory and technology".Ultimately,China has accepted the modern technology of western countries by means of"technology"and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echnology",consequently stepping into modernism discourse system.Second,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modernism has witnessed conceptual evolutions through Social Darwinism,scientism,the technical elite governance theory,which,one by one,has infused the idea to strengthen the country through technology in the areas of national defense,economy,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Third,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ncerning discourse,Chinese traditionalism is always referred to as the conservatives,the diehards,and the metaphysical school.It appeals basically that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echnology must adapt to local production mode or recreation.Fourth,the flexible swift of the Classic Marxism’s discourse not only lies in its referenc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elements,but its combining the Modernism with Traditionalism,with the dominion of creative discourse in the concept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echnology.Along the route of the vicissitudes of discourse,the idea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echnology gradually became today’s expression or rhetoric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reformatory discourse and developmental discourse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echnology;logos and utensils;modernism;traditionalism;Marxism
N031
A
1672-934X(2013)03-0010-08
2013-03-26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研究”(11JZD007)子课题“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与现状”。
李三虎(1964-),男,山西长治人,哲学博士,广州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主任、教授,《探求》杂志主编,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