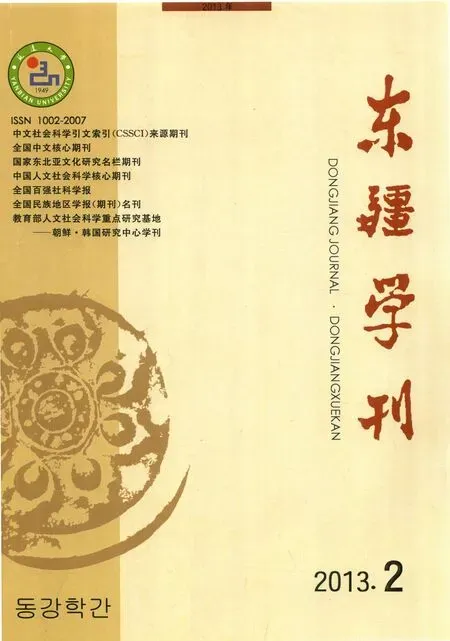试论南非合同法之“效力障碍”问题
2013-03-27杨蓉
杨 蓉
2012年 7月 30日,习近平同志在第二届中非民间论坛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则是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2011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背景下,中非贸易额仍创下 1663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147亿美元,中国在非洲落户的投资企业已超过2000家。这些中国企业,不仅为非洲人民创造了就业岗位,而且积极开展回馈当地社会、造福当地民众的各种公益活动”①习近平:《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发展——在第二届中非民间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2012年 9月 20日查阅于http://www.focac.org/chn/zt/dwjbzh2012/t956679.htm。。可以说,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更加凸显了我国对非洲国家法律制度研究的必要性。众所周知,国际法中有关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规定,仅仅是一个宏观层次的双边或者多边经贸及投资保障的框架,现实中的多国家投资及经贸合作所面临的困难早已突破了国际法上“对外国投资进行保护”的原则,细化到经贸及投资双方对契约上权利、义务的理解和争议、不当行政管理等等多个微观领域之内。
可以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如何促进中国同非洲国家经贸及投资的顺利进行”这一重大实践性命题,除了需要研究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法中的有关规则,学界更需深入到我国和非洲国家的国内法,尤其是以民商事法律为代表的国内私法的认识和研究中去,为中非经贸合作的顺利进行提供理论支持和保障。其中,南非作为非洲大陆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其法律制度在非洲大陆上极具影响力。因此,以南非为非洲法律制度研究的起点,有助于我们“以小见大”、迅速了解非洲国家法律的特征。本文主要从南非合同法有关合同效力的规范研究出发,期望能有助于中非经济贸易的发展。
一、“混合法域”传统下的南非合同法“效力障碍”问题
“混合法域”理论是随着比较法学的发展而出现的,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混合法域体系是指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法律传统或法系成分构成的法律体系;狭义的混合法域,则专指由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混合构成的法律体系。从法律特色来看,非洲国家(南非、津巴布韦、博茨瓦纳、斯威士兰等)多为混合法域,其中以南非最为典型。南非合同法的“混合法域”传统与其被殖民的历史密不可分,其所具有“罗马—荷兰法”的特征,即以罗马法为基础,在 17、18世纪荷兰形成的一种法律传统。虽然在19世纪早期,这种法律传统就已经在荷兰逐渐消亡了,但由于历史原因,使其仍活跃在南非、斯威士兰等非洲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南非合同法就是罗马—荷兰法有关合同规范的现代范本。因此,南非合同法认为,合同是两者或者两者以上当事人为实现特定意图而创制特定法律约束的一种协议。南非合同法的基本功能,即提供法律框架以服务当事人之间进行经贸交易、资源互换的社会活动。在南非,合同一般分为三大类。一类为存在强制性义务的义务合约;一类为权利可让与的让与合约;第三类则与前面两种不同,称为免责合约,即合同责任可以被免除或者被消除的情形。无论是哪一类合同,在南非来说,合同必须符合如下特征,才具有合法有效的拘束力:第一,合同当事人之间必须达成合意;第二,当事人必须具备订约能力;第三,必须具备必要的合同形式;第四,合意必须合法;第五,合同义务具有履行的可能性;第六,合意必须明确。因此,南非合同法就合同特征的规定与我国合同法相差无几。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在南非,原来的罗马—荷兰法两层蛋糕已经加进了第三层——英国法”。[1](9)时至今日,南非的合同法仍然以罗马—荷兰法的原则为基础,但也加入了英国法律处理合同问题所形成的立法和判例方面的内容。
所谓合同效力障碍,指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不能达成。从本质上看,合同效力障碍问题体现了国家对私人合意行为的评价,代表着国家对私人契约的干预,是私法之所以为法的重要表现。一个法律制度不可能规定,只要完成了外部的意思表示的事实构成,法律行为就可以有效成立。相反,一系列的限制是必要的或合目的的。[2](368)换句话说,私法自治的界限正是由于国家权力对当事人合意干涉而产生的,合同“效力障碍”代表了一国公权力对私人活动领域的管理。通常说来,合同“效力障碍”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是从“无效”与“可撤销”两种基本途径来处理当事人之间合意的效果。由于其“罗马-荷兰法”的根基,在处理合同“效力障碍”问题上,“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当事人面临着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这两个合同阶段”,是中国和南非合同法较为一致的规范,“合同成立并不一定形成合同生效的民事法律后果”是两国合同法的基本要求;然而,由于南非合同法还受到来自英国的普通法系的作用,“混合法域”的传统导致了南非在合同“效力障碍”的规范上存在着一些特别的规定和认识。如果不能认识南非合同法中有关合同效力的特别规定,那么,在中国与南非的经贸往来中,因法律差异的存在带来经贸及投资的不畅就不可避免。研究南非合同法“效力障碍”的问题,是促进两国经贸及投资效益的需要。
德国民法学家迪特尔·梅迪库斯在《德国民法总论》一书中,将合同“效力障碍”划分为“无效性和可撤销性、未决的无效、相对无效”三类。而在笔者看来,所谓三类“效力障碍”都统一在“无效与可撤销”内。因此,本文以南非“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来探讨其合同“效力障碍”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南非合同法是南非在混合法域背景下所形成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相关判例法规定的结合,就南非合同法渊源来说,可以将南非国内与“合同”相关的特别规范性法律文件、判例均归入南非合同法体系之内。
二、南非合同法无效合同的构成
与中国合同法第 52条、53条明确合同无效即合同条款无效的规定不同,在南非,由于混合法系的法律传统,使得有关无效合同的规定除散见于各部门法的制定法之外,还存在于一系列由司法判例形成的普通法先例中。从我国的合同法第52条、53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有关无效合同的规定的出发点在于对合同行为中出现的恶意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合同外第三方利益)行为进行否定评价;而在南非,有关合同无效的制定法规法则更为具体和细化,是按照合同缔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无效情形以及合同履行中产生的无效情形来分类规定的:
(一)合同缔结过程中的禁止
与我国合同法相似,南非合同法虽然也承认口头协议的效力,但对一些相对重要的合同则强制规定了必要的形式要求:书面、公证和登记。例如,南非 1956年通过的《普通法修正案》规定:采矿权的取得或转让必须经过公证,否则无效。1980年颁布的《信贷法》则规定:信贷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同年的《大宗股票控制法》规定:取得股票合同和与大宗股票相关的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且由当事人或其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否则无效。 1981年颁布的《土地转让法》第2条亦规定:除采用拍卖方式外,未经当事人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字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促进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南非合同法对一些虽然形式不符合制定法要求的合同也做出了一些调整性规定,即承认其效力,只是限制该类合同对当事人之外第三者的对抗。比如说,采矿权的取得和转让要求公证,未经登记不得有效对抗第三者。
与我国合同法第 36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不同,在南非,当事人明示合同须采用书面形式时,口头形式当然无效。因此,我国合同法所认可的“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在南非就是无效的。如普尔麦克利兰诉努赛一案中,法庭就认定:“如果当事人双方合意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的,则只有书面文件才能完整体现成立合同的协商内容。”[3](13)虽然该案例创制的先例是要求“必须有足够证据证明必须采用书面文件的形式,合同才有效”;然而,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在合同订立的协商过程中是提到了订立书面文件,但由于现实原因,导致书面文件没有得到起草”的类似情况。此时,南非合同法的规定无疑给合同当事人就合同是否有效的举证增加了难度。
当然,南非合同法关于合同缔结过程中禁止的规定,提醒我国企业或者投资者在对南非投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就合同缔结过程中有关形式要件的规范。南非合同法较中国合同法更为严格。在对南非投资活动中,双方进行经贸谈判时,倘若对合同缔结形式做出特别的规定,则一定要严格遵守当时合意形成的内容要求,尽量避免因为对合同法理解之偏差而造成合同无效的情形。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禁止
虽然南非法律区分“合同缔结过程中的禁止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禁止”两种情形,但在笔者看来,南非合同法有关履行过程中的禁止在本质上是其缔结过程中禁止的延伸。一般来说,缔结过程中的禁止多为形式要件的要求,而履行过程中的禁止则着重于合同内容的限制。例如,南非在 1957年的《公司法》中规定:雇员与雇主之间达成的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协议无效。1966年《集团土地法》规定:没有许可证,从被管制的土地、集团土地或异族人占有的土地上转让不动产的合同无效。
除了制定法中对合同无效的规定外,受英国法影响的南非在处理合同无效问题上也形成了一些遵循先例的合同无效的普通法原则。这些普通法原则所禁止的合同多为违反公序良俗的协议。在南非,这类普通法原则一般归入“公共政策空间”(Void of Public policy)。在本质上,公共政策代表着特定时期特定社团的公共意见,因此它是具有弹性的。南非法庭以“违反道德要求(contra bonos mores)”①拉丁语,英国法专用名词,意为“违反道德”。认定合同无效是非常谨慎的。一般来说,只对那些确实违反了公共政策的合同履行行为,法庭才会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做出无效裁定;不仅如此,当合同在履行时出现,所涉公共利益对抗甚至相互冲突时,法庭除了对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衡量外,合同本身的神圣性也是法庭需要衡量的。此时,合同无效的举证责任并不归于合同当事人,而是法庭需要根据合同履行中的特定环境具体研究并做出裁判。
此外,在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禁止问题上,基于英国法的影响,ex turpi原则也是南非合同法的重要内容。 ex turpi原则指的是“违反法律的无效合同不具有履行效力”。但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将该原则发展为“基于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切除违反法律规定的部分合同条款后的合同是合法的”。[4](24)当中国投资者在南非进行投资或者经贸活动时,了解南非合同法中基于英国法传统形成的有关原则和判例是非常必要的。
三、南非可撤销合同制度的构成
在跨国经贸及投资往来中,相比无效合同问题,可撤销合同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毕竟从实践来看,不论是中国投资者到东南非洲进行经贸或投资活动,还是东南非洲国民到中国进行经贸投资活动,当事人之间形成无效合同的情形是较少的,因为,无论是中国或是其它国家,无效合同的形成,其本质是触犯了当地民商事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而可撤销合同多为双方协商不清,或者存在一方当事人善意等情形,总之,可撤销合同因不同国家内民商事活动的习惯差异,大量存在于经贸实践活动中。
总体来看,不论是中国还是南非,对于可撤销合同,均可由受害方宣布合同无效。但具体到可撤销合同的种类,两国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定还是有所区别。
一般来说,南非民事法律中规定合同可撤销的情形主要为:虚假意思表示、强暴胁迫和不当影响。对于可撤销合同,受害人拥有选择权:即可以选择宣布合同无效,并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选择维持合同。受害者行使选择权做出的选择不可变更;其中“宣布无效”的选择权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行使,即在合同受损方行使宣布无效的权利之前,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宣布无效”在南非是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一,当事人可以请求法庭宣布合同无效;第二,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被违反时拒绝自己的合同履行义务。第二种“宣布无效”的情形反映了南非法律受到英国法传统影响的现实。因为就同样影响着南非法律的罗马—荷兰法传统来说,对可撤销合同的处理存在的原则是:“禁止一方当事人因为相对人违约而自己拒不履行合同;且对于可撤销合同的处理必须诉诸法院”。在南非合同法就可撤销合同问题的处理上,上议院对德瑞诉皮克的判决可视为是南非合同法在处理可撤销合同问题上实现了从罗马—荷兰法传统转变为英国法传统的开端。[5](67)其中,整个转变又在“可撤销合同之虚假陈述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上述南非合同法就可撤销合同规定受到英国法思维的影响,加之我国合同法第 54条仅仅确立了关于可撤销合同的宏观法律原则,而没有就如何判断各种可撤销行为做出具体规定,因此,当中国投资者在南非进行经贸及投资活动时,极有可能对“可撤销合同”的理解造成一定程度的混淆与模糊。仔细研究南非有关可撤销合同的认定问题,对于防范南非与中国之间的经贸风险极具意义。在此,本文以南非合同法中可撤销合同之“虚假意思表示”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分析讨论。
(一)南非合同法就可撤销合同中对虚假意思表示的认定
虚假意思表示又称错误陈述,在本质上,错误陈述是没有产生真正合意的合同条款,而只是一方当事人通过明示或者行为默示来达到引诱的目的。按照南非合同法及判例的相关规定,当受害一方当事人能够证明存在如下情形,该当事人便可拒绝履行合同:
1、虚假意思表示的目的是引诱他人缔约。泰特诉维士特一案中,法庭认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谎言导致他方缔结合同并不是成立虚假意思表示的充分必要条件。虚假意思表示只有在‘陈述方意图诱导对方当事人缔约,或者陈述方的陈述方式和陈述环境能推定陈述方具有诱导对方当事人缔约的意图’的情形下,才能成立的”[6](79~ 80)。
2、被诱导方缔结合同是出于对虚假陈述的信赖。在这种情形下,被诱导方负举证责任,即受害方必须证明如若没有对方当事人的虚假错误表示,他就不会缔约。
3、虚假陈述必须是对实质性合同条款的内容具有实在影响。受英国法传统影响下的南非合同判例法的一个原则为:只有当陈述方对实质性条款进行了错误陈述,才可能导致受害方在订立合同时受到现实损害。
4、事实上陈述与错误之间存在价值判断下的因果关系。在实践中,事实陈述和加入了价值判断的意见陈述是很难区分的。因此,就虚假意思表示的认定问题,南非以判例法中的先例明确表示:“当事人一方在善意或者诚实的前提下对某已知事物无隐瞒地表达自己的喜好,仅视为意见陈述;相反,如果没有善意或者诚实为前提,则算作是虚假陈述”。
英国法影响下的南非合同法,就可撤销合同中对虚假意思表示的认定是以判例法形成的先例为基础的,因此,在诉讼安排上以普通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模式进行,同传统大陆法系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存在显著差别;进一步来说,南非合同法就可撤销合同中虚假意思表示认定的特别规定,给中国投资者在南非的经贸及投资活动提出了不同于中国国内的要求,这种现实提醒我们的投资者在经贸及投资过程中,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缔结合同的各种细节,并及时制作相关的保存形式。从长远角度出发,当合同因为出现“可撤销”情形时,能有效维护自身利益。
(二)南非合同法关于可撤销合同中虚假意思表示的种类
我国合同法第 54条规定了可撤销合同的基本情形,“重大误解、欺诈”在本质上皆为基于特定原因所形成的虚假意思表示的外观。相比而言,南非法律虽然没有规定虚假意思表示的外观,但在探寻虚假意思表示内在的因果构造的基础上,按照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与虚假意思表示的结果,详细划分了不同的虚假意思表示:第一,欺诈性虚假意思表示;第二,疏忽或过失虚假意思表示;第三,无意虚假意思表示。具体如下:
1、欺诈性虚假意思表示。欺诈性虚假意思表示指的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做出意思表示时,明知该项陈述不真实,仍引诱不知情的对方当事人缔约。在南非,对于由欺诈引起的有严重瑕疵的合同,受害一方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可选择变更或者撤销合同。这一点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相似,但不同的是,在南非,欺诈是侵权行为的一大表现。在合同欺诈中,受害人可依照侵权法律的有关规定,获得间接损害赔偿之救济。例如弗罗斯特诉莱斯利一案中,法庭认为:“受害方不论是选择继续实施合同还是恢复原状,都不妨碍其行使侵权导致的间接损害赔偿权”[7](84~86)。
2、由疏忽或过失引起的虚假意思表示。这一法律规则亦是南非对英国普通法的法律移植。事实上,就英国本身而言,这一规则的确立也不过四五十年时间。1963年的亨德里比恩公司上诉海勒帕特斯公司一案,是英国法确立疏忽虚假意思表示的法律地位的标志。在该案中,法庭认为:“一方当事人向有特殊知识及能力的对方当事人寻求资料、信息或专业性意见时,提供方应尽慎重义务;如因其疏忽造成对方当事人利益受损,则该提供方应负赔偿责任。”①Hedley Byrne& Co.,Ltd.v Heller&Parters,Ltd.(1964)A.C.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法所讲的对疏忽虚假意思表示造成损失进行赔偿,在本质上仍是缔约过失所产生的合同责任;而在南非,有的观点还认为疏忽过失的错误陈述所引起的财产损失是侵权行为导致的结果,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并无关系。[8](54)笔者认为,南非判例法中的“侵权论”在本质上是为了体现对“疏忽或过失引起的虚假意思表示”的严苛责罚,至于到底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不过是学术探讨的分歧。
3、由无意引起的虚假意思表示。所谓的“无意”主要指合同当事人对引起虚假意思表示的后果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者是过失。行为人不存在引诱、疏忽等主观恶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也因为虚假意思表示而产生了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无意引起的虚假意思表示在法律救济上仅表现为受害方行使合同撤销权或者变更相应的合同内容,修正无意所引起的虚假意思表示,受害方无权要求加害方进行损害赔偿。
在笔者看来,南非合同法就可撤销合同中虚假意思表示的种类划分与前述虚假意思表示的认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统一体。相比中国合同法有关虚假意思表示的、较为原则性的规定来说,南非合同法的安排,给中国投资者在南非进行经贸及投资的活动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因此,中国投资者在南非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时,除了要深刻认识和理解南非合同法中的强制性法律规范,还必须清楚南非可撤销合同中的特别规定,减少因对南非合同法理解不全面而造成的投资障碍,甚至是投资失败。
四、结语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我国在非洲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78.24亿美元,同比增长 26.9%,占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总额的16.7%。[8]在法治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今,推进中非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法律制度的娴熟运用,特别是关系到合作基础的合同问题,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本文对南非合同“效力障碍”的关注,正是基于“合同”对经贸往来的基础性意义而展开的,只有在研究中加入对中国相关问题规定的对比,才能提醒中国投资者在南非的经贸和投资活动中,注意南非合同法“效力障碍“的特殊规范,进而合理利用南非合同法,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提高中国投资者在南非投资的效益。不仅如此,在广泛的意义来讲,由于历史的原因,南非私法对许多非洲国家存在巨大影响,所以,研究好南非私法的重要特征,便能更加容易地理解其它非洲国家的相关私法,并不断深化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
[1]John Dugard,Human Rights and the South African Legal Ord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2][德 ]迪特尔·梅迪克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
[3]Poole&Mclennan v.Nourse,1918.AD.404.转引自 Gibson,South African Mercantile and Company Law,New York:Jura&company Limited,1983.
[4]Du Plessis& Jacques,The Law of Contract in South Afr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5]Derry v.Peek,(1889)14.App.Cas337.转引自Reinhard Zimmermann,Daniel Visser,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in South Afric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
[6]Tait v.Wicht&others,(1890)7.SC.转引自Gibson,South African Mereantice and Company Law,New York:Jura&company Limited,1983.
[7]Frost v.Lesl,1923.AD转引自 Gibson,South African Mercantice and company Law,New York:Jura&company Limited,1983.
[8]鞠成伟:《法理共同体:秩序法哲学的核心理想及超越性意义》,《湘谭大学学报》,2012年第 4期。
[9]韩燕:《聚焦中国与南非经贸关系》,《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 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