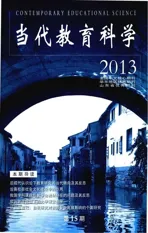后现代认识论下教育研究的当代转向及其反思*
2013-03-27靖东阁
靖东阁
后现代主义的盛行,影响了人们生活各领域的研究传统,后现代认识论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核心组成,也对传统认识论造成极大冲击。后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并宣扬非主体性、不确定性,这些思想内核都来自于后现代认识论的几个基本主题,即:无根基、零散性、建构主义、新实用主义[1],这几个主题都蕴含了后现代主义的求异思维。无根基这个主题反对反映论,认为知识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只是因人而异;零散性则反对系统性、规律性,转向差别和独特;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客观的反映,而是人的主动建构,不同的人建构的知识存在差异;而新实用主义包含无根基和零散性的思想。教育研究作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会受后现代主义的熏陶,在长期的教育研究实践探索中我们发现,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在教育研究中已不再牢固,而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与教育研究的认识论达成默契,并影响着我国的教育研究实践。
一、教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倾向及后现代求异思维的萌生
西方的强势文化深刻的影响着我国,在教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不论研究理论还是范式都在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导致我们自己的教育研究脱离了中国的根土。后现代认识论为打破教育研究的殖民主义倾向提供了认识基础。
(一)教育研究中殖民主义的求“同”倾向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契机的同时也衍生了一些问题。我国的教育研究长期以来受西方传统研究理论和范式的影响,照搬国外理论和研究范式,忽视了我国教育研究的地方特色,理性思维主导下的“一般研究范式”把文化因素挡在研究视野之外。在传统的西方理论体系中,受以客观主义和“主客二分”思维方式为特征的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支配,忽视了教育研究的文化特征,认为有普遍适用的教育学。[2]西方发达国家殖民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不仅通过政治、经济的手段,还有文化的渗透与控制,而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成果不加“中国化”、“民族化”的吸收,导致我们的教育研究跟随西潮,不仅使得我们的教育理论丧失地方和民族特色,也让教育研究逐渐走向 “天下大同”。即使从国家内部来看,研究者在一般教育理论的指导下,遵照固有的研究模式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从研究中抽离出一般的理论模型,在研究者的视界中少数民族的文化“已死”,自己的文化观念却得到“永生”。不论国际还是国内,教育研究的殖民主义倾向依然存在,试图构建一般教育理论和研究模式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教育学术领域求“同”风气慢慢逼近的同时,追求“同”而产生的负效应也相应产生。
首先,求“同”的对应面是对“异”的否定、遮蔽。我们只知道“雪”的概念在西方表述为“snow”,而在爱斯基摩人那里可以有二十几种语词来描述,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扩张,爱斯基摩人丰富的语言表述可能就慢慢消失。同样在教育研究领域,“全盘西化”的结果必然导致我们自己地方性文化和知识的“缺场”,教育理论的多样化也就荡然无存。
其次,“同”即意味着普遍化和抽象化,普遍、抽象的一般存在就使得具体、细微的东西被忽视。拿民族教育研究来说,我国西南地区是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活化石,许多原生态的、独有的教育现象和文化传统至今还保留着,用一般的理论强加于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研究,势必错过研究活生生的、民族特色的教育问题的机会。
(二)后现代求“异”思维的萌生
后现代主义反对研究范式上的宏观叙事,反对构建系统性、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否定事实背后所谓的客观真理,后现代主义把目光转向差异性和独特性。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Geertz,C.)的“地方性知识”(1oca1 know1edge)与哲学家波兰尼(Polanyi,M.)从认识论出发提出 “体验性知识”(tacit know1edge),都反映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后现代科学求“异” 思维。德里达 (Derrida,J.) 创制 “延异”(difference)一词,对确定性与同一性发起宣战。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一种意义构造原则,它提出定义不依赖于实体本身而依赖于同其他文本的肯定或否定的参照关系。“在终极意义上,意义的认同永远被拖延、耽搁、推迟下去。[3]”利奥塔(Lyotard,J.F.)对人们“共识”下的知识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他认为不存在确定性的“共识”知识,人们的“异识”才更合理。在其著作《后现代状态》中,他说:“后现代知识并不仅仅只是政权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后现代知识的根据不在专家的同构中,而在发明家的误构中。”[4]费耶阿本德批判了人类简化、抽象了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尼尔·布朗(Brown,N.)称人类的此举为“简化的陋习”,他讽刺道:“在简单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殚精竭虑,劳心伤神。”[5]吉尔兹更是对有人将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为数学模型感到哭笑不得。
后现代主义的求异思维最早运用于人类学研究,关注西方的人类学者能否把握、传达少数群族和土著居民的 “地方性知识”,反对人类学研究中的文化殖民,反对西方“帝国性知识”对“地方性知识”的同构。人类学研究中的求异思维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求同思维构成有力挑战,使得人文科学的研究不再盲目效法自然科学,并尝试从人文科学内部探究原始而丰富的真实。
二、后现代认识论下教育研究的当代转向
后现代主义尽管存在各种各样不足而被人们诟病,但是它的认识论主张也启发人们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以另外的视角审视问题。以后现代认识论为基础开展教育研究,必然发生了当代转向。
(一)教育研究更加关照民族性和本土化
全球化及其引发的教育研究的殖民主义使得西方“科学”的教育研究范式遍及全世界,当用国际通行的研究范式研究我国教育问题以求得与西方的对话时,我们也丧失了向国际传播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机遇。我国的教育研究跟随西方导致民族性与本土化的缺失,所开展的教育研究只是西方教育研究的附庸,我国的教育研究远离了本土,没有了中国的根,教育研究也慢慢走向“天下大同”。“我们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中没有处理好文化导向问题,就近乎草率地借鉴或照搬了已经步入现代工业文明或正趋向后工业文明的发达国家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经验,甚至只是经验的理论,于是这才造成了变革中所谓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问题。人们没有考虑到落差问题的背后还有文化差异问题,西方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关系问题。”[6]“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科技发展较为落后,很难全面而深刻地向世界各国展示自己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基本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文化全球化过程的单向度传播现象出现了,本来同时并存的同质化与异质化过程出现了偏差: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文化殖民现象相当严峻……所以说,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地位相等、利益互惠、资源共享并不是必然。要世界化就必须先实现民族化,没有实现民族化就不可能有世界化。”[7]
从国家内部来看,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也要考虑国家范围内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我国的少数民族虽然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小,但人口数也达到1.2亿之多,他们居住的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有些地区是专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些区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我之间的关系构成其独特的天地系统。在我国民族地区开展教育研究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理论、解决民族地区教育问题不可缺少的方面,由于各民族、各地区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化和地区差异就决定了教育研究要体现民族性和地方性。但现实往往是忽视了这些差异,对研究范式的科学化追求以及客观性知识的崇拜,导致民族地区教育理论原创性的缺失。
后现代认识论的“异”思维为我们打开了思考问题的另一个思路,它要求人们放弃追求“同”的思想情结,转向对“同”的怀疑和对“异”的肯定。德勒兹(De1euze,G.)在《重复和差异》一书中表达了对柏拉图观念与现实、本质与现象二元论范式的怀疑,试图还原二元论范式压制下的事物的本来面目,宣称差异性、不确定性和非同一性。在该书中他还构建“他者理论”并提出这么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之表现。这与存在主义的“他者即地狱”的表达形成先鲜明对比,体现了德勒兹对差异、他者的尊崇。按照德勒兹的他者理论,应批判并摒弃教育研究的殖民主义倾向,尊重当地文化,不以异域文化强加于本地教育问题的研究,也不要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教育问题抽象化为一般问题加以研究,否则其研究结论可能丧失了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不再是原创性的研究。
“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思潮也已经渗入到我国教育研究中,并对我国新时期的教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下审视教育研究,教育研究的实质上已经更换了‘参照系’,并且与传统的现代性参照系相比,后现代主义确实能够让我们发现以前不曾发现的东西。”[8]吉尔兹把“地方性知识”作为建构起一个区别于西方中心学科知识体系的本土性文化知识系统。不同民族生活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不同,其生成的生活方式和群族文化也各有差异。我们强调在教育研究中注重“文化主位研究”,即站在研究对象的文化立场看待问题,那么依据“地方性知识”看待教育问题的视角和形成的研究结论也就不同。“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不同国家的教育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教育学界对本土教育理论资源挖掘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对本土教育实践的关注也不够深入,教育学领域的研究需要在增加本土文化意识的基础上,努力推进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9]
(二)教育研究更加强调个人体验
后现代认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语言学转向阶段、解构性阶段和建构性阶段。[10]体验哲学认识论是后现代哲学认识论“建构”阶段的最新发展动向。体验哲学思想最早萌生于拉考夫(Lakoff,G.)和杰森(Johnson,M.)的著作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他们指出了传统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哲学的种种不足,提出了体验哲学(experientia1ism)。拉考夫和杰森批判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中的绝对客观性,“从前苏格拉底时代至今,客观主义的神话占据着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统治地位”。[11]因此,体验哲学的提出是突出人的体验性,反对客观主义。由于个人经历、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人的体验会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体验哲学偏偏把导致差异的人类体验放在知识系统的中心,以体现对“异”的追求,这一点与后现代哲学的反基础主义、反价值预设异曲同工。体验哲学认为人的信念是人体验外界世界的结果,人们观念中的一些相同的概念结构是由于人们相同结构的大脑和身体对同一个外在世界反应的结果,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体验的个体性,一般的、绝对化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相对性的真理。体验哲学在信念系统与客观世界联系方面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原则上,即心智内在地说是体验的;思维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12]
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使教育领域在追求一元化、绝对化真理,教育研究也在致力于发现教育问题背后的教育规律,期望能效法自然科学的标准和精确,但是忽视了教育研究中人与文化的因素。教育是人与文化的存在,割裂了人与文化的因素,教育就丧失了其本质。同一研究者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教育问题的研究,肯定要根据研究对象的自身特点进行,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研究者对同一地区、同一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也可能因为个人体验不同,研究也会有差异。这并不是说我们否定了教育理论的客观性,但至少说明真理丧失了其唯一确定性的特征,教育理论开始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体验哲学思想启示开展教育研究要摒弃理性主义的教育研究方法,强调教育研究的多元视角,容忍差异,在生活世界的体验中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这就要求人们突破教育研究的权威话语的局限,在体验与对话中消解科学主义的话语权威。进入特定场域开展研究,我们有三重门要走,第一就是适应自然环境;第二是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第三是摆正研究立场。只有做好这些,研究者才能真正融入当地的氛围,开展体验式的探究。“教育研究过程要始终抱有一种永远的‘求知热情’,除了关注主流话语,更要倾听来自边缘的声音,在为种种可能无法实现的理想服务的基础之上履行自己的责任,从而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回归人的本性,发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13]
三、对后现代认识论教育研究的反思
后现代认识论的求异思维尽管启示我们在教育研究中关注异域文化,以多元视角看待教育问题,强调教育研究的民族性和本土化,但是我们要防止该认识论的极端化倾向。因为后现代主义本是人文主义反对科学主义的一个极端体现,它在给人类各领域带来福音的同时,不少人也在诟病后现代主义极端化思想主张。后现代认识论求异思维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缺陷,我们拿“异”思维来审视教育研究只是借用其主张反对当前研究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切不可把后现代认识论奉为圭臬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防止教育研究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
从德里达的“延异”到利奥塔的“异识”,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确定性、本质性,高扬“异”的价值,使“异”不再是“同”的附庸。求异的观念无疑是对西方传统哲学“逻各斯”的否定,也宣告传统哲学的消亡,让差异成了世界的本质,绝对的真理不再存在。尽管我们反对通过教育研究抽离一般化、客观化的教育理论,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在特定情况下真理的绝对性和客观性,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而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极端化倾向可能就使我们的教育研究倒向相对主义,导致研究者各自从事着自己的教育研究,抽象出不确定性的教育理论,各种教育理论没有交集,形不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种混乱的教育理论研究的状态中更不利于教育学的发展。
尽管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各异,需要我们区别对待,但是我们都是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根,共性总是大于差异,因此不能过分强调差异。我们批判科学主义研究范式的“党同伐异”,也要警惕求异思维导致的分化,“异”只是用来引起研究者对多元文化的关注和尊重,并不是由此夸大多元文化的差异,形成地区性、民族性的教育理论。我国的传统一直是追求大同,“攻乎异端”,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求异思维通过与传统观念的博弈,使人们认识到应该辩证的看待“异”与“同”,我国的教育研究既要防止“天下大同”,抹杀了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特点,也要防止相对主义的倾向,争取“同中存异,异中存同”,发展多元化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二)警惕教育研究的主观主义倾向
体验哲学把人的感性置于知识系统的中心地位,注重人的感受性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机械反映论、唯理性主义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的感受带有主观性的色彩,以人的感受为标准构建知识体系未免会导致主观主义的倾向,这就否定了人的理性和真理的客观性。我们开展教育研究,假如摒弃理性,唯感性是从,那么研究者只是从事个人教育学的研究,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共识,教育学只会是一个零散知识堆砌的沙丘。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研究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无视“思维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原则,有意识的将亲身体验向研究目的靠近,扭曲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其研究具有主观主义的倾向,研究也就失去了价值。与他者理论同理,体验哲学只是用来反对教育研究中的唯理性主义倾向和实证主义倾向,并不能完全依靠感性的力量构筑知识体系,在教育研究中理性是不能被剔除的,理性的参与可以防止主观主义的突围。
[1]麻彦坤.后现代认识论与治疗心理学的实践认识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0(6):37-40.
[2]孙振东.略论教育研究国际传播中的后殖民主义倾向问题[J].比较教育研究,2004,(8):12-16.
[3]J.Derrida.Marges[M].Paris:Editions de Minut,1972,40.
[4]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4.
[5]尼尔·布朗等.正确发问——批判思维导引[A].张晓辉等译.走出思维的误区[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222.
[6]杨启亮.守护家园:课程与教学变革的本土化[J].教育研究,2007,(9):23-28.
[7]宋彩萍.全球化·民族化·高等教育[J].教育研究,2004,(7):66-70.
[8]张应强,赵军.后现代主义与我国的教育研究[J].教育研究,2006,(6):41-46.
[9]于伟,秦玉友.本土问题意识与教育理论本土化[J].教育研究,2009,(6):27-31.
[10]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词典[K].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59-260.
[11]Lakoff,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195.
[12]Lakoff,G.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3.
[13]申任洪,张洪刚.后现代科学观及其教育学意义[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