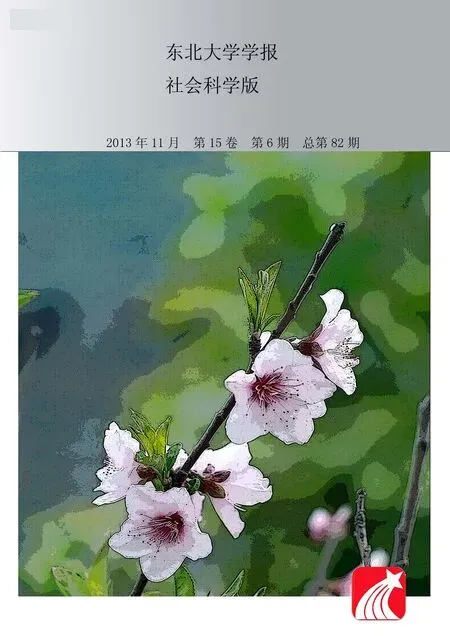明清耶稣会士来华经历对于文化传播的启迪
2013-03-23李枫
李 枫
(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9)
近年来,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开办孔子学院等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相较于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对于中华文化与他国文化,尤其是与那些以宗教信仰为其民族文化之核心内容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张力认识不足,因而缺少能够促使具有不同传统和特质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交融,并最终达到认识与超越的有效途径与策略。明末清初的两百余年间,以罗明坚(1543—1607)、利玛窦(1552—1610)等为代表的一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思想文化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迪。
一、了解他国文化根脉:寻求信仰对话的可能或起点
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疆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从语言文字到文化传统都迥异于西方的国度传播基督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事业。因此,为使基督教能够适当而有效地融入中华本土文化,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前赴后继、殚精竭虑,努力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之根脉,尝试进行基督教思想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在信仰这一层面的对话与交流,并由此取得了足以彪炳史册的业绩。
耶稣会士们所采取的从“附佛”到“弃佛”再到“补儒”的传教方式,较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附佛”是耶稣会士“传教”所迈出的第一步。传教士们在进入中国之初,曾尝试利用在中国社会和民众中已有影响的佛教来介绍自己。作为耶稣会在日本、中国澳门及中国大陆传教的负责人之一的范礼安(1538—1606),基于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及风俗习惯的认识,曾明确要求来华传教士一旦在华定居下来,就应穿僧侣的袈裟,以突出其传教团队尊重中华本土文化的特征。由此,耶稣会士曾身着“僧侣”服装,以“僧侣”身份传教;在语言上,耶稣会士们亦“附会佛教语言”。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附佛”,即借用僧侣服装及佛家用语传教的缺陷: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并非以宗教信仰为其思想文化之核心内容的国度,官方(亦即“朝廷”)对于僧侣存有负面印象;另一方面,这样的做法又极易使对宗教信仰缺乏了解的中国民众(亦即传教士们期待中的传教对象)将基督教与佛教看做是同一个宗教,或者将耶稣会混淆为佛教的一个派别,从而难以理解和领会基督教思想文化的真谛。为此,罗明坚、利玛窦等人的传教读本《天主实录》在修改并再版时,便又采取了“弃佛”的策略。这主要体现在删改一些有着典型佛教意味的词语,如“西竺”被“西国”取代,佛语的“寺”由天主教“圣堂”一词所替换;对传教士的称呼由“入教的出家者”,改为“事物修道者”,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弱化佛教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们的“弃佛”,并非全面删除一切带有佛教意味的词语,如“天堂”、“地狱”等词语,由于其词语的概念义与基督宗教相关词语的概念义相近,就被保留下来了。从对比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这类词所承载的思想文化相通,因而是词义基本对等的词。这样的删除与保留又使我们看到了耶稣会士在对这两种文化摒弃语言形式上的效法之后寻求信仰内核趋同的努力。
耶稣会士们几乎在“弃佛”的同时开始了“补儒”。“补儒”是传教士对儒家典籍、儒家思想的理解,是对那一时期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及价值观的认识与理解。从形式上,利玛窦等改穿了儒服,其名号也从“西僧”、“西士”、“番僧”改成了“西儒”或“欧罗巴人”,这在利玛窦编纂的《天主实义》中得到了印证。耶稣会士们通过翻译与阐释,努力将随时可能被中华文化摒弃为异端邪说的基督教塑造成一种与先秦儒家学说有共通性的信仰观念。比如: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曾尝试说明,儒家经典之中已然存在的“天”的概念与基督教的“天主”亦即“上帝”的概念具有共通性;儒家所推崇的“仁”与基督教“爱邻人如爱己”[1]的观念具有共通性,等等。这样一种以“补儒”的视角对儒家经典的再解读,是试图说明天主教不仅可以“救正佛法”,同时也能够“左右儒术、补益王化”。
正是这样一个由“附佛”到“弃佛”再到“补儒”的过程,我们看到了一种异域文化如何由表及里、由形式到内容,最终从文化沟通的最本质层面亦即信仰层面切入而进入中国社会的。从这样的角度,400多年前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的实践活动,对于我们今天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仍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 互动与重构:认识与超越差异的重要前提
任何一种文化,其单向的传播都是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真正有效的文化传播必须在与它种文化的互动与重构中达成。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互动与重构的过程,传教士们在“书本布道”(Apostolat der Presse)[2],亦即通过翻译出版各种书籍传播基督教思想文化的同时,就已经形成了与中华文化的互动,这使得很多传教士后来成为了汉学家。正是早期传教士的这样一种“书本布道”,成就了近代西方“汉学”的起源。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之际,传教士在华翻译编撰的中文书籍有450多种。传教士们选择了当时中国的“官方语言”汉语(官话)这样一种最具政治合法性、最接近中国文人话语方式的语言进行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互译。早期传教士对基督教思想文化的阐释与传播,其最初、也是最实际的举措是进行基督教词汇的“汉译”,传教士们正是通过“汉译”,通过在其传教活动中对这些汉译词语(如:“天主”、“上帝”、“主宰”、“慈父”、“大父母”、“天堂”、“礼拜”、“瞻礼”、“圣母”等等)的使用,使这类词语及其所承载的基督教思想文化因素在逐渐进入汉语语境的同时,也进入了中国正统的话语体系。于是,传教士们也就在汉语言文化体系内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由此,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们的汉译活动,一方面直接促进了基督教思想文化汉译词汇的形成,从而为之后相关领域的翻译活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词语理解与传播的过程也是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认同的过程。通过相关词语的汉译,基督教思想文化得以在以“书本布道”为指导思想的出版物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同时并存。由此,耶稣会士们以和风细雨般的传播与推动方式,在为汉语词汇增添新词(外来词)的同时,也使基督教思想文化的一些核心观念借助汉语言文字符号,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悄然进入汉语词汇之中,既丰富了原本就具有“海纳百川”之特性的中华文化之内涵,又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两种概念体系间建立起一种通道,由此开创了基督教思想文化借鉴与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先河。
语言符号的互译与转换,承载并连接了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认同,由此而使中华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思想文化在信仰这一层面具有了进行对话的起点与可能。
进一步分析可知: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地在华传播基督教文化,还在于其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习惯、价值取向有着较为清醒的把握。仍以对体现基督教思想文化之核心概念的词语的汉译与传播为例,耶稣会士们尽可能地使译文与中国民众的信仰及习俗密切相关。譬如:中国儒家文化尊崇父母,推崇孝道,以“民之父母”称谓君主,以“父母官”称地方官吏。为了表明对以“儒释道”为核心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亲近,利玛窦在《天主实义》里甚至将“天主”译为“大父母”:“夫父母授我以身体发肤,我故当孝;君长赐我以田里树畜,使仰事俯育,我又当尊;矧此天主之为‘大父母’也,‘大君’也,为众祖之所出,众君之所命,生养万物,奚可错认而忘之?”[3]而天主教在提及天主时,则只有“天父”这一说法,“大父母”之概念,显然是传教士们“入乡随俗”,为适应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比附而成。这种适应,将上帝与信徒之间的“敬拜—眷佑”的机制解释为子女与父母及父母与子女的双重关系,由此,“天主”、上帝与人的关系,也就转换成了“天之养人如父母养子”,“上帝”这一概念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可近可亲”的色彩。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汉语语境中进行的这种文化术语与观念的诠释与转换,一方面体现了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同时也为中国的士大夫们对其汉译术语的接纳以及之后所表现的对基督教思想文化的认同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互动与重构是认识与超越语言文化差异的重要前提。因此,今天,我们在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注重在对异族文化思维习惯及价值取向的把握的基础上通过语言的互译转换达成文化的互动、相容乃至重构,是必须重视的课题。
三、 注重搭建文化精英化与文化大众化的桥梁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国人最先理解和接受的是其所带来的器物文化,即钟、表、天文仪器等实物,进而接受体现其制度文化的历法与天文学说,而体现其文化之核心内容的宗教精神,在传播中却费尽周折,步履维艰。这样的事实提示我们:物质层面的文化现象较为直观,一般处在表层,因而容易了解,交流方便;规定着文化整体性质的理论、制度层的文化因素,则一般处在中间层面,需要深入全面地领会;而精神思想层面,是文化成其为类型的灵魂,因而最为深奥,也最为坚固与恒久[4]。因此,如果我们把文化看做是一个具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这样三个层次的有机体,就能够发现:当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接触时,“首先容易相互发现的,是物的层面或外在的层面;习之既久,渐可认识中间层面即理论、制度的层面;最后,方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层面即心的层面”[5]。
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文化间的核心内容即价值观的不同,以及汉语言文字符号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所造成的障碍等原因,中国文化走出去,长期以来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少数精英层面,即局限于少数汉学家、“中国通”圈子或学术圈内,局限于中国饮食文化等物质层面。在一定意义上,大多数普通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精神层面的精髓依然不得要领。因此,要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就必须处理好中华文化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多层传播,这就要求我们做到文化精英化与文化大众化同时并举。
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传播基督教思想文化,比较注意将文化由精英层面向大众层面的普及。为了将极易被中华传统文化(社会)摒弃为异端邪说的基督教解读为一种与先秦儒学有着诸多共通性的学说,从而为基督教思想文化进入中国主流社会及大众群体创造条件,也为了对天主教的教义与儒家经典的文化概念进行比附、对接、解读,以寻求耶儒两种文化在语言符号上的共性,传教士们在努力使自己精通汉语并熟读儒家经典的同时,十分重视发现、培养和利用中国的一批文化精英(亦即士大夫们)充当助手。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即为代表。正是在徐光启、李之藻这样一批士大夫的帮助下,利玛窦的专著《天主实义》、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等得以出版。有记载表明,《几何原本》正式出版前,徐光启曾多次悉心推敲与校对相关专业词语。中国士大夫们的这种参与,使得由耶稣会士们引入中国的基督教思想文化,从表层的语言符号到核心层面的思想内容,都更为贴近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及源自于本土的思想文化。由此,来自于异域的基督教思想文化也就具备了由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而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的可能。比如,利玛窦在《天主实义》正式出版之前,曾将其手稿交给李之藻、王孟濮、冯应京等中国士大夫,广泛听取这批中国本土“容教人士”的意见,并请其修改润色。传教士通过中国士大夫(文化精英人士)的这一翻译和传播网络,使得能够体现西方基督教思想文化之核心观念的词语逐渐本土化并得以较为广泛地流传。由此,“精英化”的基督教思想文化逐渐进入“大众化”的层面,基督教思想文化由贴近到进入,再到被认同,逐渐深入到社会大众的心中。
当然,文化精英化与文化大众化当然不止于文化典籍学术翻译或通俗读物的编译,但今天,为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着力培养一大批熟悉中华文化(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异国学人,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近年来,大批异国他乡的青年学生热衷于学习汉语,汉语国际推广规模越来越大,这表明了我们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的文化自觉。这样来自他乡的莘莘学子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也浸润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与氛围之中,如果引导和培养得法,他们将可能成为能够使中华文化走入他国文化,走向他国民众,进而深入他国民众人心的生力军。
同样,文化的大众化也呼唤有志于汉语教学的志愿者走出国门。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和汉语课堂上,有一大批志愿者在从事汉语教学,这是文化大众化的一支基本力量。但孔子学院不应是只重视教授汉语的机构,它的定位应是推广传播中华文化的桥梁,除了语言教学,还应重视一切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样式的传播与交流,中国的书法、绘画、戏曲、服饰、民间工艺、传统艺术等等民间文化样式或文化符号更多地进入西方社会,将能够有助于不懂汉语的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接触并进而接受中华文化,从而实实在在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参考文献:
[1] 新约·哥林多前书[M]∥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0:301.
[2] 李奭学. 晚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M]. 北京:三联书店, 2010:393-402.
[3] 利玛窦. 天主实义[M]∥郑安德. 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四.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94-95.
[4] 庞朴.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83.
[5] 李枫. 对外汉语文化因素教学的阶段性划分[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0(4):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