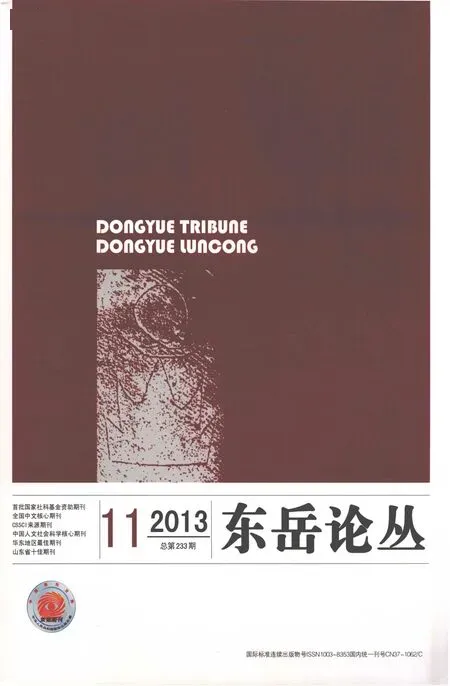论泰州学派平民儒者的政治认知
2013-03-22贾乾初
贾乾初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100;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有学者根据近年实证研究的结果指出,“从社会观的变化来看,中国政治文化也正在向有利于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的式微还是较高的人际信任程度,都表明中国公民在自发合作以及民间社会的活力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人们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缺乏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文化基础的认知可能是一种误判。”①楚成亚,徐艳玲:《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我想,这种“误判”的造成,大约同我们对中国政治文化以士大夫为载体的王权主义特征认知有关。在这种认知当中,“民”、“万民”、“小民”或“愚夫愚妇”、“匹夫匹妇”之类称呼和他们的生活,更多地被当成一种抽象的指称而存在。在精英叙事的传统中,这种抽象的指称,作为历史陪衬是经常被忽略掉的。前述研究结果至少告诉我们三点:一是“中国公民在自发合作以及民间社会的活力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二是中国未必真正缺乏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文化基础;三是这影响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当然,这只是基于当下实证研究的一个结果。那么,“中国公民在自发合作以及民间社会的活力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只是当下才有的现象吗?这个“潜力”有没有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对“民间社会的活力”发挥了怎样的影响?或曰“民间社会的活力”与传统政治文化是否存在一个相互整塑的关系?对明代泰州学派平民儒者政治认知的研究也许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回答。
一、政治认知与传统中国的政治认知
简单地讲,“所谓的政治认知即政治主体获得政治知识的过程。”②佟德志主编:《比较政治文化导论——民主多样性的理论思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政治认知是政治文化研究当中的基础内容之一。强调它的基础性,是因为政治认知会促成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的认同、形成与转化。站在现代政治学理论立场,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获得政治知识的过程。它包括认知对象(内容)与方法(思维),关于权力与权力构成是政治认知的主要方面。政治认知的主体既是政治文化载体,同时也是政治认知的客体。由是可知,探讨某一政治文化现象或研究具体政治文化的特征乃至变迁,由政治认知的分析入手,是不可回避且最为切实的路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的特征限定了传统中国政治认知的基本格局。他们的政治认知所体现的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特征。
第一,士大夫阶层的政治认知是一种由血亲情感拓展开来的伦理化政治认知。
按照《大学》里展现的儒家理想人生设计,由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开始,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此理想人生设计显现出的普遍政治价值指向是确然不移的。其间,修身是关键环节,所以《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这里,士阶层的政治认知过程也就是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即是由身、家所涉及的血亲情感、血亲关系而逐步拓展开来,由家而国,在家国同构的传统政治社会基础格局中,确立自己的政治认知,强化对以君权至上、父权至尊、伦常神圣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念认同。由血缘认同发展为权威认同,从而使士大夫的政治认知显现出一种深重的伦理化特征。
第二,士大夫阶层的政治认知思维,是一种善恶两分绝对化的思维方式。
葛荃教授以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晚明东林党人为对象,从中概括出了士大夫阶层政治认识过程中“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式。这种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要点有三:一是价值判断取决于本原性价值认定;二是善恶两分的价值对立是必然的、绝对的;三是善恶两分的价值合理性判定具有绝对的权威性②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65页。。毋庸讳言,这种思维方式使政治认知流于简单化和模式化。“致使儒家文化在认识层次上始终徘徊在类比和循环逻辑的思维迷宫里,无法脱身。”影响至今的“君子”“小人”、“好人”“坏人”之辨及相关话语,正是士大夫阶层政治认知思维的生动体现。
第三,士大夫阶层对政治权力有较为深入的认知,但缺乏权利观念。
在君主政治框架之下,士大夫阶层对王权主导下的权力来源、权力构成、权力运作,有较为深入的认知。但同时,由于“君主政治体制及其政治权力结构决定了君臣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主与仆,在君权的宰制下,为臣者们必须要恪守忠君义务”,因而,他们根本缺乏对政治权利的观念。这种基本政治格局只能导致以“忠君义务”为唯一价值取向的普遍臣民观念。很显然,作为臣民,即便是作为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士大夫阶层,亦不知“政治权利”为何物,更不会产生维护和强调“政治权利”的强烈要求。其根源在于,他们对自身政治主体的认知是存在巨大缺陷的。
第四,作为政治认知主体,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认知尚停留在类主体认识方面。
儒家所盛称的“人禽之辨”命题所凸显出来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应该区别于禽兽草木之类的整体面貌。因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所能给出的仅仅是人的类主体意识的理性觉醒。”③以上引自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149、62页。这里没关于人类“个体”认识的觉醒。就是说,儒家文化的塑造与熏育导致了政治认知主体意识的重大缺陷——士大夫阶层没有个体主体意识。他们对家国天下、人类群体的强烈责任心与道德意识,以及对个体“人欲之私”的批判与自觉抑制,鲜明地体现出这一阶层的群体特点和缺陷。
二、平民儒者及其政治认知
王艮所开创的泰州学派之独具魅力,恰在于它对平民儒者的哺育。尽管对于这一学派的构成与区分,学界尚未达成充分共识。但对于泰州学派哺育出大量平民儒者,形成了中国儒学发展上独具特色的平民儒学一脉,是基本能够予以认定的。至如平民儒者具有异端色彩乃至“赤手博龙蛇”的狂侠精神以及诸多“近代性”萌芽,更是吸引了大量思想史学者的研究兴趣。这些平民儒者因其身分与历程的原因而与典型的士大夫阶层具有很大区别④本文此间所讨论的平民儒者,是以王艮、颜钧、何心隐、朱恕、韩贞等为代表的纯粹平民一系,而不包括泰州学派中如徐樾、林春、赵贞吉等完全成为士大夫的儒者类型。,故而,在政治认知方面,他们表现出不同于士大夫阶层的特点。
(一)“不完整”的儒学教育
泰州学派中的平民儒者一系,从它的开创者王艮开始,由于出身低微,为生计所苦,大都没有接受过正规而系统的儒学教育。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反而使他们对于学习充满着非同一般的热情。除此之外,即便是曾为“诸生”的平民儒者们,也大多对那种体制内的教育充满着厌恶和反抗。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与正统儒家文化“学而优则仕”的修、齐、治、平的规范体制设计有所不同,带有更多的自我教化的色彩,因而显得尤其令人注目。
据《年谱》所记,王艮虽7岁“受书乡塾”,但11岁时即因“贫不能学,辞塾师就理家政”,直至25岁,“客山东,过阙里谒孔圣及颜曾思孟诸庙,瞻拜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归则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①王艮:《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8页,第68页。一般而言,元、明时人大致在15岁之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②程瑞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40页。,在学习《论语》、《大学》、《孝经》这些儒家基础读物的年龄上来讲,王艮显然已经太迟了,且条件不好,只得充分发挥主动性,将书放到袖中“逢人质义”。
王艮再传弟子颜钧虽家境尚可,但似乎头脑不甚灵光,“十二岁始有知识,”③颜钧:《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第23页。“儿时不慧,十九读《孟子》弥日不成诵”④李炜:《同治永新县志人物列传》,载《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据《明儒学案》所载,其他平民儒者如朱恕“樵薪养母”,韩贞“粗识文字”,夏廷美“未尝读书”⑤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19、720、720-721 页,第703 页。,多为艰辛的生活所累。他们所接触到的教育无非是《四书》之类儒家最基本的读物,他们深入体认,并据以自负的经典依据,也不过如此,文献中记述下来他们那些稍显粗陋、直白乃至笨拙的文风和话语或能透露出个中消息。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他们既无那种清高自傲的士大夫身份的拘缚,亦不为儒典教条所囿,而更多体现出自由自在的天性。
颜山农、何心隐、邓豁渠等人虽然曾有“体制内读书”的经历——“为诸生”,但都表现出对这种儒学教育方式的厌恶与反抗。文献中所记述的颜钧“习时艺,穷年不通一窍”⑥颜钧:《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第23页。、何心隐“芥视子衿”⑦邹元标:《梁夫山传》,载《何心隐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0页。、邓豁渠“不说学”⑧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19、720、720-721 页,第703 页。等,都极为直观地表明了他们对科举“时艺”的厌恶与反抗,主要是因为他们学道领悟与高度的自觉性,遂愈发不能忍受科举套路对心灵的桎梏与对性情的压抑。
说他们所受儒学教育“不完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体制内”按部就班学习的机会,他们中有的人在这方面曾颇有前程(如何心隐);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只是围绕着“四书”等几种儒家基础读物用功,而是因为他们自觉地投身于体制之外,抛弃了“学而优则仕”的标准儒学教育目标与人生之路。他们满怀激情与抱负,投身于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政治活动之中,以自己的实践表现出对体制的某种批判性认识,或对这种体制表现出不积极主动予以合作的态度。王艮、王襞父子坚持不走仕途便是最典型的表现。
换言之,作为体制内道路,通过“学而优则仕”而实现儒者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具备现实性的。他们所选取的修、齐、治、平道路,是直接面对着平民阶层的社会政治实践。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学”,他们的政治认知,才更纯粹,更切近自己的心灵,也更饶有意味。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固然得益于家庭、师承,但因了他们主体的觉醒,而更多地是积极的“自我教化”的结果。
(二)赤身担当的狂侠精神
王阳明自信“良知真是真非”,标举出“狂者胸次”⑨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127页。的襟抱与性情,遂使阳明学脉中人高度认同,因而其后学多具此种特征。阳明的良知学,为后来者主体意识的觉醒打开了缝隙。在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平民儒者一脉中,更是激起思想与行动的滔天巨浪,演化成赤身担当的狂侠精神。
王艮自身本就具有狂生特质。《年谱》载,他29岁时“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住语默,皆在觉中。”⑩王艮:《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8页,第68页。其欲为圣贤救世之志,竟“狂”致入梦。同具狂者特质,布衣王艮与士大夫阳明却颇为不同。相比于王艮,作为士大夫的王阳明显然要矜持得多。生活环境的不同,一方勇于担当,无所畏惧,而另一方则久历官场,深知险恶。
王艮受阳明接引,欲益狂放,以至仿古礼,制五常冠、蒲轮车,上书“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沿途聚众讲学,行事极为高调,一路直至京师,“复讲论甚勤,冠服车轮,悉古制度,人情大异。”这种情况,令王阳明及一般士大夫弟子极为紧张,阳明在京弟子纷纷劝其南返,阳明亦亲致书王艮的父亲,遣人促归。王阳明以王艮“意气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①以上引自王艮:《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归来后,阳明三日不见王艮,直至他认错为止。
布衣王艮的倡道热情,表现为一种对“道”的权威的高度认同,从而迸发出欲淑人淑世的政治激情,我行我素,率性狂放,兴味盎然,他却不知道政界的凶险。在王阳明一班士大夫看来,在当时阉竖当道的政治环境中,这种行为纯是取祸之资,得谤之口实。事关生死,不可不慎,所以不得不对王艮予以裁抑。在王权专制条件下,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即使是德高望重的儒家“君子”——士大夫们,也只能变成缺失权利意识的政治侏儒。显然,在“高扬个性、崇尚自由”,自由表达政治激情方面,平民儒者走得更远,因为在体制外的原因,他们高度认同只有自己所体知的“道”(价值)的权威性,而对当权者颇为藐视。
颜钧33岁时师从王艮弟子徐樾(号波石,?—1550),36岁赴泰州学于王艮门下。颜钧自泰州归后,作《急救心火榜文》会讲于豫章(今南昌),“信从士类千五百人”②黄宣民:《颜钧年谱》,《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颜钧之所以如此自信狂放地以布衣身份,希图以他所理解、承继的“道脉”,从“正心”入手,来“挽救”这批求取功名的士子们的“焚溺”,很大的原因是从王艮那里得到的那种勇于承当的平民儒者风骨。他坦言:“今农愤悱继统于后,盖有得于受传,遂放乎四海,思天下焚溺,由己焚溺也。农之学,自授(受)承于东海,单洗思虑嗜欲之盘结,鼓之以快乐,而除却心头炎火。农之道,传衣钵于西江,专辟形骸凡套之缰锁,舞之以尽神而尽涤性上逆障。”③颜钧:《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颜钧以此种狂侠精神讲学,期以救人救世,撼人心魄,因而影响甚巨,颇为当道不容,“世人见其张皇,无贤不肖皆恶之,以他事下南京狱,必欲杀之。”颜钧弟子罗汝芳(号近溪,1515—1588)为营救颜钧,竟至“不赴廷对者六年”④以上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4页。,将自己的仕途前程置诸脑后,甚具狂侠精神。颜钧自己,陪遭朝廷贬斥的同门赵贞吉(号大洲,1508—1575)同赴广西荔浦贬所,远赴云南寻老师徐樾尸骸,葬于王艮墓旁等等,皆是极显勇于承当和实践的狂侠精神佳话。
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的狂侠精神都是在关涉社会政治的实践中展现出来的。这表明他们一方面继承了阳明“狂者胸次”,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士大夫那种制度与心理上的严重桎梏;更重要之处在于,这还与他们的主体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有关。
(三)“保身”、“安身”挺立的自主意识
王艮的保身说意味着以王艮为代表的平民儒者的政治认知,已经关注到了个体主体,强调了个体主体“身”作为政治实践的前提与根本的极端重要性——“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⑦王艮:《王心斋全集》,第29页。从而为布衣儒者因何具有超强的自信心与勇于承当的狂侠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解释。将作为个体主体的“身”提高到家国天下之本的高度,并予以集中论述,这在之前的儒家中是没有的。这里的“身”,显然具有政治主体意味。值得注意的是,王艮对“身”的主度重视,所蕴含的主体自觉意识,不但促成了泰州学派平民儒者以布衣身份热衷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实践的整体风格,而且进一步促进了泰州后学们对于个体之“欲”的肯定①泰州学派平民儒者对身的重视,亦与其对生命精神的强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平民儒者们对人“欲”的肯定便成为一种惯常现象。其中,王栋“人欲不能无”的思想,颜钧“制欲非体仁”的思想,何心隐提出的“育欲”说等代表性的言说便是泰州学派这种情况的体现。,从而发展出何心隐、李贽这样的富有时代特色与个性特征的“异端”思想人物。
三、平民儒者政治认知的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社会成员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会给这一个体的政治认知打下深刻烙印,会深刻地影响个体的政治思维、政治情感。泰州学派平民儒者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确有不同于士大夫阶层之处,他们的政治认识具有自身特征。这种相异之处,恰恰蕴藏着成为突破士大夫主流政治文化桎梏的萌芽。
(一)通过经典的简约化把握来凸显政治价值认同
对儒家核心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易》等的通俗化、简约化、神秘化,确属平民儒学的特色之一。如王艮等人所说的“《大学》是经世完书,吃紧处,只在‘止于至善’”②王艮:《王心斋全集》,第3页。,“今夫《大学》以修身为家国天下之本”,“今夫《中庸》以慎独,致中和,位育之至”等便体现了这种通俗化和简约化。神秘化在颜钧那里表现得更突出,他在论述《大学》、《中庸》、《易》时说:“大学中庸,大易六龙,三宗学教,乃夫子一生自操仁神为业,晚建杏坛,聚斐明道,易世传世,破荒创造,为神道设教,人师代司造化,专显仁神,同乎生长收藏,莫为莫致,无声无臭于天下万古,即今日之时成也。”③以上引自颜钧:《颜钧集》卷二,第17、18页。颜钧自述,一生得力处不过是《大学》、《中庸》,因而他不断围绕《大学》、《中庸》两文宣扬、演绎。
对经典简约化的把握与神秘化地崇拜,增长了平民儒者的道德自信,强化了他们挺立自身的学派特征。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特征凸显出的是他们的政治价值认知。这套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价值结构的核心是王权至上、父权至尊与伦常神圣④参阅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7页。。亦即是说,平民儒者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儒家核心经典的学习与把握中,认知并认同了传统政治价值。
王艮说:“古之人欲仕,出疆必载贽,三月无君则吊,君臣大伦岂一日可忘?”他申论“王道”时说:“夫所谓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造言乱民是也。”⑤以上引自王艮:《王心斋全集》,第45、64页。虽身为平民,王艮不仅对王权至上、父权至尊、伦理神圣那套政治价值深为认同,而且将之勾画到自己的理想政治蓝图当中,这必然导致王朝认同。站在王朝认同角度,平民儒者似乎与一般社会大众并无不同,而站在政治价值认知的角度,平民儒者基于政治价值认知所导致的王朝认同,表现得更积极。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履行政治义务的主动性上。
(二)履行政治义务具有主动性
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义务是按照特定方式行为的要求或责任”,而且义务问题“牵涉政治统治的道德基础”。显然,平民儒者依据他们的政治认知而鼓舞起来的义务感,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道德义务范畴。安德鲁·海伍德强调:“道德义务最重要的形式是‘政治义务’,即公民承认国家的权威,并遵守其法律的义务。”⑥以上引自[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175、174页。就是说,平民儒者基于王朝认同而产生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实践形式上表现为“政治义务”。这种看法放到泰州学派平民儒者身上,依然是具有说服力的。就平民儒者的社会政治实践而言,他们言行中体现的履行政治义务的主动性,鲜明表达出他们对国家权威及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的认知和认同。而“实践理论和信念的直率性”⑦[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正是泰州学派的特征。
泰州学派平民儒者履行政治义务的方式,主要是讲学。泰州学派平民儒者的言说、行止方式更为亲近底层,所以其履行政治义务的效果显然更好,影响也更大。在他们的讲学过程中,阐发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即所谓“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如王栋(号一庵,1503—1581),以此六条为内容,各作诗一首,名为《乡约谕俗诗六首》。颜钧除了“劝忠”、“劝孝”,更是用浅白易懂的四言韵文作《箴言六章》并各附诗二首,来一一阐发明太祖六条“最高指示”。这在表达他们自觉的王朝认同上,最明确不过了。
废水[15- 16]取自广东东莞的一家造纸厂废水处理车间,测量数据显示了好氧段废水的工况。如图2所示,数据包含170个样本点,8个废水变量,其中左边纵坐标分别代表的是进水化学需氧量(CODinf)、出水化学需氧量(CODeff)、进水悬浮固形物(SSinf)、出水悬浮固形物(SSeff);右边纵坐标表示流量Q(104 m3/d)、pH值、温度T(℃)和DO(mg/L)。其中,把CODeff和SSeff作为输出变量。在MATLAB中分析处理170个样本数据,将前140个样本数据作为训练集,后30个样本数据作为测试集。
平民儒者履行政治义务的主动性,还表现在积极主动地参与地方事务、乡村秩序建设上面。王艮《年谱》载,御史洪觉山听了王艮论“简易之道”后,大为叹服,“于是觉山请订乡约,令有司行之,乡俗为之一变。”又载,“时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乃造先生谋。先生竭心经划,二公喜得策,一均之而事定,民至今乐业。”①王艮:《王心斋全集》,第74、75页。王艮通过帮助官员制定乡约、谋划分灶产方案等,切实地履行了他的政治义务,进行了政治参与。王艮后学陶工韩贞学有所得后,“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三,第720页。。他的教民化俗实践,达到了没有人去官府打官司的程度,因而深得当政者赞赏。可以说,平民儒者积极主动地履行政治义务,在配合地方官员维护政治秩序方面,显示了重要的政治功能。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对于意形态化的政治价值的认知和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
(三)政治设计的简单化和空疏化
就总体来看,平民儒者也未能逃离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情怀的熏染。并且,因为平民儒者的布衣身分,他们缺乏士大夫阶层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与运行方式乃至“潜规则”之类的深入体认,因而他们关于政治设计的认知较之士大夫阶层,更具有简单化与空疏化的特征。
王艮勾画的理想政治蓝图,并不复杂,他突出强调了“简易”的办法。他认为实现理想政治,只须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切围绕“孝”做事情就可以了。所以,兴孝是首要的政治问题。朝廷应该“初月,颁取天下之孝者,无择其贵贱贤愚。次二月,颁取在各司之次位。次三月,颁赏爵禄。次四月,任以官事。次五月,颁以举之司徒。次六月,颁取进诸朝廷,天子拜而受这,登之天府,转以颁诸天下,以能教不能,是以孝者教天下之不孝者也。”一切围绕“孝”,以“孝”来统摄政治与行政工作,不可谓不简易。正如他一向认为的那样,“古之善为政者,必有至简至易之道,易知易从之方”。然而这一切都要寄希望于政治权力的认可,并由上而下来施行。显然,离开最高政治权力的认可与推行,真正践行之,这种在他看来如此“有效”的简易之道也是绝然不可能的。“然非天子公卿讲学明理,躬行于上以倡率之,则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卒,亦不可致矣。”③以上引自王艮:《王心斋全集》,第51、48、66页。王艮自然明白其间的关键之处在于“天子公卿”的“躬行于上”,这同时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王艮的政治设计是以高度认同现有政治权力合法性为前提的。
平民儒者的政治认知水平主导了他们的政治设计。很显然,他们既对政治体制与政治运行的复杂性估计和认识不足,又缺乏相应的理论深度。因而,他们的政治设计流于简易化和空疏化,缺乏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实属必然。惟一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基于政治认知而抱持的道德乐观主义,以及这种道德乐观主义支配之下的主动精神。
(四)政治主体认识的深化
平民儒者对于履行政治义务的主动性,承担“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自然与其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道德觉醒有关。然而,我们如果仅仅将之归结为平民儒者的道德觉醒确实是有些简单化了。他们在政治主体的认识方面的确是有所深化的。
王艮的“淮南格物”说,在这方面大有意味,他对《大学》中的“格物”进行了创造解释。在他那里,“格物”实质上就是“修身”,而“身”与“天下国家”同为“物”,其中“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紧接着他又指明:“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④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民国东台袁氏编校本,第15-16页。。的确,“‘安身’是构成淮南格物说的一个核心概念。”⑤吴震:《泰州学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艮那里的“安身”并非理论建构与逻辑推衍,而是一种必须切实行动的道德实践。这显然与平民阶层对“身”的生存具有更深刻的生活体验有关。
伦理化的政治传统,使得道德主体在现实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自然成为政治主体。对政治主体的认知,在以王艮为代表的平民儒者这里深化了。我们不得不承认,王艮将“身”(既包含肉体的人,也包含精神的人),当作其学说的一个核心问题来认识,是对政治主体的一种客体化认知。而对“身”及其价值的客体化认知,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主体意识,从而为王艮之后的平民儒者沿着“身”——“吾”——“私”——“真”的路向思考下去,打开了缺口。颜钧、何心隐之流狂放的社会政治实践,都是沿着这一路向拓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平民儒者在社会政治实践中表现出的强烈的义务感,或者说是履行政治义务的主动性,王艮初见王阳明时所说的“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敢忘”①王 艮:《王心斋全集》,第70页。,其实是潜在蕴藏着主体政治权利意识的。只是这种政治主体的权利意识没有被明确地强调出来罢了。
四、结 语
总之,平民儒者的政治认知因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与士大夫有异,而具自身特点。他们更注重将经典简约化,藉以把握和认知传统政治价值。正是由于对传统政治价值的认知,和对王朝的认同,使他们在履行政治义务上具有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他们对于王朝的认同大于批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表现在他们简单化、空疏化、缺乏可操作性的政治设计上。他们对“身”的思考与实践,深化了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主体的认知。可知,传统政治文化尽管以士大夫阶层为载体,但同时也有着平民阶层出于“道”的激情,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思想资源。
并且,平民儒者们大多终生以讲学为职志,热情洋溢地参与乡村秩序的建设,以淑人淑世为理想,以像颜钧所说的“翊赞王化”②颜钧:《颜钧集》卷一,第2页。为目标,从而演化为一场富有平民特征的社会政治实践运动,他们突出展现了中晚明时代民间社会所存在的活力。这至少说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平民阶层并非是一贯地消极、被动地作为历史陪衬而存在的。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以王艮为代表的平民儒者的政治认知因其与士大夫之儒的高度同质性,而很快地淹没于士大夫精英阶层的主流政治文化中。只不过到了晚近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发生缓慢的变迁时,泰州平民儒者的政治认知与社会政治实践才被作为思想资源被发掘出来,并予以放大。不过,泰州平民儒者的政治认知与社会政治实践,的确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当中,体现出相当程度的活力。这种活力无疑已经成为平民儒学思想资源的一部分,在当下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也有可能发挥出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然而,就总体而言,基于“士、农、工、商”的传统四业分途区划而来的传统平民儒者及其政治认知,如果没有在现代民主社会与公民意识成长的条件下有一个根本的转换,它就永远不会焕化为当下政治文化建设的鲜活机缘,而只会使其中某些可喜的萌芽风干在它的历史价值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