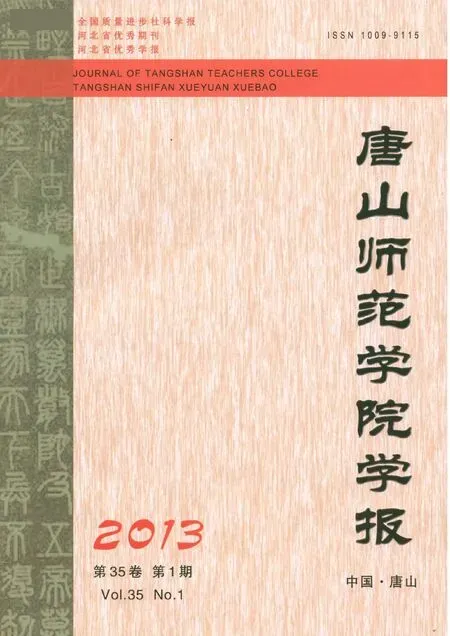海德格尔语言之思的复调性
2013-02-15郑丹青
郑丹青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一、复调性与存在
复调本是音乐术语,“不同的声音用不同的调子唱同一个题目”[1]。巴赫金在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文本分析时,将音乐中的“复调”概念引入小说理论中,经多方阐述成为其哲学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由隐喻演绎为概念,由术语提升为范畴,其涵义在多重变奏中不断绵延而日益丰厚。它们既是指文学体裁,也是指艺术思维;既是指哲学理念,也是指人文精神。“在美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艺术观照上的一种视界,因此而有‘复调型艺术思维’;在哲学理论‘复调’指的是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建构真理的一种状态,因此而有‘复调性关系’。”[2]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及《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等书中,“对话”是巴赫金反复阐述的一个核心概念。对话性(对话关系)是其复调理论的基石。对话是复调得以形成的质的规定性。巴赫金的“复调性”的核心语义乃是“对话性”。经巴赫金的多方阐发“复调性”不仅指称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更是把它提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复调性”作为哲学理念,其精髓乃是不同主体间意识相互作用的对话性,其根源乃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性。在巴赫金看来,凡是能够表达一定含义的事物,只要是以语言符号表现出来的,相互间就会有对话关系。任何存在只有经过对话,才能实现思想的、情感的、意义的交流,才能建立起人与物之间、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这样相互关系显现存在,对话是人的存在以及世界的本质。因此,对话思想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特征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将此在与世界联系起来,将世界问题和人的问题联系起来,又通过此在这一中介把世界现象最终同存在问题勾连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复调理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有着内在的“对话”关系。
二、海德格尔语言之思的存在论特色
1. 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存在关系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切哲学的永恒主题。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探讨。由于运思的方式不同,其探索道路殊异。存在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主线,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存在之外并无非存在”,“存在是一”,“存在与思维统一”等著名命题后,不知有多少哲人穷毕生之力,踏上这漫漫长途……如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书中所预言:存在之为存在,这个永远令人迷惑的问题,自古被追问,将来还会永远追问下去。”这是“存在”的命运,亦是哲学家的天命。
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在其认识论的框架中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之中。自柏拉图开始到笛卡尔直到尼采的整个西方哲学史,是形而上学的历史。海德格尔发出“克服形而上学”的呼声并踏上了克服形而上学、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的“林中路”。海氏为了把人从抽象的本质世界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他首先对西方哲学的根基——“存在”观念发起挑战。他认为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存在可以被遮蔽得如此之深远,乃至存在被遗忘了,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也无人问津。”[3,p42]同时,海德格尔也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往往是以某种存在者的面目出现,离开具体的存在者来询问存在的意义只会沦为空话,因此必须以存在者作为起点来追寻存在的意义。“我们应当从哪种存在者掇取存在的意义?我们应当把哪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好让存在开展出来?出发点是随意的吗?抑或在拟定存在问题的时候,某种确定的存在者就具有优先地位?”[3,p8]要寻找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既要有能力把审视存在的方式说清楚,又要有具备领会、发现的能力。“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Dasein]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3,p9]海氏认为众多存在者中只有一存在者能担此角色,这就是此在[Dasein](Dasein,又译亲在,缘在,本是等)。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有两项特征:一是此在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人的一切行动包含着对存在的领会,人首先在他的行动中而非首先在理论认识中领会存在。另一项是此在的存在“总是我的存在”。此在的两个特征都要从“此在在世界之中”的现象出发来探索,也就是说根据我们称为“在世界之中”这一存在建构来看待和领会此在的这些存在规定,从而展开对存在的追问。以下我们要分析的是:何谓世界?此在与世界的关系如何?它们又是如何与存在问题联系起来的?
如何理解世界?首先应明确的是世界不是传统认识论中作为主体对象的客体,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认识的客体就会把它理解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亦即世界成了“存在者”,这样就仍然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泥潭之中。对于何谓世界的问题,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作了比较集中的论述:“世界并非现成的可数或不可数的、熟悉或不熟悉的物的单纯聚合。但世界也不是一个加上了我们对现成事物之总和的表象的想象框架。世界世界化,它比我们自认为十分亲近的可把握和可觉知的东西更具存在特性。世界决不是立身在我们面前、能够让我们细细打量的对象。只要有诞生与死亡、祝福与诅咒的轨道不断使我们进入存在,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人始终隶属于它。在我们的历史的本质性决断发生之处,在这些本质性决断为我们所采纳和离弃,误解和重新追问的地方,世界世界化。石头是无世界的。植物和动物同样也是没有世界的。”[4,pp30-31]世界既有物的因素,又不纯然是物的因素,也不是人从自己感觉出发可触摸、可觉知的那些东西。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是指存在者如何存在,以及存在如何规定存在者。世界总是和此在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和此在有关的世界都属于海氏的世界。不能说有此在才有现成事物,但可以说没有此在就没有世界。我们不能离开此在去理解世界,也不能离开世界去理解此在,此在与世界是合一的:有此在即有世界,有世界即有此在。万物存在,但唯有人有世界,石头没有世界,动植物也没有世界。简言之,海氏是把此在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置于“此在在世界中”范围内来讨论的。他把此在与世界联系起来,将世界问题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又通过此在这一中介把世界现象(因缘反映归于此在)最终又同存在问题勾连起来。“此在生存着就是它的世界。”[5]只要人存在,具有事物的世界就在他周围敞开。20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把“‘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称之为世界(Welt)”[6]。他又用“大道”(Ereignis)代替“存在”(Sein)这一核心词语,四重整体的世界是大道的显现,大道与存在同一。同时,他提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了更本源的思考。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在天地神人和谐的四重奏中,作为世界的守护者的人才能与存在相遇。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才是本真的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也不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人只有把世界视作为另一个“自我”与之交往,对话,才能体验和理解世界,获得存在的意义。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海德格尔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都是围绕着对存在(Sein)的追问来进行的,在他看来,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是存在关系。
2. 海德格尔“言说”观——以词语创建存在
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思考不同于普通的、另辟蹊径。表面看来人发明了语言、利用这语言,实质上是人在语言中发现了自己。对存在的追问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主题。在他看来,要追问存在问题,就要把存在带入言词。于是,言词、语言与存在就直接勾连起来。
海德格尔的“言说”观是建立在批判传统语言观的基础之上的。人们每天都在用语言交流,因而人被称作会说话的动物。传统语言观的核心思想是将语言视为交流、传达的工具,具有明显的工具论特质。语言成为摆在人面前的东西,人们可以使用它,也可以回避它而“沉默不语”。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两千多年来关于语言的学说都是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基本模式之上,把语言的原始维度给“遗忘”了。这一“遗忘”,亚里斯多德是始作俑者。
海德格尔在《语言的本质》一文中,就亚里斯多德在《解释篇》开头有关的语言部分作了翻译:“有声的表达(声音)是心灵的体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声音的符号。而且,正如文字在所有的人那里并不相同,说话的声音对所有人来说也是不同的。但它们(声音和文字)首先是符号,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体验,而且,与这些体验相同的表现的内容,对一切人来说也是相同的。”[7]海德格尔认为亚里斯多德把语言看成一种符号系统,看成人们之间相互交流表达的工具。人们通过含有表达意义的声音的说话活动来阐明语言这本没有错,但这只是从语言可以被人所利用这一角度而言的。这种语言观的哲学基础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从形而上学对人们的解释出发,由形而上学的人想到人的逻辑、表达、发音,或是想到人在造字时对客观物象的模仿。这实质上把人类置于中心地位,突出人的主体性,其思维模式是主客二元对立。海氏的哲学旨在彻底反形而上学,他对存在的追问之路就是免蹈传统覆辙,唤出人们对存在的遗忘。在对存在追问的同时,海氏对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也作了一番深刻的思考。
他的博士论文《邓·司各脱的范畴与意义学说》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进行反思,但对于两者的联系尚无清楚的揭示。在他的就职论文中,对中世纪的思辨语法作了详细的研究,试图把胡塞尔的纯逻辑语法和自然语言的经验串联起来。后来,他又明确表示,那仍是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在其前期重要作品《存在与时间》里,这一关系只起背景作用。在《存在与时间》中引导语言讨论的基本词是“言谈”(或话语)[das Rede],相应于希腊文中的 logos,由情绪(或现身)领会与言谈,这两者通过话语得以勾连,构成此在之此生存论模式“话语是此在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建构,它对此在的生存具有组造作用”[3,p189],或者说,“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在基础是话语”[3,p188]。
《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思想方式决定了海德格尔不可能把语言的本质理解为以某种现成的言谈方式,用以表达和传达与现成事物相应的现成观念。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指出,要追问存在的问题,就要把存在带入言词。于是,言词、语言与存在直接联系起来。语言入乎言词的存在。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说:“惟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敞开领域之中,在没有语言的地方,比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因而也没有不存在者和虚空的任何敞开性。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4,p61]
三、海德格尔语言之思的复调性特点
在《诗人何为》里,海德格尔第一次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个命题通过《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使得众人周知。海德格尔以词语创建存在的语言观主要体现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下面以此书为中心重点谈谈语言之思的复调性点。
1. 以“诗意的存在”重新建立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海德格尔毕生对逻辑持一种反对态度,强调把语言、思从语法和逻辑理性中解放出来,从而恢复逻各斯的原初意义。海德格尔把逻各斯理解为语言,早期主要是指此在之话语,后期是指作为存在的语言、本真的语言、大道(Ereignis)之道说(Sage)。
正如海氏所批评的,形而上学很早就以西方的逻辑和语法的形式霸占了对语言的解救。在这前提下,存在被遗忘、被遮蔽了。为此,必须从形而上学的言说方式返回诗意的言说方式,把语言、思从语法和逻辑理性中解放出来,从而恢复逻各斯的原初意义。从原初语言上以诗性方式解说语词,探寻语词原来包涵的人与世界的亲缘关系,以及所呈现的人的洞察力与启示力量。命名召唤存在,语言给出存在,唯有在语言中,存在才成其为存在。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语言使人能站立于一切存在的“显明状”之中,若没有词语对存在之物的揭示,“显明”是不可能产生的。语言使存在敞开就是“澄明”听命名的东西。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对存在的显现,就是让存在本身说话。那么,存在是如何“说话”的呢?海氏的思路是:首先否定了流俗语言观有关“说话”的三种含义,其根据在于它是把语言视为工具,一种逻辑、语法的表达,接着他提出“语言说话”的观点。海氏认为要找到这样一种说话,最有可能是在“被说出的东西”中寻找,“因为在所说之话中,说话已经达乎完成了。在所说的话中,说话并没有终止。在所说的话中,说话总是蔽而不显。在所说的话中,说话聚集着它们持存方式和由之而持存的东西,即它的持存,它的本质。但我们所发现的往往只是作为某种说话之消失的所说”[4,p16]。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说话有遮蔽作用,其二,说话有聚集作用,它勾连着持存方式及持存的东西。特别是后者已突显“世界”的轮廓——语言创造了世界。如果非得要在所说之中寻求语言之说,海氏认为最好是去寻找一种纯粹所说,在他看来,“纯粹所说乃是诗歌”[4,p7]语言说话,其实我们所要找寻的是在诗歌中寻找语言之说话,所寻找的东西就在所说话的诗意因素之中。换句话来讲:“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话”[4,p23]——语言在某种从未被说出的东西中说话。在他看来,语言就是存在,“说话”的意思就是存在被展示于人。在“说话”这个事态中,隐藏着存在与人之间的整个关系。人“说”语言,就是居住“存在”的近旁,沐浴着存在之光,走向澄明之境;同时,人“用”语言,也就遮蔽了存在之光沦入晦蔽境地。在语言“既澄明又遮蔽的到来”两重性中,人也证实了自己的存在的两重性,人既可以切近存在之家,也中以远离存在之家。海氏提出这一语言观,“关键在于学会在语言之说中栖居”[4,p27],以“诗意的存在”,重新建立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2. 有声的聚合与无声的聚合的奏鸣
海德格尔晚期对存在的追问出现了语言论转向,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思考成为其关注的重心,其追问存在之路也走向了审美、走向艺术(诗)。这中间经历了一段语言之思的路程,如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谈到:“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4,p62],“筹划的道说就是诗”[4,p61];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又提到:“人类此在的根基是作为语言之本真发生的对话。而原语言就是作为存在之创建的诗。”[8,p47]海氏将存在、语言与诗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并有了关于原初的语言即是诗的明确表达。海德格尔后来所做的工作大都是从这两方面来进行的:一方面就存在与语言的关联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就语言与诗进行思考。前者可用“语言是存在之家”作为表征,后者可用“诗是道说的一种可能”作为表征。我们不难发现,海德格尔就存在、语言、诗所进行的思考是前后一致的,而且他所说的语言、诗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立足存在论基础来思索,因为只有在存在论意义上,语言或道说才与诗相通,即都是指向存在或曰大道运作的表征,语言是道说,诗是道说的一种突出方式,道说在诗中显现。
语言的本质在于“道说”,而“道说”的意思就是“显示,即:让显现,既澄明着又遮蔽着之际开放亦即端呈出我们所谓的世界”[7,p193]。为了端呈这世界,须有所凭借,其凭借就是词语。“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惟有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有了词语,给“物”命名,“物”才被赋予了存在。当然,这里的“物”是“意指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一切东西”[9,p152]或“任何一个当下存在者”[7,p179]。需要注意的是词语给出的不是“物”的“存在”本身,而只是通向“物”的“存在”的一条“道路”而已。换言之,词语把作为存在者的当下之物带入这个“存在”之中,并把物保持这个“存在”之中。诗人的职责是“把他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特别地亦诗意地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7,p149]。语言创造人也创造了世界,人永远以语言方式拥有世界。在讨论物、世界、筑居和四重整体时,在关于诗与思的对话的思索中,海氏试图言说存在之道说。他提醒人们:人之说话的任何词语都要从听而来并且作为听而说话。他所说的听是“倾听”——倾听寂静之音。
“人之存在建基于语言,而语言根本上惟发生于对话中。”[8,p41]这里“对话”一词是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的一句诗中挖出来的,荷尔德林的诗句为:“人已体验许多。自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彼此倾听众多天神得以命名。”海德格尔对此诗句作了阐释发挥,把“对话”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流俗观念看来,所谓对话无非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人运用语言进行交谈,对话不过是语言的一种实行方式。海德格尔则认为,对话乃是语言的本质性事件,“只有作为对话,语言才是本质性的”[8,p42];而且在人的语言能力产生时并非立即就有对话。荷尔德林说:“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彼此倾听。”能够彼此倾听就必须在词语上获得一种统一性,必须统一于单一、同一的东西之上,这种单一、同一的东西“惟有在一个持存和持续者的光照中才能够昭然若揭”[8,p42]。时间长河滚涌向前,只有当时间在延展中进入某个持存的当前,遭遇到那开启自己的瞬间,人才能够走进一种持存状态中,才具有统一于某个持存者的可能性,才能够统一于单一、同一的东西之上,才能够产生对话,从而使语言提供的通向存在者敞开领域的可能性真正实现。在对话中,诸神得以命名,万物得以命名,走入存在的澄明之中,人的存在进入持存,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在其中一个世界才真正显现出来,而这世界就是由天、地、神、人构成的四重整体。在这四方游戏中,诗人截取诸神的无声之音,把它们变为有声之言,传给他的人民;同时,诗人从民族的古老传说中听取对存在者整体的领会的原始领会。诗人以运思的方式歌唱;思者聆听者诗。诗思近邻,诗人和哲人也构成对话。“诗人命名诸神,命名一切在其所是中的物。”[8,p44]命名是对“天道之物”的说;命名使物成为物,也使词与物构成新的对应关系。在道说中语言的创造性体现出来了,一方面它连接词与物,另一方面通过词与词的自由结合生发出新的意味。这种意味就是诗意。诗意是通过词语的“暗示”而实现的,具有不确定性与多义性,语言的审美特性由此而突显出来。由于道说又总是处于某种不确定之中,存在与此在之间关于道的对话在语言构建的四重整体中具有明显的复调性。
诗人感受到存在的缺席并产生要付诸有声语言的冲动,才产生了诗歌中的世界。感受存在缺席的“动作本身”已经让诗人处于天、地、神、人的共在之域中了。这个动作就是以“寂静之听”接受道说这种无声的“天籁之音”。与此同时,诗歌“有声的聚合”组成敞开的域所——由在场者组成的显明之域;与之相对还有一个“遮蔽的域所”——未在场者的黑暗之域。道说的语言就是要让“未在场者”通过在场者的暗示到达在场,因此体现道说的语言包含有两个声部,我们把这样一个特征叫做审美语言的复调性。在这种语言中,未在场的域所将自己若有若无的影子隐秘地投射到在场的域所中,它在敞开的瞬间又逃离敞开,它就是存在或天道。简言之,语言的道说,一方面作为无声的聚合在说,另一方面它借助于显式的说而进入显明之域,是有声的聚合。天生万物,禀赋殊异。每个人对存在的不同感悟产生不同的理解。感悟可以不诉诸言词,海氏称之为作为守护者的“人”(如诗人)对“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倾听,听中发生着无声的聚合,寂静、天籁之音;也可形之于“言词”,“说”以在场者的在场开启不在场者的不在场,有声的说将四者聚合在“在场中”。不论是有声的聚合,还是无声的聚合,目的都是要将天道保持在它的整体中,整体就是一种黑暗的混沌的“无”,即“锁闭”或“遮蔽”。这两个声部的奏鸣,形成了语言的复调性。在这天、地、神、人共在的审美世界里,道说的审美语言,既要始于个体又要超越个性,超越过程就是将人放置于四方域的大背景中展示人的复杂性,存在的悖论性,生命的难以名状,说得清(天地的敞开)又说不清(神的遮蔽),在真实的幽暗中展现诗人的喜悦与困惑,召唤人们返回存在的家园,诗意地栖居于大地。
四、结语
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人寓于世界而存在。海德格尔将对存在的关注与对人的生存的探索联系起来,从存在论视域来考察人的生存状态,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人生于世,有所取舍,亦有所得失。患得患失中膨胀了欲望,迷失了自我,人云亦云中终归不知所云。自工业革命开始,人们跨入了人类、自然、技术关联三个世界并行的时代,其时代特征为极度压缩过程,只看效果。物理距离近了,然而心理距离越来越大,心灵枯竭,无所适从的生命价值遁入了意识的虚无。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中所倡导的天、地、神、人之间最为广义的大对话,其真实意图就在于消除异化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使现实人生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文学可以表达诗意,诗意源于现实生活。人因为有语言,所以能超越在场的东西,进入到存在里去;人因为有语言,能言说不在场的、隐蔽的东西,所以能相互沟通和理解,形成共同生活。于是巴赫金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存在的复调,发现了地位平等的对话双方深层次沟通的可能。
艺术向我们暗示出,作为此在而生存时精神超越物质世界的可能性。作为人的创造物的艺术处于人和技术之间,为人类架起了一座自我复归的桥梁。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巴赫金都体认到现代社会中人被抛、被扭曲的一面,不约而同向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深情地凝眸,期望借助艺术救赎的灵光,点燃了众神离去的黑夜的明灯,击打精神还乡的节拍,期望人类在复调性的对话中相互倾诉、聆听寂静之音,从而让人与世界的理想关系得以全面地呈现。
[1]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58.
[2]周启超.复调[J].外国文学,2002(4):80-86.
[3]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6.
[4]海德格尔.孙周兴,译.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5:67.
[6]海德格尔.孙周兴,译.演讲与论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5.
[7]海德格尔.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海德格尔.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