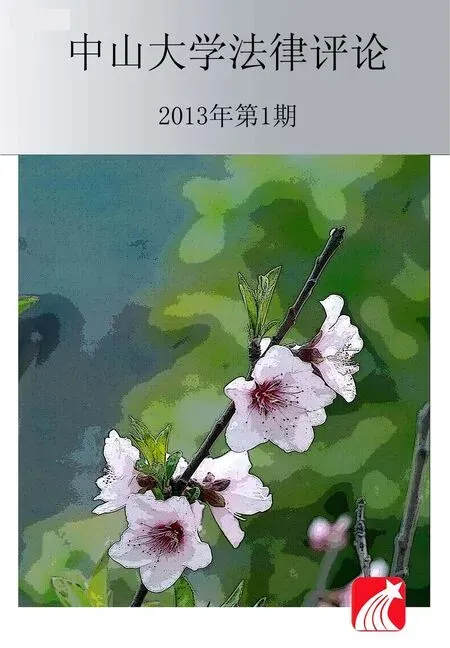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与审理程序
——以日本民事诉讼为视角
2013-01-29三木浩一张慧敏
三木浩一(著) 张慧敏(译)
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与审理程序
——以日本民事诉讼为视角
三木浩一(著) 张慧敏(译)[1]
引 言
日本民事诉讼法[2]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于1996年6月26日颁布,1998年1月1日施行,屡经修改。最后一次修改为2011年。——译者注文书提出命令及其审理程序的有关规定中,由现行法首次规定的内容有以下几条:1.220条4号文书提出命令申请的必要性要件(221条第2项);2.裁判所的文书特定程序(222条);3.用以审理文书持有人是否具有文书提出义务的“暗室程序”(223条3项);4.只针对文书的某一部分内容提起的文书提出命令(223条1项后段)。日本现行法中虽然也有其他条文规定了文书提出命令的内容,但这些条文原则上只是把旧法条文由古文转化为现代文,条文内容本身并无变化。这些条文中又有一部分,虽然条文内容本身并无变化,但受现行法新设、修改的规定的影响,其解释和运用已经与旧法颇为不同,这类规定也将是本文的探讨对象。而对于那些在解释运用上虽然具有争议,但理论争议状况与旧法相比并无不同的条文,则由于篇幅有限不纳入本文探讨范围。
一、文书提出命令的申请
1.总说
当事人要求裁判所发出文书提出命令时,必须依照221条的规定提起申请。即,当事人依据220条1号至3号规定[1]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0条(文书提出命令):符合以下情形时,文书持有人不能拒绝提出文书。1.当事人自己持有并且已经在诉讼中引用的文书。2.举证人有权请求持有人交付文书或阅览文书。3.制作该文书是为了保护举证者的利益,或者该文书记载了举证者与文书持有人的法律关系的相关内容。4.除了以上三种情形之外,如果被申请文书不具备以下任何一种情形,则持有人也不能拒绝提出文书。イ、被申请文书记载了有关文书持有人,或者与文书持有人有196条各号规定的关系的人的196条中规定的各事项。ロ、文书内容有关公务员的职业秘密,并且提出该文书有可能会危害公共利益或者显著妨害公务执行。ハ、文书记载了第197条第1项第2号的事实,或者记载了197条第1项第3号规定的事项,且未被免除保密义务的。ニ、专供持有人使用的文书(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持有的文书中,公务员组织性使用文书除外)。オ、有关刑事事件的诉讼文书或者未成年人保护案件笔录及此类事件中扣押的文书。1~3即220条的1至3号规定,4即220条4号规定。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96条(拒绝作证的权利):当证人证言涉及的内容有可能使证人,或与证人有本条以下关系的人受到刑事追诉,或者使其受到有罪判决时,证人可以拒绝作证。证言中含有可能损害以下人员名誉的事项时同样处理:1.是证人的配偶,或者与证人具有四等内的血亲关系,又或者是证人的三等内姻亲及曾是证人的三等内姻亲。2.是证人的监护人或者被监护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97条第1项:以下情形下,证人可以拒绝作证。1.符合第191条第一项规定时。2.医师、药剂师、医药品贩卖者、助产士、律师(包括外国法律事务律师)、专利代理人、辩护人、公证人、宗教人士、负责祈祷或祭祀的人员或者曾经负责祈祷和祭祀的人员等,由于其职业而获知的事实,并且就该事实具有保密义务,但却就该事实接受盘问时。(第197条第1项第2号)3.就有关技术秘密或职业秘密的事项接受盘问时。(197条第1项第3号)——译者注提起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时,必须明确以下事项:①文书的标示(可以使文书得以确定的形式要件,如文书的标题等);②文书的要旨;③文书持有人;④文书欲证明的事项;⑤按照法律规定,文书持有人负有的文书提出义务(221条第1项~5项内容)。若当事人依据220条4号规定申请文书提出命令,则除了以上①~⑤外,还必须满足第六项要件,即⑥使用文书提出命令的必要性(221条第6项内容)。[1]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下述三种方式提出书证:1.直接提交书证;2.申请文书提出命令,强制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提交其持有的书证;3.申请文书的委托提交,委托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提出其持有的书证(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19条、226条)。文书提出命令与文书的委托提出的区别在于,文书提出命令具有强制性。而文书的委托提出则为任意提出,不具有强制性。日本民事诉讼法221条规定,举证人依据220条4号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必须证明使用文书提出命令的必要性。——译者注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文书提出命令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民事诉讼规则140条1项),因此以上事项同时也是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书的必要记载事项。[2]旧法时,申请人以口头方式申请文书提出命令虽然是可能的(旧法150条),但基于主张具体事实以赋予旧法312条根据的必要性,及使这些具体事实与证明资料相关联的主张的必要性等方面的要求,使得现实事件中的文书提出命令均是以书面形式进行申请。随着220条规定对文书提出义务范围的扩大,现行法下对文书提出命令申请的审查判断变得愈发复杂,可以想见基于该条产生的事实主张也将变得愈发详细。因此才设置了民事诉讼规则140条第一项,明确规定文书提出命令申请的审理程序。参照《条解民事诉讼规则》二九七页。
上述①至⑥的必要记载事项中,⑥是现行法新创设的规定。①至⑤虽然只是简单地将旧法313条的各号规定从古文转换为现代文,但是与旧法相比,新法下的①至⑤中的某些法律解释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在以下方面予以重新讨论。第一,①、②规定的目的在于具体确定申请的对象文书。但是,当申请人依新法规定的文书特定程序[3]日本民事诉讼法222条(文书特定程序):①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如果明确前条第一项第一号及第二号的记载事项有显著困难,申请人可以以明确该文书的其他相关事项代替前条第一项的第一号及第二号。但是该其他事项的明确必须能够使文书持有人识别对象文书。这时,申请人应向裁判所提出申请,请求裁判所要求文书持有人明确该文书的前条第一项第一号及第二号内容。②申请人依据前项规定向裁判所提出申请时,除申请明显没有理由外,裁判所可以要求文书持有人明确前项规定后段中所言事项。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法律对文书特定的要求显然会发生程度上的变化。第二,新创设的第224条第3项规定了文书持有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时的法律后果。但是这一规定的前提是,未能具体主张对象文书记载了何种内容的申请也有可能被认为合法。因此,这一规定的创设是否会对①、②项规定的解释产生影响也将成为问题。第三,新创设的220条4号并未要求当事人与文书具有某种积极关系,而只是要求对象文书不存在イ至ハ中规定的除外事由[4]“イ至ハ……”日本文章的逻辑排列方法之一。类似“1至3……”“a至c……”等表述方法。——译者注。因此,当申请人依据220条4号规定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对必要
222条②中的“裁判所可以要求文书持有人明确前项规定后段中所言事项”即222条第一项第一号的“文书的标示”及第二号的“文书的主旨”。——译者注记载事项中的第⑤项要求应作相应的特别考察。
2.关于“文书的标示”及“文书的要旨”
(1)文书特定责任
221条第1项第1号中规定的“文书标示”是指,文书的标题、制作者[1]当事人提出文书作为书证时,除非从该文书记载的内容中能够明确得知文书制作者,否则必须在证据说明书中明确记载该文书的目录及制作者。、类别、制作日期等能够使对象文书得以特定的事项。同条同项2号的“文书的要旨”是指文书记载内容的概略要点。当仅依“文书标示”并不能充分具体地特定对象文书时,便可以通过“文书要旨”来补充完成对象文书的特定。[2]所谓的“文书的标示”及“文书的主旨”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区分,而且也并不具有非区分不可的实际益处。司法实务中,将二者一并记载于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书中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因此,这两项规定在具有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使某一对象文书得到特定这一机能的同时,也意味着申请人负有特定某对象文书的责任。但是,由于文书提出命令的对象文书是处于他人支配之下,所以申请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轻易地完成文书特定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对申请人的文书特定责任作过于严苛的要求,有时会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强加于申请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现行法新设了222条文书特定程序,以期减轻当事人的文书特定责任。因此,如果当事人申请利用文书特定程序,那么申请人的文书特定责任与普通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时相比必然会产生差异。
(2)申请人未申请利用文书特定程序
申请人只是申请文书提出命令,并未申请文书特定程序时,对“文书标示”及“文书要旨”的记载要求原则上应按照传统观点进行解释。即,有关这两项事项的记载,原则上必须具体到能够使对象文书充分特定的程度。但是,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留意:
[a]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如果申请人无法参与对象文书的制作过程,或者没有任何机会了解该文书的记载内容,那么要求申请人完成严格的文书特定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证据呈现构造型偏在特征的现代型诉讼中,这一问题已经显示出类型化特征。因此,在昭和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随着申请文书提出命令的证据偏在型案件数量的骤增,裁判所接连作出多项决定,对未能充分完成文书特定责任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的合法性予以肯定,[1]高松高决昭和五〇年七月一七日诉月二一卷九号一九二七页,东京高决昭和五〇年八月七日下民二六卷五—八号六八六页,浦和地决昭和四七年一月二七日判时六五五号一一页等。理论界支持这种倾向的学说也成为旧法下的有力学说。[2]竹下守夫:《摸索的な証明と文書提出命令違反の効果》,《吉川追悼·手続法の理論と実践(下)》(法律文化社,一九八一)一七二页。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现行法下,当申请人难以严格地完成特定对象文书的责任时,是否也应沿用旧法观点,对申请人的文书特定要求作较为宽缓的解释?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现行法222条文书特定程序[3]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1条(文书提出命令申请):1.提出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时,必须明确以下内容。①文书的标示。②文书的要旨。③文书持有人。④文书欲证明的事实。⑤文书持有人负有的文书提出义务。2.依前条(220条,译者注)第四号规定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必须具有使用文书提出命令的必要性。——译者注正是基于上述情形所设定,因此申请人应首先考虑利用文书特定程序。在申请人没有申请利用文书特定程序,而对象文书又未实现充分特定时,申请将不再被允许。可是,假如申请人虽然并未完成对象文书的充分具体特定,但已经明确了文书的某些事项。而文书持有人可以根据这些事项,利用自己的知识及掌握的信息识别对象文书,那么即使裁判所肯定其申请的合法性,也不会给文书持有人造成显著的不利益。另外,文书特定程序只是一种宽缓的制度,并不具有直接的制裁性。如果把这一规定理解为法律要求申请人在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必须经常性地利用文书特定程序的话,无异于强加给申请人不必要的负担(具体论述参照文书特定程序部分)。
因此,申请人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即使对象文书没有达到充分具体特定,申请人也并未同时申请利用文书特定程序,只要可以认定申请人特定对象文书时有显著困难的情形,并且依据申请人已明确的事项内容文书持有人可以识别该文书,那么便可以认为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4]森義之ほか《証拠調べⅡ》判タ九六五号(一九九八年)六页。但是,基于裁判所行使释明权的一贯性要求,在某些场合下,也可以通过裁判所对申请人进行释明,催促申请人利用文书特定程序。
[b]现行法强化了文书持有人不遵守文书提出命令及妨碍文书使用时的法律责任。当申请人具体主张文书记载内容确有显著困难,而文书持有人又不遵守文书提出命令或有其他妨害该文书使用的情形时,裁判所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1]译者注:此处的对方当事人为申请人。所主张的、本应由对象文书证明的事实真实存在(224条[2]译者注:日本民事诉讼法224条(当事人不遵守文书提出命令的后果):1.当事人不遵守文书提出命令时,裁判所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关于文书记载内容的主张真实存在。2.当事人为了阻碍对方当事人使用,而使自己持有的具有提出义务的文书毁损灭失,或者采取其他行为使该文书不能使用的,按前款规定处理。3.前两项规定的情形下,如果对方当事人难以就文书记载内容提出具体主张,并且由该文书证明的事实很难用其他证据证明时,裁判所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对该事实的主张真实存在。3项)。这一规定的前提显然是,即使申请人不能就对象文书的记载内容作出明确具体的主张,裁判所也有可能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基于这一新设规定,申请人的文书特定责任可以作出比旧法更为宽缓的解释。这是因为,如果在申请书记载事项中对文书特定作过于严格的要求,那么224条第3项的规定便几乎没有适用的余地。因此有意见认为,申请人的文书特定即使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概括性,也应视其已满足了法律要求。[3]大村雅彦:《文書提出命令⑥——発令手続きと制裁》,《新民诉大系3》二二六页。
很显然,作为申请书记载事项的“文书标示”及“文书要旨”,法律确实不会要求其具体特定到使224条3项无法适用的程度,但也不能因此便轻率地解释为从224条3项的规定中可以推导出法律对文书特定程度的要求。这是因为224条3项所谓的文书记载内容的具体主张,是指依据224条1项、2项规定作出的真实拟制的事实,而这一事实通常比文书特定要件中的“文书标示”及“文书要旨”更为具体。因此,法律虽然不会要求申请书记载事项具体特定到使224条第3项无法适用的程度,但仍然要求对象文书能够特定。从这个意义上讲,224条3项的规定并不会对文书特定责任产生直接影响。[4]旧法时有观点指出,法律对“文书要旨”的记载要求,并非是出于持有人违反文书提出命令时的设想,法院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后,也不会经常发生持有人不提出文书的问题。因此,即使在适用当时的316条及317条时,有关“文书要旨”的记载有可能会成为认定对方当事人观点真实的资料,但仍然应当将申请书记载事项是否充分与该项记载对适用316条、317条是否有帮助作为不同的问题来考虑。这一观点即使在现行法下也依然具有合理性。
(3)申请人申请利用文书特定程序
申请人在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也申请了文书特定程序的,只要申请书中有关该文书的记载事项能够使文书持有人识别该文书,该申请便被认为符合法律规定(222条1项)。这里所说的“使持有人能够识别文书的事项”,其具体性要求可以比“文书标示”及“文书要旨”低,即,申请阶段的文书特定的要求已经趋向缓和。[1]参见《一问一答》二六〇页。但是过于抽象概括,以致文书持有人根本无从识别对象文书的申请显然也并不符合法律要求。因此,即使申请人申请了文书特定程序,申请书记载事项仍需具有一定程度的具体性。关于“一定程度的具体性”的具体内容,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识别可能性”部分予以论述。
3.依220条4号规定提起的申请
220条4号规定的一般文书提出义务是现行法新设的产物。如果申请人依这一规定申请文书提出命令,则裁判所在审查申请书记载事项时,应与其他文书提出义务相区别,作个别考察。
(1)关于“文书提出义务原因”。《民事诉讼法》第220条1号至3号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与对象文书之间应具有的特别关系,即文书持有人产生文书提出义务的要件。因此,依据1—3号规定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为满足220条第1项第5号规定的要求,申请书中必须明确记载足以表明当事人与对象文书之间具有特别关系的具体事实。与此相反,220条4号规定的则是不问当事人与对象文书有无特别关系的一般提出义务。因此,依据220条4号规定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申请人很难在申请书中明确记载提出义务的原因,因此有无イ至ハ中规定的除外事由就成为记载事项中的重要问题。[2]大村雅彦:《文書提出命令⑥——発令手続きと制裁》二二七页。通说认为,除外事由的证明责任应由申请人承担。[3]有关应由申请人负证明责任的观点,参见《一问一答》二五六页;田原睦夫:《文書提出義務の範囲と不提出の効果》ジュリ一〇九八号(一九九六)六三页;竹下守夫:《新民事訴訟法と証拠収集制度》,《法学教室》一九六号(一九九七)一九页;伊藤·三六二页;松本=上野·三〇〇页など。因此,申请人就不存在220条4号规定的除外情形负有证明责任。不过,即使由文书持有人负除外事由的证明责任,[4]应由文书持有人负有除外事由的证明责任的观点,参见佐藤彰一《証拠収集》法时六八卷一一号(一九九六)一九页,石田秀博《証拠収集制度の改革》自正四八卷三号(一九九七)八八页等。从与221条5号规定(无论哪种提出义务,申请人在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都必须将持有人负有文书提出义务的原因作为必要记载事项记入申请书)及221条2项规定(依据220条4号规定申请文书提出命令的,该申请必须具有补充性)的整合性上来看,不存在法律规定的除外事由这一主张责任也应由申请人承担。只是这种情况下法律将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进行了分离。[1]即使以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的一致原则为前提,也可以通过立法将除外事由的证明责任分别赋予不同的当事人。参见中野《现在问题》二一六页、二二一页。
这样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便是申请书的记载内容及其具体程度。毋庸多言,证明不存在法律规定的除外事由的具体事实自然应是申请书的记载事项。除此之外,对象文书作为证据的重要性及替代证据的提出困难性等也应成为记载内容之一。这是因为,在旧民事诉讼法时期的判例中,裁判所在判断“技术·职业秘密”及“自己使用文书”等时便已经会考虑对象文书在该诉讼中的重要性以及提出代替证据的困难性等内容,[2]参见仙台地决平成五年三月一二日判タイ八一八号七〇页、仙台高决平成五年五月一二日判时一四六〇号三八页等。另外,札幌高决昭和五四年八月三一日下民三〇卷五一八号四〇三页中记载了以比较衡量的方法判断是否具有旧法二八一条一项三号规定的拒绝作证的权利的判例。现行法则正式立法肯定了“技术·职业秘密”及“自己使用文书”是法律认可的除外事由。旧法下的有力学说,也支持司法实务中这一倾向。[3]学术界中有观点认为,应在进行包括诉讼法考量在内的综合衡量后,再对是否具有文书提出义务作出判断。参照小岛武司《判批》判时五八四号(一九七〇)一二八页,小林秀之《民事審判の審理》(有斐阁·一九八七)二三二页。适用新法以来的多数见解认为,有关220条4号イ乃至ハ项规定的除外事由的证明责任,应结合考察诉讼物及诉讼争点的特性后相对决定的观点。[4]《新堂》五一一页。竹下教授认为,有关イ项的除外事由,持有人是否具有提出义务这一判断本身并不包含利益衡量,但在判断是否具有侵犯名誉权的情形时会加入一定程度的利益衡量因素。这种利益衡量必然会反射回文书提出义务的判断中,因此有关持有人是否具有文书提出义务也可以在这一范围内进行利益衡量。另外,有关ハ项的除外事由中,对象文书是否自己使用文书这一点,必须结合诉讼物及争点的特点相对地判断。参见《研究会〈17〉》ジュリ一一二五号(一九九七)一一九页、一二二页“竹下守夫发言”。笔者也认为,在判断举证人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除外事由时,应综合衡量对象文书在该诉讼中的必要性等因素之后决定,不应仅从除外事由的客观性质一概而论。关于记载事项内容的具体化程度,由于申请人通常很难提出该文书不具有“涉及持有人技术·职业秘密”的内容,或者该文书不是“专供持有人自己使用的文书”等具体主张,所以申请人只要能够从自己掌握的信息中合理推测出该文书的有关事项并在申请书中予以载明,或者申请人已在申请书中记载了该文书的概略事项,就可以视为该申请已经满足了法律要求。[5]参见大村雅彦《文書提出命令⑥——発令手続きと制裁》,《新民诉大系3》二二七页。因此,当申请书中已经大致载明了该文书的概略事项时,如持有人不想提交对象文书,则需就该文书记载中具有法律规定的除外事由作出具体主张。
(2)文书提出命令的必要性
法律要求,依据220条4号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必须具备必要性(221条2项)要件,即申请人申请文书提出命令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本应由举证者负提出义务的证据,通过裁判所的文书提出命令,会转变为强制他人提出。这便可能导致举证者对其可以自行收集提出的证据也不付出努力收集提出,而只是一味依靠文书提出命令将自己的证据提出责任转嫁给他人。很明显,这于文书持有人而言有失公平。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220条4号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作为证据提出方式(219条)应该是具有补充性的。而依据220条1号至3号规定申请的文书提出命令则不要求这种补充性。这是因为,依1号至3号规定申请的文书提出命令要求当事人与对象文书之间具有某种特别关系,这便使文书提出命令的必要性要求已然包含于其义务要件之中。[1]《一问一答》二五七页。
关于欠缺必要性要件的情形,立法负责人作了如下举例说明:依法令可以获得的文书,如登记簿等,以及通常情况下容易获得的文书,比如可以在有关机关复制的文书或者公开发行的书籍等。[2]《一问一答》二五七页。另外,可轻易地从文书持有人处获得的文书也不具有必要性要件。从上述实例中可以看到,多数情况下判断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是否满足必要性要件并非十分困难,因此司法实务中必要性要件的证明责任成为问题的情况也很少见。但是,如果用其他方式也可以获取对象文书,只不过会为此花费过大的成本或者存在事实上的困难时,则必须衡量情势后才能对是否具有必要性要件作出判断,这种情形下的必要性要件证明责任也会随之成为问题。从文书提出命令的补充性要求来看,应由申请人承担必要性要件的证明责任。此外,无论证明责任归属于哪一方,必要性要件的主张责任都应由申请人承担。这一点与220条4号イ至ハ的除外事由的规定并无二致。只是如果从221条1项各号的记载事项中可以当然推导出必要性要件,则可以认为必要性要件已经得到了主张。
二、文书特定程序
1.总说
申请人在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负有使对象文书具体特定的责任。即,法律要求,通过“文书标示”及“文书要旨”(221条1项1号2号)等事项的记载必须使对象文书能够具体确定。欠缺具体特定性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相应地也欠缺合法性。但是,当申请人无法参与文书制作过程,或者没有机会参与文书中所记载事项的经过时,要求申请人具体地确定文书内容未免强人所难。因此,为了使申请人能够具体地确定对象文书,日本在制定现行民事诉讼法时曾探讨过以英格兰的法律开示制度为原型,创设强制文书持有人开示信息的强制信息开示程序。[1]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民事訴訟手続きに関する検討事項》三二页《別冊NBL23号(商事法務研究会·一九九一)所収》或者参照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民事訴訟手続に関する改正要綱試案》二三页《別冊NBL27号(商事法務研究会·一九九四)所収》。但是,立法者担心建立这一制度会使司法实务发生过于重大的改变,而且现实中这一提案也遭到了一部分相关者的强烈反对。最后,各方通过讨论达成合意,代替强制信息开示程序导入文书特定程序,以期达到减缓申请人的文书特定义务之目的。由此,现行《民事诉讼法》222条的文书特定程序得以创设。[2]关于这一经过,请参照三木浩一《文書提出命令④——文書特定手続》,《新民诉大系3》一八二页以下内容。
文书特定程序的立法主旨如下:申请人向裁判所提出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时,如果申请人具体特定文书确有显著困难,则可以向裁判所申请利用文书特定程序。申请人申请文书特定程序后,在文书提出命令申请的审查阶段,法律允许申请人用使文书持有人能够识别文书的其他事项代替法律规定的必须事项(即“文书标示”及“文书要旨”)。只要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明确记载的事项能够使文书所有人识别对象文书,裁判所就不能以未履行文书特定义务为由驳回当事人的申请。除非申请人的申请明显没有理由必须立即驳回,否则裁判所均可暂时受理文书提出命令申请,并要求文书持有人明确文书特定所需要的必要事项。文书持有人应裁判所要求明确了文书必要记载事项后,申请人可补正文书提出命令申请,裁判所可以依据补正后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发出文书提出命令。但是,使用了文书特定程序仍不能完成文书特定时,裁判所必须驳回申请人的申请。[1]《一问一答》二五九页。
在运用文书特定程序时,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申请人特定文书具有显著困难具体是指何种情形(特定困难性)。②使文书所有人能够识别文书的事项是指何种事项(识别可能性)。③何种情形下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明显没有理由(即时驳回的要件)。④文书所有人不配合裁判所的特定要求的后果(不开示的法效果)等。
2.特定困难性
由于文书提出命令是一种申请提出他人支配下的文书的制度,因此申请人特定文书时自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基于这一考虑,222条1项中的特定困难性加入了“显著”这一字眼。[2]《一问一答》二六一页。即,只是单纯的一定程度的特定困难是不足以满足特定困难性要件的。只有申请人进行了符合期待的合理努力后仍不能特定文书时,特定困难性这一要件才得以满足。如下几种情况下申请人特定文书具有显著困难的:申请人是文书的“外部人员”,没有机会参与文书制作过程,也没有机会得知文书记载内容;申请人虽然是“内部人员”,也有可能参与文书制作过程,但实际上完全没有参与该文书的制作;申请人与文书中所记载事件的经过没有任何关联。不论古典型纷争还是现代型纷争,只要存在以上几种情形之一,都可以认为已满足特定困难性这一要求。具体说来,行政诉讼、劳动诉讼、公益诉讼、产品责任诉讼、医疗事故诉讼、药品诉讼、建筑纷争诉讼、知识产权诉讼等领域里存在较多的文书特定显著困难的情形。
但是,申请人并非只有文书特定程序这一种手段才可以获得特定文书所需信息。某些时候,通过当事人照会(163条)、律师照会(律师法23条2)、证人询问(190条以下)、当事人讯问(207条以下)等方式,申请人也可以获得特定文书所需要的信息。因此,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所谓的显著困难性,是否意味着以上的手段全部用尽后才能申请利用文书特定程序。笔者认为,不应当仅因以上手段没有用尽便即刻认为申请不具有文书特定的显著困难性。这是因为,如果裁判所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期待文书持有人协助申请人特定对象文书,那么坚持要求申请人用尽以上手段后才可申请文书特定程序的做法,非但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反而会给文书所有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1]《一问一答》二六一页。当然,如果通过以上其他手段可以轻易获得文书特定所需信息,那么手段未用尽这一事实便有可能成为否定显著困难性的有力证据。相反,申请人通过当事人照会等手段为特定文书做了充分努力,但由于文书所有人的妨害行为,文书特定最后以失败告终,那么这一事实也会成为肯定特定困难性的依据。另外,也应允许个别情况下依据诉讼上的信义原则(2条)减轻申请人的特定责任。[2]三木浩一:《文書提出命令④——文書特定手続》,《新民诉大系3》一九五页以下。
3.识别可能性
第222条第1项中规定,当申请人明确文书标示及文书要旨具有显著困难时,应减轻申请阶段申请人的文书特定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申请人的文书特定责任将得到完全免除,而是指可以通过记载某些使文书持有人能够识别对象文书(识别可能事项)的事项而代替文书标示及文书要旨的记载。从抽象意义上讲,这里所说的识别可能事项是指这样一些事项:通过对这些事项的明确记载,文书所有人不必花费不合理的时间及劳动便可以将对象文书与其他文书相区别,或者将包括对象文书在内的某组文书与其他组文书相区别。[3]《一问一答》二六二页。一般情况下,对象文书所属的“文书范畴”可以被认为是识别可能事项。[4]三木浩一:《文書提出命令④——文書特定手続》,《新民诉大系3》一九七页以下。旧法下曾有通过提示对象文书的范畴而要求法院发出文书提出命令的案例。如,某特定原子能发电所建设纠纷中电力公司在一定期间内向国家提交的调查资料;某一航空飞机事故中,事故调查委员会制作的事故调查报告书等。[5]三木浩一:《文書提出命令④——文書特定手続》,《新民诉大系3》一九八页以下。当事人依据新法申请文书特定程序时,可以提示上述事项作为新法222条1项所说的识别可能事项,进而申请文书提出命令。
至于文书持有人是否会为识别特定文书支付不合理的时间和劳动,则因申请人特定文书的努力程度、持有人对文书范畴及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申请人与持有人的关系及纠纷原委等多种要素而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即,所谓的识别可能性,只是为了在文书特定时为寻求申请人负担与持有人负担的调和点而使用的一个衡量性的概念。因此,在判断文书特定申请是否满足识别可能性要件时,裁判所应综合考虑申请方及文书持有人的具体情况,相应地作出判断。[1]三木浩一:《文書提出命令④——文書特定手続》,《新民诉大系3》一九七页以下。比如,由于不能归责于申请人的原因而使申请人特定文书的负担过高时,可以相应地提高持有人的识别文书的负担。此外,当文书持有人拥有较多的文书特定信息,只须通过合理推测就有可能发现申请人所求文书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申请人的文书特定要求。
4.即时不受理决定的要件
如果申请人的申请明显没有理由,即使申请人提出了文书特定程序申请,裁判所也不能开始文书特定程序,而必须立即作出不受理决定(222条2项)。这是因为,文书特定程序只是缓和文书特定责任这一要件的特别程序,当缺乏其他要件致使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明显没有理由时,就已经没有必要适用文书特定程序了。具体说来,符合以下情形时,裁判所可以立即作出不受理决定:①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欠缺221条1项3号至5号的形式要件;②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欠缺221条2项的必要性要件;③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文书持有人持有文书;④该文书已经明显没有必要进行证据调查,也不需要进行特定(181条1项);⑤不需要经过文书特定便已明确该文书不具有220条各号规定的提出义务等。[2]《一问一答》二六二页以下。相反,如果申请人提示的文书范畴只是文书含量过大,可能使文书持有人为特定文书花费过多的费用及时间,则裁判所只能要求申请人将文书范畴缩减到所有人能够合理负担的范围内,而不能立即作出不受理决定。只有当申请人不按要求缩减文书范畴时,裁判所才能作出不受理决定。[3]三木浩一:《文書提出命令④——文書特定手続》,《新民诉大系3》二〇二页以下。
5.不开示的法律效果
当申请人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满足222条1项要件时,裁判所可以要求文书持有人开示特定文书所需要的相应信息(222条2项)。但是这种情形下的裁判所的特定信息开示请求权以及文书持有人的回答义务并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根据,只能作如下三种理论上的解释:首先,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释明权的行使方式。但是,222条2项的开示请求权中的文书持有人也包括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因此这一解释并不符合传统释明权概念的要求。其次,也可以认为这是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文书持有人的协助诉讼义务。但是文书持有人是诉外第三人时,能否认定其具有协助诉讼义务本身尚存有疑问。[1]中野教授认为,文书特定程序制度的根据在于程序上信义原则(中野:《解说》五四页)。可是文书持有人是诉外第三人的时候,为何持有人和诉外第三人间会发生程序上的信义原则的效果,有关这一点的解释说明并不明确。因此,笔者认为,文书持有人对法院的开示请求具有回答义务的理论根据在于:与证人义务、忍受检查义务等一般公法义务相同,文书持有人也应负有回应裁判所信息开示请求的一般公法义务。[2]三木浩一:《文書提出命令④——文書特定手続》,《新民诉大系3》二〇二页以下。这是因为,文书特定所需要的相关信息是文书提出命令不可或缺的前提,而现行法下的文书提出义务已经成为一般公法义务(220条4号),因此作为其前提的信息开示义务自然也应该是一般公法义务。
但是,即使文书持有人违反回答义务拒绝开示相应信息,法律对此也并无直接的制裁规定。那么,如果持有人拒绝信息开示使文书最终不能特定时,裁判所是不是只能作出不受理决定呢?各界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意见分歧。负责立法的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办公室认为,这种情形下只能对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作出不受理决定。[3]《一问一答》二六三页。另,《研究会(17)》一二七页以下“柳田发言”。但是如果这类情形均以不受理决定处理,则申请人有可能被课以较之旧法实务中更为严格的文书特定责任,[4]旧法实务中,即使文书特定的程度相当概括,裁判所也可以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参见三木浩一《文書提出命令④——文書特定手続》,《新民诉大系3》一七九页以下、福永有利ほか《民事訴訟手続改正に関する要網試案の検討》民商一一〇卷四·五号(一九九四)四七页“倉田卓次发言”等。与创设文书特定程序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因此,有学说认为当持有人拒绝信息开示时,在综合研讨申请内容及案件情况的基础之上,裁判所可以视情形认定222条1项的申请已经完成了文书的充分特定并发出文书提出命令。[5]田原睦夫《文書提出義務の範囲と不提出の効果》ジュリ一〇九八号(一九九六)六五页。《研究会(17)》一二八页“秋山发言”。但是,理论上只有文书不能充分特定时,裁判所才能够依据222条2项的规定要求持有人开示特定文书所需信息。因此,视222条1项的申请已满足了文书充分特定要求的观点,严格来讲是一种理论上的矛盾。
综上,当持有人拒绝开示信息时,裁判所在对申请内容、文书特定的困难性程度、申请人为文书特定而付出的努力程度、识别可能性程度、文书的证据价值、持有人的具体情况、用其他手段获得相应信息的可能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之后,即使文书特定并未达到具体特定的程度(但达到了文书范畴特定的程度),也可以视情况发出文书提出命令。[1]参照三木浩一《文書提出命令④——文書特定手続》,《新民诉大系3》二〇五页以下。同样见解的其他文献可参照中野《解说》五四页,大村雅彦《新民事訴訟法とアメリカ法——争点整理·証拠収集の比較を中心として》自正四八卷一二号(一九九七)九〇页以下、京都シミュレーション新民事诉讼研究会《文書提出命令の申し立てとその審理》判タ九七四号(一九九八)一一页等。法律对此也应作出正面的肯定。当然,这种观点或许并不符合立法当局的意愿,但是不这样解释会导致无法达成文书特定责任的缓和。而缓和文书特定责任正是创设文书特定程序的目的所在,因此,过于拘泥于立法当局的意愿反而会与立法宗旨南辕北辙。另外,即便采取这种解释,222条1项的规定仍是以文书的识别可能性为要件的。所以即使仅以222条1项规定的特定程度发出文书提出命令,也不会给文书持有人带来显著不利益。[2]如果要追究本文不得不采取这一观点的原因,那么源头便要回溯到222条一项和二项的逻辑关系上。如果出于合理保护文书持有人的要求,那么只要向持有人提供足以识别对象文书的信息便已足够,因此既然已经在一项中规定了识别可能性要件,就没有必要再在二项中规定文书特定程序。从这一意义上讲,不得不说像《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三四条b项规定的那样,直接以识别可能性或文书目录的特定为要件,即刻发出文书提出命令的制度,在理论上更容易被理解。可是,出于立法上的妥协,现行法仍然导入了文书特定程序。这是因为,所谓的识别可能性,是介于特定与不特定之间的一个微妙的概念。如果以其为提出命令的直接要件,那么从警惕文书提出命令的机能过于扩大的立场来看是个威胁,裁判所的判断负担也会因此加重。所以,温缓的现行法并未采取这样激进的要件=效果,而是采取了以文书特定程序为新基轴的妥协方案。这便使现行法的文书特定程序变成一种不具有制裁措施的软性信息开示请求,以及文书持有人对这一请求进行半自发性回应为内容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只有在预设和谐的环境中才能充分发挥其机能。相反,如果申请人并未申请文书特定程序且只完成了识别可能程度的特定时,如果文书持有人采取脱离立法者设想的预设和谐模式的行动,比如无正当理由拒绝回应申请人的申请时,要想得出符合旧法实务及学说潮流的解决方案,就必须采取可能并不符合立法原意的法律解释。综上,笔者认为,当裁判所按某种特定的文书范畴发出文书提出命令时,文书持有人应提出文书范畴内的全部文书。另外,当持有人不遵从这一文书提出命令时,有关该文书范畴内的全部文书均可以适用224条及225条的制裁规定。
三、暗室程序
1.综述
申请人依据220条4号规定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由于该号规定认可的是一般文书的提出义务,因此裁判所审理申请人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时,审理对象并非是220条1至3号的当事人与对象文书之间的关系,而是对象文书是否具有220条4号规定的イ至ハ项除外事由。也就是说,裁判所审理依4号规定提起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时,必须审理判断该文书是否具有220条4号规定的イ及ロ的证言拒绝权的情形以及该文书是否为ハ项规定的自己使用文书。在审理是否具有以上除外事由时,文书具体记载了哪些内容便成为问题关键。而事实上裁判所很难在不看文书的情况下对此作出判断。裁判所只有在直接阅读文件后才能切实地对文书是否记载了文书提出命令的除外事由作出正确且迅速的判断。但是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将文书的记载内容向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披露,那么法律为保护文书中记载的秘密及个人隐私,特意规定イ至ハ项内容并将其文书提出义务排除的立法用意就会落空。
因此,现行法规定,当有必要对220条イ至ハ项规定的除外事由进行审理判断时,裁判所可以命令文书持有人提出该文书,但是任何人都不可以要求该文书开示[1]用于提出或提交对照笔迹或印章的文书,参照适用223条规定。另,223条3项内容在平成十三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成为现行民事诉讼法的223条6项。——译者注(223条3项)。另外,持有人提出文书后,裁判所认为必要时也可以由裁判所暂时保管该文书(《日本民事诉讼规则》141条)。基于这一规定与美国信息自由法(FOIA)中规定的裁判官室的非公开审理程序的相似性,这一程序从立法之初起多被称为暗室程序[2]《一问一答民事诉讼法》二六六页。。这里所说的223条3项后半段的“任何人均不得要求开示持有人依本条规定提出的文书”,不仅指与本案无关的人不能依据民事诉讼法91条的规定要求阅览、复制诉讼记录,以及其他的一般公众的文书开示请求也将不被允许,而且适用暗室程序时,这一程序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也不得公开。即,223条3项的暗室程序是一种只有裁判所能够阅读持有人依暗室程序提出的文书的审判程序。与此不同,美国信息自由法中的暗室程序则并不当然排除当事人代理人的同席[1]但是美国情报公开法的暗室程序审理实践中,几乎没有原告代理人的同席请求被允许的实例。宇贺克也《アメリカの情報公開(七)》自治研究七三卷三号(一九九七)四六页。,从这一意义上讲,日本的暗室程序与美国的暗室程序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概念。
2.暗室程序的运用
(1)关于补充性
有意见认为,实施暗室程序应遵循补充性原则[2]奥博司:《文書提出命令⑤——イン·カメラ手続》,《新民事诉讼法大系3》二一四页以下。(以下简称“补充性学说”)。即,只有在仅依靠申请人及文书持有人提出的主张和进行立证活动无法对是否具有除外事由作出判断时才能启用暗室程序。如有其他方法可以对对象文书是否具有除外事由作出判断,则不能使用暗室程序。这一见解以暗室程序不符合程序合法的要求因此不应被鼓励[3]奥博司:《文書提出命令⑤——イン·カメラ手続》,《新民事诉讼法大系3》二一五页,有关补充性原则的合理性只列举了一个原因,即暗室程序限制了当事人公开原则因此可能会侵害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为前提,主张如果通过间接证据的积累可以使裁判所对对象文书是否具有除外事由作出判断,那么就不应适用暗室程序。但是这一见解有可能受到以下批判:第一,补充性原则只着眼于暗室程序的程序合法性问题,但是暗室程序实施过程中的程序问题并非只要满足了程序合法性要求就都能够解决。第二,伴随暗室程序的一系列问题而产生的利害关系在各个案件中各不相同。补充性原则所主张的单一处理方式无法灵活对应各种情形。第三,裁判所本来就不能够无条件实施暗室程序,而是只有在裁判所“认为有必要时”才有可能实施该程序(223条3项)。因此是否有必要增加新的适用要件(补充性原则要件)值得推敲。[4]《研究会(18)》ジュリ一一二八号(一九九八)九二页“柳田幸三发言”。第四,如果在必要性要件上增加补充性要件,那么违反补充性要件实施的暗室程序将被认为当然违法。可是,用这种方式否定事实审裁判所[5]日本的裁判所分为事实审裁判所和法律审裁判所。事实审裁判所是指对案件事实予以审理认定的裁判所。在证据调查环节,事实审裁判所具有程序裁定权。——译者注在证据调查环节的程序裁量权是否合理同样存有疑问。由于以上这些对补充性原则的批判同时也是考虑运用暗室程序时的重点问题,因此有必要进行具体探讨。
一般认为暗室程序有以下问题:①由于申请人不能阅览暗室程序中的文书,因此暗室程序侵害了申请人的程序保障权利。②经过暗室程序后,即使裁判所判定持有人对该文书没有提出义务,但事实上也有可能已经形成了对该文书的心证。③暗室程序中有可能会混入有关证据必要性的判断(证据价值判断)。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并不简单。比如,①和③所指的问题多数情况下对申请人不利,而②中所指的问题多数情况下则是对持有人不利。只不过,在各个具体案件中暗室程序的这些利弊,随着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审理进程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考查暗室程序实际运行过程中当事人各方实际背负了何种不利益时,不可脱离案件具体情况一概而论。
另外,围绕上述问题点又附带产生了复杂的议论。比如①中所说,文书申请人在暗室程序中没有机会对持有人提出的文书发表意见。这于申请人而言确实不利。可是如果因此便放弃利用暗室程序,那么申请人则就“对象文书不具有法律规定的除外事由”负有证明责任,很显然对于申请人而言这种情况更为不利。关于第②点,有反对意见认为:刑事诉讼中也存在证据排除的规定(刑事诉讼规则207条),因此相信身为法律专家的裁判官可以作到心证分离。[1]《研究会(18)》ジュリ一一二八号(一九九八)九三页“福田刚久发言”。另外,人们一般认为事实上形成的心证似乎对文书持有人不利,但是有时候文书虽然具有秘密性,但其内容及因此形成的心证却是对持有人有利的。因此关于暗室程序中形成的裁判官的事实上的心证对诉讼各方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2]裁判官到底能否做到心证分离是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是裁判官在对案件进行判断时的一种心理准备,因此笔者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并无多少意义。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使用暗室程序会否使当事人产生法官能否公正审理案件的担心。关于第③点,既有意见认为应禁止在暗室程序中对对象文书的证据必要性进行判断,也有意见认为在暗室程序中彻底排除证据必要性判断的想法不具有现实性[参照本章2(3)部分论述],很难得出明快的答案。
如上所述,暗室程序的各问题点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实施暗室程序时,无论是申请人还是文书持有人都各有利弊。具体事件中哪一方当事人产生了何种不利益因事件不同而异。因此,笔者认为,脱离具体事件一味强调补充性原则并不具有建设性意义。事实上司法实践纷繁复杂,既存在视案件的具体内容及审理经过应暂不适用暗室程序的情形,也存在应该果断实施暗室程序的情形。具体案件具体属于何种情形,则应由受理诉讼的裁判所裁量判断。
(2)裁判所的裁量权及其界限
虽然裁判所具有是否适用暗室程序的裁量权,但正如223条3项所规定的,只有在难以判断是否具有除外事由,因而“有必要”适用暗室程序时才可以适用暗室程序。不符合必要性要件的申请不能适用暗室程序。但是,除非明显不具有适用暗室程序的客观必要性,否则“是否具有适用暗室程序的必要”终究仍是由裁判所裁量判断。也就是说,223条3项赋予了裁判所裁量决定是否适用暗室程序的权利,但同时也禁止裁判所在明显没有实施暗室程序的客观必要性时适用暗室程序。即,223条3项规定了裁判所适用暗室程序的裁量权,同时也规定了这一裁量权的界限。[1]竹下教授认为,不应提倡贸然运用暗室程序。在运用暗室程序之前必须进行何种程度的审理才是运用暗室程序时会遇到的问题。《研究会(18)》九二页,“竹下守夫发言”。因此,一般情况下裁判所裁量决定是否适用暗室程序并不存在违法问题。但是当裁判所的裁量超越法律规定的裁量权范围时则会产生违法问题。由于很难一般性地表述在何种情况下裁判所的裁量决定会超越法律规定的裁量权范围,所以我们可以先研究何种情况下裁判所可以积极实施裁量权。当然,不符合积极裁量权特征的裁量行为并不当然构成超越裁量权,只能说这些裁量行为具有超越裁量权的可能性。
以下情形应当积极实施暗室程序。即,当事人就对象文书中所记载的全部内容或者其中的某一部分不具有法律规定的除外事由的证明,已达到优势证据标准的盖然性要求(即,就除外事由不存在这一事实,申请人的主张及立证已达到优势证据原则的要求[2]竹下教授认为,裁判官在暗室程序中得出的有必要阅读对象文书的这一心证,以现有的心证概念来看,应是证据优越性这一程度的心证。参照竹下守夫《新民事訴訟法と証拠収集制度》,《法学教室》一九六号(一九九七)一九页。)。一般认为,为了对对象文书是否存在除外事由作出最终判断而使用暗室程序是妥当的。因此,当就对象文书不存在除外事由的证明没有达到优势证据所要求的盖然性标准便适用暗室程序时,或者裁判所虽然有其他手段可以就不存在除外事由作出判断,但裁判所却适用暗室程序时,都有可能构成超越裁量权。要求申请人对对象文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除外事由证明达到优势证据的盖然性标准,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并不希望在连基本程度的盖然性都不具备的情况下适用暗室程序,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对证明标准作出比优势证据更为严格的要求,那么暗室程序已经基本上没有适用的余地。另外,将不具有比暗室程序更为妥当的其他方法作为可积极实施暗室程序的条件,则是因为如前所述暗室程序具有种种无法否认的弊端。
关于代替暗室程序的其他妥当方法,补充性学说主张通过积累间接事实而对是否具有除外事由作出判断。[1]参照奥博司《文書提出命令⑤——イン·カメラ手続》,《新民事诉讼法大系3》二一五页、田辺诚《証拠収集手続について》,《民商法杂志》一一〇卷四·五号(一九九四)七二七页以下。确实,当通过积累的间接事实可以对对象文书是否具有除外事由作出判断时强行适用暗室程序明显并不妥当。但是,现行法之所以设立暗室程序本来就是因为有时候依靠积累的间接事实无法对是否具有除外事由作出判断。因此,很难期待只依靠积累间接事实便可以代替暗室程序。关于这一点,作为暗室程序的有效代替手段,后述美国信息自由法的司法实务中正在推行在库索引程序。日本民事诉讼中审理文书提出命令的除外事由时,也应检讨实施该程序的可能性。
(3)关于证据必要性的判断
民事诉讼法设立暗室程序的目的不是为了审理对象文书是否具有证据调查的必要性,而是为了方便裁判所审理判断申请人依220条4号提起的申请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除外事由,继而决定是否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因此,毫无疑义,法律不允许为判断对象文书是否具有证据必要性而使用暗室程序。但是,如果裁判所为判断是否具有除外事由而决定适用暗室程序,并在暗室程序适用过程中通过阅读持有人提出的文书判明该文书与本案无关,那么此时裁判所是否能以文书不具有证据必要性为由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呢?关于这一点,理论界颇有争议。否定说认为,暗室程序归根结底是为判断对象文书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除外事由而设置的,因此,即使裁判所阅读文书后认为该文书没有证据调查的必要,也不能以此为由驳回申请人的申请。[2]参照田原睦夫《文書提出義務の範囲と不提出の効果》ジュリスト一〇九八号(一九九六)六五页。另见,《研究会(18)》八九页“青山善充发言”。而肯定说则认为,证据必要性的判断与除外事由的判断在根本上无法彻底分开,暗室程序的调查结果反映有关证据必要性的判断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因此,暗室程序的调查结果中绝对不能包含证据必要性的判断这一观点未免失于偏激。[1]参照研究会(18)九十页“秋山乾男发言”。另外,竹下、铃木两位教授赞成秋山发言的这一观点。如果只考虑暗室程序的立法宗旨,那么否定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正如肯定说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在暗室程序中裁判所已判明没有必要对对象文书进行证据调查,而依照否定说则只要对象文书不具有除外事由裁判所就必须发出文书提出命令,那么这时裁判所应当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可是这种情况下即使裁判所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当事人已在暗室程序中得知该文书没有证据价值,自然也不会对文书提出命令及对象文书抱有期待。因此,笔者只能支持肯定说的观点。[2]奥博司在《文書提出命令⑤——イン·カメラ手続》,《新民诉大系3》二二〇页中论述道,裁判所一旦阅读了对象文书,确实很难将文书中得到的有关证据必要性的判断从心证中分离。
但是司法实务中有时也会出现更为深刻的问题。比如,实践中曾有这样的判例(注释54)[3]东京高裁决平成一〇年七月一六日金判一〇五五号三九页。:原告X认为Y侵害了自己的专利权,提起诉讼要求Y停止侵害。为了证明Y的侵害事实,X依220条4号规定申请文书提出命令,要求Y提出Y持有的一份文书。对于X的请求,Y则主张该文书记载了Y的技术秘密及涉及Y的职业秘密,拒绝提出该文书。因此,该文书能否依220条4号ロ[4]平成一三年日本民事诉讼法修改后,二二〇条四号ロ项变现行民事诉讼法二二〇条四号ハ项。——译者注的规定及197条1项3号的规定免除提出义务便成为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原审裁判所依据223条3项命令Y提示文书,并利用暗室程序进行了审理。通过暗室程序的审理,裁判所明确了以下事实:①该文书记载的方法与X的特许方法不同,②该文书记载的Y的方法中有应予保护的职业技术秘密。基于以上事实,裁判所驳回了X的申请。X不服裁判所的驳回决定,向上级法院上诉。上诉审适用暗室程序审理后,作出了实质上与原审相同的决定(部分驳回)。这一案例引发的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前述1的判断实际上是能够决定诉讼物[5]诉讼物是日本民事诉讼法中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概念。中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相对应的概念,笔者认为日本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物更接近于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译者注存在与否的证据评价。即,这一案例启示我们,暗室程序中不只是会牵涉到证据必要性的判断,而且有时这一证据判断甚至可能会轻易影响到对诉讼物存在与否的判断。另外,裁判所通过暗室程序阅读文书,得出该文书不能成为判断诉讼物存否的根据时,便可以合理推导出该文书不具有证据的必要性。由此,如采用肯定说,则暗室程序中的证据判断为法律所许可,那么裁判所的这一裁判便也合法。虽然以上逻辑也有勉强之处,但为了避免导致对没有证据价值的文书也发出提出命令,不得不承认裁判所的处断是合法的。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明确的是,虽然暗室程序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审理判断一般义务文书是否具有除外事由,但暗室程序在实践运用中也不可避免地可能会混入有关证据必要性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有时甚至会影响裁判所对诉讼物的判断。而且,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像普通的心证形成过程一样寄希望于裁判官的心理准备,因为裁判官即使依靠自己的良心也无法避免这一问题。如此看来,223条3项的暗室程序暗含着立法当初未能预料的副作用。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出现上述的不尽如人意的处理,笔者认为无论怎样都应当在司法实务中有意识地养成有效利用在库检索程序的习惯。
3.其他问题点
(1)3号文书与暗室程序
从法律条文的表述上可以明确得知暗室程序是为判断对象文书是否具有220条4号イ至ハ的除外事由而设置的程序。但是,220条3号文书是否也可以类推适用暗室程序呢?关于这一点,学者们的见解产生了分歧。[1]肯定说赞成220条3号文书类推适用暗室程序。参见山下孝之《文書提出命令②——弁護士から見た文書提出義務》,《新民诉大系3》一五一页、第二页京弁护士会民事诉讼改善研究委员会编《新民事訴訟法実務マニュアル》(判例タイムズ社·一九九七)一五八页以下《森脇純夫》、《研究会(17)》一一六页“铃木正裕发言”等。与此相对,否定说反对类推适用暗室程序。否定说是目前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的通说。参照《一问一答民事诉讼法》二六六页。理论上,这一问题取决于4号规定的除外事由是否可以类推适用于3号文书。如果4号规定的イ至ハ的除外事由同样适用于3号文书,那么用以审理4号イ至ハ的除外事由的暗室程序自然也应当适用或类推适用于3号文书。相反,如果4号规定的イ至ハ的除外事由不能适用于3号文书,那么裁判所审理文书持有人是否具有3号规定的文书提出义务时则与旧法时相同,最终也不过是直接类推适用证言拒绝权(196条、197条)或是考察该文书是不是“自己使用文书”(此处的“自己使用文书”与4号ハ的“自己使用文书”概念不同),那么便不应适用暗室程序。但是,现实中3号文书与4号文书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确。申请人针对同一文书申请文书提出命令,如果仅因偶然运用了3号规定或4号规定竟导致结论不同,[1]实务中,当事人在主张持有人负有提出义务的原因时,重叠主张二二十条三号、四号的情况应该也不少。《研究会(17)》一一七页“秋山发言”。那么也未免显得过于技巧性,这种解释自然也很难被认为是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当文书记载的内容有关持有人的秘密或隐私而该文书又实际上成为当事人双方的争点时,即使申请人是依3号规定提起的申请,只要裁判所认为运用暗室程序并无不妥,那么该文书就可以被认定为实质上符合4号规定的文书,可以适用暗室程序(这将导致除了“申请的4号文书”,“具有4号文书性质的文书”也将被认可)。理论上讲,这种解释无疑颠倒了法律要件与法律效果的关系。但是220条3号与4号的立法本身便为追求妥协而牺牲了理论上的整合性,而这也必然会反映在220条3号与4号的关系中,所以对这种不合理性我们除了包容别无选择。
(2)暗室程序与当事人的同意
第223条3项规定,暗室程序的审理对象只能是一般义务[2]译者注:220条4号规定的持有人的文书提出义务是一般的文书提出义务,所指文书为一般义务文书,也称一般文书。220条1号至3号规定的文书提出义务是限定的文书提出义务。文书的除外事由,审理方法也只能是由受诉法院的裁判官对持有人提出的文书阅读。那么当事人的合意是否可以扩大暗室程序的审理对象范围或者改变暗室程序的审理方法呢?比如,当事人达成合意运用暗室程序审理220条1号至3号文书的除外事由[3]森義之ほか《証拠調べⅡ》判例タイムズ九六五号(一九九八)七页中认为,在审理认定220条1号乃至3号文书是否具有提出义务时,如果持有人申请由裁判所单独阅读文书,而申请人也同意的话,那么事实上就可以适用暗室程序。;或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在暗室程序中就文书的证据必要性进行调查[4]青山教授认为,应允许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决定运用事实上的暗室程序来判断证据的必要性。参见《研究会(18)》八九页以下“青山发言”部分。;再或者文书持有人同意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参加暗室程序(当然,这种同意通常是以持有人与申请人达成秘密保护合意为前提);又或者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文书,双方当事人同意相关方面专家进入暗室程序对文书作出适当评价等。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合法性与适当性两个方面分析上述当事人合意的暗室程序的妥当性。首先,当事人合意的暗室程序在合法性上应该不存在问题。这是因为,如果暗室程序中背负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在法律允许不适用暗室程序时主动认可并同意适用暗室程序,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合意的暗室程序违法。相对于合法性,这种合意的暗室程序有时在适当性上会存有疑问。比如第1及第2种情形下当事人合意的暗室程序实质上是一种不规则程序,因其违反对审原则及公开审理原则,无论双方当事人如何同意,裁判所对这两种扩大审理对象的暗室程序都应审慎,只有在有特别必要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另外,第3及第4种情形下合意的暗室程序可能会涉及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秘密及个人隐私,因此当事人是否有同意适用暗室程序的权利、应该用何种程序如何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这种权利,以及当这一判断发生错误时应由谁承担责任等,这些问题都必须慎重考虑并予以事先解决。
(3)所有人不提出文书的后果
裁判所依据223条3项要求文书持有人提出文书时,持有人如果不按要求提出文书,法律并没有相应的制裁规定。关于这种情况的处理,通说认为除外事由的证明责任应由申请人承担,因此当文书持有人不回应裁判所的提出要求致使无法判明对象文书是否具有除外事由时,依证明责任原理便应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如此,则暗室程序实际上便难以发挥功能。而目前的有力说则认为,持有人不按照裁判所的要求提出文书这一事实本身便可以作为证据材料,推定该文书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可以不提出文书的除外事由。[1]参见奥博司《文書提出命令⑤——イン·カメラ手続》,《新民诉大系3》二二一页,《研究会(18)》九三页“福田发言”部分。这一见解认为,在裁判所要求持有人提出文书前,关于该文书是否具有除外事由,裁判所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心证。但是,如果文书持有人拒绝提交文书并且不能提出合理理由,那么便可以认为有关除外事由不存在的事实,裁判所已经形成了具有高度盖然性心证,并且这一心证因为持有人拒绝提交文书这一行为而得到推定。笔者基本赞成这一观点。另外,有见解认为,由于暗室程序以当事人对裁判所的信赖为前提,因此“文书内容不适宜被裁判官得知”并不能成为拒绝提交文书的合理理由,只有文书内容涉及国家的安定秩序等特殊事由才能成为拒绝提交文书的合理理由。[2]参见《研究会(18)》九四页“伊藤真发言”部分。笔者也赞同这一主张。
4.在库索引程序
在库索引程序是在美国信息自由法(FOIA)相关诉讼中确立起来的审理程序,是裁判所用来判断某特定信息是否法律规定的非开示事项的方法之一。在库索引程序要求被请求开示信息的信息持有人(一般是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制作分项索引,即所谓的“在库索引”[1]关于美国信息自由法相关诉讼中的暗室程序及在库索引程序,松井茂记在《アメリカの情報公開法二》ジュリ一〇九二号(一九九六年)四五页、常本照树在《情報公開法と司法審査》ジュリ一一〇七号(一九九七)五九页以下作了概略介绍。。该索引要求信息持有人明确注明不能开示的信息,并说明该信息不能开示的理由。在库索引并没有固定的制作方法,一般情况下是由信息持有人制作一个详细的一览表,结合相应的法律规定注明不能开示的文书并说明不能开示的理由。在库索引中必须具有能够使申请人及裁判所阅读并理解的某文书不能开示的明确理由,并且只有此内容才是在库索引的必须内容。[2]参照行政改革委员会事务局监修《情报公开法要纲案(中间报告)》(第一法规·一九九六)二五二页。在库索引中并不要求具体记载有可能导致危害信息的秘密性及个人隐私的内容。
由于暗室程序中裁判官独自对持有人提出的文书进行阅览判断,因此会产生上述2(1)中所述的各种问题。而在库索引程序中,文书持有人可以在不开示文书内容的前提下,向申请人及裁判所示明不能开示的文书与法律规定的除外事由的关联性,因此在库索引程序被认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暗室程序的弊端。另外,运用暗室程序有时会因裁判所必须阅读大量的文书而导致诉讼迟延,而合理有效地利用在库索引程序则可以减轻裁判所的工作负担,实现审理的迅速化。因此,在美国的有关信息自由法的诉讼中,反而是运用在库索引程序进行审理成为原则。当案件通过在库索引程序得到充分审理后,就没有必要并且也不应当运用暗室程序了。[3]有关暗室程序是在库索引程序审理不充分时的最后手段这一论点,请参照 Hayden v.National Security Agency/Cent.Security Serv.,608 F.2d 1387(D.C.Cir.1979)等判决。
因此,一般认为,日本在审理对象文书是否具有提出命令的除外事由时,在裁判所听取文书持有人的意见之后,原则上也应该在暗室程序之前先适用在库索引程序。如果文书持有人要求适用在库索引程序,那么裁判所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这一要求。[1]有关在暗室程序之前应先运用当事人要求适用在库索引程序的观点,请参照坂本団《証拠収集制度の改革をめぐって》自正四八卷七号(一九九七)八四页以下、松浦正弘《文書提出命令の意義と課題》自正四八卷一〇号(一九九七)五六页等。与此相反,也有观点认为,很难一概而论在库索引程序与暗室程序到底孰优孰劣。[2]《研究会(18)》九二页“柳田发言”。另外,美国的司法实践已经确认了不讨论是否可能适用在库索引程序而直接适用暗室程序的做法并不妥当。笔者也认为,只要充分尊重了文书持有人的意见,那么实施在库索引程序不会对文书持有人产生显著不利益。因此,除个别的不适合适用在库索引程序或者适用在库索引程序会影响诉讼效率的特殊情况外(比如信息持有人制作在库索引的负担过重,或者持有人对文书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本身拒绝回答的情形),应当养成裁判所以利用在库索引程序为原则审理除外事由这一习惯。另外,日本如果导入在库索引程序,那么必须先明确在库索引程序在诉讼法上的地位。裁判所主动提示文书持有人申请在库索引程序的,可以视为裁判所实施的一种释明权行为。而裁判所必须尊重文书持有人适用在库索引程序这一要求的依据,则在于法律规定只有裁判所认为“有必要时”才可以实施暗室程序(223条3项)。顺及,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通过宣誓供述书提出在库索引程序的适用申请;日本民事诉讼法如果引入在库索引程序则大概会通过当事人的诉讼准备文书及陈述书提出该程序的利用请求。
四、针对文书的一部分的提出命令
1.综述
当对象文书中的某一部分被确认为没有提出必要或被确认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提出义务时,申请人能否就其他部分提出文书提出命令呢?关于这一问题,旧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确规定。学说和判例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假如文书中的一部分内容被确认为没有进行证据调查的必要或者被确认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提出义务,而文书的其他部分则被确认为具有证据调查的必要性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文书提出义务,那么就没有理由断言裁判所对该文书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发出文书提出命令。[1]参照《一问一答》二六四页、《研究会(18)》八二页“柳田发言”。因此,现行法明文规定,上述情况下,裁判所可以就文书中不具有证据调查必要及不具有文书提出义务的内容以外的部分发出文书提出命令。由于这一制度使涉及个人隐私及具有除外事项的文书在去除相应内容后的提出成为可能,因此不仅能保护文书持有人的利益,更具有积极促成法院发出文书提出命令[2]田原睦夫《文書提出義務の範囲と不提出の効果》ジュリ一〇九八号(一九九六)六四页。的效果。另外,双方就文书的某一部分是否具有除外事由,或者就去除某一部分内容后发出的文书提出命令是否妥当有争议时,可以适用暗室程序予以解决。
2.文书的一部分的含义
对于文书的一部分这一概念的理解,各论者间存在着细微差别。第一,不同作成名义的若干文书被装订成一个文书时,如果申请人对其中的某一作成名义文书提起文书提出命令,那么该文书作为装订合一的文书的一部分,可以适用文书提出命令。关于这一点,各论者间并无异议。[3]参照《研究会(18)》八五页“竹下发言”。第二,就一个单独作成名义文书中的特定页或特定事项提起文书提出命令时,如果该部分具有相对于其他部分的独立性,那么裁判所也可以就该部分发出提出命令。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将除外部分贴上可以事后取掉的标签并注明其为除外内容后,要求持有人提出文书原件,或者要求持有人将经过认证的文书副本中的除外部分涂黑后提交该副本(《民事诉讼规则》143条)。[4]参照条解民诉规则三〇五页。再或者在获得对方当事人及裁判所同意后,由持有人提出文件抄本(复印件等)。[5]参照《研究会(18)》八七页“柳田、福田各发言”。第三,对于是否可以在去除了文书中特定词汇或特写项目后(涂黑等)再命令持有人提出经认证的文书副本或者文书抄本,比如命令持有人在将会计账本中交易对方的名称、工资总账中的个人姓名、护理记录中有关其他患者的记载等去除后提出副本或抄本,则有肯定说和否定说等不同见解。[1]持肯定意见的见解参照《研究会(18)》八五页以下“竹下、秋山各发言”。持否定意见的观点参照《研究会(18)》“福田、柳田各发言”。另外大村雅彦在《文書提出命令⑥——発令手続と制裁》,《新民诉大系3》二三三页中,明确地表明了其肯定的立场。否定说重视原件提出主义及文书独立性的观点,认为这种方式的文书提出命令已不符合立法原意,对这种形式的文书提出命令予以否定。而肯定说则认为,在有些时候,这种方式的文书提出命令能够很好地调整保护秘密及个人隐私与查明案件真相这两个诉讼要求的关系,应予肯定。因此,除非因为删除相关事项会使文书内容改变,或者使文书失去原本的意义,否则,我们将认为223条1项的后半段内容同样认可了上述第三种方法的文书提出命令。[2]旧法下有判例命令持有人提出删除专有名词后的文书抄本。参见大阪地决昭和六一年五月二八日判时一二〇九号一六页(二件)、鸟取地决平成元年一月二五日诉月三六卷三号三三七页。但是,以上决定均在上诉审中被撤销。
(初审:巢志雄)
[1]作者三木浩一,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民事诉讼法、破产法、民事执行法、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等,代表作有《初めて学ぶ新民事訴訟法》、《初めて学ぶ破産法》、《ロースクール民事訴訟法》、《条解民事再生法》等,E-mail:koichi@law.keio.jp。
译者张慧敏,女,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民事法方向法学修士,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博士生,研究领域为诉讼法学,代表作有译文《日本民事诉讼法共同诉讼制度及理论——兼与中国制度的比较》等,E-mail:xiaomin81823@yahoo.co.jp。
感谢作者授权刊发本文中译版,原文出版信息:みきこういち:《文書提出命令の申し立ておよび審理手続》,载于竹下守夫编《讲座新民事诉讼法Ⅱ》(弘文堂,一九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