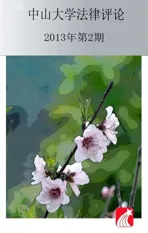法律适用中的形式逻辑与实质正义——以审判格推理中的价值缺失为视角
2013-01-29于海涌,张东明
一、形式逻辑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尴尬
任何一个逻辑推理都是由某一个或几个命题作为前提和某一命题作为结论所构成的,它是由一个命题或几个命题推出另一个命题的过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由法官独立审判案件”正是将待决案件的事实置之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下,以获得特定判决的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这个演绎推理过程是三段论的典型格,即以普遍原理为大前提,以特定情况为小前提,由此推导出特定情况应该得到的结论。由于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大量使用这种三段论推理的格式,因此这种典型的三段论格式又被称为审判格[1]杜汝楫:《侦查与审判中的逻辑问题》,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264页。。司法审判的过程,其实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最后得出判决的推理过程。[2]梁慧星:《民法解释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不过法律的适用绝对不是简单的形式逻辑推理,毕竟形式逻辑只研究推理的形式和规则,而不研究任何特定推理的内容。一旦我们将形式逻辑运用于司法审判,并关注判决的结果是否能够实现正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司法审判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可能的价值缺失。审判过程完全符合形式逻辑,但判决的结果未必能够实现正义,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尴尬现实。本文试图从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入手,对法律适用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与价值缺失问题进行分析检讨,以求教于高明。
二、法律规范:对审判格中逻辑大前提的分析检讨
“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指在一切审判活动中,都要以法律的规定作为判决的唯一依据。在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过程中,其无疑处于大前提的地位。根据三段论的逻辑规则,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这个大前提不仅必须是一个周延的全称命题,而且必须是一个真命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正确的判决,那么就判决的法律依据(大前提)而言,这就要求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不仅包罗万象、明确具体(全称命题)而且是能够代表绝对正义的(真命题)行为规范。很显然,这是对立法者的能力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
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在广度上应力求具有普遍性,在深度上应力求具有确定性,以便尽可能地涵盖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制定出各种具体、实际的解决方案,这样才不仅有利于普通市民准确地把握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从而确定自己的行为规范,而且有利于法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地引律据典,找到其审判推理的大前提。然而,即使立法者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并努力地为之而奋斗,其结果也必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必然要受到立法者的认识能力的诸多限制。
(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由于物质世界运动的绝对性和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人对世界的认识只能是一定广度和一定深度的认识,他不可能穷尽一切而掌握绝对真理。再高明的立法者也摆脱不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往往只能够关注社会的普遍情况,这就使法律一方面成为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就使它远离了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现实,那么在普遍情况下能够实现正义的法律,如果适用于某一特别情况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牺牲个别正义的情形。而立法者对于其根本就毫无认识或无法明确界定的事物,立法者也就只能依靠法律的空白地带或基本原则的弹性(例如民法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帝王条款)疲于应付,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残缺不全和千疮百孔的。
(二)从操作层面来看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都是立法者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的、适用于未来的行为规范,因此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法律在被制定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过时了。超前立法的现象每每是立法者自鸣得意的杰作,但不可否认,法律仍然主要体现为对现实既存利益关系的肯定和维护,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仍然体现为经验主义的产物,那它自然就不可能摆脱因经验不足所留下来的缺陷和遗憾。
(三)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看
一旦法律制度已经设计了一种权利和义务的方案,那么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预见性,立法者就会尽可能地避免对业已存在的制度进行不断的修改、废除和重新制定。这就意味着,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会出现僵化和滞后的一面,既定的法律往往会成为社会进步的羁绊。即使立法者可以通过废、立、改来克服法律的保守性,我们且不说法律修改程序的漫长和复杂,其实修改法律和制定法律一样何尝不同样受到人们认识能力和经验主义的限制?从普遍意义上讲,现实生活的变化要比法律变化快速得多。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口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缺口重新打开来。[1][英]梅因:《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5页。正是由于对立法者立法能力的不信任,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否则的话,他们将永无止境地制定这类烦琐的法律,并为使它们达到完善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修改这些法律”[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1页。。
尽管立法者为了给人们制定一个完善的法律而殚心竭虑,但其结果却注定令人失望。之所以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不够全面、不够明确和变动不居的,主要是因为法律所应付的是人类关系中最为复杂的方面。市民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每个自然人的个性和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变化莫测的人生都呈现在法律的面前,而在我们这个万花筒式的工商业社会中,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即使在一个比较静态的农业社会中,人们也从来没有创造出能预料到一切可能的纠纷并预先加以解决的、包罗万象的、永恒不移的法律规则。在现代,新的生产和交换形式、新的交通和居住方式、新的社会风俗、目标和理想——所有这些革新因素,使得制定出以后可以用来解决一切法律问题的固定规则这种希望,只能成为泡影。[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0页。如果立法者不能给法官和市民提供一个完美的逻辑思维的大前提,那么我们则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论断:法官利用这个并不完美的逻辑大前提所作出的判决自然也就无法保证其必然为真。
三、案件事实:对审判格中逻辑小前提的分析检讨
“以事实为依据”,就是指司法机关审理一切案件,都只能以客观事实作为唯一根据。在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过程中,其处于小前提的地位。根据三段论审判格的逻辑规则,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不仅大前提是全称命题,而且小前提必须是一个肯定命题,否则其结论就必定为假。换句话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为了保证判决的正确性,其对事实的认定(小前提)不仅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肯定命题),而且必须是真命题。任何一个案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都是由特定的事实所构成;而任何案件的发生都可能留下相关的证据,例如,书面合同、函件传真、在场的证人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证据为证明案件的事实创造了条件,固属无疑。然而,如果自信地以为所有的事实都能够用证据证实,或者认为证据所证实的事实就是案件发生的全部客观事实,那么我们这种自信中暗含的假定前提就是:案件发生后所留下的证据可以恢复案件发生的全貌,换句话说,就是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完全等同案件发生的事实。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盲目乐观。在司法判决中,根据证据规则可以认定的事实与发生的事实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可能出现完全错误的情形,这在审判实践中并不鲜见。
假如原告借款10万元人民币给被告(实际发生的事实),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当时没有要求被告出具书面借据,而且当时也没有其他人在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拒不还款且矢口否认有借贷关系,我们可以想象,法官“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审判,其判决认定的结果只能有一个: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发生借贷关系(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这正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所可以预见的审判结果。案件实际发生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之间的偏差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在法院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存在许许多多的错误来源,言辞证据更是首当其冲。就当事人陈述而言,由于当事人是争议法律关系的主体,案件如何处理与他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当事人的陈述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两面性和趋利避害的色彩。一方面他们亲身经历了案件的发生过程,对案件的事实了解得最为清楚和全面;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陈述对判决结论的影响。从自己的利害得失出发,对自己有利的就陈述,对自己不利的就不陈述;对于有理的事实就强调,对于无理的事实就加以掩饰。在陈述中会有意无意地夹杂着夸大或缩小的成分,甚至可能歪曲事实真相、故意作虚伪陈述。这样当事人的陈述就会形成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虚实难辨的复杂局面。就证人证言而言,由于证人是凭借自己的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个人体验感知案件情况的,他要经过信息的接受和记忆,然后以言辞表达的方式向司法机关完成提供证据,这样证人就具有身份的不可替代性和言辞表达的主观性。证人在提供证言的时候,就不能排除有作伪证的证人、有偏见的证人、发生误解的证人等。由于受证人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对证人证言的采信往往也会使法官陷入“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的尴尬境地。民间有句俗语:“好人往往死在证人手里”,也许可以体现对证人证言一种无奈的心情。
与难以捉摸的言辞证据相比,视听资料、书证、物证、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似乎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较高的可靠性,但也并非没有缺陷,视听资料比较容易伪造、模仿、涂改和剪辑,只要对磁带进行消磁和剪辑,就可能改变其内容,同时因为雷电、浓雾等天气的变化或因为树木、农作物、其他物体的遮蔽而造成视听资料判断上的错误或误差也在所难免。此外,书证可能会被伪造、篡改;物证可能会随着自然的变化而毁灭、腐烂、灭失;鉴定人可能缺少必需的专门性知识;勘验现场可能因为自然力量(如暴雨、狂风或日晒等)或人为因素(如伪造现场)而遭到破坏等等,不一而足。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案件的真正事实和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毕竟不总是保持同一性。案件的真正事实可能永远无法通过证据加以证实,而证据能证明的事实却根本不是案件的真正事实。尽管法院制定了专门的证据的举证、收集、保全、质证、审核等规则,力图恢复案件的原貌,力图使逻辑推理的小前提为肯定的真命题,但在司法实践中,永远会有大量非理性的、偶然的、推测性的因素。不可否认,法院判决中认定的案件事实,有些是真正的事实,有些接近于真正的事实,有些则是与真正的事实截然相反的错误事实。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一旦逻辑的小前提不是真命题,那么其结论也就未必为真命题,也就是说,一旦法院通过证据规则认定的事实与案件的真实事实可能存在并不一致的情形,那么法院的判决就有存在错误的可能性。
四、司法判决:对审判格中逻辑结论的分析检讨
在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过程中,法官的判决相当于逻辑结论。纯粹从三段论审判格的逻辑规则来看,如果大前提为全称命题,小前提为肯定命题,则结论必然为真。然而既然法律规则决非完美无缺,案件的事实也并非真假易辩,根据逻辑规则这本身就预示着结论并不必然为真。更何况,即使法律的规定全面而具体,证据足以恢复案件发生的全貌,这也并不能意味着正义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实现,因为案件的判决还必须通过法官来进行,而法官并不是机械的自动售货机,在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如何采信相互冲突的证据以及判决的制作过程中无不需要借助法官的主观能动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判决的过程中充斥着法官的主观因素。刑事案件中尚存在“罪刑法定”、“禁止类推适用”的排除法官的主观性过多地介入的情形,而民法则大相径庭,法官运用类推适用、限缩或扩大解释、漏洞补充以及帝王条款等进行判决的情形比比皆是,民法与刑法、行政法相比,因法官的介入而使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更为明显。我们将案件的独立审判权交付给法官,并期盼实现正义,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有一个乐观的期待和假设:法官是熟悉法律规则的、铁面无私的、有良知的理性人。
首先,就寻找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而言。即使立法者制定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法律,但法官在解决具体的案件的时候,在能够作三段论逻辑推理之前,法官必须寻找其需要适用的法律规范,以便找到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这个过程就是“找法”的过程。找法的结果有三种可能:其一,有可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其二,虽然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过于抽象,无法直接适用。其三,根本就没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即存在法律漏洞[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8页。。无论寻找的结果为何种情形,无不依赖于法官的解释和主观价值判断。按道理讲,如果法官都是熟悉法律规则、铁面无私、有良知的理性人,那么对于同一案件,由不同的法官进行审理,他们应当作出相同的判决。但实际生活中,同一案件由不同的法官审理,其结果却往往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领悟能力上的差异。知识和观念是相互联系的,知识愈是复杂,观点的差距也就愈大。面对同一个事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其持有的观点也会因时而异。现实生活中,案件的胜诉或败诉经常因法庭的更换而变动不居的情形并不鲜见。根据1914—1916年对纽约市治安法院几千个轻微刑事案件处理的调查,结果表明治安法官在其处理同类案件中的差别达到惊人的程度。在送交一个法官处理的546个被控酗酒的人中,他只释放了一人,约99%的人均被判有罪;而在由另一法官审理的673个被控酗酒的人中,79%的人被宣告无罪。[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1页。面对同样一个法律,不同的法官可能会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面对同一个法律漏洞,不同的法官可能会作出不同的解释或采用不同的漏洞补充方法,这就难免法官会把从自己头脑中一系列混杂概念中得出的谬误结论奉为合法的解释。“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采纳这一公理,等于放弃了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见。[3][意]贝卡里亚:《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其次,就事实的认定而言。法官在判决时,除了找法(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以外,法官还必须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认定(三段论推理的小前提)。就实际意义而言,成文法不过是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对权利行使者不信任的物化形式,它将法官的种种私欲、情绪冲动等非理性因素限制在不得溢出的范围以内。然而,如果希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正义,不可能仅仅凭借严密周全的法律规范,还必须凭借理性法官对事实的认定。面对诉讼双方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法官那种不可预测的独特个性会使案件事实的认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也就是说,尽管立法者纸面上的法规是精确和固定的,但法官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却是捉摸不定的,这同样会使法官的判决可能变动不居。根据弗兰克的观点,法官或陪审团具有一种实质上不受控制的和实质上无法控制的事实裁决权或最高权力,即确定哪个证人的证言被认为是正确的而加以接受的权力。[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在许多情况下,法官在确定事实的过程中所适用的隐秘的、无意识的、个性化的规范,会使客观上严密周延的法律规范变得无效。尽管法律规范精确而固定,但事实的认定却变化不一,这就相应地使案件的结果同样呈现不确定状态。
最后,就判决的制作而言。法官最终制作的判决书是其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逻辑思维过程的体现,给人的印象似乎判决也是按照严密的逻辑推理出来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法官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思维过程只存在于公之于众的判决理由中,普通人的正常思维过程都不是通过三段论的推理作出的,尽管法官经过专门的职业训练,但他同样是人。在法官的思维过程中,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并不是按部就班地逐步完成,因此法官判决的过程无法避免要夹杂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2]前法官哈奇森(Joseph E.Hutcheson)在《直觉的判断:司法中预感的作用》一文中具体描述了自己作出判决的过程:“在我看过手边所有材料并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就让我的想象力发挥作用。我陷入沉思,等待着感觉和预感的到来。这个预感就是了解问题的直觉的闪光,它是能把问题和决定连结起来的火花。”在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和对证据的采纳将信将疑的情况下,对于若干个可选择的结论,在法官举棋不定时,结论往往会随着法官的价值判断和对证据的采纳而不断改变。而在法官进行选择和价值判断时,法官的同情心、性格、脾气、情绪、偏见,他在生活中某种痛苦或幸福的经历,他在潜意识中对当事人的反感或喜爱,他的宗教信仰、种族观念、权利意识,他对被害人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的表情或对被告人一个冷酷的眼神的回忆等等,都可能增加或减少法官作出某一价值判断的决心和对证据的取舍,从而使犹豫不定的法官作出坚定的抉择并附上充分的理由。其实,在理性的逻辑推理后面,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法官个人的主观因素和个性色彩。
五、形式逻辑实现实质正义的现实路径
在司法实践中,试图根据形式逻辑进行推理,而其逻辑结论都能够实现司法正义,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我们可以通过现实的努力最大限度地去实现司法正义。
(一)法律的解释与立法漏洞的补充
如果法律规范不够明确具体,过于抽象模糊,法官在裁判案件的时候就需要在明确法律规范的内涵和外延后才可以适用,这就要借助法律解释。例如,民法解释通常有扩张解释、限缩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以及比较解释等方法。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该条没有明确规定非法人组织是否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显然文义过于狭窄,因此可以对法律条文的涵义可以扩张解释为:“非法人组织也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就是扩张解释的运用。再例如:《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兄、姐”可以成为监护人之一。这里的“兄、姐”显然过于宽泛,不应当包括尚未成年的兄姐在内,所以应当限缩法律条文的文义,将“兄、姐”缩小解释为“成年兄、姐”,这就是限缩解释的运用。通过各种解释方法,其最终目的就是使法律规范中的模糊区域予以具体明确。
如果法律规范抽象模糊,法官尚可进行法律解释。如果法律规范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定,法官完全没有解释之余地,那么法官该如何应对?对于立法中没有规定的情况,称为立法漏洞,法官在适用时,必须对立法漏洞进行补充。漏洞补充的方法大致有三种,第一,依据习惯进行漏洞补充。习惯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还是十分强大的,按照先例行事总会给予社会生活一定程度的确定性、连续性和安全感,因此尊重习惯便成为立法者尊重民商法律的稳定性、继承性所立足的文化心态。从心理学的角度考虑,人类有重复在过去被认为令人满意的经验或安排的先入为主的心理倾向。各国民法常常以明文规定习惯对法律的补充作用。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条就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瑞士《民法典》第一条规定,本法未规定者,审判官依“习惯法”;我国《合同法》第125条就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交易习惯”就是确定该条款真实意思的方法之一。第二,依据判例进行漏洞补充。判例在我们国家并非法律的正式渊源,但法院的判决不可能变化无常,一旦对某类案件作出判决以后,以后遇到同类案件,如果没有特别反对之理由,必然作出相同或相似的判决,在法院的长期运作中,遂起到补充法源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针对个别案件所作出的批复、解答或判决,对法院审理案件具有事实上的影响力。法院在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时,判例便成为重要的补充法源。第三,依据法理进行漏洞补充。如果既无习惯可考,也无判例可循,法官依据什么作为判决之依据?这就不得不求助于法理。所谓法理,是指法律之原理,也就是根据法律的基本精神演绎出来的一般规则。在实务操作中,法理的具体化必须依赖法官的努力,只有从法理中获得了具体的规范,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条、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项、意大利《民法典》第3条第2项均承认法理为法律的补充法源。
任何法律,无论其体例如何完备,规定如何周密,模糊与缺漏终属难免,而在民商法领域法官又不得借口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凭借有限的条文,审理无穷的案件,捉襟见肘是常见的现象,通过法律的解释和漏洞补充,从而使千疮百孔的法律规范至少在理念上可以达到“疏而不漏”的效果,从而为法官审理一切案件寻找到了判决的法律依据——审判格的逻辑大前提。
(二)证据的预先收集和保存
为了能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恢复案件发生的原貌,这就要求当事人在案件没有形成诉讼之前,采取“防患于未然”的策略,提前注意证据的搜集和保存,例如,订立书面的合同、办理公证、保存往来的传真和电子邮件、进行现场录音录像、保留物证等。这种预防措施可以避免诉讼后证据的灭失、毁损,防止利害关系人故意歪曲事实、隐匿证据,避免证人故意作伪证或者因遗忘等原因发生误差。当然,这种预先收集、保存证据的做法会增加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在商事活动中尤其会降低交易效率,增加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也使收集和保存证据成为当事人难以承受之累,甚至影响当事人的正常生活。[1]至于证人证言,原则上证人必须亲自出庭,接受双方的交叉询问,这样才能较好地避免出现伪证或者偏向性证言。不过,从案件的审理来看,这种“居安思危”的主观心态便于举证,使案件发生的事实尽可能通过证据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从而为法院的判决奠定坚实的基础——案件真正发生的事实,即审判格的逻辑小前提。
(三)法官的精英化和超然地位
审判的过程必须依靠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法官必须具备精良的法律专业素养,能够准确领悟法律的精神,熟练运用法律规则,能够灵活处理各类案件,从而使法律的普遍规则能够在各种形形色色的具体案件中实现个体公平。这就要求法官的队伍必须精英化,也就是说,法官必须经过严格的遴选程序,确保只有具有很高法律专业素养的知识精英才能够进入法官的队伍。
精英化的法官,只是表明法官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作出公正的判决。在审判中,高素质的审判人员还必须处于超然地位,才能够作出公正的判决,也就是说,法官不应当受到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法官只对法律负责,这样的判决才能够更接近公正。如果法官的任免、晋升、工资收入等受制于人,甚至法官为了追求非法收入故意枉法裁判,那么法官在判决之际,除了考虑法律之外,还必须考虑案件之外的因素,一旦案件的判决直接影响法官自己的切身利益,法官就不再是一个超然的裁判者,而成为一个利害关系人。尤其在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之际,如果法官不是处于超然地位,自由裁量权就不利于法官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实现判决的妥当性,一旦法官受到了外来的压力或利诱,那么自由裁量权也就为法官提供了胡作非为的最佳理由,并为法官滥用职权留出了弹性空间。
一个具有很高法律专业素养的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又处于超然地位,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官能够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决——审判格的逻辑结论。
六、结论
通过对审判格的分析,我们发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由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作为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以法律为准绳”,是因为我们假设法律规范是包罗万象、明确具体、代表绝对正义的行为规范。“以事实为依据”,是因为我们假设案件发生后所留下的证据可以恢复案件发生的全貌。“由法官独立审判案件”,是因为我们相信法官是熟悉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则、铁面无私、有良知的理性人。但事实上,立法者不是万能的上帝,司法官也不是自动售货机,而证据和事实却长着一副变化多端的脸,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漏洞补充、证据的预先收集和保存、法官队伍的精英化、法官的超然地位等各种方式的努力,极力使司法审判中形式逻辑的推理结论最大限度地接近实质正义,但司法审判的过程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无疑会导致法律所追求的安全、公平、效率等价值目标发生不同程度的缺失,这就难以避免在某些情况下邪恶也会披上正义的外衣,堂而皇之地从法庭走向人世间。
审判的过程中难免发生价值缺失,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力主放弃法治的理想。离开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由法官独立审判案件”,无异于接受强权漫无约束的恣睢放纵和胡作非为,市民的生活将丧失最起码的安全感。任何最优的方案都只能获得廉价的、理论意义上的喝彩而为现实所排斥,第二等好的但现实可行的方案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尽管法律存在着种种弊端,并不完美,但审判格的应用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与人类创制的大多数其他社会制度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它只是现实可行的第二等好的理性选择。
(初审:杨彪)
法律适用中的形式逻辑与实质正义
——以审判格推理中的价值缺失为视角
于海涌 张东明[1]
司法审判的过程,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最后得出司法判决的三段论推理过程。即使审判过程完全符合形式逻辑,但判决的结果未必能够实现正义,这就是必须面对的尴尬现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由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作为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漏洞补充、证据的预先收集和保存、法官队伍的精英化、法官的超然地位等各种方式的努力,使形式逻辑的推理结论最大限度地接近实质正义,但司法审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无疑会导致追求正义的价值目标发生不同程度的缺失。
审判格;司法审判;形式逻辑;实质正义
作者张东明,男,安徽淮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 作者于海涌,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民商法学,代表作有《法国不动产担保物权研究——兼论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绝对物权行为理论与物权法律制度研究》《论不动产登记》《英美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在中国的本土化》等,E-mail:lpsyhy@mail.sys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