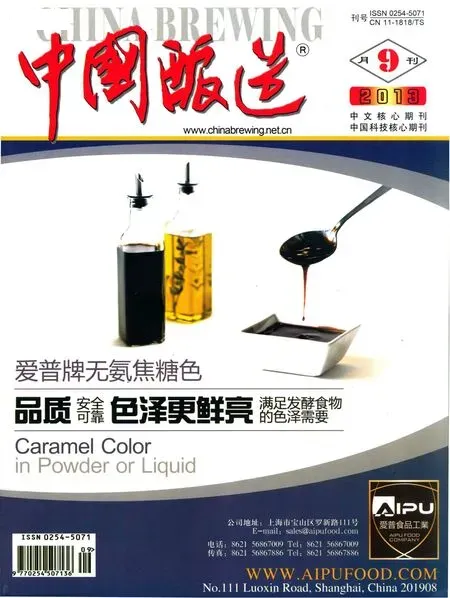“葡萄”名称的来源考释
2013-01-26温建辉
温建辉
(山西晋中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
自汉代“蒲陶”一词出现以来,在文献中出现了“蒲陶”、“蒲桃”、“蒲萄”、“葡桃”、“葡萄”等不同的文字表达,如《史记》中写作“蒲陶”,《汉书》中写作“蒲桃”,《后汉书》中写作“蒲萄”。对于“葡萄”一词的来历有不同的说法。有学者认为[1-2]是源于希腊文“botrytis”;也有学者认为[1-2]是来自波斯文“budawa”。而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3]“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是聚饮之意、“醄”是大醉之态。按李时珍的说法,之所以叫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的酒能使人饮后陶然而醉,于是取“酺”与“醄”字的谐音,将其叫作“蒲桃”、“蒲陶”或“葡萄”二字。此说法在我国各种葡萄酒书籍和网络媒体上广为流传,似乎已成定论。但通过历史的分析,并结合山西介休等地的方言推断,“葡萄”这一名称是来源于波斯语“budawa”的音译,而不是来自希腊文“botrytis”的音译;至于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对“葡萄”这一名称的释义,不足为据。
1 “葡萄”名称的来源考释
1.1 “葡萄”的名称来自音译,而非意译
中国史书中,最早提到“蒲陶”一词的是《史记》。自汉代至宋代的诸多文献中,葡萄之所以有“蒲陶”、“蒲桃”、“蒲萄”、“葡桃”等不同的文字表达,是因为栽培葡萄属于外来物种。对于外来物种的命名,主要有按其原名音译、意译、音意兼译等3种方式。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所谓“葡萄”是来自“酺”与“醄”的释义,既不能算作音译,也不能算作意译,更不是音意兼译。因为葡萄不等于葡萄酒,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葡萄本身既不可以“聚饮”,更不会出现“大醉之态”,只不过“可造酒”而已。
对于“葡萄”名称的解释,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是意译。据希腊学家罗念生考证[1],汉时“蒲桃”(葡萄)二字的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trytis”;而汉学家劳费尔在其名著《中国伊朗篇》(Sino-Iranica)里认为葡萄一词是波斯语“budawa”的对音。民俗学家、《细说万物由来》的作者杨荫深先生在研究了《史记·大宛列传》和《本草纲目》后认为[4],“此蒲陶注家均无解释其命名之意,大约当是译音”,李时珍的解释“恐出想象之辞”。有些西方学者认为[5],“葡萄”一词在汉代的发音相当于希腊文batrus或波斯语budawa的译音。
法国学者布尔努瓦对葡萄的名称作了这样的解释[6]:“《汉书》以两个汉文方块字‘蒲陶’来称葡萄及其枝藤,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仍是对一个方言词的对音译名,很可能是出自一种伊朗语,某些人将此视为希腊文中葡萄串的词botrys的音变。无论其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原形如何,‘蒲陶’始终以一种近似的写法‘葡萄’而一直保持到现今的汉语中。”苏振兴先生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中提到[6]:“葡萄为希腊文batrus之译音,亦有人认为是伊斯兰教budawa之译音。中国史书《史记》、《汉书》中均称‘蒲陶’,《后汉书》中称‘蒲萄’,后来才逐渐使用‘葡萄’这一名称……葡萄之得名,至今仍莫衷一是。”
1.2 从介休方言探音译本源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专家学者们都认为汉语中的“葡萄”这一名称是由外文音译过来的,而不认可李时珍的解释。对于希腊文,共出现了3个相似但不同的词汇,即botrytis、botrys和batrus;而波斯语,只出现了一个词汇,即budawa。但究竟是来自希腊文还是波斯语尚无定论,下面不妨从地方方言中去追寻。
方言传承着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是一笔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大学吴永焕指出[7]:“语言除了其的工具性之外,还是人类历史的见证者。语言的背后沉淀着人类文明丰富的信息。”语言又是表音或表意的符号系统,对于外来物种的名称如果采用音译,一定会和原有词汇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在山西介休、平遥、孝义等地的方言中,“葡萄”一词的读音并不是现在流行的普通话读音“putao”(汉语拼音),而是读作“budao”(汉语拼音),与波斯语“budawa”的读音非常接近,而与希腊语“botrytis”、“botrys”、“batrus”等词的读音相去甚远。此外,在介休一带,对于葡萄藤常常称为“budaowan”(汉语拼音),也与波斯语“budawa”的读音非常接近。由此完全有理由推论,“葡萄”一词是来自波斯语“budawa”的音译,而不是来自由希腊语“botrytis”、“botrys”、“batrus”等词的音译,不必再争论不休。
1.3 介休方言中完整地保留了汉语中的古音义
语言和民俗具有历史的传承性,现代语言之中的任何一种方言都是由古代语言发展演变而来。介休一带在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保留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8],无论是源于春秋时期的清明“寒食节”的遗风、还是“筛铭旌”古俗,在历经两三千年之后的今天依然留存。在古代民族语言方面,随着历代的多次民族融合和历史变迁,许多地方的胡、汉语言中的词汇,早已伴随着民族的融合难以辨认了,但唯有在介休的方言土语中,各民族语言的残痕还暴露的非常强烈,一些古音义也得以完整保留。介休方言中,一些词的用法直接传承于古汉语,如“入”字与“进”字的区别使用就非常讲究和规范,现在我们常说的“进来吧”,在介休方言中是“入来吧”,这是因为在古汉语中“入”和“出”相对应,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量入而出”;在古汉语中“进”和“退”相对应,如“进退两难”、“不进则退”。由此可见,介休方言中的某些用词比现代汉语更规范、更科学,也更具有古意。
探索古代历史与文化的起源,方言古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如今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黄侃先生曾言[9]:“固知三古遗言,散存方国。考古语者,不能不验之于今;考今语者,不能不原之于古。世之人或徒慕艰深而多书古字,或号称通俗而昧于今言,其皆未为懿也。”语言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方言中大量古汉语的语音和词汇的留存是语言的活化石。从介休方言的读音“budao”去追寻“葡萄”一词音译的渊源,完全符合训诂学、词源学、语源学的基本方法。
1.4 波斯与中国的交往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还有几句重要的话很少有人注意:“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可见,安息也出产“蒲陶酒”,而且是个大国。安息帝国座落在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与中国汉朝之间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之上,是古波斯地区主要的政治及文化势力和商贸中心,也是东西陆路的要冲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间站[10]。在中国许多汉墓出土的丝织刺绣中,其艺术图案都受到古代波斯工艺美术的浓重影响。在中国新疆、敦煌、山西等地发现有波斯的文物碑刻及宗教书籍,在许多地区还出土了波斯银币。
波斯是世界上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11-12],由波斯往西,葡萄和葡萄酒传到希腊,希腊成为欧洲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此后又从希腊传到罗马以至整个欧洲。由波斯往东,葡萄和葡萄酒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自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来,波斯与汉朝的交流十分密切,而希腊与汉朝的交往并不直接,需要以波斯一带为中介,从这些因素分析,“葡萄”来自波斯语“budawa”的音译也更为合理。
2 李时珍《本草纲目》对“葡萄”释义的牵强附会
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虽然是我国古代本草学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东方百科全书,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也有许多迷信的成分和牵强附会的解释,如:“雄黄能杀蛇毒,妊娠佩戴,转生男子,炼之久服自身轻;要生女子,佩戴雌黄。”“妇人觉有妊,以雄黄一两,绛囊盛带之,养胎转女生男;以雌黄半两素囊盛带之,可转男为女。雌黄炼服,久则身轻,可入仙家。”对于许多物质名称的释义纯属个人想象,望文生义,如对“兔”名称的解释,是因为兔“吐而生子,故曰兔。”并且,由兔子的三瓣嘴推论出“孕妇吃兔肉,生子缺唇。”如此等,纯粹是牵强附会。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葡萄的释义,也同样是个人想象,望文生义,但目前被许多文献[13]所引用,特别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从最早出现“蒲陶”的《史记》到明代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在这漫长的1500年期间,从未有文献提出过类似李时珍“酺”、“醄”二字意译的观点,就连《本草纲目》的校注者[3]也认为“蒲桃及葡萄皆是译音,不必有意。”
3 结语
我国是文明古国,酒与酒文化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广泛的民众基础[14],但是在许多方面仍然谬误层出。我国是葡萄属植物的起源地之一,但在汉代之前,并不叫“蒲陶”(葡萄),而是称为葛藟、蘡薁等。就像我国唐代就有用葡萄酒蒸馏而得的蒸馏酒,但不叫“白兰地”,而归为“烧酒”之类;古代也用麦芽制酒,但不叫“啤酒”。据说披萨(比萨)饼起源于中国,是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传到了意大利,但现在中国“比萨”一词却是来自“Pizza”的音译。
现在一般把葡萄分为野葡萄(山葡萄)和家葡萄(栽培葡萄)两大类,但在农耕文明尚未出现之前,现在所栽培的植物都处于野生状态,葡萄也不例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通过选育、驯化,一部分优质的野生葡萄发展成为栽培种,欧亚种葡萄也是由野生葡萄选育而来,汉朝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原产于我国的葡萄属植物约有30多种,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大江南北,现在统称为野葡萄[15-18]。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食用野葡萄或用其酿酒的记载,如今一些远山里的农家和近山的市民仍有食用野葡萄酿酒的习惯;吉林省通化葡萄酒公司和长白山葡萄酒厂的山葡萄酒还多次被评为全国优质酒,出口海外。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陶片中,有用野葡萄酿酒的证据[19],说明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之一。葡萄酒文化源远流长,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1]卫 斯.从佉卢文简牍看精绝国的葡萄种植业[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65.
[2]古贺守.葡萄酒的世界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4]杨荫深.细说万物由来[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5]海 滨.进贡与却贡——唐诗中葡萄的象征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09.
[6]李次第.葡萄酒的中国因缘[J].考试周刊,2011(51):232-234.
[7]吴永焕.汉语方言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对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39-43.
[8]刘俊礼,刘向东.介休拾古[N].晋中日报,1998-10-3.
[9]罗东先.新乡方言古语词浅释[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3):39-43.
[10][法]阿里·玛扎海里,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11]张建才,高海生.走进葡萄酒[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12]胡小健,杨荣华.葡萄酒漫谈[J].中国酿造,2001,20(4):4-7.
[13]李 华,王 华,袁春龙,等.葡萄酒工艺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4]曲 超,张根生,洪海成,等.中国历史上酒文化研究落后于酒文化发展的原因[J].中国酿造,2010,29(1):176-180.
[15]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编撰委会.中国自然资源丛书·山西卷[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
[16]刘孟军.中国野生果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7]孔冬梅,张义贤,张 峰,等.山西庞泉沟自然保护区植物学[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18]王万贤,杨 毅.野生食果资源[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19]李 华.葡萄酒品尝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