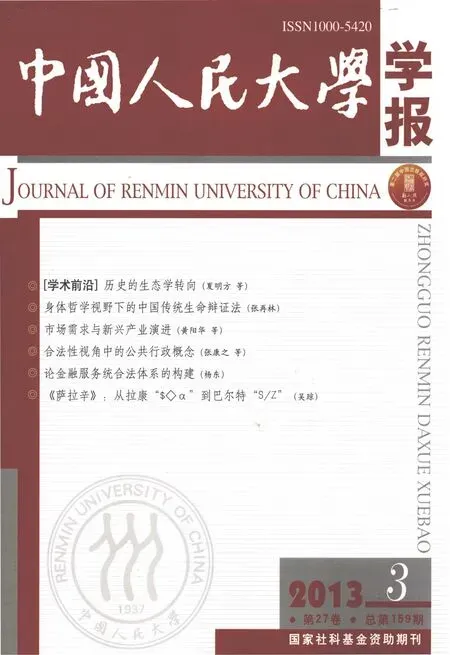小农、士绅与小生境——9—17世纪嘉湖地区的桑基景观与社
2013-01-22王建革
王建革
17世纪嘉湖地区的桑基生态农业闻名于世。生态学家根据 《补农书》等资料,进行了生态系统的分析,投入与产出的数据表明这种农业有着非常高的产量和效率。[1]目前,这一生态系统的生态史过程与人及环境关系不甚清楚。这一地区从沼泽演化成桑基稻田或桑基鱼塘,其中既有各种水文与生物活动的过程,也有各种人群对环境的利用。六朝以来,这一地区的士大夫群体也在经营着环境,他们将自己的审美情趣灌注到山水环境之中,他们经营的生境有一个从大到小的过程。宋代以后,小农成为主体,小农在越来越狭小的生境上经营稻作并植桑养蚕。田野之上有着各种的生态循环,不单有物质流与能量流,还有景观流和审美流。立意于这一基础,生态史的研究必须与文学史与艺术史相结合,这种结合也给生态学以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一、大环境的分化
早期开发沼泽地带的主体是屯田军和豪强。六朝时期火耕水耨,农业产量不高,环境的丰富度却很高。休耕使田野的植物种类丰富,天目山及其以东的山前平原还有各样的树类和水生植物。山水之间,官僚、士绅和大家族占山泽经营园林别墅。士大夫的园林别墅依托着当时门阀和豪强体制,形成庄园环境。“田园别墅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生产项目,成为包罗万象的小王国。通过田园别墅中直接劳动者的劳动,山林川泽更多地开辟,增加了新的耕地,疁田(火耕田)、湖田在更大范围内出现;竹木的斩伐和栽植,蔬菜、果树的栽植,以及渔场的设置,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物资供应。在规模较大的田园别墅中甚至还有水利灌溉事业的兴建。”[2](P65-98)作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创人,谢灵运的许多灵感来自浙东和杭嘉湖一带的山水沼泽,尤其是天目山溪流的景观。由于靠近苏杭等著名城市,乡村地区就成为士大夫置园林别墅的地方。谢灵运移籍会稽时, “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 “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川之畔。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囿在前,果园在后。”[3](P1745-1755)
自谢灵运以后,山水之间的太湖东部和钱塘江一带成为士大夫的理想居住地。 “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自田之湖,明显是可以围垦的小湖泊和小水沼之地;自园之田,则是自家经营的圩田。水流与田地的景观也是非常有序,有早稻,晚稻,也有麦豆。既有农业,也有山水。 “栖孤栋于江源。敞南户以对远岭,辟东窗以瞩近田。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广大的田野,丰富的水草。“水草则萍藻蕰菼,雚蒲芹荪,蒹菰苹蘩,蕝荇菱莲。虽备物之偕美,独扶渠之华鲜。播绿叶之郁茂,含红敷之缤翻。怨清香之难留,矜盛容之易阑。”园林中有非常讲究的竹类、高大乔木和各种鱼类、鸟类。[4](P1760-1763)与谢灵运的大规模园林相比,徐勉的田园风格更适合一般士大夫,他的田园属于经济与审美兼得。 “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他的经营历尽周折,“由吾经始历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阴,塍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迥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芰莲”[5](P383-385)。当时士大夫的这两种家居景观一直对后世田野产生影响。
一般农民依托上层与豪强从事农业劳动,满足于生存与安全。由于农业与生活的需要,桑蚕经营也早就形成。谢灵运有 《种桑》诗一首:“诗人陈条柯,亦有美攘剔。前修为谁故,后事资纺绩。常佩智方诚,愧微富教益。浮阳骛嘉月,艺桑迨闲隙。疏栏发近郛,长行达广埸。旷流始毖泉,湎涂犹跬迹。俾此将长成,慰我海外伇。”[6](P85)在广大的屯田区,农民在编户下固定居住,行村社制度,乡村对河道、圩岸以及树木种植皆有详细规定。周朗言: “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处,须官兴役,宜募远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给其粮种。凡公私游手,岁发佐农,令堤湖尽修,原陆并起。仍量家立社,计地设闾,检其出入,督其游惰。”农户难有单独形成小生境的能力,由于实行户等税收制度,农户也没有积极性改善环境。“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居屋如此,政府仍然督催田野开发,推动桑树的种植。周朗又说:“田非疁水,皆播麦菽,地堪滋养,悉艺纻麻,荫巷缘藩,必树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则叙之以爵,有司亦从而加赏。若田在草间,木物不植,则挞之而伐其余树,在所以次坐之。”[7](P2093-2095)在这种情况 下,农民即便开发 田野,也只能集中地形成农业景观。当时的水稻田处于“疁水”状态, “疁”是一种休耕状态的火烧地, “水”是灌水状态的水稻田。旱地原处抛荒状态,强制开垦变成麦豆地,便没有休耕。唐代的农民也几乎没有单独经营环境的权力,地方官却可以任意开发景观。 “大历十一年,颜鲁公真卿为刺史,始剪榛导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属灾潦荐至,沼堙台圮。后又数十载,委无隙地。至开成三年,弘农杨君为刺史,乃疏四渠,浚二池,树三园,构五亭。卉木荷竹,舟桥廊室,洎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备焉。”[8](P3798-3799)北宋时期,嘉兴仍有许多缘水树木的景观。梅尧臣诗题有:“秀州通越门外八九里临水多佳木茂树以便风,不得停舟,一赏怆然为诗。”当时水漾甚多, “密树重萝覆水光,珍禽无数语琅琅。惊帆瞥过如飞鸟,回首风烟空断肠”[9](P237)。但更多的士绅经营小园林,苏东坡的同僚杭州通判梅宣义就是一个典型,“不惜十年力,治此五亩园。初期橘为奴,渐见桐有孙”[10](P1718)。
宋代的基层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村社制度的崩溃促使小农侵占了以前的公共河道与圩岸,在小环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安船沟泾和居住地。“人户各有其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为家。欲其行舟之便,及凿其圩岸以为小泾、小浜。”[11](P270-271)大圩遭到破坏是乡村制度不行之故,村社制度不行与公田招佃有关,租佃的农民是小农。宋代的小农是有相当自由度的小农,郏亶言: “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 ‘白塗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12](P270-271)租 户 可 以 任 意 地 选 择 休 耕 地,
说明农民可以自由流动。“间年淹没”可能是指休耕一年。也有收租后放水招佃的, “秋收了当,即放水入田,称是废田,欲出榜招人陈告,其田给予告人,耕田纳税,即已给予告人,后有词讼不得受理”。秋收后出榜招人,经营者是佃农。[13](P4898)佃农固定后成为小农,小农可以在田野和房前屋后经营自己的小生境。南宋以后大量的移民的进入使河网更加细化,小生境增多与小农经济增多同步。在湖州湖溇区,湖田的发展也使临水的小生境可以形成小园林,格外有诗意。“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蘋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14](P268)明代嘉湖地区的河网基本上以三条运河为纲:东部的嘉兴古运河;中部的土塘运河、平望以南的东塘运河。[15](P141)以运河为基础,条分缕析。溇港地 区的淤积和开垦使临水湖田生境得以发展。细化的河网有小桥,连接着各处分散的小居住点。文徵明的 《曲港归舟图》描绘了远山近港,那应是湖田与天目山相映的景观。归舟行于曲港,曲港被树木包围,临山处的湖田有许多树木。[16](P240-241)小桥、流水、树木使小生境显出美丽。
二、桑基小生境
蚕桑文化起源于华北。 《诗经》幽风七月即寓采桑文化于其中,六朝华北的 《陌上桑》更有丰富的体现。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无论是上层士大夫还是下层乡村和,都仰慕采桑女罗敷,采桑女形象得到了上下层一致的赞美。[17](P29-30)六朝时吴均的《陌上桑》只有田野与采桑女。“袅袅陌上桑,荫陌复垂塘。长条映白日,细叶隐鹂黄。蚕饥妾复思,拭泪且提筐。故人去如此,离恨煎人肠。”[18](P829)桑荫垂塘,反映的正是圩岸之桑。这个时期圩田尚大。宋代以后,湖泊与荡地开垦加速,嘉湖地区形成大量的桑基小生境,小生境伴随着小池塘,以此形成大量的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士大夫的生境园林建设也逐步以小池塘为中心。苏轼就特别欣赏小池塘的生境。“草满池塘霜送梅,疏林野色近楼台,天围故越侵云尽,潮上孤城带月回。”[19](P2547)南宋朱淑真多次提到池塘。她描述立春前景色时言:“梅花枝上雪初融,一夜高风激转东。芳草池塘冰未薄,柳条如线著春工。”池塘柳树景观在春景中突出,夏天的桑树只是绿色,这时一般不养蚕。“枝上浑无一点春,半随流水半随尘。柔桑欲椹吴蚕老,稚笋成竿彩凤驯。荷嫩爱风欹盖翠,榴花宜日皱裙新。”[20](P11661)蚕月是四月,入夏时蚕月已过,桑叶是剩下的桑叶。这时有竹筍、荷花与石榴花,景观丰富。湖州一带的蚕桑已经很发达,许多其他生业的人也在经营蚕桑。 “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使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今已仲春,拘而用之,使之蚕桑失时,种莳失节,终岁必有困穷冻饿之患。”[21](P679)园林景观的营造在宋代达到高峰,南宋的嘉湖田野远比后期秀美。入元后,经济与文化都受到极大的破坏,也少有桑基景观的诗。元末王冕笔下的桑基农业仍是一片萧条,“田夫奔走受鞭笞,饥苦无以供支持。蚕姑且将官布办,桑老田荒空自叹。明朝相对泪滂沱,米粮丝税将奈何”[22](P188)?元末小生境仍在发展, “元故儒梁寅有凿池溉田之议,其略云:亩亩之间,若十亩而废一亩以为池,则九亩可以无灾患,百亩而废十亩以为池,则九十亩可以无灾患”[23](P837)。
明代人口增长,市镇发达,小生境桑基农业恢复并进一步生态农业化。小农依水道经营小圩田生境。“凡傍田之处,必开溇荡。又必开塍以通沟洫。”[24](P586)有人在高山处看湖州平原景观时非常美丽。“俯视平原沃野万顷,高者皆桑,低者为菑畬。清溪萦回,横直相间,若界画然。溪之外为落舍漾,清水漾,风帆往来,菰蒲交映。”[25](P171)在湖田区,这里正临天目山水,这一景观滋育了元明时期众多著名画家的山水意识,在这里造园的士绅一般也是以小生境为主。营园专家也认为这里可以在小生境下形成小园林。 “江干湖畔,深柳疏芦之际,略成小筑,足征大观也。悠悠烟水,澹澹云山,泛泛渔舟,闲闲鸥鸟。”[26](P69)湖州晟舍镇临太湖,处溇港围田区。南塍村 “旧多园林,南岸有长荷花池,桃李相间成行,近荻塘时见风帆来往,颇有西湖风景。桑基小景观与船景相配,特别雅致,有诗曰: ‘半飞桑陌半平畴,叶叶风帆出树头,一片行云留不住,引人遥望入南楼’”[27](P984)。环境优美与水乡的植物多样性有关系,小生境内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四时美景。早期多园林,正是过度开发才引起景观单一化。
科举制度使士大夫多从小农家庭产生,既出自桑基小生境,审美需求往往也是小生境的景观,加之土地的升值,农家田园规模逐步减小,大量士子只得在小生境基础上寻求发展。家园小农化使士大夫只好寓理想情趣于小生境。张履祥重实践,提出凿池形成小环境,在小环境基础上精细经营,以此形成士绅的优雅生境。 “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种田之亩数,略如其池之亩数,则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不可通于沟,通于沟则妨邻田而起争。周池之地必厚;不厚,则妨邻田而丛怨。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这种小生境也需要很高的成本,池塘边种桑竹,然后筑室。 “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林、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旁室穿井。如此规置,置产凿池,约需百金矣。少亦需六、七十金。其作室亦需此数,非力所及也。积渐废产以置产,约略相当,作室则全无措手矣。”[28](P122)这种耕读之境需要士人家庭长期积累,一般人达不到。贫穷的士大夫只好混同于一般的小农生境,在桑荫相连、居屋相邻的田野中,看不出他们的特色。
桑基小生境越多,原生态质生境愈少。池塘越来越小,难以养鸭。张履祥言:“吾地无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无大水泽,不能多畜鸭,少养成亦须人看管。”[29](P1420)平原没有大水荡养鸭,围垦已达饱和,自然景观日益减少,开垦形成的多是桑基鱼塘和桑基稻田。湖溇区的小生境因种植而形成。 “滨湖诸民,遍植杞柳填委诸溇,日积月累,渐成芦荡。洼者为鱼池,广者为桑地,溇港不得泄其归,启闭无所因其候,此其归纳受病一也。”[30](P469)桑树在湖溇圩田中的景观非常明显。池塘是养鸭养鱼之所,可以供小家庭禽蛋和鱼之用。“数弓营隙地,百指凿清泉。春涨鸭头水,光摇鱼尾天。”[31](P780)河网的分割形成小水潭,这种水潭是圩田旱涝保收的根本。20世纪50年代,高地仍然重视这种小水体。海宁袁花公社溇潭数量达到1 408只,面积1 559.3亩。这些小水潭成为小农经济的“金饭碗”[32]。小水潭是圩田小型化的产物,估计大量形成于元代以后。嘉兴天旱时,农民多挖引水河,增挖小池塘。西部多为荡地,明代的深水开发也形成这种小池塘和小块湖田。“堤之功莫利于下乡之田,余家湖边,看来洪荒时一派都是芦苇之滩,却天地气机节,宣有深、有浅、有断、有续,中间条理,原自井井。明农者因势利道,大者堤,小者塘,畍以埂分为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吴江人往往用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经见,二十里内有起白手致万金者两家,此水利筑堤所以当讲也。”[33](P138-139)
明代发达的市镇与商业网络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桑蚕利润增高。嘉湖地价的节节升高得自于种桑以后的升值空间。小生境内也出现了桑基扩展的现象。农民长期的挖河泥堆叠过程使田野的地表出现参差不齐、高低不平的现象。“小农经济基础上自发地发展桑园,引起耕作上许多不便,桑园是分散的,东一块西一块,为了加高桑园的土层以及每年挑稻秆泥作肥料,桑地日加高而稻田却愈挖愈低,而且高低不平。这也是为当时抵抗自然灾害造成许多困 难。”[34](P46)这种堆叠为小农基础上的生态农业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河泥的有效氮含量并不高。俞荣梁先生对陆家湾村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表明,河泥的氮素投入量为6斤/亩,仍高于水草、稻草还田、垃圾、菜籽饼和人粪尿的氮素投入,低于猪粪、羊栏肥和化肥。[35](P9-19)但河泥对土壤的作用是其他肥料无法取代的,河泥含有许多的无机和有机胶体,能调节营养元素的平衡,提高土温,加厚耕作层。[36](P131-132)这种高肥力土壤加外蚕桑与湖羊,才支持了生态农业的高产量。麦稻二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产量水平, “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关”。在桑叶一般收成的时候, “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37](P101)。
桑园经济与生态农业的发达,促进了田野景观单一化,士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当然难寻风景独特的别墅。万历年间 《西吴枝乘》有: “湖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环堵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而别墅山庄求竹木之胜无有也。”[38](P549)要经营园林,成本甚大,面积也不太大。 “古之乐田园者,居于畎亩之中,今耽丘壑者,选村庄之胜。团团篱落,处处桑麻,凿水为濠,挑堤种柳,门楼知稼,廊庑连芸,约十亩之基,须开池者三,曲折有情。”在桑基农业地带要经营十亩之园,要费很大的工夫。许多士绅只在居住地之旁兴园林,南方的村庄散居,一般农家并不像北方那样紧密排列,一些乡绅在这种小面积的隙地里营造小园林。“宅傍与后有隙地可葺园,不第便于乐闲,斯谓护宅之佳境也。开池浚壑,理石挑山,设门有待来宾,留径可通尔室,竹修林茂,柳暗花明,五亩何拘,且效温公之独乐。”[39](P837)桑争稻田,利润趋高,高雅的成本也提高。许多乡绅也可好好利用桑林景观。双林镇镇北有一处六七顷大小的田地。明代南浔的董份购得后从 “四围桑柳中画为池,芙蓉绕岸,菱芡浮波,多构台榭,邀名俊读书其中”。一旦大家庭崩溃,兴盛一时的园林也很快转化为桑林。双林镇沈家园原为明末沈秱宅第的后圃。“与族人楷宅连,故园亦属楷,花木甚多,池可二亩,余皓月澄波,濳鱼游泳。国初楷宅被焚,园遂废,今桑柘成阴,余成廛舍矣。”[40](P528-529)大园林由于经营成本上升被废,废弃后的园林自然被小农开发成桑基乡村。嘉兴南湖的勺园非常有名,钱谦益、柳如是和吴梅村在此留下诗句。由于水面较多,废弃后成为渔庄。 “惟老柳数十枝,蘸波稍雨,尚是当年故物。遥望之,幂历迷离,犹极有致。舍舟缘陂而入,则渔娃罟师七八家。芦中系艇,柳下晒罾,蟹簖虾笼,错落滩畔,亦颇不败人意。”乾隆年间成为渔村,许姓人增多成为“许家村”,渔业资源不能养活这么多人,田野逐步与周边地区同质化,成为桑基圩田的村庄。只是旧时的园林仍有一点痕迹,现代人仍会看到“村内陂塘曲径,风景依然秀丽”[41](P32)。
小乡绅只好在房屋旁挖池栽竹以维持雅致,同时栽桑获利。张履祥言:“基址、坟墓,各宜思粮之所出,坟旁种芋芅,便可取薪。基址宽旷,则前植榆、槐、桐、梓,后种竹木,旁治圃,中庭植果木。”下层乡绅要像农民那样经营稻田,“大凡田所坐落,平日决宜躬履畎亩,识其肥瘠,计其宽隘。及泥荡水路,莫不画图详记”。一旦租出土地,还要非常详细地了解佃户的生产生活状态[42](P88、268、275),越来越像一个小地主,生活场景越来越缺乏多样性。陈确认可种在山边的桑树有着相对的雅致,他称赞一位友人的居处时言:“周案桑田,闲闲十亩,可为隐者之居。居前后皆山,其南山青松深处,与邬子之间相对者,则秋浦、磊齐二吴先生之墓在焉。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43](P219)山水之间有桑树,略有兴味。
三、物种结构与社会分工
春秋战国期间,孟子在小农生境中设计了桑的位置,其设计既照顾到小生境也关乎大环境。大环境的山林与湖泊之物种依赖官方管理,百亩之田和房前屋后的动植物由小农安排。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4](P54-58)战国时期,北方田野的大环境已逐步丧失。嘉湖地区也面临着大环境丧失,小环境重复的问题。明清时期蚕丝利重,百姓以桑蚕为重,田野中的野生动植物逐步减少。但士大夫与小农的环境仍有分别,其房前屋后植物与家庭饲养的动物仍有不同。
后期的文人虽然保留着歌咏田间桑树和采桑女的传统,却不愿意在自己的房前种桑。余怀从《莆风清籁集》辑了一首很著名的 “苕溪四时艳歌”,诗中没有桑树的位置。 “兰苕发春香喷玉,风篁拔地敲新竹。雪水分流合四溪,浅草茸茸遍山谷。文舠擁酒看桃花,绿叶青青是妾家。屋里镜奁藏小凤,门前杨柳散啼鸦。”[45](P175)这里有 江南最一般的普通景观树种,却没有桑树。柳树本是北方物种,因植柳可以固堤,故柳树在江南随着塘浦圩田的兴起而大量推广。唐初的柳岸应是大圩之岸。白居易有诗:“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杭州一带感潮河多种柳, “浦干潮未应,堤湿冻初销。粉片妆梅朵,金丝刷柳条,鸭头新绿水,雁齿小红桥”。苏州塘浦圩田发达,种柳最多。 “金谷园中黄袅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46](P1220、1544、1662)宋 代 以 后 大 圩 崩 溃,小圩增多,变窄的圩岸会减少柳树的种植。宋代士大夫家里种植甚多,且品种甚高。 “柳,以垂者为贵。吴下士大夫家,有得凤州种者,其半拂地,复堆如尺。石湖、绮川两傍亦有之。”[47](P450)
桑基圩田扩展的确使植柳大为减少,但这一过程是缓慢的。前文所述的南宋朱淑真诗中生境仍然多有柳树,范成大关于余杭一带的诗歌也提到了桑与柳。 “落花流水浅深红,尽日帆飞绣浪中。桑眼迷离应欠雨,麦须骚杀已禁风。牛羊路杳千山合,鸡犬村深一径通。五柳能消多许地,客程何苦镇匆匆。”[48](P28)元代的太湖湖田需要固堤,柳桑并重。 “浙西在水中做世界,官司常常深浚水路,居民常常修筑围塍。自丙子年水政废弛,积水不去,一遇淫雨,桑柳枯朽,田土荒芜,百姓离散亡。”水利崩溃使桑柳枯死,恢复这种景观就要恢复水利社会。“古来各围田甲头,毎亩率米二斤,谓之做岸米,七八月间,水涸之时,击鼓集众,煮粥接力,各家出力浚河,取泥做岸。岸上种桑柳,多得两济,近因水涝,围岸四五年不修治,状若缀旒,桑柳枯朽。”[49](P31)由此可以看出,元代农村仍然重视柳树种植。
六朝时期的江南文人像北方文人一样爱竹。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讲兰亭之处 “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50](P2099)。有大量用于庭院景观的竹品种分化,谢灵运言: “其竹则二箭殊叶,四苦齐味。水石别谷,巨细各汇。既修竦而便娟,亦萧森而蓊蔚。”沈约注曰: “二箭,一者苦箭,大叶;一者笄箭,细叶。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黄苦。水竹,依水生,甚细密,吴中以为宅援。石竹,本科丛大,以充屋榱,巨者竿挺之属,细者无箐之流也。修竦、便娟、萧森、蓊蔚,皆竹貌也。”[51](P1761-1762)苏轼在杭州时仍感到茂林修竹。 “曲水池上,小字更书年月。如对茂林修竹,似永和节。”[52](P87)当时环境中的竹林非后期可比。随着平原地区开发,大规模竹林减少,优雅的小竹林和单株竹兴起。元代李衎的 《竹谱》记载了许多湖州产的竹类。哺鸡竹原在山中,亦进入人家的庭院。 “哺鸡竹又名鸡捕竹,出苏湖山中,人家庭院亦或植之,不甚高大,凡八种,大概相似,节叶差异,笋出亦有早晚,食之极甘脆。”还有一种鸡窠竹,“鸡窠竹,江南处处有之,为篾柔靱,秋生笋,每一竿有十数笋绕之,如鸡抱子”。高大竹子本山中之物,为了产笋也引到平原。“象牙竹出会稽山中,大概与常竹不异,但笋出肥壮,微弯屈且纯白,状如象牙,故名。笋味甚佳,嘉禾境内亦时或有之。”一些竹非常适合在池塘边以野生状态生长。“莠竹喜生池塘及路傍,茎细节髙,近下曲屈,状若狗脚,南土多茅少草,马见此物必欲食之。”又有间道竹。 “间道竹,生两浙山中,人家庭院亦有植之者,竿如水竹,节差密,叶如毛头。竹颇痩长,叶上有淡黄间绿细勒道五七行,每丛或生至十四五叶。吴兴周公谨知县其别业在杭,一丛数本。”[53](P59、74、111、133)文 人 尽 量 在 其 生 境 中 安 排种竹。倪赞的 《水竹居图》中 “远岫平林,山前溪水渚坡,坡上杂树五株,树后茅屋丛篁”。其《松亭山色图》更画出了房前屋后的“长松修竹”。这时的小生境中有竹松搭配,甚为高雅[54](P132、176)。松竹搭配的居住点山边有,平原难有,松不像其他景观植物一样可以人为种植,居住点附近的单株松往往是早期植被群落的遗存。元代的生境不像后期那样破坏严重,画中才有松。后期的家居环境找不到松。唐寅的 《水事幽居轴》只以一丛居屋边的高挑竹丛显其风韵[55]。长期以来,文人寄性情于竹。嘉兴李良年言:“予少嗜竹,园居种竹数亩,环于吾堂,未尝一日不看竹也。后被家难,弃其园,徒市中,隙地绝少,自叹不复有昔日之乐,而移其嗜于画竹。”[56](P489)
明代的圩岸柳明显减少,小生境内多种桑竹。长兴 “多良田桑竹之饶,耕鱼之业,足以卒岁”。“筼筜”的古意是水边竹,挖塘种竹,正合士大夫的雅兴。吴兴的李元润以前定居市镇,后迁乡里, “徒莲庄蔪荆薙草而居,公志大,虽贫能经营,爽豁有藕池、桑竹、圃园、馆亭,可以憇数十客,文学益有名,士多附宾”。经营桑竹可以脱贫致富,更兼商业经营。随着竹类用品的兴盛,吴兴的竹类也成为经营的项目之一了,“吴兴当具区之浸,苍弁群山,蜿蜒而负郭。苕霅二溪交灌争输,其产多蚕桑竹木,鱼稻果蓏之利,故其俗号殷富,然其人习水走陆负,重历险悍者业渔盐、事剽劫”。即便如此,大面积的桑竹仍然可以形成美景, “不溪襟带清邑,每过輙乐其清佳,壬子孟秋,偶得半日闲荡,舟干元山下板桥,跨曲港,水色如碧油,桑竹映发,使人幽绝”[57]。这里所说的是余不溪周边的桑竹景观。小生境中少柳,但柳仍种于主要的水路沿岸,吕留良有诗: “船经柳树根中出,人度芦花梢上来”。在村庄中,由于吕留良比张履祥较为富裕,其二十多间房屋的家园仍然有两个养鱼池,既种桑树也种柳。 “南阳庄屋廿间多,两个鱼池一种荷。临水轩窗供老友,遮桥桃柳引村婆。青桑出子虫铺蟥,紫竹开花雀羃窠。百事荒芜须振刷,跛奚便了奈愁何。”[58](P359、375)
至于动物的种类,士绅与小农有甚大的差异。为了生态农业的持续,小农不得不养猪、养湖羊。“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59](P217)种田伴随着养猪环境,读书却需要一种相对安静优雅的庭院,士农环境必然有分异。小农的养殖业与桑基农业相结合,形成最有特色的生态农业。鱼塘本身可以维持生物多样性,形成农业生态系统循环的源与库。为了维持鱼塘生态系统,小农尽可能地从外部摄取资源,除了蚕粪以外,还有其他草和小生物。“湖州畜鱼必取草、籴螺蛳于嘉兴,鱼大而卖,则价钱贱于嘉兴。盖吾地鱼俱自湖州来,及鱼至市巳离池数日,少亦一二日矣,故鱼瘠而价不能不贱。若以湖州畜鱼之法而尽力于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鱼价复高,又无溃溢之患,损瘠之忧,为利不已多乎。陶朱公古法即不能用,湖州畜法可仿也。尝于其乡见一叟戒诸孙曰:‘猪买饼以喂,必须资本,鱼取草于河,不须资本,然鱼肉价常等,肥壅上地亦等,奈何畜鱼不力乎?’”[60](P1420)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系统几乎是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他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61](P51-52)
小农家庭还要营造人为的小生境以供养蚕,除温室外,还要预备山棚。蚕在未驯化前原吐丝于树,为了诱导蚕在家庭环境下吐丝,要人为地制造出山地树木假象。“蚕老作茧架以处之,谓之山棚。须因地制宜,牢固平稳,需用竹木簾帚绳索诸物,宜先时一一整顿,屋多,棚与地蚕各据一室,屋少者,即于地蚕上架之。”蚕入山棚以后,山棚下“著火一周,用炭火极旺”,其时 “小蚕宜软,老蚕亦宜软,软则易于成茧”[62](P823)。小农家庭养蚕用木炭生火,而江南柴炭资料少,小环境形成不易。小农要养蚕,一般乡绅也养蚕。张履祥言: “小女因蚕务,在舍日久,有失侍奉之节,心窃不安。但此事实为吾乡衣食之本,妇功之所特重者。两载以来,见其丝茧不成,必缘育饲不尽其道,故欲其就母氏再加教习,使得熟谙,他日不至休其蚕绩,以懒妇隳损家声,则区区私愿,所祈不负明德者也。贫家之女,不期俭而俭,所忧不勤耳。”[63](P156)张的训女方法是嘉湖地区生存竞争所致。
四、小结
自宋代以后,嘉湖地区是江南经济社会的新成长区。小生境使这一地区承载了大量的人口,承担了江南重赋,也滋养了大量的人文知识分子。尽管田野日趋单一化,各阶层人民勤劳经营,田野生态仍然相对美好,诗人称明代最好风景是农桑。“小艇出横塘,西山晓气苍。水车辛苦妇,山轿冶游郎。麦响家家碓,茶提处处筐。吴中好风景,最好是农桑。”[64](P33)越来越小且越来越农业化的田野,形成了最好的生态农业,滋养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审美意识。尽管景观开放度和物种丰富度大不如以前,小生境也容易使人封闭自守,许多知识分子的确走向“慎独”,但这一地区毕竟是中国最好的经济与生态景观区域,大量知识分子潜隐乡间,使小生境充满了人文与生态之美,明末诸贤也在这种小生境内产生。
[1] Wen Dazhong and David Pimentel.“Seventeenth Century Organic Agriculture in China:Ⅰ.Corpping Systems in Jiaxing Region”.HumanEcology,1986,14 (1):1-14;Wen Dazhong and David Pimentel.“Seventeenth Century Organic Agriculture in China:Ⅱ.Energy Flows through an Agroecosystenm in Jiaxing Region”.HumanEcology,1986,14 (1):15-28.
[2] 唐长孺:《三到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唐长孺文集——唐书兵志笺正 (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1。
[3][4][51] 《宋书》,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梁书》,卷25,徐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6] 黄节:《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7] 《宋书》,卷82,周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校》,第71卷,《白苹洲五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 苏舜钦著,傅平骧、胡问陶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第3卷,成都,巴蜀书社,1990。
[10][19]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 《苏轼诗集》,第32卷,寄题梅宣义园亭,第47卷,秋晚客兴,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12] 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第19卷,水利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3] 徐松:《宋会要辑稿》第5册,食货六,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北京,中华书局,1957。
[14]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15] 张内蕴、周大韶:《三吴水考》,第3卷,吴江县水道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7册,史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6] 杨建峰编:《文徵明》,第577册,史部,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
[17] 王士禛选,闻人倓笺:《古诗笺》,五言诗,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8] 李昉:《文苑英华》卷280,乐府十七,吴均:陌上桑,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4册,集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0] 朱淑真撰,魏仲恭辑,郑元佐注,冀勤辑校:《朱淑真集注》,第1、4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
[21] 王炎:《双溪类稿》,第22卷,上宰执论造甲,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5册,集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2] 王冕著,寿勤泽点校:《竹斋集》卷下,陌上桑,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23][39] 徐献忠撰:《吴兴掌故集》,第11卷,水利,山乡水利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24] 嵇曾筠等监修,沈翼机等编撰:雍正 《浙江通志》,第102卷,嘉兴府,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1册,史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5] 董斯张:《吴兴艺文补》,第32卷,顾应祥:“东林山新建眺远亭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679册,集部、总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6] 计成原著,陈植注释:《园冶注释》,第1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27] 同治 《晟舍镇志》,第2卷,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4卷,上海,上海书店,1992。
[28][29][60][63] 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第5卷,别楮,第50卷,第6卷,与陸教垂,北京,中华书局,2002。
[30] 董斯张撰:崇祯 《吴兴备志》,第17卷,水利第1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史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1] 朱彝尊撰,王利民等校点:《曝书亭全集》,《笛渔小槀》,第4卷,古今诗四十四首,丹徒公于濋源堂后穿池种荷赋诗四章,敬次原韻,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32] 沈文华:《抓大事、促大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情况汇报》,桐乡,桐乡县档案馆,农业机械水利局档案,56-1-8,1973年12月12日。
[33] 朱国祯撰:《涌幢小品》,第7卷,堤利,北京,中华书局,1959。
[34][61] 中共浙江省嘉兴地方委员会政治研究室编:《嘉湖蚕桑资料》(内部资料),第2部分,民国时代生产概况,1961。
[35] 俞荣梁:《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补农书〉的启示》,载 《农业考古》1985 (1)。
[36]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所:《中国肥料概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
[37] 张履祥辑补,陈恒力、王达校释:《补农书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38] 宗源翰、郭式昌等纂修:同治 《湖州府志》,第29卷,舆地略,风俗,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第24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40] 蔡蓉升:《双林镇志》,第2卷,水道;第11卷,古迹名胜,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卷(下),上海,上海书店,1992。
[41] 吴藕汀:《鸳湖烟雨》,北京,中华书局,2010。
[42] 陈恒力编著,王达参校:《补农书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
[43] 陈确:《陈确集》上,文集第九,纪二,暮投邬行素山居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
[44]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2卷,梁惠王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
[45] 余怀著,李金堂编校:《余怀全集》诗集,味外轩诗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6]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校》,第18卷,《忆江柳》;卷二十三,《新春江次》;卷二十四,《苏州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7] 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第29卷,土物,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48] 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第3卷,余杭道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9] 任仁发:《水利集》,第3卷,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0] 《晋书》,卷80,列传第50,北京,中华书局,1974。
[52]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劝金船,北京,中华书局,2002。
[53] 李衎:《竹谱详录》,第3、4、7、10卷,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54] 杨建峰:《元四家》,倪赞 《水竹居图》,《松亭山色图》,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
[55] 唐寅:《水事幽居轴》,上海博物馆藏。
[56] 李良年撰,朱丽霞整理:《秋锦山房集》,第17卷,墨竹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7] 董斯张:《吴兴艺文补》,第34卷,第40卷,袁袠:复刘司空书二首;王穉登:喜留亭记;胡胤嘉:不溪偶记,明崇祯六年刻本。
[58] 吕留良著,徐正等点校:《吕留良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59] 姜皋:《浦泖農咨》,续修四库全书,第976册,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2] 光绪 《菱湖志》,第12卷,蚕桑,《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4卷,上海,上海书店,1992。
[64] 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第492卷,明诗次集一百二十六,暮春山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