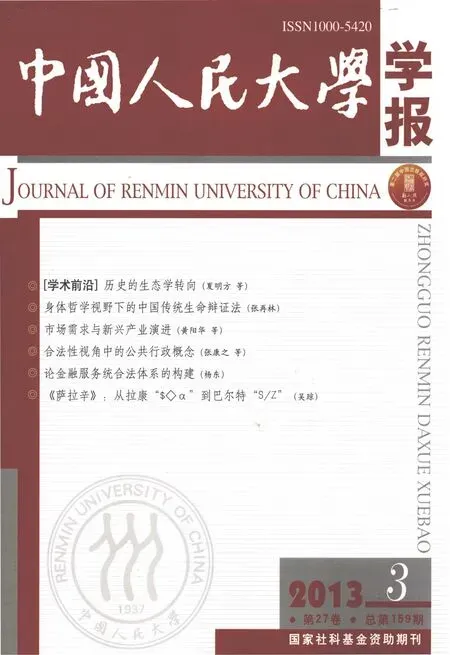没有边界的城市:从美国城市史到城市环境史
2013-01-22侯深
侯 深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城市史学经历了数十年发展之后,现已渐趋式微。然而如果从另一角度考察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领域更为细化,并且同其他的史学分支学科相结合后展现出新的生机。在这些新生学科中,城市环境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试图梳理城市环境史将自然与城市在历史背景下进行结合的过程,考察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其发展前景。
目前国内外对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兴起及流变均有研究见诸文字,然而这些研究基本侧重该领域的形成初期,分析其兴起与环境史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鲜少将其置于美国城市史学研究的背景下进行反思,同时对环境史学自身方法与思维转向对城市环境史产生的深刻影响重视不足。①关于美国城市环境史学理论的国外重要研究文献包括:Martin Melosi.“The Place of the C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1993,17(1);Christine Rosen and Joel Tarr.“The Importance of an Urban Perspec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1994,20;Harold Platt.“The Emergence of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Urban History,1999,26(1);Joel Tarr.“Urba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Complementary and Overlapping Fields”.In Christoph Bernhardt(ed.).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European Citie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New York:Waxmann Verlag Gmbh,2001;Andrew Isenberg.“Introduction:New Directions in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Isenberg(ed.).The Nature of Cities:Culture,Landscape and Urban Space.Rochester,New York: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6.国内重要相关研究文献有:包茂红:《马丁·麦乐西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载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 (4);高国荣:《城市环境史在美国的缘起及其发展动向》,载 《史学理论研究》,2010 (3)。正因如此,现有研究无法充分解释为何在威廉·克罗农的拓荒之作 《自然的大都市》大获成功之后,美国城市环境史学者却很少循此路径阐释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生态与社会的历史变迁。[1]本文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美国环境史中 “文化分析”方法的大行其道有密切联系。由于文化分析聚焦种族、阶级与性别,以及这些不同社会群体对自然的认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集中在城市行政边界的内部,分析下水、垃圾、污染等环境问题以及各色族群的环境遭遇与思考,忽略了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对其不断扩张的腹地产生的生态影响和两者之间长期进行的生态交换。因此,本文在结论部分指出,城市环境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在时间、空间与思想维度上打破城市的边界,从而发掘城市与其腹地之间密不可分的生态与文化联系。
一、城市史的“环境”转向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属于城市的时代。汹涌的人潮从乡村流入城市,在那里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当20 世纪到来之际,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已远远超出乡村人口,而城市人口的绝大部分又居住在大都市当中。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工业的种种发明将更多的人从躬耕田畒中解放出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大量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此同时,食物、水以及其他资源从乡村源源不断地运入城市,以支撑城市的运行。然而,城市人群却基本上没有参与生产这些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资源。一个普通的城市人同他们所生活的地球,或者与那些延续他们生命的自然力量与资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
美国可以说是站在这个急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之最前沿。正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化的时代中,产生了当代美国历史学。大部分当代美国历史学者成长、生活在城镇、郊区,因此,对他们而言,渴望理解城市的历史是自然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历史是城市的时代,如果希望对其做出透彻的诠释,历史学者就必须关怀城市的历史以及它在推动现代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较为平静、单一的乡村历史相比,会聚了不同族群、文化的城市历史似乎更加丰富多彩、高潮迭起,而以此为主题的史学研究相对而言也更为多元、广泛。
当城市开始在美国景观上迅速蔓延之际,美国学者便开始书写城市的历史。但是,城市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整个美国历史学界开始脱离先前政治史的圈囿时,方才真正出现。这一新生领域开始研究城市的历史特点和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作用。那些自成一家的新城市史学者倾向于将城市视为一个进程,而非一个具体的地方,借用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方法,开始对城市中间那些泯灭自己声音的人群予以关注,以对抗传统史学的精英研究。新城市史学的主题主要包括社会与政治的变迁,阶级关系的起源,以及种族、民族与性别冲突。而这个新领域也呈现出跨学科的特色,在其研究中大量引入社会史、建筑史以及城市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美国新城市史学的拓荒之作为斯蒂芬·塞思托姆出版于1964年的经典著作: 《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该书采用了大量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研究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在1850年至1880年间的社会变迁。它对以后10年甚至20年间美国城市史的叙述都产生极大影响。该书运用 “自下而上”的叙述角度,亦即通过社会底层人群的见闻、经历进行研究,同时对不同族群向上流动的社会模式加以比较。[2]与此相比较,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城市传记的史学叙述方式则较少受到社会学的影响,试图对一个特定的城市进行历史叙事。同个人传记史家相似,城市传记史家力图将城市中间各种复杂的侧面串联起来,如其源起、领袖、经济基础、交通、市政、地理扩张、人口特点、学校等,叙述一个城市的历史。每一个特定的城市赢得了某种综合个性,而不再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因此,城市再次变为一个具体特殊的地方,拥有丰富的细节和叙事的趣味,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埃德温·伯罗与麦克·华莱士在1999年出版的 《戈瑟姆:1898 年前的纽约城市史》。[3]
然而,尽管在30年前城市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但是它此后的发展,却颇有几分虎头蛇尾的味道。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这个学科似乎已见式微。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便是,美国的很多大学停止开设这一领域的课程。堪萨斯大学是美国典型的州立大学,以它为例应具一定的代表性。在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共有近40位教师,100余个研究生,近500个本科生,但是该系却几乎没有开设城市史方面课程。而在美国每年的就业市场上,为城市史或者以城市史为主的新设职位几近于无。城市仍然在一天天地扩张,为何一个曾经如此充满希望的学科开始丧失它的吸引力?
近年来,城市史学者一直在讨论其领域的未来。克莱·麦克沙恩提出了对这一领域颇为悲观的结论。他指出这个领域非但不再是史学的宠儿,而且还落后于史学的整体发展。在他看来,城市史缺乏清晰的界定与核心,对风云变化的社会现象的讨论匮缺,也失却了方法论上的精确。他援引斯图尔特·布鲁民的观点,认为 “在城市史著作中,缺乏理论或者方法,缺乏这一学科的特点,这是一个迄今仍然准确的观点。当然也有例外……但是他们都并非主流……这种对理论与方法的兴趣的缺失将很有可能使我们为同行,特别是社会科学家所轻视”。
然而,城市史中存在的问题似乎要比缺乏方法论上的精确更为严重。麦克沙恩同时承认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都已陈旧,今天,已没有多少新论著来推动该领域前行并使之更具影响力。在列举比较了当前被引率较多的书籍后,他指出,事实上,所有这些作品的被接受程度都未能使它们成为广泛认可的经典著作,而引用率最高的那四部作品甚至不是学术著作。麦克沙恩总结道:“看来城市史与历史学科内其他领域存在极为显著的断裂……然则城市史究竟是否仍是一门学科,如果它没有产生一部经典之作,即使是一部有争议的经典之作?”[4]这一悲观评价至少说明:在美国,城市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难以保持其一贯性或者继续其对历史学者的持久影响。它没有吸引新生代中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者的力量,也未能撰写出促使这个学科继续发展的著作。在城市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城市史学者却脚步拖沓,意志不坚。
我们不妨以一种更为乐观的角度来审视之:城市史并非衰败了,只不过是发生了改变,它渐渐地脱离了同社会学领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却以一种城市史学者未曾预知的方式,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开始重整旗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美国历史学科发展的必然。美国城市日趋扩张,其问题亦日益复杂、细化。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城市,或者对具体某个城市进行个案研究,无论从精准性、可行性,还是历史叙事的吸引力而言,都比从前将城市化视为一个统一而缺乏个性的过程更具魅力。因此,一方面,为个体城市立传成为众多新生代城市史家的选择。而另一方面,城市史自身开始逐渐分裂或融入其他的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或者种族、阶级、性别研究,或者环境史。城市史并没有渐渐死亡,它只是改变了重点、角度和方法。
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将环境史定义为对历史中人类社会与文化同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他在 《地球的转变》一文中写道:“环境史研究的是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位置。它所研究的是非人类世界,一个究其根本不由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与过去所有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处他所指的自然是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的一切生物的、地理的以及物理的根本元素。自然是一切非科学或技术的各种力量的集合;至少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这些力量包括气候与天气的周而复始,各个大陆的地质状况,太阳的能量,动植物的进化与分布,生态系统的形态与运行。所有的这些力量构成了一个人类必须学会与之共存并且适应的世界,即使我们也一直试图逃离这些力量。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人类对自然世界施加的影响在不断增长,甚至在今天地球的气候都在因人类的活动而改变。但是人类只是改变自然,并没有创造自然。自然从来都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秩序,相反,它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这种变化的状态早在人类诞生之前便已存在。而毫无疑问,自然也将从我们所强加的改变中存活下来,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灭绝之后的很长时间,它仍将以某种形式存在。[5](P46-48)
那么自然,作为非人类所创造的力量与存在的组合,又在城市——这一文化的产物中扮演什么角色?无疑,城市是人类生活的环境,然而早先的城市史却很少将城市视为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环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美国城市史学家对城市的历史进行研究时,往往对人类更为宽广、古老的经历,采集、游牧、农耕时代的经历,及其同城市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对城市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等都心存漠然。城市被视为人类独有的创造,同自然毫无接触,关于它的故事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城市被看做是一系列建筑、街道、政治集会、工厂及其内部的劳资冲突,以及不同族群的人们相接触、碰撞的区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在研究城市问题时引入了人文生态学,虽然冠以生态之名,不过是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作为一种模型,套用于人类社会之上。借用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群落、生态位、小生境、竞争、平衡等概念解释城市社区中各个群体、阶层的变迁、对抗与合作。人文生态学对积极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城市史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他们中间,鲜少有人将城市看做河水流淌、植物生长、微生物蔓延、能源消耗、物质资料相交换的地方,一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人类自身的健康相互纠结的地方。虽然这种旧有的研究将城市与自然人为隔离,但环境史学者却正在将城市带回自然当中,或者将自然带入城市当中,将城市视为一个人文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相互交织、作用、共同演化的有机体,从而赋予城市史研究一个全新的方向。[6]
城市—郊区景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环境史领域中崭露头角,到20世纪90年代立稳阵脚,现在已是该领域研究中最受欢迎的新视野。历史学者意识到城市不仅仅对即使距离它最为遥远的荒野地区的使用或者保护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城市自身也是自然保留着自己的力量并且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地方。自然不止是远方的草原或者森林,它同样包括我们居所周围流动的空气与水,那些令城市机器忙碌不堪的能源,还有所有在城市中间寻找到它们的生态位的植物、动物与微生物。凯特勒恩·布罗斯南、安德鲁·赫利、马丁·麦乐西、亚当·罗姆、乔尔·塔尔等学者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人与自然之间交界面的思考,并且证明人类的居住区同人的生理系统一样,是一系列存在物的集合,需要补给与排泄,而城市的新陈代谢系统的运作,就像农场或者工厂,也同样根植于自然当中,即使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人工的创造与自然力的共同结果。[7]
在一篇关于城市环境史的综述中,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开创者之一乔尔·塔尔将现有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发展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研究人为环境与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二,研究针对缓解环境问题所做的社会反应的努力与作用。第三,探讨自然环境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第四,分析城市与他们不断扩大的腹地之间的关系。第五,研究城市中间种族、阶级、性别与环境问题的关系。[8]在这五个方面,环境史学者在最近的20年间不断有新作问世。从早期麦乐西等人对城市环境进行的综合研究,到今天诸多学者关注一个具体的城市,彼处的城市、人类活动与思考、与它的周边自然的相互作用。至此,城市环境史研究也越来越扎根在土地中间。新一代的城市环境史学家同他们的环境史同行一样,关注城市景观中细节的变化,寻求每一个具体城市在环境史意义上的特性,重新书写一个城市的“传记”。
二、自然的大都市
如果说早期城市环境史学家同城市史学同行一样,关注点尚在城市内部,考察人类活动、政策实施与技术使用,如垃圾与污水处理,能源利用与工业污染等对城市环境与人群健康产生的影响。那么,新的研究模式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均打破了城市的人为边界,通过时间上将城市的演化史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所经历的更为漫长的农牧业历史的结合,从而在空间上对城市环境史的疆域做出了根本性的拓展,对城市与其腹地的环境进行整体的有机考察。这一研究始于威廉·克罗农所著的 《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一书。《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于1991年,赢得次年的班克罗夫特奖。它不仅为城市传记史的书写开创了一个新范例,也为城市环境史的开疆拓土打开了新的局面。芝加哥,这个在美国西部异军突起的大城市,长期以来是美国城市史中的研究焦点。无论是传统的政治史学家抑或新生的社会史学家均在那里找到施展史才的天地。然而克罗农的著作却将史学家研究芝加哥的天地扩展到了整个西部的苍穹之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思考这个自然的大都市形成的原因。
在 《自然的大都市》为城市环境史开疆拓土之前的十年,塔尔与麦乐西两人已在环境史的版图中为这一新领域树立了地标,然而 《自然的大都市》的出版具有两层重要意义。①关于塔尔和麦乐西对于城市环境史的贡献,国内学者已有详论,本文不再赘述。除包茂红、高国荣文外,参见王栎:《美国环境史学家乔尔·塔尔的城市环境史研究》,载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 (1);毛达:《城市环境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探析》,载 《世界历史》,2011 (3)。首先,在20世纪80 年代博得盛名的环境史学家如沃斯特、克罗农、罗德里克·纳什等人皆以农业与荒野环境史著称,在环境史本身尚属新兴学科之际,城市环境史更是边缘。而作为环境史风纪创立者之一的克罗农投身这一领域,则令城市环境史进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中心地带,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克罗农通过 “商品流动”对都市及其腹地进行二重研究,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经济系统的交叠层面上,追索城市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模式。
克氏的新模式建立在对冯·杜能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创立的杜能圈所做的生态史解读之上。1826年,冯·杜能出版 《孤立国》(TheIsolatedState)一书,在该书中,杜能对中心城市与其腹地的经济与地理关系设计了一个简化的模式。一个中心城市譬如一个独立国,其腹地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与城市市场直接发生联系。通过计算地租与交通耗费,农民理性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据此而决定城市腹地农业生产的环状分布。距离城市最近的生产圈主要从事蔬果与乳业活动;第二圈则为林业圈;第三圈是粗放型粮食生产圈;最外一圈进行畜牧业生产。克罗农承认,虽然相较于城市及其腹地复杂多变的实际关系,这一假设过于简单抽象,然而它仍能够行之有效地解释芝加哥在19 世纪的迅速崛起。不同点在于杜能圈的林业圈处于城市外围的第二环,遵循普鲁士自17世纪以降发展的 “有效利用”的科学林业,而美洲大陆在芝加哥兴起之际尚且处于资源不竭的神话当中,因此毫无节制的森林砍伐位于畜牧业的外环,而最外围则是美国西部地区19世纪的荒野与土著人的采集狩猎与皮毛贸易。当然,克氏对于杜能圈的运用也绝非止步于局部上的修正。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一个经济与地理学的理论作出生态学与历史学的发展,使凝固的理论融入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9]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克罗农指出杜能圈对于城市在其腹地的辐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演替的故事。资本所向披靡的力量改变的不仅仅是令林立高楼取代遍布河畔的丛生野蒜,同时也刺激了整个大平原地区经济体系与生态系统的变更。正是在这里,克罗农走出了割裂城市与自然的人为边界,在城市资本运行的井然秩序中发现了城市与城市之外乡村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杜能圈的每一环新的拓展都是一个新旧生态系统交替的过程,整饬的麦田取代本土的草原,饲养的牛羊占据了野牛群的生态位,而五大湖地区的森林则在肆意的砍伐中迅速消失。克罗农强调,这是第二自然取代第一自然的过程,是一个由经济、技术、政治力量塑造的生态系统取代自然力量形成的生态系统的过程。
“第二自然”的概念绝非克罗农的首创,然而将之引入环境史的研究却是自克氏始。早在《土地的变迁》一书中,克罗农便已通过土著人对新英格兰土地的使用模糊地提出了这一概念,而在 《自然的大都市》中,克罗农开始坚定不移地推动对此概念的思考。此概念是对城市环境史学家长期讨论的自然与人工环境关系的调和,其初衷在于强调人工创造的环境与自然的生态系统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而环境史恰恰发生在这种联系之上。然而,在克罗农的引导之下,对于第二自然的讨论则不再停留于城市环境史的领域,而是吸引了大量的后现代史学家,令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对 “自然”进行解构。①在 《自然的大都市》出版后三年,克罗农编辑出版了论文集Uncommon Ground: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New York:W.W.Norton &Co.,1995.在其中,克罗农及其他作者对自然、荒野等概念进行解构,推进了对 “第二自然”的思考。起先,在部分环境史学家看来,人造环境一词太过冰冷,而第二自然则更为温情脉脉。此后,在后现代主义浪潮冲击之下,部分环境史研究者也积极投身于语言学转向的洪流当中。在后现代的解构之下,自然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建构,而非客观的物质存在。而同此浪潮互为声势的则是以种族、阶级、性别为主线的后现代文化分析。对于任何一位新锐史学研究者而言,后现代首先意味着挑战权威,个中过程极为冒险,然而又充满趣味智性。沃斯特、克罗农等人当年在历史学界的异军突起便是对兰克以降西方史学范式的挑战,而在环境史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当日的叛逆已成今朝的权威,新的叛逆者应运而生。这一波新的挑战便来自深受社会史研究浸淫的中青代环境史学人。他们认为,老一辈的环境史学者将自然与人关系中的人作为类,因而罔顾在此交互作用中,科、属、目、种等各色族群、阶级、性别的人同自然关系的不同。这里预设的前提是自然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产物,地球上已无未经人类干涉的生态系统。如此一来,形成了后现代环境史学家的逻辑:既然自然是一种文化建构,人工与自然环境之间则不存在差别,那么,环境史对自然的强调便成为无的放矢,一切研究便又回到对于人工环境或曰文化力量的讨论之中。
沃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转换的到来,因此强调自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存在,从而对抗历史研究乃至人类思想中对待自然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傲慢和忽视。在其经常为城市环境史学家所诟病的段落中,沃斯特写道,在人类以各种方式对自然进行改变与修正的今天,“‘自然’和‘人工’之间似乎就可能不存在实际的区别了。然而,差别是值得保存的,因为它提醒我们,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力量在运转……这些力量冲击着人类的生活,激发起某种反应、某种抵抗、某种雄心。因此,当我们跨越人类自我关照的世界,并与非人类的区域相遇时,环境史便发现了它的主题。”②该文原为沃斯特为其所编辑的论文集The Ends of Earth:Perspective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所写的长跋。[10]
事实上,环境史自发端伊始,便未曾忽略对社会边缘或者弱势群体的关注。从沃斯特在 《尘暴》中对生态难民充满同情的描述,到卡洛琳·麦茜特在 《自然之死》中对女性与自然特殊联系的强调,到克罗斯比在 《哥伦布大交换》中对白种人文明优越论的质疑,再到克罗农在 《土地的变迁》中对印第安人生存状态的肯定,环境史学家在环境史开创之际,便挣脱了精英史、政治史的羁绊,发现了历史构成中的不同力量与关系。[11]与其同时代社会史创立人的不同在于,他们的视野更加广阔、深邃,使史学的关照穿透形形色色的事物,到达一个同我们息息相关而又不尽相同的世界中。自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这是环境史对历史学最大的贡献,而就此学科目前的发展来看,环境史学筚路蓝缕三十年后,在这场转换的冲击下,很有可能转回到 “人类事物”是史学唯一主题的老路上。
克罗农虽然勉力推动对第二自然的思考,但是如此发展势头却绝非他的本意。无论是在 《土地的变迁》中他所流露的对印第安人和谐土地关系的青睐,还是在 《自然的大都市》中对动物权利、道德经济的坚持,克氏始终怀有对自然 (或如他所言的第一自然)的存在的尊敬与同情。在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中,他着力在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的联系,而非泯然一同。就此点而言,克罗农与沃斯特对环境史发展的期许是共同的。正是在 “跨越人类自我关照的世界,并与非人类的区域相遇”中,这两位环境史大家得以声气相投、握手言欢。
回到城市环境史的研究,环境史文化转向的浪潮在这一人工与自然系统之间差异极其微妙的领域中风起云涌。 《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之后,一片美誉之中自有批评的不谐之音。其中最具分量的批评恰恰着眼于克罗农在一本城市史著作中对城市不同人群对自然的认识与需要的刻意回避。克罗农所讲述的芝加哥故事是资本力量驱动下自然能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转,而非城市中文化、经历大相径庭的人群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无疑,这与方兴未艾的文化分析手法多有龃龉。因此,虽然由于克罗农的加入,城市环境史得以大行其道,但真正追随克罗农所建构的城市环境史模式的中青代史家却寥寥可数。①继克罗农之后,力图打破城市边界,研究城市及其腹地生态与经济关系的著名研究包括:Mike Davis.Ecology of Fear:Los Angel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1998;Kathleen Brosnan.Uniting Mountain &Plain:Cities,Law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long the Front Range.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2002;Stéphane Castonguay.Metropolitan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Montreal.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11。
三、后克罗农时代
在《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两年之后,罗伯特·戈特利布的新书 《推动春天:美国环保运动的变迁》问世。[12]该书付梓以来,毁誉参半,然而无人能否认它对以往美国环保运动叙述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19世纪后期的环境改革被描述为城市之外的活动,无论是以科学林业开其绪的资源保护改革,还是以国家公园肇其端的自然保护运动,似乎总是在田间野外大展宏图。这种叙述无疑大幅度地窄化了一场远为复杂、综合的环境改革运动,也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内城进行的环境正义运动变成无本之木。戈特利布则指出,美国环保运动究其根本,乃是对19 世纪后期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的修正,而其出现的中心位于在此时期兴起的各大都市,集中体现为进步主义时期的各类城市卫生医疗改革。种族、阶级与性别在 《推动春天》的推动下,进入了早期美国环保运动史的疆域,而城市也在其中赫然崛起。
戈氏之书很难被视为真正的城市环境史著作,然其对城市环境史的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环保运动与政策都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主题,而城市在占据环保运动史半壁江山的进步主义时期环境改革运动研究中始终身份暧昧,对此,戈特利布的著作无疑有廓清迷雾之功。其对环保运动边缘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健康与环境健康的密切联系的关注,更对他的研究同行进一步拓展城市环境与不同社会族群之间关系的研究深具启发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戈氏对于美国环保运动起源的研究,并非试图恢复一场被史家窄化的运动全景,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将之再度窄化。作为一位环境正义运动的行动主义者,他自有其政治与社会诉求。当他将早期环保运动的阵地由乡村、荒野转移至城市后,他使工业城市社区的公共卫生改革成为环保运动发展的核心脉络。而据此论述,这场在很多方面超越人类狭隘的自我关照,追求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的平衡、美丽与健康的运动,似乎成为人类尤其是某个人类特定群体对自身健康的考量。自然在其叙述中再次被边缘化了。而这一倾向在运用文化分析手法的新一代环境史学人那里则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 《推动春天》之后,社会史学者安德鲁·赫尔利出版 《环境的不平等: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阶级、种族与工业污染,1945—1980》。此书堪称城市环境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的典范。其所选择的城市并非如芝加哥、纽约、匹兹堡等大都市,而是位于印第安纳州一个鲜为人知而饱受污染之害的小型工业城市——加里。赫尔利的研究揭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主要是居住于内城的黑人贫民与白人劳动阶级。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恰恰是环境污染中的弱势群体,而环境的不平等正是社会的非正义的体现。同大多数社会史学者一样,赫尔利在他的研究中表达出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深刻同情以及对环境不平等的严厉批判。然而,同大多数社会史学者不同的是,赫尔利的研究关注到了人类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之外的空气、水与能源。
赫尔利的著作在环境史学人中间大获成功,很快跻身大多数环境史研究课程的必读书目,而赫尔利的个人定位却饶富趣味。无论公开的访谈,还是私下的对话,赫尔利都将自己视为一位社会史学者,否认环境史学者的标签。一年一度的美国环境史学会也鲜少看到赫尔利的身影。在最近一次中国环境史学者高国荣博士为赫尔利所做的访谈中,一段对话颇引人深思。当被问及其目前所做的研究为何时,赫尔利回答说他目前没有从事环境史研究,而是在做历史遗迹保护的问题。他接着谈到,他的朋友——环境史学者大卫·斯特拉德林认为这仍然是环境史研究,并且强调但凡涉及地面景观的问题,无论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都是环境史研究的一部分。赫尔利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非人类的自然只有成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才能被算作环境史方面的成果。对我而言,环境史有这样一个门槛。自然应该是环境史研究的中心”[13]。赫尔利的否定不免令先锋的后现代环境史学人有一相情愿之嫌。但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从研究客体来看,一部自然隐退的城市史著作应当如何寻求环境史特具的视角,它如何能够超越前代的城市史研究;而从研究方法来看,一旦城市环境史研究为简约的文化主义所主导,它是否仍然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幸而,并非所有的中生代与新生代环境史学人都愿意踟蹰于人类事物与文化分析的旧邦。在2000年,亚当·罗姆出版了 《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蔓延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一书,为城市环境史研究再放异彩。其贡献表现在多个层面。首先,该书的开疆拓土之功不容忽视,20 世纪50年代后美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以批量住宅为标志的郊区蔓延,城市与乡村交界的郊区成为美国城市人群的基本栖息之地。在城市史的研究中,不乏关于郊区研究的佳作。但是在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中,罗姆则首开郊区研究之风气。然而,该书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它 “第一次使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切实地立足于由土壤、水源、动植物、空气以及人类所构成的土地共同体之上,考察在郊区蔓延的过程中,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各种矛盾,人们在生理层面、物质层面、审美层面、道德层面、科学层面以及生态层面对这些矛盾的认识与反思,及其对社会的影响”①有关笔者对该书的论述参见侯深:《〈乡村里的推土机〉与环境史研究的新视角》,载 《世界历史》,2010 (5)。。同时,罗姆能够坚守环境史始建时的初衷,与自然科学保持严肃的对话。由此, 《乡村里的推土机》既保留了历史学者所擅长的文本分析与历史叙事,又娴熟地采用大量缜密的科学数据与理论,使其对这个土地共同体的理解摆脱了文化政治学的羁绊。而这种跨学科的交流,更使得人文学者认识到,自然不是狭义的仅供解构的词汇,亦非仅仅透过人类审美想象方始存在的景观,更是客观存在的独立力量与物质现实。
罗姆的著作出版于2000 年,该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的分水岭。此后十年间,城市环境史研究蔚然大观,新作不断。从由麦乐西与塔尔主持的匹兹堡大学出版社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领域学者十年间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孜孜探求。②关于匹兹堡大学出版社城市环境史系列,请参见其网站信息:2012 -09 -05,http://www.upress.pitt.edu/browseDetailList.aspx?initial=43&type=series。此外,城市环境史学者还出版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包括:Martin Melosi.The Sanitary City: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Matthew Gandy.Concrete and Clay:Reworking Nature in New York City.Cambridge:MIT Press,2002;Matthew Klingle.Emerald City: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eattl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David Stradling.Making Mountains:New York City and the Catskill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在此中间,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于2010年关于波士顿的新作——迈克尔·罗森所著的 《查尔斯河上的伊甸园:创造波士顿》。[14]对于任何一位史家,重写波士顿这一美国最早的城市与文化重镇,都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自19世纪美国历史学发端,此城即成研究焦点,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相关研究不胜枚举。然而,罗森之书却得以在诸多佳作中异军突起,获得包括次年普利策奖最终提名等五种图书奖项荣誉。作为克罗农的高足,罗森在撰写他的城市史著作时,无疑对其师的大作深加琢磨。在他所讲述的波士顿导湖引水、填埋扩城、疏浚海湾、创建公园、发展郊区的故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自然的大都市》中所强化的城市同其腹地环境的内在联系。更进一步, 《查尔斯河上的伊甸园》将波士顿各类族群对待自然的期许与态度,以及因此导发的冲突与妥协引入讨论,对自然进行了文化的解构,加强了克罗农所思考的第二自然观念,由此而实现城市环境史的文化转向。
幸而,罗森的解构是谨慎且颇有节制的,虽然在一方面,他注意到不同文化、宗教、种族、阶级背景的人群对待自然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他们所向往的城市景观也存在差异;但是在另一方面,罗森并未将自然完全视为一种文化建构,从而彻底否定自然与人文景观之间的区别。正如波士顿景观的实际城市规划者,罗森这位波士顿城市历史的撰写者同样看到了自然对于波士顿人所设的种种限制,因此,他的著作描写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与争议,也是人作为一个共同的群体同自然之间的对抗、协调与依存。也正因为如此,较之以往的相关著作,罗森的新作对波士顿这座旧城故事的叙述更为全面深刻。
然而,如同他的大部分同行,罗森的著作并未能对克罗农所创立的城市环境史模式进行更深层次的拓展。克罗农在芝加哥崛起的历史中,看到城市的人为边界不仅局限了历史学者的想象,更是对城市本身演进过程的片面解读。因此,他呼吁打破城市的边界来研究城市的环境史。但迄今为止,虽然城市环境史学者在短短三十年间已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但他们的著作仍然大多驻足于城市的边界之内。他们讨论城市有机体内部的新陈代谢,城市人群与环境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同群体对待城市景观的不同认知,环境正义与社会公正之间的逻辑关系。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是城市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必要,而且仍将保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在城市的资本影响力愈行愈远,不仅超越自身的行政边界,甚而跨越国界、洲界的今天,城市人群与自然之间的纽带也越来越复杂。克罗农书中的芝加哥消耗的只是大平原的草原与五大湖的森林,彼时的芝加哥人只是从美国的西部获取食物与能源;而今天,任何一个自然的大都市食用的可能是加利福尼亚的水果、山东寿光的青菜、巴西的黄豆、澳洲的牛肉。支持城市运转的能源可能来自遥远的非洲、动荡的中亚、荒寂的西伯利亚。而城市排泄的垃圾污染着广袤的海疆,各种工业、生活废气则直抵太空。正因为如此,环境史学者需要对克罗农所建立的研究模式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打破城市的边界,并非意味着城市在环境史中的消失,相反,城市依然是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中心;更不意味着城市与乡村以及荒野之间的混同,正如沃斯特所言,差别是存在的,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城市环境史学者需要关注在差别当中存在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建立在时间维度之上;换言之,城市环境史的书写不应当同更为古老而持久的自然史与农、牧历史之间发生硬性的割裂,而应当将城市的发展放入这个地区整体演化的历程当中进行思考。其次,史家可以在空间维度上发现这样的联系,亦即将城市物质环境的演进同其所消耗的遥远而广阔的腹地结合起来,发掘其中的经济与生态互动,进而考察由于这些互动而引发的环境与社会变迁。再次,这样的联系还存在于城市人群的想象层面,也就是说,要将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与想象同野性而自由的景观相结合,这其中包含着消费社会对于自然资源匮缺的忧虑,城市人审美想象的延展,对待生物多样性的解读,以及最终如何在一个日趋城市化的星球上维系生态系统的健康、美丽与永恒的追求。①笔者的箸作The City Natural: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13).即是通过研究19世纪后期出版于纽约与波士顿的环境杂志 《园与森林》及其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扩展城市环境史研究在思想层面的领域。
[1] William Cronon.Nature'sMetropolis:ChicagoandtheGreatWest.New York:W.W.Norton,1991.
[2] Stephan Thernstrom.PovertyandProgress:SocialMobilityinaNineteenthCenturyC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3] Edwin G.Burrows and Mike Wallace.Gotham:ahistoryofNewYorkCityto1898.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4] Clay Mcshane.“The State of the Art in North American Urban History”.JournalofUrbanHistory,2006(32):594-595.
[5] Donald Worster.“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In Donald Worster(ed.).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theEcological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6] 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载 《史学理论研究》,2001 (2)。
[7] Kathleen Brosnan.UnitingMountain& Plain:Cities,Law,andEnvironmentalChangealongtheFront Range.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2002;Andrew Hurley.EnvironmentalInequalities:Class,Race,andIndustrialPollutioninGary,Indiana,1945—198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Martin Melosi.GarbageintheCities,Refuse,Reform,andtheEnvironment,1880—1980.College Station:Taxes A&M University Press,1981;Adam Rome.TheBulldozerintheCountryside:SuburbanSprawlandtheRiseofAmericanEnvironmentali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Tarr.TheSearchfortheUltimateSink:Urban PollutioninHistoricalPerspective.Akron,Ohio: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1996.
[8] Joel Tarr.“Urba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Complementary and Overlapping Fields”.In Christoph Bernhardt(ed.).EnvironmentalProblemsinEuropeanCitiesofthe19thand20thCentury.New York:Waxmann Verlag Gmbh,2001.
[9] 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0] 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载 《世界历史》,2011 (4)。
[11] Donald Worster.DustBowl:TheSouthernPlainsinthe1930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Carolyn Merchant.TheDeathofNature:Women,EcologyandtheScientificRevolution.San Francisco:Harper &Row,1980;Alfred Crosby.EcologicalImperialism:The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900-19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Cronon.ChangesintheLand:Indians,Colonists,andtheEcologyofNew England.New York:Hill and Wang,1983.
[12] Robert Gottlieb.ForcingtheSpring:TheTransformationoftheAmericanEnvironmentalMovement.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1993.
[13] 高国荣:《关注环境与城市的公共史学家——安德鲁·赫尔利教授访谈录》,载《北大史学》,2012 (17)。
[14] Michael Rawson.EdenontheCharles:TheMakingofBost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