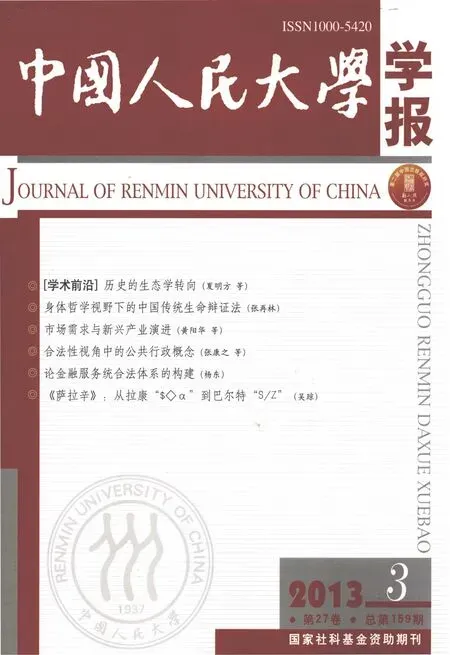变迁世界中的环境史学:进化、环境健康与气候变化*
2013-01-22南茜兰斯顿
南茜·兰斯顿
随着环境史学的日益成熟,其研究视野从美洲荒野史扩展到全球范畴。同时,环境史的文化史转向也标志着在过去的十年中,性别、阶级和种族史学家同样也将很重要的研究视角带入这个领域。然而,坚守环境史研究的核心见解——自然不仅仅是人类历史戏剧上演的舞台——依然非常重要。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在不断的妥协中塑造着彼此的历史。
本文将简要地从三个对未来研究有重要价值的角度对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第一,进化环境史;第二,环境健康与社会的历史;第三,气候变迁及其过往的研究。
一、进化环境史
埃德蒙·罗素 (Edmund Russell)等环境史学家最近号召历史学家们把更多关注投向进化论,因为将历史与生物学两个领域联系在一起,可以使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更为深刻。从全新世开始以来,人类就一直是创造进化的重要力量,因此不考虑人类在自然中扮演的角色就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最近的生态历史。环境史的重要理念的确是“自然不仅仅是人类戏剧上演的舞台”,但是自然也不能完全决定人类的历史。人与自然一直互相妥协,塑造着彼此的历史。①有几篇文章回顾了这些辩论并提出了进化论方法对人类史研究大有裨益的强有力证据,参见Edmund Russell.Evolutionary History:Uniting History and Biology to Under Life on Earth.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Dan Flores.“Earthlings:Evolution and Plac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Donald Worster.“The Living Earth:History,Darwinian Evolution,and the Grasslands”.Both in Douglas Cazaux Sackman(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Hoboken,New Jersey:Wiley-Blackwell,2010.
大部分生态学家认同这个观点,尽管他们可能会在关于人为与非人为活动对抗过程的重要性问题上存在争议。然而,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与进化的影响相比,人类文明更为重要,从而忽视进化论。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因为害怕陷入生物决定论而抵制进化思想。在本文中,我将用自己对有毒化学品史的研究来证明,采纳一些进化论的方法对历史研究是大有裨益的。不少化学工业史学家,研究过在化学制品广泛使用过程中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过去的研究只关注人为因素而忽略了化学品暴露的大背景。还有的历史学家研究合成化学品对环境造成的改变,同样,这种研究固然重要,但也因为受衰败论观点羁绊,认为自然处于被动地位,极度脆弱易受破坏。一种环境进化的视角,能够让我们找到人类与合成化学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去发现我们对身体、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进行简化和控制的尝试总是失败的原因。
不少人文研究者担心,生物进化论学家是那种认为人类只是 “基因”及繁殖策略 “运载工具”的生物决定论者。他们认为,进化论会导致仅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人类历史,轻视文化力量,而人类也将被还原为毫无自身意志的、移动的物质。②理查德·道金斯在 《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人类是自身基因的运载工具的观点。参见Richard Dawkins.The Selfish Ge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1](P4)但这是对进化论的误解。30年前,一些社会生物学家的确试探性地做过一点基因决定论研究,但进化论与基因决定发展与行为的观点毫无关联。③威尔逊的 《社会性:新的综合体》一书的出版激起诸多关于生物决定论和历史进化的讨论。他后来出版的 《人性论》一书,同样颇具争议性。在厄丽卡·司格卓尔的 《真理的捍卫者:从一场为科学而战的社会学辩论谈起》中,对这场论争进行了很好的整理。参见E.O.Wilson.Sociology:The New Synthesi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E.O.Wilson.On Human Na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Ullica Segerstrale.Defenders of the Truth:The Battle for Science in the Sociology Debate and Beyo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与之相比较,进化论更贴近历史,因为它是一门在特殊、偶然背景下方具意义的、关乎变化策略的科学。进化论并没有同化差异,恰恰相反,它让我们懂得:作为历史建构,基因、身体和群落都是由协商塑造而成的。
在这里,我以基因为例加以说明。在现代生物学中,基因可以是除一成不变的确定因素之外的任何东西,它们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现代生物学家将基因形容为源自 “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成长、生活和死亡经历”[2]的 “信号网络中悬浮的介质”。我研究中的一个例子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内分泌扰乱物是合成化学品,它可以干扰荷尔蒙在胚胎形成中的作用,增加不孕、癌症,以及——最具争议性的一点——增加很多物种的双性症几率。当然,双性症是脊椎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动态的多样性表现之一,但是它的出现频率现在可能因为工业废弃物而发生了改变。[3]
畅销书中提到内分泌干扰物总是冠以这样的标题:“自然的雌性化”,而科学论文则会用 “男性危机”,或者 “人类睾丸——面临风险的器官?”这类题目反映出针对性别差异稳定规范的巨大文化焦虑。[4]作为对这些标题的回应,一些文化理论家不再理会人们对内分泌干扰物的忧虑,认为其所反映的不过是一种对本质主义的、生物决定论的性别差异所持的信仰。[5]
但即便在我们需要拷问对男女本质属性做出的假设时——这些假设支撑着对内分泌干扰素的一些解释,我们也同样需要意识到人类与其他动物分享着亲缘关系。性别差异在进化时期是十分不固定,随着微小的环境波动迅速改变,而这种不固定和多样性使性发育模式对合成化学品尤为敏感。[6](P134-151)
畏惧生物决定论不是很多历史学家不理睬进化论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那些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评论家们所表达出的观点:进化论将人类赶下万物之灵的神坛。在 《物种起源》出版150多年后,人类例外论的信仰依然强大。[7]我在 《毒躯》讨论化学史的过程中发现,这种人类例外论主张是化学工业声明中的重要部分,尽管实验室和野生动物实验结果都显示这种物质对其他动物有很大毒性,化学工厂仍声称自己的新产品对人体是安全的。[8](P28-60)
合成化学品踩在 “自然”与 “人文”世界的模糊边界上。它们是工业社会的大量人造产物,而此工业社会则产生于具体的文化背景下,其背后正是不露形迹、悄然发生的更深层次的历史进化。可是,它们却逐渐成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并且由于其化学持久性特点,能够在我们直接接触的自然环境中长久存留。正如唐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所说,没有人是完全孤立的个体。我们都是本我和异我组成的网络,一张由我们的个体特性和DNA 与寄生虫、细菌、病毒的集落交织在一起的,构造了我们身体的网络。我们最深的自我意识反映了我们自身的、文化的和进化的历史,包括数百万年前,在免疫学层面上看来, “异物入侵”人体的病毒,在合并进DNA 后,又反过来调节我们对生存的化学网络的响应。[9](P199-233)[10](P149-181)
进化理论赋予历史学家两点核心理念。第一,它告诉我们非决定性和变化一直是这个仍在形成中的世界的核心特征。我们的知识并非建立在与生俱来的既定事实之上,也没有绝对的道德能把人类放在一个静止世界的中心。第二,我们生存在一个充满了关系,连接和无序纠葛的世界中。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在各个方面都根植于环境。人类历史的出现并不是孤立于其他物种之外,而是存在于至今仍在进行中的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不断妥协中。
二、关于环境健康与社会的历史
许多环境史学家都将他们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源管理冲突上,这种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政治和经济历史。正如理查德·怀特 (Richard White)对铁路的研究显示的那样,在资源开发中,没有东西是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资源是带有偶然性且因时而变的。称一种物质为资源,就把它从自身错综复杂的生态关系中抽离出来,孤立地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中,但这种孤立只是一个假象,我们始终和那些自然要素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即便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11]
当矿藏从地下挖掘出来,树木在森林里被伐倒,当洪水被拦泄,河流被束缚,当动物由伙伴变为家畜,我们就开始了一场微妙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毒化进程。例如,硒——一种完全自然的化学物质——沉睡于地球的沉积层中,直到人类在挖掘其他东西的过程中发现了它,并将其定义为一种资源。随后,由于水流冲刷矿区,硒进入到鱼体,并由之到达人类体内。①更有趣味的讨论,见2012年2月22日《纽约时报》刊载的莱斯利·考夫曼的文章《突变鳟鱼为矿区带来新思考》。美国鱼类与野生生物服务中心对鳟鱼数据的评论见2012年1月发表的 《科技评论:烟谷矿区——硒标准详细报告》。参见Leslie Kaufman.“Mutated Trout Raise New Concerns near Mine Sites”.New York Times,2012-02-22;“Technical Review:Smoky Canyon Mine Site-Specific Selenium Criterion Report”.January 2012,http://www.fws.gov/contaminants/pdf/ReviewSmokyCanyonMineSeleniumReport.pdf。汞、砷、铅、酸排水这些纯粹的自然物质,离开我们的矿区,就摇身一变成为毒素和致命武器,改造了人类的身体,尤其是生殖、孕育、老化和死亡,与此同时,也影响着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
针对资源大举开发的风险监管最终失败,是因为这种监管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风险评估基本原则之上:分离原则。第一,风险评估假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抽离出来,分离于社会关系之外,成为一种资源。第二,风险评估认为身体可以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分离。政治科学家斯蒂文·克劳史密斯 (Steven Kroll-Smith)和 沃 斯· 兰 卡 斯 特(Worth Lancaster)称之为 “启蒙运动激发出的思想,认为身体和环境一直以来就是两个孤立的现实……通过假定身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类别差异,立法机构可以颁发一个 ‘污染排放许可证’,在污染物 ‘未达到足以使环境毒素危害人体健康的门槛限度’的情况下,给予公众弄脏环境的权利”[12]。
其暗含的假设是,人体和环境已经分离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可以污染土壤、水源或者空气,而丝毫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但是环境史的重要见解之一就是,人类身体和人类社会一样,是一个运动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物质和文化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们的身体,这一动物的身体,存在于对我们及我们赖以为生的世界来说十分复杂的生态关系中。
探测合成化学品的新科技和新方法,让我们越来越注意到无处不在且持久不断的内分泌干扰素——那些干扰荷尔蒙作用的合成化学有毒物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身体。身体负荷分析表明我们身体中的化学成分正在发生变化,也反映出我们日常生活环境的改变。有毒化学物质是工业社会的人工产物,而此工业社会则是在高度具体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但是,它们逐渐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作为持久性化学物,大部分能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很长时间,长到我们会忘记它们最初是人造的或者合成的。
三、关于气候变化与历史的研究
当人类迅速改变地球以至于我们共同经历的一些历史正在消失,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再现时,气候变化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环境史的意义①更多关于气候变化与历史的研究,见南茜·兰斯顿的 《空气》一文。马克·凯里也曾发表过大量讨论气候变化与环境史的论述,如他的新书 《在融化冰川的阴影里:气候变化与安第斯社会》。参见Nancy Langston.“Air”.In Douglas Cazaux Sackman(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Hoboken,New Jersey:Wiley-Blackwell,2010;Mark Carey.In the Shadow of Melting Glaciers:Climate Change and Andean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但是直到现在,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对气候变化问题还是不甚关注。早在1915 年,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 (Ellsworth Huntington)就提出,“气候不仅仅对人类历史有重要影响”,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化。他进一步阐释道,气候影响人类的食物、自然资源、寄生虫和疾病、从事的职业、生计及生活习惯。它也是 “导致迁移、种族混合及自然选择的最重要的 (因素)”。对亨廷顿来说,气候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类历史并且决定了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等级。虽然他的结论在当今社会没有获得多少学者的支持,但无疑为气候史研究留下了一份不朽的遗产。不幸的是,这个遗产一直阻碍着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的合作。[13]
亨廷顿的狂热环境决定论、对文明的种族主义分类,以及对气候是历史的 “根本性”因素的过分强调,使得在美国产生出一种旷日持久的反对将气候纳入人类历史研究范畴的研究陋习。作为对环境决定论的反抗,美国学界的思想钟摆摇向另一个极端——某种文化决定论。在其中,人文学者从根本上忽视环境,反之假定只有人类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路径。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界仍然对环境变迁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持明显的怀疑态度。
在欧洲,一种不同的研究传统获得了发展。法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勒华·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研究显示,历史学家可以提供可量化的、严谨的并且足够细致的数据,从而重现一定区域内准确的气候变迁。[14]一代气候史学家们用他的方法探索气候变迁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希望找到气候变迁在影响粮价下跌、饥荒以及经济波动等导致政权更迭的因素时留下的印记。[15]
但是那些寻找气温或降雨量变化关系的尝试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干旱不能预示高死亡率,更不能证明王国将要垮塌。欧洲社会那时产生了一种以粮食的多样化、谷物储藏、贸易扩大以及福利体系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16]这种恢复力意味着社会、政治因素可以使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远远超越了数据分析能够解释的程度。
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全球各地的学者不仅探索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即气候变化是不是经济和人口混乱产生的原因,也开始关注其间接影响。其中最令人着迷的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工作,如安德鲁·达格摩尔 (Andrew Dugmore)、克里斯汀· 凯勒 (Christian Keller)和托马斯·麦克盖文 (Thomas McGovern)考察了气候变化可能对社会网络产生的影响,并反过来作用于社会恢复力。[17]小冰期对格陵兰岛古挪威人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气候与人类社会关系复杂性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90年代,麦克盖文和他的同事阿斯垂德·奥格尔维 (Astrid Ogilvie)讨论过 “气候变化影响、农牧生计基础的失败以及无力适应是导致古挪威人在格陵兰定居走向失败的几个重要原因”[18][19](P127-154)[20](P327-339)[21](P385-393)。麦克盖文的论文因杰拉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而为更多人所知,后者在 《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导致古挪威人缺少应对气候改变恢复力的原因,是“即便当外界条件改变,长久以来的核心价值观丧失作用时,仍然不愿对其重新审视并加以改变。中世纪格陵兰岛上的古挪威人缺乏一种主观意愿: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那群迁移而来的挪威农牧人,鄙视因纽特人为异教猎户,甚至当挪威停止向格陵兰派遣商船,且气候变冷到不能进行农牧活动后依然如故。他们因此最终绝迹,把格陵兰留给了因纽特人”[22]。
近几年来,麦克盖文和他的同事们将之前关于格陵兰岛古挪威人应对气候变化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在2007年一篇重要论文中,考古学家安德鲁·J·达格摩尔、克里斯汀·凯勒 (Christian Keller)和麦克盖文认为,不仅是气候本身,经济与贸易方式的变化也导致了格陵兰岛上的定居者们被边缘化,并因此最终被抛弃。作者考察了可以促生古挪威人对环境变化恢复力的因子后,认为那些使格陵兰岛古挪威人在大多数殖民地可以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也正是导致其在小冰期衰落的原因。古挪威人并不是一群 “墨守成规”的人,他们创造了一套复杂的生存体系,足以应对正常的气候波动。[23]拓展食物资源范围可以为古挪威人解决一般的食物匮乏问题,但是这个系统的运作建立在广泛的家庭合作体制基础上。且这种足以应对小变动的合作体系,在气候变化开始拆散聚居地之间的联系时,就有可能被击垮。
换言之,格陵兰岛的古挪威人很可能不是因为人口规模过大、自然资源有限而崩溃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人口下降过低,拆散了他们赖以维系、以之应对环境波动的社会合作机制。考古学家们并不认为环境变化对古挪威人不重要,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在古挪威人对气候变迁的顺应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在对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性研究中产生了以下一些主题。
其一,各个社会用自己以往的环境经验——他们分享的环境历史——指导未来。环境记忆通过教授人们如何监测土地使用、人口水平,以及经济活动来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在一个地方生存。但是在突然爆发的、不可预知的变动中,共同的环境历史记忆可能会具有欺骗性。历史学家可以检查当人们试图去适应不可预测的变化时,使用和误用的环境历史记录。
其二,经济和政治结构决定一个社会对环境变化的恢复力。例如,建立在多种资源开发基础上的经济体,在环境渐变的过程中可能不会那么脆弱,因为当气候变动的时候人们能够替换资源;但是古挪威人的例子显示,这种经济体在环境突变时可能会更加脆弱。建立在较少种类资源的商业开发基础上的经济体,可以将分散的聚居体整合起来,但是如果一个聚落依赖的远方市场在气候变化中受到影响的话,它的脆弱性也随之提高了。
其三,规模大小确乎重要:一个社会对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因变化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唐纳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认为,很多现代、复杂社会在应对自然变异的过程中,学会通过“用大量人力财力集中克服绝大多数的自然变迁。他们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金钱,补偿地方性损 失,从 而在混乱中创造稳定状态”[24](P68-69)。这种手段可以帮助降低气候小变动时经济的脆弱性,但是却可能增加其在大规模、爆发性的环境变化中的风险。
其四,这些研究表明偶然性是环境史的核心。生物物理学条件,如气候变迁,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决定任何历史事件的唯一因素。人类选择也很更要。一个城市不会仅仅因为气候变动而崩溃。气候改变对不同聚落的影响方式不固定,对同一个聚落中的不同团体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在面对迅速恶化、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及社会转型之际,究竟什么是环境史学家力所能及、而自然科学家与社会史学家力有未逮的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传译工作:对生态学家讲述文化改变,对其他历史学家叙说生态变迁,用一种两个群体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让他们明白各类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不参照那些可能与我们的生态未来不再相似的生态历史,我们又怎能恰当而有责任感地生存呢?
[1] Robert W.Sussman,Audrey R.Chapman(eds.).TheOriginsandNatureofSociality.Hawthorne,NY:Aldine De Gruyter,2004.
[2] Anne Fausto Sterling.“The Bare Bones of Sex:Part 1-Sex and Gender”.Signs,2005,30(2):1491-1528.
[3][6][8] Nancy Langston.ToxicBodies:HormoneDisruptorsandtheLegacyofD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4] Deborah Cadbury.AlteringEden:TheFeminizationofNature.New York:St.Martin's,1999;A.Giwercman,N.E.Skakkebaek.“The Human Testis—An Organ at Risk?”.InternationalJournalofAndrology,1992(15):373-375;and“Masculinity at Risk”.Nature,1995(375):522.
[5] Celia Roberts.“Drowning in a Sea of Estrogens:Sex Hormones,Sexual Reproduction,and Sex”.Sexualities,2003(6):195-213.
[7] W.Ross Blackburn.“Evolution,Human Dignity,and Crafting Public Policy”.CrisisMagazine,2012-05-03,http://www.discovery.org/a/18981(accessed October 12,2012).
[9] Donna Haraway.“The Biopolitics of Postmodern Bodies:Constitutions of Self in Immune System Discourse”.In Linda S.Kauffman(ed.).AmericanFeministThoughtatCentury'sEnd:AReader.Cambridge:Blackwell,1994.
[10] Donna Haraway (ed.).“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In Donna Haraway.Simians,CyborgsandWomen:TheReinventionofNature.New York:Routledge,1991.
[11] Richard White,Railroaded.TheTranscontinentalsandtheMakingofModernAmerica.New York:Norton,2012.
[12] Steve Kroll-Smith,Worth Lancaster.“Bodies,Environments,and a New Style of Reasoning”.Annalsofthe 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2002(584):203-212.
[13] Mark Carey.“Beyond Weather: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History”.Forthcoming in Andrew Isenberg (ed.).OxfordHandbookofEnvironmental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14] Le Roy Ladurie.TimesofFeast,TimesofFamine:AHistoryofClimateSincetheYear1000GardenCity.N.Y.:Doubleday &Company,1971.
[15] Christian Pfister.“The Little Ice Age:Thermal and Wetness Indices for Central Europe”.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ry,1980(10):665-696.
[16] John D.Post.“The Impact of Climate on Political,Social,and Economic Change:A Comment”.Journalof InterdisciplinaryHistory,1980(10):719-723.
[17] [23] Dugmore,Andrew J.,Christian Keller,and Thomas H.McGovern.“Norse Greenland Settlement:Reflections on Climate Change,Trade,and the Contrasting Fates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North Atlantic Islands”.ArcticAnthropology,2007(44):12-36.
[18] Dugmore et.al.“Norse Greenland Settlement:Reflections on Climate Change,Trade,and the Contrasting Fates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North Atlantic Islands”.ArcticAnthropology,2007 (44):12-36;McGovern,Thomas H.et al.“Northern Islands,Human Error,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A View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Change in the Medieval North Atlantic”.HumanEcology,1988(16):225-270.
[19] Thomas H.McGovern. “Management for Extinction in Norse Greenland”.In Carole L.Crumley (ed.).HistoricalEcology:CulturalKnowledgeandChangingLandscapes.Santa Fe,N.M.: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1994.
[20] Thomas H.McGovern.“The Demise of Norse Greenland”.In William W.Fitzhugh and Elizabeth I.Ward(eds.).Vikings:TheNorthAtlanticSaga.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0.
[21] Ogilvie,Astrid E.J.and Thomas H.McGovern.“Sagas and Science:Climate and Human Impacts in the North Atlantic”.In William W.Fitzhugh and Elizabeth I.Ward (eds.).Vikings:TheNorthAtlanticSaga.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0.
[22] Diamond,Jared.“The Ends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Them”.NewYorkTimes,2005-01-01.
[24] Donald Worster.“Climate and History:Lessons from the Great Plains”.In Jill Ker Conway,Kenneth Keniston,and Leo Marx(eds.).Earth,Air,Fire,Water:HumanisticStudiesoftheEnvironment.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