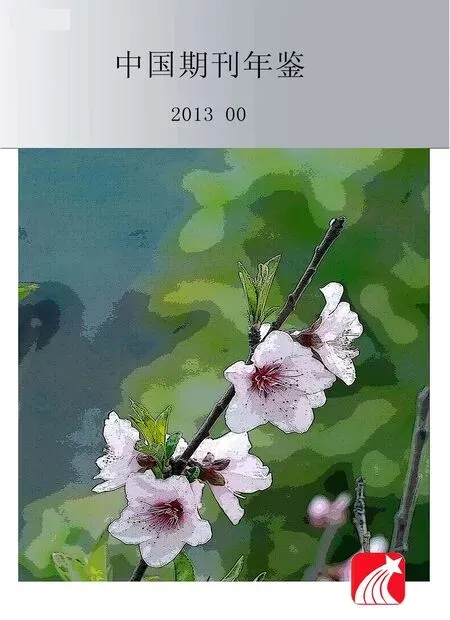历史夹缝中的编辑
——论早期《小说月报》的编辑王蕴章
2013-01-22李直飞
李直飞
历史夹缝中的编辑
——论早期《小说月报》的编辑王蕴章
李直飞
王蕴章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是“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他清末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参与编刊首版《辞源》。曾任《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主编10年。他与恽代英、胡愈之、叶圣陶、沈雁冰、黄宾虹、廖仲恺、叶浅予、胡寄尘、周作人、郑振铎等为伍,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一个时代。
早期《小说月报》带有新旧文学过渡的特点,[1]除了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更重要的是跟杂志的编辑紧密相连,分析早期《小说月报》的这种性质,编辑的影响便至关重要。王蕴章参与了《小说月报》的创刊和改革前《小说月报》的最后几卷的编辑,他的编辑思想直接影响了早期《小说月报》的性质与风格,《小说月报》的过渡性质正是在他的手上形成和完成的。通过对王蕴章前后两次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对杂志的定位、内容的取舍、栏目的设置、封面和插画的编辑等分析,可以看到作为一位在新旧历史夹缝中的编辑,是如何设法平衡新旧矛盾及以求跟上时代步伐所做的艰难努力。王蕴章第一次任《小说月报》的主编是从1910年7月到1911年12月,共编辑杂志19期。
王蕴章在《小说月报》创刊时任主编,对这份杂志是充满着喜悦和幻想的,这从他对《小说月报》的定位可以看出来。创刊的“编辑大意”说:“本馆旧有《绣像小说》之刊,欢迎一时,嗣响遽寂”,“本报以 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为宗旨。”[2]明显地,《小说月报》有着继承《绣像小说》的雄心大志。作为清末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的《绣像小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格调,在读者中口碑甚好。《小说月报》创刊便说明自己和《绣像小说》之间的继承关系,显然编辑是对《小说月报》的未来充满了幻想。《小说月报》借《绣像小说》的辉煌抬高自己,但《小说月报》的期刊定位却没有走《绣像小说》一样的路线。《绣像小说》在其创刊号上刊载《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表明:《绣像小说》的期刊定位是相当明确的,开启民智,力图救国的意图十分明显。而在《小说月报》的“编辑大意”上却是“ 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为宗旨”,两相比较,《小说月报》的定位也强调教化功能,却平缓了许多,并且突出了“材料丰富,趣味 深”,杂志的“趣味性”倾向加浓。
在之后的“征文通告”里,说“现——身,说——法,幻云烟于笔端,涌华严于弹指,小说之功伟矣”[3]。这里突出了小说的现身说法,有将小说视为“游戏“的味道。而另外一则广告:惟一无二之消夏品,夏日如年,闲无事求,所以愉悦性情,增长闻见,莫如小说。[4]在这里小说成为了驱遣睡魔的消夏品,与中国传统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观点相差无几,小说的教化功能淡去,娱乐功能,趣味性在增强。这显示了编辑王蕴章文学观念的传统保守的一面,旧的文学观念占着上风,将期刊的作用定位为娱乐中教化民众。在“编辑大意”里有:“本报卷首插图数页,选择綦严,不尚俗艳。专取名人书画,以及风景古迹足以唤起特别之观念者。”这里突出了卷首插图栏,是别有新意的。当时的期刊喜欢以美人图为卷首图,而《小说月报》卷首插图以花鸟风景为主,追求中国古代文人淡雅空灵的雅趣。这表明了王蕴章编辑《小说月报》一开始坚守雅的一面,但同时,从《小说月报》前两卷的实际插图中,我们又看到王蕴章在当时市场风气影响下俗的一面。在王蕴章编辑的前两卷《小说月报》中,也采用了妓女的照片做插图。如二卷三期的“北京名妓谢卿卿、李银兰小影”,二卷四期图画中的“北京名坛扑朔迷离图”等。
从王蕴章对《小说月报》封面和插图的设计,我们不难看出,王蕴章在编辑《小说月报》时,基本的倾向是介于雅俗之间,在追求雅的情趣时,不时又流露出民初文人常见的俗化倾向的编辑风格。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王蕴章在第一次编辑《小说月报》时,视杂志的作用为在娱乐中教化民众,将杂志定位于雅俗共赏之间,但是,王蕴章又绝非顽固不化的守旧分子。这从王蕴章的栏目调配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将这时期《小说月报》的栏目设置与晚清的小说杂志的栏目设置做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王蕴章在这方面的进步。
除了在小说栏目的编排上形式越来越显得有条理,不再将“短篇小说”与“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并列在一起,显示了编辑对小说文体特征的清晰认识,分类方法更为科学合理之外,王蕴章在《小说月报》上新设的“改良新剧”一栏意义重大。正是这个栏目为中国现代话剧剧本的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小说月报》刊登白话体的类似于现代话剧剧本的改良新剧时,中国的话剧刚刚起步,还没有成熟意义上的话剧剧本。这是《小说月报》中惟一一个从一开始就充满新文学意味的栏目。而这两个栏目也使这份杂志与同时期别的杂志相比,一开始就有一种趋新的态势。从“改良新剧”栏目所刊载的剧本中,可以明显看到戏剧的变革:白话的语言,对话的表现形式,新式标点的采用等。这些都是我国现代话剧诞生前很了不起的实验与准备,显示了王蕴章进步的一面。
王蕴章第一次编辑《小说月报》的这种守旧的文学观念带来的雅俗共赏的期刊定位、旧中有新的编辑方针,很好地契合了当时一般读者的心理,从《小说月报》最初的销售量不断上升就可以看出来。《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三号有一则广告说,《小说月报》第一年和第二年售得连报社都没有了希望从读者手中回购,可见其销售势头不错,也可见王蕴章的编辑方略是适合当时的文学市场的。
这种状况到王蕴章1918年第二次编辑《小说月报》时就发生了逆转,如果说王蕴章第一次编辑《小说月报》时是带有着喜悦的幻想的,到他再次主编《小说月报》时则承受着艰难与失望。《小说月报》的销量在1918年开始下滑,显现出败象出来,到1920年“销数步步下降,到第十号时,只印二千册”[5]。
《小说月报》的销量下降,时人总结说:“其原因由于主编者不能随时代而变其取舍之目标;发行者不能就社会群众之心理以使其方术。”[6]这里明显指出当时小说杂志纷纷停刊的原因是不能跟随时代变化、不能顺从社会群众的心理,也就是《小说月报》的期刊定位与受众之间的心理出现落差。而这里所说的时代与社会群众的心理出现了变化,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就是新文学的出现与崛起。《小说月报》销量下滑的时候,正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渐入高潮的时候。《新青年》1915年创刊的时候只印了一千册,可到了1917年前后,它的发行量激增到了一万五千册,多出来的数量,自然要夺去不少像《小说月报》这样的读者,这只是《新青年》的数量,还有其他如《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相加起来,再加上《申报》等报纸发行量的快速提升,[7]自然对《小说月报》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小说月报》的销量下降,说明《小说月报》此时的期刊定位与编辑方针跟读者市场不再合拍。在王蕴章第二次编辑《小说月报》的时候,他的雅俗共赏的期刊定位很明显向俗的方面倾斜。尽管不能说此时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但这时期《小说月报》刊载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偏多却也是事实。鸳鸯蝴蝶派就是商业与文学的结合,主张文学游戏人生,娱乐身心,王蕴章与鸳鸯蝴蝶派有着紧密联系,自然与这种文学观有相通之处。对比一下当时《新青年》的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差距。《新青年》2卷5号刊登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紧接着刊出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周作人鲜明地提出了“人的文学”。在新文学的倡导者这里,文学不再是作为“游戏人生”的工具,而是作为“人的文学”,作为一种改变国家社会的力量提出来的。当时的作家也认识到,现代报刊具有传播知识、控制社会、引导阅读、重造文学、舆论监督等功能。[8]这些都跟王蕴章越来越保守的还视文学为“小道”,提倡文学“趣味性”的观点无疑是有着相当的差距的。同时,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1号完全改用白话,1920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至此,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而在王蕴章后期编辑《小说月报》的时候,所用语言依然还是文言文,至1921年革新之后,《小说月报》才全部将文言文改成白话文。在语言改革上,《小说月报》也慢了新文学半拍。实际上,作为编辑的王蕴章也为了跟上时代潮流在做着努力。《小说月报》从第十一卷开始“改良体例”,添设“小说新潮”一栏“以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将“小说新潮”栏目交给新文学作家茅盾去编辑,又在《小说月报》上设置了“文学新潮”“编辑余谈”等带有新文学倾向的栏目,前者以刊载新体白话诗为主,后者以刊登新文学理论批评为主;同时在编辑中,王蕴章还注意与读者沟通,九卷四号设了“小说俱乐部”,推出续写小说等形式;九卷十一号创办了“寒山社诗钟”,以此将作者、读者联系起来。但是,他的这些改良都没能挽救《小说月报》的销量下降。从他的实际编辑活动来看,文学观念守旧让他希图在新旧文学之间寻求平衡,这时期的《小说月报》既刊登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和林纾的译作,也刊登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他希图文白并举,而社会的风气也已经不容他这样做了。当时,鸳鸯蝴蝶派和林纾正作为新文学的靶子遭到严厉批判,新文学正在迫使鸳鸯蝴蝶派和林纾向“俗”和“旧”定位,让他们在读者眼中声名狼狈,这对《小说月报》的销量构成消极影响。就在这场旧文学与新文学的较量中,王蕴章作为编辑显示出了他的两难境地:“他对新旧文学并无成见,他觉得应该顺应潮流;他又自辩,他不是‘礼拜六派’,但因《小说月报》一向是‘礼拜六派’的地盘,他亦只好用他们的稿子;他现在这样改革,会惹恼‘礼拜六派’,所以他是冒了风险的。”“冶新旧于一炉,势必两面不讨好。当时新旧思想斗争之剧烈,不容许有两面派。果然像王莼农自己所说,他得罪了‘礼拜六派’,然而亦未能取悦思想觉悟的青年。”[9]处于新旧文学的历史夹缝中,作为带有很深旧派色彩的编辑王蕴章,向新文学的方向变革自然有着巨大的艰难性和漫长性,他的每一次努力,都见证了这种步履维艰,而时代的潮流不允许他这种小步的改变,不久后,茅盾就将他的主编地位取代了,开始了《小说月报》新的序幕。
王蕴章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之后,就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闲时栽花养草,过起了他这一类过渡性知识分子在新文学兴起之后最普遍也最适意的生活。也许,作为处在历史夹缝中的编辑,这是他最好的选择了。
[1]谢晓霞.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J].宁夏大学学报,2002(4).
[2][3]小说月报(第一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宣统二年七月出版.
[4]小说月报(第二年闰月增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宣统三年出版.
[5]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M].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79.
[6]范烟桥.中国小说史[M].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3:238.
[7]都海虹,赵媛.邵飘萍“北京特别通信”特点浅析[J].新闻界,2011(2):159-160.
[8]李天福.沈从文的报刊编辑理念及当代价值[J].新闻界,2011(3):158-160.
[9]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M].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189.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