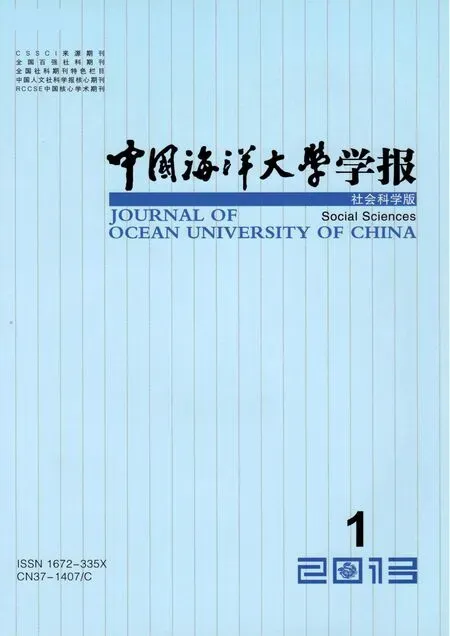海洋公共管理学:缘起及其框架体系设想*
2013-01-21孙立坤
王 琪 孙立坤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海洋公共管理学:缘起及其框架体系设想*
王 琪 孙立坤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以公共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变化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自身的构建面临着深化和发展的问题。在海洋管理的过程中,传统的海洋行政管理形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面临着公共性和工艺性严重不足的困境。将公共管理的相关理论成果应用到“海洋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去建构起一门“海洋公共管理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且海洋管理理论在自身的演变和传承过程中已经证明“公共性”的成长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与公共管理学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呼应性。作为公共管理学一脉新的分支学科,海洋公共管理学框架体系的建构及其丰富化尚需要学界共同的努力予以完成。
海洋公共管理学;缘起;框架体系
公共管理学(Science Of Public Management)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作为旨在研究“公共管理”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的一个研究领域,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欧文.E.休斯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典范,因为两者在理论基础、价值追求、策略安排、公共服务主体、组织形态等方面的认识和主张上都有较大的不同。整体而言,相较于公共行政重过程与程序,奉行“管理主义”的公共管理更重结果。[1](P8)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是在解决和回应不断出现的公共事务治理问题中进行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实践性。从公共事务治理的角度,“海洋管理”是人类一项涉及到海洋的“集体行动”的实践活动。从历时态的维度看,我国海洋管理先后经历了“行业管理”、“综合管理”等管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海洋管理的“公共性”在不断成长与发展,但上述管理形态更多地从属于“海洋行政管理”的范畴。进入后工业社会,这种管理形态下大量的治理问题也随之产生,譬如海洋综合管理中公众参与的碎片化、涉海管理公权力部门间因权责不明和权力分散导致的“九龙闹海”乱象、海洋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的匮乏等。这就需要我们借鉴公共管理学的一般基础理论并同海洋管理实践的特殊性相结合予以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公共管理学亦需要在相对具体的公共管理领域和实践中应用和检验自身理论的正当性和准确性,重视特定重要领域公共问题的研究和治理,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一、海洋公共管理学的缘起
“海洋公共管理学”概念的提出和缘起既是基于对既有各种海洋管理理论形态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海洋管理实践认识的深化,并在吸收公共管理学一般理论基础上而形成的。
(一)传统海洋管理形态的公共性:偏狭及其超越
海洋管理理论有一个流变的过程,而学界对“海洋管理”的概念界定缺乏严格的共识,但一般都认为海洋管理指向的是特定主体对各类海洋实践活动的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本文论题设定将“海洋管理”置于“公共管理”的范畴中,因而剔除了海洋实践中诸如企业的逐利经营等的工商管理、企业管理因素,重点探讨围绕着公共目标(如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权益维护等),公共部门采用特定的手段和机制进行的海洋管理实践活动。就海洋管理中的公共性而言,学者们的研究思路、研究进程和关注点经历了一个从偏狭到广阔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上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分析:
1、海洋行政管理形态
整体而言,海洋行政管理这种管理形态倾向于从狭义上去认识和界定海洋管理,即将海洋管理作为一种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行政管理实践活动。例如郑敬高等编著的《海洋行政管理》便是采取这一研究视角,“所谓海洋行政管理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一个方面,是政府对人的各种海洋实践活动主体的管理”,“是国家海洋行政机关及其授权的职能部门依据法律行使国家权力,对各种海洋实践活动和国家海洋事业实施管理”。[2](P25,P123)这本著作同时对海洋行政管理的特征、目标、任务、行业化及区域化管理、实现手段、原则、实施对象等进行了探讨,但均围绕传统公共行政的范式进行。
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专题研究》一书将海洋管理内嵌于“行政管理”的框架中,认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边界指国务院(国家海洋局)与企业法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并认为“国家与国务院间(此处国务院指政府,笔者注)的管理,企业法人内部组织和自然人的管理以及自然人或组织对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的管理”不能称其为“海洋行政管理”。[3](P20)
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的《美国海洋管理》将海洋管理解释为“政府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干预行动”,并结合美国的政治生态确定了海洋管理中政府的十项职能,包括海洋研究、资源收集、财政赞助等。[4](P2-3)
上述学者在研究海洋管理理论的过程中将海洋管理定位于“海洋行政管理”,其共同的一个特征是内在地把政府列为海洋实践中垄断一切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这更多地具有“形式公共性”的特征,与工业化时代的“管制行政”模式相适应。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中两种重要的管理形态是“行业部门管理”和“综合管理”。
“行业部门管理”主要指的是专业性的海洋行政管理机构对海洋公共事务进行的归口管理,比如海洋渔业、海上交通、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均属于行业部门管理的范畴;而“海洋综合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政府对海洋的宏观管理和克服行业管理导致的行业间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海洋管理中的矛盾,它指的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的、影响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5](P90)海洋综合管理的主体仅限于综合协调性的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因而具有较强的传统公共行政色彩,作为这种治理模式下的“民主”实现形式是“民主参与”而非合作治理。综合来讲,尽管行业管理和综合管理均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但是正如《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中指出的:“综合管理与行业管理有相辅相成的作用,都是海洋管理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不能互相代替。”在特定的涉海公共事务范围内、特定的发展时期两者均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能简单地对两者予以否定。
2、海洋区域管理理论
海洋区域管理*笔者注: 学界很多学者也将“海洋区域管理”称为“区域海洋管理”。理论是超越传统海洋行政管理中的海洋综合管理形态的一种理论形态。传统海洋综合管理的主体单一、严格依据既有行政区划进行涉海公共事务管理,尽管可以发挥其超越行业部门管理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克服海洋管理纵横交错、条块分割的弊端,但是鉴于海洋的流动性、生态性、关联性、系统性以及与行政区划无关联等,海洋事务很难被严格框定在特定某一行政区域内,在这样的状态下,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理论(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EBM)兴起,而海洋区域管理便是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而提出的。
王刚、王琪《海洋区域管理的内涵界定及其构建》一文认为海洋区域管理的内涵囊括了以下四点:海洋区域管理是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是基于生态的管理但不是唯一的;海洋区域管理是公共管理;海洋管理是多种手段结合的管理。之后该文进一步论述指出海洋区域管理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并不是所有海域都适用于海洋区域管理。在应用海洋区域管理的时候需要设计其适用原则、考察目标海域特性、划定海域范围等。[6]
周鲁闽将海洋区域管理的概念界定为“以特定生态系统区域为地理单元,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计划和传统文化等手段,统筹协调解决区域内主要海洋问题的过程和机制”。[7](P21)从这里可以看出,海洋区域管理与海洋综合管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两者均涉及多区域、多部门、多行业、多学科的协调与整合,具有整体性治理的色彩。但是海洋区域管理的主体更加多元和广泛,包括政府、涉海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科研机构等,至少从这一方面来看,海洋区域管理的公共性的外延远大于海洋综合管理。
在研究海洋区域管理的过程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研究协调各个治理主体(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综合管理部门与行业管理部门、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公众、政府与企业等)间、涉海行业间、人类社会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等。在这里,相较于海洋行政管理范式(政府垄断一切涉海公共事务),海洋区域管理理论无论是从治理主体、治理价值取向、治理结构、治理手段等角度来看都超越了既有的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而具有了“实质公共性”和合作治理的韵味。从学理基础来看,海洋区域管理的核心理念和策略安排均属于公共管理学的范畴,比如其综合协调机制与公共管理学的整体性治理思潮在思维和机制上高度一致;又如海洋区域管理所主张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理念也来自于公共管理学的“治理理论”;海洋区域管理的很多技术机制如绩效评估、电子政府等也必须参考公共管理学的既有研究成果,因而尝试着将海洋管理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范畴中是必要且必须的。
从涉海公共事物治理的角度,将海洋管理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视角中去研究具有一定可行性,并且这在学界已有较多但同时又不成体系的探讨。笔者认为,“海洋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至少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建立依据:
其一是“海洋”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海洋无论是从其经济价值如交通价值、资源价值,还是从政治价值如空间价值、军事价值,以及科学文化价值如科研等角度还是从生态环境、国土等价值角度,都由于其产权的模糊性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再加上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使得其负外部性极易被放大,因而对涉海事务的治理以及涉海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多元公部门主体来加以实现。
其二是“海洋”的独特重要性。在21世纪,海洋被视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21世纪也被称为是“海洋世纪”。目前全球一半人口居住在海岸线以内60km处,而且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4。所有这些的根本原因在于继陆地之后海洋逐渐成为人类能量、空间、资源等需求的新来源,人类对海洋的依赖程度正空前地稳步增大。人类已经认识到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从我国涉海国际事务来看,我国在黄海、东海、南海均面临着与相关当事国严峻的海洋权益维护问题,在这些过程中,我国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痼疾就是公共性治理的不足,例如民间组织力量的薄弱等。因此针对海洋进行专门的公共管理学的探讨和建构,有助于摆脱涉海的诸如“公地悲剧”、“囚徒困境”等公共事务治理的顽症,同时亦有助于丰富海洋管理理论体系和公共管理理论体系。除了海洋管理具有浓厚的“公共管理”色彩这一向度之外,尽管在诸如湖泊、草原、湿地等领域也存在着“公共管理”的因素,比如我国太湖治理中就涉及到产业、环境、水利等纵向管理部门和两省一市,需要从公共性出发进行整体性治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湖泊治理、草原治理、湿地治理等领域均要同等地建立起“湖泊公共管理学”、“草原公共管理学”、“湿地公共管理学”等概念和理论体系。很显然,建立海洋公共管理学是由海洋在21世纪的独特重要地位而决定的——海洋承载了21世纪我国在能量、空间、资源、地缘政治、国际秩序等多重维度的重要价值。
其三是海洋公共管理学者社群、学者社区的广泛存在。“工业社会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家庭日常生活的领域分化,而走向后工业社会诸领域的融合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因此在社会治理中也出现了合作治理的要求”。[8](P138)从我国的国情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甚至有些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中,公私合作治理、跨部门合作、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网络治理、整体性治理等理论流派都体现着公共管理生活中“实质民主”的色彩。在这样的语境中,显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在海洋管理中,需要用“公共管理”这种新的治理范式去解释、解决、回应海洋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在这方面,很多学者的专著和论文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比如以鹿守本的《海洋管理通论》(1998)、管华诗和王曙光的《海洋管理概论》(2002)、郑敬高的《海洋行政管理》(2003)、王琪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2007)、俞树彪的《海洋公共伦理研究》(2009)、崔旺来的《海洋管理的公共性研究》(2008)、吕建华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一种公共管理视角的定位及构建》(2007)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研究成果奠定了“海洋公共管理”的基础。另外,我国涉海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及其相关学科下存在着一大批研究海洋公共事务治理的学者;近些年我国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也存在着一些研究海洋公共管理具体重大问题的项目;我国海峡两岸海洋海事大学“蓝色策略校长论坛”也已连续举办了三届等,这些学者社区、社群的学术活动由于学科领域的广泛性和相对分散性,尽管没有明确围绕“海洋公共管理”这一主题进行系统研究和探讨,但对于“海洋公共管理”的一些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启蒙研究。
其四是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的转变。尽管关于公共管理学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存在争议,比如其研究边界不明确、不存在统一的理论基础等,但是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下的“管制行政”,作为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新模式,它在价值追求、治理主体、治理流程、治理手段、治理工具、治理效果等方面追求的是“服务行政”,更具有实质的合理性和公共性。用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的话来说便是传统的“环式民主”行政方式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我们需要在“公共能量场”中构建起正当性的“话语”,改变公共政策制定领域政府的“独白”局面,走向政策“对话”。[9]种种因素已经表明,公共管理学科和理论体系的繁荣与发展为我们构建海洋公共管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技术可能性。伴随着公共管理范式和学科的确立与发展,“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应当密切结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解决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实际研究中应当更多地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并坚持客观性和中立性,力争超越简单的观察评述,揭示问题的本质,从而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10]这意味着在一些重大的领域公共管理学需要建立相应的子学科或者称之为“领域学科”去回应和解决那些重大的公共管理问题。海洋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一个新生的重要场域,在理论上面临着自身构建不足、指导实践不足等问题,客观上迫切需要构建成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
(二)作为“公共管理实践”的海洋管理:碎片化及其整合
实际上,在传统的海洋管理中已经存在着很多“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实践。譬如我国成立于1996年的民间保钓组织“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联合全球华人保钓组织保护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成立于2007年6月1日的民间公益性海洋保护组织“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将“推广海洋保护理念、提升公众海洋意识和普及海洋科学与保护知识”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成立几年来在社会上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又如2008年夏季奥运会期间为了保正青岛奥帆赛的顺利举行,整治附近海域的大规模浒苔,青岛市政府动员了大量的市民来配合清理潮间带和附近海岸上的浒苔,将公民参与作为既有海洋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辅助支撑。再比如2011年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后,包括“自然之友”、“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在内的诸多环保NGO就曾联名向中海油和康菲公司提起公益诉讼,显示了尚处在公民社会启蒙阶段的中国涉海事务NGO的力量。
在治理工具的向度上,作为公共管理的海洋管理有着积极的同时又不成体系的实践。例如在海洋环境的治理中,海洋排污权交易、海洋生态税等市场机制措施已经在很多国家包括我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又如在海洋公共事务治理中,民营化等一些治理理念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也得到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实践:近年来,舟山市政府为加强对数量众多的无人海岛的开发,广泛采用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项目融资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要义在于为了发展本地公共事业,像开发无人海岛,建设灯塔等涉海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对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提供一种特许权协议作为项目融资的基础,由私营企业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安排融资,承担风险、开发建设项目并在有限的时间内经营项目获取商业利润,经营期结束后,依据既有的协议将该项目转让给相应的政府机构。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及民营化的内涵来看,诸如此类的公私合作治理涉海公共事务的实践,无论是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政府决策、政府权力还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来看都具有更多的“公共性”,作为公共管理实践的海洋管理符合大的趋势所向。同时应该看到,诸如涉海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治理工具如志愿服务、凭单、补助等以及更多融资机制如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模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等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相关的适用性问题。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我国海洋管理中存在着一定的“公共管理”色彩的实践,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因为它为我国海洋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正如《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所指出的:“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证海洋的可持续利用,单靠政府职能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这既是对我国海洋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公共管理实践的一个肯定,同时也是对未来海洋公共管理实践的一个战略规划。但是同时应该指出,无论是在公共性还是在工艺性上,这些海洋公共管理实践还是低层次的、碎片化的、不成体系的。公共管理的一个前提假设在于权力、资源、信息在社会的适度分散可以提高整个社会治理公共事务的效率。从我国海洋管理的“公共管理”视角来看,尽管已经存在一些积极的公共管理实践,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实践存在着“碎片化”的倾向,表现在:①公民参与缺乏流程化的机制,在实践中更多地是处于非正规化的、临时的参与,公民参与的形式或者说途径是单一的,与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治理”相去甚远;②海洋公共事务治理中的NGO发育及其作用路径不够健全,既有的涉海NGO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以及参与方式、资源汲取能力、自我生存能力、业务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③海洋公共事务治理中多个治理的主体缺乏协调、整合、信任机制,多个涉海主体之间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缺乏一种实质有效的机制整合成一股正向的力量去治理海洋公共事务。同时,海洋公共事务治理的工具、手段和方法论也是相对单调。这就需要在理论层次上创新研究海洋公共管理的相关基础理论问题和热点、关键问题,因此构建起一个“海洋公共管理学”理论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应有之举。
二、海洋公共管理学的框架及其构想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倾向于“颠覆”和“打破”存在于学科和次级学科之间的各种界限,创造出一种综合多种学科和多重维度的视角,以形成一种“有机的社会理论”。[11](P179-180)海洋公共管理学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方面需要研究和借鉴公共管理一般的理论,另一方面需要研究海洋公共事务管理的特殊性。
(一)海洋公共管理学构建的原则
笔者认为,在构建海洋公共管理学的过程中应该把握住如下几个原则:
其一,注重海洋公共管理理论的系统性。“海洋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一脉分支学科,在基本的理论预设、价值追求、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应该与公共管理学保持一致,从而在学科耦合上保持连贯性和传承性。这既是丰富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需要,也是丰富海洋公共管理理论自身的需要。另外,海洋公共管理学科的构建还应该重点关注公共管理学科最前沿的一些理论热点问题,例如新公共管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公共管理哲学等,在关注基础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前沿问题,从而把握住公共管理大的趋势,防止海洋公共管理理论的滞后性。
其二,把握海洋公共管理的生态性。海洋公共管理学一方面应该将“海洋公共管理”与一般的公共管理学不同的地方及其特殊性作为一项重点研究。海洋自身无论是从其资源价值、交通价值、空间价值、国土价值等来看均出自于一个流动的、不稳定的、模糊边界的生态体系,单纯依靠某些特定行业、特定职能部门、特定执法力量、特定公共治理主体及手段,在传统行政区域内无法管理好海洋这个生态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生态系统的区域海洋管理”的概念才被学界日益重视。另一方面,把握海洋公共管理学的生态性还应该立足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进行建构。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体制、市场发育程度、公民社会发育程度、政府能力和职能、行政管理体制等因素与西方大相径庭,因此需要立足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客观生态环境,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衔接起来,探索符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发展特色的“海洋公共管理学”。
其三,突出海洋公共管理的应用性。海洋公共管理从学科定位上讲属于公共管理学的子学科,是公共管理学在具体公共领域中的分支学科,相较于母学科它具有更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以解决具体的海洋公共事务为研究旨归,因而应该注重研究我国海洋管理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例如海洋强国战略、海洋公共外交等。正如陈振明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必须更加积极地回应对改革开放的实践需求,增强其实践性和应用性,促进知识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使公共管理学成为一门能够解决现实公共问题,促进公共治理的学科”[12]如果海洋公共管理学不能对海洋领域公共事务的治理做出建设性的贡献、不能对海洋公共管理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那么它作为一门公共管理学的子学科和研究领域,就会丧失指导实践的能力。
(二)关于海洋公共管理学框架的设想
如上所述,海洋公共管理学的框架建构应该兼顾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和海洋公共事务治理两个要素,但更多的应该探索“海洋公共事务治理”的特性。笔者认为,所谓海洋公共管理指的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公共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海洋公共管理学框架体系应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海洋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础既应该囊括公共管理一般理论如治理理论、系统整合理论、权变管理理论也应该囊括海洋科学中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诸如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其二,海洋公共管理的主体及其整合。在这里主要涉及海洋公共管理中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在海洋公共事务治理中各自的职能、作用范围、作用路径、运行机制等的明晰化和整合。
其三,海洋公共管理的客体。准确界定海洋公共管理的客体即海洋公共事务的范围是构建海洋公共管理学十分关键的问题。本文倾向于将海洋公共事务界定为包括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海洋权益维护等在内的所有非企业营利事务的总和。其中,海岛管理作为海洋公共管理的特殊范畴之一,需要学界去关注和研究,综合利用政府、社会组织的力量去管理好公共事务意义上的海岛。
其四,海洋公共管理的职能管理体系。包括了海洋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危机管理、财务预算管理、信息资源管理、战略管理、海洋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海洋公共管理中的法治、海洋公共政策体系等,这些内容基本上包含了公共管理学下“服务行政”所要求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
其五,海洋公共管理哲学和伦理。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公共管理哲学和伦理是一个在学界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例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已经连续召开了七届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学界各类核心期刊上都有关于行政哲学和行政伦理学的专版。“行政伦理研究是出于矫正公共行政学形式化、效率导向、控制导向等片面性的需要而提出的。由于人类正处于一个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行政伦理学也契合了20世纪后期以来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13](P24)从本质上讲,无论是海洋公共管理哲学还是海洋公共管理伦理都是研究海洋公共管理价值的,旨在向海洋公共管理实践提供科学的、规范化的、合乎逻辑和大趋势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宏观价值导向。
三、结语
20世纪后半期以来,整个社会科学处于一个大变革、大分化、大整合的时期,学科与学科的综合与交叉成为一大特点,也因此产生了一些新兴的学科,公共管理学本身的产生就是这一趋势的结果。用公共管理的道理和思维去研究海洋管理中的事情具有时代所赋予的合理性。既有的“海洋公共管理”在理论层次上面临着对实践指导不足、体系不完整等问题,在实践过程中尽管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都还是不足的、碎片化的,无法支撑起21世纪我国海洋管理实践的需要。我国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转变需要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去治理海洋公共事务,更需要学界共同努力、高度重视,构建起一个系统的“海洋公共管理学”并就重大的海洋管理问题提出针对性的策略。
[1] (澳)欧文 E.休斯.张成福等译.公共管理导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郑敬高等.海洋行政管理[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
[3] 滕祖文. 海洋行政管理专题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3.
[4] J.M.阿姆斯特朗,P.C.赖纳.美国海洋管理[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5] 王琪.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
[6] 王刚、王琪.海洋区域管理的内涵界定及其构建[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8,(11):43.
[7] 周鲁闽.区域海洋管理模式框架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8] 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 (美)福克斯,(美)米勒,楚艳红等译.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0] 薛澜、彭宗超、张强.公共管理与中国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瞻[J].管理世界,2002.(2):53.
[11] 魏文斌.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2] 陈振明、李德国.走向规范化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J].东南学术, 2009.(2):99.
[13] 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MarinePublicAdministration:OriginandConceptionofItsFrameworkSystem
Wang Qi, Sun Liku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Marine Public Administration, which takes the laws of pubic management and public affairs as its study object, is a new emerging discipline and faces problems of further constructing. In the process of marine management, the traditional marine administration lacks publicity and technology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t is dispensable and practical to apply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to marine public affairs and then construct a discipline Marin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ddition, the history of marine management has proved that publicity grows with an inexorable trend, which shows a consistency and compatibility with Marin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subdisciplin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s construction and enrichment need joint efforts by academic circles.
marine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igin; framework system
D63-3
A
1672-335X(2013)01-0009-06
责任编辑:鞠德峰
2012-10-2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平崛起视阈下的中国海洋软实力研究”(11BZZ063)、国家海洋局咨询中心项目“中国海洋管理哲学研究——海洋公共管理研究专题”的阶段成果
王琪(1964- ),女,山东高密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海洋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