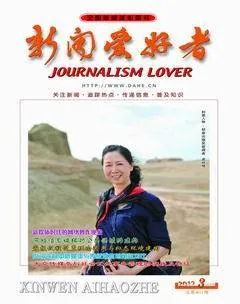《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叙事艺术
2012-12-29马春花戚晓波
新闻爱好者 2012年5期
【摘要】本文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福尔摩斯探案集》这部风靡全球的侦探小说集进行整体的分析,从叙事模式、时间、情境等方面力图发现这部作品中鲜为人知的叙述奥秘,并希望丰富叙事学在侦探小说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叙事;叙事艺术;《福尔摩斯探案集》
作为“侦探迷”,笔者对一个个睿智机敏的神探十分钦佩。但在众多的侦探中,福尔摩斯的名字无疑是最响亮的,有人甚至认为他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让小说中的人物“复活”,这得益于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但更多的应该归功于作者在小说中展现的特殊的叙事手法。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学的一些理论,对这部作品从叙事模式、时间、情境等方面做全面细致的分析,以丰富对该小说甚至类似侦探小说的研究。
“双层结构”的叙事模式
说到叙事模式,不难看出在《福尔摩斯探案集》[1]中,有一种大致的程序:案件的当事人在生活中发现难事或遇到麻烦,有些甚至会危及生命,于是找到福尔摩斯寻求帮助,最后,经过福尔摩斯的调查和分析,看似神秘的真相得以揭示,案件得到解决。在此,该侦探故事没有遵循一般小说的线性结构模式,为了引起读者兴趣和设置侦破难题的需要,案发的情景本该是整个故事发展逐渐产生的一个片断,但被叙事者提到了小说的起始处。由此发展,读者便一直处于侦探小说的“双层结构”中,叙事的主要线索是福尔摩斯解决案件的过程,但这种“侦破故事”的魅力在于如何侦探到破案的关键线索,以及如何将侦探到的信息碎片不断收集梳理,将其还原成“犯罪故事”[2]。读者表面上看到的是“侦探故事”,而实际上真正牵动人心,力图挖掘的是“犯罪故事”。在探案过程中,正是叙事中对信息的藏(罪犯)与露(侦探),来强化小说的叙述张力,非常有效地达到操纵读者和控制读者的欣赏心理和情感需求的目的,让他们时刻试图追逐着探案者的脚步,力求在追求真相方面保持同步,直到案件最后侦破。
匹配节奏的叙事时间
作为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叙事非常关注时间,这是由侦探小说的特点所决定的:时间有时甚至意味着与罪犯较量的成败。任何小说都包括事件自然发生的故事时间以及这些故事在叙事文本中真正呈现出来的叙事时间。《福尔摩斯探案集》对叙事时间十分讲究,调配好叙事时距和频率,弹出了文章适当的节奏。
就时序而言,在宏观结构方面,《福尔摩斯探案集》采用顺叙、倒叙与插叙结合的手法。所有故事的开端都是“罪犯故事”的一个片断,逐渐向案件真相揭示的结尾迈进,这无疑是顺叙的手法。但更重要的,正是对案发之前线索的整合,包括对犯罪动机、背景等这些先于案发就已经存在的信息的挖掘,通过倒叙与插叙的手法,让读者能了解案件的侦破进展,但是,当读者从此类叙述中收集的信息不足以揭示真相时,福尔摩斯顺势登场,揭开谜底,让读者的情感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例如,在《血字的研究》故事中,第一部分运用顺叙的手法,向我们展开了从案发到侦破的部分,抓住了凶手,在一定程度上让读者的感情得以宣泄,充满了对正义得以伸张的满足。第二部分,作者花了极长的篇幅,介绍了这起连环谋杀案的起因,运用倒叙的手法让读者了解了此案的复杂性,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激起了对杀人者的同情和被杀者的愤慨,彰显了文本的张力,更激发了读者对福尔摩斯的钦佩。最后,从凶手的口中通过插叙的手法补充必要的信息,解除读者的所有疑惑,将故事画上圆满的句号。
在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长短比较中产生的时距方面,《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灵活地使用了场景、概要以及停顿等。运用场景来叙述故事的实况,这时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大致一致。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对话。《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随处可见的对话便是一个个场景的展现。当事人对案件的简要描述,福尔摩斯与华生关于案件的分析,案件告破后福尔摩斯对所有疑惑的解答等等,许多都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大量的直接引语所形成的等时性叙述,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也减缓了叙事速度,让读者从紧张的故事情节中暂时舒缓紧绷的神经。同时,对话中福尔摩斯或华生不时地打断与提问,也解开了读者对案件的部分疑惑,为读者自我建构部分案件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可能性。概要的使用则主要是在案发开端,当事人或者警察对于案件的描述。《血字的研究》第三章葛莱森对谋杀现场的概述十分简练,其实整个犯罪现场所呈现的远非这些,但作者只用了短短几行字就解决了,显然叙述时间大大小于故事时间,在整个案件中起到引子的作用,这种对线索材料的略述或淡化,只为读者与福尔摩斯提供了在当事人眼中呈现的表面线索,但却足以勾起对案件的兴趣;另一方面,紧接着福尔摩斯对现场的勘查,作者对现场的一景一物都做了细致的描写,这时故事没有推进,一直停留在一个时间点上,但叙述却缓缓地铺展,叙事时间大大长于故事时间,这便是停顿。表面上,侦破故事似乎没有进展,但正是这些静态的描写,让读者与福尔摩斯一起全方位地掌握一切需要的线索,并常常补充了苏格兰场的警探们忽略或曲解的重要线索。正是通过时而拉长时而缩短的时距,才产生了别样的效果。
正是由于作者不断变换叙述节奏,时急时缓,徐疾有致,才使得《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故事更加牵动读者的心弦。除了讲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不太重要的事,如苏格兰场的两位探员对案件过于简单的分析,常见的叙述频率是讲述多次发生过一次的事。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故事中,相关人物一一出场,对于此案又有了不同的叙述与猜想。这样便出现了不同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的、多次的叙述,而且是对同一事件支离破碎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叙述。正如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从不同的角度提供或补充了案情,多条线索的平行、交叉或嵌套,增强了案件的层次感和复杂性,挑战了读者正常的逻辑判断与有限的推理能力,需要读者和福尔摩斯一起分辨真假,拨开云雾,对这些非线性的材料进行线性还原。而正是这种挑战读者逻辑认知的还原过程,才是该侦探小说至今风靡的原因之一。
“目击者”类型的第一人称叙事情境
离开了叙述者,则一切叙事都毫无依附。叙述者与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干,两者之间的不同关系构成了叙事情境。“构成叙事情境的要素有三项,即叙事人称、叙事聚焦、叙事方式。”[3]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华生扮演着多重角色,但最值得关注的便是他是绝大多数探案故事的叙述者。小说中的华生医生,以第一人称“我”的所见所闻,引领读者进入小说主人公福尔摩斯的探案世界。作为聚焦者的“我”——华生,是小说的次要人物,所以是内部聚焦。“我”是福尔摩斯探案过程的旁观者和目击者,因此多数时候只能表现作为目击者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以及自己通过这些材料对案件的推断,但不能直接表现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对福尔摩斯的探案过程也是停留在比读者多一些、而永远比福尔摩斯有限的范围。
这种限制性叙述视角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华生”致力于建构自己的叙事,讲述一个个事件以证明自己文本的合法性[4],这样就拉近了读者与故事本身的距离,让他们如身临其境一般,增强了故事的逼真度和亲历感;另一方面,透过华生有限的视角,在探案过程中,又维持着侦探小说时时设置悬念的需要。作者需要在“与读者进行的智力竞赛中共同破解凶案,而读者也因此在叙事悬念的延迟与破解中得到更多审美愉悦和认知满足”[5]。例如,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华生医生通过日记体的方式将案情调查的进展透露给福尔摩斯,但此时由于福尔摩斯并不在巴斯克维尔庄园,也就不在华生医生的视线聚焦范围之内,读者不免会疑惑:福尔摩斯此时在做什么?他对案件的看法如何?正是这些答案的缺失,让读者不得不暂时与华生一起,通过点滴线索,自我建构犯罪的部分,这也就达到了作者强化“读者参与”的目的。
无论是小说“双层结构”的叙事模式,相得益彰、灵活多变的时序、时距、频率构成的叙事时间,还是所采用的“目击者”类型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情境,无疑都为《福尔摩斯探案集》在侦探小说领域内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许柯南·道尔在写作时并不知晓“叙事学”这一术语,但他无疑为叙事学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参考文献:
[1]Conan Doyle,Sherlock Holmes: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M].New York: Bantam Dell,2003.
[2]张学义,宋建福.侦探小说的非线性认知叙事范式[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5.
[3]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63.
[4]袁洪庚.欧美侦探小说之叙事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228.
[5]熊杰.柯南·道尔《血字的研究》中的叙事悬念[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6):31.
(马春花为长江大学一年级教学工作部讲师,文学硕士;戚晓波为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讲师,文学硕士)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