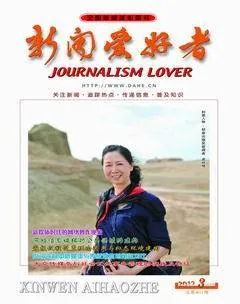流浪中的守望
2012-12-29刘文霞
新闻爱好者 2012年5期
【摘要】弗·纳博科夫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申卡》真实地反映了俄罗斯第一代侨民在西欧动荡不安的生活。作家从现实和回忆两个视角再现了俄侨流亡生活的艰难和对“逝去的天堂”的守望,不愧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杰作。
【关键词】流亡;回归;逝去的天堂;守望
流浪的缪斯
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物质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迅速下降,大批俄罗斯人流亡到国外,掀起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在这次移民浪潮中,许多已经蜚声文坛的俄罗斯作家也移居国外,他们与在流亡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一起,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中“流浪的缪斯”,其作品也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就是这些“流浪的缪斯”的杰出代表。
纳博科夫出生于彼得堡的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后失去了家园,被迫在西欧过着流亡生活,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20世纪20至30年代,纳博科夫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作家。但由于法西斯活动的猖獗,他被迫于1937年带着具有犹太血统的妻儿从德国移居到法国。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前夕,他们又移居到美国,开始再一次的流亡生涯。纳博科夫一生流亡,对流亡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深切感受到了流亡生活的苦与痛。他的作品,从《玛申卡》到《洛丽塔》,从《卢仁的防守》到《微暗的火》,其主人公无一不是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流亡者,他们在通往寻找自我归属的道路上踯躅,内心充满了苦闷和矛盾。
《玛申卡》是纳博科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故事语言朴实,结构清晰紧凑,讲述了俄侨们忧郁的现在和难以“回归”的过去。十月革命爆发后,柏林成为最大的俄侨聚居地,有“境外俄罗斯”之称。1924年,德国发生经济危机,俄侨在柏林的生活急剧恶化,大批侨民开始辗转去往当时经济较为稳定的法国。《玛申卡》的故事就发生在1924年4月,讲述了青年军官加宁在柏林的流亡经历与他对初恋的回忆。
铁道边的旅馆
一切都浓缩在铁道边的一家破旧旅馆里。纳博科夫由远至近、从外到内对这家旅馆进行了描述。它正处于铁道的十字交叉口,从远处看,就像一列正在缓缓行驶的火车。火车经过时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不仅使窗户上的玻璃哗哗直响,里面的房客还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颤抖。狭小的门厅里堆满了柳条旅行箱等杂物,使人一不小心就会“把小腿磕在上面蹭破皮”[1]11。房东太太从旧挂历上撕下来六张日历分别贴在六个房门上当做房间号,房间里摆放的是她拼凑的旧家具,过道的尽头是乱糟糟的厨房、狭小的卫生间和脏兮兮的洗澡间——纳博科夫让七个人物聚集于此。
旅馆主人是一个嫁到德国的俄罗斯老妇人,一年前丈夫去世后,她租下了相邻的那套公寓,开了这家膳食旅馆,房客是六位性格各异、职业不同的俄罗斯侨民。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是波特亚金,他是一个失去了读者的俄罗斯诗人,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他不得不拖着病体一次又一次地到柏林警察局申请前往法国的护照和签证,而语言不通造成的麻烦,加深了他的痛苦。克拉拉是一个德国公司的打字员,贫穷、孤单和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使这位年轻的俄罗斯姑娘始终认为自己像一个外星人,对一切都感到绝望和无奈。主人公加宁体格健壮,敢于冒险,曾是沙俄军队的一名军官,在克里米亚和苏联红军的战斗中头部负伤,伤愈后因无法回到俄罗斯,辗转流亡到西欧。他到柏林刚刚三个月,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他几乎什么都干过,但他仍然一贫如洗,居无定所。他对在柏林的生活感到绝望,打算前往法国,但流亡生活又使他对未来缺乏信心和希望,他犹豫不决,多次改变行期。六个房客中,只有阿尔费奥洛夫对在柏林的流亡生活感到满意。阿尔费奥洛夫自称是数学家,不久前来到这里。相对于其他俄罗斯流亡者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原有的俄罗斯已经死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它忘记,并且认为,只有忘记过去,才会生活得更好。他劝波特亚金留在德国:“这里有什么不好?留在德国是一条笔直的捷径,而去法国是一条曲折的弯路,回俄罗斯简直就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大弯路啦。我喜欢这里,无论是工作,还是在街上散步,都会很开心。我会找到一个永久居住地向你们证明的……”[1]31他一再告诉众人,妻子玛申卡很快就会从苏联来柏林和他团聚。
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宁发现,阿尔费奥洛夫的妻子正是他的初恋情人。在此后的四天里,加宁断断续续回忆了他和玛申卡在彼得堡的爱情经历。这样,一个皮肤黝黑、头发如丝般光滑的俄罗斯女性形象在他的记忆中复活了,“这个形象迅速代替了他的意识中柏林的现状,成为一种真正而又恒久的现实”[2]。
远逝的白桦林
流亡便意味着无家可归,所以,“回归”的渴望大过任何一种情绪。在《玛申卡》中,纳博科夫采用双重叙事手段,一方面描述俄罗斯侨民的流亡生活现实,另一方面回忆加宁与玛莎(玛申卡)在彼得堡的浪漫爱情。现在的柏林生活动荡、贫困、令人痛苦,而过去的彼得堡生活安宁、富足、甜蜜;前者是活生生的真实生活,后者则是记忆中的“虚构世界”。然而,无论是对纳博科夫还是对加宁,后者都更为真实、更为恒久。
故事的第一个叙事层面是对流亡生活的真实描述,而加宁对白桦林中浪漫爱情的回忆则构成了第二个叙事层面。加宁的回忆,使“逝去的天堂”复活了。对天堂的重构是从彼得堡郊外度夏庄园开始的。如果说膳食旅馆里的“现实世界”是封闭的、冰冷的,甚至是动荡的,纳博科夫的描写视角是由外至内的,那么,与此相反,“逝去的天堂”则是完全开放的,作家对度夏庄园的描写视角也是从里到外的。带有铜饰的柔软温暖的床,照在床边的灿烂阳光,窗外枝头上鸣啭的小鸟,天空中明亮的云彩,构成了一幅宁静的图画。客厅里的白色家具、桌布上绣着的朵朵玫瑰、白色钢琴的道道光影、精致可口的茶点,又勾勒了一幅既温馨又平和的画面。纳博科夫把加宁的回忆视角作为自己的叙事视角。记忆的触角随着加宁的大病初愈后走出了他的房间,走出了彼得堡乡下的庄园,延伸到了白桦林中的林荫道。在林边的谷场音乐会上,在熙熙攘攘的快乐人群中,情窦初开的加宁遇到了“似曾相识”的玛申卡。此后的整个夏天,深谷之上的凉亭里、隆隆作响的水磨坊和平静的小河边都留下了他们相依相偎的身影。
小说中,现在与过去、现实与记忆、真实与虚构交互辉映,流亡者的真实生活与主人公美好的爱情回忆交织在一起,真实再现了俄侨流亡生活的悲惨境遇。一内一外,一开一合,一冷一暖,两个世界,两种生活,苦难和幸福,动荡和安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回忆中初恋的甜蜜和激情,不仅加强了他们在流亡中的痛苦,而且强化了他们渴望回归的情绪。
白桦林以及白桦林中的林荫道不仅是俄罗斯的象征,也是俄罗斯人的精神家园,更是流亡者们心灵的故乡。离开白桦林和林荫道,流亡者注定会失去自己的天堂,他们只能在流浪中用记忆来守望这个失去的美丽天堂。
矢志在守望
纳博科夫十分注重“细节”,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懂得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细节”[3]。在《玛申卡》中,纳博科夫通过描述细节使流亡生活的“现实世界”和流亡者记忆中的“幻想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更加突出了流亡者矢志守望“逝去天堂”的信念。
纳博科夫对细节的强调首先表现在他对主人公性格的刻画上。阿尔费奥洛夫对流亡生活漫不经心,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分寸,和旅馆里的其他同胞相比,他独具一格。他看似庸俗,却很现实,表达了包括纳博科夫在内的一部分俄侨流亡者最朴实的愿望和最真实的想法。纳博科夫通过描述一些琐碎信息来刻画阿尔费奥洛夫这个形象,不仅表现了流亡生活给主人公带来的种种磨难,而且向读者传达了一种最真实的思想,预示了俄侨流亡者回归无望的命运。因为无论是对阿尔费奥洛夫还是对纳博科夫来说,他们的祖国俄罗斯“已经死了”,成为一个“逝去的天堂”,只能在记忆中得到永恒。
纳博科夫还通过阿尔费奥洛夫之口,对玛莎做了详尽的描写。玛莎身材瘦小,眼睛炯炯有神,阿尔费奥洛夫把她比做“一朵柔弱的小花”,认为她能够在十月革命后活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纳博科夫刻意使阿尔费奥洛夫处处给读者留下一种迂腐的印象,然而,受到白银时代象征主义文学深刻影响的纳博科夫,恰恰就是通过阿尔费奥洛夫之口,提醒读者留意小说中那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所蕴涵的象征意义。玛莎虽然外表柔弱,却有一个坚强的灵魂,经受住了革命和动荡生活带来的一切磨难。在此,纳博科夫提醒读者,玛莎身上具备俄罗斯女性普遍的美德,她们隐忍坚强、热情善良,是祖国俄罗斯的象征。
纳博科夫着力刻画的另一个细节是膳食旅馆。旅馆所处的位置和里面的摆设,以及火车经过时受到的震动,都使这座破烂不堪的房子看起来像一列正在缓缓行驶的火车。纳博科夫称它为“火车房子”(дом-поезд)。“火车房子”成为一种意象,贯穿全文。在小说的开头,流亡生活的不稳定特征就是通过对旅馆里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拼凑的家具和火车经过时哗哗直响的窗户玻璃等细节的描写来展现的,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具备了“火车”的特征。克拉拉独自飘零在异国他乡,当她对加宁感到失望、在房间里独自伤心流泪时,她听到了左右两个相邻的房间里传来了各种噪音,她感觉自己就像“住在一座不停地左右摇摆、上下沉浮的玻璃房子里,正摇摇晃晃地飘向某处。火车经过时发出的轰鸣声……(不仅)在对面紧邻铁道的房间里听得见,而且在这里也听得见,甚至连床也颤抖着,似乎要跳起来一样”[1]38。在小说的第14章中,“火车房子”的意象再次出现。舞蹈演员科林兄弟为即将离去的加宁和波特亚金举行离别晚宴,六位房客和房东太太聚集在科林兄弟的房间里喝酒聊天。其间,对前途感到迷惘的加宁抛开众人,走出房间。在走廊里,他再次感受到了火车经过时房子的颤抖。对于他和其他流亡者来说,这房子就像一列不停向前奔驰的火车,旅馆只不过是流亡途中的一个小站。
加宁对“逝去的天堂”的向往和对回归的渴望,使他在离别晚宴上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终于采取了一种不光明的恶作剧行为。他灌醉了玛莎的丈夫阿尔费奥洛夫,又把阿尔费奥洛夫的闹钟向后拨了三个多小时。第二天凌晨,他奔向火车站迎接他心爱的玛申卡。可是,在他即将到达车站的一瞬间,一抹亮光把他从幻想中惊醒。他突然顿悟:春花秋月依旧,故国不堪回首,家乡的白桦林已经远逝,和玛莎的恋情早已结束,所有这一切和拒绝了自己儿女的祖国一样,只能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成为记忆中“逝去的天堂”。
和纳博科夫的其他作品一样,寻找记忆中的幸福、守望“逝去的天堂”和逆向的乡思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他笔下的主人公,无论是《微暗的火》中的金伯特,还是《普宁》中的铁莫非·普宁,都和加宁一样,在流浪中守望着“逝去的天堂”。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们既为“天堂”的幸福陶醉,又因为“失去”而感到痛苦。纳博科夫善于在杰出的细节中留住过去,在优美的文字中守望“逝去的天堂”。在《玛申卡》中,“细节”背后的大关怀是作者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对人性和生活的关注。
(本文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01330)
参考文献:
[1]Набоков В.В.Маwенька//Король,■ам■,в■леm,соб.романов и рассказов[M],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2004.c.11.
[2]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M].刘文飞,陈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49.
[3]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申慧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