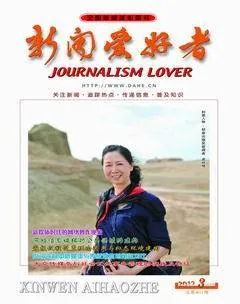还原真实的张孝祥
2012-12-29孙洪杰
新闻爱好者 2012年5期
比起国力强盛的汉唐两代,史学家不无嘲讽地称赵宋王朝为“弱宋”。而南宋王朝更弱,它以1126年金人入侵南迁始,至1279年又在蒙古铁骑践踏下宣告灭亡。战争的阴霾始终笼罩着南宋政权,而统治集团内部的和战之争亦始终没有停息过。生活在南宋前期的张孝祥和张元干同被视为开辛弃疾爱国词派先声的重要的爱国词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张孝祥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然而,《宋史》却说他“出入二相之门,两持和战之说”,这让张孝祥千百年来一直承受着不白之冤。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笔者试图从张孝祥的两篇作品《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和《念奴娇·过洞庭》来还原真实的张孝祥——“文如其人”,当然,人亦如其文了!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南宋主战派将领张浚挥师北伐,但因准备不足,加之前线将帅失和,终致此次北伐兵败于安徽符离。一时间,朝廷上下议和言论甚嚣尘上,宋孝宗刚刚燃起的一点儿“中兴”希望一下子又破灭了,他开始遣使与金人谈判,酝酿新的“和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张孝祥义愤填膺,遂在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一阕: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至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这阕《六州歌头》写作之时,正值宋军新败,南宋小朝廷奴颜婢膝乞求议和之时。词中描绘了金兵的磨刀霍霍,投降派的奔走乞和,抗战志士的悲愤难平,沦陷区人民翘首企盼南宋军队挥师北伐、收复失地,边塞的冷漠空虚,以现实主义的写实笔法活画出一幅生动的时代画卷。
词一开篇,写词人登高望远,“长淮望断”,当时的淮水正是宋、金的分界线,望断长淮,极目尽边塞,不见南宋方面操练军队、整装待发,唯见荒草丛生,几乎与关塞相平。可以想见,南宋边防前线的杳无人烟、荒凉冷落。“征尘暗”三句,写边塞景象。在如此重要的边塞前沿,唯闻边声悄然,不见守军,正说明南宋当局边备废弛,文恬武嬉,也可想见当时投降势力之猖獗。“追想”以下六句,追忆当年金灭北宋往事,故国蒙难,神州陆沉,悲愤之情,溢于笔端。然后笔锋一转,由对历史的追忆转而描绘现实,写强敌压境,宋、金隔淮水对峙,淮水北岸的金兵毡房连成一片,正借打猎来演习军事,而且是在夜晚,骑兵打着火把把整个淮水都照亮了。其声势之大,用心之昭然,可想而知!“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是金人对南宋政权的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更是金兵对南宋军队的威胁与嘲讽。南宋一方边备废弛、斗志消沉,而金人一方正加紧灭宋的步伐,这种情况当然是“遣人惊”了。这个“惊”字,不但体现了当时形势的严峻,而且蕴涵着作者的期望,希望唤起宋人的警惕,激发宋人斗志,别具深意。
词的下阕痛斥投降卖国,感叹报国无门,不仅写出了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而且传达出包括沦陷区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驱逐金寇收复失地的共同心声。过片处词情悲愤,极为沉痛。“念腰间箭”四句写因议和而南宋一方边备废弛,杀敌的利器也被尘封虫蠹,继之以“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三句,写出了一代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悲愤痛苦。徒有壮怀激烈,却报国无门,随着岁月流逝,人也一天天年华蹉跎,可收复“神京”依然渺不可期。这不由让人想到后来陆游的诗句“报国欲死无战场”,这是对当权的投降派的控诉,也是对国人的呼唤,希望国人乘势而起,收复神州,一统山河。自虞允文采石矶以少胜多、克敌大捷以来,南宋人民心情振奋,中原人心向宋,纷纷起义抗金。可南宋小朝廷却违背民意,乞求和议,打击、排斥抗战派人士,词人怎不感叹“时易失”。至此,词人所表达的感情如果还是隐晦曲折的话,那么至“干羽”以下六句,则直斥主和派的投降误国,笔锋如刀似箭,激愤之情喷薄而出。结尾以中原父老对宋孝宗御驾亲征的渴望,反讽南宋小朝廷的误国无能。沦陷区人民日夜翘首企盼的南来的“翠葆霓旌”,却不顾沦陷区百姓对故国朝廷的念念不忘,早已决意要苟安江南一隅了。与张孝祥同时代的范成大,在七年之后写下了同样沉痛的《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张孝祥是耳闻,是依据民心向背的合理推测,范成大却是使金途中的亲眼所见,但他们所传达的感情却是一脉相承的。清代潘德舆评范诗:“沉痛不可多读,此则七绝至高之境界,超大苏而配老杜者矣。”[1]用来评张孝祥的这句词,除去诗词体裁的不同,应当是十分切合的。结句更是词人愤激之情的直白宣泄。之所以会让词人“忠愤气填膺”,只能是因为词人对国家命运和时局的深切忧虑。作此词时,张孝祥正以都督府参赞军事兼领建康留守的身份临淮巡边,希冀能一酬壮志,完成恢复大业。但是,隆兴北伐失败以后,宋孝宗及当权派已完全吓破了胆,正在酝酿新的和议,所谓“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而作为抗战派中坚的主将张浚,正承受着投降派的攻击和多方面的压力。对张孝祥而言,时势几近绝境,以他一人之力,怎会有力回天?他也只能是“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了。
全词深刻地表现了时局的危急,概括了宋金的政治军事形势,强调了收复失地的民心,表达了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强烈悲愤。全篇节拍短促,音调激越悲壮而又一气呵成。清人陈延焯赞美它:“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至末处,如惊沙乱飞,谁不起舞?”[2]也难怪主将张浚“为之罢席而入”了。[3]
不可想象,如果张孝祥真的是一个在战与和之间左右摇摆之人,他怎能写出有如此强烈爱国激情的作品来!不难想象,张孝祥如果不是和张浚一样的抗战志士,而是一个战和不定的人,又怎能写出如此慷慨激昂的爱国词篇,那张浚一定会拍案而起,怒斥他的表里不一,而不会感动得“为之罢席而入”的。作为一个始终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促使张孝祥积极地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儒家强调的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使他充满忧患意识,唱出了慷慨激昂、壮怀激烈的爱国词。“在国事孱弱的环境里,在‘先天下之忧而忧’成为士大夫追求的风范的社会里,他的呐喊合乎了那个时代,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心声。”[4]张孝祥在南宋初年宋金对峙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以自己的词,抒发着胸中的忠愤之气,以号召、激励国人,实现收复失地的理想。尤其是在朝廷上下一片和议之声、投降派得势、主战派遭受种种打击的政治气氛里,能置个人前途、利益于不顾,而一心只想着国家、民族命运,张孝祥的爱国情怀愈显可贵。这样的人,怎能说是“两持和战之说”呢?
张孝祥除了是一个坚定的抗战志士之外,还是一个冰清玉洁“表里俱澄澈”的人。我们可以读读他的《念奴娇·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孝祥任广南西路(今广西和广东西南一带)经略安抚使,虽“治有声绩”,却终因早年一心请缨杀敌,收复失地的政治理想触忤了朝中执政的投降派而“被谗言落职”;次年即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张孝祥由桂林北归,路经湖南洞庭湖时写下了这首词。词作依然是宋词写作常见的格式,上片写景,下片抒情。读者从作者所写之景、所抒之情里,不难体会词人坦荡的襟怀和绝尘的思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不是有句名言“一切景语皆情语”吗?
词作起首写八月秋高气爽,天朗气清,洞庭、青草二湖平静无波,为全词定下了淡然出尘的基调。在这里,“风”难道仅仅是指自然界的风?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词人政治生命里的“风”,但词人意志坚定,谗言诽谤并不能在他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的内心就如这辽阔的洞庭、青草湖一样,“更无一点风色”。八月洞庭湖水势浩大,烟波浩渺。正如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所言:“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这被词人形象地比做是“玉鉴琼田三万顷”。耐人寻味的是,这时洞庭湖上定是舟船如织、往来穿梭,何以会仅有词人“扁舟一叶”呢?这不禁让人感受到:词人政治生命里风雨虽然猛烈,而且也没有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但词人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早已将打击、谗言置之度外,因为“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这恐怕不仅仅是说临近中秋月圆,月光柔和皎洁,映照着澄澈的湖水,湖水也仿佛分享了明月的光辉,上下通明,通透无瑕吧?显然语句更在于表明:身处此等景致之中,词人的心已然摆脱了世俗的羁绊而纤尘不染,直欲与这月、这水融为一体。此时,词人似乎已参透了宇宙的奥秘,与时空达到了心灵的默契。纷纷扰扰、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恐怕是没有耐心细细品味这般景致的。这般景致,无人共赏;这种心境,无人理解,词人颇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寂寞。在那样一个时局危绝、国家民族命悬一线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种处境只能增添词人的愁绪,何谈真正的超脱?“妙处难与君说”,不是真正的悠然自得,而是满含对时事的失望,以及无限酸楚、无可奈何的叹息。
词的下阕直抒忘怀世俗、超然物外之情。“应念岭表经年”三句,追忆往昔,由于自己坚持抗战,为当权派所不容,屡遭诬陷打击,直至被迁蛮荒之地,但矢志不渝,依然问心无愧、襟怀坦荡。词人形容他在官场一向光明磊落,品行高洁,连肝胆都如冰雪般晶莹而毫无渣滓,但这却无人知,只能由明月孤光洞见自己的纯洁肺腑。“短发萧骚襟袖冷”,活画出词人的孤高形象。他头发稀疏、衣衫单薄,却并不以为然,依旧悠然泛舟于这秋夜洞庭之上,并大胆地做出了这样的想象:“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他要以江水为美酒,以北斗七星为酒器,天地万物为宾客,饮尽滔滔江水。独酌无趣,而又世无知音,怎么办?那就邀天地万物为宾客。这俨然是忠肝义胆,唯天地可鉴的自我表白。至此,词人已全然摆脱了仕途失意之悲,直欲融入自然化境。想到忘情处,词人不觉扣舷长啸,早已忘记自己身在何处。词的开头,词人还点明了时间是在“近中秋”,为什么结尾处却“不知今夕何夕”了?写下这首词时,词人才34岁,显然不是年纪大糊涂了。想想词人坎坷的仕途,再细细品味词中刻画的意境,我们就会明白,词人面对这纯洁的自然美景,抛却了功名富贵、宠辱得失,让自己的心灵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得到休憩和归宿。俗世的一切已经不能成为他的羁绊,邀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今夕何夕”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恐怕这正是王闿运在《湘绮楼词评》中赞美张孝祥这首词“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犹有尘心”的原因了。[5]
想想这首词“玉鉴”、“琼田”、“素月”、“明河”等一系列幽寂凄清的意象所构成的清幽的境界,进而营造出的那个纯洁无瑕的世界,这分明折射出的是词人高洁超脱的情怀,“以我观务,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嘛!天然景象与词人心象浑然无迹地化作一体,词人高洁的人格、高尚的气节和高远的胸襟都融化在了这一片皎洁晶莹的月光湖影之中,词人的人格操守不是就如同这明月朗照下的湖水一样,“表里俱澄澈”吗?
张孝祥胸中涌动的,始终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在张孝祥短暂的一生中,虽然备受排挤,屡进屡退,终至大志不能伸,但他始终不曾改变自己的志向。作为胸藏韬略、丹心可鉴的爱国志士,张孝祥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才能,金戈铁马、风云变幻的时代又使他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即使是他的“湖海平生豪气”不能运用,报国济世的理想破灭,一腔忠愤不为时人理解,他也只是以“扣舷独啸”来纾解胸中忧愤,从未背叛自己的内心。“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正是张孝祥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潘德舆.养一斋诗话[M].上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