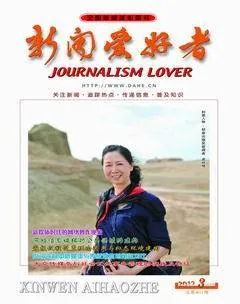电视剧新《红楼梦》的文化元素分析
2012-12-29王聪贤
新闻爱好者 2012年5期
【摘要】新版《红楼梦》电视剧播出已有一年多,在众多关于新《红楼梦》的讨论中,笔者选择从电视剧中的文化元素来分析。本文共三节,第一节是新《红楼梦》电视剧的“梦幻结构”分析,梦是中国的文化之一,对《红楼梦》中“梦”的改编可看出导演在剧中对文化元素的处理;第二节是新《红楼梦》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分析,从人物形象看电视剧拍摄存在的问题;第三节是新《红楼梦》电视剧中的中国文化分析。希望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能为名著翻拍提出建议。
【关键词】电视剧新《红楼梦》;文化产业;《红楼梦》
作为文化产业案例的项目开发与内容生产的文化创新,重拍《红楼梦》电视剧,并因此进行文化资源动员的审美发掘与艺术表现,把人物、情节、细节、环境、语言的文学作品内容与知识元素、产业元素的人类学科学依据的内容生产融为一体,环环相扣地推动情节,展示细节,烘托环境,展开悬念。[1]新《红楼梦》电视剧的情节既不同于62版越剧《红楼梦》电影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也不同于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宝黛爱情和家族兴衰双重主线,它没有集中表现某一主题或几个主题,只是简单化地按高鹗续写的120回通行本的基本情节来拍摄,过于注重形式上的尊重原著而缺乏内容创新。
新《红楼梦》的“梦幻结构”分析
《红楼梦》的结构,是以全书十二个“梦”为脉络来建构整部小说的。《红楼梦》中的“梦”可谓篇幅宏大、笔触细腻、文采绚美、构思精巧、寓意深刻。全书恍如一场大梦,梦中又有无数小梦,环环相扣,前后照应,组成了一个美妙绝伦的艺术结构。[2]93《红楼梦》小说里甄士隐的“葫芦梦”和宝玉的“红楼梦”构成第一个“独立”的梦幻框架,在87版《红楼梦》里没有这两个梦的内容,为快速切入主题,第一集便是林黛玉别父进京都,新版《红楼梦》分别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细致地展现了这两个梦。剧中“葫芦梦”采用画面特效处理,先是甄士隐魂魄离身从家里来到太虚幻境,对太虚幻境的描写可谓宏大唯美,白云飘浮制作出的仙境和通往警幻仙姑的桥都很精美,演员的凌波微步也展现了仙境的美妙,这一画面的特效处理恰当,体现了导演李少红所擅长的宏大场景和精美画面的制作。甄士隐听得一僧一道在讲述红楼梦故事的缘起,这段谈话按小说内容编排,对整部电视剧的结构安排较以往的影视是一种创新,但内容拘泥于小说。宝玉的“红楼梦”场景也是太虚幻境,画面变化更为丰富精美,这里加入了昆曲的元素作为背景音乐,使“红楼梦”进入幽暗凄迷的氛围,宝玉与警幻仙姑在桥上对话,演员并没有进入这种氛围,对话直白而演员表演缺乏变化,随之宝玉在警幻仙姑的带领下游玩各司,在表现剧中人物命运结局的纲要时又采用了画面特效,这段画面设计及旁白和背景音乐处理上恰当合理,但仍只局限于艺术形式上的表意。第一个梦是二位神仙到“警幻仙姑”处交割“情事”,第二个梦是“警幻仙姑”将“情事”授意于宝玉,这才构成“独立”的梦幻结构,但在剧中这一内涵没有得以体现,人物台词及整个编排都按照小说的形式来简单取舍,缺乏创意改编。
第二个梦幻框架是“家族盛衰”,这里有两个梦都是王熙凤所做,87版《红楼梦》和新版《红楼梦》电视剧都只写了第一个梦即秦可卿死后托梦给王熙凤。由于受时代和科技的影响,87版《红楼梦》的梦境表现得简单,但导演对小说改编得恰到好处,演员的台词不拘泥于小说,为突出主题做出了合理的改编,演员在梦境中的表演让观众感觉到真实,王熙凤睡觉的姿态表现出紧张忧思,秦可卿的语气幽怨无奈,这些情绪都符合家族盛衰梦,这段改编尊重原著的内涵。新版《红楼梦》中导演严格按小说来拍摄,却也只写了一个梦,破坏了这一梦幻框架的完整性,剧中对这个梦的描写表现出人物性格幽怨、画面飘逸,台词完全如小说,又是一处形式重于实质的描写。
第三个梦幻框架是“红楼痴情”,这里有小红梦贾芸、宝玉梦蒋玉菡和金钏、宝玉梦拒绝金玉良缘、紫鹃试宝玉真情的梦,这四个梦是曹雪芹为赞扬真情而著,另外还有柳湘莲懊悔梦和尤二姐梦尤三姐两个梦,曹雪芹有意安排尤氏姐妹的故事作为大观园的结束曲。87版《红楼梦》选取了小红梦贾芸、紫鹃试宝玉、柳湘莲和尤二姐的梦,并且都做了改编,描绘出大观园“情”的心路历程的开始,肯定了宝黛的爱情,对尤氏姐妹的悲剧命运表示同情。新版《红楼梦》中删去了小红梦贾芸的情节,对曹雪芹选择这个梦作为开始对情的严肃讨论没有把握住。
第四个梦幻框架是“红楼回归”,这里只有宝玉梦晴雯一个梦,虽然只有一个梦,但在整个梦幻结构中至关重要,宝玉看到的“薄命司”中第一个人物晴雯回去了,最后一个秦可卿也回去了,了解了人间的“情”。而两部电视剧都写了这个梦,都按小说的内涵加入了这个梦,87版《红楼梦》仍做了改编,而新版《红楼梦》基本是按小说来拍的。小说里“梦幻结构”的叙事艺术有三个特点,一是用结构主线和人物组织成许多网眼,使其有多头绪的发展空间,二是始终以人物性格为核心去组织生活和安排情节,三是前后呼应,击首动尾,既悬念丛生,又丝丝入扣,就像精品的织绣一样,图案都具有立体感的艺术效果。[2]107-109
新版《红楼梦》在梦幻结构的设计上重于87版《红楼梦》,这体现了现代媒体技术与制作的优越性,导演李少红在这些局部内容的处理上过于注重形式创新,在整体结构布局上没有显示出创新元素。改编是对小说文本的再次解读和创造,要适应时代和新的艺术形式的需求,87版《红楼梦》受影视技术的局限,但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和艺术转换的规律,根据宝黛爱情和家族盛衰的主线来有选择地安排情节和布局电视剧结构。而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整体结构则表现出没有焦点,主题也凸显不出来,就是简单地在叙述故事,并且叙述得没有创新,它的可取之处在于对影视技术的应用,制造出了宏大唯美的场面。
新《红楼梦》中人物形象分析
87版电视剧《红楼梦》创造了一个时代,一个疯狂迷恋“红楼梦”的时代。电视剧的成功固然可以归因于强势媒体的传播力度,归因于剧本改编的严谨细致,但是,其演出阵容的强大,演员表演的出色,塑造了许多观众心目中的“林妹妹”、“宝姐姐”、“宝玉”等经典形象,也是其之所以成功而不可忽略的原因。[3]87版《红楼梦》的演员外形和气质都符合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而新版《红楼梦》在演员的选择上并不成功,演员并没有严格按海选的结果来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海选的权威性,说明那只是一场娱乐的盛宴,就演员本身而言,黛玉、宝玉、宝钗等演员外形与原著描述相去甚远。原著中描述的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而蒋梦婕饰演的林黛玉,整体形象有点婴儿肥、眉毛粗、眼神缺乏神采,不能体现出黛玉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的形象。原著中描写宝钗是“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剧中少年宝钗太过瘦弱,不是书上描述的丰盈圆润的外表,也与原著形象不符。原著中描写宝玉是“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少年宝玉的饰演者于小彤形象不够饱满,眼睛总是乱转,英气不足。
演员外形的选择很重要,演员造型也很重要,造型艺术是直接冲击观众视觉的影视艺术,而叶锦添为演员设计的戏服和额妆备受争议,这直接影响了整部电视剧的视觉效果。造型设计是整部电视剧最具创意的设计之一,但这种追求虚化的戏剧感设计不符合原著精神,是叶锦添大胆的个人尝试。
剧中最能塑造人物形象的动作语言也被简化,快镜头的频繁使用和过多的旁白使演员难以入戏。黛玉常听母亲说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所以她在进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留意。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中黛玉从下船到进贾府时一直听到的是男低音的旁白和诡异的配乐,接着就是快镜头的过度使用,不知道到了一处什么地方黛玉就一个人在那了,院子里的人该干什么还是在干什么,一点不似有远客来的热闹,黛玉刚观望了一下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又是快镜头还很突兀地插进两个丫鬟,然后就是鸳鸯简单的话语并把黛玉带进屋,导演安排的这段情节过多地使用快镜头,未能给黛玉表现她的细微心理的机会。87版《红楼梦》对表现黛玉的心理颇费心思,黛玉从下船到贾府也是坐轿子,一路上她仔细观察沿路的建筑,尤其是到了宁荣街,她细看建筑和观察门外的小厮,到了贾府就有人通报,园里就热闹起来,当周瑞家的扶她下轿时她没有说一句话,在丫头的陪同下去见贾母,这段画面将黛玉的形象表现得鲜活丰满。
87版《红楼梦》人物形象塑造成功,尤其是王熙凤出场拍得十分成功。新版《红楼梦》王熙凤的人物造型显然不如87版的,再看演员演技,王熙凤的笑声是最具特色的,但旁白一如既往地按小说内容读着,王熙凤的笑声诡异,为配合旁白她握着黛玉的手笑着时又是慢镜头,整体上让人感觉别扭,直到旁白结束人物间才正常地谈起话来,可见导演对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形象没有理解和再创造,人物形象显得干瘪。
新《红楼梦》中的中国文化分析
《红楼梦》中蕴涵着丰富的中国文化,有中医文化、民俗文化、园林与美食文化、中国戏曲文化等,然而新《红楼梦》电视剧没有细致地将这些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与审美创造,这是作为文化产业案例翻拍的缺失。
《红楼梦》中有丰富的医药文化,如冷香丸、人参养荣丸和张友士给秦可卿看病等,这些都蕴涵了深厚的中医文化。新版《红楼梦》中宝钗提到冷香丸的配方时还没讲完就被打断了,极易给观众造成这药只是个传说的感觉,然而这药从医学原理来说蕴藏着丰富的中医理论知识,红学研究成果中就有相关介绍,但没有在电视剧中对其融入再生产,其他的医药也没有在电视剧中有细究其源的。
再看《红楼梦》中的民俗文化如节日风俗、婚嫁风俗、祭祀风俗等在剧中是怎么展现的。过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小说中费了很多笔墨来写这个节日,而剧中对置办年货描写就只有第二十五集中贾珍收租的一段,接着就到了腊月二十九,过年的风俗由旁白来介绍,祭祖拍得细致一些,但没有融合祭祀的文化,剧中有一个人主持仪式,接着就是贾珍等人拜祭,旁白仍按书上的内容介绍着这一切,这种只是按风俗去做的设计无疑错失了展现中国文化的机会,毕竟影视面临的是全球性的市场,细致地拍摄中国文化才有利于其传播和传承,即便是中国的观众也不能完全理解过去的文化,导演有必要好好研究这些并通过影视再创造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红楼梦》中蕴涵的中国文化还有很多,新《红楼梦》电视剧都没有将其细致地表现出来,这不利于名著精神价值和艺术成就的体现,因此,无论何时改编名著,都应尽力做好充分准备,尽量了解文本内涵再作整体改编,合理布局结构。也只有这样,名著翻拍才能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皇甫晓涛.创意中国与文化产业[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
[2]马经义.中国红学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3]陶今.《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D].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09.
(作者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生)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