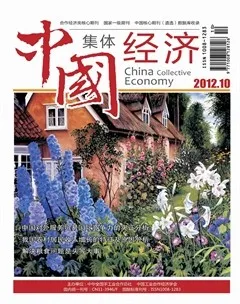破坏性技术创新条件下的利益群体影响分析
2012-12-29熊立
中国集体经济 2012年4期
摘要:评价技术创新的诸多模型都强调创新成功要基于一种不破坏现有价值链成员合作行为的前提下去吸收和消化新知识。然而,这些模型都未能对面临争议性和破坏性较强的创新情境下如何协调上述关系作出全面的解释。破坏性创新往往可能带来令人难以适应的新经营环境,这就需要技术开发者把诸多环境不确定性降至最低化。尤其当涉及到诸多的人际冲突协调问题。文章通过整合利益群体、创新和学习理论,为企业建立起一个评价破坏性技术创新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模型。
关键词:破坏性技术创新;不确定性;利益群体;试错法;逐步社会工程
一、破坏性技术创新
早在20世纪中期,熊彼特(1942)和彭罗斯(1959)就已指出技术创新不仅是困难重重和代价昂贵的,更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蒂斯(1997)和温特(2002)进一步强调拥有某种难以模仿的差异化技能可使企业走向持续发展之路。但是,一些学者同时认为技术创新可能具有“能力破坏性”(Tushman,1986;Christensen,1997),致使现有能力的失效或低效。如数码相机的诞生,不仅影响到胶片相机生产行业,连同其价值链上所有相关产业都受到巨大牵连。这便是为什么破坏性创新又被称为颠覆性或革新性创新。
尽管学者们从产业、企业及其价值链关系网三个层面着力研究了破坏性创新行为的影响,但对企业外部的“第三方”社会力量却关心甚少,这便是Freeman(1984)所概括的二级利益群体:社区公众、环保人士、媒体、网友、宗教群体、科研机构、社会名人等。国内也有学者像盛亚(2009)主张企业技术创新不再独立,而是由广泛的利益群体网组成的共享活动,但他未将不同性质的利益群体划分开来看待。
本文将破坏性技术创新带来的技术、组织、商业和社会不确定性区分开来,对相对低复杂度和模糊度的利益群体问题(一级利益群体如供销方、顾客和互补品),采取“试错学习法”(波普尔1959,2002)比较恰当,因为不确定性低以及利益群体关系较紧密。然而针对更广泛的社会二级利益群体,她们数量众多,生存目标、观念和需求也不一致,很难单独实施“试错法”。此时“逐步社会工程”(波普尔1945,2011)将取而代之。“逐步社会工程”的核心理念就是“firstthingsfirst”,强调步步为营,先调和最急迫和重要的社会问题,在不断摸索中逐步建设和谐社会。
二、创新的不确定性
与其他技术创新相比,破坏性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新发明、新技术和新市场,还意味着整个产业的更替和政策的改革,因此它更需要尽可能降低诸方的不确定性。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些不确定性定义为四类:技术、商业化、组织和社会不确定性。
早在20世纪80-90年代,破坏性创新所带来的技术可行性、商业化问题和组织能力不确定性就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一些学者强调一项新技术的诞生不仅要在技术上获得成功,还要满足市场需要,并能够得以充分地组织实施利用,甚至把组织能力的概念扩散到了整个供销价值链的组织上(Teece,1986;Afuah,1998;HendersonandClark,1990)。但笔者主张企业还应把更大范围内的二级利益群体包含进去,尤其针对那些给人们带来不菲利益的同时也对环境、健康和社会起到副作用的破坏性创新行为。
三、管理利益群体
根据Freeman(1984)的定义,影响企业实现其目标或被企业所实现的目标影响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谓之一级或二级利益群体。一般而言,一级利益群体都需企业直接为之负责,如员工、顾客、供销方、合作方等;对二级利益群体企业则需间接关注,如公众、媒体、竞争者、社会活动家等,因为她们可以给企业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如果把创新行为和利益群体联系起来分析,可以采纳Hall和Vredenburg(2003)的划分方法,即以创新所带来的价值增值链为标杆,把利益群体分为链内群体和链外群体。链内群体有着一致的利益、要求和权利,即所谓“同舟共济”;而链外群体往往有着大相径庭的利益和观念,致使企业更难识别其重要程度。破坏性技术创新特别需要关注和分析二级利益群体的反应。例如,由于链外群体的观念大相径庭,有些人不敢信任一项新技术,还有些人因为各自立场、道德或利益原因,有意地不认可。在不考虑她们反应的情况下便将全新技术推广上市,很容易造成巨大社会性问题,而这些社会性问题反之又致使技术的商业化和组织实施受阻,最终伤害到企业创新的效果。这就是说,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蔓延,企业的创新行为不再只需对链内群体负责,地球另一端的某个声音兴许就能决定某项创新的命运。
那么,分析创新增值链时把链外群体包含进去应该可以更有效地降低潜在的环境不确定性。在此笔者建立起一个直观的模型(见图1),用以展示破坏性技术创新与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图1中,正下方所谓“创新增值链群体”描述的是所有利益、观念和目标一致的价值链内群体,他们通过创新可以使自身目标得以实现,并且利益最大化,同时使企业价值链内外达到增值的效果。图上方的群体则均为链外群体,他们的目标、价值和立场不一,且相关程度有异,但共同点就是都对企业增值链实现存在潜在的干扰。左侧箭头表述的是由二级到一级利益群体的相关程度,右侧则表述的是群体复杂度和模糊度的大小。由于二级群体复杂度和模糊度很高,甚至有些时候用“?”来表述,代表企业很难界定哪些二级群体是最至关重要的。另外,政府部门的角色较为独特,他夹在二级和一级群体之间。政府既有能力直接决定企业的一些行为,又可以站在监督和旁观的角度影响这些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复杂的情形会产生。如同样是反对一项创新,环保分子的态度是担心它会影响人类健康,而金融投资方所担心的是该创新在短期内无法产生大的回报,仅仅是对产业长期发展作出贡献是不够的。这就是说,企业也许面临一个“症状”,但要解决的绝不是一个“问题”,解决方法也就复杂起来。
四、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笔者建议采用波普尔(1945,1959)著名的“试错学习法”和“逐步社会工程”来降低创新不确定性,以解决利益群体可能产生的问题。
(一)试错学习法
针对相对低复杂度的创新情境(一般出现用于链内群体,或当利益群体数量少、立场相近时),“试错学习法”颇为有效。具体来看,该方法可解决技术、商业化和组织不确定性带来的诸多问题。
1.技术不确定性:通过演示一项技术的可行性,如为某项技术申请并通过政府相关法律(质量)标准,或请代表性利益群体试用。
2.商业化不确定性:降低商业化不确定性的唯一显著手段便是经济回报的产生。建立一个优秀的营销团队是技术增值的必要手段。例如,一个工业供应商可以将新技术最先卖给大工厂的工程师们,获得这些最关键的利益群体认可后,自然不愁商业化问题了。
3.组织不确定性:由于链内群体的战略目标都是一致的,他们通过新技术所获得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一般而言出现了协调问题都可以通过磋商解决,不存在任何原则上的根本冲突。
许多企业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却仍无法顺利发展新科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普遍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不确定性。
(二)逐步社会工程
随着问题的复杂化和模糊化,试错的成本愈高,必须采用“逐步社会工程”这一理念,针对特定情境和重大问题,优先解决,步步为营。
社会不确定性:即由二级利益群体带来的可能对创新效果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尤其针对大型企业。有时一项转基因技术用于食品后,“绿色和平主义者”和生物科研机构便开始宣扬其可能的害处,这不仅给企业施加了巨大压力,也影响到整个价值链的供销水平。因此,企业必须尽快找到最关键的二级利益群体,然后运用公关等手段,竭力证明一项创新的社会合法性。
五、结论
技术创新的管理实践迫切地需要企业正确识别更广泛的利益群体(盛亚,2009)。当今许多企业在资金充裕、研发团队一流的条件下,面对环境给予的创新机会,仍徘徊不前;另一些企业则在良好地解决了技术、商业化和组织协调问题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推广其创新,这都是因为它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技术、商业化和组织问题,还有社会性问题。本文在破坏性创新情境下,通过分析四种不确定性与两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企业在破坏性技术创新过程中,首先要解决技术可行性问题,以对内部利益群体负责;其次要解决商业化问题,对价值链成员负责;再次是要解决社会认可问题,对二级利益群体负责,这样一项破坏性创新才能名副其实地得到推广。
参考文献:
1.Schum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