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温和与坚硬
2012-12-29王悦微
中国周刊 2012年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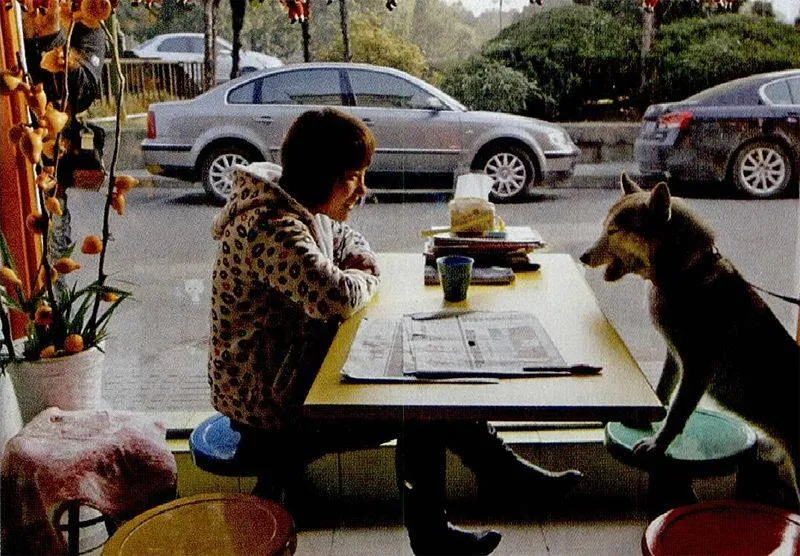

“小富即安的城市,能忍也就忍了,出得门来就已经是历史性突破。”
青石巷32号
小时候看《戏说乾隆》,看到皇帝爱下江南,于是就很向往。想象中,那是一个草长莺飞,碎雾桃花,姑娘们袅袅婷婷走在田埂上的地方。于是就问我妈:“我什么时候能去江南呢?”
“我们这里就叫江南啊!”我妈哈哈大笑。
“双飞燕子几时回?竹外桃花蘸水开。”少年时无意中看到吴冠中先生的《双燕》,纸上正是自己心心念念中向往的江南。据说此画就取材于宁波海曙区的月湖,画上两只乳燕,飞于湖畔的黑瓦白墙上,虽色彩以灰白为主,但掩盖不住满纸的勃勃春色。
几年后,我考入宁波二中,这所历史悠久的中学,正位于月湖南端的松岛上。从镇上到中学,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中间经过大片大片的稻田,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满目皆是的紫云英,磅礴的香气直往敞开的车窗扑来。
车行至南站停靠,不远处便有一汪明澈的湖水,形似月牙,故得名月湖,这湖从唐贞观年间开始开凿,一直是宁波文人们的聚集地。
月湖一带的巷子名也颇见雅意,比如菱池街、拗花巷。江浙的建筑不像西方的哥特式那样宏伟壮观,喜欢掩映在葱郁的树丛中,露出个淡淡的飞檐。
当年无数次行走在这样遮天蔽日的树荫下,觉得满心欢喜,不仅是因为这一路好风日,更因为宁远。
他住的青石巷32号,正在这小巷深处。
90年代的宁波市区内,散布着很多青石巷这样的街道,狭仄,悠长,比如莲桥地,比如郁家巷,大院里住了好几户人家,彼此熟知,往前数几辈就早已相识。
房子大都有些年头了,显得简陋陈旧,但在一片低矮的房屋里突然会冒出一两栋特别精致的小洋楼,石刻的门匾,写着耕读传家之类。虽已因时间太久而显得字迹模糊,但依然透露出庄重的家学渊源来。
宁远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当年也是华府豪舍,据说是赵姓的祖上中了举人以后盖的。当我去时,爬山虎几乎覆盖了整面后墙,风吹来时,一层层如波浪般涌着。
宁远和我一个班,成绩很好,人又温和,两家的长辈又曾是同学,见我来城里上了学,便常叫我去吃饭。
宁远的妈妈很会做饭,尤擅长做宁波点心,比如汤圆之类。糯米粉必是自家亲自去买米、浸泡、磨浆,然后倒进纱布袋子里,悬挂在屋前,等里面的水分慢慢沥干,袋子里留下的就是糯米粉,宁波话里称之为汤果粉,可以用来做汤圆或圆子。
汤圆馅也是很讲究的,除去磨碎的黑芝麻,黄豆粉,白砂糖这些之外,最要紧的是得有板油。揉好板油要费很大工夫,全靠一双手在那里揉啊捶啊,最后把它跟其他原料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捏成小圆,裹进汤圆里。待煮熟后捞起一咬,馅儿汩汩流出,唇齿间一片浓郁的香气。
而若是把汤圆搓小,又不放馅儿,就成了小圆子,也就是宁波人俗称的汤果。煮汤果的时候要放酒酿,也是自家做的,方言叫浆板。这两种甜点心,是宁波人过年必吃的食物。
像大多数宁波女人一样,宁远妈妈很爱花工夫在这上头,不必过年,家里时常做来,还叫我和宁远送去给各家邻居。我在功课之余就常能吃个痛快。
多年以后,当我坐在某一个气势磅礴的酒桌前,时常想起那些甜甜糯糯、透着温婉文气的点心,就如同宁波人的气质,安宁,埋头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自得一番惬意和安闲。
江湖上流行一句笑谈,叫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意思是说宁波话太硬,听起来像吵架,但宁波人本身是不事争执的。比如在街头,尤其很少看到大肆争吵的,即便是两辆自行车当头撞上,只要撞得不严重,顶多抱怨声“耨咋回事体啦?”(意为“你怎么回事”),也就各自走开,不太会当街大吵起来。凭着靠海的便捷,又是历史上早期的通商口岸,这个富庶的小城没有尖锐的性格,有着小富即安的温和。
忠叔的抛轮厂
当年青石巷32号已成为一个大杂院,从“文革”开始,陆陆续续住进来十几户人家,低矮的屋檐连成一片。
宁波的天气就是这样,梅雨季节里,雨下得细细密密,檐下终日滴着水,渐渐连成一条线,落到大水缸里去。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这是江南四月里独有的霉味,尤其是前门的祠堂,这种气息幽深而绵长,仿佛是从每一面瓦片,每一根柱子里散露出来的。那祠堂,其实早作了宁远爸的小工厂。他原是车队里的会计,我叫他忠叔,果真是耿直又忠厚,看着脸上总是笑呵呵。
据说后来在队里呆不住,被人排挤了出来。他和老婆一商量,就开起了这个家庭小工厂,专门生产抛轮。
说它小,是因为忠叔手下一共就三个员工,其中一个还是自家老婆。九十年代初,正是外来务工潮兴起的时候,大批的外乡年轻人涌进宁波城来,尤以安徽、四川等地居多,邻近的北仑区吸纳了大批外乡青年,尤其是服装厂、模具厂等。他们大多二十来岁,甚至更年轻。
忠叔也赶了个潮流,招了两个安徽姑娘来做活。
一个抛轮可以卖二十几块钱,在当时是挺可观的价格,所以有时忠叔自己也会上手裁剪拼缝。他戴着老花镜端坐在小椅子上,晒着太阳干着活,老猫眯着眼睛蹲在墙角,看起来很是温暖。
温暖背后是并不浪漫的现实。宁远有个哥哥,叫小川,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有些傻气,街道安排进了福利厂,算是照顾,只是收入微薄。娶了个同病相怜的媳妇,婚后还跟爸妈住一起。宁远妈找了粘信封的活计,粘四个可赚一分钱。白天做抛轮,晚上粘信封。她独创了一套粘法,信封刷地铺开,只露出一角,用刷子刷上一层薄薄的浆糊,拿裁好的纸板往信封中央一放,两个指头上下一翻,再一抚,信封就平整地粘好了。
宁远妈是个很能吃苦的女人,因为常年干活,四十岁刚出头的人,手都粗了,一到冬天还长冻疮,手指头都是紫红色的。都说江南女子多婉约,在生活面前,读过一本又一本琼瑶小说的宁远妈最终还是放下婉约,像个男人一样地拼命干活,以维持家里的生计。
当时的宁波女人,比如我妈,大多也是这般辛苦。操持家务,谋划生活,不过性格上还是难脱江南女子的柔和,宁远妈偶尔因为发愁家里的开销不够用,跟忠叔争执几句,自己先把眼睛红了。
我曾想帮她一起干,但手脚太慢,宁远妈说,干得时间长了,才能熟能生巧。
接不到信封活儿的时候,她就四处托人去找活,有时是粘药袋,有时是缝小布熊,缝好一个给五分钱。她缝得又利索又妥帖。有时宁远做完了作业,便帮她一起缝。但宁远妈不太喜欢他干这个,总催他去读书。父母这样辛苦拼命地干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宁远,大院里最会读书的男孩。忠叔素来敬仰读书人,他要供儿子读最好的大学,离开这个大杂院的生活,去过另一种人生。
这是他有一次喝着小酒眯着眼跟我爸说的,宁远是他的骄傲。
想想办法,总还能过得下去
这样勤勉的生活,在宁远初三那年开始,变得越发艰难起来。
1995年前后,正赶上工厂大规模倒闭,不时传来工厂关门、工人下岗的消息。像梅子食品厂那么辉煌的工厂,说倒就倒了。接着是电气成套厂,第二机电厂,小川所在的福利厂在苟延残喘了两三年后也倒闭了。
邻区的棉纺厂在那年的年底被收购兼并,愤怒的下岗女工们结队去市政府门前示威,打出的横幅是“上山太早,做鸡太老。”
宁远的舅妈也去了,她在棉纺厂做了十五年的“三班倒”,被告知不必再去了。连辛苦都不能了,一下空得心里发慌,她来宁远家哭了好几次,不知怎么办才好。厂里的姐妹来约她一起去,相互壮壮胆,她就跟着去了。晚上忠叔在饭桌上谈起这个事来,叹着气说:“厂里效益不好,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劝她还是不要出头的好,再闹也闹不出什么来,要是惹出点麻烦来就不好了。”
“想想办法吧,既然都这样了。想想办法,总还能过得下去。”他最后总结道。
抛轮厂生意不太好做了,忠叔将两个安徽姑娘辞退,说还是自己干吧。我放学后,有时会去他家吃个饭,给他们打打下手,比如帮宁远妈把粘好的信封叠好,用纸条扎成一捆一捆的,但粘信封的活儿也没以前多了。
即便光景不太乐观,那年春节,大家还是鼓起兴致来去买了炮仗,一起合伙去磨了糯米粉,做了年糕。大年初三,爸妈带我到宁远家拜年,爸跟忠叔对坐着喝酒解愁,发完牢骚又宽慰彼此。
那一年,我爸也下岗了。人到中年突然失去工作,没有专长又没有学历,何去何从,四顾茫然。他想去蹬三轮车,但是当时三轮行业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牌照也很难办得出来。
我拿着年糕去他家的炉子上煨着吃。煨年糕是我的拿手戏,微焦而脆,香气扑鼻。
煨好了年糕,我拿去跟宁远一起吃。他心事重重,越发拼命地读书,连铅笔盒上都写着“一定要考进效实中学”这样的话。
这所创办于1912年的百年老学校是全市学生向往的名校,考进它,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重点大学。当时老校区已拆迁,但留下一棵当年的银杏树,每到秋来,黄叶锦重重地落了一地,曾在效实中学念过书的中年人们,路过此地,总不免要感慨惆怅一番。
江南文入骨子里那种浪漫情怀,是跟这个城市里的老建筑,小巷子,以及繁花,落叶和一池秋水难以分离的。但宁远把效实中学定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却无心流连那些浪漫,他发狠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的性格里有一种和父母那一辈不同的决绝。
唯有读书高
宁波人崇尚读书,这是有传统的,不知道是因为天一阁的气质影响了这个城市,还是因为这样的城市,才孕育出天一阁这样的藏书楼。
现在,宁波人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自己和自己的城市: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甬江另一边的镇海,二十几万人的城区小镇,诞生过26位两院院士,画家贺友直、顾生岳、陈逸飞俱是同乡。忠叔祖籍北仑大碶,早些年,这个碶字甚至在智能拼音状态下都找不到,只能勉强以“契”字代替,但就是这么个地方,面积不过105平方公里的小镇,却被称为华侨之乡,镇上的小学,有气派的教学楼,是由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的严信才夫妻捐资造的。
忠叔生平最信读书二字,虽因“文革”而耽误了自己的学业,对儿子的教育却充满期待,看作是全家第一等的大事。宁远也确实争气,班里数他成绩最好。
宁远考上效实中学的那年夏天,也正好是忠叔的抛轮厂正式倒闭的日子。那年夏天对忠叔来说是忧喜交加,不过他还是很自豪地请我们吃西瓜,说请人介绍了一份工作,打算去北仑区的某家火电厂烧煤。
烧煤是个体力活,干一天给四十块钱,需要穿着很厚的工作服,在炉子前去铲煤,一铲子下去很沉。到了夏天,炉子前火热的温度把全身的汗都给吸完了,结成一层盐花挂在衣服上,在深蓝色的工作服上特别显眼。
忠叔说,想到赚了钱能供儿子读书,觉得很高兴,咬咬牙也要干下去。
对他来说,更高兴的是宁远的哥哥小川给他添了个孙子。媳妇是河南人,家里太穷,过不下去,经人介绍,嫁到宁波来,想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后半生。生了小孩后,给起名叫梦甬。甬是宁波简称,媳妇在这个儿子身上寄托了自己全部的城市之梦。
街道福利厂倒闭后,小川在青石巷的大樟树下摆了个摊,卖馄饨粢饭,生意还不错。宁远妈的眼神差了许多,年前出了次车祸,锁骨里撑了块钢板,便不再接那些粘信封的活儿。
苦中也有作乐的时光,街道有时会放露天电影,青石巷的街坊们几乎都会涌出来看。端着椅子摇着蒲扇,小孩子尖叫着追来追去,只有宁远还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做题。我也考上了效实中学,但却始终没学会他那么用功的念书劲头,非要考到第一才肯罢休。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
高考后,我跟宁远都考到了北京。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学校念的却不是同一所,刚开始还常约着一起吃个麻辣烫,到后来就渐渐疏远了。再后来,联系也越发少了,几年后真正再约着见面,居然是一起去看青石巷32号。
是的,青石巷,乃至整个月湖西区,都要拆迁了。
这不过是宁波大规模拆迁中的一部分。在不远的鄞州区,整个村整个村地被改造,被推平,拔地而起的是林立的高楼。在北仑区,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征用,盖起了成片的厂房和公司。江北在拆,镇海也在拆,新楼盘日新月异,海曙也未能例外。作为浙江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宁波在努力证明着什么。
隔着这么多年的距离再回去青石巷,仿佛屋通人性,知道人要走了,房子也显出暮气沉沉的沮丧来。缸里的水发绿,门前的葡萄藤疯长,结出的葡萄却是又酸又小。自从那年抛轮厂停工后,祠堂里冷冷清清,只有老猫偶尔在门槛边蹲着晒太阳。
在街上摆豆腐摊的老陈一家搬到了江东去住,他们在那里买了新房,据说宁波的行政中心要从海曙转移到江东了。后门那家的林阿婆去世了,再也看不到她颤颤巍巍为大家收衣服的身影,站在院子里,只觉得俯仰之间,皆为陈迹。
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崭新。
青石巷一带,有不少依着月湖而蔓延连续的院落,有杨容林的青房阁,藏书数万册,有当代核科学家戴传曾的寓所,名日访庐,此名为他的祖父、清光绪年间举人戴季石所书写。不远的青石巷中,有清代鸿儒黄宗羲曾讲过学的张家祠堂。当年明代兵部尚书范钦建造的天一阁,把宁波的士子都聚拢其中,这些明清留下的大片老宅,若是一拆了之,着实可惜。
宁远家的邻居,在电视台工作的老袁头为此没少奔波,又是联系媒体又是发微博,呼吁留住老城精神,不要沉沦在千城一面的CBD高楼里。那晚住在月湖,听到不远的机器轰鸣,深感在经济发展面前,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何等卑微渺小。
月湖西区已经拆了一部分,第二天跟宁远穿行在混乱的工地间,杨老太太推着自行车追上了我们。她退休前曾是医院院长。自从拆迁开始后,她花了很大力气来研究相关法律,和政府打起了官司。“我不是为了多争取赔偿,我是真心可惜,这么气派的老房子,你看那些雕花,多么漂亮,应该要留下来的。”她说。
忠叔也觉得可惜,但他更担心儿子过于投入对拆迁的抗争中去。“房子是老了,看起来也破,换个地方住住也好。反对的事,你让别人去做就好,我们安分守己过过日子,不要去惹是非了。”他这样劝道。
青石巷一带的老街坊们最终选了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聚集在一起,在废墟上开了一次音乐会。当《凯旋进行曲》的小号声缓缓响起的时候,我的眼睛隐约有泪意。
宁波是一座温和的城市,似乎习惯了逆来顺受。因为温和,因而也少了几分血性,当各地强拆血案不断,人们不惜以血肉之躯来保卫自己的故园时,宁波极少听说这样的暴力冲突,即便是抗议,也是用音乐会这样美好而伤感的形式来诉说自己的情怀。
这让我想起泰坦尼克上那些拉着小提琴坦然面对大海倾来的乐手们,他们是谦逊的,节制的,甚至是胆怯的,他们更愿意过安安稳稳不起波澜的小日子,诚然他们也是如此怀念老墙门,怀念邻里之间相互照应的日子,不想因为拆迁而越住越远,住到那些房价相对便宜许多的郊区去。我怀念那些曾走在青石巷树荫和花香里的时光。
我对这样的息事宁人是有所失望的,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出得门来就已经是历史性突破
在今年10月22日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这个城市的人们会以这样决绝不妥协的姿态走上街头,抗议PX项目,包括忠叔。
即便是在反PX游行的前一天晚上,很多人,包括我,还是不相信第二天的广场会真的聚集起人群,虽然微博上早已传得轰轰烈烈。
就在不久前,钓鱼岛事件轰轰烈烈,很多城市传来打砸日本车辆的消息,在宁波,你大可以放心地开日本车出门,没有人来关注你开的到底是国产车还是日系车,人们更相信,买车的头顶选择是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和安全性,而不是关注如何才能表现得更爱国。爱国,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连小学思想品德课上都是这样教育的。
“不要去,你远远地看着就好了。”忠叔知道宁远要去广场,很不放心。
“镇海那一带的空气怎么样,你也知道的。”我忍不住说,“场场都酸雨,海水都是劣四类,实在叫人坐不住啊!”
忠叔叹了口气,不说了。小川的儿子有哮喘病,是过敏性体质,做了好几次雾化。医生说,空气太差了,现在很多小孩都有这毛病。
宁远妈倒是很支持的,她说,家里天天打扫,还是天天一层灰,是太不像话了,她要跟我们一起去。反正大家就站在那里呼吁呼吁,又不会做过分的事。
“那么明天,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后来,一向老实本分,甚至有些窝囊的忠叔说。
第二天是周末,市政府门前聚集了不少人。有一个年轻人扔了个矿泉水瓶子过去,马上有人喊道:“不许扔瓶子!”“要理性表达!”更多人是持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在门前默默地等待着,或是掏出手机来发个微博。他们并不激动。
在广场上的聚会也同样是温和的。有人戴着抗议Px的口罩,在广场上闲走着,有人举着抗议的牌子,当队伍里有人唱起了国歌时,不断有人加入到合唱队伍中去,声音越来越响亮,就像一潮海水涌来,拍打着堤坝,又很快退下,歌唱完了,大家继续等待。
我们在广场上碰到了几个青石巷的邻居,有日子没见了,自从拆迁后,大家各居城东城西,难得能遇到,老陈还送了我一个口罩,说也是别人送给他的。
夜色开始降下来了,宁远说先回去吃饭吧。我想,明天就是周一了,大部分人都会回去上班了吧?如果就这样散了,那这次抗议恐怕就是宁波人的绝唱了。纵观这上百年,有谁见过今天这样的阵势?小富即安的城市,能忍也就忍了,出得门来就已经是历史性突破。
没想到结果来得很快,回去吃晚饭的路上,市政府发布消息,宣布永久取消PX项目。忠叔打电话叫我们快回家吃饭,他新做了些年糕来,味道很不错。
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不少打着双跳灯的爱心车队,这些是免费提供接送的志愿者。这是今年第二次看到双跳灯闪烁,上一次是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强台风中。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一直这样来理解宁波人的温和,甚至是妥协。只是没想到在这次PX抗议上,这种温和显得如此有力。PX工程所在地是镇海,那天,镇海很多人步行三个小时,从几十里外走到了市中心。
宁波人也有坚硬的一面,我仿佛第一次发现这温和后的力量。
第二天上班时,街道已平静如息,仿佛这场轰轰烈烈的活动从未出现,消散得这样彻底,电瓶车公交车自行车连成洪流,快速地在眼前流过,就如同无数个曾经的早展。
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试图寻找这个城市历史中坚硬的一面。除了鄞江桥人民的反清政府抗租运动,还有一则是在清道光年间,宁波人浴血拼杀,抵抗外敌侵略,保卫家园,取得了镇海保卫战的胜利,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获得全胜的一次重要战役。只不过,那也是接近200年前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