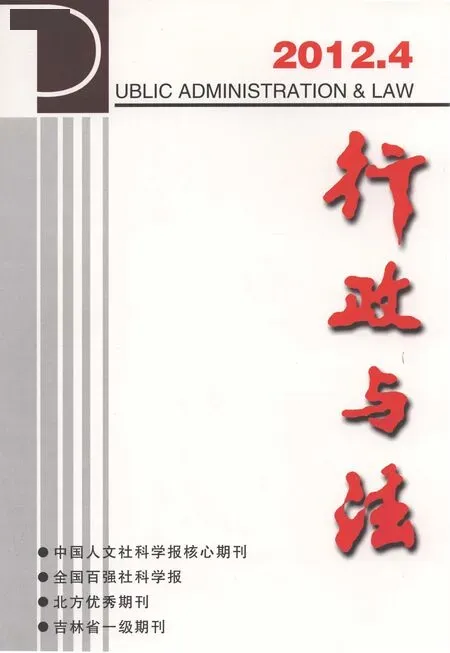城管执法的权威与困惑
2012-12-23王洪芳
□ 王洪芳,李 铮
(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城管执法的权威与困惑
□ 王洪芳,李 铮
(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当前,我国城管执法问题凸显。加强并完善城管立法,合理配置城管执法的职责权限,回归城管机构的行政机关性质,明确城管执法人员的公务员身份,既是合理有效回避城管执法现实尴尬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积极、正确应对城管执法难题的当务之急。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城管执法;困惑;权威
现代行政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正在进行着 “从摇篮到坟墓”式的全方位管理,政府行政的理念已经摒弃了“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之传统,正沿着“能提供更多服务的政府才是更好的政府”之时代方向变迁,百姓不仅要求政府把社会管理好,还期盼政府能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谋求更多的福祉。尽管“小政府、大市场”已然确立了在一个国家中“官、民、市场”各有分工、融洽相处、和谐发展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和作用力度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扩张和深化之势,学界做出的“我国目前阶段的行政权处于‘积极行政’的状态”之结论并不为过,[1](p11)而城管执法正是这种“积极行政”的结果。
一、城管执法的法律和现实意义
(一)城管执法是我国法律确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必然结果
一直以来,在行政权的积极作用过程中,我国行政管理存在“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执法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这些问题在城市管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鉴于“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之现实揶揄,1996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16条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我国城管执法的产生正是得益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确立。
所谓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指将若干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集中起来,交由一个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有关行政机关不得再行使原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它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降低行政执法成本,建立“精简、统一、效能”的行政管理体制,解决行政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多头执法、职权交叉、重复执法、行政执法机构膨胀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贯彻实施该制度,1996年4月,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中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认真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据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在北京等城市进行试点,随后,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和《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相关要求。在此过程中,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作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可以说,“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确立,催生了城管的诞生与发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即是城管部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
(二)城管执法是我国城市管理的现实需要
城管执法作为我国政府应对和解决现代城市管理问题的一系列行政管理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其作用的产生主要源自政府对以“健康卫生、整洁有序”等目标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管理秩序的积极追求,以及市民对以“安全安定、清静宜人”等标准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管理秩序的迫切需求;其作用的范围主要有针对城市管理中的有关市容环境、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环境保护、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等行政管理事务;其作用的手段主要是采取柔性的劝导说服、批评教育以及刚性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其作用的法律依据主要在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其作用的目的是重在规范和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效率和水平,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必须肯定,城管执法的存在,不仅缓解了无证经营、以街为市、乱搭乱建、占道停车等城市顽疾,还相对有效地解决了行政机关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加大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提高政府行政服务水平、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满足百姓在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多元需求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城管执法不能回避的现实尴尬
然而,城市管理作为一项需要对城市的一切活动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和市政等全方位管理的复杂系统工程,其对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的要求随着我国城市发展步伐的日趋加快而与日俱增。
城管执法是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而城管则是现代城市管理的生力军,一方面,文明、整洁、有序的城市秩序离不开城管的执法管理与服务,但是城管所面临的问题大多是城市管理中的复杂、尖锐、棘手的问题,面对的执法对象多为下岗工人、无业游民等生活困难、缺乏保障的弱势人群,被管理者的多元利益诉求常与城市执法所追求的一元目标以及具体要求不相协调甚至矛盾或背离,这些客观困难的存在使得城管执法常常处于因各地政府所要追求的城市管理目标不能无缝对接市情民生的现实需求而产生堆积起来的矛盾交织中,城管执法不被理解、接受,甚而遭遇敌视乃至抗拒,由此,“暴力抗法”现象在很多地方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城管从上个世纪末产生至今,国家一直没有制定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其执法活动进行规范,城管长期性地“借法执法”,执法活动经常性地面临“师出无名”、“底气不足”之质疑。同时,法律规范的缺失必然带来法律监管的缺位,城管执法频频暴露出执法违法、执法不当等问题,“暴力执法”也成为部分行政相对人心目中城管执法的代名词,我国各地城管执法面临着一系列不能回避的现实尴尬。
(一)各地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不尽统一
城管是在日趋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根据《行政处罚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法律规定,应地方政府解决日渐纷繁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而成立的一种执法机构。纵观我国当前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多以地方政府规章、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为主,其在“法律位阶”上的依据除了《行政处罚法》第16条针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所做的总括性规定外,并无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律规范,即使地方性法规也为数不多,且呈现出执法依据各自为阵和法律位阶的低层次性特点。城管执法依据的不完善,无疑会让城管执法权力行使得不到有效的规范和控制,而对于城管执法权威的树立也是有所削弱甚至损伤的。
(二)各地对城管执法职权范围的划定不尽相同
城管执法管理的事务具有典型的城市区域特征,由于各地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各自为阵,故而各地对城管执法职权范围的划定也不尽相同,不像其他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具有全国统一性的特点。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400多个城市开展了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其中,多数城市根据国务院国发[2002]1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决定》的规定,重点在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环境保护、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管理以及其他适合综合管理的领域,合并组建综合执法机构,在执法的职权范围上实行“7+1”模式。①依据国发[2002]1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决定》的规定,我国城管执法的职权范围由七类确定的职能和一个兜底条款构成,即所谓的“7+1”模式。随着城管执法在全国范围的不断推广,有的地方在城管执法职权范围上则实行“4+1”模式或者“10+1”模式。
(三)各地对城管执法机构的称谓、性质和执法人员身份的规定不尽一致
城管是城市管理中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构,从对《行政处罚法》第16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的规定理解来看,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构应为行政机关,国发[2002]17号文件进一步明确:“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应作为本级政府直接领导的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独立履行规定的职权,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城管作为各地政府应对城市管理需要而设立的执法机构,理应作为本级政府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一个行政机关而设立存在,但是,各地城管执法实践并非完全如此。
首先,在称谓上,城管执法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地方叫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例如北京;有的叫城管执法局(大队),例如上海;有的叫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例如广州;有的叫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例如成都;还有一种可能出现的最新称谓叫城市行政执法部门,例如四川。②《四川省城市行政执法相对集中处罚权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第3条:“城市行政执法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设立的行使城市行政执法相对集中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依法独立履行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在城管执法机构的性质上,目前主要表现为三种:一是作为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的行政机关,二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三是事业单位。未能形成与其职能履行相适应的、统一规范的执法机构。城管执法机构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其执法人员身份的差异。在城管执法人员的身份确定上,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的则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再次,城管在省级以上政府中并不像国内其他行政机关一样拥有对口的行业主管部门,这在我国法定和惯行的“国——省——市——县(区)”四级政府行业管理体制中实属罕见。与此同时,城管也就自然而然地回避了来自于上级政府的必要约束和监督。这种状况极易纵容城管因随性膨胀成为城市管理中的权力野马而难以驯服。
三、城管执法权威的树立
在我国当前城市管理中,城管执法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各地政府对城管执法存有的借助于城管执法之手,以达到管理城市、服务于民的理想和预期。由此,每一个城管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都应当成为城管执法权的严格实施者和忠诚捍卫者,不能对手中的权力有所图谋或者恣意妄为,而每一个生活、学习、工作在城市中的人都不仅有权成为城市管理成果的受益者,而且也有义务成为城市管理成果的自觉维护者和城市管理行为规范的模范遵守者,“城管”不应成为“暴力执法”的代名词。
笔者认为,把握和顺应我国大力提倡和践行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脉搏,完善并健全城管立法,合理配置城管执法的职责权限,回归城管执法机构的行政机关性质,明确城管执法人员的公务员身份,既是合理有效回避城管执法现实尴尬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积极、正确地应对城管执法难题的当务之急。
(一)厘清城管立法思路,确保城管执法有法可依
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和重要环节,其基本要求在于“权自法出、法律优先、法律保留、行为有据、程序规制和司法审查”,[3](p36-38)其中“行为有据”不仅要求行政行为应有事实根据,而且要有法律依据,旨在强调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做到“有法可依”。
当前,我国各地城管执法呈现出“依据不足、分散立法”的状况,故而加强城管立法,提高城管执法依据的位阶,完善城管执法程序就成为破解城管执法困境的首要举措。
在完善城管立法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认为,突破当前城管执法分散立法的局限,统一全国城管立法实乃现实所需,且势在必行,但同时大家也客观地指出,目前统一城管立法的时机尚不成熟。马怀德教授认为,“虽然目前由于涉及行政体制改革等问题,城管立法还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没有法律依据,城管部门终究难以更好地完成工作。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待条件趋于成熟后,还是应该及早出台全国统一的城管法。”[4]
笔者认为,在统一城管立法短期内难以实现,而城管执法又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城市管理现实所需之下,着眼于未来全国性城管立法的统一规范,立足于各地城管立法的科学完善的确不失为当前的务实之举。
(二)通过城管立法,科学设定和细化城管行政处罚权
环顾我国各地城管的执法范围,既有“7+1”模式,也有“4+1”模式,还有“10+1”模式,其中在“7+1”模式中,主要涉及城市规划管理、市容环卫管理、市政公用管理、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而在“10+1”模式中,还增加了对国土、水利渔业和烟花爆竹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5]不同模式的选择,一方面固然是各地城管执法实际的现实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各地城管执法在职责权限设定方面的困惑和迷茫。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确立是城管执法的基本依据,因而行政处罚自然成为城管执法的主要方式,但根据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 “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城管执法既不能单纯地以罚代管,也不是简单地只罚不教、重罚轻教,而应通过处罚的方式达到预防、纠正违法行为,教育行为人不再违法和引导社会公众自觉守法的目的。要充分实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仅仅赋予城管概括笼统的相对集中处罚权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全国性的城管统一立法和地方分散立法的途径,合理配置城管执法权力,对可以交由城管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的范围进行科学的设定和细化。
(三)以《行政强制法》为依据,合理规范和控制城管执法所需的行政强制权
“城管执法是将以行政处罚权为中心的执法权进行集中,减少和避免行政执法权之间的交叉重复。”[6]在城管执法中,行政处罚权是城管执法权力的核心,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行政处罚作为针对行政违法实施行政管理的一种结论性处理手段,并不是每一桩、每一件、每一次城管执法的必经环节和必然选择,因而立法单单赋予城管行政处罚权还远不能适应城市管理的需要以及对城市管理问题的解决,在科学设定、细化城管行政处罚权的基础上,还需赋予城管执法实效得以有效发挥的其他管理权限,例如合理规范和控制行政强制权。
在行政强制的适用过程中,乱用、滥用行政强制和行政强制手段不足一度成为长期困扰我国行政强制的两大问题。就城管可采用的行政强制措施而言,除了暂扣权和强制拆除权以外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因而无法有效满足城管执法的实际需要,而在城管是否拥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问题上,城管自身虽然没有获得法律授予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然而,在整治城市违章建设、乱搭乱建、城市房屋拆迁等城管事务中经常性地扮演着强制执行机关的角色。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赋予法院强制执行权的过程中,除了人身权利之外,可以赋予城管必要的财产方面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对当事人的财产进行查封和暂扣等。
2011年7月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们盼望已久的 《行政强制法》,该法以规范行政强制避免公权力滥用为立法宗旨。随着2012年1月1日起该法的正式施行,城管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和运用将会于法有据,更趋科学规范,而人们对城管执法素来保持的 “行政强制权会否被城管乱用、滥用”的警惕和担忧也将不再成为立法赋予城管执法所必需的行政强制权的掣肘。
(四)通过立法,回归城管执法机构的行政机关性质,明确城管执法人员的公务员身份
如前文所述,在各地城管制度构建和执法实践中,城管表现为一个在此时彼地性质皆不尽相同的 “不定性”机构,其中的尴尬与无奈令人深思。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作为行政处罚权的一种特殊运用方式,是通过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变行政处罚各自为阵、分散行使的传统执法模式,将那些可以集中起来的行政处罚权交由一个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这种权力分配和运行模式的改革,其实并没有改变城管处罚权力的行政处罚权性质,因而在城管执法机构的性质确定上应当还其国家机关的本来面目,明确其行政机关性质和执法人员的公务员身份。笔者认为,立法对城管是国家行政机关性质的明确定位,既不是行政机构“简而不减”的恶性循环,也不是对城管执法权力的扩权冲动,而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一行政管理模式的固有要求。这种名符其实的权力回归和身份定位对于改善和推动城管执法实效是必要的。
首先,能让行政相对人了解城管执法活动的公务性质,服从、配合城管执法,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其次,通过城管自身的“严格、规范、文明、和谐执法”,让行政相对人对其执法活动萌发内心的理解和认同,进而转化为行动上的自觉配合和支持。
再次,能够帮助城管执法人员树立正确的权责意识,依法合理行使法律赋予的执法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增强城管执法人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职务保障感,从而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城管执法工作,提高执法效率。
“权威就是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城管执法权威的树立除了依托于法律的保障外,在现实管理中,国家和各地政府必须厘清城市管理发展思路,科学规划,民主决策,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积极回应、合理平衡城管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力争做到求同存异,恢复和重建政府与社会、城管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本应具有的管理与服从、服务与监督关系。当然,城管也应对自身执法进行因时、因地制宜的经验积累、教训总结和方式方法改革,惟有通过城管自身的积极有效作为,城管执法才能获得行政相对人的内心认同和自觉支持,而唯有建立在科学、民主、法治基础上的权威才能成为令行政相对人心悦诚服的真正权威。
[1]胡锦光.行政法专题研究(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韦红霞.城管执法存在问题及对策探析[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0,(03):63.
[3]王鹰,金光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
[4]城管屡遭暴力抗法 执法改革试点12年仍难全国立法[EB/OL].http://www.chinanews.com,2009-04-18.
[5]四川省城市行政执法相对集中处罚权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八条[Z].
[6]杨小军.城管执法机构性质与城管执法体制[J].行政管理改革,2010,(04):26.
(责任编辑:牟春野)
Confusion and Authority of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Law Enforcement
Wang Hongfang,Li Zheng
Current issues for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law enforcement are get ting tough in China.The correct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can avoid the embarrassment of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law enforcement,and the measures are also the priority to positively or correctly tackle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problems.The measures are as follows:First,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urban management legislation.Second,rationally allocating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obligation and right's limits.Third,resuming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ion bureau's nature as an administrative organ,making it sure that the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 are civil servants.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law enforcement;confusion;authority
D922.112
A
1007-8207(2012)04-0024-04
2011-12-23
王洪芳(1975—),女,苗族,贵州遵义人,四川警察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李铮(1969—),女,四川绵阳人,四川警察学院副教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
本文系2010年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城管执法的权威与困惑”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Z10A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