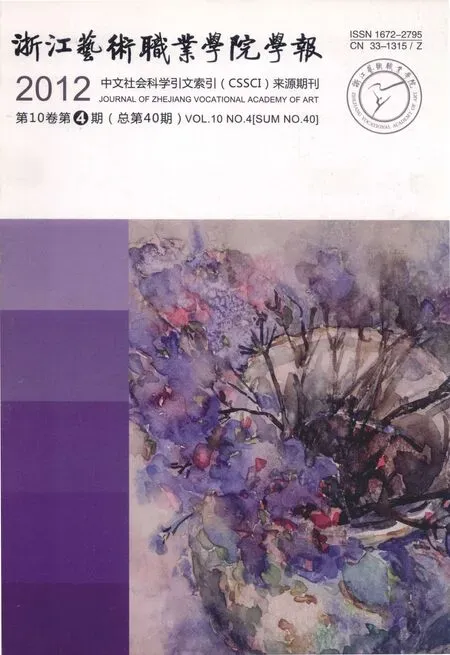非遗保护的困惑——以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乐舞为例
2012-12-19孟凡玉
孟凡玉
MENG Fan-yu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正面临着种种困惑。随着信息世界化、经济全球化,地球正变得越来越“小”,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我们正日益成为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的村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信息化的影响无孔不入。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安徽贵池荡里姚——一个地处山区的小村庄,虽然地处深山,也不能置身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之外。公路交通逐步变得便利,村村通电,电话成了寻常家庭的常见之物,手机也很普遍,个别家庭还有了电脑。为了进出方便,摩托车的拥有率比普通平原地区要高出许多。电视机依靠村民自己装配的信号接收“锅”,能看到的节目比城里人都多。外界信息实时传入深山,过去因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信息传递较慢、与外界交流较少而保留古老文化的条件正在逐步消失。
经济大潮的冲击显而易见,人们经济观念的改变,价值观的悄然变化,直接影响到其参与傩活动的态度,席卷大地的打工潮更是让许多村落的傩活动几近崩溃。当地每个村子都有一批人常年外出打工。按照传统的习俗,演出到正月十六才结束,这时候再出去就找不到好的工作岗位了,有固定工作岗位的人放假也不可能延续到这个时候。刘氏家族迫于无奈,前几年经过九村协商,把开演日期提前到正月初二,这样还是有许多人在轮到本村演出之前外出打工。笔者听到村里老人说起来,傩活动维持最难的就是外出打工的太多,人手短缺,很多会唱的、唱得好的人外出,使村里的傩活动近于瘫痪。还有人告诉我,刘街村有一位唱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出外打工以后,即使春节回家,也不再参加傩戏演出,原因也没有人知道,估计要么是接受了新的思想,要么是怕耽误打工外出,或者还有其他难以猜想的原因。我在刘街遇到几位对傩戏前景看法极为悲观的人,他们预言刘街的傩戏不出三年就会消亡。说这话的人有两位是温文尔雅、很有修养的大学生,有一位是当地学校的老师,说话时忧心忡忡,十分痛惜。甚至,代表刘街傩戏到山西临汾、江西南昌演出过的刘街傩戏元老刘臣余老先生在言谈中也流露出许多无奈,表露了厌倦的情绪,说“不想搞了”。看来他也是为刘街傩戏操心,太累了。
因为照顾外出打工人员,提前演出的村子很多,太和章2006年提前到正月初五,南边姚也提前到初五开始。缟溪曹因为日期提前演出中放铳出了伤人事故,而不敢提前。其他一些坚持按传统日期演出的村子也因为人员外出而捉襟见肘、无法应付。
荡里姚村因为本村经济状况较好,附近又有些矿山、企业,也有人在附近打工,受到外出打工的影响稍微小一些,所以他们还是按照传统的日期演出,并且是当地为数不多的连演两个晚上的村子之一。但演出时间已经大大缩减,演出的态度、技术水准也都是大受冲击。
笔者在荡里姚考察的几年中,每年都会遇到村里发生在乐舞、戏曲演出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虽然具体情况表现不一,其实质都是现代化进程在傩文化中的折射与反映。荡里姚以及贵池各村傩活动所面临的情况是全国各地传统文化处境的缩影,既有其特殊性,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现择取典型事例简要分析如下,以展现荡里姚傩仪式乐舞以及全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状况。
一、劳务风波
2005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五,这天是傩仪式乐舞活动最热闹的日子,白天有朝庙活动,晚上有丰富的演出活动。
晚饭后,我来到祠堂准备拍摄,还没有开始,就被客气地“请”了出来。原因是舞台上一位老者 (约60岁)在向村支书姚鸿斌讲着什么,发生了争执,不便让外人知道。请我出来的是管事人之一姚克继,他说:“我们自家有点事,我们先处理一下,等会去喊您。”尽管我很想在现场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也不能不尊重“局内人”要求回避的意愿,于是只好暂时回避。
后来了解到,原来,2004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四套拍摄“华夏纪行”节目,在荡里姚拍了傩戏。荡里姚专门组织了一场表演,电视台给了3000块钱的报酬。由于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额外演出,电视台又给了这么多的报酬,在劳务报酬分配上产生了纠纷。今天,矛盾终于爆发了。发生争执的是一位张姓村民,他对其中的一笔打扫祠堂的小工开支不满。这笔开支是940元,一个小工20元,折合47个工时。这位村民认为自己的儿子参加了演出反而没有报酬,吃了亏,打扫祠堂的人占了便宜,因而大为不满,于是发生争吵。
至于吵架的细节,当时人们守口如瓶,我也不便刨根问底。时间久了,隐讳就少了些,2006年我再来考察时比较详细地了解到一些情况,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村民的评价等。
这一吵,至少耽误了50分钟的演出时间,最后,当晚的演出内容被简化,精简掉的内容是傩戏《孟姜女》,本来每年正月十五要演《孟姜女》,过去演全本,近年来已经简化成只演选场,这天干脆全部被精简。不过,迎神、仪式乐舞、送神是不能减的,照样演出了。
这一场吵闹,是由于有了额外的经济报酬引起的,中央电视台的拍摄活动无意中成了破坏本年活动的“罪魁祸首”。
二、罢演风波
2006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七,这是荡里姚每年傩活动正式开始的日子。吴国胜雄心勃勃,打算当晚演出傩戏《刘文龙》全本。因为是用同样的曲调演唱,熟悉一下近几年没有唱过的场次的唱词即可,再说,舞台上忘词还可以提词、帮唱,也可以解决,不是太难。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活动中扮演《五星会》中的喜星、《新年斋》中的大和尚、《刘文龙》中的刘父等重要角色的姚建秋在开演前不见了,到处都找不着。他下午还参加了排练,晚上正式活动却罢演了。无奈之下,只好找人临时顶替,让姚家伟演喜星、章端桂演大和尚、姚克靖演刘父。姚家伟过去没有演过喜星,戴上面具出场表演、站位还行,就是《五星会》是高腔演唱,喜星有一段唱,他唱不出来。好在这里的傩戏普遍可以帮唱,他在别人的帮助下演了下来。章端桂是太和章村的骨干,在本村里每年演《新年斋》的大和尚,今年被吴国胜邀请到荡里姚打算合作演出傩戏《刘文龙》,没想到要演大和尚,主持做斋。好在章端桂舞台经验丰富,尽管唱词、曲调、表演方式都不一样,他用荡里姚的唱词 (可以看唱本),用自己的唱腔也把一个持续时间近50分钟的《新年斋》仪式完成了。姚克靖过去常演刘父,很熟悉唱词、曲调,但他年事已高,需要在人的搀扶下登台,颤颤巍巍的令人担心。结果,《刘文龙》只演了二、三场,就草草结束了。演出全本《刘文龙》的计划就此彻底泡汤。
这件事的起因说起来话长,和一次国际会议的交流活动有关。2005年6月,江西省政府在南昌市举行“中国江西国际傩文化艺术周”,大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傩活动代表队参加大会交流活动,笔者亲临现场,看到还有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类似于中国傩活动的代表队参加展演。由于安徽贵池傩影响颇大,当然也在被邀请之列。问题就出在这次赴南昌的交流演出上。贵池市文化局在刘街乡选了11个人,组成贵池傩代表队,在大会上参加交流演出。在这11个人当中,包括太和章村4人、荡里姚村4人、刘街村2人、缟溪曹村1人。荡里姚的4人分别是吴国胜、姚家伟、姚惠文、姚新祥,参加活动组织、喊断与演出等。姚建秋认为自己平时参加的活动最多,也有人提议他去,结果没有去成,非常恼火,不仅觉得没有面子,也觉得失去了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还觉得他们都拿到了一些演出报酬,又到外面游览了一番,这些全没有自己的份,总之,是吃了大亏。从那时起,他的心气就一直不顺,这次事件,就是他郁闷心情的总爆发,他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显示自己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果然,他的罢演使得演出活动受到严重挫折,只好草草收场。
2006年8月,时隔半年,我再次来到荡里姚,姚建秋向我解释罢演的原因,他说一是因为南昌开会没有去成,肚里有气,但他强调那不是因为“有钞票”,而是因为没有受到重视,他说,“平时演出缺谁的角色都让扮演,但是外出演出却没有份”;二是因为春节请人来合作,他认为行不通,“人家的东西是好,但你没有本事学来也是白搭,人家走了还是带走,没有用”。这又涉及到2006年春节演出期间的另外一件事,都是前后互相关联的。
不管以后情况如何,是否能够和好如初,这一次罢演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这一次,主要是国际会议“惹的祸”。
三、傩戏改革风波
2006年春节,吴国胜邀请太和章村章端桂、章常荣、章光辉、章艮保来到荡里姚村合作演出,请他们扮演剧中角色,“规范”高腔唱腔,指导舞台动作。
这次改革的动因,我曾经问过吴国胜。他说,自从上次准备去南昌演出的集训期间,他听了太和章村几位艺人的高腔演唱后,认为他们唱得好,本村的演唱、动作都需要改进,再加上到南昌看了很多的演出,更觉得不改不行,所以决定邀请他们来改造荡里姚的演出。
这件事在荡里姚傩戏成员中引起了支持和反对两种不同的态度反应。村民有认为他们几位唱得好听、表演得好的,也有认为不如本村的傩腔好听的人。
2006年元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因为今年没有年三十,今天就是除夕。我来到荡里姚,住在吴国胜家里,和他们一起过年,受到主人和村民的热情招待。晚上的年夜饭结束之后,吴国胜、姚家伟、姚建秋三个人在吴国胜家里聊天,在谈及今年准备请太和章的高腔艺人来帮助荡里姚傩戏改革时,发生了一场争论。在场人:姚建秋 (简称“秋”)、姚家伟 (简称“伟”)、吴国胜 (简称“吴”)、笔者。谈话进程如下:

讨论内容备 注笔者:你刚才唱的是《五星会》的唱腔吗? 因为姚建秋刚刚唱了一段高腔,笔者故有此问。秋:我唱得不对,那你唱一个我听听嘛!这是与姚家伟的争辩。因为姚家伟刚才说姚建秋唱得不准,所以姚建秋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开始与姚家伟争辩。我决定静听,不再插话。伟:我唱你听?我唱不到①,反正我听着不是那个腔。姚家伟受父亲姚克水亲传,他的判断应是有依据的。不过高腔的确难唱,家伟不会唱。秋:总得有点像吧?一个是诗词,一个是节奏,一个是音,哪个是高音,哪个是低音……姚建秋曾经说过每个人都会有些不一样,我估计他认为唱得不一样似乎不是什么十分严重的问题。伟:你根据什么知道哪个是高音,哪个是低音?你那个戏本子打了什么记号?嗓音提高,情绪渐趋激烈。因为太和章的剧本《和番记》上有提示演唱的曲谱符号,当地称“圈点”,在去南昌演出的合作中姚家伟多次听太和章艺人、文化局人员说起,故有此问。笔者也看到过太和章村的“圈点”谱。秋:记号没得②。 声调不高,明显底气不足。吴:人家是有记号的。 插言,支持姚家伟观点。伟:冇记号你咋知道高音、低音?人家本子上那个符号比那个工尺谱还要早些个,他们那个本子上打个点、打个点的,那是原始的记载,从老本子上下来的,发展到工尺谱,工尺谱发展到这个,是正规的。语气肯定,有理有据。显然是受到了文化交流的巨大影响,说话中讲了不少大道理,流露出对“有谱”的崇拜心理。但是,没有谱就不知道音的高低的说法值得商榷。秋:傩戏腔,我…… 几近崩溃,快招架不住了。面对谱子的“权威”,他也没有可以辩驳的说词。伟:属于高腔类的,他们有五十多个牌子,要你讲,你一个也讲不到,就像《新水令》,他有四个《新水令》调,我家老头子是靠嘴里吐出来的,那个并不是绝对准确,遇到什么,这个音、那个音,有漏掉的。继续阐述,论据确凿,难以辩驳。谈话中提及的“靠嘴里吐出来的”指的是荡里姚恢复傩戏时,唱腔都是姚家伟的父亲姚克水老人口传的,村民称“是从肚子里吐出来的”,包括剧本《刘文龙》也是如此。我一开始听不懂这话,很长时间以后才听懂了这个词汇。秋:那要补。 已不再争论,进入商讨。伟:补也没得谱。 姚家伟把乐谱看得很重。秋:就是五六工尺上六五…… 姚建秋只是知道,并不会唱工尺谱。
①“唱不到”,当地方言,意为不会唱、唱不出来。
②“没得”,当地方言,意为没有。
①之后谈话进入心平气和的状态,是另外的话题,与此主题无关,略。
这场自发的争论,无疑是他们心声的自然流露。他们都喝了一点酒,情绪较为激动,在我面前也没有任何掩饰,真实可爱。另外,从他们如此认真的争论可以看出,不管持何种观点,他们都是热爱傩文化的,有着极强的责任心。
这场争论姚建秋表面被说服,不再反对改革,也参加了正月初七白天与太和章几位艺人的合作排练。但是,晚上演出还是因为多种原因而罢演,使2006年初七的演出匆忙收场。
与姚建秋一样,姚有志也是一个改革的反对派。他对我说他的理由是:“傩戏是古老文化,是有民族特色的,各家有各家的特色,人家的再好,是人家的。”他的反对态度至今未变。但他却没有因此罢演,照样参加了所有活动的打鼓,似乎打鼓是他的职责,不能放弃。
四、旅游开发的潜在威胁
2006年7月28日,在与吴国胜的电话中,他告诉我他们已开始开发傩的旅游项目,现在一些旅游团来,他们会表演一两个傩舞,如舞伞、打赤鸟等,招待游客。我问及报酬时,他说暂不收费,属于招待性质,由村里负责发给表演人员工资,将来会考虑适当收费。
我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纳入旅游项目以后,活动的积极性会受到刺激,可能会是一个促进,也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担忧的是表面的繁荣有可能带来深度的破坏,也有使傩活动变质、走形的可能。但我不能对村民自己的选择作任何干预,没有在电话里发表任何“该怎么样”或“不该怎么样”的“指导”意见。我认为,无论将来荡里姚傩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事情,历史本来就是如此,它不会因个人的好恶而改变自身的发展轨迹。
我的担忧也是有根据的,与荡里姚近在咫尺的梅街镇的傩活动因为发工资而后在没有经费时陷入瘫痪,今已停止活动;2005年6月,我在江西的考察,遇到江西乐安县文化馆的卢学津先生,他是一位每天接待游客的傩队的艺术指导。在我的追问下,他承认他们那里因为每天表演,已变得信仰淡薄,表演也变得有点“油”了。荡里姚村傩活动的危机我已亲身经历几次,比如2005年春节因争吵而推迟演出并取消了傩戏《孟姜女》演出的事,2006年春节的罢演风波,都与经济有些瓜葛。这一次,他们脆弱的傩活动还能经得起旅游开发的强烈刺激吗?
2006年8月18—22日五天里,我再次来到荡里姚。半年来,村落里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村口菜地被改造成了停车场,接待旅游车辆;村委会办公室卖给了旅游公司,成了旅游公司的办公楼;村西白洋河小桥被重修抬高,下设拦水坝,成了“漂流九华”的起点;桥的上游一侧挖出了一个水塘,供游人划船;村中通往白洋河的小路用水泥一直铺到河边;河边建起了供游客暂歇的茅屋,还有一个在建的大房子;村中有十五户人家挂牌经营“农家乐”,为游客提供就餐服务;村里有一些人成了旅游公司的雇员,傩戏骨干姚家伟是旅游公司办公室主任,姚有财是清洁工,还有人负责放排,等等;傩戏会打起了“姚街傩戏欢迎您,以傩会友以戏怡人”的横幅,欢迎观摩傩戏。
这些变化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在传统的节奏里,几十年也未必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现在,因为还没有和旅游公司在演出报酬上达成协议,一般的游客来还没有演傩戏招待。但是,有些知道荡里姚有傩戏的旅游团会额外要求演出,旅游公司通过村委会与傩戏会洽谈,每一场给些报酬,请他们演出。
2006年8月20日,我在荡里姚看了两场招待游客的演出。旅游公司答应每场给200元报酬,吴国胜要求再加30元香火钱用于敬菩萨,这样,每一场演出旅游公司付给傩戏会大约230元报酬。
这两场演出都是只演了舞伞、打赤鸟、舞回子几个乐舞,连乐队一起共有十几个人参与。如何分配酬劳,暂时还没有形成制度。
由于目前接待的旅游团体还不多,演出场次较少,开演之前的烧香敬神还比较虔诚、认真。但不知道如果每天都演出好几场,那会变成一种什么情况,会不会也像江西乐安县的傩活动那样,接待旅游的时间一长,信仰淡化,变得油腔滑调起来。
8月22日,就将来姚街傩的未来发展问题,我专门采访了傩戏会会长吴国胜。采访时间:2006年8月22日上午。地点:吴国胜家。采访人:孟凡玉。受访人:吴国胜。
孟:您是姚街傩戏会会长,身份比较特殊,您对姚街傩戏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和计划?
吴:第一步先把舞伞调整一下,培养50岁左右不出去打工的人。第二个呢,舞伞培养一个最小的小鬼,姚新祥的侄子,名叫冬冬 (音)。现在舞的话基本上差不多了。这要看将来的发展,将来要是能发展成旅游项目的话,我们可以不等他们安排,固定的时间,搞一场,半个小时,几个节目都可以。还有就是再雕一套不开光的脸子,现在这一套脸子点过光的,平时不用,只春节用。我们还计划把荡里的资料在祠堂前设个展厅,我们现在在收集资料。大概就是这些,走一步想一步。(吴说这番话是很连贯的,显然早就考虑过。)
孟:我猜想你们要再雕一套面具是不是因为这一套点过光的忌讳比较大?
吴:是的,点过光的忌讳大。再一个方面,这一套是宗族性质的,再雕一套就是傩戏会团体性质的。现在这一套脸子是姚街宗族,神秘的,最好不用,这一套只放在每年正月初七、十五的演出、祭祀的时候才用。
孟:我的一个担心就是你们搞旅游演出,时间长了就没有神秘感了,如果另雕面具,可能就不一样了。
吴:是的,给游客表演就用不开光的一套。
孟:另外一个问题,旅游开发,会带来一些经济收入,这会产生哪些好的、不好的影响,你考虑过没有?
吴:我认为,负面影响还是有,他们搞旅游开发,傩戏的神秘色彩给曝光,天天看还不曝光吗?时间长了就会把祭祀的神秘感破坏掉。正面的就是给老百姓增加一点收入。
孟:会不会因为经济收入,带来一些利益上的冲突?
吴:利益上的冲突这是正常的,不管哪一场演出,收入的分配都是个问题,在新脸子雕好之前,协调的难度怪大的。
孟:还有一个问题,去年从南昌回来您就有一个改革的计划,您是受到什么触动产生这个想法的?
吴:我们去的时候,先在乡里集训,我就领会到这一点,一个,演戏人要精悍,个个都能干,再一个要全能,文场也行,武场也能打,个个都能打,个个都能演,随便动哪一个都不影响演出。再一个,昨天已是第三次去太和章,我认为他们从演技、唱功来说都比我们好。我们现在是看起来个个都行,实际是个个都不行,这是我最困难的。
孟:想吸收一点他们的经验?
吴:是的。上次把太和章的几位请来,我们内部不统一,有人反对,不准搞。我这台戏,如果有这样三个人 (指章端桂、章常荣、章启发),就唱起来了,一个生角,一个旦角,一个丑角。
孟:你们今年的“吃腰台”是你家承办的吧?
吴:是的。我们这里姚家有几个房头,东边、大房、二房、三房、邻房,人口不均匀,有的只有一两家人了,摊派不下去了。
孟:“吃腰台”形成新的制度了吗?
吴:今年初七、十五基本上是我一家人弄的,村里补贴了一点,明年就改成上街、下街轮流。
孟:变成两个生产队负责了。具体谁负责呢?饭菜谁来烧?
吴:这由生产队决定,找一家人也好,集体烧也好,都行。我今年搞一次,过渡一下子。从明年开始两个村民组轮流搞。
孟:“腰台”一次要多大的开销?
吴:“腰台”从初七早上迎神下架以后开始,温蛋、水饺、面条、点心,还有早上的早点,初七晚上的“腰台”,还有十五也是一样的,大概要六桌饭,大约要1000块钱。
再雕刻一套面具、培养小演员、培养女演员、培养老演员、学唱别村的唱腔、把宗族性质的变成协会性质的,这些计划如果都得以实施,会对荡里姚傩的存在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将促使荡里姚傩活动由祭祀型向娱乐型、由宗族型向村落型进一步转化。
2006年12月,30枚新面具雕成,是花了近7000元在青阳县请人雕的,与老面具形象不同,也没有开光,准备用于接待旅游及外出表演。村里如此投资,已然把傩作为一种旅游资源看待了。“上山拜菩萨,下山看傩戏”,也是很有号召力的文化品牌。看来,提莫西·赖斯所说的“音乐是商品”的隐喻极有可能就要变成现实,荡里姚傩又将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化内涵了。
目前,因为干旱,国庆节以来河水几乎断流,漂流活动暂时中止,旅游开发的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但是,旅游开发显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平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会给荡里姚的傩活动带来极大的影响,使它迅速发生质变。
五、学者、会议、媒体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不断进入考察的学者同样会对当地文化状态产生影响,包括笔者在内,尽管我一直在努力争取把这种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但是,也有喜欢在村民面前高谈阔论的学者,告诉村民什么才是“对”的,哪些东西“错”了,等等。这从村民不时冒出的专业术语中可以隐约察知。比如村民姚克鸿在荡里姚剧本前撰写的《傩戏漫谈》一文中所用的“宫廷傩”、“寺院傩”等词汇,即可略见一斑。2005年春节,我向村民聂根生打听一件事,他竟让我问一位外来的学者,说“他老人家比我们知道的还多些”。
会议的影响从“罢演风波”已可见一斑。另外,如今正月十五朝青山庙六家见面,就是在一次接待会议时为了壮大声威而设成的,过去六家是按传统的既定顺序,依次进行,并不见面。
报纸的报道,电视台的报道,他们都很在意。2005年正月初七,安徽电视台现场录像、采访,第二天就在《安徽新闻联播》中播出,后来还送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播出。这在山村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不仅看得认真,并且议论纷纷,看见谁了、谁谁上了电视了、谁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好,等等,很长时间都不能平静。同时,这还让十里八乡的村民羡慕不已,着实风光了一番。吴国胜告诉我:上年演“问土地”,问到傩戏如何时,土地公公答得非常好,今年傩戏真的特别好,应验了。
笔者注意到,2005年正月初七他们演得很认真,正月十五却因为争吵迟迟没能开演,后来还大幅度简化内容;2006年情况刚好相反,正月初七草率收场,而正月十五却红红火火。 “巧合”的是这两次演得认真、红火的,都有多家媒体和多位考察学者在场,而这演得草率的两次,除了笔者这个已被他们当作“老熟人”的外人在场外,再没有其他外来人在场。这大约不是巧合。学者、会议、媒体等外界因素肯定会影响到傩的存在状态。2004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四套拍摄“华夏纪行”引发的2005年春节因劳务报酬引发的争吵,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自从贵池傩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后,他们似乎一下子繁忙了许多。2006年10月,荡里姚傩戏应邀到黄山参加民间艺术节,演出几个节目,村里租车去了很多人,报酬是3000元。2006年11月28日到合肥安徽省黄梅剧院演出8分钟节目,去了15个人,被评为省级二等奖。演出的节目是《关公登殿》,由姚家伟扮演关公、姚惟武扮演周仓、姚惟胜扮演关平,与春节演出的人员完全不同,并由池州市文化局专业舞蹈演员李大成辅导两天。节目的内容与形式悄然变化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为一些文化带来生机、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在深层次上对其文化形态、信仰基础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
六、结 语
综上可以看到电气化、信息化、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打工潮,还是旅游开发,等等,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当然也有机遇,这都是无法避免的。
笔者写这些争执、矛盾的“事件”,目的当然不是要评判谁对谁错,指出应该如何才是对的,应该走哪一条发展道路。毕竟,我们文化学者并不是评判文化高低的“裁判”,笔者没有“裁判员”的身份,也没有人赋予我裁判的权力和资格。
笔者之所以关注这些事情,实在是出于对现代化背景下存活的傩活动的生存处境的思考和忧虑。其实,这似乎谈不上是忧虑,因为假如有一天他们自动放弃了这些活动,我也无法判断那对他们来讲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对研究者来说肯定是很大的损失,但我们研究者也没有剥夺文化拥有者自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给被研究对象。学者似乎不应该拥有一方面自己住高楼大厦,另一方面要求研究对象一定要保持刀耕火种、树巢穴居生活状态的权利。我认为那是很自私的心态。我们没有干涉的理由,也没有干涉的权力,我们能做的只有尊重文化“局内人”自己的选择。
看起来,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保护与发展的冲突也是荡里人不可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他们计划再花钱雕刻一套面具,以减少现有这套开过光的面具的使用频率。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原来开过光的面具有许多禁忌,不是可以随便碰的,客观上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春节正式傩活动的神秘与神圣色彩,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无论如何,这种试图保护传统,协调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努力也是十分可贵的。但究竟会如何发展,现在还无法预料,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虽然这里讨论的只是一个村落的乐舞、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遇到的尴尬,其实,全国各地、各类别的非遗项目的保护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相似的挑战,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