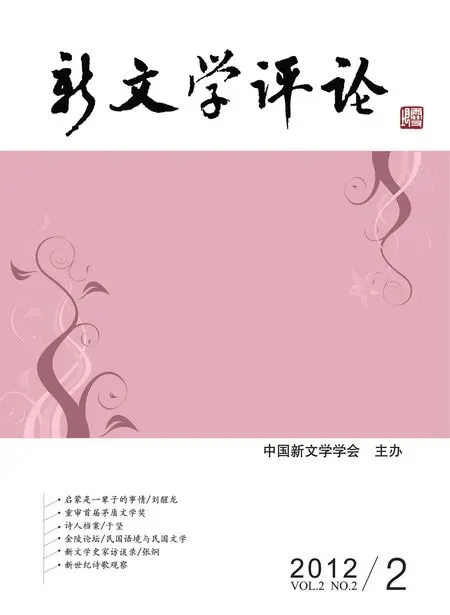民国文学的善“女子”
2012-12-18◆李璐
◆ 李 璐
民国文学的善“女子”
◆ 李 璐
废名是民国时期极具个性的作家,他在创作领域的诸种尝试对今天的文学有很多启示。选择这一题目,是因为废名的作品中,女子形象及其行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她们既是废名作品的主要人物,又是寄托了废名的审美理想、体现出废名审美观的重要元素,体现出废名作品的一些重要特征。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这一问题,从审美特征等角度对废名的作品作出探索。
一、废名关于“女子世界”的理念
废名经常在创作谈中说到女子和孩子的世界对于他创作的巨大意义。在小说和新诗中,废名不仅在塑造女性形象上煞费心力,更常常直接感叹女子世界的神奇力量。
女子世界对于废名的巨大意义首先在于它的启发性。从废名的一系列小说可以概括出废名反复申述的一些主题。主题一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人物关系模式,即主人公和他从小定亲的妻,以及从小一起长大的十分亲密的女伴。由于定亲后会有避嫌,所以从小青梅竹马、长大后也最牵挂的女伴,不是妻子,反而是亲密的小友。所以废名的短篇小说中,《柚子》、《鹧鸪》都反复写对柚子一生颠簸的喟叹和牵挂;长篇小说《桥》中,所有最玲珑剔透、永瞻风采的意象,都给了细竹,而不是琴子。在《桥》的上篇,废名会写到琴子的爱中有时飞来一个“妒”的影子;《桥》的下篇,废名还借大牛、小牛两个人物探讨了打破外在规约情况下的可能,结果是悲剧。这些反复申述的故事体现出废名常所萦怀的一个主题,这给了废名创作以原型和材料。主题二是一系列聪明懂事的女子。从《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到《桃园》中的阿毛,女子都是安静懂事的、宽容的。三姑娘为了陪伴妈妈、不看正二月间城里的赛龙灯,阿毛在临死前也只有小小的一个想吃桃子的愿望,都体现出女子世界的善与美。这是废名写作的关键点所在。
废名在《纺纸记》中说:
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位狐狸是顶懂得爱情的人,前生也一定还是一个女子,五百年的修练又变一个好看的女人来替女人报仇,所以身边别无武器,有一面镜子……连丑妇效颦都比你们《列女传》做得有意思多了。①
这里废名将他的创作偏爱说得十分清楚。废名喜爱美丽果决的女子,她的武器可以只是镜子,她顶懂得爱情。“丑妇效颦”比《列女传》有意思得多——即使效颦的效果不好,这爱美、向美的行为本身也很有意思。从现代观点看,载道的《列女传》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人的情感和个性,在审美上启发意义较小。这些地方都透露出废名在审美倾向上的执著追求。
废名在《中国文章》里说:“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②也正是在《桥》里,废名的化身小林说,“厌世者做的文章总美丽”,却又对琴子和细竹说,“你们我想不致于抱厌世观,即如天天梳头,也决不是可以厌倦的事”③。
这几段话综合起来看,可以梳理出废名的思路。如果完全厌弃世上的一切,那就不会留恋美丽的文章,梳头也不会令人不厌倦。所以废名所说的厌世,指的是厌弃实际、厌弃世俗,原因是功利的世俗生活中缺少理想。所以废名揄扬“厌世派”的文章,因为厌弃世俗,才能追求理想、追求文艺上的美丽。而女子梳头是很美丽的,所以废名才说天天梳头就不会“厌世”了。美是支撑废名世界的柱石。
因此,废名在《女子故事》中频频引用李商隐的诗:“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梁王司马非孙武,且免宫中斩美人”,“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④。这些诗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视世俗社会的功利价值。死且不怕,就可以肆意追求美丽和性格的张扬了。这是在文学上的张扬。
废名有一首诗写道:“我在女人的梦里写一个善字,我在男子的梦里写一个美字,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⑤废名这首诗的逻辑是,缺少什么我就给予什么。这里反映出废名的想法:女子缺少善,男子缺少美,厌世诗人就给他让他不厌世的东西,小孩子可以得到一个世界。为什么废名在这里会认为女子缺少善呢?原因是废名在这里写的是世俗中的女子、现实中的女子,他认为她们缺少他理解的善。这里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废名在作品中塑造的女子,都不是现实中的女子,是寄托了废名理想的女子。厌世诗人给他什么呢?给他“好看”的山水。山水是非人为的东西,而且是“好看”的山水,这里体现出废名用以拯救世俗、厌世的良药是“美”。
二、废名的“女子世界”由幻想中的女子构成
关于这个问题,废名在分析温庭筠等作家的诗词时作了详细讨论,体现出废名自己的审美追求。废名在《谈新诗》中说:
我再举一首《过楚宫》七言绝句,“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他用故事不同一般做诗的是滥调,他是说襄王同你们世人不一样,乃是幻想里过生活哩。
废名说温庭筠:
他是画他的幻想,并不是抒情,世上没有那么的美人,他也不是描写他理想中的美人,只好比是一座雕刻的生命罢了。英国一位批评家说法国自然主义的小说家是“视觉的盛宴”,视觉的盛宴这一个评语,我倒想借来说温庭筠的词,因为他的美人芳草都是他自己的幻觉,因为这里是幻觉,这里乃有一点为中国文人万不能及的地方,我的意思说出来可以用“贞操”二字。⑥
这两段话把废名的审美观说得很彻底。废名所说的“幻想”是熔铸了作家生命的一个雕塑。专注于美的作家,不依恋于现实生活中的题材和意象,而是忠于自己的一种审美理想。因此,这种幻想中的女子,往往凝注了作者在精神上的认可和追求;这种幻想中的感情,往往特别执著,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所依凭而特别显得专一和有操守。所以,废名会称扬襄王的依恋梦中美人,会用“贞操”来形容温庭筠所创造的审美世界。
废名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他的短篇小说《柚子》、《浣衣母》、《初恋》、《阿妹》、《鹧鸪》、《竹林的故事》、《浪子的笔记》、《菱荡》中的女子都如璞玉般真纯,心地良善,几乎不与现实世界发生任何功利上的关系。在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桥》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细竹和琴子这两个人物,可以说寄托了废名对善与美的理想。她们纯粹是精神性的存在,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出废名的审美追求。琴子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⑦,是儒家精神的体现。琴子感觉到小林更爱细竹一些,她的心理是“再者,她的爱里何以时常飞来一个影子,恰如池塘里飞鸟的影子?这简直是一个不祥的东西——爱!这个影,如果刻出来,要她仔细认一认,应该像一个‘妒’字,她才怕哩”⑧。这种温柔敦厚的心理,可以反映出废名寄托的审美理想。但这种温柔敦厚也难以抑制感情的独占性所带来的波动。在小林赞叹细竹“真好比一个春天”时,“琴子实在忍不住哭了”。琴子说的最极端的话是“你以后不要同细竹玩”⑨。她并非真的不让他们一起玩,这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体现出温柔敦厚理想与感情独占性的挣扎,这也就是琴子极端表达的极致了。所以小林一句“我们两人的‘故事’,恐怕实在算得很有趣的一个”立刻“说得琴子微笑”⑩。这些地方都写得很丰富。琴子身上体现出废名对“善”的理解,她的身上体现出废名对儒家审美理想的一种追求。
而细竹,体现出废名对道家审美理想的追求。细竹的举手投足,都真率自然,而仿佛上合天钧,总是引起小林赞叹和思考。比如“杨柳”一节,细竹很爱和孩子一起玩,她为孩子们扎杨柳球、最后那一个扎得最好,所以孩子们都来争夺那最后一个了。小林因此说:“就因为一个最好,惹得他们跑,他们都是追那个孩子。”细竹说“是呀,——那个我该自己留着,另外再扎一个他!”小林笑说“上帝创造万物,本也就不平均”。这个小细节浸透了道家思想的特征。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道家认为一切比较而来的结论都是相对的,没有比较就没有占有的心、没有争夺的心。所以废名通过这个小细节表达了他在这个问题上对道家思想的赞同。而细竹,就作为承载道家思想的人物,在小说中成为某种精神和品格的象征。
从这个角度,废名塑造的女子形象,承载着很重的文化内容。所以她们与小林进行的一场场审美鉴赏和参禅悟道,都是了解废名审美观的钥匙。废名借莫须有先生之口说自己“偷偷的把一切之网自缀在身上,也就错综得很可观”,这是废名从传统文学资源中吸取他认为有建设性内容的一个夫子自道。从这些地方可以探寻废名审美观的内核。
废名对女子美的高度赞赏中,也充满着自省和自嘲的意味。如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批评小学生抄袭鲁迅的《秋夜》时说:“夫贾宝玉并不一定讨厌,只是因为他将女人比作水做的,于是个个人崇拜女子,有些肉麻,故贾宝玉令人生厌了。”但其实废名在写“女子世界”时受《红楼梦》的影响很明显。除细竹、琴子这两个人物的设置类似黛玉、宝钗以外,废名也常在作品中引用《红楼梦》中的意境和典故。所以,废名这里对贾宝玉的“生厌”,与他自己一贯的审美观是相合的。因为他讨厌滥调,强调作家在运用已有的文学资源时要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他对自己推重女子会否是袭用《红楼梦》而成为滥调是有警惕的。而他也自信有与《红楼梦》不同的关于女子美的理解。我认为废名创造的女子的理想世界与《红楼梦》中的女子世界不同的核心在于废名并不像曹雪芹那样要写出“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然曹雪芹所写的女子中也有幻想的成分,但废名的人物与思想精神的结合特别紧密。从这一点上,可以将废名的小说称为“思想文化型”小说。
三、废名的审美观与当时的环境
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废名“十年造桥”意味着什么呢?
废名对他所处的思想文化环境一直非常关注。从1926—1927年间他的《死者马良材》、《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狗记者》、《俄款与国立九校》、《共产党的光荣》,1930年的多篇《闲话》和《国庆日之朝》等散文可以看出,废名对当时的政治和言论形势很关心,并且见解激烈。其中1925年废名写给徐炳昶的《通讯》尤其体现出废名对思想文化的关注。废名说:
所以目下最要紧的,实在是要把脑筋还未凝固,血管还在发热的少数人们联合起来继续从前《新青年》的工作。现在虽说有许多周刊,我敢断言都是劳而无功。几乎近于装点门面。尤其不必做的,是那些法律政治方面的文章,因为我们既不要替什么鸟政府上条陈,也无需为青年来编讲义,——难道他们在讲堂上没有听够吗?我们要的是健全的思想同男子汉的气概,否则什么主义,什么党纲,都是白说,——房子建筑在沙地上,终久是要倒闭的。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1925年时,废名与鲁迅《呐喊》的观点很接近,认为培育健全的思想,才是对当时中国最有意义的工作。废名也一直以思想文化建设为目标。到1930年办《骆驼草》时,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不谈国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虽然谦称“如斯而已”,但“好文章我自为之”的自负显而易见。而且,废名对“不谈国事”有一个说明:“既然立志做‘秀才’,谈干什么呢?”可见,废名不是不关心国事,而是认定作为“秀才”可以做的工作是对当时的环境有意义的,他也自认为这个工作是他该当要做的工作。所以,废名的“十年造桥”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的。废名的这个思想变化轨迹与同时期的老师周作人有很大关系,本文不展开了。
在这个意义上,废名将女子美提升到极高的位置,有很多深意。首先是女子美给废名以灵感。除了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外,废名的《无题》诗也给了这一点以写照:“梦中我梦见人间死了,这个境界正好比一个梦,伊手上还捏一个东西在那里玩,偷偷我看了一眼,正是伊给我的光明。”其次有反“文以载道”的意味。废名是新文学的作家,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多处提到新文学与八股文作家的区别在于言志与载道的区别。这里的志与道,可以作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之志”与“圣人之道”的理解。废名并不是不体道,但他的体道完全是个人性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这也是对古典传统中太多文统、道统而归根结底是习气和权力争斗的污浊空气的反拨,所以废名会接近执拗地不顾一切其他世俗标准,在作品中执著追求女子美的价值,一再称扬女子世界的神奇,甚至连女子的身边之物也都具有神奇的力量:
起初他看得琴子站在水上,清流与人才,共为一个自然,联想到“一衣带水”四个字,……慢慢他笑道:
“我记得一个仙人岛的故事,一位女子,同了另外一个人要过海,走到海岸,无有途径,出素练一匹抛去,化为长堤,——我总觉得女子自己的身边之物,实在比什么都现实,最好就说是自然的意境,好比一株树随便多开一朵花,并不在意外,所以,这个素练成堤,连鹊桥都不如。”
将琴子身边的清流联想为琴子的衣带,进一步想到女子的素练化为长堤的故事,且认为这个长堤胜过“金风玉露一相逢”的鹊桥,废名在这里将女子的身边之物比作自然的意境,将其比喻为一株树“随便”多开一朵花。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随便”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词——这个花开得毫不费力气,非常有力量,而且有风致。这就是废名对女子身边之物所怀的崇敬之情。所以《桥》中的小林以一种惊异的态度面对琴子和细竹的种种容止,《莫须有先生传》中的莫须有先生对房东太太的外甥女也表现出手足无措的神态。这也正与废名在《女子故事》末尾引用《聊斋志异》里葛巾玉版的故事形成一个呼应:女子以及女子的身边之物具有神奇而强大的力量。

注释:
①废名:《纺纸记》,《废名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6页。
②废名:《中国文章》,《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1页。
③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20页。
④废名:《女子故事》,《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6页。
⑤废名:《梦之二》,《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3页。
⑥废名:《谈新诗》,《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4页,第1635~1636页。
⑦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7页。
⑧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⑨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568页。
⑩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页。
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