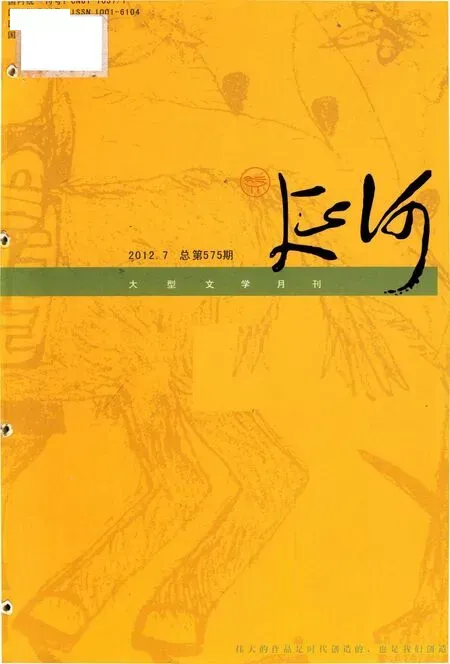你什么时候死
2012-12-18孙智正
孙智正
我没想到去她那里这么远。
公交车缓缓地开过一座桥,缓缓开过一座桥,沿着一条河走,走着走着经过一座山,从山脚下慢慢绕出去,路边出现了好多密密挨挨的白杨树,白杨树和白杨树之间,有几个四五十岁的男人蹲在地上铺地砖,其中一个举着橡皮榔头一下一下砸。
再往前,路边开了条很大的沟,沟边翻起两道土坡,潮湿的泥土漫到马路中央,两边的车都慢下来,我沟里站着那些人,不断地掀起泥土,猛一下甩到土坡上,其中一个穿着蓝色的背心,我知道,这种背心容易掉丝。
汽车开到这样的地方不容易,过了这段,两边是开阔的田野,速度重新快起来,到一片别墅区前车停下,我下车,这车还要往前再开一站。
我走进别墅区,门口站着的保安身上有一根橘黄色的绶带,我笑了笑,也不是太好笑,还是笑了下,眼前一条笔直的水泥大路一直往前通去,感觉会绕地球一圈,串起一条条小一点的水泥横路,像无穷多的丰,路口挂着牌子,富贵园几栋到几栋,我一直往前走,知道在往北走,两边的房子一模一样,大概过了七八条横路,我看到了牌子上的73栋,根据指示右拐一直往东走,从60栋开始走到73栋,每栋房子前面都有小花园,有的种着花草,有的种着树,有的搭着凉台,所以,这是有区别的,我到了73栋前面,铁栅门关着。往里探望,四层小楼,正门左边种着三四棵树,一棵特别高,不知道什么树,右边种着一圈花草,一蓬竹子,还有一架葡萄,白色的水泥架子,看上去真好看。
我还看着,才发现草木后面是一堵玻璃墙,玻璃墙拉着帘子,帘子开了一角,那里有座沙发,沙发上好像坐着个人,能看见一个后脑勺,我敲了敲铁门,后脑勺转过来一张脸,恐怖片里经常后脑勺转过来一个后脑勺,青天白日吓死人。
她看见我笑了,很快站起来在那里消失了,只剩一张沙发在那里,过了会儿,门开了,她笑着从里面走出来,跟变魔术似的。她穿着一套红色的运动服,底下是拖鞋,拖鞋看上去应该是软底的。
我跟着她走进厅里,她屁股挺大。厅里放着柔美的音乐,不知道是什么音乐,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她去倒了一杯冰水过来,我喝了半杯。她递给我一张纸巾说,过来挺远的噢。这纸巾像有些笔芯,有股腻人的香味,我擦了擦额头说,还好。我找了扔纸巾的地方,她伸过手来,我把纸巾放在她手掌上,她扔在脚旁的一只蓝色的垃圾桶里,垃圾桶看上去像个玻璃杯子。
我不知道说点什么,她在看着我笑,我有点尴尬。我说,这放的是什么音乐。她说了个名字,我没听明白,她仍旧笑着,过了会儿说,想不到你长这么大了。我说,呵呵。她说,当初你也就上初中吧,老和我弟弟一块玩,脸一红一红的,话很少。我说,呵呵,小春现在去干什么了。他叫徐春,我们叫他小春。她叫徐青,我还没想好叫她什么。
徐青说,他么,跟着他姐夫做生意。停了下她问,你工作忙不忙。我说,还好,上班很忙,下班就没事了。她捂着嘴笑了,不知道在笑什么。她接着问我单位情况,住在哪里,女朋友怎么样,常回家看看吗,平时有什么爱好,打算什么时候买房子等等。
我一一作答,回答完之后,客厅里只剩下音乐,这个厅有半个篮球场这么大,天花板很高,玻璃墙一角摆着沙发,另一角摆着一盆很大的绿色植物,植物的顶剪得又平又齐。我们现在坐在东墙下的两把竹椅上,对面西墙上挂着一块很大很大的电视板,不知道音乐从哪里传出来,或许是天花板。她双手搭在椅背上舒服地坐着,胸很平,许多屁股大的女人胸都平。
我把她刚才问我的问题全部问了她一遍,她也一个个回答了,最后叹口气说,其实有个工作也不错,至少每天都有事情做,现在我天天懒得动,胖得厉害。
实事求是讲,她不胖,不过皮肤和神情看得出来,她在屋里呆得太久了。我问她在家都做些什么。她说,就听听音乐喽,有时听到好音乐我都哭呢。我说,呵呵,我都听不懂,我喜欢有人唱的那种。她说,哦我知道,其实纯音乐才好听,人声的表现力很差,跟乐器没法比,你说钢琴那多丰富啊。我说,是啊。她站起来,指着一个角落说,那里本来有一架钢琴,很好的一架钢琴,她说了个外国名字,大概是钢琴的品牌,她的手一弯,模拟钢琴屁股的曲线,现在那里摆着一个柜子。
她说,我以前每天早上就坐在这里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弹弹,弹着弹着就舒服了,有时候眼泪都会下来,但不是难过,不是哭,就是,很奇怪很奇怪的感动。
我说,嗯,我明白。她说,现在没了,前年还是大前年,小春的姐夫生意不好,拿去卖了。我说,现在能不能再去买一台。她遗憾地笑了笑说,能,但我不想买了,几年没弹手都生了,听听就行了。我说,哈哈,不是怕买了又卖掉吧。她说,呵呵,现在他的生意还算稳定,很忙,前几天刚从海南回来,现在又去上海了。我说,噢。
她说,下午你没事吧。我说,嗯。她说,那要不看张碟吧,坐着也挺闷的。我点点头。她上楼去了,我坐在椅子上等,看着刚来时她坐的那张沙发,这张沙发宽大得像床,她和他老公再加小春躺在上面都没问题。
过了会儿她拎着一只化妆品礼品袋下来,里面有二三十张碟,她说,这些碟都是我朋友推荐的,说都值得看看,你挑张看看吧,我平时一个人都不怎么看。我看了下,苏菲玛索的片子几乎齐了,莫妮卡贝鲁奇的也不少,还有燃情岁月这一系的片子,我说,这都好像没什么好看的,挺女人的。她笑着说,你不喜欢看啊。她也一块翻,翻出一张铁皮鼓,她说,这张不错吧,好像是讲战争的。
我说,那就看这张吧。
徐青把墙帘和窗帘都拉起来,厅里光线温馨。影片开始一片开阔的湿气腾腾的平原,祖母穿着肥大的裙子坐在地上烤土豆,祖父被警察追,从地平线的远处跑到眼前,钻到祖母的裙子下,警察追到了,祖母告诉他们祖父往某个方向跑了,在祖母回答警察问题的时候,祖父在祖母裙子底下坐活栓运动,活拴运动,这是君特格拉斯说的,祖母的身子一耸一耸的,警察
奇怪地看了她几眼就走了。徐青笑着说,这些警察真笨,那男的在底下没干好事。我说,呵呵,真有想象力。想象力未必是好事。
再过了一会儿,讲妈妈和情人偷情,在旅馆里迫不及待地脱衣服,还有很粗俗的对白,影片挺碎的拍得,我看得有点不耐烦,性爱场面出现还觉得有点不自在,徐青不是这样的,她笑得很开心,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喜剧片啊。
看完这个片子,时候不早了,徐青坚持要留我吃晚饭。我坚拒。她说,是不是女朋友在家等着啊。我说,呵呵。她又说要我带两瓶红酒回去。我坚拒。她说,有两个选择,要么留下来吃饭,要么带走红酒。我带走了红酒,她送我到院子里,她说晚上吃完饭后在葡萄架下坐坐感觉很不错的。我说,呵呵,那应该很凉爽。葡萄叶子上没有虫子掉下来吗。她说,以后常来玩,你跟小春朋友吗,我们既是老乡,我还是你姐姐呢。我说,好的啊,下次你也来我们住的地方玩,请你吃饭。她说,好的啊,看看你女朋友。
我拎着两瓶酒走了几步,回头望了眼,她已经回房去了,我抬眼望了望这幢楼,这楼干嘛四层高,三层和四层有什么用,也许可以用来做春宫或者隐居。
我走出小区,想着这两瓶酒。
我站在小区马路对面等车,那个保安的衣服上有条橘黄色的绶带,我还是笑了一下,过了会儿车来了,我拎着酒上车,轻轻地放在脚边,用小腿贴在车厢壁上。汽车开得很快,到那段开沟的地段,速度又慢下来,路边的劳动人民不见了,他们回去吃饼了吧,再往前车过了山,过桥时我差点就想把酒拎起来扔到河里。车还在往前走啊,我没睡着,在离家还有两三站的地方,下了车,车站上好多人,我走进路边的一个小区,没走几步就看见那种尖头方肚的垃圾箱,完全可以轻松地把酒塞进去,我走到垃圾箱前,才注意隔着人行道边上有家小店,门口坐着三个老男人,他们在喝小二,围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几个尼龙袋,大概里面有煮花生、麻辣烫、羊肉串,和他妈的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什么吃食。
我继续往前走,楼道口都有安全门,进不去啊,经过几个楼道,我想了想,走到一家楼道门口,上面贴着一张纸,找11号房请按*字键,我就按了下,过了会儿有个女声喂了下,我说,我是楼下的忘了带钥匙了,能不能给我开下门。那女声哦了下,门滴滴开了。我推门进去,楼梯口摆着好多自行车,我把酒放在一辆自行车的车蓝里,就退了出来,走出小区到车站等车,现在的天气不错啊,不热不凉的,天边还有晚霞,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二十来分钟后,我回到家,家里空荡荡的,厅太大也不好,拖地麻烦,大概再过一小时,乔非才会到家。我打开电视,在放大上海1937,里面的人短小精悍很会打的样子,跟过江龙风格差不多,我盯着表看,看了半小时把电视关了去买菜,已经想好了,买几个西红柿、青椒和豆角,1块5毛钱的面,可以做出三碗面,晚上一人一碗,剩下的一碗,明天一人半碗当早饭。
小区门口正在修地铁,马路上竖起一排蓝色的隔板,隔离带内一只机械手正在嘎啦嘎啦扒花坛,几个工人躺在一条土槽里抽烟,一定很舒服吧,我从边上走过去,那只机械手转弯时往里弯着手掌,小心地避开旁边的电线,操纵室里坐着个工人,跟汽车人似的,再往前是个报亭,报亭也是蓝色的,一对中年夫妇看着,现在他们正蹲在报亭门口吃花卷,再过去几步
就是地铁站,已经竖起了八座水泥拱梁,入口围着青纱帐,等修好,不知道这个报亭生意很好还是被拆掉,马路对面当然也在修地铁站,路上搞得尘土飞扬,我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右转,路边也有隔离板,多走了好几百步在前面绕了个弯到菜市场,花了五六分钟时间买好所有东西,顺着原路回来,把刚才看见过的景物倒着看一遍。
回到家里,我先把豆角洗干净,切好,洗青椒和西红柿,一起洗好一起切也不要紧,不过这次是一样样洗一样样切,青椒把帽摘了,再开膛破肚去籽,切丝,西红柿就柔美地搓搓,切成瓣,剥蒜,冰箱里有肉片,不过乔非说,不放肉也不要紧,那么,就不放了,先炒豆角,这也是乔非说的,北京的豆角不好熟,老听到豆角中毒的新闻,但还是得吃嘛,炒熟点,就先炒它,炒得瘪下去了,加蒜青椒炒,炒得也瘪下去,看看差不多了加西红柿,炒出红汁来,再炒会儿加盐,加鸡精,翻两下,关火,盖盖,放一边等乔非来短信说快到家了,舀起三分之二的菜,加热水,煮面条,煮个三四分钟,酹点冷水,酹这个字不知道对不对,面快熟了加刚才舀出的三分之二菜,煮一会儿,加盐、鸡精,另外一个要注意,煮时要用筷或勺子不断搅锅,不然面条容易粘在一起,这就是南方的面条和北方面条最大的区别,起锅赶紧吃,马上坨。
我炒完菜赶回房间看电视,电影还没完,看上去是要看结局了,一个老头在念洪门规矩,一个小胡子看上去像坏蛋,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一个赤膊的正义青年要受门规处死,三刀六洞之类的,旁边还有个日本青年,小胡子让正义青年自杀,日本青年不同意,要凌迟他,大家吵了起来,小胡子背后站着个女的,她取下项链,乘乱把鸡心里的药粉倒在茶杯里,跟小胡子的茶杯换了下,旁边有个眼神犀利的青年看见了,但他没说什么,小胡子正吵着,不知为何要喝口水,一喝就倒地死了,死前还说,谁放毒,茶里有毒,霍元甲也是被人在茶里放毒毒死的,然后大家打了起来,这时门话响了。乔非的短信还没来。
我跑去接,不是乔非忘带钥匙了,是邮局的问我能不能帮邻居收下报纸,他好像好几天没在家了,我叫他放在他家防盗门内好了,给我的话我也这么处理,我跟他也不熟。邮局的噢了一下,我给他开了门。回到房间,电影里还在打,不想看了,换到13频道看娱乐新闻,我听到有人咚咚跑上来,敲了敲隔壁的铁门,大概就是邮局的人上来放报纸了。
孙悦怀孕了,她给宝宝写了首歌,袁咏仪生小孩了,她叫他还是她小魔头,因为这孩子每次拉屎都不拉干净,过一会儿拉一点过一会儿拉一点,她就要不停地换尿布啊,萧亚轩的脚好像又出毛病了,画面回放她和小猪跳性感的舞,腾一下跳到他腿ending定格,蔡依林的胸好像在二次发育,大得有点蹊跷。乔非还不回来,也没短信,我有点烦了,到客厅的窗口看看外面,其实只能看见很短一段路,就算她回来,也未必能看见。
我回到房间继续看电视,过了会儿,拨她手机,她的铃声换了,一个小女孩很皮的声音唱,你的电话我不接,别人电话我都接,你的电话我不接,不接不接就不接,我笑了,觉得很好玩,听了几遍之后就恼了,挂了电话再打过去,这个小女孩一直唱着,我挂了电话,狠狠地空踹了一脚,甩得膝盖疼。
我发短消息过去,问她怎么回事,没听到电话吗,什么时候回来。
她没回。我给手机里的好多电话都发了短信,一条条都回过来了,我给自己号码发了条,过了会儿也收到了,不是手机问题。我想这是怎么了,再到客厅的窗口望,那段路空着,我把电视关了在沙发上坐着,再拨电话过去。这时那小女孩只唱了几声,乔非接了起来,声音很正常,我说,没听到电话吗。她说,放在包里没听见啊。我说,你回来了吗。她说,回来了啊,快到家了。我说,好,那我下面条了。她说,下吧。
我挂了电话,到厨房里,从锅里舀出三分之二菜,把1元5角面条全下锅里,加热水,拿着筷子搅啊搅,热气上来手还挺热的,过了三四分钟,我把剩下的三分之二菜也倒锅里,拿勺子搅,加盐,喝了喝,酸酸咸咸的,味道不错,再加点鸡精,搅了搅,这时门响了,乔非回来了,看上去很疲惫,不过她笑了下说,做好了啊。我说快了。
我盛好面条到房间里,她已经换上了宽松的衣服,洗了脸。我们俩一块坐着看电视,新一轮的娱乐报道开始了,有个傻乎乎的女记者问萧蔷,你觉得演好赤壁大战里的那个角色有难度吗,还有一个记者问伊能静怎么理解才女这个词,伊能静说,蠢材的材好了,以后大家可以叫我蠢材,记者接着问起知道刚才在台上唱的那首歌,他把歌名说错了,伊能静纠正了他,他问她知道是这是哪个民族的歌曲吗,伊能静翻脸走人了。
吃了一会儿,乔非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啊。过了一下她说,你是不是以为我不回来了啊。我说没有啊。她说,我老担心你有一天突然走了就不回来了,然后我再也找不到你了,你会不会这么做。我说,不会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她说,我觉得你会,你要走的话一定是一声不吭的走的。我没说话。她说,我走的话肯定会先跟你说声,你放心吧。我说,嗯。
她说,今天晚上面条挺好吃的。我说,没有吧,我觉得不够辣。她说,这样刚刚好。我说,好啊,那我以后就这么做。我还没吃完话,手机响了,网友金叫我去他家喝酒,他叫了好几个朋友。我答应了。
我跟乔非说,有个写诗的叫我去他家喝酒,我吃完饭就去。乔非说,嗯,你去好了。我说,我会尽早回来的。她说,好。我放慢速度,跟她差不多时间吃完,把碗拿到厨房浸在锅里就走了。乔非在看电视。
天已经完全黑了,不过到处是路灯,金说在三环上就有到他家的车,到三河大厦下车一直往西走就可以了,到三河的车很多,我去过那里。我花了半个小时走到车站,花了半分钟等到车,花了半个小时到站下车,我一直往西走,走了半个小时,两边都是写字楼,还没到住宅区的样子,前面远远看到的两个小区,房子都矮矮的,不像是金住的小区,因为他说的房间号是1903。我只好一路问遇到的人,遛狗的少妇,散步的老夫妻,社区保安,出租车司机等等,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打金的电话,他问我在哪里,我说就在附近了吧。我告诉他附近一幢写字楼的名字,他没听说过,问我是在三河下车一直往西走吗,我说是的啊,他说那你可能走得还不够深,大概要走三四十分钟呢,你到时候再问问怎么走。我说,好吧。
我继续往前走,走穿了整个写字楼区,前面是住宅区,不过隔着一道墙,我问路边一个小卖店主某某小区怎么走。他说,这个名字很熟,倒听说过,不过不知道在哪里,好象就在这一片。这时我背已经出了汗,四周是茫茫夜色和巨大的楼群,前面停着一辆出租车,我朝它奔去,司机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我感到很高兴,问他知道某某小区吗。他说,好像就在附近,我给你问问,他用对讲机问了问,过了会儿,对讲机里传出一个声音指点他怎么走怎么走。
他示意我上车,我上车了,他跟着对讲机的指点走,走着走着车要过一座桥,我和他都觉得似乎不对了,我又拨通了金的话,交给司机。司机一直在说话,大概说了二十分钟,突然把手机还给我,很愤怒地说,这个人肯定不会开车,一点也不会指路,开车的人三句两句就说清了。手机很烫,屏幕黑着,看来没电了,我说,那你现在知道怎么走了吗?他说,我不知道啊,我都被他绕晕了,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我说,好,我下车。
我付了钱下车,这车马上一路沙尘地去了,夜色茫茫,前头是座巨大的立交桥,身后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区,我知道在北京,但不知道在哪里。
我往回走,决定不去金家,路边好多洗头店和小吃铺,我不找这些,好不容易前面出现一家网吧,很高兴地进去了,登记小姐问我拿身份证,我很诚恳地告诉她真的没带,她没说什么,我把钱给她,她给了我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很长的登陆码和密码,这个网吧其实很大,这附近一定有什么大学,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一边就是墙壁和竹窗帘。我隐身登陆QQ,把msn调成显示为脱机状态,然后去看各个论坛和博客,还去金这个傻比的博客看了看,给他留言说找不到地方不过来了。我不知道他傻比司机傻比还是我们三个都傻比。
我看到乔非也在线,不知道在干什么,有个少女走过来拉开旁边的椅子,椅脚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尖叫,我看了她一眼,她正在不好意思地吐舌头,我继续看论坛,边上还空着很多椅子的啊,她屁股一沾座就把拖鞋踢了,盘腿坐在椅子上,看着我的电脑屏幕,过了好一会儿她还看着,我看了看她,她穿着黑色的短裤白色的T恤,年纪十七八,吃着一根雪糕,我感觉现在这么打扮还吃雪糕的话,可能会冷,她的头发全黑,披在脸蛋旁边,我扫了眼她的脸蛋,她笑了笑,我没说什么,我没在看电影,她在旁边看什么,感觉又不像是鸡,过了会儿她哎呀一声,按了下屏幕,又吐了吐舌头,系统看来早已启动,她熟练地登入,看电影,同时开了QQ和QQ游戏。
我就不再管她,QQ群里有人发了楼凤信息,这提醒了我,我不想再上网了,座位斜对着厕所入口,刚刚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进去了,身材好得要人命,我等着她出来,过了会儿她目不斜视地出来啦,真高啊,又瘦,穿着紧身的红色背心,头发高梳着,脸很亮,不过看不见她腿,她摇曳着走过大厅,好多人在看她,我看着她走到vip包间里,命不好,等下要找的不是她。
我下机,看了边上的小女孩一眼,她沉浸在剧情里,我出门直接打的,汽车在环路上奔驰,我知道自己在哪儿了,红子的楼很好找,不过花了我四十多块车钱,在车上我想到要先给她去个电话,但是手机没钱了啊,我想过问司机借,但是管他妈的,先到了她那里再说吧。她住在一个全是旧楼的小区里,不过有很多树,很安静,白天在路上看到的都是老头老太太,我找了找她的门,二门还是三门,最终我确定是三门,因为我仰头看见了她房间的窗帘,粉红色的,没拉严,灯亮着,可以看见窗口旁边立着一个柜子,柜壁上贴着一副画,这副画是我送给她的,一对外国青年男女,女青年只穿着条毛边牛仔短裤,裤门没扣,裤子快要滑脱下来了,幸好撅着屁股,很丰满的屁股,撅着,顶着站在她背后的男青年的小腹,男青年怀抱着她,手臂挡着她的胸,她的手臂搭在他手臂上,四条手臂在她胸前缠绕,就是这么一张照片,地摊卖十块钱一张。
楼道没装门禁,我上楼拍了下手,灯亮了,楼梯乌黑,转台上摆着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鸡笼啊鞋盒啊垃圾袋啊,到了三层,我拉了拉防盗门,锁着,紧紧的,我拍门,过了好一会儿先听见拖鞋打地的声音,接着红子的声音在里面问,谁啊。听上去挺欢快,我报了名字,她开了门,穿着件粉红色的睡衣,上面有一颗颗小心心,她瞥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转身就往房间里走,睡衣衣摆下是两条白腿,白腿下是脚,脚上穿着玻璃拖鞋,我关上门,跟着她进房间,关上房门。
房间里灯很亮,电脑开着,电视也开着,静音状态,一个歌手在无声地引吭高歌,她背对着我坐着看电脑,我坐在她床上看她背脊,她在视频聊天,咯咯笑着,过了会儿把睡衣掀起来,搁在胸上,过了几秒猛的放下,一阵狂笑,笑得几乎从椅子上滑下来,有时她一手按着胸,一手按着鼠标,有时两手按着,有时用嘴咬着睡衣衣摆,我看了下,对方的视频框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个什么人。
她转过头睕了我一眼说,那个人在问你是谁呢?我说,哦。她哈哈哈笑着说,我就告诉他是个客人喽,很有文化的啊,是个大学生。我说,你不用告诉他这些,跟你们聊天有什么关系。她说,随便聊喽。我说,聊点别的也可以啊。她做出调皮的样子晃了晃头说,哦。我说,怎么看不见他。她说,他的摄像头坏了。我说,不会吧,他可能就是把摄像头遮了,可能在网吧什么地方,不好让你看见。她说,哦,不知道啊。
我坐在床上看电视,有时候瞄一眼电脑屏幕,看不见他们在说什么。过了会儿她说,他让我跳舞给他看哎,要不要给他跳。我说,你让他汇钱再跳。她想了想说,嗯,要先汇钱,谁知道他是不是骗子。她噼里啪啦打了会字说,他不汇钱就不给他跳是不是。我说,嗯。她又打字,说,可是我很想给他跳哎。我说,那你就跳啊。她先坐在椅子上扭起来,过了会儿站在椅子上,让叉着的大腿对着摄像头蹲了会儿,又把椅子挪开,两只手在身上摸来摸去地跳,由于没有音乐,我感觉,她跳得不是特别好,我始终看到的都是她的背。她旁边就是大衣柜,镜子前面挂着玻璃片串成的帘子,玻璃片有的是花,有的是鱼,有的是小猫的脸,有的是心,红红绿绿蓝蓝黄黄,她的手臂撩到帘子,就哗啦啦一阵响,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在镜子前面挂帘子,大衣柜旁边的窗台上摆着好几盆富贵竹,有一盆黄色的假花,旁边有一只圆形的鱼缸,鱼缸里有一条橘黄色的金鱼,从我这里看去,有一个巴掌那么大。
现在她不跳了,像个输入员一样安静地坐在电脑前打字,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笑一下。我看大衣柜的画,有一角掀起了,我问她有没有胶带,她说没有啊,什么胶带,真难听。我在桌子上找了找,放着好多她的瓶瓶罐罐,纸巾,果汁什么的,我看到有一罐502,很奇怪,问她怎么会有502。她说,什么502啊。我举给她看,她说,上次买的喽。我挤了些在画上,画纸太光滑,胶水流到我手上,食指和中指马上粘在一起,我不管它,先把画贴上,再用手掌拍了拍,掌根也粘了些胶水,差点又把画带起来。
我到卫生间洗手,水龙头的扳手断了,基座还在,我一拧,拧开了,上面硬梆梆的一层胶,看来她买了502想把扳手粘在基座上,真够傻的啊,我生生把食指和中指扳开,水根本洗不掉胶,只好慢慢撕,慢慢撕,慢慢撕掉一些。我回到房间里,她还坐在电脑前,我去看鱼,看了会儿觉得不对,仔细一看,那鱼腹胁肿胀,全身的鳞片都竖了起来,看上去很恐怖。我又看了会儿,没跟她说,她应该没注意到吧。
过来会儿她转过头来笑着说,你不想等了吧,马上就好噢,我就聊几句。我坐在床上,房间里没有别的椅子,过了会儿,她站起来,电脑还开着,朝我笑了下,把灯关了,开了一盏粉红色的壁灯,房间里立刻暧昧起来了,她说,等下噢,她出去了,好像去了厨房,回来时捧着一个盘子,我知道上面有红酒、白酒、矿泉水、水杯、湿纸巾、酒精、滚珠、试管等,她用脚踢上门,把盘子放在桌子上,坐到床上吩咐我躺好,她说,我们要开始了哦。口气很像日本女优开始做化学实验。
等我凌晨醒过来时,红子光着屁股跪在椅子上,面对着窗口,电脑屏幕的灯一闪一闪的,我先弄出些声响,感觉她已经知道我醒过来了,我问,你在干什么。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我爬起来站到她旁边,外面没什么好看的,就是环路上特别明亮的路灯,和不时开过的车辆,轮胎发出特别大的声音。我在她边上站了会儿,回到床上继续睡。早上再醒过来时,窗外亮了,但应该还很早,红子躺在旁边闭着眼睛,我起来穿好衣服,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我说,我走了。她没说话。
我出门,尽量轻手轻脚地关上房门,关上屋门,关上防盗门,楼道里灰白的颜色,透过窗户看到,楼道外面也是这样的颜色,我走到楼下还有点凉气袭人,很多树在雾气里,几点了呢,我摸了下裤袋,手机不在,忘在红子的枕头下了吧,我很懊恼,不愿意再上去一趟,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顺便告诉她她的鱼快死了吧,建议她扔掉,我可以把它捞起来,下楼时顺便扔掉。
我重新爬楼梯,快到三楼时,听到楼上的门好像响了下,还没到门前,看见手机就摆在门口地上,这太危险了吧,很可能被别人先拿走,我拿起手机,看了下红子的屋门,就下去了,出楼道口时,看了下时间,才7点多一点,我抬头看了下红子的窗户,窗帘还是没拉严,那副画还可以看到,我往地铁站走,路上雾气慢慢浓起来,有变成蒙蒙细雨的趋势,到地铁站我又看了眼时间,快八点了,离我昨天在公交车站等车,过去了22个小时零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