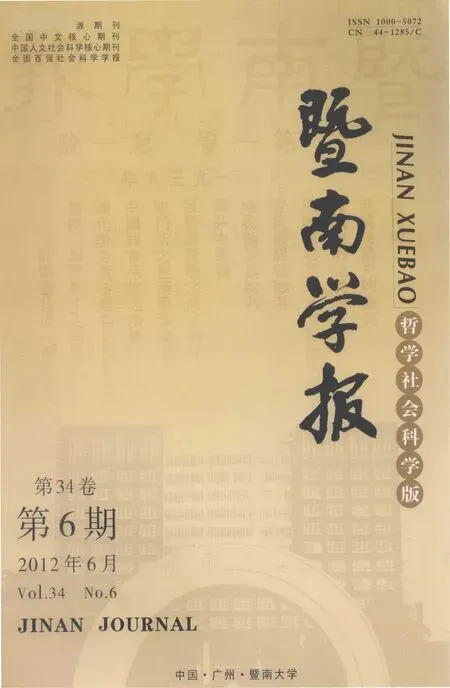水仙花小说中的美国媒体批判
2012-12-18李志萍
李志萍
(暨南大学外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水仙花小说中的美国媒体批判
李志萍
(暨南大学外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水仙花生活在北美华人受到极度排斥的时代。她拒绝接受当时的报刊媒体对华人的“黄祸”式丑化、异化、扭曲的类型化表征,选择用自己的笔“在报纸上为华人作战”。她在短篇小说《天山的知音》和《摇曳的影像》里质疑、批判美国媒体权利的支配使用,鞭挞媒体参与其中的体制化种族主义排华,揭示报刊媒体采用文化帝国主义方式生产有关华人族群文化的知识的不可靠性以及该知识在主流媒体的流通对华人社区造成“暴力性”伤害。
水仙花;美国媒体;“天山的知音”;“摇曳的影像”
水仙花(1865—1914,原名Edith Maud Eaton)被当代北美学者誉为亚裔北美文学先锋、华裔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小说家。她生活在北美华人受到极度排斥的时代,当时的华人和其他亚洲人居于北美种族文化金字塔的最底部,法律地位比非洲人还低[1]。伴随针对华人的五花八门的歧视性法令、法规的,除了暴力排华事件,还有报刊杂志等媒体对华人的丑化、异化表征。水仙花勇敢地选择用自己的笔捍卫在北美的华人,“在报纸上为他们而战”[2]264。除了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报纸上发表无数有关华人的新闻报道外,她在1896—1913年间用“水仙花”的笔名在美国影响重大的全国性报章杂志(Overland,Century,the Independent,Good Housekeeping,New England Magazine,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等)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速写文章,并在1912年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春香太太》(Mrs.Spring Fragrance),使华裔开始在美国文坛有了自己的声音。
当时的《纽约时报》如此评论《春香太太》:“伊顿小姐奏响了美国小说的新音符。她试图向白人读者描述西海岸美国化了的华人、那些与他们通婚的白人以及在这种通婚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的生活、情感与愿望。”[3]这番评论中肯地道出水仙花的作品抗拒、颠覆、重塑当时美国文学有关华人表征程式的重大文学意义。她的创作没有沿用她那个时代的“黄祸”①早在13世纪,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率军两次攻至东欧,欧洲人由此感受到来自东方的危险。19世纪初叶,英国一些学者在书中将成吉思汗蒙古西征称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后来美国的一些学者、作家用“黄祸”指东亚人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包括可能来自亚洲的军事侵略,亚洲劳工对白人劳工造成的就业竞争,所谓的亚洲人的道德堕落,以及有盎格鲁-萨克森血统的白人与亚洲人的基因混合。文学的形式。她把接触到的北美华人社群转化为新的文学叙事视角,以在美国的普通华人(包括妇女、儿童)为故事中的主人公,赋予他们主体性,富有真诚同情心地关注他们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活、思想与情感。基于对北美唐人街及其居民们繁杂的日常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水仙花作品的主题丰富多彩,向读者塑造客观真实的美国华人形象,描绘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北美唐人街详实画卷,真实地展示一个被美国传媒歪曲了的世界,以此来抵制美国传媒对华人及其社区的扭曲表征或客体化。
值得指出的是,有着报刊从业人员视野的水仙花对当时北美传媒对华人及其社区进行歪曲再现背后的根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她洞察到美国媒体通过生产有关华人族群文化的“伪知识”参与美国的体制化种族主义排华,并在她的短篇小说“天山的知音”(Tian Shan's Kindred Spirit)和“摇曳的影像”(Its Wavering Image)里对此进行了批判。而若干年后人们才见到福柯、萨义德论述帝国主义文化生产体系中权力与知识无法逃逸的共谋关系的论著面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仙花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比她同时代的作家或后世的族裔文学作家都更为深刻。只不过她以文学作品作为对不同文化意义进行建构和抗争的场所,所能使用的话语范畴、表述方式受到文类语言以及历史语境的限制。本文将试图剖析她如何使用文学策略在上述两篇短篇小说里质疑、批判美国媒体权利的支配使用,鞭挞传媒参与其中的体制化种族主义排华,揭露报刊媒体采用文化帝国主义方式生产有关华人族群文化的知识的不可靠性以及该知识在主流媒体的流通对华人社区造成“暴力性”伤害。
一、水仙花所处时代北美排华背景及媒体对华人的表征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华人移入美国始于1849年加州的淘金热,移入加拿大始于1858年的弗莱泽河的淘金热。华人飘洋过海来到北美赚钱谋生是因为中国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西方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政治战乱以及经济盘剥。而美国和加拿大都忙于“帝国建设”大业和横贯大陆的铁路建设,劳力稀少是个大问题,引入华人劳工是个解决办法。但华人涌入不久,反华情绪就开始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两国的白人劳工利益组织都游说他们的州或省政府通过五花八门的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令决议以限制华人从业。反华暴乱和驱逐事件时有发生。到水仙花1873年随父母移民至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时,反华运动已在加拿大、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存在了二十多年。
在北美构成反华主力的除白人劳工、政客外就是追求轰动效应的报刊媒体。在水仙花生活的时代,报刊上的新闻文章、社论、致编辑信中大肆渲染华人劳工带来就业竞争威胁和其他社会问题。一些记者热衷于在华人社区猎奇,危言耸听地报道华人阴暗面和华人社区的邪恶犯罪,制造了华人恶魔形象。这些渲染恐华情绪的“黄祸”式报道和当时鼓吹人种优劣的种族主义论调催生了报刊及各种通俗读物中的“黄祸”式“唐人街文学”。“唐人街文学”往往把华人千人一面地刻画为神秘、邪恶、荒谬、古怪、无恶不作、道德沦丧、具有威胁性、不可同化、不可理解、没有人性的异教徒外国人,是与文明持有者白人相对立的“他者”,而唐人街则被表征为滋生犯罪的恶臭沼泽地。这类故事戏剧化地宣扬华人对白人造成的威胁以及华人与白人之间永久的、不可调和的差异——那些把白人定义为体貌、精神和道德方面更为优越、使种族霸权一再得到重申的差异。
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精辟地指出:美国传媒制造、加工、定义了决定我们信念、态度、最终行动的各种形象和信息的流通[4]147。华人、唐人街的负面形象在水仙花所处时代的北美报刊中复制、流通而得以恒化,商业化的媒介生产的偏见型知识取代真正的历史文本进入大众社会思维,对现实生活中的华人造成伤害,使他们的处境日益恶化。报刊传媒对华人的“黄祸”式丑化、异化、扭曲表征把当时的恐华、反华情绪煽得日炽,使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排斥和仇视都获得了表面上的道义支持,成为媒体限制华人这一长期话题的注脚,以知识的形式为美国种族主义排华和内部殖民政策提供堂皇的理由,给白人施之于华人的罪行披上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
对社会现实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报刊从业人员水仙花对美国传媒参与维护美国社会种族秩序显然既有体会又有深刻认知,她在小说《天山的知音》和《摇曳的影像》里表达了这种洞见。
二、《天山的知音》
《天山的知音》开篇即明确地道出美国媒体用以感知和表征华人与白人的双重标准:
如果天山是个美国人而中国是个禁止他踏足的国家,那么他的大胆事迹和令人胆战心惊的冒险就一定会激发出许多报刊杂志文章、小说和短篇故事。作为一个英雄人物,其光芒必定会使杜威、皮瑞、或库克相形见绌。然而,由于是个中国人,美国是禁止他踏足的国家,他仅被美国报纸记录为“一个狡诈的东方人,‘采取邪恶的手段和徒劳的诡计’在躲避我们英勇的海关官员的警戒。”唯一一个对他的经历有特别兴趣的人是芬芳。[2]160
这段引文中的对立性假设既揭露了美国的媒体作为权力机器的一部分与美国政治、法律沆瀣一气的体制化排华,又讥讽了种族主义的本质主义假设。水仙花采用复制美国媒体修辞话语的策略批判其对华人的表征立场。美国报纸用形容词“英勇的”描述作为美国主流社会代表的海关官员,而我们知道海关官员、律师、传教士这些白人权力机制的代表在水仙花的故事(例如与《天山的知音》一并收在《春香太太》里的“在自由之邦”)中不是英雄而是恃强凌弱、趁火打劫之徒。于是宰制性白人文化为英雄主义设定的标准就受到了嘲讽。引文中“狡诈的东方人”和“邪恶的手段”等用语正是“唐人街文学”用来刻画华人的套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恰如其分地描述过西方文化霸权针对东方进行想像使用的词汇传统:如西方本身一样,东方是有着历史和思想、影像、给予它为西方而存在的现实和在场的词汇传统[5]5。水仙花在引文中的对立性假设展示了“唐人街文学”、美国媒体凭借这类词汇传统构建对华人的扭曲表征的荒谬性和非真理性。
美国媒体的修辞话语的谬误性随着故事的展开、人物性格的发展得到更进一步的揭示,“美国报纸”退隐到缺乏洞见的旁观者地位。故事叙述者拒绝美国报纸对华人的修辞设定。读者看到天山确实“狡诈”,因为不公正的限华、排华法律迫使他每次为了见自己意中人都得设计出新方案穿越蒙特利尔和纽约州北部地区之间的边界;同时,这个人物又具有“英雄性”,因为他通常都能成功。在水仙花发表作品之前,美国报刊小说从未把亚洲男人表征为能够拥有浪漫激情和英雄主义[6],相反,这种表征“缺陷”被认为是他们本身人性上的“缺陷”。《天山的知音》还击了这样的偏见。故事叙述者用抒情、诗意的语言描绘天山与芬芳两心相悦地一块散步,描述他对芬芳的强烈爱慕:“——他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只能想着芬芳。芬芳!芬芳!她的脸就在眼前,声音就在耳旁。——他弄明白了自己的情形。他爱芬芳,就像美国男人爱他要娶的姑娘一样。”[2]162天山为见芬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边界:
这次他划着一条印第安人的战用独木舟冲过拉奇恩急流上面一英里处的那条河流,在一个礁石环绕、无法进行追捕的河湾处上了岸。那是一项危险之举,因为他得径直穿过圣-劳伦斯河迅疾的湍流,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汹涌的急流让人感觉他似乎确实得把生命交给怒吼的奔流。但他以不屈的勇气前行,他每次把桨插入水中,都把那只独木舟送到浪涌之上,穿过浪端的白泡沫,直到最后经过诸多冒险到达岸边。[2]161
性格独立的芬芳不听从父命,要自己选择婚姻对象,虽然“她喜欢她父亲就如他喜欢她一样”[2]163——击碎美国传媒关于华人父亲不爱女儿的表征。她似乎也“狡诈”,她勇敢地女扮男装追随天山的足迹溜到边界,故意让自己被捕以便与他一道被遣送回中国。由于她的目的是出离北美而非进入,这种“狡诈”显然与“美国报纸”设想的相去甚远。这对既有浪漫激情又不乏勇气的恋人最终相聚在关押触犯移民法规者的监牢里,正印照了故事开篇对美国传媒与政治、法律合谋的体制化种族主义的讽刺性批判。
三、《摇曳的影像》
水仙花的《摇曳的影像》直接地触及报刊媒体侵扰问题,批判美国报刊媒体采用文化帝国主义方式生产有关华人族群文化的知识的不可靠性以及该知识在主流媒体的流通对华人社区造成“暴力性”伤害。
在这个故事里,帕恩是像水仙花一样有一半华人血统的姑娘,她过世了的母亲是白人,她一直和华人父亲生活在唐人街。马克-卡森是个白人记者,他被报社派去旧金山唐人街搜集素材写一篇特别报道。这个白人记者在帕恩父亲的店里见到帕恩之后就有意接近她,想利用她获知唐人街的一切。获得帕恩的信任及好感后,马克-卡森在她这个桥梁人的带引下进入了他本来无法进入的唐人街社区的一些地方并“因为她的缘故受到兄弟般的招待”[2]102。就在他于月光下唱歌赢得帕恩的芳心和初吻的次日上午,“他开始写几周前承诺给自己供职的报纸的那篇特别报道文章”[2]104。他的文章见报后,帕恩知道自己被背叛了。
小说中试图搜出唐人街秘密以写出耸人听闻的故事来确认、强化读者们头脑里有关唐人街的刻板印象的白人记者马克-卡森是个“唐人街文学”中的老套人物。帕恩看完他写的报道想到的就是这种恒化华人刻板印象和煽动当时流行的“黄祸”思想的报刊记者,她感觉那些“爱她的人视为神圣而神秘的事物被残酷地暴露、无情地展示在嘲笑、不理解的外国人面前”[2]105。
对唐人街社区而言,媒体人马克-卡森是个圈外人,他对华人族群毫无道德责任感。“在记者室里他被称为‘为了一篇报道愿意出卖灵魂的人’”[2]102,因此报刊需求使他只想发掘唐人街可销售的差异性供他的读者们消费,使他们获得娱乐和心理满足。他是带着水仙花时代的人种学理论促成的种族主义文化观这一先入之见来接触唐人街社区的。他深信华人生活方式低劣于白人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被萨义德称为东方主义的文化认知和价值判断使他在月夜里与帕恩独处时望着楼下挂着灯笼、混杂了各色人群的唐人街会不由自主地感叹道:“上面真美!下面真丑!”[2]103。他后来唱给帕恩的小夜曲同样喻示二分对立的文化价值判断:月亮和它破碎的倒影,/它的影子将会出现,/作为天堂爱的象征,/以及这儿摇曳的影像[2]104。他的歌唱的是月亮及其水光中的倒影,“也暗指柏拉图式的理想、‘美’的形式及世俗‘不美’的表现之间的美学划分。唐人街的生活,就像下面‘破碎的倒影’,对应于丑陋表现的较不重要的世俗世界。”[7]268
他武断地替帕恩选择种族身份并努力给她灌输种族对立、隔离思想:“你不属于这。你是白人-白人。”[2]103为使她像他那样疏离唐人街社区,他还把她的“真实自我”与她日常和华人相交往的自我区分开来:“但他们不理解你,”他继续说道。“你的真实自我对他们而言是很陌生的。他们对你看的书-你思考的思想有什么兴趣?”[2]104他借用“真实自我”的概念暗地里把智力生活与西方文化和习得联系在一起,把人类文明理性与华人分离开来。在他的种族对立的思维空间里,东方主义二元论价值分层再次得到隐含的表现:白人被建构为特权的文明持有者,其文化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情感表露方式是衡量别的种族文化优劣程度和人性拥有程度的基准线,华人则被定义为“非我族类”的“他者”。因此他看见帕恩为他的歌声打动而哭泣时会不无偏见地说:“那些眼泪证明你是白人。”[2]104
马克-卡森在为自己写那篇对华人社区造成新闻伤害的报道找借口时也自然地运用东方主义论调:“不管怎样,那只是迷信,这些东西必须被揭露并消除。”[2]106他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以西方的观念和行为为标准,把华人文化斥为非知识或反知识,以确定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武断地认为华人文化需要西方的关注、重构和拯救。他报道唐人街的动机决不是让他的白人读者对其邻居的生活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他的意图是通过在主流报界贬损它而将之予以推翻,使西方文化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存在。他利用帕恩进入了唐人街的一些地方,自以为由此获得了洞见,但事实上他只是基于先入为主的种族主义或东方主义文化差异思想生产有关唐人街的知识,以不尊重和缺乏理解回报帕恩的开阔胸怀和善良仁慈。他的文章透过东方主义描绘唐人街,恒化“黄祸”式扭曲表征,加重白人社区的恐华症和华人社区对白人的不信任。
水仙花在小说里用了“剑(sword)”这一意象来喻示马克-卡森一类的报刊记者及媒体对华人社区造成的新闻伤害。故事中的帕恩不喜欢和白人相处,“像躲避锐利剑刃一样躲避他们好奇目光的仔细审视”[2]102。白人这种把华人当作“奇异”事物来“了解”的种族主义审视构成了一种明显的暴力形式。记者马克-卡森对于唐人街社区既是白人种族主义审视者,又是另一种“剑”的持有者——他手中的笔是媒体权力的象征,可以把他的白人种族主义审视转化为报刊媒体中流通的华人表征和有关唐人街文化的知识,让读者在阅读想像中也体验把华人生活当作“奇异”、落后事物进行白人种族主义审视的快感,重申白人优于华人的神话,以真理的形式定义一种有利于白人的种族关系,当然这所谓的真理用福柯的话来说“不过是围绕权力机制编制的真理话语”[8]。帕恩看到报上他的揭露性文章,终于明白他是把唐人街当作“美”的对立面——丑陋表现的世俗世界——来表征,他对唐人街社区的表征是扭曲、“摇曳的影像”。她痛苦地喊道:
“‘被出卖了!被出卖了!被出卖成个出卖者了!’——是无意识中干的吗-那残忍的打击?啊,他很清楚那把刺透她和其他人的剑会把所有其他人的疼痛送到她的内心深处。没人比他更清楚,被他称作‘一个白人女孩、一个白人女子’的她宁愿自己赤裸的身体和灵魂被暴露,也不愿那些爱她的人视为神圣而神秘的事物被残酷地暴露、无情地展示在嘲笑、不理解的外国人面前”。他对这一切如此了然,如此清楚,漫不经心地唱歌俘走了她的心,然后带着她印在他唇上的吻,微笑着转身戳了她一刀。[2]105
水仙花使用“刺透”、“疼痛”、“残酷”、“无情”、“戳”等词汇将华人社区遭受新闻伤害的暴力性诉诸笔端,强调了报刊媒体之“剑”联手种族主义或东方主义话语一道更进一步地蹂躏弱势民族。
四、结 语
水仙花生活在北美反华活动甚嚣尘上、排华愈演愈烈的时代。当时的报刊传媒把华人表征为“黄祸”,以宰制性的文化霸权生产出有关华人的偏见型知识信息进入公众社会思维,操纵了人们的意识,加剧恐华情绪的蔓延,鼓励种族主义的排华和内部殖民政策,对华人利益造成伤害。水仙花对北美报刊传媒利用扭曲的华人表征构建大众意识显然有清醒的认识,她勇敢地拿起笔为华人辩护。她在短篇小说《天山的知音》和《摇曳的影像》里直接批判美国媒体权力的使用,鞭挞传媒参与其中的体制化种族主义。她用自己的声音挑战和对抗北美报刊传媒牢不可破的合唱背景,赢得了伊莉莎白-艾蒙斯(Elizabeth Ammons)这样的评价:“水仙花冲破了万马齐喑般的死寂和系统化的种族压迫,发现了她自己——创造了她自己的声音——这是本世纪初美国文学史的胜利之一。”[9]105
[1]Annette White- Parks.Sui Sin Far/Edith Maude Eaton:a Literary Biography[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Foreword.
[2]Sui Sin Far.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M].Edited by Amy Ling and Annette White-Parks,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3]“A New Note in Fiction,”[N].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7 July 1912.
[4]Randall M.Miller.Ethnic Images in American Film and Television[C]∥Pennsyvalnia:Science Press,1978.
[5]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
[6]Dominika Ferens.Tangled Kites:Sui Sin Far's Negotiations with Race and Readership[J].Amerasia Journal 25:2 1999,PP116-144.
[7]Rachel C.Lee,Journal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Asian A-mericans and Literary Responses,1910 -1920[C]∥Edited by King-Kok Cheung,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8]周祥林.福柯晚期思想的伦理关怀[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4).
[9]Elizabeth Ammons.Conflicting Stories: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I106.4
A
1000-5072(2012)06-0032-05
2009-09-23
李志萍(1970—),女,江西井冈山人,暨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
广东省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汉语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批准号:06JDXM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