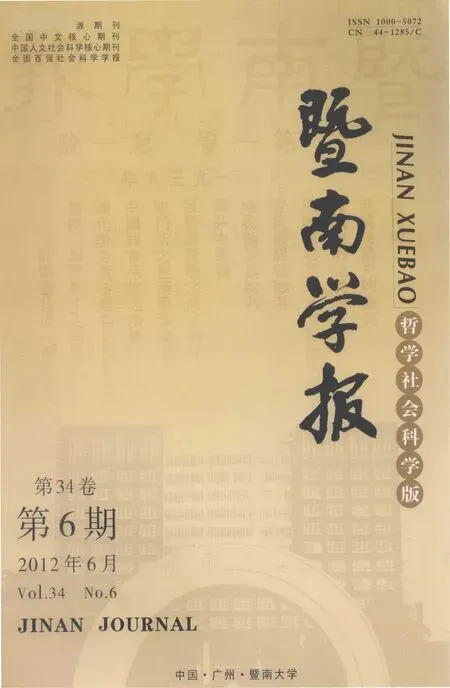论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特点
——兼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分立”观与“语词兼收”观
2012-12-18曾昭聪
曾昭聪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论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特点
——兼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分立”观与“语词兼收”观
曾昭聪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词目是辞书中被解释的对象,明清俗语辞书收录词目的特点一是“字”、“词”、“语”兼收,二是“词”“语”为主,“词”占重头。从明清俗语辞书“语”“词”兼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认为辞书编纂中“语”“词”兼收与“语词分立”是可以并存的,明清俗语辞书的“语”“词”兼收现象不能简单地判为不足。
明清俗语辞书;词目;特点;语词分立;语词兼收
所谓“词目”,是“词语条目”的简称,即辞书中被解释的对象。在语文辞书中,“词目指的是词典中要加以诠释借以建立词条的任何语言单位。语文词典的词目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素,也可以是词组,甚至也可以是句子,但主要是词。使用汉字或近似汉字的,词目也可以是‘字’。”[1]93词目是辞书的叙述对象,也是辞书进行检索的标志[2]40;词目是辞书的起点与最重要的内容,辞书中词目的收录原则关系到辞书的性质与质量。词目应有“唯一性”,即在某一部辞书中,词目是“字”、“词”、“语”中的某一种,但明清俗语辞书有所不同,本文将其归纳为两个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分立”问题。
一
明清俗语辞书以“俗语”为收录对象,这个“俗语”包括俗语词,也包括熟语。除此以外,明清俗语辞书中还收录有一定数量的“字”。也就是说,明清俗语辞书收录词目的特点之一即是“字”、“词”、“语”兼收。
所谓“字”,即以“字”为词目,释语以解释字形或字音为主(少数以“词”为词目但释语仅涉及字形字音者亦为此类);所谓“词”,以“词”为词目,释语以解释词义或列举体现词义的书证为主;所谓“语”,则以熟语为词目。明清俗语辞书中收有明确的“字”类的有《目前集》、《通俗编》、《证俗文》。
《目前集》有“俗字部”。该部词条正文前有一“小序”:“《中原音韵》为词曲而设也,而所收皆诗韵之字,作者遇俗字,每每杜撰。今略检录于左,好事者或有取焉。”其前八条是:“风颵、鞭鞘,俱萧韵。”“潲,雨溅,音哨。”“晒,也。日干物,所卖[切],泰韵。”“雷,呼骨切,质韵。”“霎,雨声。又片时也。色洽[切],合韵。”“渗,寒貌。沁韵。”“晱,失冉切,晱电。通作‘’。琰韵。”“颴,似缘切,风转也。”[3]2150可以看出,《目前集》以释字音为主。
《通俗编》卷三十六为“杂字”类。举其前五条于下。“雩,《尔雅·释天》注:江东呼蝀为雩。《音义》云:雩,于句切。[按]今俗呼蝀若‘候’,或若‘吼’。《丹铅录》、《田家杂占》俱因‘候’音作‘鲎’,《湖壖杂记》因‘吼’音作‘’。而‘鲎’为闽海水族之名,‘’则蚍蜉也,与‘蝀’何相涉耶?俗音盖本‘于句’之切,而读‘句’为‘彀’,若《大雅》‘敦弓既句’之‘句’耳。”“凙,《楚辞·九思》:霜雪兮漼溰,氷冻兮凙。‘凙’音‘铎’。今呼氷檐为‘凙’,是此字。”“趖,《说文》:走意。苏和切。欧阳烱词:荳蔻花开趖晚日。是也。杨维桢《游仙录》言日西从‘夕’旁,非。”“霉,音眉。《说文》:物中久雨青黑。《博雅》:败也。《楚词·九叹》:颜霉黧以沮败。《淮南·修务训》:尧瘦臞,舜霉黑。《古隽略》:黄梅雨之梅当为霉,因雨当梅熟之时,遂讹为梅雨。《臞仙肘后经》:芒种逢丙入霉,小暑逢未出霉。用此字。[按]今俗所用‘霉’字,《正字通》始收载。”“踔,《史记·货殖传》:上谷至辽东地踔远。索隐:踔,音勅教反。《卫将军传》:逴行殊远,而粮不绝。逴与踔同。《说文》作‘’。[按]今作窵远,‘窵’为窅深,非远也。《元典章》:‘大德间奏过受了宣勅,嫌地远窵不赴任的後,不叙用。’已如今误。”①原书“按”字,标点本加方括号,今引用时从之。又,末例引《元典章》,排印本原标点误作“……不赴任的,後不叙用”,按“後”为语气词,表假设,故当于“後”后点断。今正。[4]789-790按,“雩”条释“雩”各种俗体之音义;“凙”条释字音兼及当时方言本字;“趖”条分析字形;“霉”条辨正俗字;“踔”条则辨本字、同源字与通假字。由此可见,《通俗编》关于“字”的解释兼及形音义。
《证俗文》有关于古字、奇字、别字、误字的考释。卷十三有“古字”,如“,《礼·郊特牲》‘所以交于旦明之义也’,注:‘旦当为神,篆字之误也。’顾宁人《金石文字记》曰:神,古碑多作,下从旦。《庄子》有‘旦宅而无情死’(《大宗师篇》),亦读为‘神’。盖昔之传书者遗其上半,因讹为‘旦’尔。”[5]2453卷十四是“奇字”,如“,音矮,不长也。”“䦟,音稳,坐于门中稳也。”“,亦音稳,大坐亦穏也。”“仦,音奶,小儿也。”[5]2457卷十五是“别字”,如“隋,原作随。文帝以周齐奔走,不遑宁居,故去辵作隋。”“吴,《吴志·薛综传》:无口为天,有口为吴。案此虽借为谐语,然可见当时已有此字。”“斋,《篇海》:同‘齋’。案此疑亦俗字,艸书有之。”[5]2458卷十六是“误字”,如“杜十姨,杜拾遗之讹。”“先生号甪里,李济翁《资暇录》云:汉四皓,其一号角里先生,角音禄,今多以‘觉’音呼,误也。……案《礼·丧大记》‘君大夫鬊爪实于绿中’注:‘绿当为角声之误也。’是知‘角’古音禄,不独‘角里先生’之‘角’从此读也。”[5]2464,2465《证俗文》关于古字、奇字、别字、误字的考释主要以字形和字音为主,其中“奇字”、“别字”与我们今天的“俗字”概念基本一致。
明清俗语辞书中未有明确的“字”类的,往往也暗含一些关于“字”的考释。例如清梁章钜《称谓录》卷八“女之夫”类目第一条是“壻”,第二条是“聟”:“案:此皆壻之异文也。《礼记·昏义》‘壻执雁入’,《释文》:‘壻,一本作聟。’《唐公房碑》‘期聟谷口山上’,王羲之《女聟帖》‘取卿为女聟’,皆作聟字。杨子《方言》:‘东齐间谓之倩’,《风俗通》‘怪神女新从家来’及唐第五公等《华岳硕碑》题名,皆作字。《诗》‘有女同车’,笺:‘壻御轮三周。’《释文》‘壻,一本作。’《仪礼·士昏礼》注‘壻之室也。’《释文》又云:‘壻,一本作。’《左》文八年传‘公壻池之封’。《释文》又云:‘壻,一本作。’据颜光禄《干禄字书》云:‘聟、、壻三字,上俗,中通,下正。’则壻①按,此“壻”字刻本如此,當為“”字之誤。亦在通俗之例矣。”[6]122该条释语纯为文字考证。又如陈鳣《恒言广证》卷二“单字类”中有数十处指明“俗字”,其它地方亦常指出“俗字”。
再以清梁同书《直语补证》[7]为例,可以以之为代表看出明清俗语辞书中字、词、语分别所占比重。先列出《直语补证》所录之条目②以下所列举条目中,凡是《直语补证》原文另起一行者(即表明是不同词条者)均加顿号隔开;不另起一行者(即两个或多个词目列在同一条目中),不论“字”、“词”或“语”依原文以空字符隔开;原文不另起一行、本为不同词条但中间不空格者,引述时加斜杠标示。下文举例称引时为表明不同词条,原同一条目中的“字”、“词”或“语”间不论是否有空白均改为相应的标点符号。:
从词目上来看,《直语补证》共列416个词目作为解释对象。所解释的“词”中,大多以单词立目,但有的一个条目中实际上包含几个词条,如“管家、长随”、“周年、月尽”,分别有两个词条,“茶筵、祭马下、烧纸”有三个词条,而多者达七个词,如“媳妇、外翁、外婆、伯翁、叔翁、伯婆、叔婆”。所解释的熟语中,有单条立目者,如“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有数条共立一目者,如“得志猫儿雄似虎,败翎鹦鹉不如鸡。火烧纸马铺,落得做人情。龙居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三条俗语共存于一个条目。甚至有以民间歌谣立目者,如“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两个合梳头;大个梳做盘龙髻,小个梳做杨篮头。”分而计之,则共有字、词、语条目452条(除去重复的“先生”、“媳妇”两条不计)。
《直语补证》是典型的“字”、“词”、“语”兼收的俗语辞书。
其中的“字”,如“南无 迁葬”条:“并见《广韵》。无、南无,出释典模字组,莫胡切。迁、迁葬,千字纽,苍先切。今人不知,一以为别字,一以为俗字矣。”(P898)按,此释“南无”之“无”、“迁葬”之“迁”之来历,认为“无”非别字,“迁”非俗字。“国、、齐、斎、斈”条:“今市侩书之,皆起于宋。见孙奕《示儿编》云(唐历城县千佛崖石刻,有‘家国安宁’语,从方内王,知唐已然矣)。”[7]917按,这里所解释的是“国、钱、齐、斋、学”五个汉字的俗字字形。又如“萨四十”条:“北方称三作开口声。《北史》:李业兴使梁武帝,问其宗门多少,答曰:萨四十家。政与此同。”[7]887此释方言读音。也有的是在词的释义中兼及文字形体或读音的,如“”:“钟鼎字,音乃,乳也。今人呼乳为奶,呼服娘为奶娘,亦有所自。”[7]876释义兼指读音。又如,“媳妇”一词两见,一是“媳妇外翁外婆伯翁叔翁伯婆叔婆”条[7]906,讨论词义;后面又有“媳妇”一词[7]906,则专门讨论“媳”字字形。专门从“字”的角度进行解释的内容相对较少,基本上祇有上面所列数条。
其中的“词”,大多是讨论俗语词意义或来源,如“正经”:“《论语》:‘攻乎异端。’疏:‘言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深也。’”[7]876此指俗语词出处。又如“泡”:“凡物虚大谓之泡。《方言》:泡,音庖,‘盛也,江淮之间曰泡’。注:‘肥洪张貌。’至今犹然。俗音如抛,庖之讹耳。”[7]879此释义兼指出俗语词之出处。从“词”的角度进行解释的条目是最多的。
其中的“语”,即熟语、歌谣。例如:“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共收四音节以上成语、惯用语74条。
“字”“词”“语”兼收是汉字形音义结合的根本特点在辞书编纂中的具体表现,也是字词不分的表现。由于汉字汉语有其特殊性,可以由形析义,从声探义,所以在词义的探讨中往往会与字形字音相联系。例如《俚言解》卷二“糖”条:“音情。《韵府》注:滑糖也。頬聚。《音韵》注:清糖也。《集韵》注:饴也。饴亦作,以米糵煎汁成糖。《汉书》‘含饴弄孙’是也。与餳字不同。从易,餳从昜,音唐,即古糖字。如晹暘二字不同,晹音释;埸場二字不同,埸音奕也。范至能诗:‘凫子描丹笔,鹅毛剪雪英。宝糖珍粔籹,乌腻美饴。’英、皆庚韵。”[8]30按,《俚言解》此条探讨词义,兼辨字音与字形,所以应该算是“字”“词”综合的条目。①然其所辨亦并不准确。《汉语大字典》“”注:“同‘餳’。”《说文·食部》:“餳,饴和馓者也。从食,易声。”钮树玉校录:“此即糖之正体,当从昜作餳。”清程际盛《骈字分笺》卷上“饴餳”注:“、餳一物,初无二义,其分为二字两音,当自陈以后始也。”
二
明清俗语辞书中词目的收录原则之一是“字”“词”“语”兼收。从总体上来看,收“字”的不太多,像上举的《直语补证》虽是“字”、“词”、“语”兼收,但以“词”为主。除上举收“字”诸辞书外,其他明清俗语辞书多是“词”“语”兼收而以“词”为重,所以我们概括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特点之二是:“词”“语”为主,“词”占重头。具体来说,则有的是以“词”为主,有的以“语”为主。只有少数是仅收“词”或仅收“语”的。
明清俗语辞书中绝大多数是“词”“语”兼收而以“词”为主。这里以清罗振玉《俗说》[9]为例。该书所收全部词条不多,分别列举于下:
太阳、月宫、雷公电母、旋风、天造地设、下雨、下雪、气候、路上、水脚、黄泥、地底、街头、半路、外国、鞭春、打春、守岁、新正、月内、多时、平素、平常、期限、二月二龙抬头、叔父、佳子弟、男人、元配、继配、亲兄弟、侄女、堂兄、堂弟、表兄、表侄、织造、童生、罚俸、履历、告身、书办、告示、赏格、准、关防、号薄、白契、德政碑、脱鞾、抄书、句子、义塾、学生、仿本、卷子、一本、一部、曲子、书目、行状、八行书、小队、马队、请安、交杯酒、看新妇、三朝、满月、后事、照尸、影、辞灵、丧出然柴、柩底置孝经、合葬、铭旌、石人石马、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火葬、普天同庆、全福、反叛、声名、名声、不中用、穷人、铁汉、寒士、恶少、尊贵、等候、生怕、从小、舒徐、出去、出来、过来、上来、下来、回来、分别、计策、殴打、相好、得罪、富足、失收、判命、奔波、横事、性暴如雷、留意、快活、自由、天分、蓬头、梳头、神头鬼面、鹁角、玉体、剃面、闻香、身材、经手、手心、手里、八字眉、眉心、一毛不拔、气喘汗流、劲、志、小便、大便、出恭、不入耳之言、老爷、乃兄、息妇、孙息妇、大人、卑职、泰水、亲家母、晚生、老师、某甲某乙、太岁、土地神、宅神、刘猛将军、幽冥、纸钱、焰口、观音经、道士、法师、小沙弥、佛事、功德、行香、香火、合掌、礼拜、还俗、来生、纸房子纸人纸马、生活、国手、推命、看命、流年、圆光、地理、医称郎中、剃头称待诏、儒医、药剂、瓦匠、船家、妃子、老婆、老娘、梳洗、匀粉、房钱、蝇头微利、鹅眼钱、毛钱、债主、交、城墙、浴堂、场屋、店面、学堂、中门、屋檐、粉壁、门扇、公馆、门地、瓦屋、当中、中央、四角、傍边、前头、外头、邻居、跨竃、牙门、家堂、后门、隔子、石磉、门限、牛屋、衣纽、衣服、帽檐、纱帽、丝线、真珠、背心、镮子、钐子、朝衣、皮衣、帽子、兰干、茧丝、袴裆、细布、手帕、针线、袈裟、绳床、竹床、竹床子、毯子、蒲合、床脚、床边、床头、香案、灯台、上灯、点灯、粪船、抽屉、倚子、马杌、杌子、材、灵柩、水车、盒子、竹火笼、手炉足炉、笔架、笔头、笔床、镇纸、界尺、水牌、笔筒、千里镜、红纸、艸纸、芦席、粉合、折扇、扇面、扇柄、宫扇、竹片、酒海、茶船、盘子、迭子、甆器、石狮子、火石、腊烛、白腊烛、花腊烛、金刚钻、麻绳、杂货、刀子靶、粮食、麻油、腊八粥、干饭、就酒、粉团、薄饼、包子、茶食、圆子、糖圆、馓子、果子、月饼、春饼、狮猫、水牛、鹊子、雀子、九头鸟、鹅蛋鸭蛋、鱼秧、田鸡、水鸡、苍绳、蚊子、橘子、种子、小麦、竹子、仙果、瓜子、根须、烟火、地老鼠、起火、球灯走马灯、赌钱、一张、一下、一条、六十花甲子、七旬、元来、诚如、情知、自然、蚤已、居然、什么、恐防、神气、粉碎、气愤愤。
上述词条是《俗说》所收全部词条,共347条。其中“字”1条:“准”①该条释语:“按《五经文字》云:《字林》‘準’作‘准’。则‘准’為‘準’之俗体。翟氏《通俗编》引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说,误。”[9]327,馀皆为“词”或“语”。真正的“语”祇只14条。这样统计,“词”(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共有332条。因有少数多音节条目实际上是两个词,如“雷公电母”、“鹅蛋鸭蛋”、“球灯走马灯”。而有的多音节条目实际上是一个双音节词:“医称郎中”、“剃头称待诏”,因把释语放在了条目上,实际上词目应是“郎中”、“待诏”。所以《俗说》所收“词”实际上还不止332条。可见,《俗说》中除少数条目为“语”之外,绝大多数为“词”。
“词”“语”兼收而以“语”为主的辞书可以清郑志鸿《常语寻源》[10]为例。该书分上卷、下卷。上卷又分甲册、乙册、丙册、丁册,下卷双分戊册、己册、庚册、辛册、壬册、癸册。甲册收“天赐”、“风闻”、“土著”、“玉成”等双音词142条。乙册收“孔方兄”、“作天公”、“表表者”、“富家翁”等三音节词(含部分短语)108条。丙册收“在掌握中”、“入我彀中”、“妙手空空”、“善始善终”等四音节词语(以成语为主)106条。丁册收“人力回天”、“坐井观天”、“衣钵相传”、“卧雪吞毡”等四音节词语(以成语为主)99条。戊册收“逢人说项”、“恭谨无比”、“皆大欢喜”、“见猎心喜”等四音节词语(以成语为主)101条。己册收“百发百中”、“同床各梦”、“不过罚俸”、“出人头地”等四音节词语(以成语为主)118条。庚册收“迭床架屋”、“势如破竹”、“胸有成竹”、“推心置腹”等四音节词语(以成语为主)80条。辛册收“百金中人产”、“民以食为天”、“家常饭好吃”、“习惯若自然”等五音节惯用语130条。壬册收“公生明偏生闇”、“住东头住西头”、“东家食西家宿”、“只问人不问官”收六音节惯用语78条。癸册收“事无不可对人言”、“放下屠刀便成佛”、“好官不过多得钱”、“书中自有黄金屋”、“宁为鸡口勿为牛后”、“三十年老娘倒绷孩儿”、“三世做官方知穿衣吃饭”、“智者千虑”四句、“欲人勿知”四句等七音节至十六音节惯用语106条。总计1068条。由此可知《常语寻源》以收录四音节词语为主,共504条,占全部词条的47%多。
三
明清俗语辞书在词目的收录特点上,撇开极少数“字”不说的话,主要是“语”“词”兼收。而当前学术界有一种“语词分立”的观点,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原则似与之矛盾,而事实上,我们认为两种观点是并行不悖的。以下试略加讨论。
“语词分立”观的主要倡导者温端政先生指出:
目前语词类的辞书越来越多,分工也越来越明确。总的来看,“语”类的辞书不见有收“词”的,而“词”类的辞书几乎都收到一定数量的“语”。……应当说,在过去“语”类辞书相当缺乏的情况下,以词为主的词典兼收“语”,是可取的。但现在看来,在语文辞书分工越来越细致的条件下,再这样做,就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拿公认的的优秀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来说,在收“语”方面,包括词目的选择和释义,在同类辞书中是最具有权威性的。但仔细推敲起来,仍有一些问题。表现在:1.所收的“语”不够平衡,存在残缺不全的问题。……2.所收的“语”,缺乏明确的标准,带有某种程度的任意性。……3.所收的“语”在释义上有的缺乏准确性。……实行“语词分立”,让词典集中收词,全力做好词的释义工作,解释好每个词汇单位的意义,使词典真正成为词汇研究的成果,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上述问题。“语”的收集和整理,让给“语典”去做,让“语典”成为语汇研究的成果。不论从眼前来说,还是从长远来说,这都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做法。[11]
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对辞书编纂具有参考作用。前面我们说到,明清俗语辞书是“语”“词”兼收的,那么这种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兼收模式是不是就完全不可取呢?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可取,我们认为“语”“词”兼收也有其道理:
其一,“语”“词”兼收符合中国传统语文辞书的编纂体例。作为俗语辞书而兼收“语”,这是中国辞书史的传统做法,从明清俗语辞书到当代权威性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均是如此。因为“语”多有地域性,有常用与不常用之别,在一般的词典中收有部分地域性不明显而在生活中常用的“语”,对读者查询、学习来说,未必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温端政先生说《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语’不够平衡,存在残缺不全的问题”,“所收的‘语’,缺乏明确的标准,带有某种程度的任意性”,“所收的‘语’在释义上有的缺乏准确性”,这不是《现代汉语词典》不应该收“语”的理由,而是应当改善其收“语”的三个方面。也就是说,《现代汉语词典》应当在收“语”的范围、标准及释义方面再下一番功夫,使其更加适应其阅读对象的需要。当然,《汉语大词典》或其它面向不同阅读对象的辞书也一样。
其二,“语”“词”能否兼收与“词”和“语”的划分密切相关。一方面,“词”的判定标准从理论上来说虽然容易明确,但实际上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学界关于某些专书的词的数量的认定往往有所不同,原因即在此。以三字组合的语言单位为例,“三字组合中为学界视为词的单位和大于词的固定短语的单位在数量上不分轩轾,如何将它们正确地划分开来就已是令人颇费斟酌的问题,而将三字组合中的一部分视为词,另一部分看作是自由短语,就使问题更趋复杂,由此产生出来的三字组合词汇单位类型的判定问题就尤显突出和重要。”[12]94-95当然,双音节语言单位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已经收入辞书中的双音词,就有一部分被人认为并不是“词”。因此,辞书编纂中,对于“词”和“非词”的判定,往往要凭语感。虽然不同的人语感也有所不同,但“根据多数人的语感,总会显示出一种倾向性,这恐怕也就是目划分词和非词的唯一可行的依据。”[1]94正因为“词”“语”均为语言单位且有时不容易区别开来,所以,要在辞书编纂中实行“语词分立”的原则,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读者使用角度来说,要先判定一个查找对象是“词”还是“语”然再去找“词典”或“语典”,其难度同样是可以想见的。另一方面,“语”也不可笼统视之,而是划分为两个部分。“熟语包含两大类异质的单位,言语性的常语——谚语、名言(包括格言、警句)、套语、俚语(成句子的俚语);语言性的固定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名语、专门用语、准固定语。常语……祇具有搬引性而不具复呈性。固定语则与词的功能相当,没有句调(特别是句末语气调),含义体现概念,具有复呈性,一般充作句子成分。”[13]46可见熟语中的“语言性的固定语”在功能上与词一致,若要从“词典”中抽出来,不论在词典编纂还是在使用上都有所不便。因此,针对不同的读者,我们可以编纂单纯的只收录熟语的“语典”,但似不可能编纂出单纯的“词典”。在“词典”中“语”“词”兼收,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其三,“语”“词”兼收符合语言哲学的“意义使用论”。所谓“意义使用论”可以简略归纳为:“一个词语的意义由它所在的语境所决定,表现为该词语的使用,甚至表现在言语的用意之中;孤立的、静态中的词语难于确定其本身的意义。”因此,在辞书编纂上,“词目本身应该尽可能多地反映词语实际运用的情况。除了收录词或词素之外,也应该收录固定词组、习语和短语。这是因为后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词语的使用环境,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词义(许多词组、习语或短语的意义并不是其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和揭示词语的性质(主要是搭配能力)。”[2]40-41从外语词典来说是这样,从明清俗语辞书来说也是这样。
正如温端政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语词分立’并不意味着语、词对立。把语和词绝对地对立起来,人为地割断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样是不可取的。语和词至少有三点是一致的:1.都是语言单位。2.都是语言的现成的‘建筑材料’。3.都负载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传统文化。”[14]71-72我们从明清俗语辞书“语”“词”兼收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分析之后认为,“语”“词”兼收与“语词分立”是可以并存的,明清俗语辞书的“语”“词”兼收现象不能简单地判为不足。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是尊重传统、尊重现实;二是加强汉语词汇学理论研究尤其是“语”、“词”的区别性研究,提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水平。
[1]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2]何家宁.语言哲学的“意义使用论”对词典编纂的启示[C]∥黄建华,章宜华主编.亚洲辞书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明)赵南星.目前集[M].长泽规矩也编.明清俗语辞书集成[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清)翟灏.通俗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5](清)郝懿行.证俗文[M].长泽规矩也编.明清俗语辞书集成[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清)梁章钜.称谓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6.
[7](清)梁同书.直语补证[M].通俗编(附直语补证)[C].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8](明)陈士元.俚言解[M].长泽规矩也编.明清俗语辞书集成[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清)罗振玉.俗说[M].《迩言》等五种[C].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0](清)郑志鸿.常语寻源[M].《迩言》等五种[C].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1]温端政.论语词分立[J].辞书研究,2002,(6).
[12]周荐.三字组合与词汇单位的确定[A].词汇学词典学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3]舒辛撰写.现代汉语词汇研究[A].林焘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4]温端政.再论语词分立[C]∥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责任编辑 范俊军 责任校对 王 桃]
H131
A
1000-5072(2012)06-0139-08
2012-01-01
曾昭聪(1969—),男,湖南洞口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汉语词汇训诂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批准号:09BYY048)。究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但相关研究尚付阙如。因此,本文拟对其收词特点(即收录词目的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明清时期的俗语辞书数量很多。所谓俗语辞书,这里指的是记录并诠释汉语俗语的辞书。其中较著名的是由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辑集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他从日本公私庋藏的中国古籍中精选有关书籍二十种,于1974年由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这二十种辞书是(按《集成》收录的先后顺序):明陈士元《俚言解》、明陆嘘云《世事通考》、清顾张思《土风录》、清梁同书《直语补证》、清易本烺《常谭搜》、清史梦兰《异号类编》、清梁章钜《称谓录》、清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清伊秉寿《谈征》、清高某(静亭)《正音撮要》、清唐训方《里语征实》、清蔡奭《官话汇解》、清北洋陆军督练处《军语》、民国周起予《新名词训纂》、民国李某(鉴堂)《俗语考原》、明张存绅《(增定)雅俗稽言》、明赵南星《目前集》、明周梦旸《常谈考误》、清郑志鸿《常语寻源》、清郝懿行《证俗文》①长泽规矩也在《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中为每一部辞书作了解题,其中有误题作者姓名、朝代、书名之处,这里已作了更正。详笔者所撰《长泽规矩也〈明清俗语辞书集成〉解题补正》,《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9期。。除收入《集成》者外,明清俗语辞书还有不少。例如,在《集成》于1974年在日本出版之前,北京商务印书馆已先后排印出版了《恒言录 恒言广证》(1958年)、《通俗编(附直语补证)》(1958年)、《〈迩言〉等五种》(1959年),而此后中华书局亦排印出版了《称谓录亲属记》(1996年)、《通俗常言疏证》(2000年)。
明清俗语辞书在中国辞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以收录当时的通俗常言为主要任务,并且在词语的最早用例、词源与理据、词语的文化内含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语料,值得我们重视。从编纂体例角度来说,明清俗语辞书也很有特点,在辞书编纂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今天的辞书编纂理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