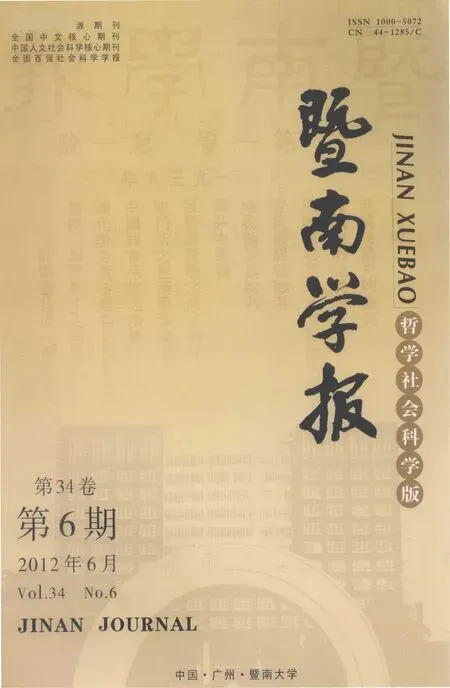情绪 真率 音乐
——郑振铎对新诗路向的追求
2012-12-18陈振文
陈振文
(福建江夏学院人文系,福建福州 350108)
情绪 真率 音乐
——郑振铎对新诗路向的追求
陈振文
(福建江夏学院人文系,福建福州 350108)
郑振铎是中国新诗的拓荒者之一,集论、创、译于一身。他的诗论丰富、深刻而富开创,是新诗史上重要的文论,涵盖了新诗的本体论、创作论以及新诗的鉴赏和批评等主张。情绪、真率和音乐美是郑振铎新诗本体论、创作论与审美标准的内核。
郑振铎;新诗;诗论;审美标准
郑振铎(1898—1958),字警民(铎民),笔名西谛、C.T.、郭源新、玄览居士等,祖籍福建长乐,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曾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郑振铎自“五四”始创办、编辑各种社会文化和文学刊物。1920年代初,公开倡导“血和泪的文学”乃至“革命文学”,并撰写大量理论文字为新文学护航。1930年代中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文学论争集》,所撰导言更是一篇“极好的现代新文学小史”[1]381。郑振铎对初期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是中国新诗的拓荒者之一。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郑振铎诗歌的研究比较薄弱,通常认为郑振铎对新诗的最大贡献是在对外国诗潮、诗人和诗作的译介方面。郑振铎虽然并不以诗名世,但在新诗开拓者中却是资格较老,且集论、创、译于一身的作者。在新诗运动史上,相较创作的成就和影响,郑振铎的诗论与译介显得更为突出。郑振铎有关新诗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包括《论散文诗》(1922)、《诗歌之力》(1923)、《何谓诗》(1923)、《诗歌的分类》(1923)、《新与旧》(1924)、《抒情诗》(1933)等,是新诗史上重要的文献,涉及了诗的本体论、创作论以及新诗的鉴赏和批评等问题,对什么是新诗,诗歌的本质与特点是什么,新诗与旧诗的区别及其与散文的区分,什么样才是一篇好的诗歌作品,诗人和革命家的同质性,等等,都作了系统而周密的论述。在新诗历经百年而命运坎坷的今天,检讨新诗的创作实验和理论探索,重新审读郑振铎的诗论,其诗学价值依然熠熠闪光。
一
中国的文学革命是以新诗开始的。五四时代暴飙突进的精神,反映在文学上即追求摆脱一切旧套,打破传统诗歌格律的限制成为新诗人要推倒的第一扇墙。但由于受传统诗词的长期浸染,“旧文学的习惯太深,故不容易打破旧词调的圈套。”[2]2这扇墙也最牢固。郑振铎在《〈雪朝〉短序》中鲜明地挥出了一击重拳:“诗歌是人类的情绪的产品……诗歌的声韵格律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要一概打破。因为情绪是不能受任何规律的束缚的。”[3]3这段话的诗学价值不在打破“诗必有韵”的传统,因为早在1917年,几乎与新诗的出现同步,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就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的主张。其意义更在于刷新对诗歌本质的认识,突出强调了“情绪”。传统诗论“诗言志”,后人虽也训“诗”为“志”,训“志”为情,但还不是纯然的个人内心的情、意。郑振铎后来还进一步解释这种“情绪”的特质在于:它常以“暗示的”文句“直接引起读者的情绪”。和其它体裁的文学有着区别:“论文——文学化的——所含的情绪的要素较少”、“戏曲则是表现的作品,不如诗之含有最多量的情绪的元素”、小说虽是史诗的变化,但“是叙述的。”[4]342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有一句至理名言:“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的情绪”,这一经验尼采用一部书去阐述,郑振铎在认同中给予了进一步发挥,使人一见就明白诗的性质。
有破总要有立。推倒了格律这扇墙之后,所有的论者都面临着回答“什么是新诗”。对此,刘半农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胡适之的《谈新诗》、周无的《诗的将来》、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俞平伯的《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等有关新诗的论文中多有阐发。但对比他们之间对新诗的本质和要素的概括,相去较大。这里选择同期表述接近且类似的几个论者进行比较,来解读郑振铎的主张。郑振铎提炼了构成新诗的四个基本元素,用公式表示就是:诗=情绪+想象 +思想 +形式[4]340。王独清的主张是:诗 =(情 + 力)+(音 + 色)[5]871郭沫若的回答是: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6]8关于诗的“形式”,郑振铎解释为“最能传达,最美丽的形式”,再比照他个人的创作,可以理解为涵盖了“适当的文字”、“音”、“色”。如果用概括文学的一般公式“内容+形式+表现”来解读三者对诗的认识,其要素是相似的。郭沫若把“直觉”和“情调”列首,是从诗学的逻辑起点,也就是美学家所谓产生“诗的境界”的二个条件来认识诗的本质,在这一点上是受到克罗齐美学的影响。相对郭氏,郑、王把“情绪”前置,与中国传统诗论贴得更近,诗人必先情动于中而才形于言,是从诗歌的“力”来认识新诗。郑振铎对诗歌之“力”也有过议论,他认为的诗歌之“力”包括“诗人的想象力”、“诗人的表现力”和“诗歌感化力”[4]364。结合“情绪”后的三元素,特别是“思想”,郑振铎所说的“情绪”也就有了知性的蕴涵,传递着要使思想知觉化,使感觉情绪化,是在对对象的情感体验中升腾起的一种不脱离感性表象的审美理解与领悟。这也烙上新诗初期说理是主调之一的痕迹。但定义的阐述仅停留在本质和内涵的界定上是不够的。比如,被康白情、朱自清、胡适、郑振铎等人同声称赞,被称作新诗里程碑式的杰作,周作人1919年写的《小河》,在有人看来全诗五十八行,黑乎乎一片不分段落。每行之间,意思连贯,全无分行的必要,也没有叫做诗的必要。对郭沫若的《瓶》,也有人认为是杂记,不是诗。甚至,1932年冰心在《冰心诗集》的自序中还说自己的“《繁星》,《春水》,不是诗。”[7]1可见在区分新诗与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上,当时是相当朦胧的。这就需要对新诗的外延进行规定性描述,区分新诗与旧诗,界定新诗与其它文体,包括散文诗与散文、杂文等的区别。郑振铎给新诗与散文划了个界线:其根本区别“绝不是于‘形式’,而在于精神。”[8]即“不在有韵无韵的关系,而在于诗有诗的情绪,散文有散文的情绪”[9],所以,“只管他有没有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不必管他用什么形式来表现。有诗的本质——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而用散文来表现的是‘诗’;没有诗的本质,而用韵文来表现的,绝不是诗。”[4]341
在“散文诗”作为作品和概念引进后①第一个使用“小散文诗”这个名词的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中国新文学中,第一个引进、译介“散文诗”这个文学品种(名词)的是刘半农。,有人对“散文诗”的存在发生了怀疑。郑振铎在手边没有什么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花了五个小时一气呵成《论散文诗》。他是国内最早就这一文体的性质、特点进行理论探讨的人。这之后,滕固、王平陵等也应和发表了意见。正如,由“诗”而“词”而“曲”,是古代诗歌文体演进中名称的更迭,代表一时代一文体中兴和形态特征,为“散文诗”这一新文体正名,不仅是对“诗体解放”的拓展,是诗学的进步,也是郑振铎认识和接受新的文体所持的科学的文艺观。
关于新诗与旧诗的区别,刘延陵曾指出:“‘新诗’与‘旧诗’的异点并不如寻常人所思仅仅在形式方面,‘新诗’和‘旧诗’的区别尤在于精神上的区别。”“新诗的精神乃是自由的精神”,“可说是求适合于现代求适合于现实的精神。”[10]这一点是与郑振铎相通的。但郑振铎对“新”与“旧”的认识上要比刘延陵走的更远些,他认为“文艺的本身原无什么新与旧之别”,他不以“新”与“旧”作为“评估文艺的本身的价值”,而是从文体的进步去认识“新诗”与“旧诗”。他认为新的思想还要用新的文艺、新的文体去承载,“新酒必须装在新的皮袋里”,这是“文艺的正路的路牌。”[4]376诚如王国维所言:“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发表其思想感情。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11]104
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郑振铎最后给诗歌下了一个自认为“较周密较切当”的定义:“诗歌是最美丽的情绪文学的一种。它常以暗示的文句,表白人类的情思。使读者能立即引起共鸣的情绪。它的文字也许是散文的,也许是韵文的。”[4]367-368这个定义从诗歌的情绪本质、暗示手法、接受程度、形式自由四个方面来界定新诗,突出强调了“情绪”,显示出新的、具有现代性的诗歌本质规定的生成。
新诗在初期以隔绝与古诗的联系作为代价,换来新诗的新文化急先锋的角色。但“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现代诗歌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这是一种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一方面,这是由中国深厚诗歌传统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现代诗歌创作所承担的超负荷的非审美的功能与责任,也严重地内伤了中国诗歌的自身发展。”[12]5今天,在新诗历经百年而命运坎坷后,再来反思新文学运动,来评价新诗的历史意义,特别要评判新诗在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意义,也只有从新诗的本质切入,才能比较客观的认识这一文体的历史地位。否则,只会简单的得出新诗是新文学运动中“收获最少影响最微”[13],“成就最差,成熟也最迟”[14]190的一个失败的文体的结论。
二
“五四”思想启蒙时期,“写实主义”成为“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在文学上的反映。茅盾曾把“写实主义”归纳为初期白话诗的三大特点之一。写实主义的精神,表现在题材上是社会现象和人生问题的最大抒写。初期白话诗中写社会问题的作品很多,如康白情的《草儿在前》、《女工之歌》,刘半农的《学徒苦》、《相隔一层纸》,刘大白的《卖布谣》,胡适的《人力车夫》等。这些诗作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痛苦,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反封建的精神[15]。
“写实主义”离不开“真”。早在1920年,郑振铎在推介俄国文学时就说:“俄罗斯的文学,……专以‘真’字为骨的;它是感情的直觉的表现;它是国民性格,社会情况的写真;它的精神是赤裸裸的,不雕饰,不束格律的表现于文字中的。所以它的感觉,能够与读者的感觉相通,而能收极大的效果”。鉴于“中国的文学,最乏于‘真’的精神,它们拘于形式,精于雕饰,只知道向文字方面用功夫,却忘了文学是思想,情感的表现”,他急切地呼唤“另起一新文学”[16]1。这种强调“真实”的观念,也成了郑振铎评价作品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题材的真,情感的真,甚至描写手段和效果的真,都成为他批评和鉴赏的基本原则。同时,因为诗歌毕竟是“主情的文学”,“是人类情绪的产品”,更侧重情感的表达。但也并不是任何情感的释放和宣泄都可能是诗,核心之一就是这情感必须是真实的,是不必考虑别人会怎么看,社会怎么看,怎么议论。要真实,真实到敢于袒露最深沉情感的地步,才能涌出使人颤栗的语言。正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西方开辟了一个诗的时代,除开诗中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价值外,它所表现的情感是极为率真而大胆的,甚至为当时世俗所不容的。所以,郑振铎特别强调情感的“真挚”:“我们分别那好的文艺的作品,与那够不上称为文艺的作品,不能用理智的道德的标准,只要看他所表现的情绪是否真挚恳切,它的表现的技术是否精密、美丽。任它是‘恶之花’也好,‘善之花’也好,任它歌颂上帝也好,歌颂萨坦也好,任它是抒写人生的欢愉与胜利,或抒写世间的绝望与残虐,只要它所表现的情绪是真挚的、恳切的,它的表现的技术又是精密的、美丽的,那末它便是一篇好的文艺作品了。”[17]一言以蔽之:“文艺作品,第一要有浓挚的情绪……”[18],“要有不能不说的话,有迫欲流泄的情感,然后做出来的才是真诗。”[19]而这种流泄,“在创作时:/是‘写作态’如潮水似的涨着……/是热血涌沸,大声疾呼着……”[20]他明确地宣布:“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祈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率’的残害者。”[3]3
郑振铎进一步区分了文艺(叙述)真实与生活真实:“所谓‘真实’,并非谓文艺如人间史迹的记述,所述的事迹必须真实的,乃谓所叙写的事迹,不妨为想像的,幻想的,神奇的,而他的叙写却非真实的不可。如安徒生的童话,虽叙写小绿虫,蝴蝶,以及其他动物世界的事,而他的叙述却极为真实,能使读者如身临其境,这就是所谓叙写的真实。至于那种写未读过书的农夫的说话,而却用典故与‘雅词’,写中国的事,而使人觉得‘非中国的’,则即使其所写的事迹完全是真实也非所谓文艺上的‘真实’,决不能感动读者。”[21]
“真实”是文学的基本原则,算不上哪一流派特有的文学主张。郑振铎之所以特别强调真实性,诚如陈梦家在第二个十年编《新月诗选》的序言中所说:“真实的感情是诗人最紧要的原素,如今用欺骗写诗的人到处是,他们受感情以外的事物的指示。”[22]1这种以“真”为基准的评判标准与中国传统的“尽善尽美”的诗歌审美原则之间已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表现了他的战斗性的一面,也是他“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和提倡“血和泪的文学”在诗歌领域的彰显。他主张在取材方面更加倾向于揭露现实社会、表现现实人生,而不仅仅是关注诗人个人内心情感的“真实”。
在五四期的新文学运动中,新诗是最早结有创作果实的部门,这在当时是含有深刻的战斗意义的。当时,新诗就像海中的冰山,时而露出一角,时而淹没在汪洋之中。当时反对新诗的人也特别多,提倡新诗的意义绝不仅只在打破形式格律的束缚和提倡用白话写诗方面,而同时是含有深刻的反封建的意义的。文学革命一定要在新诗的提倡上得到胜利,才可以使新文学取得正宗的地位。与郑振铎为新诗进行理论建设一样,他的译介工作也是对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助威和捍卫。
郑振铎在译介外国文学上是不遗余力的,他是积极吸收借鉴外国诗歌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报刊杂志上积极译介外国诗潮、诗人和诗作,特别是1921年初开始,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对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评介和作品的翻译,不仅帮助了这一时期的新诗人寻找新鲜的异域营养、发现新的创作途径,而且也为中国新诗走向多样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催生了以冰心的《繁星》、《春水》为代表的,这一后来人们称为“短诗”或“小诗”的新诗体的诞生。事实上,每一次文学新质的获得都是新旧文学交互厮磨和中外文学双向影响的结果,正如周作人所说:“中国现代的小诗的发达,很受外国的影响,是一个明了的事实。”[23]创作小诗的冰心、宗白华和何植三等人正是在阅读了郑振铎、周作人等人翻译的泰戈尔诗歌和日本俳句后促成了1920年代的小诗创作潮流,特别是郑振铎译介泰戈尔及其作品《飞鸟集》、《新月集》,改变了中国新诗在翻译上的审美趣味和译作的选择范围。郑振铎自己也创作小诗,随意地把自己的生活感受或回忆,三言二语地写下来,简短通俗,隽永清新,使人耳目一新。他的描景小诗美丽、清新、安谧;写心境时真切、动人,想象新奇;描写刹那间感触时,则真率、质朴,透着对人生的思索。
三
汉字表音兼表意,声音与意义本不能强分,有时意义在声音上见出还比在习惯的联想上见出更微妙,所以有人认为讲究声音是行文的最重要的功夫。朱光潜就深信“声音节奏对于文章是第一件要事。”他深有体会地说:“读音调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样有节奏的运动。”[24]82
文学与音乐共生、融合。诗歌作为一种音乐性的语言艺术,音乐美是诗歌美学的普遍性法则。随着新诗运动在1926年复兴以后,诗坛对新格律并不感到是镣铐。对诗歌语言的锤炼也越来越受到作者的重视。实际上,新诗创作者们反对把新诗的内容框锁在格律圈里,但并不反对诗的音乐性。郑振铎在1919年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我是少年》被赵元任选入《国语留声机课本》,灌制唱片,传唱海内外,不仅体现了他对新诗音乐性的追求,也显示了他驾驭音律的能力。从《我是少年》到诗集《战号》,许多诗篇讲求旋律和节奏,注意吸收诗歌传统中回环复沓和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激荡的思想感情。
在有关诗歌的专题论文中,郑振铎对诗与音乐的关系、诗的音乐性等问题多有涉及,有的虽吉光片羽,却蕴含丰富的美学思想。首先,他把诗歌分为三类:抒情诗、史诗和剧诗,“史诗和剧诗,都是为叙事的,抒情诗则是为反省的,”[25]462“抒情诗的种类极多,如挽歌、颂歌、儿歌,以及民间流行的大部分歌谣都可以算是抒情诗。”其次,他认为“抒情诗在一切文学形式中,又是最近音乐的,因为它和音乐都是完全从感情的泉里喷流出来的。”“抒情诗在一切诗歌之中……占着诗歌国里的正统皇座。说不定抒情诗也许竟要成为诗国中唯一的居民。”因为,“诗歌本是最丰富于情绪”,任何诗“如果把它们这种抒情的分子取出,便如从美酒中把酒精取出,从蜂房中把甜蜜取出,简直不能成其为诗了”[25]478。在他看来,诗中的音乐性,宛如美酒中的酒精,是渗入式的,是内化了的。
郑振铎在《儿童世界》的征稿启事、编读往来信函、为友人和文学出版物写的序、跋,以及有关儿童读物的专题文章中都涉及儿童作品,包括儿童诗的创作问题。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音乐性,郑振铎曾在《小说月报·安徒生号》的卷头语中用赞赏的口吻,引用了勃兰特《安徒生论》中的一段话,这也可以看作他对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音乐性追求:
无论谁,如果要写故事给儿童看,一定要有改变的音调,突然的停歇,姿势的叙述,畏惧的态度,欣喜的微笑,急剧的情绪——一切都应该织入他的叙述里,他虽不能直接唱歌、绘图、跳舞给儿童看,他却可以在散文里吸收歌声、图画和鬼脸,把他们潜伏在字里行间,成为一大势力,使儿童一打开书就可以感得到。[26]
儿童文学重表现情趣,而情趣就多半要靠声音节奏来表现。上述这段话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儿童诗歌的,但一切艺术均以音乐为旨归,歌吟更是儿童的一种天然需要,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音乐性追求自然是“文中应有之音”。对儿童诗在音乐性与思想性的取舍上,郑振铎的态度更是激进:“儿歌和童谣都是以音节为主,而思想情绪次之,读来全无意义而却甚为儿童所欢迎。”[27]89这话说的固然有些偏激,但郑振铎对儿童诗音乐美的追求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诗歌的音乐美,郑振铎追求适合表现思想和感情的某种音节和调子的音律的美,不刻求韵脚,多切自然的音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及李白的诗歌时,郑振铎有过一段评价,表达了他理想中的诗歌内容与音乐完美结合的典范:
他(李白)的诗如游丝,如落花,轻隽之极,却不是言之无物;如飞鸟,如流星,自由之极,却不是没有轨辙;如侠少的狂歌,农工的高唱,豪放之极,却不是没有腔调……几乎个个字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
吟之使人口齿爽畅……恰好代表了这一个
音乐的诗的奔放的黄金时代。[28]320-321
乐曲中三拍的节奏最为舒缓,最适合表现情绪。七言绝句时代三个音尺也契合了这一特点,最能入乐,取得和谐的音韵效果,吟诵时有沈德潜所谓的“一唱三叠”的“飘忽”之感。朱湘对七言绝句在通过音乐表现情绪的成就上,也首推李白[29],这与郑振铎可谓相投,但他对李白七言绝句的音乐美多少还停留在感性的层面,并没有展开论述。在这一点上,郑振铎上述的描述和分析是现代作家中最为全面而精到的。
郑振铎对古典戏曲文献和蕴含韵律的弹词、宝卷等“说唱文学”整理的宏富成就,以及五四前后兴起的“歌谣学运动”影响下他对民歌的收集和研究,可以推断他是深谙音律的。这些方面的浸染,而习得的吟诵规范,自然也会流露在他的诗艺创作中。郑振铎创作的儿童诗题材广泛,四季、早晚、微风、星辰、雀鸟、鱼猫等,都是他的歌咏对象。现今留存的约三十首①郑振铎所写的儿童诗歌,在已出版的七卷本《郑振铎文集》没有收录,二十卷本《郑振铎全集》收。其中六首在《儿童文学》目录中注明是“曲谱”,由许地山作曲,郑振铎作词,这里也算作其儿童诗。另据《儿童文学》第4卷第3期目录,有西谛的诗歌《夏天的梦》,实为图画童话。另,《纸船》其实是译自泰戈尔《新月集》,不应计入。,这些作品充满了幻想与童趣,节奏活泼、欢快,音乐旋律优美,而且这种音乐性与诗情诗意、故事情节十分谐适,为儿童文学,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阵地,插上了音乐的翅膀。
[1]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2]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3]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黄安榕,陈松溪,编选.蒲风选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6]田寿昌(田汉),等.三叶集[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7]冰心.冰心诗集[M].北京:北新书局,1932.
[8]郑振铎.答钱鹅湖君·跋[J].文学旬刊,1922,(33).
[9]郑振铎.通讯(与许澄远)[J].文学旬刊,1921,(14).
[10]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J].诗,1922,1(2).
[11]王国维.人间词话新注[M].藤咸惠,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81.
[12]郑家建.东张西望——中国现代文学论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
[13]屈轶(王任叔).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J].文学,1937,8(1).
[1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M].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
[15]茅盾.论初期白话诗[J].文学,1937,8(1).
[16]郑振铎.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M].耿济之,编译.北京:新中国杂志社,1920.
[17]郑振铎.小说月报·卷头语[J].小说月报,1924,15(2).
[18]郑振铎.小说月报·卷头语[J].小说月报,1925,16(11).
[19]郑振铎.通信(与鸿杰)[J].小说月报,1923,14(3).
[20]郑振铎.小说月报·卷头语[J].小说月报,1924,15(1).
[21]郑振铎.小说月报·卷头语[J].小说月报,1924,15(5).
[22]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M].上海:新月书店,1931.
[23]仲密(周作人).论小诗[N].晨报副镌,1922-06-21.
[24]朱光潜.散文的声音节奏:艺文杂谈[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25]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四卷)[M].天津: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26]郑振铎.小说月报·卷头语[J].1925,16(9).
[27]郑振铎.复周得寿函[C]∥郑尔康,盛巽昌.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
[2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29]朱湘.王维的诗[J].小说月报,1926,17(1).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I206.6
A
1000-5072(2012)06-0119-06
2011-03-15
陈振文(1969—),男,福建长乐人,福建江夏学院人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地方文献研究、郑振铎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郑振铎儿童诗歌的音乐性研究》(批准号:JB1129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