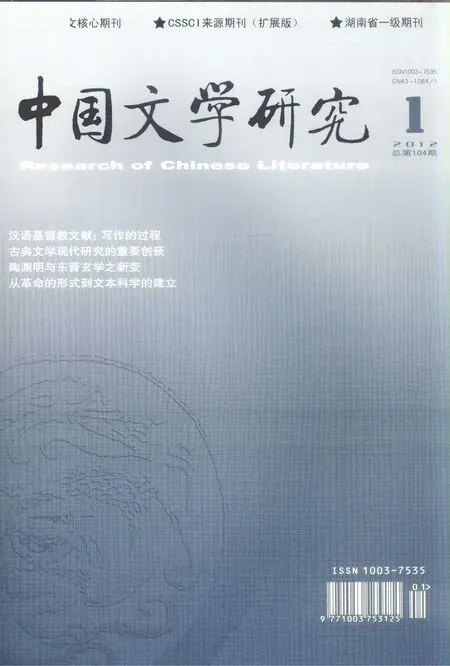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死亡”迷雾、现代性危机与批判精神:读吴子林编著《艺术终结论》
2012-12-17江飞
江 飞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置身于全球文化工业的情境中,艺术如何担当起将沉沦的个体从物化的文化氛围中解放出来的重任,这是我们以及这个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正如尼采所言,“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1〕当我们通过吴子林选编的这本《艺术终结论》,再次集中审视黑格尔、阿瑟·C.丹托等人的“艺术终结论”或是J.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的时候,我想不仅仅意味着对艺术(文学)和时代的尊重,更意味着对人类自身存在危机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努力建构精神未来的尊重。
在我看来,“终结”二字似乎已成为某种传染性的理论修辞策略,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艺术的终结”、“文学的终结”、“文学理论死了”等诸多命题,在表达一种决绝的评判姿态和制造话题效果的同时,更暴露出评判者内心的犹疑、焦虑和片面的深刻。更重要的是,这种“终结论”话语权始终在欧美那里,然后伴随所谓的“全球化”进程向世界各地蔓延,对于非西方世界比如中国来说,这种外发性的撒播的理论是颇值得警惕的,无论如何,“终结”一个对象或宣判对象的死亡是容易的,而使对象避免终结、走向新生则是不易的。在编者看来,“终结”一词有着“复义”的性质,即它既有取消、结束之义,又与开始、再生相互联系在一起,而死亡、终止则是对它的误读。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不是要宣判艺术的死亡,而是为艺术指明走向“真理”的出路。黑格尔在其“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理念论的基础上,根据绝对精神的发展逻辑,认为艺术在表现绝对理念上存在着局限性的缺陷,而作为真理表达的高级形式的哲学必然取代作为真理表达的低级形式的艺术。黑格尔的错误在于将艺术与真理、道德的关系理解为线性发展的关系,而实际上艺术(或美的形式)与其真理内容、宗教或伦理关怀之间可以发生同时共在的关系。〔2〕与黑格尔的纯粹哲学思辨不同,丹托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思潮和艺术现场中反思艺术的,他反复声明,自己和汉斯·贝尔廷提出的艺术终结论,并不等于宣称艺术已死,在丹托那里,终结的是从18世纪以来逐渐确立起来的那种美的自律的高级艺术,它已经不能满足自身不断创新的要求,因此它必将走向终结,所以他所言说的是:关于艺术的某种“叙事”已经终结,但是被叙事的“主体”却没有消失。无论黑格尔还是丹托,或是海德格尔、阿多诺,虽然“历史地预测艺术的未来”是危险的,虽然艺术离真的死亡依然遥远而未知,但死亡的危机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只有拨开这种“死亡”的迷雾,艺术的死亡危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凸显出来。
归根结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艺术的终结不仅仅是现代艺术的危机,更是现代性的危机。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所揭示的实际上就是包括审美艺术在内的文化现代性与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断裂。可以说,艺术是这种现代性危机在后现代消费社会最有代表性的症候表现。黑格尔之所以强调理性的重要并提出“艺术的终结”问题,其最终原因正是一种现代性的价值立场,一种整合的乌托邦信念。当然,这种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叙事”到了丹托那里则变成后历史阶段艺术史叙事的终结,“一切皆可,一切皆得为艺术”,在解放艺术自我意识的同时,又将艺术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之中。不可否认,在后现代消费社会,“艺术品被简化为相同的效用单位,丧失了原有的本质属性——异质性,物品的内在价值被消减为相同个体所具有的相同交换价值和价格,量取代了质。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产业化的文化就是同质文化。”〔3〕这种“同质文化”似乎正实现了丹托所言的“所有艺术都是同等和无差别的艺术”(all art is equally and indifferently art),然而这种抹平了差异的艺术也恰恰表明了“后历史艺术”的危机,断裂的现代性的危机。
虽然这种现代性危机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传统与现代”、“先锋与媚俗”、“自我与他者”等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在现代、媚俗和他者的视域中,艺术(比如文学)正遭遇“物化”、“技术化”与“生活化”的危机与挑战。无论何种艺术,都必须面对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问题,而在物自身发挥媒介功能的时代里,艺术与其说是观念艺术,不如说是媒介(mediatic)艺术,它被“物化”(thingified)为可机械复制的失去“光晕”的商品,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马丁·马勒内语),其审美价值形式彻底服从于商业文化的价值形式,抹杀了意义存在的本质并导致了艺术的自我解构。也正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依靠“技术”实现了艺术品的大规模生产,科学本是以更强的普遍性和同一性为目标的,而艺术却总想要创造特殊性(singularity)和一次性的事物,现在,艺术越来越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工艺或设计艺术,这已经成为高级的自律艺术终结之后的一种现代艺术,虽然有利于实用与审美的结合,但这种普泛化艺术的传播却也在无形中构成对审美的消解和对技术(主义)的膜拜。
在阿多诺那里,艺术代表着真实经验,因而实际上就是真理本身;艺术提供了校正现代性的手段,因而可以帮助我们拒绝同一性的暴力;艺术品从经验世界中独立出来,并展示了独立于日常世界的另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实体。〔4〕然而这种浪漫主义的表达并未能阻止艺术坚定地走向日常生活,我们已经亲眼见证了日常生活上升为艺术,艺术下降为日常生活的双重运动,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不复存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理论问题,更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生活问题。在文化工业中,艺术品已然丧失了它应有的价值,艺术抛弃了真理,而转向了肉身,转向了生活,转向了自然,正是在日常性的狂欢之中,我们再次遭遇了艺术非神圣化和艺术家明星化的悖论过程,日常生活的过度审美化使现代艺术的抱负成为乌托邦,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艺术/艺术家不是在技术化世界的庸俗和艺术商品化中堕落,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架繁殖机器(沃霍尔)。当然,彭锋认为,前卫艺术、通俗艺术、设计艺术和生活艺术,是艺术终结之后的主要艺术形式,并将艺术复兴的主要希望寄予生活艺术,这种艺术的关键不是艺术作品,而是艺术人格,甚至主张要“回到手艺,回到技术,回到人用手用个体生命去感知事物,回到人的生命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5〕我明白,在科学强势的当今时代,需要艺术来维持人用感觉用身体同世界打交道的能力,需要艺术来维持人之为人的身份,但我又不免疑虑:后现代的生活已将每个生存个体置于高度平面化、概念化甚至同质化的困境之中,在技术理性或实用理性的思维统摄下,艺术家如何葆有个体性的、非同一性的感觉与体验,如何才能在尘世中创作以造就对生命/艺术沉沦的调解,如何才能超越有限世界的同质性并在先锋与大众、高雅与通俗之间找到通往艺术人格的道路?
这种疑虑似乎也是整本书隐在的某种心情,并显现为一种深沉的文学焦虑。在选编的这十四篇论文中,有关“文学终结论”的讨论占据了一半的篇幅,这既说明了“黑格尔的幽灵”最先徘徊在文学场域的上空,也说明了编者以及更多文学研究者所共有的批判意识与人文情怀。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之所以会在中国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自然是与中国步入电子图像时代过程中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研究合法性的恐慌相联系的,而这种恐慌又与当代文学的“边缘化”处境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终结”其实就是“边缘化”,也就是说,因为现代科技飞速发展而导致了艺术家族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文学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霸主地位被影视艺术所取代,科学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全面统治者,文学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当然,从编者所选编的几篇文章来看,对“终结论”的批判和对文学研究的希冀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文学边缘化本来就是文学发展的常态,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就在文学自身中,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场域,这一独特的审美场域的奥秘就在于文学语言之中(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文学完成了它的统治,但文学性渗透在后现代思想学术、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和公共表演之中,文学性应当成为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终结”的不是文学甚至不是一个时期以来获得了文学代言人身份的精英文学,而是精英文学统治大众文学等其他文献生产类型的大一统文学场的时代和历史(单小曦《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场裂变》),如此等等。正如吴子林所说,无论是强调艺术的独立自主性和本体性功能,还是强调艺术的政治化功能,无论是乌托邦式的救赎,还是文化上的感性革命,批判精神始终是我们在思索“文学终结论”时所要汲取之物(《“文学终结论”刍议》),我想,这也是我们在面对所谓的“世界文论”和当前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等问题时所必备的精神所在吧。
必须注意的是,“艺术终结论”背后是现代西方人对于自己的现代处境与遭遇的生命追问,这种追问在中国所引起的回应与误读似乎超出了本土文化的现实与想象,所以,我们一方面必须在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探讨图像社会或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现代艺术的意义或真谛所在,对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来说,妄自菲薄或杞人忧天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为艺术(特别是文学)寻找到不可穷尽的创造的可能性,多元的艺术观念、混杂的社会形态和独特的艺术传统,是中国当代艺术拒绝“终结”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借助他者的眼光来反观和批判自身的艺术现实或理论缺陷,一如詹明信把对现代性的反抗寄希望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在他看来,第三世界文化构成了对第一世界文化进行审视、批判的立足点(《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所以,我们可以不赞成希利斯·米勒所说的“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但我们不得不重视他所关注的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的征兆之一,即“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6〕在我看来,这的确是“终结论”命题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紧迫而实在的现代危机。
正如编者所说,“‘艺术终结论’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一场关于艺术与历史、艺术史与人类现实世界的讨论,更是涉及人的存在的问题,其中体现了人对世界相关的精神方式。”〔7〕与其说这本书是对过去了的“艺术终结论”的理论阐释和总结,不如说它开启了一扇人与世界精神对话的新生之门——只要人存在,艺术(文学)就不会终结,艺术史或文学研究就不会终结,精神就不会消亡!
〔1〕尼采:《悲剧的诞生》,第129页,华龄出版社,2001年版。
〔2〕沈语冰:《哲学对艺术的剥夺:阿瑟丹托的艺术哲学观》,吴子林编《艺术终结论》,第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3〕〔英〕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第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版。
〔4〕朱国华:《认识与智识:跨语境视阈下的艺术终结论》,吴子林编《艺术终结论》,第1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5〕彭锋:《艺术的终结与重生》,吴子林编《艺术终结论》,第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6〕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第16-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7〕吴子林:《艺术终结论·导读》,第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