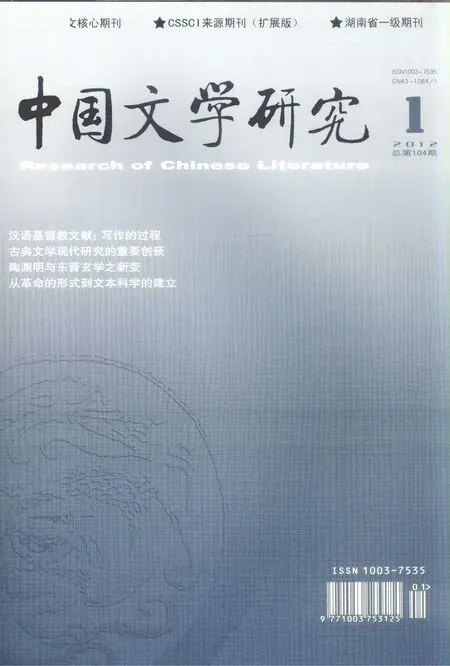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人民性”与“人民性”文学的二律背反
2012-12-17王再兴
王再兴
(上海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44;怀化学院中文系 湖南 怀化 418000)
“人民”/“人民性”的语义曾经逐渐发生过极大的改变。在此,我们不妨回溯这组语词在时光和历史中的旅行,以及它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摇曳不定的身影——“人民性”文学和相关论争,大致考察一下它们哪些意义已经失落,哪些意义又在发生,而今它在中国当下的文学中又面临着怎样的“意义”处境。
一、经典表述中的“人民性”与文学
在别林斯基那里,早年对“人民性”的用法和他之前的普希金差不多,主要着重于这个俄文词汇的“民族性”含义(如1835年的《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但“人民性”在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却有了深层的变化,他写道:“大自然是艺术底永恒的楷模,而大自然中最伟大和最高贵的对象就是人。农民难道不是人吗?——可是,在一个粗鄙而没有教养的人里面,有什么令人发生兴趣之处呢?——怎么没有?他底灵魂、智力、心灵、热情、和性癖,总之,一个有教养的人所有的一切。”〔1〕在这里,“农民”作为一个劳动者,虽然粗鄙、没有受过教育,但在“人”的意义和人的“内容”上,被认为是平等的个体。到了杜勃罗留波夫,这一词义则更进了一步。他对人民性有着独特的阐释,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他借评论普希金,留下了一段大家熟知的文字:
我们(不仅)把人民性了解为一种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语汇,忠实地表现其仪式、风习等等的本领……在普希金的作品里,这一切都有:他的《水仙》是最好的证据。可是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这在普希金却是不够的。”〔2〕
虽然这篇文章被人提得更多的,是所谓“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的说法,在其后的时间里更被导出了写作者立场的“悲悯和同情”或“人民同情”话题,但杜勃罗留波夫在此所提出的,乃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人民的诗人”(艺术家)必须与人民真正地融为一体,有命运和精神的共通感(或者说深层意义上的“生活”共享感),没有任何偏见。——简言之,不能是“第三者”,或者旁观者的态度。这是特别关键的一点,它不再混同于某种可能只是表面的态度,也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代言”问题(虽然这确实是一个“入口”)。毋宁说,后世20世纪中国关于“人民性”文学的诸多争论,可能正是与这一点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清晰的指认和梳理有关。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关于“人民性”的认识,在俄国民粹派那里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曲解。王晓华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详细辨析了俄国民粹主义者主要是从“整体性”(集体性)而非“个人性”来强调“人民性”意义的。正是从这里,王晓华先生发现了民粹派“代言”的不彻底性和负面的历史效果: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自始至终有着重大缺陷,一是忽略个体公民的主体性,二是“他们在将人民视为需要表达和提升的底层民众时仍保留着居高临下的姿态,故而真正的平等精神在他们内心深处是缺席的。他们不是以个体公民的身份而是以代言者的高蹈姿态到民间去的,所谓的深入民间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对平民生活的考察”。〔3〕
这种对于人民性的“整体性”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那里走得更远。据伍世文、伍世昭先生《关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一文认为,将文学直接与人民(性)相联的,是李卜克内西,他主要提及了应当将被压迫群众作为描写对象,对人民的本质有正确认识,从人民大众本身的观点出发去表现人民等三个方面。〔4〕其后,在政治内涵上继续拓展上述人民性含义的是列宁(列宁所认为的“人民”主要即指“无产阶级和农民”〔5〕)和斯大林。可以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李卜克内西,再到列宁、斯大林,基本的路径是循着:表达人民的生活与思想(马克思:“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等)——把被压迫人民作为描写对象(马克思评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李卜克内西《论艺术》等)——艺术属于人民,写作为劳动人民服务(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等)——反映生活发展和时代的本质“真实”(列宁;斯大林等)。这个人民性概念,就完成了它的从最初的表现内容,到表现对象,到表现立场,再到政治性高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转变。这虽然是一个理论提高的路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人民”同时也从最初被尊崇的对象,衍化为了最后主要是需要被教育和被提升的客体。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1930年代初俄苏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教育人民”的意思,即所谓“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二、人民性:“人民”在20世纪的中国
五四前后,蔡元培、胡适等的“劳工神圣”,鲁迅对人力车夫的“仰视”,郁达夫的“你也是同我一样的么?”(《春风沉醉的晚上》),都赋予了“民”这个词汇以某种新的政治性内涵。如蔡元培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中第五章《职业》表达了“职业无高下”,“今核之于道德,则不必问其业务之异同,而第以义务如何为标准”,所以“劳心”、“劳力”之分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蔡元培在此书中虽然提到了“教育农民”,但原文是“故启发农民,在使知教育之要,与夫各种社会互相维系之道也”。其中的“教育”从行文逻辑上看,是指上文的“即子女教育,亦多不经意,更何有于社会公益、国家之计耶?”这与列宁、毛泽东、周扬等人的“教育农民”的说法并不相同。〔6〕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蔡元培在此所说的“劳工”,虽然“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但标准在于“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的事业”,强调具体的劳作意义。这种劳工的生活本身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感:“他们(凭藉遗产的纨绔儿、卖国营私的官吏、克扣军饷的军官、操纵股票的商人、领干修的顾问谘议、出售选举票的议员等——引者据上文)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在这一简短的演说词中,蔡元培两次提到“我们要认清劳工(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7〕胡适在1921年的《平民学校校歌》中,也宣扬“大家努力做先锋,同做有意识的劳动”,称“靠着两只手,拼得一身血汗,大家努力做个人,——不做工的不配吃饭!”〔8〕梁启超在1922年的《敬业与乐业》中同样认为,“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当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你不必羡慕我,我不必羡慕你。”并称,“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不二法门”,“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9〕等等。
“人民”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其意义也发生着持续的变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938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等诸多著作,都阐释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思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0〕事实上,在那个作为文艺方向的“工农兵”的称谓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主要的(后来被以参加劳动的方式“改造”),工人大多数在此前不久还是潘训《乡心》(1922)中的阿贵、以及夏衍《包身工》(1936)里的“芦柴棒”们一类人,他们本来就来自于农村,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向来被称为来源于工人和农民,即“工农红军”或“人民子弟兵”。换句话说,延安时期,虽然有“人民”的称谓,但要紧的却是,他们确实是自食其力“劳动”着的人民。这也可以从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中《改造“二流子”》一节的内容得到互证,可以看到,延安当年对于“二流子”的改造,目的就是要将其改造成为“劳动”者,并且这其中伴随着被改造者个人自尊的恢复。〔11〕这些都意味着劳动者得到了正面的社会认同。
说明这一点,恰恰是因为这个“人民”的概念,在后来的发展中扩展了内容,从而也导致了它的某些意义的淡化。首先是包括了“社会主义建设者”。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辨析了“人民”和“敌人”两个概念,再一次提到“什么是人民”的问题,并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他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2〕这个“建设者”的提法,在建国后与“脑力劳动”的概念差不多同时被普遍地倡导,〔13〕这既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被纳入劳动阶层申明了合法理由,但也不得不说,它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劳动”与身体劳作的关系,“劳动”初始概念中的“辛勤”、“汗水”、甚至“苦难”等原本属于抹布阶级才具有的特点,开始向“知识”、“能力”、现代化“创造”等转移。当然,随同“劳动”的上述特征一起转移的,还有“劳动”的“尊严”感。在此,农民群体,一个在国家的工业化规划里迅速与“知识”、“能力”等绝缘的阶层,其整个阶级在延安时期因“劳动”而天然赋有的尊严感,就变得难以为继了。而与之相反的是,由于上述“社会主义建设者”概念的确立,知识分子几经辗转,终于成了“人民”的一员。但是,这也预伏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中产阶层的崛起,以致于以“知识”或者“技术”的现代性正义与“劳动”的身体劳作特征分道扬镳了。而且,这种变化在1979年通过邓小平的声音得到了确证;并且“人民”的身份此时进一步扩大到相对比较宽泛的“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1979年6月15日,《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外商”、“外资”蜂涌而入。这时,甚至“知识”或者“技术”的现代性正义也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劳动”的身体劳作特征进一步稀薄,“人民”的概念进而扩展至“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现代性正义出现了“资本”这一新锐光鲜的面孔,社会尊严感更迅速地向所谓“民营企业家-成功人士”(1990年代的“民营企业家”,新世纪初的“成功人士”)身上聚焦。此种情形,绵延至今。
三、1949年前后:“人民性”文学的歧变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民”一词的“失重”过程(汗水、苦难、辛勤等意义的冲淡与流失),原本从康、谭时代到五四时期的那个既与“劳动”、也与“尊严”等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人民”/“劳工”概念,发生了深度变化。它的平等、反叛、解放等内涵特征原本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冲动力,在1949年后的讨论中被予以转化。今天再回溯1949年前后“人民性”文学的意义处境,确证当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节点。
虽然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直接命名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但依照报告的内容,其中“人民”的主要意义之一,是受“各种政策”“指导”和“教育”的对象。周扬并引证了毛泽东的说法:“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就说过:‘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在最近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说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4〕在这里,“人民”(或者“工农兵”,“农民”)自身的解放、平等与尊严实际上已经处于悬置状态。同时期周扬及毛泽东对于“人民”的看法,似乎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极力要求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5〕的那个“人民”,已经有了很大不同。1949年10月25创刊的《人民文学》,虽然刊名冠以“人民”,但其主编的任命制(须经过文协全国委员会选举和党组批准的程序),创办时登记人为国家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主管出版工作的官员,以及作家、官员、编辑等三位一体的编辑群体,对《人民文学》形成规约的《文艺报》、《人民日报》等特点,都说明这个“人民”与同时期周扬及毛泽东对于“人民”的看法基本相近。〔16〕1950年,蒋祖怡的《中国人民文学史》和赵景深的《民间文艺概论》先后由上海北新书局于4月、9月出版,“工农兵”和“人民性”是书中的显著话语。但这两本原为积极姿态的著作,其“人民文学”的称谓却引起了莫大的争议,苛责的批评甚至一直延续到1954年。这次的规训的后果,是“人民性”从五四传统趋向了新的后延安传统;“人民性”的语词被压抑进了古典文学批评中。它的指向现实社会的政治冲动被化解,反而成为新的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证词。
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在体制权力约束性力量的底层,“人民”一词的政治创造性和推动力其实仍然一直在文化的“记忆”里存活着,它导致了对于“人民”一词意义的缠绕和争夺。例如,“人民”同样是胡风1945年《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中的高频词汇。但它的意义却显然指向大众自身的自由解放,及“民主”。胡风称,“如果说,不是自由解放了的人民大众,那所要争得的自由解放的民族不过是拜物教的幻想里面的对象。……对于燃烧在解放愿望和解放斗争里面的人民大众的精神动向的保卫和发扬,……就正深刻地反映了民主主义的要求”;“……作家……如果他只能用虚伪的形象应付读者,那就说明了他还没有走进人民的现实生活,如果他流连在形象的平庸里面,那就说明了,即使他在‘观察’人民,甚至走进了人民,但他所有的不过是和人民同床异梦的灵魂”。〔17〕1946年,郑振铎的《<文艺复兴>发刊词》更是明显地将这种“人民”的理解回溯到了五四传统。此文称:“……人民之友,人民的最亲切的代言人的文艺作者,你必须为人民而歌唱,而写作;你必须在黑暗中为人民执着火炬,作先驱者。在抗战期间,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今后你必须继续的更努力的为民主而写作。你的责任决不会减轻,你不应该松懈下去!”〔18〕同年雪峰(即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则鲜明地提出了“人民力”的概念,对于“人民力”作为文艺思想力、艺术力的来源做了富有激情的陈述。〔19〕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人民”的批判,在这一类文章中,由来都是非常审慎的,通常比较少见;相反,倒是对于人民的推崇和尊重之情,常常是这一类文章的共有特色。
因缘际会,赵树理在当年成为一个谈论作家如何与人民共享命运的绝好例证。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说,“农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只表现在通常文学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这是他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有了这个观点,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20〕1946年的周扬似乎不像后来1949年那样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急于“提高”和“教育”人民(农民),甚至不惜曲解毛泽东的原话之意,(以毛泽东那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为例,原话是指要农民改变小生产观念的困难,意思集中于经济方面。)因为在这篇《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农民或者群众还是一个自在自足的概念,他还会说“群众的意见总是正确的”。到1947年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则更鲜明地提到了上述话题: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解放区农村伟大的改变过程之一部。无论故事的安排,人物的心理、行动、思想情感的描写,都从不使我们感到很不自然,矫揉造作,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这就是因为他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同生活,一同斗争,思想情绪与人民与他所表现的农民的思想情绪完全融合的结果。这也就是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学习的一点。〔21〕
同篇文章还说,“文艺工作者今天的根本问题仍是与工、农、兵思想情感相结合,也惟有如此,才能最后的真正的解决了形式问题。”这里,无论是周扬,还是陈荒煤,在评赵树理的道路时,都回归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那个与工农兵结合,与实际的革命斗争生活结合的话题。借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说法,这乃是赵树理有着内心深处的与中国农民的共命运感,它绝非仅仅是一种容易“扮演”的写作姿态或规范,而是一种生命感,一种近乎“信仰”的内质。如果不是这样去看,或许将很难真正理解赵树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真正意义,也将无法理解他在农村题材原本已经成为十七年的题材热点之后的暗淡命运,以及他的作品中的那些深层忧虑和隐痛。一种作家对于农民(人民)的共命运感,必然融贯了作家的出身、生活历史、情绪、荣辱与共等血肉相联的因素,它回应了九十多年前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那个严肃的话题。
四、另两次“人民性”文学的论争
如果我们确认上述“人民”(“农民”、“工农兵”)一词所包含的政治性创造意义,以及以之为中介的“作家-创作”关系体现出来的作家与人民的共命运感的话,则这种依托于“人民文学”的观念(有时借名为“现实主义文学”),争取恢复“人民”一词的那些不安定的意义(政治创造力和革命性)的努力,在建国后仍然沿着胡风、秦兆阳等人的路径被承续了下来(参见李红强:《<人民文学>十七年1949-1966》)。虽然,结果也无法成功。以至于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思想斗争问题》(1959年)中说:“现实性、革命性、民主性、社会性、民族性、群众性,等等,都可以概括到人民性的范畴中去。反压迫、反剥削、反映阶级矛盾的人道主义,反映民族矛盾、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反封建制度、反封建上层建筑的反封建主义,等等,当然是进步文学中人民性的主要内容。”〔22〕对“人民性”做出这样宽泛的定义,其实反映了当年定义的无力感。一些诸如“现实性”、“革命性”、“民主性”、“群众性”等带有政治冲动力的内容和那么多的以“反”字为前缀的充满斗争意味的短语,都填充在此时的“人民性”概念里,也再一次说明了这个语词本身的动荡不安的内在特征。它代表了“人民性”这个词汇一些原初意义的闪现。“这些思想内容,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始终一致,是与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刘大杰先生如是说。
第二次关于“人民性”的集中讨论发生在新时期之初。何其芳在1977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毛泽东之歌》一文,首次披露毛泽东关于“共同美”问题的论述,引起文艺和学术界的很大反响。1979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本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讨论热烈地展开了,这次讨论集中于“共同美”和“人民性”问题。多数人认为不同的阶级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审美标准,认为文艺除了具有阶级性之外,也可以具有人民性;人性的共同形态只有通过对生活的真实描写,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此次的争鸣因“人性、人道主义”的话题而来。这里表达了“同情和悲悯”的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话题在此时原本起源于对“阶级性”的反拨。(在有代表性的朱光潜先生上述文章中,作者说道:“据说是相信了人性论,就会否定阶级观点,仿佛是自从人有了阶级性,就失去了人性,或是说,人性就不起作用”;“人性论和人情味既然都成了禁区,共同美感当然也就不能幸免。人们也认为肯定了共同美感,就势必否定阶级观点”,等等。〔23〕——这里重提“人性”和“人情”语词,并将目标指向“阶级性”、“阶级观点”,显然可以明显地看出与1950年代后期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人的讨论相通的地方,从而接续了上一轮未充分完结的“人民性”/“阶级性”争鸣;而这次讨论在1984年因胡乔木的文章而终结的形态特点,也并非巧合地俏似上一轮讨论的结局。)虽然有作家在新时期初表达过,“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顾疼痛,死了的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24〕但正是在这之后的一个时期,“人民性”一词中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命运共享感在整体意义上开始消退。这种消退过程与蔡翔先生和王晓明先生所称的“新意识形态”的凸起正在同时。于是,一种原本共命运的姿态,就退而为仿佛“第三方”旁观视角的姿态。而第三次关于“人民性”相对集中的讨论,发生在2004、2005年及以后。较为突出的如方维保先生、王晓华先生等,其争论的基本点,正在于这个已经发生过多次变化的“人民同情”和不太彻底的“代言”。昔时的“平等”、“尊严”等含义已经在时间中大部失落,这一次“人民性”的讨论由此留下了某些未完成的话题。期间另有孟繁华先生“新人民性”的提法(2003年),和陈晓明先生“后人民性”的提法(2005年),等等。
五、结语
总结起来看,“人民”/“人民性”的“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式的内涵是应该予以注意的,它定义着真正的“人民的诗人”的要求。在上述二人那里,它意味着“人”的平等、一种内在的精神、生活方式的正义、以及反阶级化等内容。但在后来的意义历史中却更多地偏向了“人民”的治理性,人民的个人性和生活理想更多地转化成应该被批判和提高的内容。在20世纪的中国,“人民”一词的发展变化与上述衍变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着不太相同的一面。“人民”一词在传统中保留了作为“劳作阶层”和“被治之民”的双重特点。五四前后,由于蔡元培、胡适、鲁迅、梁启超,乃至包括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倡导,“人民”作为“抹布阶级”和“劳工阶层”,带有了劳动正义、尊严、生存方式的道德感等特质。这一内涵,即便是映衬在鲁迅等启蒙主义的“国民性”批判话题之下,也是一个坚韧的存在。由此,它也穿越1930、40年代,甚至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召唤着中国自己的“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式的“人民的诗人”。但在1949年后,“人民”只以抽象的集体性面目被描述,成为主要应该被“指导”、“提高”、和“严重教育”的能指。“人民的诗人”的诠释也向这种含义归属。“人民性”一词的“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式内涵部分地以“阶级性”的方式被压抑向古典文学的范畴。新时期以后,“人民性”以“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的名义而复苏。然而,一方面,这种对于“阶级性”的反拨存在着恢复“人民性”概念历史记忆中的政治激情(冲动)的可能,但也应该承认,另一方面这一新的“平等”替代了原“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人”的内涵、内在精神、生活方式、尊严等方面对抗“阶级化”的平等。这种替代使这个词汇重新发生了较大的语义转移。这一转移可以看出它与新世纪“人民性”和“公民性”的争鸣不无联系。从“怜悯和同情”、“人民同情”及“代言”体文学的语义里,我们正可以看到上述替代所发生的转变:不独劳动者个人性和生活方式的正义变得难以申明,而“劳动”与“尊严”的原初意义也业已基本流失;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写作那里,“人民性”一词的意义不安定与政治创造性虽然被努力召唤,但多半仍然显得暧昧不明。由此看来,作家和批评家的责任,或许应该在“人民性文学”的召唤之下,更多地争取复活它曾经有过的劳动、道德感、尊严、与正义等积极冲动。因为它们正是文学的力量。
〔1〕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A〕.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327-328.
〔2〕杜勃罗留波夫.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A〕.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389.
〔3〕王晓华.人民性的两个维度与文学的方向〔J〕.文艺争鸣,2006,(1):25-26.
〔4〕伍世文,伍世昭.关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A〕.刘纲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8辑)〔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6-127.
〔5〕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A〕.列宁选集(第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7.
〔6〕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31-235.
〔7〕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19.
〔8〕胡适.平民学校校歌〔A〕.胡适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36.
〔9〕梁启超.敬业与乐业〔A〕.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019-4020.
〔10〕〔1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一卷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812、808.
〔11〕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7-65.
〔1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毛泽东选集(第五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63-402.
〔13〕参见扶小兰.各历史时期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的比较研究及其现实意义〔J〕.探索,2009,(3):25-26.
〔14〕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A〕.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1999(上)〔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57-159.
〔16〕李红强.《人民文学》十七年(1949-1966)〔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1-52.
〔17〕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J〕.希望,1945,(1):3-4.
〔18〕郑振铎.《文艺复兴》发刊词〔J〕.文艺复兴(上海),1946,(1):6-7.
〔19〕雪峰(即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下)〔J〕.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1946,(3).21-26.
〔20〕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N〕.解放日报,1946-8-26.
〔21〕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N〕.人民日报,1947-8-10.
〔22〕刘大杰.中国文学史中的思想斗争问题〔J〕.上海文学,1959,(10):115.
〔23〕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J〕.文艺研究,1979,(3):39-41.
〔24〕高晓声.解放思想和文学创作〔A〕.创作谈〔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