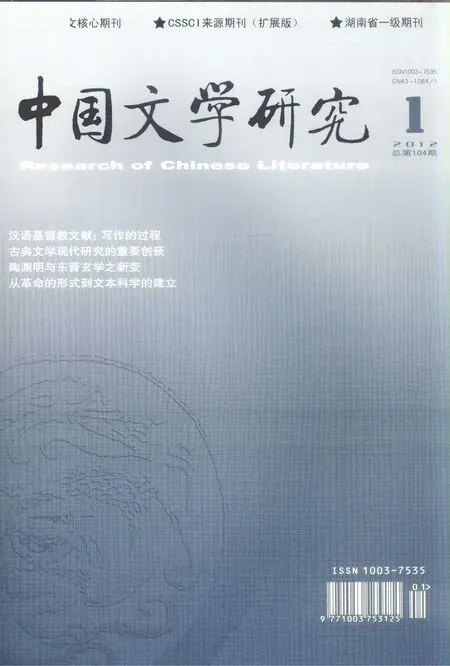现代文艺创作美学中的“童心说”
2012-12-17袁文丽刘绍瑾
袁文丽 刘绍瑾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广东 广州 510521;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童心”,是一个重要的古典文艺美学范畴,同时又是现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经常使用的概念。“童心说”有着深刻的文化传统,是四百年前李贽高扬的一面思想旗帜,其目的在于反传统、反礼教,提倡人性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正所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1〕;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即提倡有为而作,认为只要是发自真心至情的皆成至文,皆可推陈出新。然而,“童心说”作为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理论和主张,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在科技和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童心”这一概念仍在继续使用,而且备受艺术家和批评家们的青睐。我们常常听到“童心”的字眼:童心未泯,永葆童心,童心可贵;文章以“童心”为题材,充满了童真、童趣、童味……诸如此类云云。现代语境下使用的“童心”说,不仅积淀了传统的意义内核,更加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不仅立足于本土文学和文化的土壤,而且吸收了域外文学和人本主义思潮的“童心”意蕴;不仅吸收了现代心理学的营养,更有文化人类学的含义;既是具体的“童心”,又具有抽象的品质。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文化及社会境域中,立足于文学与“童心”的关系,可尝试从主体倾向、创作过程、文学作品三方面对创作美学中的“童心”意蕴作全面探讨。
一、现代作家的“童心崇拜”
成年人的心理状态和儿童的心理状态有着很大的区别。成年人大多被世俗名利所羁绊,忘却了人类自然的本性。但是儿童是天真烂漫的,他们拥有未经文明社会和成人世界浸染的自然本能和自然情感。儿童自由、淳朴的心性,被深刻体验过的成年人认作生命的本原、归宿和最高境界。正如自称为“儿童崇拜者”的丰子恺所揭示的那样:“我初尝世味,看见当时社会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忆当时的意识,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2〕
童心成为净化灵魂,建构理想人格的审美工具。在西方社会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影响下,早在18世纪中叶,卢梭就开始了“儿童的发现”,并指出儿童是不同于成人的独立存在的个体,教育应该使儿童贴近他的自然感性状态,有机、自然地成长,使其避免受到文明时代的“副产品”的病态“污染”。而“审美拯救人类”,“亲切地俯就儿童的童心”,成了席勒医治现代社会各种弊病的两剂最重要的药方。随后,在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风起云涌下,一批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华兹华斯等在其作品中热情歌颂赤诚的童心,唱出了诸如“儿童是成人之父/我希望以赤子之心,/贯穿颗颗生命之珠”〔3〕等脍炙人口的佳句。面临现代文明带来的精神危机,童心被当作拯救濒临崩溃的世界的最后希望,因为惟有圣洁的童心尚未被日益发达和霸道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吞噬和异化。自由、率真的童心便成为美好人性的代表,成为远离罪恶与苦难的审美乌托邦。
发现和重视儿童,并无比地向往童心,是新文学作家们的一大亮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文学旧传统,新文学的作家们在“人的文学”的全新的文化语境中,自由的抒发对儿童、对童心的无限热爱之情。著名的作家学者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老舍、郑振铎、丰子恺、郭沫若、冰心、叶圣陶等人,纷纷用自己的语言赞美童心。标举“性灵”大旗的诗人徐志摩,自称是个“自然的婴孩/误入人间峻险的城围”,“青草里满泛我活泼的童心”〔4〕。女作家冰心赞叹孩子是“灵魂中”“光明喜乐的星”,他们“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5〕。丰子恺更是热烈的赞美儿童,认为儿童“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孩子们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有着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6〕……新文学的作家们不仅吸收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某些新鲜思想,而且在创作中将“童心”外化为纯真、善良、仁爱、自由等美好品质,所表达的更倾向于抽象的“童心”。可以说,现代的“童心”内涵与李贽的“童心说”在大体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李氏的“童心说”并不彻底,在封建伦理纲常根深蒂固的影响下,在“父为子纲”的压抑下,“人”,个体独立的人,尤其是儿童,不可能真正受到尊重和平等的待遇,他指涉的只能是抽象意义上,哲学意蕴中的“童心”义理。现代作家们对童真和儿童心性的维护,也正是对自由纯真的心灵世界和对童心这一艺术境界的维护。
现代作家们重拾“童心”的大旗,重新发现被掩藏很久的“童心意识”,这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使命感。一方面,他们对处在封建父权压迫下的儿童有了强烈的解救愿望,对童心充满无限的向往、激情与希望;另一方面,作家们脱去了传统的枷锁在自由的语境中,象孩童一样尽情的抒写着自我。正是这样一种大背景,致使他们在成年之后,依然能葆有童心,常常有意无意地用一颗童真的心打量这个世界,用自己的笔构筑“童心”的文学天地。
二、创作过程的“童心”思维
沈从文说:“所有故事都从同一土壤中培养成长,这土壤别名‘童心’。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既无宗教信仰,无文学艺术,无科学思想,无燃烧情感证实真理的勇气和诚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历史文化即转入停顿,死灭”〔7〕,沈氏一语道出了童心与文艺创作的心理基因。在某种意义上,“童心”等同于“文心”,其实质就是一种艺术精神。
童心之思是“绝假纯真”的,既不受文化成规的影响,也无需迎和他人的功利目的,只是纯粹的按照自我本真的意愿和方式言说。现代作家们拽着内心深处所崇拜珍视的“童心”,大胆而热情地进行文学构思和创作,在对作品的品评和欣赏中,处处可以发现其留下的烙印。“童心”成了一种创作思维、创作美学,彰显着“童心思维”与文艺创作的血肉联系。
首先,童心思维富有诗性气质,是一种“诗性智慧”,是诗人艺术家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维柯就把具有“诗性智慧”的原始祖先称作“人类发展的儿童时代”,把其“万物有灵论”的特征直接比作“正象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它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活人”〔8〕。由此可见,“儿童”、“童心”,在维柯的观念中,实质上就是“诗性智慧”的体现。儿童总是对世界充满最新鲜的感受,最奇特的想象,最纯真的思想。对成年人而言,时间无情地磨钝了感知,在重复的节律中,亦磨去了对世界鲜活奇特的感受,这对创作来说是一种悲哀。文学需要对世界的独特发现,需要新奇的目光,敏锐的感知,而这正是童心的“诗性智慧”所具有和发挥的。当代作家汪曾棋对此评说道:“孩子是最能把握周围互不干涉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能完美地捕捉住诗”。〔9〕儿童天生就是些诗人,在看这个世界时总是与大人的眼光不同,并对大自然有着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敏感。
皮亚杰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和儿童的游戏,繁简虽有不同,而历程却是一样”〔10〕,说明了童心式的审美心理与文学创作的必然联系。随着现代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的发展,童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和意义逐渐被发现。童心被作为一种极具个性特点和诗性精神的突破常规、常理、常法的事物倍受关注,儿童天真、陌生、非理性的眼光被认为对作家审美体验的生成极具意义。他们往往视宇宙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个体,物与我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丰富的想象常产生出新奇的象征意象。儿童的这种“万物一体”的思维特质与文学创作所必须的审美移情的艺术境界是极为类似的。在现代文学中,有许多作家认识到童心的这一特点,并借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审美眼光来体验和观察世界。叶圣陶就曾提出“文艺家有个未开拓的世界而又是最灵妙的世界,就是童心”,童心的“纯任直觉”、“物我同一”“就是文艺家的宇宙观”〔11〕。丰子恺则更进一步总结出童心化的“绝缘”、“直视”的审美理论。在其《艺术论》里,“绝缘”是一个核心概念,即悬置一切“读书识义理”而来的“闻见道理”,直视一切物象本身。现代作家作品中的稻草人、小白船、“赤心国”和杂糅魔性与神性的湘西传奇等意象,无疑便是童心诗性思维应运而生的创作。
其次,童心思维的创作直接体现在别具一格的儿童视角的运用。即以儿童的眼光、态度、思维方式和趣味取向,来挑选素材,组织情节,表现与儿童感知发生联系的那部分现实生活图景。作家们试图以纯洁的童心来净化“早已失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12〕的成人们已变得粗俗的心灵,于是对不可复返的童年追忆构成了成人作家们寻找精神乐园的最基本的内容之一。他们重新使自己“回到”童年,以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叙事策略和语言句式,去重新诠释和描绘外在的世界。这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其目的在于借助儿童身上几乎不受任何变化和意识形态浸染的生命原初体验,作为一种艺术途径来实现对生存世界更新鲜有力的揭示,也是借童心之杯浇心中块垒。
质朴无华的童心和感性直觉的思维形式,令儿童更善于忠实地记录生活的原生态内容,而且当他们“用清澈的目光看这个世界时,他必然要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倾轧、尔虞我诈……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个蓝晶晶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清明,充满温馨。”〔13〕于是,儿童视角里的人生就有了更多的诗意、美和快乐。儿童视角策略的选择,也使熟悉的生活在儿童单纯、诗化的展现方式中呈现出了陌生的新鲜面孔,从而也就将文章的主题引向了深入。一种儿童式的鲜明和不经意间的深刻,从对这复杂现实的稚气把握中透示出来。看似稚拙的儿童视角中往往渗透的是独特而深邃的个体生命体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对自我心灵的追问成为文本的深层意蕴。
再次,纯真的童心外化在作品结构和艺术风格上,则表现为追求艺术形式的返璞归真,简单自然的风格。童心是自然而素朴的,儿童的思维与表达总是趋向最简单的形式,以童心创造的作品当然“以自然而为美尔”〔14〕。童心的“绝假纯真”在艺术风格上就表现为稚拙、自然的格调。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笔老到是一极,稚拙也是一极,所谓“大巧若拙”,所谓“平淡乃是绚烂之极”,即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至高的艺术形态。如同中国人物画有范曾的精巧,也有关良的稚朴,有时后者反胜前者。作家在技术性上的考虑,如言语、结构、意象、情节、节奏等,似不是着力营造的,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作文的机心,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亦看不出刻意雕琢之迹,行文的过程全凭一颗天然的赤子之心;文学的语言似是随手拈至,信笔提来,随意自然,却天机活泼,全是“童心自出之言”(李贽《童心说》)。这正是文学艺术上追求的“化工”之境。
周作人素朴不雕的笔致,亦是这返璞归真话语方式的体现。他很早就强调“美文”:“只是真实简明便好”,在周作人看来,简单就是真实。但文章求真并非易事。他说:“我自己作文觉得都有点做作,……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是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修养不足的缘故”。〔15〕周氏以谦虚的口吻道出了达于这种至高艺术境界的要求:不仅需要艺术家们在写作方面练就很高的技巧,而且在心性修养方面必须达于童心的至境,即尽力去除各种社会历史文化的种种陈规遮蔽,不加一点粉饰,还其本来面目。
三、作品中的“童心”表现
作家们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形象来表达着其对童心的解读和崇拜。文学作品中的童心表现,往往是多层面的、复杂的艺术现象。但是,大体上仍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其一,表现在儿童文学方面。在“五四”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的发现”的总目标的冲击下,“儒家三纲”之说土崩瓦解,文艺家一方面吮吸着西方人本主义的营养,特别是杜威“儿童本位观”的思想,使儿童问题一时成为新文化建设的焦点。随着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提出,随着鲁迅“救救孩子”的一声呐喊,文艺家们“童心崇拜”的创作热潮此起彼伏,儿童文学开始崭露头角。儿童文学是适合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如童话、儿歌、故事、儿童小说、散文等。这类作品大多反映儿童生活、思想感情以及儿童的向往与幻想世界,周作人、冰心、丰子恺、叶圣陶、张天翼等都是现代比较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
陈伯吹先生曾提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16〕这里指出了童心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儿童文学的创作,要求作家怀着一颗天真稚嫩、充满梦幻的童心,设身处地从儿童的眼睛去看世界,去表现世界。在作品呈现的感性直观中,描绘孩子与大自然、与现实生活天真无邪的和谐一致,描绘其心灵中那质朴的想象,那可爱无邪的童趣。这样既吻合了儿童读者的心理状态,易于引起他们的感受、共鸣,又不违背文学自身的规律,体现了儿童文学特有的艺术性。
其二,以儿童为表现角度的作品。作家们试图以自我或经验自我的儿童视角组织文本,以自己对儿童、对童心的真切感受,真切把握童心思维特质。通过对童年多种心理阈限及其动态成长过程的真切体验基础上的摹写,揭开了童心的诗性本质与现实的粗糙面目之间的隔膜梳离,蕴涵着独特而又强大的心灵感染力和震撼力。儿童视角是成年作家借用儿童的思维方式和纯净心灵,为观照世界和反观自身提供的一个全新的审视和观察角度。比较早期的儿童视角的引入便是从鲁迅、冰心、叶圣陶、丰子恺、废名等开始的,其后得到了一批当代作家如莫言、余华、王朔、汪曾祺、苏童等人的接受甚至青睐。其中鲁迅的《社戏》、《故乡》就运用“少年迅哥”的视角去感受生活。莫言的一系列小说《红高梁》、《铁孩》、《红蝗》、《罪过》等都杂糅着儿童视角的叙述。
许多现当代作品中展示出以儿童稚气的眼睛看生活,以单纯的心灵感受生活,一切都在童心的笼罩之下。但是作品反映的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并非儿童能读懂的。这些童心表现却给作品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格调,产生浓郁的童趣。这应该说是对儿童生活的超越,是童心的艺术升华。又如丰子恺的《华赡的日记》,冰心的《分》都是以儿童形象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是不谙世事的华赡和刚出生的婴儿,作家以他们无知、稚气的口吻,用儿童独有的惊奇和敏感去触摸感受成人世界中事件和情感,借助儿童身上几乎不受任何文化或意识形态浸染的生命原初体验,作为一种艺术途径来实现对生存世界更鲜活有力的揭示。
其三,以童真、纯洁、善良、母爱为表现主题的作品。“童心”在现代语境中不仅指涉具体的童心,而且有着抽象的深刻含义,它是真、善、美等美好人性的代表,是人间的净土和人类精神家园的象征,现代文学的很多作品中就以其为圆心,呈现出童真、纯洁、善良为表现主题的系列作品。这类作品并不以儿童为本位,只是在成人的立场与儿童平等地对话和交流,达到相互间心灵的沟通。如冰心的小诗《繁星》、《春水》,歌唱自然、童真、母爱,创造了许多童话般的境界,读后使人企盼返回童年,去领受那纯真的美。像冰心这样怀着母爱与童真的女作家,从现代到当代几乎构成了一种女性文学传统。从庐隐、苏雪林直到今天的王安忆、铁凝等,一大批学院派的女性作家都有很多“童心”主题之作。苏雪林常动情地倾吐对于母爱浓浓的孩童般的依恋与不舍,在其散文《母亲》中就流露出真性情:“我的性灵永远不成熟,永远是个孩子。我总想倒在一个人的怀里撒一点娇痴,说几句不负责任的疯话”。〔17〕即便在母亲去世后,她恍惚地感觉到精神上仍有一位关怀着她的“母亲”,字里行间对母爱的眷恋伤感又无比虔诚、执著,而且将人类情感中最永久最难忘的经验准确地提炼了出来,让人读来不由感慨啼嘘。
结语:“童心说”的现代价值
在市场经济的迅速演进的今天,随着现代科技与传媒手段的推进,快餐文化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人们传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冲击。社会人文环境的恶化,严重地影响着当代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品位和发展方向,许多文人在商品大潮前迷失了自我,“他们由产生失落、困惑、焦虑、浮躁、愤怒直到放弃理想、责任、操守、良知、道德,以极其庸俗的精神和相当卑劣的姿态出现在崭新的历史舞台上”〔18〕。他们满足于一种脱离真实生存经验、缺乏本真思考的伪现实主义。在“边缘化”的当代文坛中,传统的经典之作被解构,所谓的文学沦为了纯粹的消费品,文学成为非文学。
文学精神价值的存在和体现,就是以真诚而深刻的文字,揭示人与社会的状态和内质,剖析人性的深刻与复杂,用真善美来启迪人们的心灵。这就要求作家永葆一颗纯真的“童心”,创造出动天地、泣鬼神的“天下之至文”。“童心说”的精神养料正好为重构当代文学的立场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引导文学创作从本真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出发,既不流失为权力话语的工具,又不迷失于外在社会文化的潮流之中,从而构建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本心。“只要艺术家怀有人生的满腹柔情,奋力拨开现实人生的层层雾霭,以最纯真的生命感受靠近人类童心的林地,艺术就会为童心的造化之功显出人性的诚实和温暖。换言之,一个真正具有艺术灵魂和审美精神的社会,必将是一个童心焕发的社会,因而也必将是一个凝聚人类之爱和孕育生机的社会。惟其如此,我们说,充满童心的艺术既是爱的艺术,也是诗的艺术,更是希望的艺术。”〔19〕
“童心”是从事文艺创作的重要条件,“童心说”呼唤人们以自己的“本心”去体味外在的世界万物,去重拾失落的“文心”。童心的率真、超脱、赤诚、无私与无畏,是一切真正艺术家不可缺少的宝贵品质,是现代社会一切文明人所应葆有的美好品格,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精神气质。诚如丰子恺先生所说:“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20〕
〔1〕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A〕.据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以下凡引李贽语,皆据是书。
〔2〕丰子恺.缘缘堂随笔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311.
〔3〕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15.
〔4〕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1卷〔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5,221.
〔5〕金宏宇选编.冰心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294.
〔6〕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5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116,253,114.
〔7〕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248.
〔8〕维柯.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62.
〔9〕汪曾祺.汪曾棋全集:第6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7-288.
〔10〕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175.
〔11〕叶圣陶.叶圣陶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21.
〔12〕参照周作人.阿丽丝漫游奇境记〔A〕.自己的园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4.
〔13〕曹文轩.面对微笑〔M〕.济南:泰山出版社,1999.252.
〔14〕李贽.焚书(卷三)·读律肤说.
〔15〕周作人.雨天的书·日记与尺犊〔A〕.周作人自编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16〕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
〔17〕苏雪林.苏雪林文集(2)〔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269.
〔18〕陈耀明.中国文学,世纪末的忧虑〔J〕.新世纪,1996(2).
〔19〕郑元者.美学心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1.
〔20〕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5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