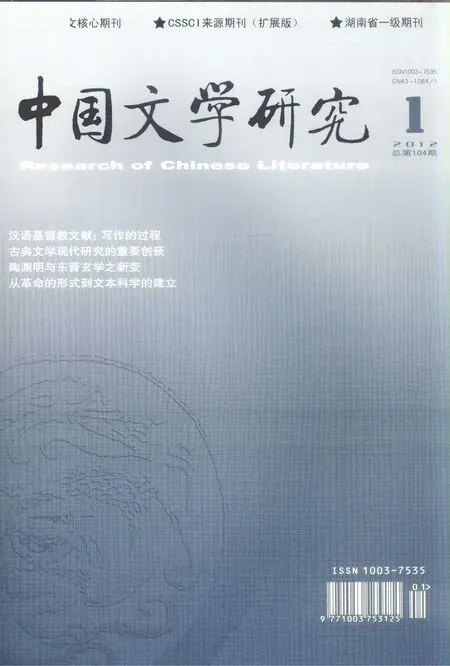创伤视角下权力与身体的互动:读裘小龙的《红英之死》
2012-12-17刘白
刘 白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
从创作策略来看,美国华裔文学经常游移在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往往从本民族的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以此建构自己的文化权力机制,试图改变以往的文化权力“失语”状态,并倡导从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从华裔作为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所特有的立场和情境出发,来建构自身的主体性。最近几年,以哈金、裘小龙等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以写当代中国的人物和故事取胜,在多元化的美国文艺界成绩斐然。裘小龙的“陈超”系列颇受西方读者欢迎。处女作《红英之死》因其作为“对社会和文化的关注超越了一般概念的侦探小说”而先后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奖和白芮推理小说奖,而后获得了“安东尼小说奖”,即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然而,尽管国内对华裔文学不断深入,相比较对其他华裔作家如汤婷婷、谭恩美、哈金的研究来说,对裘小龙作品的研究则十分薄弱。本文拟从创伤视角来审视《红英之死》中的权力机制以及个体创伤的关系,这对于丰富国内的裘小龙研究乃至华裔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创伤理论把个体的创伤置于社会层面,梳理出其中蕴涵的社会制度、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机制。作为一个认知视角,它认为个体层面所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伤害同样揭示了社会层面中的权力关系,体现出社会对个体的安顿和权力的分配。从创伤视角审视作品,能揭示文本中个体在权力机制中的命运,以及它所反映出的作家对话语权的争夺意识。
与创伤相关联的是身体概念。它作为当代文化理论的关键词,在当今社会承载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1〕(P1)。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身体也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有着多重指涉的文化符号。身体既是一个被表现的客体,也是一个有组织地表现出概念和欲望的有机体,两套表现系统相互缠绕和重叠。“身体的标记不仅有助于辨认和识别身份,它也指示着身体进入文字领域、进入文学的途径:身体的标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字符’,一个象形文字,一个最终会在叙述中的恰当时机被阅读的符号”〔2〕(p28)。在中国文化中,身体同样有着多种所指:“‘身’在汉语思想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的‘身’为肉体,无规定性的肉体、身躯;第二层面的‘身’是躯体,它是受到内驱力(情感、潜意识)作用的躯体;第三层面的‘身’是身份,它是受到外在驱力(社会道德、文明意识等)作用的身体——这种‘身’观念,坚持人的‘身心’二元论,而且把‘心’看成了‘身’的主宰。”由此可见,汉语中的“身”不仅指涉人的肉身实体,也认识到了此一肉身实体是包含着实践驱力的实践者——躯体和身份。〔3〕(P16-17)
小说的主人公陈超和案件的受害者关红英个体的命运都在权力机制中展开,在小说的意义结构中无不弥漫着主人公的身体意象,两个主人公的不同命运结局也通过相应的身体意象来进行展示。在小说里,裘小龙构建了较为丰富的身体象征以及所隐射的权力符码,他将个体层面的身体体验与社会层面的文化权力融合在一起,从而构建了两个互相呼应的机制。
二
在《红英之死》中,主人公陈超是位刑侦队长。就他的工作环境来看,他所在的公安局无论从其社会功能或从内部机制上来说都是典型的权力机构。在这种权力体制下,个体在潜意识层面认可并服从于权力的影响,逐渐上升到对权力的自觉意识。就人物所遭受的创伤来看,陈超所遭受的第一次创伤就是他初恋的失败。陈超在北京学习的时候,在图书馆遇见了心仪的姑娘凌。这是他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古色古香的图书馆和恬静的姑娘完美地构建了他的诗意世界:“在图书馆里呆上一天是十分惬意的:在彩色玻璃窗下,绿色罩子的台灯旁研读;在古色古香的院子里闲逛,而院子里面的青铜鹤雕像呆呆地望着游客们;在长廊里面出神地漫步;眺望飞檐上的黄龙瓦片跟天上的白云穿织在一起……”。〔4〕(P386)这个带有诗情画意的场景描述在文本的语言表层构建了个体的感情世界,然而朦胧的爱情刚刚产生就被权力无情地击碎。当凌告诉他她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时,陈超意识到了横亘在他们之间无形而强大的现实,两人随后不得不分手。这场失败的初恋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陈超与凌的社会身份差异而招来了社会现实对感情的干涉,但从深层的社会权力机制分析,这段感情上的创伤影射了陈超在权力机制中所遭受的排挤。个人精神生活层面的感情挫折以及社会机制层面的权力受挫是这段创伤所要表达的表层与深层内涵。
小说中,陈超在接手杀人案之后和助手一起开始了调查取证工作。然而,上级给他派了一位思想僵化的领导张政委来监督其工作的进行,并对陈超处处牵制。在陈超所处的权力体系中,张政委就成为一个权力象征,时时提醒陈超在权力机制中的受控和被压制状态。而这种状态与陈超失恋后所遭受的感情创伤相呼应。
个体所遭受创伤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使个体对身份产生了迷失感,在精神上陷入焦虑状态。焦虑作为现代社会中人的普遍心理状态是无可回避的。弗洛伊德认为,真实的焦虑是对于外界危险或意料中伤害的知觉的反应,它和逃避反射相结合,可视为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表现。作为一种心理要素,它是个人实现其自我认同的障碍前提,这种状态会导致对存在的怀疑和自我价值的否定,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也随之而变得脆弱。而焦虑的来源几乎都有一个创伤性的经历,小说中陈超失恋的经历成为其独立性主体意识构建中一道无可回避的伤痕。陈超不时地感受到了失落,“偶尔,他会享受夜深人静时的那一丝孤独,但此时令他感到的却不仅仅是独自一人的忧伤,这感受就好像是连他存在的意义都值得怀疑”。〔4〕(P333)
另一方面,在焦虑和创伤成为自我认同的精神障碍反面的同时也具备积极意义。有时候,焦虑和创伤能成为一种动力,推进个人的自我认同,并最终在认同中缓解焦虑和创伤。小说中陈超具备两种身份:诗人和刑侦队长。这两个貌似不相关的角色在陈超的生活中不时交叉,却因本身互相独立而无法相融。在作品中,陈超更多地表露出了一个诗人的气质,在办案过程中他常联想起诗歌。《红英之死》中充斥的大量诗歌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特色。然而,主人公对诗歌的热爱并非仅出自于纯粹的文学爱好。从中我们同样可以梳理出深层的权力关系。
因为创伤的严重性,在一般情形中,遭受创伤的人会出于自我保护而否定或压制以往的回忆。但这种情况在陈超身上出现了例外——他并没有回避或否定创伤,而通过诗歌建构自己的治愈途径。诗歌并非是陈超逃避现实的方式,而是一种积极的治愈方式,书写本身就是对创伤性经历和记忆的治疗和弥补。陈超通过诗歌回忆并重复以往的创伤经历,并将受伤的经历认同为个人历史和个人身份的一部分。对于失败的初恋,陈超没有逃避,而用诗歌回忆了当初的时光。在陈超写的一首《离别》的诗作中,有这样两句:“‘时间是一只鸟,栖息在枝头,然后飞走,……’‘你肯定是因为某一次难忘的别离有感而发的,’王枫说。‘同一个与你十分亲近的人的分离。’她的直觉是对的,他想。”〔4〕(P14)
按照弗洛伊德的“艺术白日梦”和荣格的“原型说”,文学艺术可以让创作主体的幻想得到补偿,释放创作主体的压抑和紧张。文学作品也就成了作家被抑制的心理欲望需求的升华,从而使文学具有了心理治疗的作用。从创伤意识的理论层面来说,个体意识的创伤经历可以从自传体记忆中提取出来——从广泛的终生主题到事件的一般描述,再到创伤特有的详细知识,这些表征则与记忆中相应场景的感官特征、情绪和生理反应相连。个体如果能主动地从创伤中“编写故事”,他就越能够在创伤之后恢复对自己的控制。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文本具有治疗的功能。其中,回忆和叙述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个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审视过去。艺术在这里赋予了受创伤的个体一个渠道,使得他们被压制的回忆得以浮出意识层面。当他们被压制的回忆被想起并表述出来的时候,这种对于创伤的叙述和再叙述就具有了权力上的意义,有助于赋予个体以力量,构建他们的权力现实。
对创伤经历的回忆既是意识层面上对感情的留恋,在政治层面上也有着对权力的渴望和追忆,对于处于权力等级制度中的陈超来说,没有什么比获得权力上的优势地位更具有实际意义的了。此时,政治和意识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并最终消融。同时,权力在他身上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去考虑现实世界的定位,这也使得他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与感性世界中截然不同的务实性。之前的创伤性经历影响了他的性格,甚至渐渐沉淀为其潜意识的一部分。在办理关红英案件期间,当陈超遇到了政治上的阻力被停职,在被逼到绝境之时,他写信向北京的凌求助,采用了现实的策略而并非诗人的思维来赢得现实世界的权力掌控权。同时,“潜意识中,他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在那些日子里,他几乎都没有想到过凌。在邮局写下的那封信根本就不是出于浪漫的原因:是绝望之际的一时冲动——是求生者的本能。”〔4〕(P447)
陈超的这段内心自白清楚地表露出了他潜意识中对权力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描述的文本表层无法看出,也是对他之前的唯美意境的反讽。文本的意义重心在此刻发生了转移,开始承载更多的现实内涵。陈超因凌在北京的关系获得了政治上的青睐而开始平步青云。这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转折点也同样被赋予了鲜明的身体象征。凌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来到陈超的房间,随之开始了唯美而怀旧的性爱。两人的性爱可以被看作为创伤的治愈,如果说陈超的初恋宣告了他初期权力尝试的失败而受到创伤的话,此次的性爱不仅在个体层面是对陈超感情的弥补,在权力层面上也预示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机。
三
从创伤视角看案件的受害者关红英,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两个人物在权力机制中结局的明显反差。在作品中,关红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对于生活和幸福有着自己的追求和向往。陈超在搜查关红英的屋子的时候,他发现了关红英以往的照片:
有黄昏时斜靠在一条独木舟上的,她穿着件有条纹的休闲衬衫和一条贴身的裙子,脸上的神态平静祥和;……有跪在一座小桥泥泞木板上的,手摸着赤裸的脚踝,向前俯在栏杆上,身体的重量全靠她的右腿支撑着。”〔4〕(P79)
这些唯美的艺术照同样具有诗的意境,这个意境与陈超之前的唯美想象如出一辙。陈超以他诗人的眼光隐隐感受到关红英对生活和感情也曾有美好的憧憬和向往,这些被关红英珍藏的照片映射出了她心灵深处对于自我世界和幸福的渴求。
作品中陈超和案件的受害者关红英有着类似的经历,并同样在感性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徘徊,在性格上均体现出理想与务实的双重性。关红英与陈超一样,同样经历过感情上的创伤。她的初恋被权力体制干扰、破坏,给她的心灵留下了创伤,并使得她对感情和生活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是关红英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权力关系对她的成功干涉,并使得她在人生的天平上逐渐向权力妥协。就关红英和吴晓明的关系来看,关红英之所以选择吴晓明这样的纨绔子弟作为依托,是创伤所带给她的意识形态影响:以功利性的权力观作为她的生活观和人生观。从人物形象而言,与陈超相似,关红英同样具有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双重张力。而关红英与陈超不同的是,她所依赖的感情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当关红英把吴晓明拍摄的色情照片藏起来,试图要威胁对方时,吴晓明孤注一掷将她杀害。试图在权力关系中把握主动的关红英不幸以她悲剧的人生收尾。
关红英的死作为身体的悲剧性终结,也喻示了她政治生涯上努力的失败。而陈超的创伤在与凌的性爱中得到了象征意义上的愈合,并随后成为仕途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作为同样遭受创伤的人物,他们的结局截然不同,从这一点上来说,陈超是幸运的。这两个人物命运的鲜明对比赋予了文本以强大的张力。两个身体符码作为权力体制的两极,在文本中有效构建了权力体制运行的机制。
通过创伤视角对作品中人物身体符码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创伤所隐含的权力关系无处不在。创伤的产生暗示着主人公在权力机制中的失势,而创伤的愈合也伴随着权力的恢复和优势地位的树立。小说中,裘小龙以创伤作为权力机制运行、变化的符码,通过对创伤的考察,可以清楚地厘清主人公在权力机制中的发展轨迹。
四
在裘小龙的文本中,理想意境的构建与现实精神矛盾地融合到了主人公身上。而这种二元结构也与文学文本和现实内涵的表层与深层意义遥相呼应。作为符号化并被赋予了历史文化意义的身体和它蕴含了中国文化元素的文学文本在本质上是同体、同质的。也就是说,符号化的身体成为了叙述中的一个关键,承担了故事的重要意义。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与外文本的真实作者和读者的肉体相比,文本内的身体本质上是虚构的,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建构。如果文学批评仅仅从人物社会身份的角度来评判,显然不够。我们在分析新一代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时候,更要对作品所流露出的创作群体的身份意识有敏锐的感知力。在裘小龙的小说中,身体不但承载了社会与自我身份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国华裔民族身份的认同意识。写作中自我认同的焦虑折射出对其社会身份确认的期待,以及作为弱势群体对中心抗争的焦虑。作为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少数族裔,华裔文学作家在少数族群身份认同的问题上或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艰难选择,或在主流文化体制的空间下寻求生存及抗争策略,这一切都有形无形地与文化体制中的权力机制相关联。作为身处文化边缘的华裔作家,裘小龙的创作也无形中成为被压制群体努力抗争、争夺话语权的意识载体。在他的作品中,身体不仅成为剖析文本意义的有效意象,帮助读者分析作品中的权力机理,也透露出新一代美国华裔作家对权力机制的敏感和关注。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
〔2〕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
〔3〕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2005.
〔4〕裘小龙.红英之死〔M〕.俞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