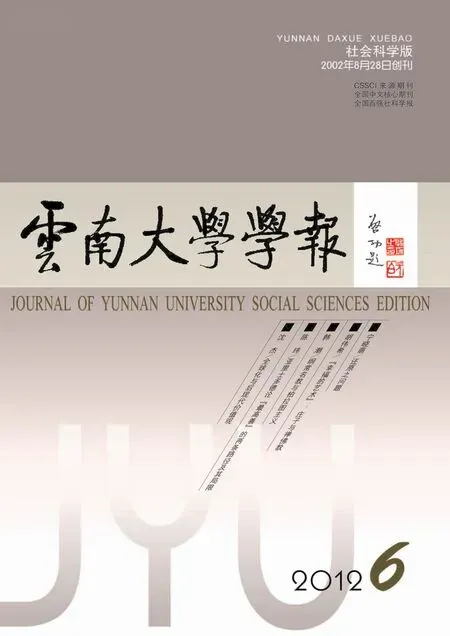“幸福的艺术”:庄子与禅佛教
2012-12-09胡伟希
胡伟希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1]
从中西哲学史可以看到,从很早开始,幸福论就进入了哲学的视野。作为古希腊哲学之集大成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两大主干——政治学与伦理学,便可以视之为对人类如何达到幸福之境的研究,前者将幸福的实现诉诸于人类公共生活,后者强调个人德性对于幸福的重要。在中国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亦重视对幸福的探究,于是有《论语》和《孟子》这样的经典出世,它们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一样,也认为幸福有赖于人类的社会公共生活与个人德性的完善,并且对社会的政治与道德生活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然而,除了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儒学注重从社会公共生活以及个人德性的角度来谈论幸福之外,中国的庄子和禅佛教也以其对幸福的独特理解而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对于庄子与禅佛教来说,幸福不仅与社会公共生活和个体的德性有关,而且它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因此,庄子与禅佛教主要是从幸福的方法论与“技艺”的角度来谈论幸福。庄子与禅佛教的幸福论包含四个方面:顺生、适意、无执、中观,它们分别展现了个体追求幸福的某一种方法论途径,合而观之,则构建了一门完整的“幸福的艺术”思想体系。今天,挖掘庄子和禅佛教的幸福学思想遗产,不仅有助于开辟我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理解的视野,而且对于当今人类如何追求幸福来说亦具有思想启迪。
一、顺生:个体有限性的超越
庄子幸福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幸福与个体类型的关系。换言之,庄子认为,个体幸福的追求要顺应个体自身的生命形态,而这种个体的生命形态,是由个体的生理、心理等条件决定的。庄子的这一思想,是通过“鹏雀之喻”的寓言来展开的。
《庄子·逍遥游》中说:北海有一种鱼,名字叫“鲲”,后来化为大鹏鸟,扶摇直上九万里,要飞往南海。这时候,树丛间的雀嘲笑大鹏鸟说:你干嘛要花那么多力气飞往南海呢?你看我,就在这小树丛间跳来跳去,一点也不费力气,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吗?这就是有名的“鹏雀之喻”。假如说“鹏雀之喻”是关于幸福的一种“隐喻”的话,那么,庄子心目中的幸福何所指,历来却人解人殊。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庄子认为幸福是有大有小的,有的人的幸福理想非常远大,就像那大鹏展翅一样;可也有的人的幸福目标十分狭窄,就像那树丛间的雀一样。如果仅仅从这则寓言的表面叙事情节来看,似乎是这么回事。但假如我们真以为庄子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那就小看了庄子。因为以思维之深邃见长的庄子,是不会满足于用那么大段的文字来阐述这样一个简单事理的。
为此,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夫之写了《解庄》这本书,其中对“鹏雀之喻”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进行了梳理。他说:鲲鹏与雀的确都是在追求它们各自的幸福,因此,雀不必站在它自己的幸福立场上“以小笑大”,讥讽鹏鸟对于远大幸福的追求;反过来,鲲鹏也不必打心眼里瞧不起那雀在树丛间跳跃所享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以至于去“以大悲小”。假如鲲鹏和雀各执著于它们自己的幸福而取笑对方的话,那么,这就是对幸福的莫大误解,是“皆未适于逍遥者也”。[1]原来,对于王夫之来说,幸福不是其他,就是“逍遥”。逍遥又是什么呢? “逍者,响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1]故逍遥其实是逍与遥的合称;或者说,逍与遥合起来才谓之逍遥。在庄子文义里,逍又解作小的意思,遥表示大,假如将大、小分别视作两种对立的幸福人格类型的话,那么,完美的幸福就存在于“逍遥”之中。
为何庄子要将幸福理解为“逍遥”?要了解这个思想,让我们来看看庄子哲学中与“逍遥”联系在一起的“无待”概念。王夫之解释说:“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实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天均,则无不逍遥矣。”[1]所谓无待,就是没有对立面。人们通常都是以有待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对幸福的看法也如此,总喜欢将幸福划分为大与小、高与低,而去追求那最大与最高的幸福。庄子认为,所谓幸福之大与小、高与低,都是从“有待”的立场看问题的结果;而真正的幸福应当是无待的,即不站在“有待”的立场,破除将幸福划分为大幸福与小幸福的看法。而幸福之大与小的界限一旦破除,则意味着幸福只有一种,这即是“逍遥”的幸福。
说幸福之无法区分为大与小,其根据在于:幸福本质上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属于人的精神性的体验,而精神性的东西是无法以外部世界的眼光来将其划分为多与寡、高与低的。就以体育运动来说,爱好打篮球的人在篮球运动中可以体验到莫大的幸福,而对于一个不爱好运动的人来说,要他去打篮球不仅无法享受到幸福,反倒对他是一种折磨。所以,庄子认为:幸福是很难通过外部世界找出一个公认的标准来加以衡量的。假如硬要从外部世界中确立一个标准来对幸福加以衡量的话,这就是“有待”(有待于物)。这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这正如有人以毛嫱为美,而鱼见之却会吓得潜入水底;猫头鹰以腐鼠为美食,而人类却感到恶心一样。既然幸福不是有待的,那看来就只能是无待的。
既然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有待的,而所谓幸福是无待的幸福,那么,完美幸福似乎就应该是跳出世间的幸福了吧?但对于庄子来说,并非如此。庄子所理解的“无待”并非是一个出世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种不同于“有待”的眼光与见识。因此,它并非是出世的,而是对现象界的一种超越——它要求的是转换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与视角,以无待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与周遭世界。以《逍遥游》中的寓言为例:鹏鸟之扶遥九万里固然是“大”,但这种大却是有待的:它需要鹏鸟翅下的空气才能成其大;况且,世间也还有比鹏鸟飞得更高更远的其他物类。反之,雀在树丛间跳跃虽显得矮小,但它却不需要高空中的浮力;而且,比起地面的蝼蚁来,它的跳跃又不知要高出多少了。所以,庄子不由得感慨: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1]此处之所谓小知、小年,不是从有待的角度来谈的,而须从无待的角度来理解才对。也就是说,在无待的眼里,无论是以小讥大,或者以大悲小,由于局限于一己的有待视野,终究是属于小知与小年,而真正的大知、大年,是那无待的眼光与视野。在无待的视野中,世间物其实是无所谓大、小之分的,幸福亦然。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庄子心目中的无待,就是教我们超越世间有限的存在,而去追求那精神性的无限。无待即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说我们在世间可以呼风唤雨,凭一己之主观意志任意妄为的自由,而是指在精神世界中,我们有可以改变对事物的看法与理解的自由。一旦确立了这种自由意识,我们就可以在世间寻找到可欲的幸福了,这正如雀哪怕在低矮的树丛中也可以享受到难以名状的快乐一样。
但在这里,我们或许还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鹏鸟之扶摇直上九万里所获得的幸福与雀在树丛间跳跃所获得的幸福,难道真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吗?回答是:唯唯否否。假如从世俗有待的观点看,鹏鸟之展翅凌空而上,的确给人一种志向高远、气势宏大的感觉;而雀在低矮的小树丛间跳跃,其志向并不高远,其视野并不开阔。从世俗的观点看,这是对的,因此,世俗的幸福往往是有待的幸福,既然是有待的幸福,它们当然是有大有小了。但假如我们从无待的眼光来看问题,则这两种幸福都是一样的,皆属于有待的幸福。可见,幸福之有大有小,只在现象界的有待世界里才有意义;一旦超出了现象界,关于幸福之大与小的说法,也就失去其意义了。所以说,幸福到底是有大有小,就取决于我们是用无待的眼光,还是以有待的眼光来看待与理解幸福了。
然而,讨论假如仅仅到此为止,尚未得庄子谈论“无待”的更深层用意。庄子以鹏鸟与雀的故事来说明幸福之不分大与小,其最终目的还不在要我们将鹏鸟与雀的幸福作等量齐观,而是教我们:尽管我们是有限的存在,生来具有种种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去追求幸福与享受幸福。应当说,庄子提出“无待”这个思想,是为了阐明个体如何去实现幸福的“幸福之方”的问题,这就是“顺生”。
所谓顺生,就是接受并且顺应我们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有限性。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有限的,而且是一种定在,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了这种有限性,就意味着无法成就另一种有限性。这对于我们每个人之追求幸福来说,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就好像我们生而成为鹏鸟,就无法享受雀之快乐,或者生而为雀,也无从去体验那鹏鸟凌空之幸福一样。但庄子通过“逍遥”与“无待”的讨论,教我们服从命运的这一安排。因为从“逍遥”的观点来看,逍即是遥,遥即是逍,它们在“本体”的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假如将幸福领会为真正精神性的幸福而非日常的快乐的话,那么,真正完美的幸福其实也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幸福,而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幸福其实是无分大与小的。所以,假如将幸福视之为一种精神性体验的话,那么,雀固然不应当讥笑鹏鸟之志,却也未必去羡慕鹏鸟之幸福。反过来也一样,鹏鸟不应悲悯雀的幸福观之卑微,也不必放弃自己的高远追求而学那树丛间的雀。总之,造物主创造了芸芸众生,那么,作为这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就应当接受这有限性的命运安排,并且在这有限性中享受与体验那造物主赐予的幸福!
乍看起来,庄子达到的这一结论似乎会使人对幸福的看法变得“悲观”,即现实中的完美幸福是不存在的,完美幸福只能在无待的本体界中寻获。其实不然。庄子关于无待的幸福,表面上看似乎有那么一种悲观或“顺受”的味道,骨子里却是乐观与通达的。乐观与通达不同于快乐,快乐毕竟是在现象界之中或人作为生物性存在所能够体会与享受到的,而唯有这种超出了普通快乐的无待的幸福,才是作为一个有精神生命的个体才配享受与能体验到的。既然我们已经成为有限性的存在,那么,我们都会享受与拥有这种生物性生存都能感受与体验到的快乐,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此之外,再去寻找与追求一份超出这种平常快乐的幸福呢?从这种意义上说,庄子不是教我们不食人间烟火与逃离人间快乐,而是教我们不要将日常快乐就当作幸福,更不要仅仅满足于人间快乐。人的生命包含着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这两种维度,造物主赋予我们每个独特的个体以两个生命: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那么,我们为什么只选择其一,放弃其二,而不去将这两种生命都加以实现呢?
由此,我们认识了庄子:一个不逃避幸福,毋宁说是向往幸福,并且对幸福有着执著追求的庄子。但庄子对于幸福的理解又是异常地通达与彻悟。准确地说,是在意识到人的有限性的存在之后,面对这种有限性存在的一种通达。因此,庄子不仅教人接受个体命运的安排,更教人去承担。接受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而承担则意味着去实现。因此,所谓顺生不是消极地承受现实,无为地接受命运加之于人的一切,而是将造物主强加于人身上的有限性,视之为完成人的无限性的前提条件与现实载体,从而去再造生命。而这种经过再造的生命由于已经在有限的生命中融贯了其对于无待的向往,就不再仅仅是有限的生命,而是生物性生存的有限性与无限的精神性合一的生命,这才是人的真实的,或者说得以完成的生命。
因此,庄子提倡人生要作“逍遥游”。庄子将包含“鹏雀之喻”这个故事的篇章命名为《逍遥游》,是一种点睛之笔。在庄子那里,个体对幸福的追求其实是通过“游”来实现的。庄子提倡“游于方内”,方内也即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以有限方式存在的,现实世界的人亦然;所谓游于方内,不是教人仅仅作为有限性的存在物而存活,而是教人如何在这有限性中体现那无限的存在。人如何才能在有限性的世界中活出个无限来?庄子的“鹏雀之喻”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造物主创造了鹏鸟与雀,这为它们去追求幸福提供了生物性的前提条件,但它们应当是各自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追求与实现幸福,这才是它们各自生命的最终完成。否则,它们就仅仅是作为有限性的存在,而无法实现那无限性。故而,幸福的真谛其实是生命的真谛,生命的真谛是以造物主赋予每个个体的“形式”去追求与实现那各自的幸福。这各自的幸福是无法彼此比较其大小的;对每个个体而言,幸福的方式是顺生:安于与接受造物主的安排,在有限性中去完成自己,这样才可以获得幸福。
“逍遥”即“游”, “游”即“逍遥”,庄子这一思想是对个体如何成就幸福的深刻思考。它表明:个体幸福的实现其实是追求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合一的过程。假如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能够合一的话,这就达到了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此亦即“自然律与自由律的合一”的完成。而对于庄子来说,这一值得期许的美好幸福并非空想或纯粹的理论思辨,它的确是可以通过个体的生命实践去完成的。
二、适意:幸福“由我作主”
庄子的“逍遥游”给人的另一种启示是:衡量真正幸福与否的尺度是“适意”。这也意味着:幸福是给自家享用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有的人在他人的眼里看似幸福,其实他未必真的幸福;也有的人的生活在他人眼里似乎难以是幸福的,甚至是悲苦的,可是,就在这种常人或他人难以理解的生活状态中,他却体会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这说明:幸福说到底是人作为主体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与精神体验。心理类型不同,精神向度不同,其对于幸福的理解,以及对幸福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既然幸福源自于个体的真实生命感受,那么,就不用在乎他人对幸福的看法如何,也无须顾及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对幸福的理解了。我们每个人,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方式去追求与实现幸福。
然而,所谓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方式,又意味着什么呢?对此仍可深究。我们作为个体的人活在世间,其行为与处世方式,有许多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比如说:工作要遵守纪律,上街要遵守交通规则等。除了这些社会生活的共同规则必须遵守之外,还有一些个人的行为或者个人意愿,从表面上看,它们好像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其实并非真的“自我作主”,而是由外在因素在间接地起作用并决定,这就好比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之喻”。就人这个个体作为有限性的存在来说,也许“身不由己”是我们的宿命。所谓“身不由己”是说我们每个人作为有限性的存在物总是无法摆脱现象界加诸于我们的限制。但是,现象界的这种限制却不能强迫我们去做连“自己”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否则我们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对幸福的追求好像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去做的,但它并未给我们带来幸福,其原因也就在于这种“由我作主”的似是而非的性质。
看来,讨论幸福是否真的由“我”作主,的确成了一个问题。为此,要对“我”是什么,以及如何理解“自我作主”,做一种语义上的分析。
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发现,我们每个个体包含三个我:自我、本我、超我。自我是现实当中作为社会角色出现的我,显然,这种自我多半是以适应人的社会性生存为目的的,但人在完成或实现这种社会性角色的活动过程中,未必一定能获得幸福。也就是说,幸福虽然不必然与社会性角色的我相排斥,却也未必就与它相融契;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人的作为社会角色的我与个体幸福相冲突或不协调的例子。因此,所谓个体的幸福由我作主,显然不是指由作为社会角色的我来作主。超我是指人所向往的一种理想人格,这其中,道德人格是最重要的内容。然而,且不说不同的人的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不一,对于道德内容的理解也因人而异,重要的是:道德人格固然是人所向往的一种人格,然而,道德人格是指个体自愿或者自觉的一种生命追求,这种生命追求属于个体赋予他自己的“应然”,而从个体的心理体验来说,应然属于一种道德人格,却不能与个体的幸福完全划上等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例子是:不少人正是由于牺牲了个人对于幸福的追求,才得以完成其道德人格或得以实现其道德的意志。因此,只能说:道德人格的建构可以使人感受到生命的尊严与崇高,但它本身并不是幸福;或者说,道德的尊严与崇高虽然不与幸福相排斥,却终究不能代替幸福。因此,所谓幸福由我作主的我,也不可能是超我。
至于本我,是依快乐原则行事的,它似乎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幸福的意思相接近。然而,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本我有其特定的涵义,是指个体的“性欲”的最大满足;尽管这里对“性欲”可以给予一种较宽泛的理解,但说到底,它毕竟还是一种生物性或生物本能的欲望的满足。因此,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也无法充当“由我作主”的我。
既然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我”出发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那么,再来看看庄子。按照庄子对幸福的理解,幸福既然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那么,决定幸福的就应当是一个精神性的我了。或者说,既然幸福是指精神性的幸福,那么,能满足或者实施这种精神性的幸福的行为主体,必定是精神性的个体存在。所以,对于庄子来说,幸福的获得只能是由作为精神人格的我作为主宰。但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说精神性的幸福应当由精神人格的我作主,并不是说有一个可以脱离开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以及道德性的我而另外存在的我,毋宁说,精神性的我就内化于人的本我、自我以及超我之中,是人之精神人格对它们的导引。为了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自我、超我相区别,这种作为幸福之基石的我,可以称之为“真我”,庄子称这种真我为“吾”。为了与其他的“我”相区别,或者说不要让这个“真我”被其他的“我”所遮蔽或替代,庄子提出的“幸福之方”是“吾丧我”。庄子严格区分我与吾的做法,对我们讨论幸福究竟由谁作主这一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
对于庄子来说,幸福的追求首先要符合个体的精神性人格,也就是适合真我之意。个体的行为或活动是否给人带来幸福,就是要适合自己,这里的自己指真我。我们平常的行为或活动未必是由这种真我所选择的,其结果就未必能使人感到幸福,这是适意的其中一种含义。但适意除了这种含义外,还有一种更深的含义,这就是要适合个体的生命存在类型。因为我们说真我不能与人的其他各种“我”脱离开来,毋宁说它是对其他“我”的导引。这就好比其他的“我”是一匹马,而“真我”是驾驭这马的骑手一样——优秀的骑手固然不会放任马随意地跑,但他对马的驾驭也一定会顾及马的性状与脾气,从而让马服从他的召唤和命令。因此,“吾丧我”除了肯定真我之存在外,其积极意义还在于强调这个真我对于其他我的统辖与支配作用。此亦即适意不仅仅是适真我之意,还包括要适合个体的具体的感性生命内容。而正是适意意味着适合个体的感性生命内容,我们才看到了个体幸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换言之,大千世界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幸福,就源自于个体对幸福的追求有各种生命类型。故适意者,也即适合于不同的幸福生命类型也。以“鹏雀之喻”为例:鹏鸟有鹏鸟的幸福生命类型,雀有雀的幸福生命类型,适合它们生命类型的,即为幸福,否则是不幸福,甚至是痛苦。所以,对于幸福的追求来说,雀不必去效仿鹏鸟之幸福,鹏鸟也无须去称羡雀之幸福。它们各有各的幸福。假如生而为鹏鸟却想获得雀之幸福,或者生而为雀却想获得鹏鸟的幸福,则是不适意的。不适意则不幸福。这种不幸福与其说是根源于个体的感性生命类型的限制,不如说是违背了个体的幸福要与个体的感性生命类型相适应这一适意原则,从而导致了个体的精神性存在与其感性生命存在的分离。这样看来,个体对幸福的感受与体验具有差异性,乃源自于个体感性生命类型的不同。应当说,个体感性生命类型的多样化,是宇宙生命与人类生命进化的结果,面对这种进化,我们无法改变它,而只有接受它,且从享用幸福与体验幸福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成全它。也就是说,正因为个体的感性生命分化为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每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才可以去选择与领略各自不同类型的幸福。个体生命对幸福的感受划分类型则意味着任何个体再也无法包揽与体验所有幸福,但幸福类型的分化却有利于个体感受与体验幸福之深刻。而作为个体的人来说,与其说是希望体验多种的幸福但不深刻,毋宁说我们更愿意去获得某种极其深刻的幸福体验。而幸福与快乐的区别,以及幸福质量之高下的真正分野也就体现在这里。
三、无执:幸福作为过程
以上,我们讨论了庄子哲学中关于幸福的两个概念:顺生与适意。顺生指的是要承受个体生命作为有限性的存在,幸福的实现就在每个个体的有限性存在之中。适意指的是个体幸福的独特性,强调每种生命类型都可以体现与实现幸福。然而,无论顺生或者适意,它们谈的都是现实中的个体存在如何获得幸福的方法与门径,这就预设了幸福似乎是一种个体须去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
这种对于幸福的理解并无谬误之处,然而,它还不能遍及幸福生活的所有内容。换言之,假如作为个体的常人或凡人这样去理解与追求幸福的话,这并不为非,但是,这种常人或凡人能够追求或获得的幸福,并不能涵盖关于幸福的全部意义。换言之,幸福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或精神世界,还有它的为常人或凡人所难以企及处。唯其如此,它值得我们向往并去追求。作为一种可以达到的具体人生目标的幸福,与作为一种理想或理念而难以达到的幸福,这两者都可以成为生活的动力,但其对于个体精神生命之意义来说却是不一样的。因此,当讨论了常人或凡人可以期盼或可能获得的幸福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作为人生之不可企及或难以企及的幸福理想或幸福理念。这种幸福理想或理念尽管不存在于或难以存在于现象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只不过,它是存在于更为纯粹的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然而,对于追求幸福的人来说,它仍然是需要的。有谁能说:人生在世,只需去追求那仅存在于现象界的东西或事物呢?也许,悬置一种明知不可实现或难以实现,却仍然要去追求与寻获的幸福,这本是作为有限性的理性存在物的人的特权,也是人作为人之价值与意义所在。动物与其他生物仅会对现象界之现实存在的东西与事物发生兴趣;唯有人,他的兴趣是超出现象界之实存层面的,他对于幸福的探究也是如此。那么,这种不存在或难以存在于现象界,却存在于纯粹精神世界的幸福,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了与前面提到的常人或凡人能够企及的幸福相区别,在这里,我们将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的幸福称之为“纯粹幸福”。这种幸福,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一种“无执”的幸福。或者说,无执是纯粹幸福的同义词:假如个体真的是处于无执的状态时,那么,他可以说就达到纯粹幸福了。反过来说,假如要获得纯粹幸福,这意味着个体是生活于无执的世界之中。那么,究竟什么是无执?
所谓无执,是破一切执。这一切执包括我执和法执。我执容易理解,指的是对人的有限性的执著。前面讲到的顺生,既是对个人有限性的一种顺应,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个体生而俱来的有限性的一种破除,而对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先天生物性差异作等量齐观,此谓之破俱生我执;而所谓适意,既是对个体的感性生命形式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各种后天“我”之执著的破除,此谓之破分别我执。无论是破俱生我执抑或破分别我执,它们都是常人或凡人所希冀的幸福所必具的前提条件。
然而,对于真正的或纯粹的幸福来说,仅仅破我执还不够,还必须破法执。何谓法执?我们看到,前面所谈的顺生与适意,固然包含了破我执的因素,甚至庄子还提出了“无待”的概念,但这种破我执以及无待的幸福,仍然是有其执著。其执著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关于以幸福作为人生目标,以及如何去达到这种人生幸福的观念。这种对于幸福观念的执著,就是一种执著。而从真正的无执来看,幸福是不应当作为一种执著的目标去加以实现,也无须去实现的。因此,“幸福”既然是一种执,那么,以无执之法眼观之,它并不存在。或者说,假如它真的存在的话,也只能是一种“幻相”。故《中论》云:“如幻亦如梦,如乾闼婆城;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2]
以此观之,顺生与适意对“执著”的破除并不彻底。这是因为,任何顺生与适意对于幸福的追求,仍然预设了一个与有待相对的“无待”的幸福目标,并且肯定追求幸福之主体的个体“我”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顺生与适意对于个体之“我”来说,只是一种实现幸福的手段与工具,而非真正的幸福本身。而真正的“破执”或者说“无执”,不仅要破除将幸福作为一种目的去追求的执著,而且要破除作为追求幸福之主体的“我执”。当然,这不意味着对顺生与适意的否定,而毋宁说是对顺生与适意作为幸福的一种新的理解。换言之,世间本不存在一种要让个体去追求与实现的绝对意义上的或本体意义上的“幸福”;任何个体,只要它的行为与活动是顺生或者适意的话,那么,他就是幸福的。
这样看来,无执并非是对顺生与适意的消解,毋宁说是对顺生与适意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肯定。也就是说,本来是作为达到幸福之门径与方法看待的顺生与适意行为,其本身即是幸福。故无执的幸福观的根本意思是说:幸福不是作为个体要达到的目标出现的,而追求幸福的过程本身——顺生与适意就是一种幸福。看来,这与其说是将幸福视为人生要去追求与实现的终极目的,不如说是视幸福为一种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幸福不是对象性的存在,也不是作为先验目标而存在,而是呈现为生活的风格与状态。任何个体活动只要是顺生与适意的,那么,个体本身就已处于幸福之中了。
说到这里,要防止对无执的错误理解。无执不是要取消一切活动,包括幸福活动;而只是说:这一种活动,包括追求幸福的活动,其本身应当是无目的、无意念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无我”的。这也就是禅宗所说的“三无”:“无念”(无作为理想或理念的幸福)、无相 (无作为对象或目标的幸福)、无住 (无作为追求幸福之主体的我)。六祖慧能的偈子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3]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这种关于无执的幸福的理解,也包含在庄子的思想中。但那是另一个庄子,一个不同于提倡“逍遥游”的庄子。假如说在《逍遥游》中,庄子借“鹏雀之喻”表达的是对于顺生与适意的幸福的追求的话,那么,在《齐物论》中,就出现了另一个庄子:一个将幸福理解为“无执”的庄子。
所以,在《齐物论》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庄子将幸福作了这样形象化的描绘:“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就在这种“庄周梦蝶”的“物化”过程中,庄周与胡蝶实现了角色的互换,而这一互换的结果就是“无”:无所谓庄周,无所谓胡蝶。或者说,庄周就是胡蝶,胡蝶就是庄周。每一个有审美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才是审美之极致。审美之极致也就是幸福之极致。故无执的庄子在这里提倡的是作为一种审美之极致的幸福。
这种幸福或许难以出现在人间,但它却是真实的存在;其存在之真实一点不亚于存在于现象界之真实的幸福。现象界中的幸福或许是多变的,有多种形态的,而无执的幸福是唯一的或绝对的幸福。它或者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涅槃”,或者是庄子所说的“天籁”。但确切地说,它又并非完全脱离人间烟火。换言之,它其实是要在人世间修出世法,要在多变的幸福与多种形态的幸福中达到那不变的、唯一的幸福。这种幸福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将个体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合一的幸福。不过,它是以无限为体,而以有限之肉身为用。这种以有限作为达到无限之工具与手段,其幸福的落脚处已不在有限的现象界,而在超越的本体界。故而,幸福的有限性与幸福的无限性通过无执的方式终又获得了统一。对于执著于这种幸福的个体来说,它并非只是虚幻或不切实际的梦想,而是仍然要在人世间实现的幸福。不过,它已远远超越了尘世或世间的幸福或快乐,而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性幸福。
如何比较无执之幸福与顺生和适意的幸福呢?应该说,这两类幸福都是个体值得追求的幸福,其不同之处在于:顺生和适意将幸福落实于人间世,其幸福的含义更多的是世间的幸福。这种幸福对于个体来说可以说是完美的幸福,但它毕竟由于落实到现象界,故又只是一种“有限的幸福”。换言之,我们每个个体生命在现象界中获得的,只能是有限的幸福。但除此之外,作为幸福的理想,个体还应当去追求那无执的幸福。无执的幸福要求彻底泯消一切差别,包括泯消个体我的“有执”。这其实是一种超越了世间的有执幸福才能体验到的幸福。
这两种不同的幸福,王国维分别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来加以概括。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出。”[4]在这两种幸福中,世界都是以审美的方式呈现的。这两种幸福都值得欣赏,作为幸福都值得追求与向往。然而,前一种幸福是人人通过努力追求而可达的,后一种幸福却不必人人能达,或者说是常人难以达到的。能够达到或体验到这后一种幸福的人,可称之为“圣人”。孔子晚年所谓的“六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对这种圣人式的幸福感的体验与说明。无执的幸福已不是将幸福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要去加以实现,而是将之作为生命的一种境界去追求与实现,它已经消解了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幸福,其对于生命的意义与看法已发生了根本转变。对于这种人来说,幸福不是其他,而属于人生的一种境界——无我之境。
四、幸福的中观之境
然而,假如将幸福视之为境界的话,那么,无我之境还不是最高义的或胜义谛的幸福。这是因为:这种幸福虽然破除了一切执,但这种非要破除一切执本身,仍然是一种执著——对无执的幸福的执著。也许,从最胜义来看,真正的或彻底的破执是破而不破,不破又破,或者说既破执又不破执。假如从这种对破执的理解来看,我们就进入了中观的视野。也许,这才是一种完满的幸福。
所谓完满的幸福,①在这里,完满的幸福的涵义不同于上面所说的通过顺生或适意可以达到的现象界中的“完美幸福”,本文认为,完满幸福是一种关于幸福的理念,而完美幸福是指世间可以获得或实现的现实幸福。意味着它是一种既包括有执的世间幸福,又包括无执的出世间的幸福的幸福。因为只有有执的世间幸福与无执的出世幸福之合,才可以称得上完满意义上的幸福。在这种完整意义上,有执的世间幸福与无执的出世的幸福终于统一起来了。或者说,由于同时具备有执的世间幸福与无执的出世间的幸福,于是幸福才谓之完满。问题在于:这如何可能?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问:什么是中观?
《中论》云: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就是有名的龙树“中观四句教”。然而,对于这四句的理解,历来说法不一。有一种解释是: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它们实质上是“空”;虽然是空,但作为“假名”之有,它又是存在的,并非空无所有。假如对四句教作如此的解读的话,那么,除了同时肯定假名之有与空皆为存在者之外,它并没有提供更多的意义。假如以此看法来解释幸福,它除了承认作为假名的世间幸福与作为空之出世的幸福可以并存之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意思。
看来,作为一种试图兼容两种幸福的中观理论,其对幸福的理解当不如是。那么,如何理解这四句教的意思?这当中,智者大师的看法可谓深得其中三昧。他解释四句教说:“……若一法即一切法,即是因缘所生法,是为假名,假观也。若一切法即一法,我说即是空,空观也。若非一非一切法,即是中道观……。”[5]依智,一即一切法,是属于现象界的事;而一切法即一法,属于本体界之最高存在。移用于来理解幸福,则可以说:现象界的幸福是假名;而作为本体之最高存在的幸福是空。这两种幸福皆为幸福。
“观”,简单地理解,也就是人为的看法。这里看来,有执的幸福与无执的幸福皆取决于人观,假如没有人观的话,也就无所谓有执的幸福与无执的幸福了。所以,智认为,依中观的理解,若非一非一切法,即是中观观。在这里,所谓非一,是指非“一法即一切法”,所谓非一切,是指非“一切法即一”。看来,只有对这二者加以否定之后,才可以称之为中道。假如移用于对幸福的理解,所谓中道的幸福,就是既否定假名的幸福,亦否定空的幸福,然后才实现的。
问题是,假如真是如此,两种幸福皆否定的话,那么,幸福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幸福到底何所指?这里要注意的是:智否定的是人观,而并非否定中道观或中观。在这里,中观是以对两种人观否定的形式出现的,但作为中观,它并非“无观”,更不是人观。什么是中观呢?其实,在龙树的四句教的后面,紧接着有下面的四句话: “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6]这四句话可以说是中观的正面的意思。但它的意思又很难完全用文字表达出来。总的来说,它想说的是:所有的“法”,包括一法与一切法,其实都是从“因缘”生出来的。假如移用于对幸福的理解的话,它的意思是说:无论作为一法的本体之最高幸福,还是作为一切法的现象界之幸福,其实都由因缘和合而生,其原因是因为所有的法,包括一法与一切法,都对于人来说才有意义。作为一法的幸福与一切法的幸福来说也是如此。
换言之,幸福不是可以脱离人之个体存在的独立存在,只要我们追求幸福,我们都只能在个体的存在当中去追求幸福。那么,这所谓的幸福,包括有执的幸福或者无执的幸福,只有对人来说才有意义,或者才会存在。其实,这也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没有世界,只有世界化”的意思,假如将这话引申一下,可以这样说:“没有幸福,只有幸福化。”原来,通过中观,我们终于知道了:幸福不是别的,只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观或者方式。
说到这里,真正的中观的意思,并非只是否定式的,并非只是对两种幸福观的否定。毋宁说,它是在揭示了两种幸福之来源或产生之根据之后,再确立一种中道的幸福观。
这种中道观的幸福观既不落于两种幸福的哪一边,也不否定这两种幸福的任何一边。而是既肯定两种幸福,又否定两种幸福;在否定两种幸福之后,又肯定两种幸福,如此而无穷。这种说法似乎难以理解,甚至有点神秘。
其实,依中观,既然幸福对于人之存在才有意义,而作为个体的人之存在属于一种有限性的存在或“偶在”,我们要在这种偶在中寻找或发现幸福,就必然无逃于人观的命运,或者说,总不得不以人观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包括幸福。而人观的世界与幸福无非两种:有执的与无执的。就执而言,它们是等价的,无法比较高下的,只是观之不同所决定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人观有这两种,而在于这两种观还以悖论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假如我们采取有执的眼光来理解与看待世界和幸福,就无法采取无执的眼光来看待与理解世界和幸福。反之亦然。因为我们作为有限性的个体,无法在同一时间点采取两种不同的观物方式。这也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体的人,无法同时获得有执的幸福与无执的幸福。即使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获得两种幸福,其实是以其中一种取代或者置换另一种幸福的内容为代价的 (就是关于无执的幸福是以无执来代替有执,将有执的幸福视之为过程,然后等同于无执的幸福一样,这种无执的幸福不是彻底的无执的幸福)。
应当说,对此幸福的悖论,中观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或者说,中观之提出就是为了消除个体在追求幸福时遇到的这种悖论。如何解决这种幸福之悖论呢?中观认为,所谓的有执幸福与无执幸福,既然是作为人观才出现的,因此,这两种幸福并不具有绝对本体的意义,而仅仅是一种关于幸福的“方便说法”而已。方便说法也即“随机说法”:根据不同的时间点、环境与机遇,而随时随地变换自己的视角或者说观。
这样看来,作为人观的有执幸福与无执幸福,并非既定不变的,而是可以而且应当随时调整的。换言之,在某些时间点,我们可以采取有执的幸福观,在另一些场合或境界下,我们可以采取无执的幸福观。而在任何时间点与环境中,我们不是采取有执的幸福观,就是采取无执的幸福观。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任何时间点,不是获得有执的幸福,就是无执的幸福。这样的话,我们不就在任何时间点,都可以获得幸福了吗?这样看来,中观的看法似乎是将在同一时间点同时获得两种不同的幸福替换为个体是否能获得两种不同的幸福这一问题。
但仅仅于此,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因为问题很可能是:人们可能会变得随心所欲,想要采取哪种幸福观就采取哪种幸福观,并且将任何对于幸福 (包括快乐)的享受都称之为中观幸福。这种情况在世间不是没有,而很可能会是普遍存在的。这其实是一种“伪中观哲学”。中观之所以反反复复以否定之形式出之,提出“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6]智之强调“若非一非一切法,即是中道观”,其道理也在这里。
因此,完整的中道观是既肯定而又否定,既否定而又肯定,肯定之后旋又否定,否定之后又再肯定……如此循环以至于无穷。为避免对中观作僵死化、绝对化、概念化的理解,中观的表达式应当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非一即一切,非一切即一;非非一即一切,非非一切即一……
假如明白了中观的表达式,那么,将其用于对幸福的理解,我们发现,它所要传达的是如下信息:
1.分别两边的幸福。对于中观来说,有执的幸福与无执的幸福皆为幸福。故中观幸福其实是肯定两种幸福。
2.两种幸福的相互转化。对两种幸福的肯定不意味着两种幸福的绝对化。换言之,有执的幸福会转化为无执的幸福,无执的幸福也会转化为有执的幸福。
3.两种幸福的相互依存。所谓相互依存,不止是说有执的幸福以无执的幸福之存在作为前提,反之亦然;而且是说这两种幸福相互补充而不可彼此替代。
4.不落两边的幸福。虽然有执的幸福与无执的幸福无法彼此替代,但不意味着分别两边的幸福就是全部幸福。换言之,有执的幸福与无执的幸福之相加不等于全部幸福。
5.两种幸福的相互渗透。有执的幸福与无执的幸福不仅相互转化,而且彼此渗透。也就是说,有执的幸福当中有无执的幸福,无执的幸福当中亦有有执的幸福。
由是看来,在中观眼里,真正的或完满的幸福是必得包括如上几个方面的内容,而又不囿于或固执于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但是,它又不是这所有方面的幸福之和。换言之,中观幸福是可以随时随地改变其面孔,但无论如何变,万变不离其宗,它又必得体现中观幸福的这个特性。
要注意的是,中观幸福作为总体幸福虽然包括幸福的这几个层面,但它在具体的某一时间点,却又必体现为这其中的某一种幸福,或者说,是以这某一种形式的幸福来渗透其中幸福。那么,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呈现为某一种幸福呢?中观将这归结为“机”。所谓机,既是机会与机遇的意思,但又是“随机”的意思;故机与其说是静止与固定的,不如说是动态与随机的。或者说,机会与机遇与其说由外部条件所决定,不如说是由主体随时根据客观情况与环境来调整自身的。因此,把握好机,就随时随地无往而不幸福。到了这时候,这就如禅诗所说的那样:“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眼前所见,无不是美丽的事物。这时,他已无须用审美的眼光来打量世界了,因为审美与美已合而为一。
如何理解这种中观的幸福呢?这种中观幸福使我们想起了禅宗。在某种意义上说,中观幸福确是像禅宗那样强调幸福是由“心”定。只要主体心境幸福了,那么,外部世界的一切无不会作为幸福的对象物而存在。按照禅宗的说法,“平常心是道”,只要去除心中一切执著妄念,保持一颗平常心,那么,则无往非道,无处非道,无时非道。而且,道就是眼前。假如将道换成幸福的说法,也就是说无往而不幸福,无时无地而不幸福,幸福就是眼前。就强调境由心造这点来说,中观与禅宗的看法是一致的。
看来,将幸福视为一种心境,这种说法似乎有些主观。但是,作为一种关于幸福的心理体验,它的确是真实的存在。这种对于幸福的心理体验不同于对无执的幸福的心理体验,在于它体验到的幸福是遍布于一切事物之方方面面而非像无执的幸福那样只朝往一个方向的单向度的幸福,是无时无刻不在而不像无执的幸福那样要在过程或活动中才出现的幸福,是当下呈现的而非像无执的幸福那样依附于现象界中的具体事物来实现的幸福。
总之,幸福体验的弥漫性而非直线性、恒常性而非流动性、当下呈现性而非依存性,是中观幸福不同于无执的幸福的特点。看来,就幸福的体验来说,这其实是一种主体的心之境界,是一种较无执的幸福之境更高层次的幸福境界。唯其如此,对于常人或凡人来说,它不仅难以达到,简直可以说无法攀登。虽然常人无法达到与体验这种幸福,但不等于这种幸福是不存在的。通常,常人只能感受与体验常人的幸福,而无法感受非常人的幸福;但常人虽然无法感受与体验,但却可以思议非常人的幸福。而中观的幸福就属于这种超出常人所能感受,但凡人却可以思议的幸福。真正获得并享受中观幸福的人,我们称之为“真人”。
五、结语:幸福的境界与分层
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了。上文中,我们从如何追求幸福这个问题开始,发现有四种获致幸福的方式:顺生、适意、无执、中观。其实,它们既是实现与达到幸福的方式,同时也属于不同的幸福类型。因为追求幸福的方式不同,往往就决定了我们能感受或体验到何种幸福。换言之,它们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与方法,同时也是幸福本身。于是,作为幸福的方法与本体在它们之中达到了合一。这四种方式都是幸福,但它们的幸福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孟子说:“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大而化之之谓神,神而不测之谓圣”,用于比喻这四种不同的幸福是最适当不过了,其中,各人追求各自向往与适合自己的幸福,可以说是一种“可欲之谓善”的幸福。但何为适合自己?真正的适合自己是适合“真我”,只有将个体的真我完全扩充与呈现出来,才是幸福,这是一种“充实之谓美”(即将真我呈现出来,个体才由衷地感到充实)的幸福。而彻底破除任何执著,包括消除了“我执”和“法执”,强调幸福是一种“无人我”与“天人合一”的状态,这才是“大而化之之谓神”的幸福。但这还不是幸福之极致。最高义的或第一义的幸福是既不追随任何既定目标与方向,同时又无往而不适的幸福,这种幸福深不可测,甚至不可思议,已经属于“神而不测之谓圣”的造化幸福了。
就这四种幸福方式来说,前面两种 (顺生与适意)是我们常人可以达到的幸福;无执的幸福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幸福 (达到的话可以称为“圣人”);中观的幸福是常人无法达到的幸福 (达到的话可以称为“真人”),虽然无法达到,但它可以思议与想像。这种思议与想像对于我们去追求幸福并非是多余的。
有人说,常人还是去做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无须去为那些明知努力而不可达的事情操心,对幸福的追求也应如此。问题在于:对于幸福来说,假如我们放弃对幸福理想的追求,不去为之努力与操心,又如何知道我们获得幸福的能力与限度究竟在哪里?
从这点来看,只能说,作为最高义的中观幸福,虽然就目前的人类来说,我们是无法达到的,但岂知到了哪一天,当人类的进化真的向“真人”的方向接近,那么,我们人类或许也就会实现中观的幸福。因此,中观的幸福虽然目前不可达,不等于它对于人类来说就永远不可达。而且,即使它在目前还不可达,但我们却可以想像,而这种想像还可以成为我们追求幸福的动力;而对于人类来说,甚至愈是难以达到或无法企及的东西与事物,就愈会激发起我们去追求它的雄心与勇气,这是由人作为“有限性的理性存在物”这一本性所决定:由于人自觉到他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所以才会要去追求与实现那超越了有限性的无限,对于幸福的追求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只要追求形而上学依然是人的本性的话,那么,对中观幸福的向往与追求也就会与人类的活动相始终。
[1] 王夫之.庄子解·逍遥游 [Z].
[2] 龙树.中论·观三相品[Z].
[3] 慧能.坛经 [Z].
[4] 王国维.人间词话[Z].
[6] 龙树.中论·观四谛品[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