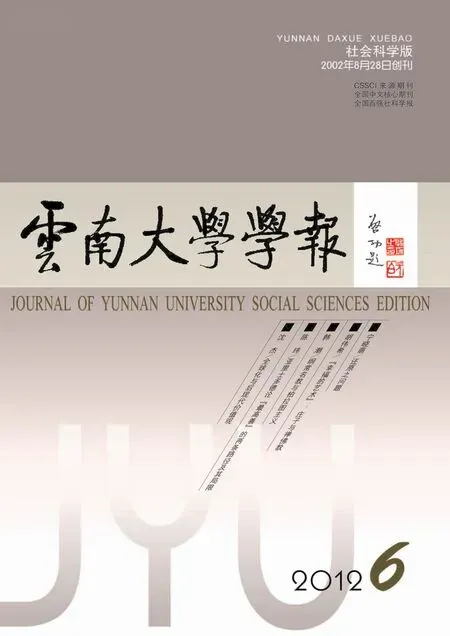诗与故事的联姻
——宋诗中的“传奇”与“志异”
2012-12-09周剑之
周剑之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中国古代诗歌历来被认为是抒情言志的文学体式,已有研究多从抒情角度观照古典诗歌,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诗歌所具有的叙事性。事实上,古代诗歌存在着一条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相互交融,共同构建了中国诗歌的特色。①目前一些学者已意识到忽视叙事视角可能会给古代诗歌研究带来的偏差,董乃斌在《古典诗词研究的叙事视角》一文中指出,对叙事视角的忽视不但会局限解读诗词的深入程度,而且不利于对整个中国文学史面貌的描述理解及对其贯穿线的认识概括。见《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蔡英俊的《“诗史”概念再界定——兼论中国古典诗中“叙事”的问题》(《语言与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也指出了这一点。“叙事”一词是中国原本就有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叙事学对叙事的定义。古代诗歌领域中的“叙事”是多层次的,既包括富含起伏情节的叙事,也包括片段式的纪事、载录式的说事等多种叙事形式。②关于古典诗歌中的“叙事”内涵,以及纪事、说事等诗歌叙事方式,笔者将撰写它文以进一步说明。不过,当我们试图重新发掘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时,富于情节、叙事性鲜明的故事诗的确是进入叙事探索的一条重要路径。
从诗歌史上看,经由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发展,诗歌缘情的特点一步步强化,并形成了唐诗以情为主的艺术风貌。其间虽有一些讲故事的名作,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以及白居易的《长恨歌》、韦庄的《秦妇吟》等,情节相对完整,人物形象突出,但以诗歌形式来讲故事、并且讲得精彩的,终究只有少数。而在进入宋代之后,以诗歌讲述故事的行为却多了起来,诗与故事之间实现了更为紧密的结合,成为宋诗中一个颇为突出、但却尚未被学界关注到的现象。本文以宋诗中的传奇志异诗为主要对象,尝试考察其所体现的宋诗叙事的倾向、及对于古代诗歌叙事传统的发展。
一、宋代的“传奇”诗与“志异”诗
“传奇”本是文言小说的一种体裁,始创于唐,也以唐代最盛。从内容上说,它兼具轶事、志怪的特点;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又有其独特之处,情节比较复杂,描写比较细致,叙事比较委婉。《长恨歌》就可以说是诗歌中的传奇,并与唐传奇中的名篇陈鸿的《长恨歌传》互为表里。尽管《长恨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这类作品在唐代仍然不太多。传奇式的诗歌在宋代越来越发展起来,通常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其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其特点是描写细致,叙述委婉,而人物生动,情感细腻。
宋代传奇体诗歌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以女子为中心、涉及男女情爱的题材最多,如梅尧臣的《花娘歌》、《一日曲》,孙次翁的《娇娘行》,徐积的《爱爱歌》,柳富的《赠王幼玉》,王山的《答盈盈》等。《花娘歌》写花娘与情郎之间的爱情故事,写两人由相识相恋到海誓山盟,然而突然发生变故,被迫分离,最终留下深深的遗憾[1](卷14,P236)。《爱爱歌》则写一名出淤泥而不染的女子爱爱,出生娼家却洁身自好,努力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与相爱的人私奔,逃离了娼家;但后来情郎被父亲追回江南,并在江南去世;爱爱则独居京师,以未亡人自称,无论其他追求者如何富贵,始终不动心,直至死去。[2](卷3)
另一类传奇式诗歌不太涉及恋情,以叙写人物的生平经历为主。这些人物通常都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如高荷的《国香》诗,叙写一位女子的经历。据诗序所言,黄庭坚曾与这位女子为邻,觉得她“幽闲姝美,目所未睹”,然而她却嫁给了下俚贫民,因此黄庭坚作诗云:“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高荷此诗,先写此女与黄庭坚比邻而居,后来嫁入小民之家;再过数年,黄庭坚去世,此女被丈夫卖给了田氏;田氏邀请诗人,请出此女同饮;坐间闲话当年,说起黄庭坚“可惜国香天不管”之诗,感慨不已;然而时间不可追回,诗人只能请求田氏为此女改名为“国香”,以追念黄庭坚当年的赏识[3](21册,卷1264,P14242)。此外又如刘敞的《阴山女歌》描写出使辽国时所听闻的阴山女子,晁补之的《芳仪怨》写南唐君主李璟之女李芳仪的生平。此外,一些诗人还开始关注民间女子的情感生活,如张耒的《周氏行》写一名船家女子的单恋,李吕的《贞妇》写一名洁身自好、不为金钱所动的农家贞烈女子的故事等。
同时,游仙的题材也进入了宋代诗歌的表现范围。喻良能的《天台歌》就是对刘晨、阮肇游天台遇仙人的故事的重写。邹浩的《悼陈生》也是一篇游仙的传奇之作。诗歌写陈生乘舟行于海上,突遇风暴,幸免于难,且获游古天宫院蓬莱峰;不久后陈生想要回去应举,不顾天宫人的挽留,执意回到家乡,才发现妻儿早已死去多年;而陈生再想要回归仙境蓬莱已不可得了,最终他发狂而死。陈生的经历与刘晨、阮肇游仙台的经典故事大体相仿,而又在诗人的详细描写中更显精彩。
除了传奇式的诗歌,还有一类诗是以记录异人异事为目的的。这类诗歌在叙事上相对简短,不像传奇体那么细腻曲折,而是重在表现其人其事异于平常之处,与魏晋南北朝盛行起来的志怪小说相类。
志异式的诗歌以记述神奇怪异的事情为主。李彭的《蝴蝶诗》写自己的朋友杨昊客游在外,一日暴卒,然心中不舍妻儿,竟化为蝴蝶飞回妻子身边,徘徊不去;刘敞的《蒋生》写广陵蒋生死十四年,其尸犹温,妻女闭门守之,却有家书从远处寄来,正是蒋生笔迹,才意识到蒋生是得道成仙了;一次大火过后,惟有破屋数椽屹立于灰烬中,却是洒扫街巷的一名贫妪的家,林希逸的《纪异诗》记录了这件异事;某天夜晚,欧阳修看见天空昏黑如有一物,其声咿咿呦呦,家中老婢说这是叫做鬼车的大鸟,载着千百鬼怪凌空夜游,欧阳修为此作《鬼车》;还有苏轼的《芙蓉城》叙述王迥与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的奇事,“……天门夜开飞爽灵,无复白日乘云軿……飘然而来谁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棂”,[4](卷16,P807)描写难以捉摸的仙人行踪,营造出一个神妙空灵的芙蓉仙境。
尽管诗歌的表达方式与散文的表达有所区别,但这些诗歌在内容和写法上的确有许多与传奇、志异小说相似的地方,不但具有相对完整的情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刻画,而且会依据基本事实补充合理的想象,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可以说,传奇志异诗在宋代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二、以诗讲故事的浓厚兴趣
宋代传奇志异诗涉及的面很广泛,人物众多,包括各种身份、各种阶层,奇事异事也各式各样,层出不穷。这些内容若在小说范围内,未必多么出奇,然而集中出现在诗歌里,就有了特殊的认识价值。具有故事性的题材大量进入诗歌,从根本上说,反映着宋代诗人对故事的兴趣。
梅尧臣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作为北宋前期积极拓展诗歌题材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创作了不少故事性诗歌,既有传奇式的,如《花娘歌》、《一日曲》写爱情故事;也有志异式的,如《寤寐谣》、《梦登河汉》描写神奇怪异之事。最能反映他对于故事的兴趣的,是几首依据历史故事改编的诗歌。如《桓妬妻》,就取材自《世说新语》。据《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娶李势之妹为妾,桓温的妻子嫉妒心很强,听说此事,带人拔刀前往质问,而到达之后,却因为李氏的美丽而心生怜爱,“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5](卷下《贤媛》,P375)梅尧臣以诗歌再现了这个故事的情境:
昔闻桓司马,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主,悍妬谁与俱。持刀拥群婢,径往将必屠。妾时在窗前,解鬟临镜梳。鬒发云垂地,莹姿冰照壶。妾初见主来,绾髻下庭隅。敛手语出处,“国破家已殂。无心来至此,岂愿奉君娱。今日苟见杀,虽死生不殊。”主乃掷刃前,抱持一长吁。曰我见犹怜,何况是老奴。盛怒反为喜,哀矜非始图。嫉忌尚服美,伤哉今亦无。[1](卷11,P180)
诗歌基本按照原文的情节展开,选取具有表现力的细节。如“持刀拥群婢,径往将必屠”一句,特地点出“群婢”的存在,既符合南郡主的身份,又彰显了她带人前往挑衅的汹汹气势。同时还借助一些细节将故事铺陈得更加细腻。郡主来到之后,诗写李氏“绾髻下庭隅。敛手语出处”,将李氏表现得非常从容。又结合情境补完了李氏的自白,如“今日苟见杀,虽死生不殊”,愈发显出李氏的楚楚可怜,于是郡主的“我见犹怜”顺理成章。虽然诗歌的最后两句是议论感慨性的话语,但就诗歌整体写法而言,诗人关注的重点不在议论,而在于故事本身。
又如《寤寐谣》写赵简子魂游天界之事,取材自《史记·赵世家》,过程曲折离奇,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于故事的兴趣。春秋时,赵简子病重,名医扁鹊说从前秦缪公也曾如此,其实是在梦中去了天帝那里。果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醒来,说起自己在梦中的经历:见到了天帝,并且射死了一只熊和一只罴,天帝赐予二笥和翟犬,预言晋国有七世的国运。不久后的一天,赵简子外出时遇到一人,自称赵简子梦游钧天的时候也在场,并为赵简子详细解说梦境,说熊和罴代表晋国的中行氏和范氏,都会被赵简子打败,而赵简子的儿子将会攻克代与智氏。赵简子的儿子毋恤是翟婢之后,赵简子死后,毋恤即位为赵襄子,后来平定了代国,消灭了智氏。晋国的发展果然与梦境所言一一相印。[6](P1786)梅尧臣此诗,所用的情节基本上都出自《史记》记载。如开头一段:
日月昼夜明,中匿暗霭物。前世有奇疾,五日瞑未殁。大夫家臣惧,鹊来视之脉不汩。尝闻秦缪公,奄奄往帝所,甚乐岂苍卒。及乎七日寤,事与此无咈。果然逾二日,觉语汝忽忽。……[1](卷22,P634)
诗歌的文字相对简练,但强化了情节的曲折,并对原文的叙事风格有所调整,凸显了神异的氛围,并以《寤寐谣》这样一个充满志异色彩的名字为题。这种改写不是为了咏史,而是从故事性的角度加以包装,使其成为诗歌里的故事。梅尧臣以诗歌形式讲述故事的这种尝试,不但表明诗歌与散文叙事没有截然的距离,同时也体现出诗人以诗歌形式来讲故事的强烈愿望。作为对宋诗面貌的形成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诗人,梅尧臣鲜明地反映着宋诗爱好故事的倾向。
喜欢在诗中讲故事的又如苏轼。李常(字公择)请苏轼赋一首黄鹤楼诗,苏轼没有描写黄鹤楼的风景,却是在诗中叙述了一个故事。《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
黄鹤楼前月满川,抱关老卒饥不眠。夜闻三人笑语言,羽衣着屐响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叩声清圆。洞中铿鈜落门关,缥缈入石如飞烟。鸡鸣月落风驭还,迎拜稽首愿执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黄金乞得重莫肩。持归包裹敝席毡,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闾来观已变迁,似石非石铅非铅。或取而有众愤喧,讼归有司今几年。无功暴得喜欲颠,神人戏汝真可怜。愿君为考然不然,此语可信冯公传。[4](卷8,P373)
诗题所谓“旧闻”,即诗中所写一位老卒遇到神仙的传奇故事。老卒半夜未眠,遇见着屐的神仙,请求学仙而不可得,退而求财,于是得到一块非金非石难以辨别之物,最后惹得官司缠身,其实他是遭到了仙人的戏弄。诗歌叙事传神而简洁,不附他语,正是志异小说的写法。宋代章炳文的《搜神秘览》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将苏诗与《搜神秘览》中的记录合观,二者叙事基本吻合。如其中一段云:“顷年有抱关老卒,夜偶不眠,起视楼前,天净风寂,明月澄淡。见三二人着屐,声响空山中,疑其鬼物,熟睨之又疑其为人也。语笑自若,叩山之石,其声铿锵然。三叩而门忽开,二三人者自门而入,烟霭冥晦。”[7]卷中所写内容也就是苏诗前八句的内容。章炳文大约生活在徽宗朝,比苏轼要晚。他所记载的这段故事有可能是从苏轼诗中转写而来。即使《搜神秘览》所记不是从苏诗而来,那么也与苏诗有共同的来源。总之,苏轼以诗歌“记旧所闻”,且与《搜神秘览》记载极其相似,可见苏轼有意用志怪小说的写法作诗。而诗歌用字精炼,造语雅致,又比小说多了几分飘渺,添了几分神异。
不仅诗人愿意用诗歌的形式来讲述故事,读者也愿意从故事的角度来解读诗歌。钟明的《书义倡传后》讲述了一名极有义气的倡女的故事。这名倡女一直思慕着“解作多情断肠句”的秦观,当秦观被贬谪郴州,途经洞庭时,倡女终于一尝夙愿,并愿以身相许。可惜世事难测,不久后秦观病死他乡,倡女兼程数百里赶往送别,临丧一恸而绝,以另一种形式完成了当时以身相许的约定。[8](《义倡传》,P1559)此诗及事出自洪迈所编的小说集《夷坚志》。就事情本身而言,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洪迈后来就在《容斋随笔》里辩诬,认为此事出于虚构。[9](《四笔》卷九,P738)尽管事情不是真实的,但诗中所写倡女对爱情的坚定忠贞,委实诚挚动人。因此,即便耗费笔墨加以辩诬,但洪迈起初将其收入《夷坚志》的行为,足见他对故事本身的欣赏。另一个例子是孙次翁的《娇娘行》。娇娘美丽多才,与相爱的人私奔结为夫妻,非常恩爱,只可惜后来被其母发现,被迫离开丈夫,孤独生活。[10](前集卷3,P33)这首诗出自《青琐高议》。《青琐高议》是刘斧辑纂的一部志怪传奇集,刘斧只在孙次翁诗前加了几句引语,就直接把这首诗收为小说集中的一篇,可见在编辑者心中,这首诗本身就已是一篇精彩的传奇。
三、传其“奇”、志其“异”——诗与故事的水乳交融
宋代诗人对故事的爱好促进了传奇志异诗的新发展。诗人对于故事的“奇”、“异”有着浓烈的兴趣,故而要“传”其“奇”、“志”其“异”。“奇”与“异”的实现,一方面固然有赖于人物、故事本身的奇特,另一方面则在于讲述故事的方式。宋代诗人越来越注重叙事笔法,在诗歌范围内施展讲述故事的手段,既以故事的曲折增添了诗歌的丰富性,又以诗歌的凝练增添了故事的深情绵缈,使得诗与故事越发水乳交融。
(一)情节的曲折与诗意的剪裁
宋代诗人善于营构曲折情节,用以深化故事的层次,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增加故事的吸引力,从而营造出传奇志异的效果。梅尧臣的《花娘歌》就是如此。尽管故事内容是比较传统的相爱与分离,情节并不复杂,但经过诗人的剪裁,就能有起有伏,委婉动人:
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声名居乐府。荏苒其间十四年,朝作行云暮行雨。格夫气俊能动人,人能动之无几许。前岁适从江国来,时因燕席相微语。虽有幽情未得传,暗结殷勤度寒暑。去春送客出东城,舟中接膝已心倾。自兹稍稍有期约,五月连航并钓行。曲堤别浦无人处,始笑鸳鸯浪得名。尔后频逢殊嬿婉,各恨从来相见晚。月下花前不暂离,暂离已抵银河远。青鸟传音日几回,鸡鸣归去暮还来。经秋度腊无纤失,爱极情专易得猜。前时南圃寻芳卉,小忿不胜投袂起。官私乘衅作威稜,督促仓惶去闾里。萧萧风雨满长溪,一舸翩然逐流水。忽逢小史向城来,泣泪寄言心欲死。“愿郎日日致青云,妾已长甘在泥滓。更悲恩意不得终,世事难凭何若此。”郎闻兹语痛莫深,天地无穷恨无已。我今为尔偶成章,便欲缄之托双鲤。[1](卷14,P236)
诗中写两人相恋的过程,从花娘“人能动之无几许”写起,作为铺垫;接着是一段恋情的逐渐展开:先写“前岁”,是“虽有幽情未得传”;次写“去春”,“舟中接膝已心倾”;然后是“自兹稍稍有期约”的浪漫幽约,以及“月下花前不暂离”的难舍难分。由淡到浓,由浅到深,将恋情写得层层渐进。等到浓情蜜意的最高点,突然“爱极情专易得猜”,转入悲剧的气氛。原本只是“小忿不胜投袂起”,哪知世事难料,“官私乘衅作威棱,督促仓惶去闾里”,两人只得分离,原本的鸳鸯爱侣顿时变得形单影只。在诗歌前半部分细腻的铺垫下,后半部分的分离愈发来得突然、来得沉重,一直延续到“天地无穷恨无已”的深深遗憾。情节的曲折带来情感的曲折,令人感慨万千。
孙次翁的《娇娘行》也是一篇叙事委曲、情节曲折的佳作。娇娘的经历,若用诗人小序中的话来说,其大要不过是“十六嫁登人解氏,二十为夺其志,遂居江淮间”,但经过诗歌的渲染,就变得曲折动人。开篇写娇娘艳压群芳,人人争识却难得佳人一顾,在这番铺垫下再写娇娘与情郎的情投意合,乃至“藏头掩面”随情郎私奔而去,足见两人一往情深。在两情相悦的故事中,最怕家庭的隔阂、父母的阻挠,然而情郎竟然说服了父亲,将娇娘“六礼安排”明媒正娶迎入了门,这几乎要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不幸的是,娇娘生病召请医生,因此泄露了踪迹。母亲得知后大发雷霆,“来见娇娘大嗟怨,怒声肆骂千千遍。扶夺上马去如飞,争奈郎踪相去远”。在上文颇为缓和的叙述语调中,这几句诗如风起云涌,生生将美好的婚姻拆散,将一个团圆的喜剧变成了劳燕分飞的悲剧。此后的娇娘“蕙心兰性欲枯死”,发誓不愿再嫁,只等待昔日夫郎。然而烟波万里,音信难觅,只能苦苦等待,白白耗费青春。娇娘的经历,在诗人一波三折的叙述中增添了悲剧的气氛,只留下曾经的美丽、短暂的欢乐和绵延无尽的遗憾。
就故事本身而言,宋代这类诗歌未必多么奇特,无论爱情、游仙、梦寐,并未超出小说的题材范围。但就诗歌而言,诗人却以丰富的叙事成功地完成了属于诗歌的传奇志异。即便读者对这些故事的模式并不陌生,但经过诗人细腻的处理,于熟悉的模式中添入不熟悉的细节、增加不熟悉的变化,使得故事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奇”与“异”的魅力,也就浓缩在了曲折多变的叙事里。
(二)诗歌代言与故事的结合
宋代传奇志异诗的另一个发展是代言与故事的结合。代言是诗歌中常见的传统,指诗人代人设辞,假托他人的身份口吻创作,设身处地地代替诗中主人公言情述事。宋代一些诗歌利用传统的代言手法,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来讲故事,从而发展了传奇志异诗的叙事模式。
在宋以前,就全篇代言的作品来说,直抒角色感情的作品占据着更大的比例。而在借助代言来讲故事的诗歌中,又往往是先从诗人的角度引出人物,然后才借人物之口进行讲述。如唐代元稹的《连昌宫词》“宫边老翁为余泣,小年进食曾因入……”先写诗人遇到老翁,然后老翁叙述安史之乱的变化。[11](卷24,P270)韦庄的《秦妇吟》,诗人先看到路边有人,“借问女郎何处来,含颦欲语声先咽。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说。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接着才是秦妇对战乱经历的长篇讲述。[12](P315)诗人遇见某人、某人讲述,这已成为唐代叙事诗中一个常见的模式。
不过这一叙事模式在宋代得到了调整,许多诗人去掉了“诗人遇到某人”的部分,而直接在诗中让人物自述。梅尧臣的《一日曲》全篇代言,一开头便是“妾家邓侯国,肯愧邯郸姝”, 以“妾”的身份展开叙事,其后有“送郎郎未速,别妾妾仍孤”,最末是“东风若见郎,重为歌金缕”,代言贯穿始终。[1](卷9,P146)这种写法的好处在于,讲述故事的同时能够比较细腻地表现女主角的心理活动。诗中写其品貌才艺的几句,“十五学组紃”、“十七善歌舞”等,若是以第三人称叙述,不过是比较客观的陈述,而诗中以第一人称自道,则显露出女主角自矜身份的姿态来。“昨日一见郎,目色曾不渝”的一见钟情,也藉由女主角自道以表露她的痴情。从结爱再到分离,只剩女主角终日思念,在闺中苦苦等待,等待之苦也从女主角口中直接道来。这首诗第一人称的直接叙述和抒情,就如同女主角内心戏的镜头特写,使戏份完全集中到女主角身上。
相比而言,在“诗人遇见某人、听某人诉说”的叙事模式中,比较强调的是诗人的旁观身份,诗人承担着见证者和记录者的角色。人物的自述经历,在诗中是含括在诗人观照的视角之内,为诗人的限知视角所局限。而在全篇代言的模式中,诗人从诗中隐去、单纯代替人物说话,就能够比较自如地模拟他人的口吻,揣摩他人的内心,并补充合理的想象。张耒的《周氏行》也是代言式的作品,写一名船家女子的恋情:
亭亭美人舟上立,周氏女儿年二十。少时嫁得刺船郎,郎身如墨妾如霜。嫁后妍媸谁复比,泪痕不及人前洗。天寒守舵雨中立,风顺张帆夜深起。百般辛苦心不惜,妾意私悲鉴中色。不如江上两鹭鸶,飞去飞来一双白。长淮杳杳接天浮,八月捣衣南国秋。谩说鲤鱼能托信,只应明月见人愁。淮边少年知妾名,船头致酒邀妾倾。贼儿恶少谩调笑,妾意视尔鸿毛轻。白衫乌帽谁家子,妾一见之心欲死。人间会合亦偶然,滩下求船忽相值。郎情何似似春风,霭霭吹人心自融。河中逢潬还成阻,潮到蓬山信不通。百里同船不同枕,妾梦郎时郎正寝。山头月落郎起归,沙边潮满妾船移。郎似飞鸿不可留,妾如斜日水东流。鸿飞水去两不顾,千古万古情悠悠。情悠悠兮何处问,倒泻长淮洗难尽。只应化成淮上云,往来供作淮边恨。[13](卷4,P43)
全诗除第一、第二两句以外全为代言。此两句虽非代言,但也有别于诗人直接出现在诗中,只是淡淡两笔交代人物背景,紧接着就进入人物的自述,有意淡化了诗人干预的痕迹。诗中的这名女子,嫁给刺船郎之后并不因撑船的辛苦而难过,却为自己与丈夫容貌的差距感到悲伤。她期待相貌般配的婚姻,因此当她遇见了真正的心上人时,是“妾一见之心欲死”的热烈执著。可惜那只能是一种无望的单相思,注定无法实现,只剩无处排遣的满怀深情。诗歌以第一人称代言的方式叙述这个故事,让女主角直接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倾倒出一腔痴情,细腻地展现了女主角的心理。故事的主角又是船家女子的身份,这种叙述方式也契合了民间女子的直白,显示出对爱情的自主追求。虽然船家女只能终止于单恋,但她大胆、真诚又痴情的性格特点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从小说的角度来看,这类诗歌的叙事角度很有特色。因为在传奇志异的小说中,叙述他人故事通常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偶有第一人称出现,也往往只是作者用于说明自己是旁观者或故事的记录者。而宋代这些诗歌充分利用代言,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来讲故事,促进了叙事视角的新变。当诗人的身份从诗歌中退出、隐藏到诗歌之后时,有可能使诗歌的表现更加自如。读者也不必受限于诗人作为旁观者的眼光,而是可以直接触摸诗中的人物。
四、宋诗叙事性的增强
从诗歌史的发展来看,在进入宋代之后,诗歌的功能和表现发生了许多改变。相对于唐诗以情为主的艺术风貌,叙事传统在宋诗里得到了张扬。宋诗的叙事性有所增强,叙事在诗歌中的表现、作用、地位等也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许多诗人对“事”有了更为密切的关注,并主动追求叙事的趣味,从而促进了诗歌叙事传统的发展。宋代的传奇志异诗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诗人不但对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加重了诗歌中的叙事分量,而且注重对“奇”、“异”的凸显,有意识地营构曲折的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并发展了代言叙事等新的故事讲述模式。传奇志异诗的种种表现,不但反映了宋诗叙事性的增强,并且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叙事传统中的重要一环,体现着古代诗歌叙事所取得的成就。
[1]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徐积.节孝集[M].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
[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
[4]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章炳文.搜神秘览[M].民国二十四年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宋刻本.
[8]洪迈.夷坚志补[M].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9]洪迈.容斋随笔[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元稹.元稹集[M].冀勤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韦庄.韦庄集笺注[M].聂安福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3]张耒.张耒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