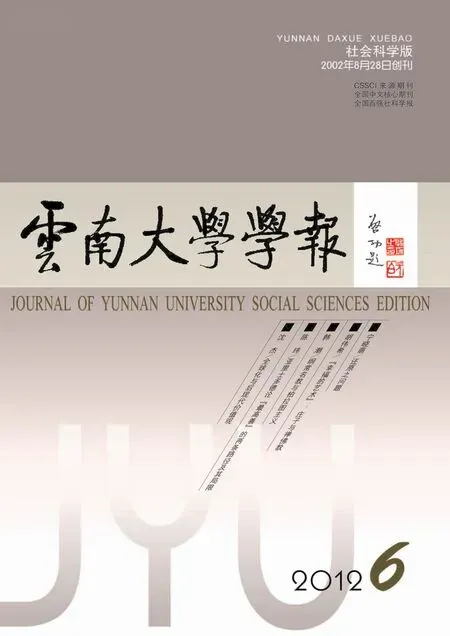从浪漫主义到审美主义:现代审美思想的本体论转向*
2012-12-09顾梅珑肖向东
顾梅珑,肖向东
[江南大学,无锡 214122]
以赛亚·伯林曾经说过:“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他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1](P8)不过,对于浪漫主义的界定,他却认为是一个危险而又混乱的工作,如同面对一个黑暗的洞穴,一旦进入,便不可重见天日,“对浪漫主义的解释和申论与其说回答了问题,不如说引起了问题”。[2](P43)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源于浪漫主义自身所包容的多重、复杂、异质、乃至矛盾对立的因素,诸如想象、热情、感伤、快乐、死亡、人性、个体性、放纵、诗意、怀旧、自然、神秘主义等等表征,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浪漫主义的“雅努斯面相”(Janus's face)。究竟什么是浪漫主义?在迄今为止对于浪漫主义所作的各种权威性定义中,存在着各种各样普遍化、表面化甚至自相矛盾的解释,究竟哪种界定才能揭示浪漫主义本质性内涵?什么才是浪漫主义的独特品质?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
当我们站在当下以新的视角重新回溯浪漫主义这一现象的时刻,便会发现,浪漫主义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它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浪漫主义萌发的18世纪正是世俗社会取代神性王国的现代转折时期,上帝已死,人类本来视为权威的东西正在消解,意识形态悄然发生着一种世俗化(Säkularisierung)的位移,浪漫主体最终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来看待世界万物和人自身的存在。刘小枫表示:“从思想内容上看,形而上学之终结,人的终结等论点,以及对原知识学的攻击和诗的隐喻、感性的美化和强调,浪漫派已着先声。在这一意义上,浪漫派思想本身就是现代性原则的一种类型,它包含着对现代性的独特提法,对现代政治和日常生活结构的转变的独特反应态度。”[3](P187)可见,浪漫主义问题首先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并且和现代人的感性萌发有着密切的联系。
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施米特在否定了对浪漫主义的种种印象式的定义之后,曾经深刻表明: “要界定浪漫的事情 (Romantischen),不能以任何被浪漫地感受的对象或论点为起点,不能以中世纪或废墟为起点,而应以浪漫的主体为起点。这里涉及的总是某种类型的人,要从这类精神的人自身来理解 [浪漫]。”[4](P4)一旦把关注的眼光从五花八门的浪漫化现象转向拥有感性精神的人自身,浪漫主义的问题便和审美现代性的问题联系起来了。审美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针对启蒙运动以来工具理性的弊端而呈现出来的一副感性面孔,它独具的感性纬度,被用以纠正规训社会平庸、功利、压抑的社会现实,批判、反驳工业文明的物质主义,最终让现代人达到释放生命获取自由的目的。审美对于理性主义的对抗必然造成二者之间激烈的冲突,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现代性内部最主要的矛盾,已经有许多现代哲学社会学家关注过这一现象。马泰·卡林内斯库在他的代表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明确提出了“两种现代性”的概念,即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与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一方面是社会领域中的现代性,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本质上属论战式的美学现代性,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5](P343)这两种现代性有着深刻的矛盾:“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另一个若非公然非理性主义,也是强烈批评理性的;一个是富有信心和乐观主义的,另一个是深刻怀疑并致力于对信心和乐观主义进行非神秘化的;一个是世界主义的,一个是排他主义或民族主义的。”[6](P343)
将审美现代性概念作为背景引入进行阐释,才能看清浪漫主义的“庐山真面目”,证实浪漫主体“人”的绝对权威,由此,一切混乱状态便可以重新得以清理,其中的矛盾现象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释。浪漫派那种无风格的风格,那种千变万化的姿态,那种天马行空甚至有些怪异奇特的现象,很显然最终都停留在那些不带任何责任的私人情感领域中,它最精美的成就也存在于个人最私密的感情之中。在浪漫主义里,审美创造的主体已经把精神中心转移到了自己身上,正如施米特所阐释的那样,他表示:“浪漫派是主体化的机缘论 (subjektivierter Occasionalismus)。换言之,在浪漫派中间,浪漫的主体把世界当作他从事浪漫创作的机缘和机遇。”[4](P15)总之,表面看来纷繁复杂的浪漫主义问题,最终是一种审美、心理层面的东西,它和人的内在情感世界密切相关。浪漫主义的问题显然就是审美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方面,和浪漫主义相关的种种现象也都可以从感性主体的角度加以解释,其矛盾混杂的表现与现代性内部复杂纠葛的状况是紧密相连的。
浪漫主义的主体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现代进程中产生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对现代性进行着激越的批判,是针对启蒙现代性弊端的第一次反戈。卡林内斯库曾经表示:“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5](P48)他所表述的这一时期正是欧洲浪漫主义全盛时期。哈贝马斯也曾经将早期浪漫主义视为通往审美现代性的“第一步”。在启蒙理性和机械文明日渐转化为压抑灵性和窒息生命的新统治权威时,浪漫主义以其特有的感性表达方式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作出了首次具有明确意味的反思和批判,而它的武器正是审美。对于浪漫主义来说,它所确立的主体中心表现在自我表达、艺术自足、诗化现实等各个层面,不仅在“人的情感、想象等审美领域里完成了主体性的现代性的革命”,而且对资产阶级机械文明与工具理性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它所张扬的情感、想象、灵性、诗意境界挣脱了黑暗、僵化、冷冰冰的机器世界,第一次对启蒙主义的传统与神话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正如张旭春所说:“浪漫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作出的首次具有明确意识的审美反思和审美批判,其美学旨趣和价值取向构成了审美现代性毋庸置疑的最初的精神源泉”。[6](P51)
总之,浪漫主义开启了通向现代审美主义的最初道路,它在西方文学与文化思想中有着种种深刻的表现:德国浪漫主义的神秘倾向、英国浪漫主义的自然之风、法国浪漫主义的宗教崇拜,都能从审美现代性角度予以解释;同样,诺瓦利斯的黑夜情结、华兹华斯的田园梦想、拜伦与雪莱的昂扬激情、雨果瑰丽奇幻的想象世界,均是浪漫主体寻求的多重出路。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思潮,浪漫主义承载着太多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开启了走向现代审美主义思潮的关键一步。
二
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与挑战“上帝”的时代,我们却从许多浪漫主义者那里发现了种种奇怪的“返魅”的现象:施勒格尔兄弟呼吁人们回到远古的神话时代,年轻诗人诺瓦利斯的诗歌里永远飘荡着黑夜和死亡的气息,荷尔德林多次深情呼唤神灵的回归。这些“返魅”现象的出现,在日渐“祛魅”的现代社会是很值得玩味和深思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步步颠覆了传统的神学观,乐观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在这个时候,重新描绘宗教、神话的世界的确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令人颇为费解的现象,不过仅仅用倒退来解释这种现象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现代性实际上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在原始的巫术时代,人、神、物相互交混、万物有灵,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开始解体。随着理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丰富,人类试图剥下自然和世界的神秘外衣。不过,科学理性在掀开世界神秘面纱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恐慌,他们成了无法掌控命运的渺小生物;启蒙主义 (Enlightment)发出的耀眼光芒在刺穿笼罩在世界周围黑色暮霭的同时,也刺穿了人们的生存信念。奥·威·施莱格尔曾经专门撰文对启蒙运动作了批判。在他看来,启蒙主义根本无法解决人的生存恐惧和情感需要,他要求人们必须学会敬重黑暗,他说:“古老的宇宙起源学说早已说过,夜是万物之母,现在,这个说法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又东山再起:人们认为,世界脱胎于泰初的混沌,通过爱与恨、同情与反感的相互作用而成形。生活的魔力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一片黑暗,我们存在的根正是消失于其中以及无法解答的奥秘之中。这就是一切诗的魂。而启蒙运动由于缺乏对于黑暗的最起码的尊敬,于是也就成了诗最坚决的敌人,对诗造成了一切可能的伤害。”[7](P378)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浪漫主义诗人与文学家开始以义无反顾的姿态重新返回人类因为狂妄自大而离弃的神性本原:诺瓦利斯在他的《夜颂》中唱起了黑夜与死亡的赞歌,霍夫曼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离奇曲折、古怪恐怖的故事,夏多布里昂深情呼唤宗教的回归……
科学认知和理性主义无法解决人类的原始痛苦和隐秘的情感需求,朦胧夜色笼罩下的神秘世界似乎能够承载个体那颗饱受伤痛的心,满足情感无拘无束的奔流。归根究底,浪漫主义的“返魅”来源于心灵的某种需要,来源于人类对现实世界恐惧的真实体验,与现代个体内在情感世界紧密相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审美式的神秘主义显然不同于蒙昧状态下的神秘主义,并不是出于对世界的一无所知,而是着重表现个体对世界的体验和感受,立足点已经从彼岸挪到了此岸。诺瓦利斯笔下的黑夜寄托了诗人那种隐秘的情感需求,给失去爱人的痛苦心灵提供了幻想中的慰藉,让他能够在夜色的掩映下和爱人快乐地相会。同样,呼唤神灵的回归也源自这样的情感和灵性的需求。个体生命是有限和短暂的,这种有限性和短暂性使人很难从自身获得自足完满,更不用说从启蒙主义所造就的那种僵化刻板的生活方式中了。体验到自己的局限并渴慕救赎的生命个体,往往会在内心深处产生出对超乎自身之上并且具有某种无限和永恒意味的事物的追求和依赖,宗教及神学信仰的重要性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这种信仰显然是和个体的生存焦虑、恐惧以及渴望超越现实的情感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和传统宗教、神学的内涵已经有所不同。它并不出自无知,而是根源于个体内在的心灵需求和真切的生命感受,浪漫主义的出现正预示着现代主体性本位的建立和人的感性情感地位的提高。
理性主义除了把个体拉出了世界神秘的母体和神灵温暖的怀抱之外,还以其特有的运作方式戕害了生命的完整性。随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虽然分享到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但必须面对由此带来的无灵性的机械世界,生命体被强行分割和重组,成了飞速运转机器上的呆板零件。浪漫主义者敏锐地感觉到,现代文明在双重意义上戕害了人的灵性生命:一方面,功利主义的欲求使得生活日渐乏味,人们成了利益和金钱的奴隶;另一方面,知性思维、技术规则和专业分工破坏了个体生命的丰富和完整,人成了没有生命的断片。和灰色的文明图景相反,在浪漫主义的世界里,处处洋溢着生命活力和诗情画意。张凤阳表示:“当浪漫作家以其与大自然的神秘交感,谛听着清泉的吟唱和树木的低语,从奇花异葩的眼睛读出相思的神情,乃至于在古堡废墟、精灵鬼怪、巫术魔法中咀嚼某种神奇意味的时候,他们都是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现代文明的功利旨趣、知识旨趣的抵御与抗争。”[8](P397)浪漫主义者认为,只有在诗和艺术化了的世界中,人类才能超越现实的鄙俗,恢复被现实异化和肢解了的身心,寻找到一片充满温情和想象力的审美化了的乌托邦,强烈呼唤健全丰盈人性的回归。因此,无论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品中充满传奇色彩的骑士故事、魔幻色彩的恐怖小说,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展现的宁静平和的田园风光、奇特瑰丽的湖光山色,还是法国浪漫主义小说中充满幻想的天堂国度、异域风情,都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诗化”的结果,是诗人心灵深处情感的最真实的表达,个体的情感需求在诗意的王国中最终获得了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浪漫”实则是一个审美的概念,浪漫化就是“诗意化”,那些充满了想象和奇幻色彩的异国景象如果没有强烈的感情的推动是不可能产生的,那个被浪漫化了的审美世界背后隐藏着个体丰盈恣肆的情感狂潮,正如刘锋所说:“无疑,这种审美化的枢纽就是绝对自我和自由的主体性,因为正是浪漫主体将世界消解成触发审美情趣的机缘和机遇。”[2](P47)可见,浪漫主义者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而是生活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这也是他们审美感性精神最为集中的表现。
提到浪漫主义,人们还会想到火一般的激情、放荡不羁的反叛、天马行空的想象、无拘无束的自由,这些因素构成了浪漫范式对古典范式的巨大挑战,最为契合现代审美思想感性至上的特征,掀起了丰富充盈的情感狂潮,人的感性生命力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解放。按照贝尔的说法,卢梭为张扬感性的现代主义文化立下了一块划时代的界碑,他的《忏悔录》直白而又尖锐地表达了一个真实的自我。此后,浪漫主义掀起了表达个性的狂潮,蕴涵着巨大的感性颠覆力量,这在英国诗人拜伦、雪莱,法国小说家雨果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他们用惊世骇俗的语言和昂扬澎湃的激情对抗着丑陋的社会现实,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掀起了一股反功利、反理性、反世俗、反规范的颠覆性潮流。这类艺术家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反叛姿态更为接近后来审美主义思潮感性张扬的风格,蕴涵了一种“情感对理智的价值优先性”。[8](P357)
三
总体说来,浪漫主义凸显了现代社会的审美感性趋向,它首次确立了情感对理智、诗对现实、审美对功利、天才对庸众的价值优先权,树立了审美主体的绝对权威,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动,对后来成熟阶段的审美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由于浪漫主义毕竟处在审美主义思潮的萌发阶段,并且此时的资产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这使得它和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审美主义思潮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浪漫主义者往往把个人的审美情怀和其伟大的政治抱负、社会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放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个人的自由获取必须和社会的民主进程血脉相连。可见,他们的感性反抗不单单是为了获得感官的享受和快感的满足,而是最终融入启蒙主义理想之中,二者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浪漫主义诗人们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担当冲动。”“我们如果仅仅认为浪漫主义因其审美现代性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精神而与后者完全是相悖的,那么,我们又会犯下过度简单化的错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浪漫主义对审美个体主义的弘扬与现代自由对个人主体性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6](P51-52)浪漫主义者在诸多方面继承了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想,特别是卢梭的自由民权观,包括那种“人文主义的悲悯”和“感伤的道德情怀”,他们将启蒙理想进行了审美化,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在审美领域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这是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出现的浪漫主义所必然具有的理想色彩,在各国浪漫主义者那里都有不同的表现。浪漫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启蒙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和后来彻底反理性、反道德、反启蒙的审美主义思潮有着明显的不同,二者有着各自突出追求的终极目标。
其次,浪漫主义者大多企图通过自己的想象和情感弥补有限与无限、此岸与彼岸、人与上帝之间的距离,建立起审美的王国与诗意的世界,满足个人的种种生命体验和情感需求。不过,这种审美追求和世俗化的感性生存本身还是有着一定的距离,特别是许多浪漫主义者在饱受黑暗现实的迫害、无法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时刻,最终选择了远离尘嚣、归隐山林的生活。这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使得他们永远生活在虚幻的审美乌托邦中,和积极乐观的审美主义生存论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浪漫主义者虽然也强调感性,却把情感世界绝对化,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通过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试图弥补此岸与彼岸、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距离。他们还没有勇气完全抛开对于彼岸世界的幻想,更不用说直视人类此岸生存的有限性和无法逃避的生存悲剧了。因此和后来的审美主义相比,浪漫主义重在建构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的审美乌托邦,尽管它也强调个体情感和灵性的需求,但更多是为了让有限个体获得一个自足的精神空间,而不是追求现世的享受。不过,现实的苦难是否可以在充满诗意和神秘氛围的乌托邦中忘却,这还是一个问题。大多数的浪漫主义者徘徊在现实和梦幻的王国之间,生存的丑恶与苦难还是如同梦魇一般围绕着他们,这就是许多浪漫主义文学流露出感伤色彩的内在动因。可以说,审美主义者是积极的入世者,他们身处现代性中,已经学会正视人类根本无法逃避的生命的原始苦痛和现实生存的悲剧性,表示要在生命之中而不是生命之外寻找存在的理由。酒神精神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生存精神的体现,尼采说:“酒神艺术也要使我们相信生存的永恒乐趣,不过我们不应在现象之中,而应在现象背后,寻找这种乐趣。我们应当认识到,存在的一切必须准备着异常痛苦的衰亡,我们被迫正视个体生存的恐怖——但是终究用不着吓瘫,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俗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制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9](P71)这种高昂的生命意志与浪漫主义虚幻的想象世界拉开了距离,不再企图另建一个超脱人世的伊甸园,而是直面现实与人生中的痛苦与快乐。
可见,浪漫主义还是没有逃脱传统的本体论范畴,依旧试图通过某种实体,而不是从生命本身出发给人类带来救赎。所谓实体 (substance),又译为本体,一般是指能够独立存在的、作为一切属性的基础和万物本原的东西。它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首创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也是后来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
使用的重要哲学范畴。人们对实体的认识经历了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认为上帝是最圆满的实体;近代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哲学家们总结新兴科学的成就,提出了有关理念的实体观。浪漫主义通过诗化、情感化曲折表达的依旧是对一个绝对本体界的渴望,那是“一个神性的超越的世界”,浪漫派和黑格尔的差别只在于把握这个绝对本体界的中介不同,后者提倡理性思维,而前者通过 “诗化的诸中介”。[10](P112)例如,浪漫主义所崇尚的自然虽然给个体心灵与情感提供了一个徜徉的场所,维护了人类天性的本真与自由,但他们心目中的自然带有了超验性质,精神层面的自我完善已经超越了审美层面的感性自足,这同样意味着一种逃避,和后来的审美主义思想有着本质性差别。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主义将“传统的实在的绝对的本体论转变为个体感性生命的本体论”,最终确立了“生存的本体论”,[10](P112)把生命的激情、生存的焦虑、欲望的灵性作为关注的焦点,以取代传统哲学中涵盖一切的绝对实在。从生存和生命本身出发,正视人生悲剧性的世俗生存观让审美主义最终彻底脱离了传统思维的羁绊,走向了现代,最终实现了现代审美思想的本体论转向。
尽管浪漫主义和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不过必须肯定的是:在浪漫主义世界里,我们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个体越界的冲动和本能的反叛,它是世界走向审美旅途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浪漫主义所萌发的感性倾向在后来进一步扩大,从而出现了真正表现现代人世俗化感性冲动的审美主义思潮,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抗也更为直接和深入了。从浪漫主义到审美主义,显示了现代审美“人学”思想的演进趋向与本体论转折,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完善。
[1]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 [M].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刘锋.浪漫派与审美主义——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J].国外文学,2003,(3).
[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M].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 [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施勒格尔.启蒙运动批判 [A].德国浪漫主义作品选[C].张凤城,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 张凤阳.现代性谱系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10] 刘小枫.诗化哲学 [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