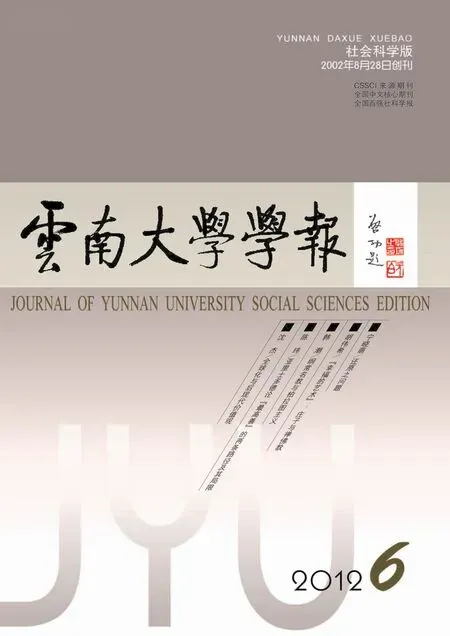Ereignis在海德格尔之思想道路上的位置*
2012-12-09杨宝富
杨宝富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存在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赓续不绝、历久弥新的课题,特别经过海德格尔的阐幽发微,甚至俨然成了整个哲学史的轴心。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处处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争锋相对,他矢志逾越形而上学的藩篱,穷原竟委,确立关于存在的真正提问方式。为此,他尝试从不同的路径切近存在问题,这种种尝试形成了他思想道路上的诸步伐。海德格尔晚年在一个讨论班 (Le Thor,1969)中曾这样回顾其思想道路:
传统上,“对存在的追问”意味着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换言之,对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追问,在此追问中,存在者乃是着眼于它的“是存在着的 (Seiendsein)” [这一点]来得到规定的。这一追问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
但是,对《存在与时间》来说, “对存在的追问”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在此涉及对作为存在之存在的追问。在《存在与时间》中,它以“对存在之意义的追问”的名义成为课题。
后来,这一措辞让位于“对存在之真理的追问”,——而最后则让位于“对存在之位置或场所的追问”——由此产生了“存在之地志学 (Topologie des Seins)”这个名称。
三个词语相互替换,一起刻画了在思想之道路上的三个步伐,[这三个词是:]
意 义 (SINN)——真 理 (WAHRHEIT)——位置 (ORT/TOPOS)[1](P344)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海德格尔对其整个思想道路的总结性回顾,我们可以径直以此为据来清理海德格尔的思想及其演变过程。然而,我们还读到他特别就自己的后期思想做过这样的说明:“Ereignis这个词……现在应被当作一个服务于思想的主导词而发言。”[2](P45)更确切地说:“自1936年以来Ereignis就成了我的思想的主导词。”[3](P370)而且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其晚期文本中对Ereignis有大量的讨论。尽管如此,Ereignis并未出现在上述所谓思想道路的三个步伐中。我们不禁要问: “意义——真理——位置”是否即是海德格尔之思想道路的整全?如果是,那么Ereignis作为其后期思想的主导词,与这个道路有什么关系?退而言之,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Ereignis与“意义——真理——位置”的关系?
一、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三个步伐
现在我们先来考察这三个步伐之间的关系,以表明海德格尔如何进入又出离其中的每一个步伐。
诚如上述引文所提,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存在问题当作存在之意义问题来追问。他认为,哲学即形而上学,[4](P68)它追问存在,但是,形而上学在追问存在的时候仅把存在当作存在性/存在状态,却无遑顾及这样一个隐含的事实,即它在这样追问存在的时候,其实已然将存在当作在场来对待,而在在场中,就有一个东西隐蔽地起着作用,即当前和延续。[3](P444)而当前乃是时间的一个维度。这意味着,形而上学从时间来领会存在,并将存在规定为在场。海德格尔指出,这时间就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意义。《存在与时间》的任务即在于通过揭示此在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表明存在者之存在的意义在于时间。此在之特著于其他存在者,在于它能够理解存在,而且理解不是此在的一个属性,亦非偶然的行动,只要此在存在 (生存),它就对存在有所理解,理解即是此在的存在。此在对存在的理解需要以时间为其视域,因此,时间就是此在的存在意义。然而,《存在与时间》没有完成原来的规划,①需要指出,《存在与时间》中的所规划的转向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实际发生的转向是不一致的。[5](P122)它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不过是“断简残编”。这就给不明海德格尔运思经验的人留下了误解的余地。海德格尔一再抱怨人们误解了它。但不待赘评,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被当作存在之意义来追问,而意义在海德格尔看来,其源初状态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语词的含义或陈述的含义;实际上,意义是筹划领域,而筹划就是此在之存在。此在于筹划中展开意义,存在者在意义这一视域中才成其存在。显然,海德格尔在此有意无意地突出了此在对存在的优先地位。因此,在追问存在之意义的时候,他着重于此在本身的敞开性。[1](P345)这种做法在理论上隐含着困境,诚如海德格尔后来反思说:“这条道路有违自身的意愿而进入那种危险中,即:只是重新成为一种对主体性的巩固。”[6](P825)
此后,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所谓的“转向”,即不再采取从此在说存在的路径 (此为基础存在论),而是反过来,从存在说此在,亦即以追问存在之真理的方式来追问存在。对于真理问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有所涉及,而且观以西方哲学史,真理问题与存在问题同样源始。正如他反对把源始的意义置于语言层面,他也反对把真理的处所放置在命题中。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说一个陈述是真的,乃是由于这个陈述所述说的存在者已经先行被揭示了。而存在者之被揭示,又是以存在之被展开为前提的。因此,真理的源始意义是展开状态。而首先展开的是此在。此在的展开状态是最源始的真理。这是《存在与时间》追问真理的路径。[7](P245)不过,这里所涉及的真理并非发生转向以后的“存在之真理”。②存在之真理区别于存在者之真理。海德格尔从存在之意义问题转向存在之真理问题,是与从存在者之真理转向存在之真理相平行的,但这不等于说:存在之意义就是存在者之真理。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与真理问题紧密地相联属,甚至可以说二者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双重主题,[8](P30)但是,存在问题之表述的转变与真理问题之表述的转变不是等同的。从存在之意义向存在之真理的转向,乃是在同一平面上视角的转换,而从存在者之真理向存在之真理的转变,乃是一种深化。在转向之后,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绽出之生存,即站出来内立于存在之真理中,为存在者之显现做准备。绽出生存就是被抛的筹划。[3](P398)表面上看,这似乎与转向之前的说法并无根本性的差异,因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然揭示出,此在之展开状态是由被抛、沉沦和筹划三个环节组建起来的统一结构,而且这三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已经把其他两个也带出来了。因而,筹划总是被抛的筹划。只是由于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问题是依存在之意义来定向的,所以与意义相联属的筹划仍然是重点所在。只有当以存在之真理问题来定向存在问题的时候,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重点才转移到存在对人的抛投上来。在存在之真理问题中,此在的展开状态乃是基于存在使用人,让人作为存在之真理发生的处所。“人之本质基于绽出之生存。本质上,也即从存在本身方面来看,关键就在于绽出之生存,因为存在占有着作为绽出生存者的人,使人得以进入存在之真理中而看护存在之真理。”[3](P407)“人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存在之真理中的,人在如此这般地绽出生存之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显现出来。”[3](P388)换言之,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之真理问题的框架内,此前所谓的作为存在者之存在视域的意义不复是由此在所筹划,而是由存在本身所决定。
由此可见,从存在之意义问题到存在之真理问题的转向,表明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路径发生了转换,其关键乃是存在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在存在之意义问题的框架内,存在者之能够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而存在,乃是基于此在能够在筹划中展开意义。而在存在之真理问题的框架内,存在者之能够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而存在,乃是基于存在将人抛入存在之真理中,并让它守护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能够显现。
无论是存在之意义还是存在之真理,都是存在者之存在的视域。形而上学追问存在者之存在,但未曾看到存在之意义或存在之真理,因此,形而上学遗忘了时间,亦即遗忘了存在之真理或存在之意义。因此,形而上学作为存在之遗忘,它所遗忘的存在不是存在者之存在意义上的存在,而是存在之意义或存在之真理意义上的存在,①在《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中,海德格尔谈到:“在我的思想尝试的道路上,我清楚地认识到一种区分,即在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和作为‘存在’的‘存在’之间的区分——此处所谓的作为‘存在’的‘存在’是鉴于存在所固有的意义,即存在之真理 (澄明)的意义来说的。”[9](P107)在这里,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究其实质乃是时间之被遗忘状态。②海德格尔指出,时间是对存在之意义的命名,对存在之真理的先命名。[4](P33-34)因此,形而上学没有真正的存在问题,它所追问的实乃非本真的存在问题,而且它将这种非真性当作本真性来对待。
但是,海德格尔并未止步于此,他对真正存在问题的追问还迈出了另外一个步伐:克服形而上学,追问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条件,亦即追问存在之位置。从存在之真理问题转向存在之位置问题,其性质与从存在之意义问题转向存在之真理问题大异其趣。在一定意义上,存在之位置问题已经出现于《存在与时间》中,因为海德格尔在那里于提出存在问题的同时就提出了解构存在论历史的任务,规划中的《存在与时间》之第二部即曾被赋予这样的任务;非但如此,在已经完成的部分中,即已随处可见对传统存在论之存在阐释的解构。之后,他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从传统形而上学将存在界定为无出发来切入真正的存在问题,而在《论根据的本质》中则从存在论差异入手来沉思存在。[3](P142)在晚年的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对存在论差异作了新的解释,他指出,存在论差异说的是:存在不是存在者,即:存在是无,或存在与无是同一的。存在论差异就是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形成了分野。形而上学所强调的是存在本身与存在者本身之间的差异,而海德格尔则强调,存在论差异说的是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本身。只有在差异本身发生之际,才有存在者及其存在。海德格尔所致思的不是处于这个差异内的存在者,也不是同样处于差异内的存在 (存在者之存在),而是作为存在者及其存在之视域的这个差异本身。形而上学作为存在论致思于存在者及其存在,故而,形而上学惟有在差异本身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而差异本身却是“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条件”,是“形而上学本身奠基于其上的位置”。[1](P309/P361)这个 “位置”被海德格尔确定为他所要深思的课题,职是之故,他的思想是地志学 (Topologie):“也即是对那样一个位置的探讨,这个位置把存在和无聚集入它们的本质中,规定着虚无主义 (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即形而上学——笔者注)的本质,并因此使人们认识到那些道路——在这些道路上,一种可能的对虚无主义的克服的各种方式才得以显现出来。”[3](P485)于此,海德格尔的思想已然及乎形而上学得以运作的地基,从而越出了形而上学的藩篱。我们知道,《存在与时间》中存在之意义问题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一般存在论奠定基础,它因而是基础存在论;存在之真理问题虽然将重心从此在转移到存在本身,但就其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而言,又与形而上学若合符节。在此意义上,对存在之位置 (差异)的追问跟对存在之意义的追问和对存在之真理的追问处于同一个平面上。这三者都是对作为存在之存在的追问。尽管如此,存在之位置问题又与其他两者有所区别。如果说,对存在之意义和存在之真理的追问偏向于直面存在问题,那么,对存在之位置的追问则以迂为直,因为在这里,海德格尔乃是接过形而上学的“存在是无”这一主题而思的,他对存在的追问因而表现为对形而上学的克服。既然是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就不免要受到形而上学的牵累。其所以如此,盖缘于这样一个困境:形而上学说“存在是无”,海德格尔也说“存在是无”,这两者如何区别开来就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因为甚至他自己也发现并承认,形而上学之完成者黑格尔即已说过“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无是同一的”,[7](P69)而他自己也规定 “存在即无”。如此一来,海德格尔与黑格尔 (形而上学)的分际将变得混芒不明。尽管海德格尔为此辩解说:黑格尔从意识出发把存在 (作为未被规定的不可中介的东西)[10](P68)规定为无,而他自己则从存在论差异 (存在不是存在者)出发把存在称作无,但此种辩解似乎无法令他满意。他在《哲学贡献》中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意识到:“存在论区分恰恰来自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 (存在性问题)。但在这条道路上,是绝不会直接达到存在问题的。换言之,这个区分恰恰成为它阻碍了对存在问题进行追问的真正界限……需要这样做:不是超出存在者 (超越),而是,越过这个区分,从而越过超越,并从存在开始,并追问真理。”[11](P250-251)海德格尔晚年也表示: “用‘存在’概念和‘存在之历史’概念来思Ereignis是不会成功的;引希腊人为奥援 (毋宁恰恰是超出希腊人)同样不会成功。存在论差异亦随存在而消失。因此之故,可以想见,人们也会将海德格尔1927年至1936年间一直依赖于存在论差异 [的做法]视作必要的歧途”。[1](P366)存在论差异尽管不是追问存在问题的恰当途径,但是,它仍然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在过渡性的思想中,我们必须经受这个矛盾:先用这个区分进行最初的阐明,但接着要越过这个区分。”[11](P251)
既然如此,意义、真理和位置三个步伐与后期的主导词Ereignis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进而考察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的Ereignis。
二、Ereignis与存在历史
前面已述及,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最初采取了存在之意义问题的形式。这种提问方式并非无的放矢。形而上学在追问存在者及其存在的时候已经从时间的视域来理解存在,只不过形而上学本身对这个视域视而不见,存在之意义 (即时间)被遗忘了。这种遗忘绝非偶然。形而上学乃是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但存在之被遗忘,不是形而上学的过错,也不是来自形而上学,相反,形而上学却来自这种被遗忘状态。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其来有自:存在自行遮蔽,而且这种遮蔽复又遮蔽自身。既然形而上学来自被遗忘状态,而被遗忘状态却是根源于存在之被双重遮蔽,所以,形而上学根本不能洞见这种被遮蔽状态。那么,如何发现存在之被遮蔽状态?这就需要从Ereignis出发。
其实,当海德格尔从存在之意义、真理和位置出发来思存在问题的时候,实质上他就已经是从Ereignis来思了,这三个步伐可以纳入到Ereignis中来。尽管如此,当海德格尔明确提出Ereignis作为思想之主导词的时候,他并非仅仅简单地将此前隐而未彰的东西用语词标示出来,而是同时也表明了思想的完善和深化。这正是本部分所欲申明的。
海德格尔的“Ereignis”一词发端于1936年至1938年间草就的著作《哲学贡献——从Ereignis而来》。而他在晚年回顾自己关于Ereignis的运思经历时,提示我们留意的文本有:《关于人本主义的信》、 《物》、 《同一律》等,[4](P42-43)、[1](P366)此外,他在《时间与存在》及其研讨记录稿,《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著述中也曾论及Ereignis。《关于人本主义的信》对Ereignis固然不是泛泛而谈,但海德格尔在此故意沿用形而上学的主导词—— “存在”,①海德格尔后来解释说:“在关于人道主义书信中……几乎普遍地,‘存在本身’这个名称已经命名着Ereignis了。”[3](P52)而几乎没有正面使用过Ereignis。《时间与存在》侧重于从存在与时间的共属关系来谈Ereignis,《同一律》偏向于从存在与人 (思想)的共属关系来谈Ereignis,《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主要从存在与语言的关系来谈Ereignis。海德格尔要求,要对Ereignis有所思,就必须投身到其中去 (einkehren in das Ereignis),去它那里获取思的规定。[4](P42)同样,我们若要瞥见海德格尔本人的Ereignis之思,必须先投身到海德格尔那里去(einkehren in Heidegger)。然而,不但海德格尔之关于Ereignis的文本统绪多端,而且Ereignis甚至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几乎所有关键概念都集于一身,并赋予它们更新了的意义。所以,任何框定Ereignis之确切含义的企图都是徒劳的。鉴于此,这里主要基于《时间与存在》来勾勒出Ereignis之丰富意蕴的大致轮廓,并据此考察它与海德格尔之思想道路的关系。
存在使存在者存在,时间又是存在的可能性,①存在并不仅仅由于时间而可能,因为,时间和存在是相互规定的,而且,存在和时间又必须在人的参与下才能使存在者存在。然而时间本身作为存在之意义和真理(作为Lichtung)又不是第一性的、终极性的东西,因此,要完整地解决存在问题,就必须把使时间成其为时间的那个东西显示出来。要回答问题,必须先正确地提出与表述问题。形而上学已经说:存在者存在。海德格尔就不能再说:存在存在,否则又将存在当成一个存在者了;同样也不能说:时间存在,否则就把时间也当成一个存在者了。如我们上面申述的那样,存在是使存在者成为存在的东西,而时间是使存在得以可能的东西,就更不是存在者了。因此,海德格尔说,不是:存在存在,时间存在,——而是:有 (Es gibt)存在,有时间;②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中用‘Es gibt Sein”,在关于它的讨论班中则分析了“Lassen”,在晚年讨论班中又用Lassen来取代“Es gibt…”。而且,这里的“有”意味着“它给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时间给出存在。既然时间不是终极的东西,又是什么给出时间的?给出时间的那个“它”为何?海德格尔认为,对于那个“它”,不能再作如此追问,否则又会落入将“它”当作存在者的窠臼。他指出:“我们应该如何把上述‘它给出存在’、‘它给出时间’这些句子中的‘它’放进眼帘呢?干脆,我们从属于‘它’的给出的方式出发去思‘它’,即从作为天命的给出、从作为敞空着的到达的给出出发去思‘它’。而就天命基于敞空着的到达而言,这两者又是共属一体的。……规定存在和时间两者入于其本己之中即入于其共属一体之中的那个东西,我们称之为 Ereignis。”[12](P19-20)、[4](P22)因此,要揭示 Ereignis 的本性,如上面指出的,应从“它”给出存在和时间的方式入手。
首先,就Ereignis给出存在与时间的方式而言,Ereignis的本性是归隐 (Enteignis)。Ereignis给出存在的方式为遣送,即给出者在给出的同时抽身而去,只让存在者显现,即让在场者在场。因此,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存在者,而对存在不管不顾。Ereignis给出时间的方式为“到达”,即在给出当前之际把曾在拒绝了,把将来扣留了。我们只看到当前,并把当前作为现在来看待,并把时间当作现在系列的延续,而真正的时间是,曾在、将来和当前相互贯穿着到来给存在者开放出一个得以显现的位置。由Ereignis给出时间和存在的方式,我们可以获得对Ereignis之本性的一个规定,即“归隐(Enteignis)”。“只要存在的天命基于时间的到达 (Reichen)中,而到达和天命基于Ereignis中,那么Ereignen的本性就自行宣示出来,即Ereignen使那最本真的东西从无约束的解蔽中隐逸而去。从Ereignen出发来思,就叫做……Ereignis自行归隐。这种归隐隶属于Ereignis本身。通过这种归隐,Ereignis并不是放弃自身,而是保留它的所有物。”[12](P23)、[4](P26)
其次,就 Ereignis与人的关系而言,Ereignis的本性是归本 (Vereignung)。上面讨论Ereignis给出存在和时间之方式的时候,暂且回避了人的因素。其实,存在者之能够存在,离不开人的参与。海德格尔认为,自古希腊以来,存在就被当作在场,而在场总是关涉到人。即使在“有存在”,“有时间”这种说法中,也已经牵涉到人了,而并不只是单纯的存在和单纯的给出。[4](P46f)那么,存在和时间、从而 Ereignis是如何关涉人的呢?就人与存在的关系来说,根据《存在与时间》和《关于人本主义的信》的解释,人为存在操心,这种操心由被抛、筹划和沉沦三个环节构成。操心只有在时间视域中才可能,如果将时间规定为敞开状态、无蔽状态的话,那么,人与时间的关系就是人内立于时间之中。《关于人本主义的信》把人之本质规定为“绽出”、“绽出之生存”,亦即站出来内立于存在之真理中。关于这些关系,必须强调的是,人的筹划是被抛的筹划,人被存在抛入存在之真理中,去守护存在之真理。然而,存在和时间又是被Ereignis占有的,故人与存在和时间的这种关系,究其实质乃是人与Ereignis的关系。简言之,这些关系都是由Ereignis建立的,而且这些关系本身就是Ereignis。Ereignis是一切关系之关系。[9](P269)在Ereignis中,存在只有使用人才成其为存在,而人只有这样被存在使用,去看护存在之真理,人才成其为人,即作为此在的人。“存在使用人,以便本质化,而人归属于存在,因此它完成其作为此-在的最极端规定。”[11](P251)在这个意义上,“Ereignis 乃是表示存在之真理与此-在之间的存在历史性共属性的语词。”[13](P81)换言之,人与 Ereignis的这种关系是本质性的关系,因此不可以说,先有人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人再去与Ereignis建立关系。海德格尔将这种本质性关系确定为Ereignis的另外一个特性,即归本 (Vereignung):“只要在Ereignen中有时间和存在,就有这样一种特性属于Ereignis,即那个只要内立于本真的时间中就能觉知存在的人本身带入其本性中。人就是这样被占有而归属到Ereignis之中。这种归属基于那种标画着Ereignis的归本。通过归本,人就被允许进入 Ereignis 之中。”[11](P24)、[4](P27)Ereignis 使用人去觉知存在,去内立于时间中,还去倾听存在之道说,并把存在带向语言。
从海德格尔对Ereignis之本性即归隐 (Enteignis)和归本 (Vereignung)的描述可见,Ereignis不是在存在、时间和人之外的另一个东西,它只是对规定着存在、时间和人三者的那种相互关系的命名。存在、时间和人在Ereignis中各各成其为自身。海德格尔的思想步伐至此,就不复是“蔽于人而不知存在”,亦不复是“蔽于存在而不知人”。因为“存在使用人,以便本质化,而人归属于存在,因此它完成其作为此 - 在的最极端规定。”[10](P251)
当Ereignis成为“服务于思想的主导词”之际,存在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转变为对Ereignis的追问。现在,存在被理解为 Ereignis,而不再像形而上学将存在理解为在场。他认为,作为在场的存在是由Ereignis遣送出来的。但是,存在在遣送的同时,存在本身被搁置了,从而有所谓的存在之诸时代,有所谓的存在之天命和存在之历史。形而上学把存在理解为在场,形而上学对存在的一切规定,从“相”(柏拉图)、“现实” (亚里士多德)、“绝对概念”(黑格尔)到“权力意志”(尼采),都有在场的特征,它们无一例外地显示出“当前”这个时间维度具有优先性。然而,当形而上学这样规定存在的时候,存在被遮蔽,这种遮蔽复又被遗忘。因此,存在历史所指的乃是,存在于发送自身的同时隐匿自身,而且这一隐匿同时又被遮蔽。“存在向我们发送自身,但以这样一种方式:它同时在其本质中就回避了。‘存在历史’这个标题说的就是这回事。”[14](P95)在此意义上,Ereignis不属于存在历史,因为在Ereignis中存在之显示自身的方式已经不是双重遮蔽,存在之遗忘在Ereignis阶段是不存在的。进而言之,存在历史之为存在历史,乃是基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这意味着,滞留于存在历史阶段上的思想 (如形而上学)是不可能发现存在历史本身的这个秘密的。换言之,存在历史作为存在历史,只有在Ereignis中才能成其所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在Ereignis中,存在之历史不是达到了终结,而是现在才显现为存在之历史。”[1](P367)“以 [存在历史] 之名,[我们]不是随意思考某个东西,而是只以更为果断的方式思考已经被思想过的东西。在对从未被瞥见的存在历史之思念中,这个存在历史才首次显现出来。”[14](P95)从 Ereignis 而来的思想沉思存在历史,故而它是存在历史性的思想。
三、海德格尔思想道路整体的结构
根据存在历史与Ereignis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大致可以回答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即:在海德格尔所勾勒的由意义-真理-位置所规定的思想道路中并无Ereignis的位置,但我们若对照Ereignis与存在的关系就可以看出,Ereignis与意义、真理和位置这三者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存在之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和位置问题,都是针对置身于存在历史中的形而上学对存在之遗忘而制定的追问存在本身的方式或路径,虽然这些方式或路径如海德格尔后来所反省到的那样并非没有偏失,但它们毕竟不是与形而上学处在同一个层面,因而已经超出形而上学的局限,尽管这种超出不能算是彻底的。因此,Ereignis与意义-真理-位置处于同一个层面,而当海德格尔提出存在之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和位置问题的时候,他就决不是从存在历史出发来追问的。但是,当思想尚只是从意义、真理或位置来思考存在,而未曾达到Ereignis之际,存在历史就未能显现。所以,Ereignis如果不被提出,而在追问意义、真理和位置的时候,作为存在之存在尚未被区分为作为在场的存在 (存在历史)和作为Ereignis的存在,那么海德格尔对意义、真理和位置的追问将是无根基的;如果不标举一个超出于存在历史之外的Ereignis,就无法洞见存在历史的本质。 “在思存在本身以及思Ereignis的思想中,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作为这样一种状态才是可经验的。”[4](P36)“随着思想投身到 Ereignis中去,Ereignis所特有的遮蔽方式才到来。”[11](P44)、[4](P50)相反,在存在历史之内是无法谈论存在之意义、真理和位置的。当然,这不等于说,Ereignis之思在解除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同时就能够解除存在之被遮蔽状态。正由于此,海德格尔才强调关于Ereignis的思想具有“暂先性 (Votläufigkeit)”[4](P42)
在思想达到Ereignis之后,海德格尔就自然而然地指出,不能再从存在和存在论差异来思了:“用‘存在’概念和‘存在之历史’概念来思Ereignis是不会成功的……存在论差异亦随存在而消失了。”[1](P366)
综括言之,Ereignis这个主导词使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成形为一个整体,在Ereignis未被揭橥之前,“意义”、“真理”和“位置”虽然为真正存在问题之提出做了重要尝试,但仍然是不彻底的,思想道路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尤为重要者在于,这三者之根基尚付阙如。更且,就海德格尔之克服对存在的形而上学阐释这一宏愿而言,从Ereignis而来的思想,较之于思想道路上的“三个步伐”,更能切中形而上学之蔽,其所以如此,端赖于在Ereignis中,存在、时间与人各各成其自身,既非存在决定人,亦非人决定存在,从而拯救了此前之诸步伐所固有的偏失。首先,避免了存在之意义问题所隐含的对重新巩固主体主义之危险。其次,避免了存在之真理问题中强调真理(“无蔽”)太过,而使存在所包含的非真理(“遮蔽”)落于第二义,而在Ereignis中,存在之显与隐同等源始,这意味着,真理和非真理具有同等地位。最后,就存在之位置问题而言,它虽试图突破形而上学的限制而直探形而上学得以运作的根基即存在论差异,但终不免自缚于形而上学的语言而无以逃遁,相反,思想在取Ereignis为服务自身的主导词后,则从实质上和语言上一并弃绝了形而上学而另辟对存在阐释之坦途。职是之故,Ereignis不仅标志着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之完成,亦且补救了此前诸步伐之偏失,而Ereignis在海德格尔之思想道路上的位置,盖在于斯。
[1] Heidegger.Seminare.Gesamtausgabe[M].Bd.15.Frankfurt am Main:Vitorrio Klostermann,2005.
[2] Heidegger.Identität und Differenz[M].Gesamtausgabe.Bd.11.Frankfurt am Main:Vitorrio Klostermann,2006.
[3] 海德格尔.路标 [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 Alberto Rosales.Heideggers Kehre im Lichte ihrer Interpretationen [A].Zur philosophischen Aktualität Heideggers [C].Bd 1.hrg.O.Pöggeler.Frankfurt am.M.:Vitorrio Klostermann.1991.
[6] 海德格尔.尼采 (下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M].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8] 比梅尔.海德格尔 [M].刘鑫,刘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 Hegel.Hauptwerke in Sechs Bänden [M].Verlag von Felix Meiner Hamburg,1999.
[11] Heidegger.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esamtausgabe[M].Bd.65.Frankfurt am Main:Vitorrio Klostermann.1989.
[12] Heidegger.Zur Sache des Denkens[M].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76.
[13] Herrmann.v.F.W.Die”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als her meneutischer Schlüssel zum Spätwerk Heideggers [A].Heidegger,neu gelesen[C].hrg.Happel,M,K ﹠ N,1997.
[14] Heidegger.Der Satz vom Grund.Gesamtausgabe[M].Bd.10.Frankfurt am Main:Vitorrio Klostermann,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