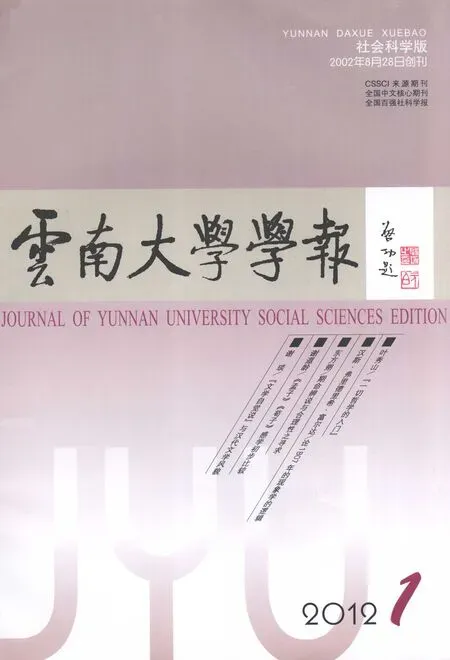“文学自觉说”与汉代文学风貌
2012-12-09谢琰
谢 琰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文学自觉说”探讨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中的关键质变阶段,即文学是如何成为独立的门类与活动的。自从20世纪上半叶鲁迅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后,“魏晋文学自觉说”主导了大部分的文学史叙事。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又连绵不绝地对此发出了反对、商榷或调整的声音,产生了“汉代文学自觉说”、“六朝文学自觉说”,甚至“春秋文学自觉说”,其中又以“汉代文学自觉说”呼声最高,影响最大。因此,全面梳理“文学自觉说”的前世今生,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古文学研究中的观念与方法,进而有可能对汉代文学风貌作出更恰当、较平允的论定。本文略作如下思考,以之求教于方家。
一、“文学自觉说”的建构与解构
1920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艺文》杂志上发表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第一次明确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此文后来被收入到《中国诗论史》中。他说:
通观自孔子以来直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期内进而形成只以对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以为,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著有《典论》一书……评论之道即自此而盛。 《典论》中最为可贵的是其认为文学具有无穷的生命。……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1](P37~38)
这个论断虽然宏观,但切入点实际上只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没有涉及创作。后来,鲁迅在1927年发表了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表面上看是结合了创作与批评而言的,具有更高度的时代概括性,所以被后世学者广泛征引:
他 (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 (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2](3卷P504)
然而,这段论述的意义指向,必须结合文风和时局去探讨,才能认识准确。孙明君指出:“本文不同于那些爬梳史料,精心推敲的科学论文,其间渗杂了许多讥讽时事的成分”,“鲁迅引述了日本汉学界的一种说法,又认为这种说法接近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因为不是他所论述的重点问题,故只是在不经意中一笔带过,不予深论。”[3]“一笔带过”云云,显然矫枉过正,但鲁迅此文在表述方式上的摇曳却是不容忽视的。他提出“自觉说”,其实只是就理论批评而言,甚至只就《典论·论文》作引申,可他前后都在谈创作,把理论批评视作创作的指导、印证与总结,于是让后世的很多文学史家就此发挥,把“自觉”看作包括理论、批评、创作在内的“文学思想”——“文学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中之外,它大量的是反映在文学创作里。”[4](罗宗强序P3)一旦“自觉说”从理论批评层面扩展到文学思想层面,它就很容易失去像《典论·论文》那样的“铁证”,而成为伸缩性很大的主观判断。比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门类自觉”、“文体自觉”、“审美自觉”三个标志出发,把“魏晋文学自觉说”推衍为“六朝文学自觉说”: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5](2卷P3~4)
然而,有意味的是, “汉代文学自觉说”同样可以拿“三个标志”作依据。比如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即便是以袁行霈先生关于文学自觉说的三个标志来衡量,汉代文学也已经完全达到“自觉”了。…… (中间略去例证,引者按)如果说中国文学有一个自觉时代的起点,这个起点也应该是在汉代,而不应该是在魏晋。[6]
此外,龚克昌、张少康、詹福瑞等学者都举出了扎实的证据,足以把“三个标志”提前到汉代。比如龚克昌云:“在汉代的赋家和帝王中,已有一些人提出或欣赏辞赋中以虚构夸张为主要特征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和以句式多变,词汇丰富,辞采华美,注重偶对,讲究韵律为主要特征的艺术形式美。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堂奥已为人们所窥见;文学艺术基本特征的内核,已为人们所掌握。”[7](P348)这体现了第三个标志。又如张少康云:“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开始初露端倪,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这个过程的完成,我以为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8]这体现了第一个标志。
然而,“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倡导者们并不止步于文学思想层面,他们还从创作本身着眼,力图用创作的新变来证明文学的自觉,这便进一步偏离了“文学自觉说”提出之时所臆想的只针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初衷。比如龚克昌提出的“自觉”依据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广泛充分运用”,“追求华丽的辞藻”,“汉赋已跳出‘诗言志’的圈子,进入‘体物’境地,并作为艺术品供人欣赏”。[7](P336~348)詹福瑞也认为:“物象的描写与文辞的运用是否华丽,也就成为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丽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文学的自觉。”[9]这些“标志”,比文学思想的“三个标志”更容易被反驳,因为他们实质上是在用自己心目中的文学标准去重新建构一些“自觉与否”的判断,而不是揭示古人的文学标准本身。因此,若从创作本身着眼,孙明君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正面论述,同样言之凿凿,他认为建安时代“文的自觉”有四个表现:第一,内容上“在情的领域奋力开拓”。第二,“意象的更新与意境的开拓”。第三, “对诗歌形式的探索”。第四,“文人集团的出现”。[3]仅仅综合以上三人的论述,我们就能得到浪漫主义、辞藻、体物、情感、意象、意境、形式、文人集团等八个标志,它们可以证明某个时代的文学在某个方面的新变甚至突破,却很难证明文学整体的自觉与否。比如,从辞藻看,汉赋显然很成熟,从情感看,建安文学又的确有质的突破,而辞藻和情感,究竟谁更重要,更能充当自觉的标志?再比如,单就浪漫主义手法而言,《离骚》为什么不“自觉”?龚克昌给出的理由是:“它的夸张主要表现在作者神游幻境,这与对现实世界进行直接的夸饰还不尽相同。只有汉赋才真正面对生活,对现实世界的大量事物进行直接的夸张的描绘。”[7](P337)这个理由本身是对《离骚》与汉赋浪漫主义特点的极其精辟的区分概括,但若作为“自觉”与否的标准,实在有点牵强——难道想象不是夸饰的更高一层的努力吗?在这样一些各说各话的讨论中,“文学自觉说”实质上已趋近于“文学发展标志说”,已从整体的判断退化为局部的争执。于是,“文学自觉说”的解构在所难免。
首先是积极解构。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指出:
本人并不太赞成用“文学自觉”这一词语来概括汉魏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因为“文学自觉”这个论断的内涵有限,歧义性太大。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兹提出供学界同仁讨论。其一,在中国古代,本没有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完全相对应的概念,只有明晰的文体观,却没有明晰的文学观。……其二,鲁迅在说到魏晋文学自觉的时候,特别强调曹丕的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个时代,但是仔细思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吗?我认为没有。如果真的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也许齐梁时代最为合适。但是这个时代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所占的时间太短,而且往往受到后代的批评。由此而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即便是曾经有人倡导“为艺术而艺术”,那也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其三…… “自觉”这个词语,不仅不能很好地解释魏晋以后的“文以载道”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美问题。[6]
这三条理由可以归结为: “文学自觉说”只能折射出先秦、汉代、魏晋文学风貌的差异,而始终未能给出足以服众的“文学”定义,于是,“自觉”的标准始终含混甚至混乱。
其次是消极解构,也就是走向“无限自觉说”。比如,有学者在春秋时期寻觅到“文学自觉”的蛛丝马迹,便倡导“春秋文学自觉论”: “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10]可见,如果把创作成就等同于思想自觉,再把思想自觉抬高为理论自觉,就几乎可以把“文学自觉”无限地提前,因为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是主观精神的活动,只要产生具备某种审美特质的成果,就是自觉。当“文学自觉说”不再包含激烈的美学关怀,而成为绾合文学史现象的空洞概念,毋宁说它已被最热情的支持者所解构了。
综上所述,“文学自觉说”最初只是就魏晋时代的理论批评风气而发,它也只能在理论批评的层面上才具备科学性。尽管曹丕《典论·论文》的原创性有待商榷,①赵敏俐认为:“曹丕在《典论·论文》所谈到的‘文章不朽说’和‘诗赋欲丽说’,既不是他的首创,他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没有做出超出前人的新的理论发展,没有比汉代其他文人的文学观念更加进步,因而自然也没有如铃木虎雄、鲁迅和李泽厚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那样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所以我认为,把曹丕的《典论·论文》看成是‘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是不妥的。”见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但其表述方式的成熟与活泼,以及作者本人的身份和影响力,都足以构成魏晋时代文学理论批评风气的规模和水平;毕竟,散碎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现象可以用幽微的证据来证明,而明晰的理论批评则只能用坚实的文献作为依据。因此,后世学者的种种建构和解构,背离了“自觉说”的初衷,在理论批评、文学思想、创作现象三个层面上不断发生跳跃、纠纷和杂糅,增添了“自觉”一词的涵义混乱,也模糊了“文学”的概念。
二、从“文学自觉说”反思汉代文学风貌
一个学术命题的价值,有时不取决于其科学性,而取决于其理论张力。 “文学自觉说”作为20世纪至今中古文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一方面不断经历着建构和解构,自身陷入混乱与无解,另一方面又不断加深着人们对汉代文学风貌的辨析和认识—— “文学自觉说”是从“魏晋自觉说”发端,维护此说者极力从魏晋发现汉代文学所不具备的特质,而主张“汉代自觉说”者,也沿袭着前者的标准,力图证明魏晋文学自觉的种种标志也出现在汉代,而对于先秦到汉代的演变,往往含糊其辞,仿佛只需证明“汉代有自觉”,“春秋无自觉”也就不言自明了。从这个角度看, “春秋自觉说”也是“汉代自觉说”的先天缺陷所诱发的。因此,“文学自觉说”的“混乱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学界对汉代文学风貌的反思史。本文将就这段反思史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再作反思。
第一是汉代文体问题。
张少康指出,汉代多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和成熟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佐证。又张少康、赵敏俐等学者指出,汉代目录学著作如刘向《别录》(或举《汉书·艺文志》)已把诗赋单列一类,《汉书·扬雄传赞》、《后汉书·文苑列传》等文献也彰显了汉代人的文体自觉。那么,汉代的文体状况,是否真的有质变发生呢?
首先,汉代的文体的确堪称“多种”,比六朝而不足,比先秦则有余。这种文体的繁衍与分化,是文学史的必然趋势,不能也无法仅从文体规模上判断某个时代是否发生了关键性的质变。所以,以量变去证明质变,无论这质变是否冠以“自觉”之名,都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其次,《别录》或《汉书·艺文志》将诗赋单列,《后汉书·文苑列传》胪列传主所著文体的细目,都是属于目录学意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体意识。但凡有典籍整理的必要和时机,都会出现新的分类,这是文化史演进的必然规律。想要证明汉代目录学意识中已经包含明晰的文体意识,不仅要考察分类之“量”,还要看分类背后的观念是否有质的变化。就《汉书·艺文志》而言,班固对诗赋的认识,仍然停留在“风谕”、“观风俗”、“知薄厚”等传统儒家诗学观上,故对汉赋诸家多持否定态度,讥其“侈丽闳衍”,仿佛汉赋和汉乐府的创作,是“六艺”之“诗”的边角料,秉承某些精神,数量又大到无法用来作为附录,只好另辟一家。就诗赋著录的方式来看,《汉书·艺文志》也显得零乱杂糅。比如把“枚乘赋”、“司马相如赋”著录在“屈原赋”下,把“司马迁赋”著录在“陆贾赋”下,把“秦时杂赋”著录在“孙卿赋”下,却又另辟“杂赋”之名,这些著录方式给后世探讨赋之来源带来了很多遮蔽和误导。至于《后汉书·文苑列传》,范晔对赋颂赞诔的清晰记载,可能已是魏晋之后文体意识的反映了。
再次,《汉书·扬雄传赞》曰:“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这段话中,“传”非“史传”之“传”,而是“经传”之“传”;“史篇”亦非“史传”之“史”,而是“史籀”之“史”;“赋”、“辞”之名,亦混淆不清。这些文体称谓的混乱且不论,更重要的是,班固对文体的认识,以及扬雄本人的意识,都必须附着于特定经典,远未悬空总结出文体的性状与风格,如《典论·论文》那般——“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就好比鹦鹉能言而不离禽兽,仅仅是模仿,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觉。
综上所述,就创作而言,汉代的文体只有量变的发展;就文学思想而言,汉代人只有目录学意识和模仿意识,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体意识。所以,汉代的文体状况,仍与先秦一脉相承,距离魏晋尚有鸿沟巨壑。
第二是汉赋的修辞问题。
龚克昌、詹福瑞等学者都明确地把“丽辞”作为“汉代文学自觉”的重要依据,龚克昌所谓“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以及“艺术形式美”,也与“丽辞”关系甚大。那么,汉代文学尤其是汉赋的修辞,是普泛意义的审美,还是自有其时代独特性?在整个修辞史上处于怎样的阶段?
先看四则材料:
《西京杂记》卷2: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汉书·王褒传》:(汉宣帝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
《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
《汉书·叙传下》: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司马相如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只是“赋之迹”,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才是“赋家之心”。汉宣帝说辞赋之“辩丽”属于“小者”,而“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才是“与古诗同义”的“大者”,因为孔子对《诗》的评价是: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同样,扬雄也以为“丽靡之辞”的目的是“将以风也”,而手段则是“推类而言”,具有认识论层面的要求。至于班固对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认识,也不仅强调“淫丽”、 “托风”,还强调“多识博物,有可观采”。综合这四条材料可见,汉代人对“丽辞”的认识与强调,都不是孤立的文学见解,而是熔铸在儒家道德观之中予以正面评价。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丽辞”具有独立于道德观之外的价值,这价值也不是以审美为第一义,而是以知识主义为精神实质,即所谓 “苞括”、 “总览”、 “多闻”、“博物”。一言以蔽之,“丽辞”不仅是审美的产物,更是知识的展现。
事实上,知识主义是先秦儒家的一贯传统,也是汉代思想史的基本精神,正如顾炎武《述古》所谓“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汉人普遍认为儒者应当博洽多闻,追求百科全书式的博览。比如扬雄《法言·君子》曰: “通天地,人曰儒”, “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张衡《应闲》曰:“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无范。”(《后汉书·张衡传》)又《汉书·楚元王传》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又颍容《春秋左氏条例》曰: “汉兴,博物洽闻著述之士,前有司马迁、扬雄、刘歆,后有郑众、贾逵、班固,近即马融、郑玄。”[11](P149)在这种知识主义的气氛中,汉代赋家自然把“苞括”、“总览”、“多闻”、“博物”视为作赋的重要目标。因此,袁枚《随园诗话》卷1的这段话虽无不偏激,也不无道理:
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艶,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
既明汉赋之“丽”实质是知识之丰富、认知之活跃,那么,接下来的六朝文学也常被冠以“丽”名,两种“丽”,区别何在?
刘师培《论文杂记》指出:
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述,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12](2册P85)
与此相似,朱光潜《诗论》也认为魏晋赋“技巧渐精到,意象渐尖新,词藻渐富丽,作者不但求意义的排偶,也逐渐求声音的对称和谐”。[13](2卷P189~190)可见,六朝之 “丽”集中体现在骈偶和声律方面,此二者不再承担知识功能,而只是为了“形式美”。
综上所述,汉赋的修辞本质是一种知识主义精神,是先秦文化的遗泽,也极大地依附于汉代文化风气,在整个修辞史上尚处于初级阶段。
第三是汉代文学的内容问题。
鲁迅对魏晋文学的界定是“清峻”、 “通脱”、“华丽”、 “壮大”,结合他前后的语境,这四个概念基本都与魏晋文学的情感内容有关,也就是所谓的“建安风骨”。而孙明君认为建安时代“文的自觉”有四个表现,他也把“在情的领域奋力开拓”列为首位。可见,在“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倡导者看来,内容的彻底改观是汉晋分野的关键标志。既然情感是魏晋人的骄傲,那么是否意味着汉代文学“寡情”或“多理”呢?
首先,就“理”而言,汉代文学继承了子部传统,但又明显不如先秦诸子深刻。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又余嘉锡《古书通例》曰:“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14](P216)子部的衰落直接导致汉代文学的思想内容的平庸化。而平庸并不意味着“少理”——事实上, “理”成为包括汉赋在内的汉代文学的终极追求。无论是讲养生,讲治道,还是讲自然规律,汉赋始终抱定“曲终”所奏的“雅”,始终坚持“劝百”之后的“讽一”。这些“雅”和“一”,基本都是已知的道理,而不是原创的思想。原创需要清晰明断的推理,而已知的道理则只需充分地纳入细节中。至于两汉之交最引人瞩目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扬雄,也难免“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之讥。因此,如果说先秦文学的思想内容主要是阐发未知,那么汉代文学则侧重于阐发已知。
其次,就“情”而言,汉诗大多是原生态的民歌,汉大赋是根本寡情的,骚体赋的情感具有浓厚的模仿性,对问体则具有浓厚的游戏性。也就是说,除了具有永恒抒情传统的乐府诗,汉代文学在情感表达上一直充满遮蔽和隐喻。相比之下,魏晋文学的情感浓度固然是空前加强了,但更重要的是,魏晋文学的情感表达方式变得直接而坦率。韩高年指出:魏晋赋风“首先一个转变,是赋的创作中‘体物’与‘缘情’并重,以及由此导致的赋的‘小品化’。”“魏晋作家多以状物为依托,借以抒发感伤忧愤之情。” “魏晋时期抒情短赋在辞赋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在七成以上,也说明了抒发情感的要求对与之相适应的辞赋文体的吁求。”[15](P279~281)可见,单就辞赋而言,魏晋与汉代就有本质区分。至于魏晋诗歌对于乐府抒情传统的灵活运用与显著突破,则早已是文学史的常识了。
综上所述,从思想内容看,汉代文学仍处于先秦文学的绵延阶段;从情感内容看,汉代文学与魏晋文学根本不同。
要言之,综合文体、修辞、内容三端而言,汉代文学仍有诸多模糊、依傍、质朴之处,在整体风貌上仍应归属于上一时代。
三、初步结论
本文梳理了“文学自觉说”的来龙去脉,并结合此段学术史,探讨了汉代文学风貌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初步结论如下:
第一,单从理论批评看,魏晋文学明显“自觉”。一旦扩衍到文学思想、创作现象,便无所谓“自觉”。
第二,从文体、修辞、内容看,汉代文学更接近于先秦文学,与魏晋文学差异明显。
第三,我们应悬置“自觉说”的本体,而关注“自觉说”的“断限效应”。也就是说,抱着追寻文学发展的某些关键质变阶段的态度,去考察各个时代文学风貌的异同。从这个角度看,“魏晋文学自觉说”包含着鲁迅那个时代对于文学本质的高度敏感与西化思考。即:
怎样的文学思想才是近代意义的?答曰,是抽象的,不是实践的。所以,只有理论批评的成熟,才堪称“自觉”。
怎样的文学创作才是近代意义的?答曰,是感发的,不是阐发的。所以,只有像魏晋文学那样的情感主义,才是“文学”。
笔者以为,这才是“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真正初衷。而在此“断限”的意义上, “魏晋文学自觉说”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合理性。
[1][日]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 [M].许总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2]鲁迅.鲁迅全集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J].北京大学学报,1996,(6).
[4]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J].中国社会科学,2005,(2).
[7]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8]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 [J].北京大学学报,1996,(2).
[9]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J],河北学刊,1998,(4).
[10]李永祥.“春秋文学自觉”论——兼与赵敏俐先生《〈“汉代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J].汕头大学学报,2010,(2).
[11]王利器.郑康成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3.
[12]刘师培.刘师培全集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13]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含古书通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韩高年.诗赋文体源流新探 [M].成都:巴蜀书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