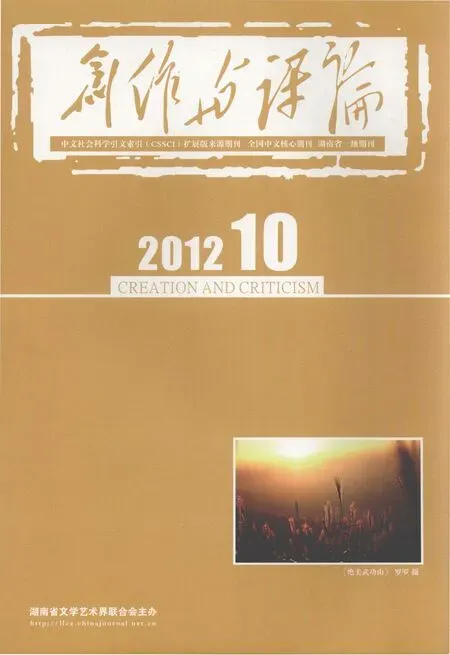“心里敞开了星空一样的光芒”——蒋三立诗歌读记
2012-11-24张清华
■ 张清华
听不见胡笳声。想苏武
想大漠上的星星,深邃,高远
想风沙一样吹来的许多许多的往事……
千年的月光,万年的霜
今夜,不眠的我提着内心的马灯
照亮自身影,相寻泪成血
这是蒋三立的胡笳十八拍,是他在不眠的深夜所写下的一首《深夜》中的句子,也是他在内心的烛光或灵魂的马灯的照耀下的一番演奏,低沉、婉转、辽远、永动,读之让人不觉有内心的怦然和戚戚焉,仿佛有电流穿越。
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纯粹”的演奏了。这本《在风中朗诵》,让我一整个下午都沉浸其间,仿佛是在听一场来自古代、或者某个桃源式乌托邦的弹拨或者倾诉。
我一直相信,一本诗集其实就是一首音乐作品,其中的每首诗彼此都具有奇妙的“互文性”——都是这音乐的一个片段,它们细细密密地连接着,互为乐句的延伸,或者背景装饰;或者也可以将其看做是一座好的建筑,每首诗都是其中的一个房间,一间密室,有幽曲的风景,别有洞天的摆设,它们彼此紧紧地连接着,互相支撑,互为背景,成为对方不可拆解和或缺的部分。这是创造的奥秘,也是其间诱人的乐趣所在。如果没有这样的境地,在我看来,一本诗集的存在理由就大大减低了。《在风中朗诵》让我相信,它是属于这样一种关系的产物,也是一个臻于佳境的范例。
我与这部诗集的作者蒋三立其实只有一面之识,对于他性格为人的细节所知无多,但他的诗歌却似乎为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其人、感知其心的很好的入口,这大约也可以算作“读其诗想见其为人也”了。在我观之,如说是“忧郁”则未免有些许夸张了,但必定他是有一颗敏感之心的,他对世界保持了如此纤细和精微的感受力,也保持了一份洁净和易于“受伤”的状态——这是一种心灵敞开的,至少是未曾放弃人格准则与情怀胸襟的状态。对于一个深入中年,且在这俗世生涯中混迹半生的人来说,委实不易。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他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尊重的诗人,一个接近于脱离了诸种功利之心的纯粹的诗人。
但这个评价我以为还不足以体现他的意义。如果要寻找一个可资比拟的例证,我想到的是四十年代的冯至——现代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分量颇重的诗人,这很奇怪,虽然我并不能确定三立诗歌写作的背景,以及影响的来源,但从诗歌的品质与诗意的取向来看,他同四十年代写《十四行诗》时期的冯至相比,确乎有某些类似之处,或许是属巧合,但至少它表明,他的诗歌写作是具有哲学质地和形而上的意味的,是有对于生命与存在的敏感之思的。请读开篇这首《一只粉虫》中的句子:
它想表明,它不是一只害虫
一生只需要一片叶子,这是它最大的愿望
它感到知足和快乐
天气一天天好起来,有一天它突然觉得自己占有的
这片叶子长得太大了,叶汁也越来越甜
它渐渐地愧疚起来,它觉得应该邀来
更多的粉虫,在阳光下享受这片叶子
它懂得,这不是因为生命的短暂
而是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
或许这首诗的结尾处理得稍显平易了些,显得不够“陌生”和苍茫,但对照冯至所表达的那种“对于存在的体验与顿悟”,以及在顿悟中所经历的“灵魂战栗”,他似乎又多了一份“在场”的具体,也更多了一份安之若素的达观与“道德感”。毕竟生命的卑微和渺小是无法改变的,在宇宙和世界的永恒中,任何孤独的个体都摆脱不了短暂留存的命运,但惟其如此,他才更应该珍视,并与他人共享这“存在的幸福”。所以,与冯至相比,三立的表达似乎又有了某些独到的新意。让我们对照冯至的诗句: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显现,狂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成屹然不动的形体……”确实,在冯至这里。生命于片刻的闪耀中显现出了它令人激动和彻悟的欢欣与苦难。诗人深刻地洞察了生命的脆弱,但又深信着那彗星般的历程中意义的不言自明,深信那渺小个体里充盈的美好记忆与凛然的尊严。冯至是厉害的,他将一只昆虫的意义升华到了哲学境地——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了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不过三立也不是吃素的,他从一个最为卑微的生命中也获取了生存的意义,书写出它的欢欣与自足,并且同样生发出对于生命与存在的哲学性的体悟。这再次证明,他特有的纤细与敏感并非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自恋,以及小情小调的怨艾与渲染,而是一种真正的彻悟与达观所支配的坦然与淡然。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生命的悲悯与礼赞,对于时光与记忆的追想,对于存在的领悟与经验,成为了蒋三立诗歌的核心与主旨。他是太纠结于此不能释怀了,以自我的生命境遇去体悟自然,以自然的法则与万象去拟喻自身,他实现了生命世界的互通与穿越,主体与镜像之间的交会与投射,如同庄子“齐一”的观物方式,也如同王国维所描述的“有我”与“无我”两种境界的合一。他诗歌中的生命形态,是如此齐整又错落地融于一体,让人不时生发出无言的感动,沉陷于百感交集的复杂心绪。
让我举出他描写最微小的生命的例证:《夏夜》、《春天的小径》、《我无法对秋天诉说》、《多想蜻蜓一样在漂浮的落叶上做一个梦》、《大地情深》……这些诗中他反复地写到“卑微闪烁的萤火虫”,写到“穿越无数季节的昆虫”,写到“溪水里游动的小鱼”,写到“干旱小径上钻出泥土的蚯蚓”,写到“四处觅食的瓢虫、一长队负重的蚂蚁”,写到“知了在柳枝上的哀鸣”,“蜻蜓一样睡在一片红红的落叶上”……当然,还有牛羊、庄稼、农人,乡间以及自然中一切善良而温和的、卑微而安详的生命。每当写到这些,他总会由衷地流露出赞美、热爱、认同和怜悯,并且从中获得启示与激励,得到满足与安宁。
这多像是冯至式的句子——
那些穿越无数季节的昆虫
在路边又想见了。/微小的
长着透明的薄翼,/从树叶里飞出
经历过冰冻的寒冷,/这些细小的昆虫
能飞在春天的暖风里,/多么不易……
又何等平易和简单的句子,但却生发出并不单薄的诗意。
然而,蒋三立并非总是借助物象来建立其诗意,在另一些作品中,他更加直接地传达了他对于生命的脆弱与孤独的看法,或是通过追想童年记忆,来表达生命中一种失落的惆怅。比如《黄昏》、《戏台》、《风》,这些篇章同前面的例证一样,异曲同工地传达的是诗人对于世界与生命的理解与彻悟。它们充满感伤意绪,但又并不沉溺于伤怀,而是如同张若虚、陈子昂、李白或是苏东坡一样,总是洞悉并达观地将其消解于一种对于自然与法则的领悟之中。某种意义上,其中既有东坡式的“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嘱,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一样的旷达,也有海子式的“大风从南吹到北,从东吹到西,你所说的曙光是什么意思”,或是“风的前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的前面还是道路”式的“哲学的悲怆”,这种悲怆,类似于李白式的“万古愁”,也接近于鲁迅式的“大悲催”——
风吹散了那些抱紧的草
又沿着这条铁轨走了很远、很远
风吹干了我送别的泪水,滋润心灵的泪水
……现在你越来越狠抖动着天空
抖动我骨骼里风湿的痛
还有远处春天里的花粒,也被抖动着
撒成很远很远的孤独
这是他笔下的《风》,你可以将这看做是“没来由”的东西,但它的苍茫与辽远还是令人难以割舍和难以错过的,难以将其视为通常的“撒娇”。而且我还要说,有时候三立的处理,还更体现出他独有的一种风格或方式,即来得更为淡然和邈远,更为细小和清逸。比如《黄昏》中的句子,便是在勾画这种“存在的怅惘”或“哲学的悲怆”的同时,又显现出了一种有意味的在场感与细节性:“山坡、河流、小路,没有什么不刻在心上/剥蚀摇晃的木桥,低矮的木屋/是不是和我一样在岁月中有着梦想/土墙边的老人蹲得和旁边的木桶一样旧了/表情有着磨损的伤感。高过屋顶的/树上的空巢,塞满了夕阳的影子/在回家的路上,丢了魂的蝴蝶,擦着暮色的清冷/翅膀张得比黑夜还宽”——
它扑打着我的心灵
像是挣扎,一下、两下、三下
确乎像当年的冯至在沉寂十余年,又忽然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敞开一样,我们无法不认为三立和世界之间出现了一种洞彻的敞开,“生存、和谐,彼此用光芒照亮”,他从对象世界中看到了“这么远大的夜空,这么宽广的大地”,也以“卑微闪耀的萤火虫”的姿态与身份,看见了那些让人战栗、让人冥想的存在的真理——
心里敞开了星空一样的光芒……
其实这也是在说他的艺术特点了。“方法也即是世界观”,维特根斯坦说过大意如此的话。三立对于自身与世界的认知关系的处理,对于诗意的提炼,说简单点,其实都是归结于对“生命经验”的关注这一焦点,而他的生命经验又很少是通过玄虚的观念辨析来予以表达,而是通过各种细小而丰富的生命形态来予以呈现。这也就生成了他诗歌中鲜明的细节性与视觉感,以及自然而传神、朴素又鲜活的意象传达,还有看似散漫低缓、实则充满一唱三叹的“胡笳”式、或“大提琴式”、或是“G弦上的咏叹调”式的节奏感。这些,读者从中自然有所体会,无须我再赘言。
需要再强调的一点是,三立是善于将诗意予以提炼和纯化的一位。他总能从寻常的事物与景象中,找见让人揪心的东西;从外部世界的物象中,找到和自己休戚相关的部分;从遥远或细小的客体身上,找到与精神和存在的玄虚之物互相感应的去处,这是他尤为令人钦佩的地方。虽然,在一些篇章中,他过于显得漫不经心和不事经营了,确乎有些篇章也显得过于散漫,结构和节奏不太讲究,但总地来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高手——虽然下手很“轻”,但却常常能够以轻见重,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他是“在风中朗诵”,风声确乎会掩盖或吹散他的声音,但这声音属于自然,属于善于倾听的生命,所以也就无须担心或刻意为之,因为它可以融入自然的共鸣,与天籁的混响之中。
忽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号称“深度意象派”的诗人罗伯特·勃莱,觉得三立的诗,某种程度上也很像他所倡导的一种理念,即去除理性和学院派传统的拘囿,通过引进中国古典诗、拉美诗歌,以及欧洲超现实主义诗歌中的精髓,来缔造一种“奔流于大自然的,突然从底部和下层生长出来的树干与鲜花”一样的诗歌,三立确乎没有学院派的呆板与观念的堆砌,没有“知识分子写作”的“掉书袋”气,也不存在“口语派”的粗陋与蛮俗,更没有技术主义至上的本末倒置,却有一种天然的灵敏与悠远,荒茫与丰富。这是他最值得赞赏的一点。
也许勃莱的一首《冬天的诗》中的这些句子,可以佐证三立的风格,映照他对于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态度,虽然他所表达的,是属于他自己的爱的方式,但这何尝不是蒋三立和他的世界的一种关系——
冬天的蚂蚁颤抖着翅膀
等待瘦瘦的冬天结束
我用缓慢的,呆笨的方式爱你
几乎不说话,仅有只言片语……
同样是令人惊奇的神似。含蓄、节制,但富有隐喻性与弥漫力,好的诗歌应该有这样的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