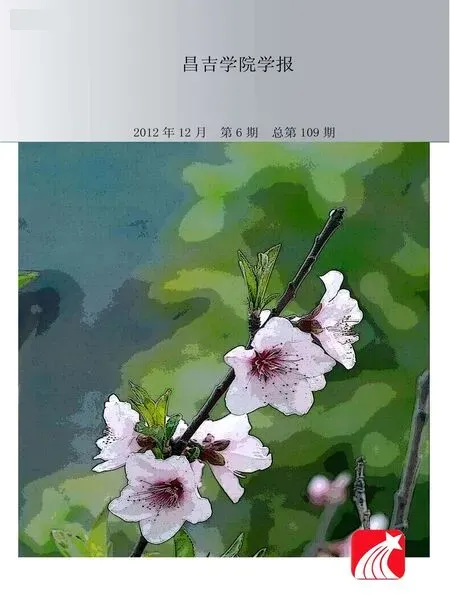网络舆情模式建构初探
2012-11-14王忠国
王忠国
(昌吉学院中文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日益发展,网民表达意见所依托的平台也呈现了多样化、便捷性等特性。由于网络新媒体自身特有优势,受众的媒介接近权由以前的获取信息权转变为通过自媒体进行信息制作和信息传播。同时,参与网络表达的受众不仅仅局限在高收入、高学历、大城市等人群,低收入、低学历、城镇农村等人群逐步活跃在网络平台上。也正是因为这一转变,通过网络舆情对社会的考察更加客观和全面。本文就是试图通过界定定义,勾勒网络舆情要素的研究,提出一个能够解释网络舆情内部关系的建构模式。该模式的建构不仅有利于认识网络舆情,还对地区网络舆情、高校网络舆情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网络舆情要素
(一)舆情的界定。由于研究对象和路径不同,对网络舆情要素的理解也不同。这些不同一个主要原因是对舆情的认识不同所致。因此,在研究网络舆情要素之前,有必要先界定舆情的概念。
舆情的概念成为我们研究和认识网络舆情的基础。有研究者认为舆情就是舆论的情况,该概念过于简单。王来华在其专著《舆情研究概论》中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1]刘毅则认为这个定义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社会政治态度是舆情的核心。张克生则认为舆情是指“国家决策主体在决策活动中必然涉及的、关乎民众利益的民众生活(民情)、社会生产(民力)和民众中蕴藏的知识和智力(民智)等社会客观情况,以及民众在认知、情感和意志基础上,对社会客观情况以及国家决策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民意即狭义舆情)”[2]本人认为该定义基本指出了舆情的最基本的内容:认知和态度。但是上述定义将舆情界定在政治态度层面,而舆情不仅仅局限在政治态度层面,实际上要比这个大的多。刘毅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到古代文献中出现舆情二字多达上千处。刘毅也对这些舆情的出处进行了分析,认为古人舆情的基本含义为民众的情绪、民众的意愿和意见。[3]综合古今文献,刘毅认为所谓的舆情是“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4]刘毅的这个定义的外延超出了政治层面,但是概念的核心依旧没有跳出前人的认知和态度层面。以上研究者的定义都认为认知和态度是舆情的一部分。
但是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对舆情的认识依旧处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根据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舆情应该是客体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对主体所造成影响的呈现。不论是国家管理者还是普通民众,要判断舆情,也是从这三个方面去认定的。因此,本人认为,舆情就是公众对所关心的各种事物所持有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综合。这里的综合包括舆情主体、舆情客体(各种事物)、认知、态度、行为等各方面的情况。而认知、态度和行为则是舆情的核心。当舆情表面上停留在认知、态度层面时,不表示没有行为,只是行为没有外显而已。之所以将行为纳入舆情范畴,首先是行为本身的存在是不能忽视的,其次行为是认知和态度的进一步延伸,最后对舆情的认定更加立体和全面。
在舆情界定的基础上,再来探讨网络舆情就容易多了。网络舆情就是网络舆情主体围绕网络舆情客体所呈现的认知、态度、行为综合。只是网络舆情中的行为(网络行为)有转向现实行为的趋势。网络环境下的舆情与网络环境之外的舆情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网络环境之外,公众处于相对沉默的状态,因此舆情相对较为隐秘。由于网络环境的低门槛、网络平台便捷性和网民的匿名性,网络舆情相对公开和透明,也相对易于观察。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一旦网络舆情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为现实行为。因此,对网络舆情的考察既要考察网络环境中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这里是指网络行为),还要考察因此而演变为现实中的行为。
确定了舆情、网络舆情的定义,再来探讨容易混淆的舆论与舆情。中外很多学者从各自角度分别对舆论做了界定。Holcombe认为“舆论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并且具备合理决断能力的观点。”[5]James T.Young 将舆论认定为一种“社会性判断”。喻国明则认为舆论是就某一争议性问题所形成的共同意见。陈力丹的舆论定义要更加综合,他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6]以上的定义都过于复杂,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以上所指舆论其实就是某种认知、态度或者二者总和,态度本身就含有情绪。而在实际生活中,行为是舆论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本人认为所谓的舆论就是指主体对客体所持有的认知、态度、甚至是行为。通过舆论的定义,不难看出,舆情和舆论既有不同又存在一定关联。
(二)网络舆情构成要素。根据网络舆情的定义,网络舆情的要素主要由网络舆情主体、网络舆情客体、网络舆情本身(舆情主体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综合)、网络舆情空间等构成。
网络舆情主体是广大网民。不同发展阶段,网民的构成和规模有着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影响到网络舆情的总体情况。网民构成越全面,网民规模越大,网络舆情就越接近整个社会舆情。根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截止到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在2012年刚开始上网的新网民中,农村网民比例达到51.8%。”[7]随着入网终端的便捷性和廉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以及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将成为我国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网络舆情更加能够反映整个社会舆情,更加具有普遍性。
网络舆情客体是指能够引起网民兴趣的中介性社会事项。中介性社会事项是整个网络舆情的激发因素,也是整个网络舆情的中心,但不是核心。中介性社会事项可以是国际公共事务、国家和政府公共事务,也可以是社会公共事务。
网络舆情空间是网络舆情存在和演变的必不可少之条件。网络舆情空间与网下舆情空间既有相同点,也存在巨大区别。相同之处在于舆情存在都必须要具备“硬空间”。区别关键在于对“硬空间”接近权的突破和“软空间”控制能力的弱化。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开发,受众的媒介接近权不断有所突破:从逐步实现从媒介获取信息,到利用媒介发表言论,再到今天可以参与媒介如微博制作信息并传播信息。在“软空间”方面,“秩序规定因素的制约作用在网络环境下发生了弱化,尤其是法律规定、伦理道德等制约方面的弱化”。[8]综合“硬空间”和“软空间”的巨大变化,网络舆情空间的互动达到了空前的频繁程度。同时,网络舆情空间的开放程度也已超出了舆情空间的开放程度。
二、网络舆情要素关系模式
根据前文所述,网络舆情就是广大网民在网络舆情空间中对某社会中介性事项具有什么样的认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出现什么样的行为的综合。根据这一表述,本人提出网络舆情建构模式,该模式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网络舆情内部要素关系。

该建构模式基本涵盖了网络舆情的四个主要要素:网络舆情主体、网络舆情客体(中介性社会事项)、网络舆情核心(认识、态度、行为)、网络舆情空间。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考察网络舆情,往往是以认知、态度、行为作为核心。但是在考察核心要素时,不得不结合其他三个要素做综合分析。因此,网络舆情不仅仅是认知、态度、行为,而是上述四个要素的综合。这里的综合不是上述四个要素的简单相加。
其次,作为网络舆情客体,中介性社会事项既可以是存在于客观现实,也可以存在于虚拟现实。
第三,网络舆情空间是中介性社会事项激发舆情的场所。对于网络来讲,舆情空间在硬件上是指网络技术、网络平台,如论坛、微博等;在软件上是指网络控制机制(把关机制不断弱化)。网络舆情空间不应仅仅是软硬件问题,还应包括舆情主体能够实现互动所必需的共通意义空间。共通意义空间是舆情产生、演变的前提条件。
第四,网络舆情的核心是舆情主体对客体所持有的认识、态度和行为。其中行为存在于网络中,也存在于现实中。而了解这三个层面,既有利于认识舆情本身,也有利于舆论引导。
第五,网络舆情空间不是封闭的,它是开放的。因此,网络舆情主体在网络上的态度和行为,很有可能演变为现实中态度主导下的行为,而该行为则会影响到网络舆情客体。
该模式是以传播学视角来界定舆情内涵的基础上建构的,因此,该模式体现了互动这一传播本质特征。同时,该模式具有理论上的参考价值,在应用上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本人认为,在理论上,该模式有助于区域网络舆情模式、高校网络舆情模式等模式建构,对社会舆情模式建构也有着一定参考价值;在实际应用中,该模式既可以解释网络舆情,也可以解释范围更小的区域网络舆情、高校网络舆情等,对于舆情预警和引导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3][4][8]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9,5,51-52,130.
[2]张克生.舆情机制是国家决策的根本机制[J].理论与现代化,2004,(4).
[5]刘建明.舆论学概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24.
[6]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11.
[7]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