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方法和调整机制创新研究——对北京市的应用与检验
2012-11-09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100872)
作为区分受助者与非受助者标准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低生活保障线合理与否,影响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也影响到受助者的生活水平。目前,各地采取不同的方法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除少数大中城市之外,多数区县一级采用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计算方法极不规范,且没有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调整机制,造成保障水平普遍偏低。因此,规范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计算方法,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调整机制是当前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要议题。
自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布思(Charles Booth)和朗特利(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开创贫困线研究之先河后,贫困线制度已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发展出预算标准法、1天1美元法、恩格尔系数法、新方法、相对剥夺法等几十种方法。在中国,随着农村反贫困研究的深入,农村贫困线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式建立之后,我国借鉴贫困线的计算方法对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发展出多种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计算方法。但是,这些新方法均存在计算复杂、难以调整等问题,因而在现实中很少得以应用。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专家马丁·瑞沃林(Martin Ravallion)等人在确定基本食品支出的基础上,通过有关统计资料建立总支出与食品支出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推算出贫困线。这一方法非常清晰地将贫困线划分为食物线和非食物线,但是非食品线的计算比较复杂,很难确定一个公认的非食品线贫困标准,而且因时点、地点和部门的不同计算得到的贫困线不一致,有时差异十分大。目前,这一方法只应用于农村贫困线的计算,没有任何地方在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计算中采用这一方法。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线计算新方法,并对这一方法进行检验。
一、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方法创新
1.新方法的理论基础
早期,人们通常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贫困的内涵,贫困线通常被理解成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从狭义的经济范畴理解贫困,其合理的“内核”在于:贫困是指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理生存的状态,而非一种被公众普遍承认的生活方式。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贫困国家,维持人体基本生存的需求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可能存在必需品和价格的不同),这是贫困的共性。在中国,最低生活保障的根本目标,就是运用国家财力帮助那些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贫困人口摆脱生活困境,使其达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换言之,贫困人口在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后,能够避免挨饿受冻,并能够享受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三条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最低生活保障线只能考虑维持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
但是,“维持基本生活”也会因时、因地而异,或者说,“绝对的”贫困线也应该是“相对的”。随着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新的消费品被添加到必需品的菜单中,“基本生存”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美国经济学家费希尔(Gordon M.Fisher)也说:“例如(19世纪80年代制订的)标准预算没有考虑电器、汽车、菠菜、收音机和1938年舒适的生活模式中可以看到的其他东西。而1950年的预算毫无疑问将使目前的一些东西看上去像窄底裙一样过时。”[1]而且,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了新的贫穷……拥有私家车的人越多,公交车上的乘客就越少,车费就越高,公交服务就得削减……拥有中央空调的人越多,煤的需求量就越少,那么没有空调的人买煤的途径也越少。煤价越高,因为贩煤的人数渐渐地减少了”[2]。也就是说,贫困线应随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另外,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阔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维持生存的内容差别相当大。如北京市的贫困人口标准只能和北京市居民收入水平来比较,不能与贵州居民收入水平来比较,反之亦然。因此,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线必须坚持与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相联系的原则,这样,最低生活保障线既体现维持基本生存,又随时代进步相应提高标准,同时还照顾到地区发展。或者说,最低生活保障线既要体现贫困的“绝对内核”,又要体现贫困的“相对价值”。
那么,如何在贫困线的计算过程中将绝对贫困理念和相对贫困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呢?阿马蒂亚·森的思想给中国农村贫困线的确定以很好的启示。他认为,“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相对标准,人民都把饥饿作为严重的贫困问题,在贫困概念中确实有一个不能去掉的‘绝对贫困’的核心,它不用进行对比就可以把饥饿、严重营养不良和可见的困难确定为贫困”[3]。由此可见,贫困包含了一个绝对的“贫困内核”,即维持人体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同时,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有尊严地生活,穷人也不例外,随着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予穷人的救助标准也应提高。根据森的思想,可以将贫困线划分食物线和非食物线两部分:食物线根据人的最低热量需求确定,重在“饱肚子”;非食物线考虑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之外的最低衣着、住房、燃料、教育、医疗和交通等必需品支出,重在“保面子”。
2.新方法的基本步骤
根据上述思路,可以将最低生活保障线划分为两部分,即食物线和非食物线,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LS0为初始最低生活保障线,FPL0为初始食物线,NFPL0为初始非食物线。
确定人体最低热量支出后,将其分解为不同的食品种类和数量,最后根据食品价格计算总支出。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Fi为第i种食品的数量;Pi为第i种食品的价格。
非食物线采用低收入群体(5%或10%)的恩格尔系数计算。即:食物线÷总消费支出×100%=恩格尔系数。进行简化后,得到:

其中:E表示低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
计算得到初始最低生活保障线后,需要根据价格指数和收入增长情况对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调整。人的热量支出与年龄、身体活动状态等因素有关,与时间的关联性不强,或者说,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确定了热量支出标准和食品项目支出内容,食物线就只与价格关联。因此,建立价格与食物线之间的联动机制,确保食物线的购买力(并不需要提升其购买力),是食物线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要保证食物线的购买力不出现下降,宜采用食品价格指数作为调整参数。根据食品价格指数的变化,每年对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调整。考虑到食品价格指数的发布具有一定的时滞,建议每年3月份公布调整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从每年的4月份开始执行新标准。由于存在福利刚性,福利标准只能升不能降,因此,凡出现平均食品价格指数下降的情形,则暂不调整食物线。建立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挂钩的机制是非食物线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建议采用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标作为衡量社会生活水平的指标。
食物线的调整公式:

其中:FPLn为本年度食物线;FPLn-1为上年度的食物线;FPIn-1为上一年度的平均食品价格指数(12个月的算术平均值)。
非食物线的调整公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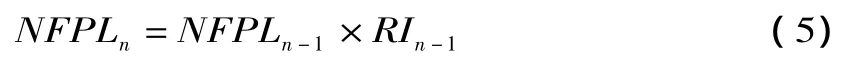
其中:NFPLn为第n年度非食物线;NFPLn-1为第(n-1)年度非食物线;RIn-1为第(n-1)年度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
根据食物线和非食物线的计算方法,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计算公式:

二、对理论标准的适度性检验——以北京市为例
为了检验上述最低生活保障线计算方法的适当性,以北京市为例进行检验。为了便于与现行标准相区分,将采用上述新方法计算得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称之为理论标准。
1.北京市理论标准的计算
为计算方便,假设以2000年为初始贫困线的计算时点,且食物线只随价格调整,不对菜篮子内容做调整。
首先,确定最低热量支出标准。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农村建立贫困线时,采取的标准是最低日摄入热量2 100大卡。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一标准已显得过低。参考中国营养学会提出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并依据世界卫生组织1985年的报告《能量及蛋白质需求》提出的标准,建议将2 200大卡/人·天(18岁~60岁的成年人口)作为计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最低热量。
其次,确定食物种类和数量。结合北京市的食品消费特征,以36个大中城市主要农副产品为依据,选取以下食品作为计算食物线的食物清单种类构成:(1)谷类。包括粳米、面粉,所提供热量各占谷类供给热量的50%。(2)肉禽类。包括瘦猪肉、瘦牛肉、瘦羊肉、鸡肉,所提供热量占肉禽类供给热量的60%、10%、10%、20%。(3)蛋类:鸡蛋。(4)鱼虾类。包括鲤鱼、草鱼,所提供热量各占鱼虾类供给热量的50%。(5)乳类及乳制品:牛乳。(6)豆类及豆制品:豆腐。(7)油脂类:色拉油。(8)蔬菜水果类。包括大白菜、西红柿、油菜、苹果,所提供热量各占蔬菜水果类供给热量的25%。根据各种食物每100克可食部分提供的热量,可以计算出提供所需热量的食物可食部质量。为方便计算,不考虑北京市与其他地区饮食结构的差别。
再次,采集食物价格,计算食物成本。以北京2000年主要农副产品的零售平均价格为计算基础。由于不同食物种类存在不同的损耗,故设立调整系数。损耗越高,调整系数越大。最后得到每天的最低食物支出为5.39元/人(见表1)。

表1 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理论标准的计算过程(2 200大卡/天)

说明:(1)食品价格为2000年北京主要农副产品零售平均价格:粳米标准品,面粉标准品,鲜猪肉去腿后骨肉,鲜牛肉去腿后骨肉,鲜羊肉去腿后骨肉,白条鸡,鸡蛋,活鲤鱼,活草鱼,色拉油一级散装,大白菜,西红柿,油菜,苹果国光。鲜奶价格是36个大中城市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项目价格监测汇总表中的普通袋装鲜奶价格。由于缺少豆腐价格数据,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2009年11月上旬的数据,北京市500克黄豆标准品(三等)的平均价格为4.065元(平均超市价5.13元和平均集市价3元的平均值),500克豆腐的平均价格为1.675元(超市价2元和集市价1.35元的平均值),则豆腐价格为黄豆价格的41%。据此假定2000年北京市豆腐的价格为黄豆标准品(三等)价格的41%。(2)食物食部能量含量数据来自《常用食物能量表》、《蔬菜、水果类食物交换代量表》、《纯能量食物交换代量表》,其中面粉的食部能量含量取值为标准粉的相应取值,猪肉、牛肉、羊肉的取值为猪肉(瘦)、牛肉(瘦)、羊肉(瘦)的相应值,鸡蛋的取值为鸡蛋(红皮)的相应值,牛奶的取值为牛乳的相应值,豆腐的取值为北豆腐和南豆腐的平均值,色拉油的取值为纯能量食物的相应值,大白菜、西红柿、油菜取值采用相应区间的中间值。参见李凤林、张忠、李凤玉主编《食品营养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254页。数据来源:《中国物价年鉴2001-2002》,中国价格信息网。
最后,计算得到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每月30天计算,则2 200大卡水平下每月的食品支出为162元/人(5.39元/天 ×30天),再加上常用调味品及辅助食品(盐、酱油、醋、糖、大蒜、葱等)的支出15元/人,得到每月的食物线为177元/人(即每年2 124元/人)。假设城镇低收入户(5%)的恩格尔系数为60%,则根据恩格尔系数法计算非食物线,即每月1 416元/人。这样,2000年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为3 540元,即每月295元。
根据食物线和非食物线的调整方法,计算出北京市历年最低生活保障线(见表2)。比较理论标准与实际标准,发现在初始贫困线的差距并不大,理论标准仅比实际高15元/月,但是自此之后,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到2010年,两者的差距已达到85元/月,2011年,北京市大幅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两者的差距缩小到64元。
2.最低生活保障收入替代率
最低生活保障收入替代率是最低生活保障线与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它是衡量最低生活保障线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最低生活保障收入替代率越高,表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表2 北京市理论最低生活保障理论标准计算过程
那么,最低生活保障收入替代率处于一个什么区间是合理的?从各国的实际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目前,经合组织多采用中位收入的40%、50%、60%三个标准来衡量贫困,即收入替代率为40%、50%、60%。一般来说,福利国家的收入替代率较高,尤其是北欧国家其收入替代率往往超过社会平均收入的60%。美国的贫困线替代率在发达国家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目前保持在28%左右。考虑到中国的财政承受能力和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情况,建议将替代率控制在20%~40%之间,越贫困的地区替代率越高,越发达的地区替代率越低。
由比较表3的理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实际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可以看出,由于新方法与实际标准在计算时采用了不同的热量支出标准,造成两者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并不大(15元/月)。这说明,采用新方法计算得到的初始最低生活保障线较为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由于调整机制不同,自此之后,采用新方法计算得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实际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差距越拉越大。①现行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调整机制如下:城市低保标准=(城市居民基本食物支出标准÷适当的恩格尔系数)±调整数。其中,城市居民基本食物支出标准由市统计局根据国家营养学会公布的年度标准食物谱及摄入量,结合本市市场价格计算后得出。适当的恩格尔系数为城市低保家庭恩格尔系数与市统计局统计的“5%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平均值。调整数通过综合考虑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物价指数、社会保障相关标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平均工资、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后得出。

表3 北京市理论替代率与实际替代率的比较(收入替代率)
再看最低生活保障收入替代率的发展趋势。2000—2010年,食品价格指数的增长小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指数,因此,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下降很快。这一时期,采用新方法计算得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替代率从34.20%下降至21.71%,下降了12.49个百分点;实际最低生活保障线替代率从32.46%下降至17.71%,下降了14.76个百分点(见表3)。这说明,新方法能有效降低最低生活保障线替代率的下降速度。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采用新方法计算得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下降速度会进一步趋缓。综上所述,由于建立了与价格指数和收入增长指数挂钩的自动调整机制,理论计算得到的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增长速度要快于实际增长速度,但这一速度并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处于较为理想的状态。
3.最低生活保障消费替代率
最低生活保障消费替代率是最低生活保障线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比值,它是衡量最低生活保障线高低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最低生活保障消费替代率越高,反映最低生活保障对基本生活的保障能力越强;反之,表明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能力越弱。
从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年,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理论消费替代率为42%左右,实际替代率为40%左右,两者均处于较为合理的范围,而且两者差距甚小;但是由于调整措施的差别,自此之后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到2011年,理论替代率下降到31%左右,下降11个百分点,而实际替代率下降到27%左右,下降12个百分点。这说明,新方法具有较为稳定的增长机制,能较好地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表4 北京市理论替代率与实际替代率的比较(消费替代率)
为了进一步检验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合适性,应比较低收入户(20%)的消费与最低生活保障之间的关系。由于缺乏历年数据,在此只比较2005年的情况。2005年,北京市2 000户城市居民家庭调查数据显示,低收入户(20%)的平均每人年消费如下:(1)食品3 218.2元;(2)衣着598.4元;(3)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382.8元;(4)医疗保健757.9元;(5)交通和通信800.7元;(6)教育文化娱乐服务1270.7元;(7)居住611.7元;(8)杂项商品与服务223.1元。上述八项合计7 863.5元。因最低生活保障只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而且针对医疗、教育和居住,我国分别建立了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和住房救助制度,因此,只考虑食品、衣着、交通和通信、杂项商品与服务,上述四项内容共4 840.4元。2005年,北京市实际最低生活保障线为300元/月,即3 600元/年,用修正的新方法计算得到的理论标准为389元/月,即4 668元/年,即理论标准更接近于低收入的基本生活平均消费支出。
4.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替代率
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替代率是指最低生活保障线与最低工资的比值,它是判断最低生活保障线是否合理的依据。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替代率越高,对有劳动能力者的就业激励就越弱,从而出现所谓“福利病”;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替代率越低,对有劳动能力者的就业激励就越强,但是也可能导致保障不力的问题,从而产生所谓的“不利用”的问题。
一般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主要取决于社会平均工资。劳动者的最低报酬与该地区劳动力报酬的一般水平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客观的联系。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制定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生活性消费水平。不考虑其他因素,单从数量关系上看,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制定所参考的要素完全不同,但两者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因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最低生活保障、参加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低工资替代率,即家庭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与参加就业时所得收入的比例。最低工资替代率越高,表明就业推动力越低;反之,则表明就业推动力越高。考虑到我国最低生活保障线一直偏低,最低生活保障与最低工资的比例为40%~70%较为合理。
最低生活保障线与最低工资保持适当差距,目的在于降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吸引力,减少福利陷阱的发生。采用新方法计算得到的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实际最低工资的比值,最大值为72.47%,最小值为54.74%,平均值为65.6%;实际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实际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最大值为67.96%,最小值为44.79%,平均值为54.69%(见表5)。采用新方法计算得到的标准并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从两个标准的发展趋势看,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替代率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实际最低工资替代率在十二年间下降了24.86个百分点,理论最低工资替代率也下降了22.98个百分点。

表5 北京市理论替代率与实际替代率的比较(最低工资替代率)
5.贫困自由度
目前,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而且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由地方政府制定,资金也主要来源于当地财政,因此最低生活保障线有所差别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不管采用绝对贫困线计算方法还是相对贫困线计算方法,两者都包含了一个基本的“内核”,即维持一个正常人所需要支出的最低热量。这部分“内核”即为食物线,它是维持个人生存的前提条件,食物线之外的必需品为非食物线,它是个人摆脱饥饿、获得自由发展的衡量指标。自由的获得对于贫困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Amartya Sen)看来,发展就是扩展人的自由,对于贫困者来说,自由是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例如避免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的死亡等等,同时又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的自由[4]。发展的自由观强调对穷人能力的培养,意义在于提高穷人进行主动参与的能动性,从而提高他们摆脱贫困的机会。
食物线一般根据热量支出法确定。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估计了在静止状态,消化食物和支持各种活动水平的情况下,保持体重的食物能量需要。中国政府在农村实施反贫困战略时,也提出以2 100大卡/天·人作为贫困线计算的能量基础。一旦确定了最低热量支出,在一国之内则只存在饮食习惯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食物组合,这些食物组合又因为各地的价格变化而导致贫困线的不同。在一个信息对称、商品流通顺畅的统一市场中,各省市价格变化并不大,因此,各省市的食物线价格并不会因此而存在巨大差异。如果受助者得到的救助款中食物线部分用于购买食品,非食物线部分用于食品以外的支出(即用于满足最低生理需求之上的发展需要),那么最低生活保障线中非食物线与食物线的比值就可以反映贫困线标准对受助者所产生的效果,这一比值可以看做是受助者摆脱贫困、获得自由发展的程度,因而称之为贫困自由度。贫困自由度的值越大,受助者自由发展的能力越大,效果越佳;反之,贫困自由度的值越小,受助者自由发展的能力越弱,救助效果越不佳。
采用修正的新方法计算最低生活保障线,食物线只随价格变化而变化,非食物线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增长。2000—2010年,北京市人均收入增长明显快于价格指数增长,因而北京市非食物线的增长明显快于食物线的增长,也就是说,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受益者的贫困自由度增加。2005年,非食物线超过食物线,此后两者的距离越拉越大。2000年,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受益者的贫困自由度只有0.67,但到2011年,这一数值提高到1.40。2000—2010年,北京市理论计算得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和实际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自由度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理论自由度上升了0.69,而实际自由度只上升了0.34(见上图)。这表明,实际最低生活保障线中的非食物增长要低于理论计算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非食物部分。所以,采用新方法,受助者的自由发展度越来越大,社会救助的效果越来越好。
本文提出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新的计算方法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有机地结合起来,形象直观,方法比较简单,且具有较好的调整机制,可以应用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过对北京的实证研究表明,采用新方法计算得到的初始贫困线与北京市实际贫困线非常接近,因此随后计算得到的理论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实际最低生活保障线逐步拉开差距。对北京市理论标准与实际标准进行比较,发现采用新的计算方法得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在收入替代率、消费替代率、最低工资替代率和贫困自由度等四方面均优于现有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因此,建议采用新的方法计算最低生活保障线,逐步规范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管理。
[1] FISHER,GORDON M.Relative or Absolute—New Light on the Behavior of Poverty Lines Over Time[R].GSS/SSS Newsletter,Summer,1996:10-12.
[2] 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142.
[3] SEN,A.K.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J].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81):285-307.
[4]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