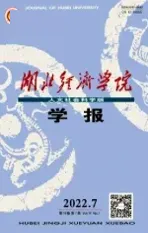宪政视域下村民自治权的权利属性探析
2012-08-15赵菊敏
赵菊敏
(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宪政视域下村民自治权的权利属性探析
赵菊敏
(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其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亟需回答的理论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点便是如何认识中国宪政体制下的村民自治权的权利属性。通过对宪政视野下中国村民自治权的权利属性研究,不仅能够从理论上回答农村自治建设在实践中遭遇的诸多诘难,而且还能进一步推动农村问题研究的深入,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对策,最终提出中国宪政建设的可能性进路。
村民自治权;宪法权利属性;自治权力;自治权利
一、村民自治权理论的再认识
中国实行的村民自治,在西方看来是农村直选,是中国从高度集权社会转变为民主法制社会的一种内外因素影响的制度变迁;也是亿万农民的价值追求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结果,而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村民自治权。基于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笔者认为村民自治权应具有特定的内涵:
(一)村民自治权是村民的一种自治权力
从国家与社会分权角度而言,村民自治是村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民主权利实现的统一。但要实现村民民主权利,离不开保障这一权利实现的力量。在村民自治中,自治权力的主体是村民。同时,这种权力不同于行政权力,它们在性质、内容和特征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行政权力强调权力的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的控制、干预和影响,有明显的阶级性、强制性、普遍约束性、国家主权性、有限性的特点。自治权力却注重于权力支配者,具有按照自己意愿和利益实现行为的自治能力或自主能力,也就是自己管理和决策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即村里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这种自治权力一方面表现为村民直接行使那些属于自治范围的权力,另一方面表现为村民通过对自己事务的自治,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因而是一种扩大了的村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国家、民主和自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马克思、恩格斯还根据社会发展和国家演进的客观规律,提出了防止国家权力蜕变的三条途径:“社会参与国家”、“社会制约国家”、“社会收回国家”。“社会参与国家”和“社会制约国家”就是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由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至于蜕变;“社会收回国家”就是国家的职能逐步归还社会,由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国家机器逐步消亡,由社会自治组织来取代。
(二)村民自治权是村民的一种自治权利
从公民基本权利角度而论,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它反映公民的法律地位和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村民既具有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又具有村民在自治中的自治权利,这是公民基本权利落实在村民自治中的具体内容,是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即由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具体化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自治权。“公民权利为公民通过民主制度参与国家管理、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权力的活动提供条件 同时 它又构成国家权力的边界,“是约束国家权力的一种重要力量”。村民的自治权利,就是农村村民对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自主决策的权利。这是由公民基本权利派生的农村村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
村民自治权利既是主体本身的行为,也是权利主体要求义务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村民既有权要求维护自身的权利,谋求自己的共同利益,也必须履行有关的义务。因此,当享有权利的绝大多数人要求少数或个别人作出相应的行为时,权利可以转化为权力,以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权利享受和行使过程中,权利又成为了一种权力。
(三)村民自治权是村民所特有的一种职权
这里所说的职权,是从村民这个特定身份出发所提出来的概念。村民自治权由法律赋予村民所有,是其他社会组织和其他公民不具有的,因而有着特定的性质、含义和内容。村民自治权,是村民的法律权利,并与此相对应规定法律义务,而自治权利和自治义务二者相互统一:自治权利离开自治义务,就失去自治意义;自治义务离开自治权利,自治形同虚设;自治行为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充分地享有和行使权利,能增强村民自觉履行自治义务的自觉性,自觉履行自治义务又为公民扩大民主权利创造条件;村民在享有自治权利的同时,负有遵守法定自治权利界限的义务。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共同反映并决定村民在自治中的政治与法律地位,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和履行自治义务的程度则共同反映村民自治能力和水平的程度。
二、村民自治权的宪法基本权利属性的求证
从一般权利到宪法基本权利的演进过程来看,“权利起初往往以一般权利的形态存在,甚至仅仅以主观权利的形态出现。当权利观念与权利类型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被认为尤其重要的那部分权利就必然诉求与其自身的重要性相适应的法规范形式予以确认和保障”——“即以一种赋予其最高法规范效力的宪法规范形式,对那些具有重要地位,并为人们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予以确认和表述,并加以保障和实施”。因此,并非每项法律权利的保障都可以或都必须提升至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的层次。理论上一般认为,一项公法权利要在“宪法上”获得依据至少应具备如下三项要件:(一)该权利在本质上已具备人权或基本权利的品质,即“该权利已具备普遍性而值得以宪法保障之;(二)该权利的实践契合宪政秩序的形式与实质。即“指合于宪法价值体系,该体系则由宪法价值决定、国家目的、宪法原则所建构而成”;(三)该权利在“宪法”上有依据,或可从相关条文中推衍出而具备宪法默示权利之特性。
若以上述四项要件为基准分析,首先,村民自治权的演进本身即是自治权的大众化、普遍化过程,没有任何国家否认其“系属每个人”之权利;其次,村民自治权保障是一个国家的宪政问题,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权宪政水平,村民自治的实践对于落实人民主权原则,达成民众政治参与,实现宪政秩序等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再次,村民自治权是行使其他基本权利的一项前提性、手段性权利;最后,就宪法权利理论而言,宪法所构筑的基本人权体系本身就不是封闭性的,而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其本身就具有透过权利推定、法解释等手段吸纳“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被认为尤其重要的那部分权利”的功能。
三、村民自治权的宪法基本权利属性之法理再解析
Robert Alexy认为一项权利之所以能成为宪法上的权利,有三方面的要素,即能够被大家理解的实际意义、政治正当性以及高于法律权利的位阶。[1]在笔者看来,基本权利的属性应该至少符合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是必须存在的。基本权利对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在社会生活而言必不可少,缺少了基本权利,则会对人的某项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比彻姆认为,基本权利是与派生权利相对的,他说,权利之所以是基本的,至少具有双重含义,其中之一的含义即在于某些特定的权利是基本的,因为他们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先决条件或必要条件。[2]第二,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基本权利不能被非基本权利所取代,非基本权利不具有基本权利的位阶与内涵;此基本权利也不能被彼基本权利所取代,其他基本权利无法满足该项基本权利的特有功能。第三,具有独立的权利价值。基本权利具有独立的权利价值,其他基本权利无法包容该项权利。比彻姆认为基本权利的含义首先在于,因为别的权利都是又他们派生,而他们自身则不再由更基本的权利所派生。[3]我们之所以在宪法意义上界定村民自治权,根本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权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要素。
(一)村民自治权的不可或缺性
中国乡村的村民自治实践已经将近二十年,这一草根民主运动对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农民民主意识的提升确实意义非同寻常,村民自治在中国的基层宪政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体现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自治的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而笔者认为“村民自治”真正的本质在于,其是处于弱势的村民个人和村民自治体保持公民权利与尊严、地方自治权免受国家权力侵害的一种宪政制度安排,是村民(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抗衡的宪政保护,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方是这一宪政实践的根本所系。
(二)村民自治权的独立权利价值
社会自治的本质是将权力从国家向社会转移,是自治的最高形式。[4]我国目前农村中出现的侵害村民权利的现象,原因则是对村范围的自治权的侵害。政府自治必始于地方,始于村民(公民)个体权利,因为几乎所有的需要由自治保障的权益均与地方有关,土地权益、自治组织设置、对于习俗和传统的维护等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均要求设置不受国家权利的随意侵害的地方体制,该地方体制的核心功能就是在面对国家强性权力时,能有力维护地方自治体组成的村民(公民)个人权利,即使这种对抗在力量对比上悬殊甚巨,但毕竟仍有一个合法的宪政机制使村民(公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有尊严、合法地斗争着,而非屈从于国家权力。虽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体,国家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这一理论设计在现实运作中难免出现中央与地方的冲突。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在立宪层次上考虑的首要问题是通过村民自治实践,赋予村民享有宪法意义上的自治权。就“村民自治”实践而言,没有制衡群体的产生,永远也不会产生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宪政。在现实中国农村,2/3人口在农村,分散且弱势,没有基本权利意义上的自治权,这个群体永远都将是马克思提过的“麻袋里的马铃薯”。在宪法文本中,把村民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制度放在一起规定,实际上也是认同了村民自治为地方自治的合宪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只有承认“村民自治”的基本权利性质,才能在此的引导下维护村民的自治权利,农村也才可以改变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受到城市工业盘剥的地位,从而在法律体系中,变模糊的“集体”为具体的“个人”,使权利概念与村民天然结合,继而取消笼统的非法学术语“集体”概念。
(三)村民自治权的高权利位阶
从学术概念上考察,“位阶”意为“依某种次序形成的阶梯”,权利位阶则指不同权利按照某种次序形成的阶梯。[5]可以说,在权利的体系中,权利位阶的存在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宪法权利的高位阶在于“higher legal norms”。[7]笔者理解,更高的立法标准主要基于权利的重要性。今天的宪政背景下,村民自治权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具体体现在:“主体自治”是人权理论的基石。
现代宪政是以人权理论为基础的,从逻辑上来看,只有主体自治才能保证主体人权产生的可能性。主体的自治权是人权的首要内容,是主体其他各种权利的基础。人权要求每一个个体的平等,这种平等是人格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平等。坚持这种平等要求,在制度上必须既要烤炉每一个个体的“意志性”的平等,也要保证每一个个体的“利益性”的平等。因此,保护人权要求主体自治,即每一个个体都享有平等的主权者身份。现代宪政理论是以保护人权为核心的理论,而人权理念的正当性又以自治为前提的。所以,现代宪政理论、人权理念能否得到逻辑上的确证,自治权的权利属性就是逻辑上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四、结语
村民自治权作为村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或者说中国村民自治最基本的内涵和概念,发现目前我国立法并没有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位,对村民自治权的合理性也未予以明确承认。这些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了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并未产生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运作模式。明确了村民自治权的宪法基本权利属性并在进一步总结村民自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依法治国的基本法律要求,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农村现阶段基本情况的村民自治的模式,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成为我国自治制度中的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重要的自治形式。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社会制度演进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8-BKS004)
[1][7]Robert 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 Rights[M].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xix.
[2][3][美]汤姆·L.比彻姆.哲学的伦理学[M].雷克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90.
[4]王禹.我国村民自治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1.
[5]张平华.权利位阶论——关于权利冲突化解机制的初步探讨[J].法律科学,2007,(6).
[6]林来梵,张卓明.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