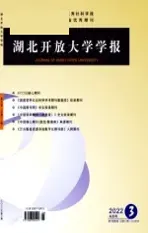无处安放的爱情与婚姻
——读《花儿与少年》
2012-08-15任文汇
任文汇
(苏州职业大学,江苏 苏州 215104)
无处安放的爱情与婚姻
——读《花儿与少年》
任文汇
(苏州职业大学,江苏 苏州 215104)
花儿与少年本该拥有公主与王子般的幸福,可生活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没能在自己的母体文化中得到滋养,从而获得更新、生长。选择寄居以后,因为“错位归属”,他们关于爱情、婚姻的一切美好设想再一次凋谢成一地碎片。小说对不同语境下人性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花儿与少年;爱情;婚姻;无处安放
作为活跃在北美华文文坛上的一个“了不得的异数”,[1]严歌苓凭借足以看穿人心的视野,足以探底人性的嗅觉,受到众多读者的追捧以及学者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她的异域书写闪烁着“新移民文学”独有的精神特质,使她成为新移民作家中一面耀眼的旗帜。
一
长篇新作《花儿与少年》延续了她一贯的新移民题材,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貌似平静温和实则忧伤凄凉的故事。如题所示,花儿一样美丽的少女,英俊潇洒的少年郎,一对惹人怜爱的小儿女晚江和洪敏在大自然的良辰美景中相会。眉目传情的喜悦,朝思暮想的苦楚,望眼欲穿的期盼,十指相扣的依偎,一吻定情的承诺,肌肤相亲的感动,从少年到青年,从总角之交到终成眷属。许多时候,他们将舞台当作人生的主体,将舞台上的短暂梦幻当作人生的真谛。这是两具几近完美的躯体,本该拥有王子公主般的爱情,但生活毕竟不是舞台。当花儿与少年走下舞台,迎接他们的是苦涩悲凉的现实人生。为了爱情,晚江毅然跟洪敏裸婚,蜗居在他们的单身宿舍。在筒子楼的五层拉上花哨的窗帘,他们的婚姻就在窗帘背后展开。如果不是因为最后一次分房未果,不是因为剧团效益滑坡,女的被派帮厨男的被分流去打杂,那他们的爱情也许就跟大多数人一样,在上下楼梯打洗澡水的殷勤中,在柴米油盐的围绕中,在世俗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转化成了亲情,但事实是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仅“最不勤奋的主角”、“最卖力的龙套”无从谈起,而且成了这个剧团最后要不到房子的一对夫妻。生活可以击垮任何美妙的事物。在未来无望的打击下,曾经的少年放弃了,因为他清楚,这十年所有的艰辛痛苦、清贫简陋是靠十年前恋爱的感觉维系的,可下一个十年靠什么呢?生活没有给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提供足够的空间。那个用被单隔出的洞房、那个剧团的厨房和衣帽间如何承载得了他们沉重的爱情?或许放手才是最深刻的爱恋。
小说的主人公面临着和时下国内年轻人相似的遭遇:“裸婚”、“蜗居”,但严歌苓写这些不是为了追逐文学的时尚,她不会为哗众取宠而赶时髦,相反作者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的侧目而视的态度,通过对现实的观照向历史和人性深处探底,看身处边缘的小人物如何在命运的般百般戏弄下活得卑贱抑或强大。正如作者所说,“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岁月都是在大的社回动荡中度过,一个决定和运动就会给生活带来云泥之别的深重改变。”[2]
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作者没有明示,但一切社会符号有都带有鲜明的社会转型期的烙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人们原有的社会理念、价值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对金钱物质的崇拜几近宗教般的狂热,而精神文化家园则呈现出一派“荒原”景象,高雅艺术遭遇寒冬。晚江和洪敏所在的芭蕾舞团在激烈的经济文化结构变动中已如汪洋中的小舟。作为个人,他们也无法继续坐享体制的甘美,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随之而来的还有精神上的无所归属感、依托感,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和茫然。曾几何时,这些文化人的精英意识及自我内在的优越感已化为往昔云烟,飘荡不知所终。在这样一个消解价值、离析中心的时代,个人又能拿什么去拯救自己的爱情?面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他们选择了无奈的逃遁。
当然导致他们婚姻解体的原因还有世俗的严苛、人际间的相互围猎倾轧以及他们自身的不安分。这对小夫妻是那样的不谙世事、浑玩未开,婚后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寻找恋爱时的激情,细纱綢做成的美丽绝伦的窗帘的放荡,北海公园“偷情野合”的刺激……在那个墨守成规的年代,恋爱后结婚,结婚后不再恋爱已成固有观念,所有出格的浪漫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低俗、下贱、无耻。当发自内心的观念只剩下自己认可的一份胆量和超群,所面对的敌人却是强大的世俗时,那么再强大的内心、再坚贞的爱情也会变得不堪一击。他们的不安分还包括公然违反“基本国策”,在儿子九华之后又生了女儿仁仁,这无异于把自己逼上绝路。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几千万个家庭,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中,因为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优势而沦为弱势的并不鲜见,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归顺和依从,但不安分的他俩偏偏不甘心沉沦,以至于他不惜牺牲婚姻、不惜扼杀两人融于岁月的爱情和亲情也要成就晚江和两个孩子的幸福。
二
花儿与少年的爱情终于没能在自己的母体文化中得到滋养,从而获得更新、生长。如果说这是晚江和洪敏遭遇的第一重人生尴尬,那么在大洋彼岸他们仍然没能获得梦想中的自由和空间。
晚江依然年轻,并且有着舞蹈演员特有的可以摧垮一切附加条件的美,加之她将舞台上未能充分展示的才情应用在菜肴创新上,无师自通地将烹饪术升华成了一门艺术,很快赢得了老律师的青睐,如愿以偿地入籍美国。随后九华来了,继而洪敏来了。昔日的花儿与少年已经相隔十年的岁月,但这个女人似乎从没有从过去的生活延续中走开。时空转换,人物非昨,可她就像出去郊游一样,或者说就像一件典当出去的物品,她知道自己终究要被赎回的。她的情感没有任何变化,那么自然的延续着过去的婚姻,她的心自然地属于过去的历史,她的灵魂仍留在过往,现在不过是外形、表象。两人的心有灵犀在诸多细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和洪敏每周通话,他们说话的方式、彼此的情感心理一如既往,而且尽管没有明言,却怀着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坚韧地等待,等瀚夫瑞老去之后有朝一日破镜重圆。凭着他们的年龄、意志,他们有足够的条件将等待进行到底。他们规划着一家四口的未来,晚江拿出她千辛万苦挣来的那点可怜的积蓄给洪敏,企图构筑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甚至有了关于新家布置的具体构想,还把家里的废旧物品进行转移。晚江深爱着洪敏和他们的儿女,像母兽一样勤于操劳和张罗,千方百计地想让这破碎的家庭重圆。就在她以为团聚的幸福伸手可及的时候,传来了洪敏投资被骗的噩耗。原来梦想一夜暴富的洪敏根本没有买房,他拿着晚江的钱以及从俱乐部那帮老女人那里借来的钱做了投资,血本无归后丢盔弃甲逃回北京。
其实投资被骗这类事发生在洪敏身上绝非偶然,因为严歌苓笔下众多女性那种纯真的生活姿态在他身上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有点简单,有点迟钝,甚至有点缺心眼。这是一种野性的原生态的美,具备这种禀赋的人更适合随性地生活,至于投资挣钱这类需要智慧乃至精明的事已经超出了他能够从容应对的范畴。
如此,一夜之间,晚江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所有关于房子、家庭的梦想通通破灭。这是小说设计的阻碍他们破镜重圆的现实性因素,但真正注定他们这种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应该是彼此心灵的迁移。晚江最终终于明白,她心目中的亲人丈夫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人了,他们在各自的十九岁和十七岁相遇、相爱,并如胶似漆,用十年的时间体味艰辛快乐,不离不弃,因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原因分裂,试图用第二个十年来寻找物质上的富足,梦想着可以再续之前的美好,可是在他们四十二岁和四十岁时再回首,发现已经回不去了,在一次次的经历中,他们的心理已经错位,为文化和生活切割着,蹂躏着。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对我们这种大龄留学生和生命成熟后出国的人,‘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即使曾是‘花儿与少年’那样天造地设的爱人,‘错位归属’也使他们不可能旧梦重温。情在义也在,回到原先位置的却已是陌生人。彼此心灵的迁移竟比形骸的迁移要远得多。”[3]作为瀚夫瑞的妻子,晚江既厌倦这种奴隶般的生活,同时又对这种生活不无留恋。十年间,她已错过了本国文化一大段的发展和演变,不自觉地为美国文化深深地感染和间离,即使回到母体文化中、回到洪敏身边,也是形归而神莫属了,和洪敏之间存在的可能性早已被现实性的追求所吞没。
三
晚江和洪敏的儿子九华,因为父母的选择,他承担了分离的一切恶果。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去留的问题上,不可能有自己的意愿。在这个中产阶级家庭里,他承受不了繁缛的餐桌礼仪和这礼仪所代表的阶层,他的笨拙和固执把自己排除在瀚夫瑞的王国之外。九华第一次与翰夫瑞会面时便由于语言障碍陷入了失语的状态,这种失语状态在九华日后的生活中成为一种常态。“半年后人们开始无视九华,他成了这房子里很好使唤的一个隐形小工。他做所有的粗话,马桶坏了,下水道不通,不必专门雇人修理。没有人再过问他在学校如何度日,连晚江都不知道他早早到学校,其实就在课堂里又聋又哑又瞎地坐上六七个小时”[4],甚至在老师家访后九华采用了断指自残的方式来表示对自己的捍卫和坚守。血淋淋的年轻失败者从此结束豪华的寄居,开始自谋生路。这个并不聪慧的男孩宁可一辈子开卡车送盒饭,也不服从母亲和继父为其安排的成长道路,他用这种自我放逐的决绝方式,喧喻了对西方文明的拒绝。这种拒绝既是弱势文化的抗争与自守,也是对他父母所作所为的一种无言反抗,极具悲壮色彩和讽刺意义。
如果说九华对西方文化所持的是一种彻底拒绝的态度,那么仁仁所持的是全盘认可的姿态。在美国的十年,仁仁已经长成一个沾着炼乳的草莓一样鲜嫩多汁的少女,尤其是在瀚夫瑞的调教之下,谈吐高雅精彩,反应机敏,礼仪完美高贵,她已经成了一个完全西化的女孩,仁仁也乐于接受这种西化,并且表现出对中国人身份的背弃和鄙夷,这主要表现为对父兄的疏离和厌弃。除了发肤还是龙的传人,其他的一切,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式,从生活习性到礼仪举止,她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少女。更可怕的是对性的懵懂认识和那个开放的环境正在把她一步步往深渊里推进,如果没有她的母亲用性和色来交换,她怕已经成了一只迷途的羔羊。面对这样一个孩子,真不知道晚江和洪敏是该感到欣喜呢还是挫败。
曾经的花儿与少年已悄然凋谢,一个黯然归去,一个寄人篱下,尴尬地存在于边缘。如今的花儿与少年,一个异化得令人怀疑血缘的真实,一个挣扎在异国他乡的的底层。
一次伤筋动骨的迁徙竟以如此黯淡的方式收场。花儿与少年在生存困境下的选择并没有使他们获得拯救,这个自由、开放、富有的国度也并非他们安居的乐土,他们关于爱情、婚姻的一切美好设想在这里再一次凋谢成一地碎片。
生命一旦被抛入尘世,偶然和必然便构成了命运身不由己的和弦。严歌苓用阅尽沧桑的心灵,不断品味感悟冷暖交织、灵魂漂泊的生命真味,对不同语境下人性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剖析。
[1] 麦琪.女作家对女作家[A].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C].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2] 傅褘男.严歌苓:在书写中走进历史[J].中华儿女,2012,(1).
[3][4] 严歌苓.花儿与少年[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Inseparable Love and Marriage——a Reading of Flowers and Juveniles
REN Wen-hui
Flowers and juveniles should have been happy like the prince and princess, but life didn’t give them enough space.Their love and marriage did not get nutrition in their own culture, thus no updating and growth is derived.After settling down, because of “dislocated belonging”, their conceptions about love and marriage faded into pieces.The novel makes a profound exploration of the double troubles faced by humanities materially and spiritually in different contexts.
Flowers and Juveniles; love; marriage; inseparable
I207.425
A
1008-7427(2012)10-0067-02
2012-07-25
作者系苏州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科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