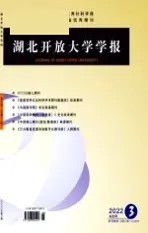《小团圆》对“伟大传统”的解构
2012-08-15王昕
王 昕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小团圆》对“伟大传统”的解构
王 昕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小团圆》的出版问世,掀起了“张爱玲热”的又一个高潮。《小团圆》蕴含着对于“伟大传统”的解构思想。这种解构主要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倾城恋曲”对“维多利亚主义道德风尚”的反叛;第二个方面是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第三个方面则是群体性反抗的解构行为。这些都为解构“传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阅读视角,同时具有深刻的意义。
小团圆;传统;解构
1976年,邝文美曾在回复张爱玲的信中谈到《小团圆》一书,她预言:这本小说将在万众瞩目的情形下隆重登场。三十三年后,2009年,张爱玲离开人世十四年后,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终于盛装出场,虽然晚了三十三年才登场,但确实是万众瞩目,轰动了整个华语文坛,在港台、大陆先后掀起了热潮。掀起热潮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究其深层内涵,小团圆对于“伟大传统”的解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利维斯在他的《伟大的传统》中曾经说到:传统是由一系列伟大的作家共同组成的。伟大的传统是客观存在的,需要理论家描述出来确认它。奠定并继承了伟大传统的所谓小说大家是指那些可以与大诗人相比相列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他们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意义,在艺术技巧上有独创性,不是为形式而形式,而是以道德目标为旨归的。在伟大传统中的作家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量。这就是《伟大的传统》精髓之所在,在利维斯看来,作家能否纳入传统就要看其是否接受了此前伟大作家的精髓,是否以自己所传承的伟大的传统作为启迪和影响。按照这一观点,利维斯归纳出了所谓的英国小说大家即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和D·H·劳伦斯。利维斯认为他们不仅是形式、手法和技巧上的创造性天才,更对道德关系有着严肃的兴味关怀。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张爱玲算不上伟大的作家,她的遗作《小团圆》也无法称为伟大的作品。《小团圆》并不是对传统的继承,相反是对于“伟大传统”的解构,但是此种解构之中承载了更深一个层次上的意义,即一种人文主体性的呈现。人文主体性所表达的不是人的自然生存需求,也不是基于自然欲求之上的任何具体特定目的,而是人超越动物界,实现人性的升华的需要,同样具有无限性特征。具体到《小团圆》的文本,其意义就是女性具有与男性平等的欲望诉求权利,其对于“伟大传统”的解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深入分析。
一、对“维多利亚”的反叛——“倾城”恋曲
《小团圆》中的盛九莉在维多利亚学院读书。维多利亚,一语双关,既是学院的名字,同时也暗示了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风尚传统。道德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思想的核心重于一种严肃的价值观,人人标榜道德的重要性。这种道德风尚传统在《小团圆》中不是启迪,也不是积极的影响,相反,它是对于女性的压抑。回溯“维多利亚主义道德风尚”,不难发现,在光鲜的表象下其实是藏污纳垢,一片混乱,这已经与自由的“维多利亚主义”背道而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当权时代,男人却认为女人是地下的,并且要求女人接受这样的观点,上层女人就是装饰品,下层女人就是劳动工具,这明显是对于人性、人本主义的违背。
这样的道德传统张爱玲是不可能接受的,在《小团圆》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小说中的盛九莉明明知道对方是有妇之夫,是万人唾弃的汉奸,年龄比自己大得多,还仍然毅然决然地去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超越了身份、阶级地位、年龄,为了爱而爱,以爱为核心。这种爱情主义超越了道德的底线,为了爱,可以不顾别人死活。为了爱,竟然希望战争继续。所以在小说里,九莉听到日军轰炸香港的消息,忍不住告诉好友比比:我非常快乐!若干年后,与邵之雍劫后重逢,听他说起二战快要结束的消息,也说希望它永远打下去。 这无疑也是张爱玲希望与胡兰成厮守在一起的心声。
可以这样说,支配张爱玲人生以及写作的不是清醒的道德理智,而是一种强大的女性的感性力量;她的最高旨归不是道德,而是她所向往的爱情主义。在她的《倾城之恋》中也有同样的表达,整座香江都城因战火毁了,才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这种具有“倾城”力量的爱情与传统意义上的“伟大”已相去甚远。从表面上看来,盛九莉只是想与邵之雍朝夕相对,独占邵之雍。但深究其中内蕴,《小团圆》呈现出的则是一种坚贞的爱情主义,这种爱情容不得一点瑕疵。只有两个人彼此坚贞不渝并永远厮守才是这种爱情主义的完满结局。从这一角度来看,深究九莉抑或是张爱玲为何没有因自己希望战火延续而感到罪恶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因为她或者是她们并不是惟恐天下不乱,而是在深陷无力摆脱的人际关系或环境中时,只要有变故发生,无论好坏,总是兴奋。 因为这变故是一种解脱,能让人在沼泽里拔出脚来。这可以视为一种“本真的回归”,是一种对“自我”的深入探询,人对“自我”的观照通常是以理想和欲望的形式来呈现的,一旦人的主体发展受到外界束缚,理想和欲望与社会现实相抵触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不稳定的心理,对“自我”、对社会的思考也会陷入到一种自我无法控制的状态。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就展现了人物内心真实的心理和本真的自我,此时的道德感已经被悬置,而“维多利亚道德主义”也已经无法肆意地压抑女性,“倾城”恋曲成功地完成了对“维多利亚”的反叛。
二、女性意识视角的解读
女性意识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所谓传统女性意识,指的是女性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之中自觉地将善良、淳朴、坚韧、宽容视为一种美德,并以此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它的形成与人类自身的生产有关。女性在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无非是抚养子女,打理家务。她们在历史过程中无法实现自我,而这种心理压抑已深深积淀于女性的精神气质和深层心理中,从而认为把自己奉献于男性是女性的天职;对于现代女性意识,乐黛云教授曾经说过:“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机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年;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小团圆》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女性意识则应该从第一个层面去解读。
曾经见到这样一种评价,即《小团圆》放到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就会相形见绌。此种说法的依据就是《小团圆》中的爱情仅仅是让人动容,而不是让人震撼;这种爱情局限在自我的小世界中,而没有上升到一个宏观的视角,缺乏一种社会的关怀。不难看出,这种评价是从传统道德的视角出发的,也就是利维斯所提到的: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道德的,只有服务于道德才有意义,才能帮人们认识发展的潜能。此种评价的本身就是狭隘的。回顾文本中的描述,在“莉雍恋”的故事里,九莉专情,之雍滥情。在九莉之前,之雍已经有三位妻子,第一位死了,后面两位离了。九莉之后,又出现了两个女子,包括一直爱慕之雍的侄女在内,在此种格局之下,邵之雍还告诫九莉:“太大胆了一般男人会害怕的”,直白地表达出其在传统文化中作为权威者的声音,然而九莉没有像一般的传统女子一样逆来顺受,而是用冷漠、不动声色直至悄然放弃给予邵之雍“二美三美的团圆梦”以致命一击。由此可见,《小团圆》站在女性写作立场上对男人的见异思迁给予了无情的暴露。九莉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而是愤起抗争,表现出可贵的自主意识,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可以说,在九莉身上,张爱玲发现了一条女性缓慢改变其身心状态和社会地位的自立自强之路。张爱玲正是借九莉的形象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女性在家庭、爱情、婚姻上开放的空间。
九莉这个人物蕴含了张爱玲现代女性意识的深刻觉醒,她希望建构一个浪漫唯美的情爱世界,充满着自由、平等和人性的光芒,并试图以此来对抗世俗传统的侵袭。她并没有做无私、宽容的贤妻,容忍其他的女性与她共享神圣的爱情,而是成为了邵之雍为代表的男人群体集体惧怕的女性——勇于抛弃无爱的婚姻。九莉不但洞见出邵之雍的懦弱,更以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将他彻底清除出自己的人生,女性自身的成长促成了男性霸权的没落以及男性神话的彻底完结。张爱玲通过《小团圆》向女性发出宣言,即要主动地去学习并掌握自我生存的能力,以独立的女性意识找寻爱情和作为女人的价值,这就使得女性在面对婚姻的不幸时有了更为明智的选择。这样的宣言、这样的心声表达,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它在自我主体意识以及人性的高度上去关照女性是更具深意的,同时也是更具震撼力的。
三、不是一个人的叛逆
《小团圆》不仅仅是九莉一个人的爱情故事,母女两代(也包括三姑楚娣)构成了一个叛逆的群体。她们的叛逆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情爱文化的解构上,这一解构有以下两个重要的标志:
(一)打胎
在传统观念之中,怀孕生子是女性的重要职责,是天经地义的。打胎则被视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是被羞于提及的。而在《小团圆》中不仅有九莉打胎的触目惊心的文字描写,同时也有姑姑所说的“你母亲‘不知道打过多少胎’”的间接描述。母亲的打胎虽然没有详细的描述,但是在阅读了九莉的惊恐时刻之后,读者也可以联想到蕊秋打胎时所经受的痛苦。母女二人构成了相互的写照,同时也是命运的轮回。她们的叛逆给她们带来了苦果,但是母女二人还是走上了相同的反叛之路,她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冲破命运的周而复始,获得自己所向往的爱情。
对于“打胎”,张爱玲依然承袭着自己的去道德化描写,她并没有视其为罪恶的令人羞耻的行为,相反,她认为这对于九莉来说是一种解脱。深究根源,就是张爱玲有着不同寻常的思考角度,她是从母亲争取自由的角度去评价这种行为的,所以让九莉做出了令人无奈的选择。直至小说结尾,九莉还一再重复不想要孩子,这多少可以视为她对于传统情爱观念的一种挑战。
(二)自主的性欲追求
在传统情爱文化之中,女性在性欲追求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多表现出一种他者或自我的压抑,张爱玲早期作品中就存在着大量压抑型的女性。到了《小团圆》,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女性拥有了自主的性欲欲望。九莉与邵之雍新婚前后的性爱描写自不用多说,而在母亲和姑姑身上,这种性欲的追求也是不难觅得踪影的。楚娣曾与九莉说过:“你母亲‘这方面的事多了’”。事实也确实如此,蕊秋离婚前后,曾和几个中国或者外国男人有过亲密的暧昧关系,而且她和这几个男人中的大多数都发生过肉体关系。就连楚娣自己也同样与几个男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绪哥哥、夏赫特都是其中的代表。
张爱玲对“传统性欲追求”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作为观照、解剖人性的重要视角之一,对性爱的态度是展现两性复杂关系必不可少的窗口。在男权话语充斥的传统社会之中,女性是被压迫的对象。男性有意地制造着一种观念和特权,为了剥夺女性的性自主权利,无情地贬低和压抑女性的性表达。“‘性的自由’,从根本上讲,也可能适用于女性,甚至还可能危及双重的标准,打破曾巧妙地被用来对女性进行控制的‘羞耻感’。”《小团圆》中的女人们颠覆了传统性爱观对女性的文化歧视,她们不再背负传统男女性爱关系中应该处于被动的精神压力,而是在一定的心理参与本能的驱使下,主动寻觅快乐。她们冲出了“牢笼”,可由于缺乏先验的文化护卫,整个道路是坎坷的、没有目标的。但是不管结局如何,她们都勇敢地迈出了自主争取幸福的步伐。
整个大家庭的叛逆,特别是母女两代打胎以及自主性欲追求的书写鲜明地体现出一种群体性的解构行为。此等为“传统”所不齿的行为就这样毫无隐晦地被张爱玲书写于笔端,传看于世人。
四、结语
《小团圆》彻底地解构了“伟大的传统”。纵观“倾城恋曲”对“维多利亚”的反叛、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不是一个人的叛逆,这三方面无一不是对于这种解构的有力支撑。这一解构不仅提供了另一种阅读视角,同时具有着深刻的意义。
[1] 张爱玲. 小团圆[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
[2] 利维斯. 伟大的传统[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
[3] 段文星. 传统女性意识与现代女性意识的冲突[J].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1.
[4] 乐黛云. 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J]. 文学自由谈,1991,3.
[5] 凯特·米利特. 性的政治[M]. 钟良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 马建高. “传奇”未满——简评张爱玲长篇小说《小团圆》[J].名作欣赏,2010,3.
I246
A
1008-7427(2012)06-0063-02
2012-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