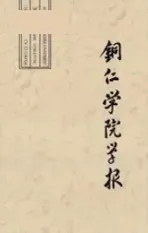略论阮籍嵇康玄学思想之异同
2012-08-15李峰
李 峰
(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略论阮籍嵇康玄学思想之异同
李 峰
(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阮籍、嵇康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存在着相似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但也同中有异。本文对阮籍、嵇康玄学思想形成的过程、玄学思想的异同作了论述,指出他们的玄学思想在形成过程中都伴随着儒道结合,二者玄学思想的异同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天人合一”、“养生”、“音乐”的诠释及理想人格的塑造几个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二人对时政和文学的取向上。
阮籍; 嵇康; 玄学思想; 比较
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继承了王弼、何晏的“贵无论”玄学思想,旨在调和自然和名教的矛盾。然当自然和名教的矛盾不可调和时,他们便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然论”①玄学,虽然其自然论玄学缺乏一套精密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它更倾向于庄子,表现了玄学的浪漫。阮籍、嵇康借文章和行为表现玄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始终贯穿着儒道结合的思想,二人都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试图融合儒道。考察阮籍的思想演变过程,我们便可发现其有明显的儒道结合、由儒入道的演变过程。阮籍家世儒学,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胸怀济世之志,“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1]206。少年阮籍,意气风发,立志要做像颜回、闵子骞那样的圣贤。随后《乐论》“礼乐并举”,论证礼乐内外、刑教一体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已提到“道德”、“自然”等概念。《通易论》“以道释儒”,其云:“大人发挥重光,继明照于四方,万物仰生,合德天地,不为而成”,“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贼之原”。“不为”与“寂寞”显然来自道家的“无为”之说。中期,阮籍目睹了曹爽集团的腐败、司马氏集团的杀戮,于是他的思想体现出儒退庄进。在《通老论》中,阮籍把《周易》中的“太极”、《春秋》中的“元”和《老子》中的“道”等同为一个概念。其所推崇的“圣人”能够“达自然之分,法自然而化”,统治的理想状态是“群臣垂拱”、“万物自化”,圣人的治世追求以无为无不为的道家思想作为原则,可以说,阮籍沟通了儒道。高平陵政变后,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已不可调和,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使阮籍由儒入道,《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便是反映这一时期其思想转变的作品。
嵇康也经历了儒道结合,由儒入道的过程,只是他的思想演变痕迹较之阮籍不是很明显。嵇康也是“家世儒学”,自小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虽酷爱道家哲学,但也未忘记对现实的关注,隐居山阳,却关心时事。他在《太师箴》中写到:“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对封建腐败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但“故居帝王者,无曰我尊,慢尔德音;无曰我强,肆于骄淫;弃彼狞幸,纳此逆颜”,又是其对当权者的劝诫,反映了他儒家济时用世平治天下的观念,只是这种观念已渗入了道家的自然无为。其《声无哀乐论》主张以“无声之乐”熏陶人民,实际上也是综合儒道,达到合乎自然的理想名教,但这种理想名教需要通过道家的“无为而治”才能达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而治。”随后面对名教的沦丧,司马氏篡逆的丑恶政治现实,以老庄思想为依托,嵇康最终走上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道路。
二、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异同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同异
天即天道,人即人道,天道与人道,可转化为自然与人类社会,可转化为自然与名教。阮籍和嵇康都试图调整自然和名教的关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但二人对“天”、“人”的理解则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阮籍认为‘天’或‘自然界’是一个有特定差别结构的、动态、和谐的整体系统,‘人’或‘人类社会’作为‘天’或自然界的产物,也应该有其相类似的结构特征。”[2]118人类应该效法自然界的秩序而建立人类社会的秩序,正如其《通易论》所提到的“天地之道”、“万物之情”,实为宇宙之秩序,圣人应依据宇宙之秩序,应时当务地采取政治策略,以达到“富贵侔天地,功名充六合”的目标。事实上,阮籍所言的“天”或“自然”是合乎名教的,或者说它带有一种政治策略和政治伦理色彩。阮籍的后期玄学吸收了庄子的齐物逍遥思想,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有了新的内涵,这时的“天”与“人”已经不是差别和对立的统一,而是无差别的原始混沌,所谓“混一不分,同为一体”。[1]133
嵇康对于天人的理解则和阮籍不同。在嵇康看来,“天”或“自然”很少具有政治色彩,它更多的是指人的自然情性。实际上嵇康也吸收了庄子的“齐物”思想,他在《释私论》中论述道:“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他提出的“无措乎是非”即“齐是非”的思想,就是要摒弃是非的差别达到无是无非,心不为是非所累,以回归到人的自然情性;“审贵贱而通物情”即为“齐万物”、“齐物我”的思想,就是要泯灭万物之间的差别,贵贱一体,智巧不用,以回归到人原始质朴的自然情性。可见嵇康的“天人合一”就是人的自然情性的回归。
(二)养生观念的同异
嵇康在《养生论》和《难养生论》中提出,养生分为养形和养神。养形重在服食;养神重在修养精神,关键在于恬淡清静,不为外物所累。他在《养生论》中强调:“善养生者则不然矣。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由此可见,嵇康强调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提倡对欲望的节制,使欲望和理智达到和谐。在此基础上,嵇康还提出要以人的自然之性节制欲望,自然之性即人的先天本能,节制欲望要顺应人的自然之性,不能强迫,而是自觉自愿达到欲望与理智的平衡。事实上嵇康并不否认欲望的合理存在,他所要求节制的只是扰乱心神安宁的种种嗜欲。
阮籍也不否认欲望的存在,也强调节制欲望,但这种节制多是以礼教来约束人的自然之性,如《乐论》以“礼、乐、刑、教”去节制人的自然之性,“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值得注意的是《乐论》还提到“乐者,使人精神平和、哀气不入。”音乐可以使人精神平和,有助于养生。事实上,阮籍狂放不羁,他并没有节制自己的欲望,反而是一再放纵,这体现出他理论和实际的矛盾,这也是其更深层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种放纵只是这一矛盾发展到极致的扭曲心理反映。而嵇康与阮籍相比,则在现实中实践着自己的理论主张。
(三)“礼乐并举”与“声无哀乐”
阮籍的《乐论》引入自然的观念解释音乐,但其自然并没有摆脱儒家名教规定的范围,确切地说,其《乐论》不出《礼记•乐记》的传统思想,并没有突破传统论乐模式。他在《乐论》中写到:“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在这里,阮籍礼乐并举,强调的是礼乐的教化功能。由此可见,其《乐论》反映的自然观念只是掺杂了道家思想的儒家观念。又如“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是说乐本之于自然。他接着论述到“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即音声的秩序演示着“天地之体”、“万物之性”,音乐指向的是天地万物,音乐的秩序指向人世之法则。“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音声的自然又在演示着人伦的自然,“万物之性”也即人伦的伦理之性。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提出声音是客观的“物之自然”,它只有“善恶”,好听和不好听的区别,而“无系于人情”,声音是客观的诱导物,它作为一种媒介诱发了人悲哀或快乐的情感,但它本身并不同于这些情感,或者说声音来源于自然,不含世俗的情感。他说:“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其度哉!”随后又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心之与声,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睽心者不借于声音也。”心与声,一个是审美主体,一个是审美客体,本身存在着不同。总之,嵇康通过《声无哀乐论》告诉我们宇宙自然是独立于我们的客观存在的,这个自然或许包括人世社会的秩序,但它不等于这种秩序,它是一种更高的存在范畴。
(四)“大人先生”与“宏达先生”
“大人先生”和“宏达先生”分别是阮籍和嵇康所向往的理想人格。大人先生“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以应变为和,天地为家;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1]161大人先生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这种超越是对于自我、社会和自然界最根本的超越,是对于宇宙的整体超越。这种超越是通过庄子“齐物”的思想而获得的。宏达先生“怀玉被褐”,忠信直道而行,同时又“泊然纯素”,不识品物。所以“宏达先生”身上既有儒家的忠信,又有老子的“无为”(泊然)、庄子的“齐物”(不识品物之细故),他是儒道的结合体。二者相比,大人先生显然是一副道家形象,阮籍、嵇康虽都有着深厚的儒家修养,但阮籍重儒,而嵇康则重老庄,由此看来,阮籍的理想人格更应该是儒道兼综的“宏达先生”,而嵇康则更应为道家形象的“大人先生”,可事实却恰好相反,这就体现出他们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矛盾。这种矛盾源于现实和环境的压抑下所产生的畸形人格。这种矛盾直接导致阮籍、嵇康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泥潭不能自拔。阮籍“礼岂为我辈设耶”,以“大人先生”讥讽虚伪的礼法之士,同时又“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非汤武而薄周孔”,同时又在《卜疑集》里反复追问自己,描述这种人格的矛盾。
三、阮籍、嵇康玄学思想在二人对时政和文学取向上的异同
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对他们个人的政治道路和文学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政事方面:阮籍主张“安时以处顺”[3]114,走向庄子顺世游世的道路;嵇康则走上了隐逸避世,“平易恬淡”[3]426的人生道路。文学方面:他们都转向老庄哲学,都注重表现本体生命、内在心灵,形成了高浑与清脱的独特文学风貌。
(一)阮籍、嵇康玄学思想下的政事
政治上,嵇、阮都游离于司马氏和曹爽两派之间,与其说他们是忠于曹魏皇室,不如说是忠于封建正统思想。事实上,他们本身并不排斥名教,而且还试图调整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但当异化的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二人便走向“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道路,阮籍甚至还提出了“无君论”。当然,批判现实的政治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理想的政治。
1.阮籍、嵇康的政治理想
阮籍、嵇康都向往上古社会,君臣秩序井然,民风淳朴。在《通老论》中,阮籍要求君王“达自然之分,法自然而化”,以达到“群臣垂拱”、“万物自化”的理想统治状态。嵇康则认为“惟上古尧舜。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4]40在嵇康看来,君王应效法上古尧舜,以天下为公,百姓才能淳朴安乐。这些都反应了阮籍、嵇康综合儒道,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的思想。可当在现实中看不到理想,矛盾已变得不可调和时,阮籍便提出了“无君论”的思想,其言曰:“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明者不以智胜,黯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1]161阮籍认为政治和社会只会给人民带来灾害,“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阮籍之所以宣扬无君主义,实际上是认为君主政权束缚了人民的本性,他所倡导宣扬的是“无为而治”。嵇康也同样如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4]309在现实中看不到圣王无为而治的理想,他便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毅然走向庄子,走向自身的感性生命。
2.阮籍、嵇康的政治态度
政治态度上,阮籍“安时以处顺”,走向了庄子顺世游世的道路;而嵇康则走上了隐逸避世,平易恬淡的人生道路。阮籍一生三次为官,前两次为官,皆以病辞;但嘉平元年之后,目睹了司马氏集团的杀戮,又入世为官,表现了其“安时以处顺”的政治观念。正如庄子所言,“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3]142螳螂以臂当车,那是自不量力,养虎顺从于虎,便不会被伤害。“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心神任随外物变化而遨游。安时以处顺,正是阮籍在那个乱世中所抱的政治态度。嵇康在曹爽被司马氏灭族后,便隐居山阳。世事多艰,到处危机重重,嵇康正是看到了这种险恶,为了避祸全生,所以隐居避世,但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他本身厌恶世俗,有着更深层的精神追求。司马氏以卑鄙的手段窃取了曹魏政权,他们打着维护名教的旗帜,大肆诛杀异己,社会上到处是虚伪的礼教徒,这些增加了嵇康对仕途的厌恶,于是他避世脱俗,隐居山阳达二十年。最终他走向庄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平易恬淡。正如庄子所言,“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生”,不热衷于功名利禄,持以一颗温和宁静的心,则不会被患难所侵袭。平易恬淡正是嵇康所想要的。
(二)阮籍、嵇康的文学取向
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阮籍、嵇康的文学作品以表现老庄哲学为出发点,追求精神的自由,表现内在的心灵,这是一种进步趋新的文学观念,是文学自觉的表现,具体而言,这种进步趋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1.诗文哲理化倾向
阮籍、嵇康的作品倾向于表现老庄哲学,表现与道逍遥的精神境界。在阮籍的《咏怀诗》里可屡屡见到这类作品,如“谁言万事囏。逍遥可终生”[1]317。人生艰难,逍遥方可保身,“逍遥”就出自《庄子•逍遥游》。“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1]332鸿鹄亦同于庄子笔下的大鹏,鸿鹄“适荒裔”亦同于大鹏“徙南冥”,阮籍写出的是一个逍遥游的境界。“夫清虚廖廓,则神物来集;飘颻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1]29这里阮籍勾画出一个恬淡无欲、自由骋想、恍惚飘渺的清虚境界,这个清虚境界亦同于庄子笔下的逍遥境界,只是这种清虚略带空灵。与阮籍相比,嵇康的逍遥境界则更有人间意味,“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2]16嵇康的诗表现的是他闲适、自由、恬淡的生活,在这里他得到了精神的满足。阮籍通过勾画清虚空灵的境界进入庄子式的精神境界,而嵇康则是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或“流磻平皋”,或“垂纶长川”,或“手挥五弦”,去亲身体味庄子的逍遥境界。
2.高浑与清脱
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阮籍、嵇康的文学思想的总体格调由建安以来的慷慨情怀转为苍凉,反映社会生活、生民疾苦的作品减少,表现内心世界、自我意识、个性形象的作品增加,玄学思想的渗入,使得阮籍“忧叹中存理遣,理遣中郁情”[5]222;使得嵇康在自然景物描绘中感发玄思,追求玄淡意趣。阮籍的《咏怀诗》充满了抑郁苦闷的情绪,阮籍在现实生活中积聚的苦闷,意图在玄理的阐发中得到解脱,《咏怀诗》中多篇都是通过对时光流逝的慨叹抒发苦闷,阐发玄理,“一日复一日,一夕复一朝”,“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1]312,时光流逝,容颜更换,而世事难料,苦闷非常。“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1]310相比天道,人生是多么短暂,既然如此,又何必执着于外在荣华、人生是非?阮籍正是这样稀释自己的痛苦,这种忧生之嗟和迁逝之悲往往以阔大的时空为背景,贯通玄理,形成了“高浑”的独特文学风貌。而嵇康则喜欢刻画自然景物,“白云”、“绿水”、“惠风”、“朗月”、“绿林”、“山鸟”,屡屡现于笔端,其《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描写长川高岗、山鸟斜阳,感情随景物的变换抑扬起落,在自然景物的倘佯中寄予玄思,表现绝俗的人格,追求“与道逍遥”的人生理想,形成了“清脱”的文学风貌。
注 释:
① 余敦康指出:“阮籍嵇康的自然论玄学是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思想发展而来的。”(见余敦康著.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00.)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高晨阳.阮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Discussion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Yuan Ji’s and Ji Kang’s Thought of Metaphysics
LI F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000, China )
Yuan Ji and Ji Kang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Wei-Jin Demeanor, and their thoughts were similar, both having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ye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ought of metaphysic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Yuan Ji’s and Ji Kang’s metaphysic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ir thought of metaphysics combines with Confucianism,and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not only reflect in their explan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life-preserving and music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ideal personality, but also reflect in their orientation of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Yuan Ji; Ji Kang; thought of metaphysics; comparison
(责任编辑 梁正海)
B235
A
1673-9639 (2012) 01-0054-05
2011-08-17
李峰,男,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09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