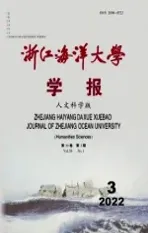从普陀山二十四孝浮雕看佛教对儒家孝文化的接受
2012-08-15罗江峰
罗江峰
(浙江海洋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部,浙江 舟山 316000)
考察中国四大佛教圣地,惟普陀山孤悬海中,既有山石之隽秀,又有海天之寥廓。普陀山,古梅岑山,处杭州湾外,位于舟山群岛中部海域。普陀山以观音大士圣应道场誉称海内,得名源于佛典《华严经》“补怛洛迦”[1]331,简称普陀,华言小白华,释言海岸孤绝处。岛上琳宫玉宇,庄严伟丽,始奉佛以来“上自帝后妃嫔,王侯宰官,下逮缁侣羽流,善信男女,远近累累,莫不信向”。[2]
普陀山三大寺之一法雨禅寺第三重圆通宝殿(又称九龙殿、九龙宝殿、圆通殿、大圆通殿)为本寺主殿。九龙殿是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拆明朝金陵(南京故宫)在明代殿宇旧址的基础上续建成的,顶盖12万片黄琉璃瓦,内顶为圆形九龙盘拱藻井,是中国寺院建筑规模最高的一座佛殿。实地调研发现,在九龙殿前月台东、南、西三面有二十四块栏板,为青石质地,每块宽127CM,高65.5CM,厚19CM,其中雕刻内容宽101.5CM,高49.5CM;栏板之间的柱子上尚存一些生动活泼的石狮子。《普陀山志》载:“第三重大圆通殿……。殿前24块青石栏板,浮雕二十四孝图,为明代石刻精品。”[3]《普陀洛迦山志》载:“第三重圆通宝殿,又‘九龙殿’……;殿外石栏间‘二十四孝图’浮雕为明代石刻珍品。”[4]330但值得深思的是,孤悬海中的佛教圣地为何置放儒家文化《二十四孝》浮雕,其目的是什么,对此进行剖析和厘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代普陀山佛教文化历史进程。
一
普陀山法雨禅寺九龙殿东西两旁为四百多年的古树,殿前的《二十四孝》浮雕刻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至明崇祯十六年(1643)之间。①《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是元代郭居敬(一说是其弟郭守正,另一说是郭居业撰)对历史上尽孝典型人物事迹的汇编,由于后来的印本大都配以图画,故又称《二十四孝图》。《二十四孝》是儒家经典《孝经》的诠释,是中国古代宣扬儒家思想及孝道的通俗读物。
儒佛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入世与出世,重点是孝亲观上。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与根本,是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和传统美德。东汉许慎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5]《孝经》也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6]而释法琳认为“识体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孰辨怨亲。”又说,“是以沙门均庶类于天属,等禽气己亲,行普正之心,等普亲之意。”[7]法琳对待父母的怪谬思想,是悖逆人伦的行为,是儒家学派不能容忍的。这种儒佛根本上的矛盾,也影响着普陀山佛教的弘扬与发展。因此,普陀山佛教要走向人间,必须解决儒佛之间的对立局面,去寻找一个切入点。至明末,普陀山高僧通过对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与儒家《孝经》的亲合,把儒家《孝经》的诠释——《二十四孝》浮雕置放在观世音道场,去实现佛儒“孝亲”的融合与会通。这一佛儒会通的事件,为后来普陀山高僧印光大师、太虚大师证悟:佛教必须向人本主义复归、佛教必须走向人间才能光大复兴,从客观上提供了实物依据,也为观世音菩萨成为半个亚洲的信仰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事实上,普陀山就是一处将佛教从虚无缥缈的来世引向人间的圣地。
二
详查《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大藏经》等有关普陀山文献、明代以来的普陀山九本山志②,关于《二十四孝》浮雕为何置放在普陀山佛教圣地无直接文献记录,现只能通过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推导这一佛教会通儒家文化现象产生的可能。
(一)观世音慈悲精神与儒家孝文化的暗合
普陀山素有“震旦第一佛国”③之称,为“五朝恩赐无双地,四海尊崇第一山”。④吏籍中关于普陀山观世音道场的记载,最早见于《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时,释迦牟尼佛在补陀落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师子座”。[8]789信徒早在“自晋之太康,唐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龄,岁奔走赤县神洲之民,至有梯山万里,逾溟渤,犯惊涛,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9]唐咸通四年(863),日本僧慧锷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坐船回国,途经普陀时触礁,后张氏居民舍所居筑庵奉之,斯为普陀山创佛之始。至明代的普陀山,由于普陀山特殊的地域位置,海寇骚扰,实行海禁,但国内高僧、名宦仍渡海不绝,普陀山佛教由此逐渐兴盛起来。
观世音全称尊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是一位悲心恳切、觉照圆明的大士。《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开篇中提到:“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10]756奉行“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11]这种大慈大悲、济世的功德和思想,想其所想,急其所急,时刻拔除众生痛苦为己任,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主张。也因教化不同环境、不同根机众生之需要,慈悲度生,随类应现,在普陀山显像南海观世音菩萨、杨枝观音、送子观音、白衣观音等。普陀山的送子观音蕴含着印度原创佛教的生殖崇拜,《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记载:“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10]757这种“求男生男,求女生女”的思想与《孝经》、《二十四孝》在孝亲观上的亲合,体现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2]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送子观音正是观世音信仰融入儒家思维与生活习惯的深刻反映,是观世音文化与儒家孝道的默契。去朝拜普陀山的信众除了希冀观世音救苦救难、消灾解厄以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孝子和贤妻的最大夙愿是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以尽孝亲。观音作为送子之神,是完全契合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观念。观世音大慈大悲的利他、平等博爱观暗合了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要支柱的传统文化主张,这是普陀山出现儒家《二十四孝》浮雕的重要内因。
(二)明代皇家与高僧隐士对普陀山儒佛会通的影响
究其外因,明万历皇帝和生母慈圣皇太后延续朱元璋三教合一思想以及皇家对普陀山观世音菩萨的崇敬,明末高僧、隐士倡导儒佛融合思想,对观世音道场《二十四孝》浮雕置放事件的产生,应该来说有着直接的推动关系。也许正是这些对民众、信徒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促进了普陀山观音道场儒佛会通、戒孝合一事件的发生,由此逐步改变了普陀山佛教与儒家相翼并行、冲突、对抗的局面,同时促进了普陀山佛教的发展与兴盛。
其一,随着佛教与儒道之间的融合日益加深,明王朝对佛教采取维护与利用的政策,并对普陀山极为推崇与厚爱。朱元璋提出了《三教论》,大力宣扬儒释的一致性,“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13]朱棣在《大悲总持经咒》序提到:“朕闻:夫观世音誓愿弘深,发大悲心,以济度群生……又况如来化导,首重忠孝。凡忠臣孝子,能尽心以事君”。[8]789而明万历神宗与其生母慈圣皇太后更崇信佛教,兴盛殿宇。《万历野获编》记载了万历五年(1577),“视慈寿寺又加丽焉,其后叠石为三山,以奉西方三大士,盖象普陀、清凉、峨眉。”[14]从“盖象普陀”可以看出普陀山佛教在海内的重要地位,同时皇家对其甚为厚爱。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神宗遣内宫太监张本、御用太监孟庭安赍皇太后刊印藏经41函,旧刊藏经637函,裹经绣袱678件,观音像、龙女像、善财像各一尊赐宝陀寺,紫金袈裟一袭赐真表。”[4]169万历三十三年(1605),奉皇太后命,并先后遣御马太监赵永、曹奉、张随、党礼、张然等来山礼佛,督造殿宇,皇太后和嫔妃等均施银两。万历三十九年(1611)神宗《再赐藏经敕》于普陀山,“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朕成恭己无为之治道焉。”[4]581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定海知县缪燧在《御题“普济群灵”额恭纪》写道:“谓释氏之慈,即吾儒之仁。其悲悯提度,与博施济众无异。”[15]182从《恭纪》中可以看到,缪燧的“释氏之慈即吾儒之仁”已经由“相翼并行”逐渐在走向会通。
其二,明万历期间朝圣、心系普陀山高僧如云,如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妙峰等,并与本山名僧一乘真表、大智真融、密藏道开、昱光如曜、朗彻性珠等关系密切,互有来往,这对创造、搭建普陀山儒佛平台尤为关键。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1543~1603),“师讳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门人称尊者,重法故也。”[16]974从《紫柏尊者全集》可知,他的思想鲜明地反映出明代儒释道会通的趋势,有调和儒释的倾向。紫柏真可说,“且儒也,释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实也。实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释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发未发,缘生无生,有名无名,同欤不同欤?知此乃可与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17]399他认为三教名异,但本质心同,并提出学儒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佛,学佛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儒,“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释,宗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谓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则妄也。或曰:敢请治病之方。曰:学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学佛而能得释氏之心,学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则病自愈。”[17]405紫柏真可一生的言论、活动都体现出“出入孔老之樊,然终以释氏为歇心之地。”[17]410紫柏真可于万历三年(1575)南归,多次游寓、说法普陀山,“凡普陀敕建殿宇,皆其奏之力”。[17]673而紫柏的高徒普陀山名僧密藏道开,早年“弃青衿,出家披剃于南海(普陀山),闻师(紫柏真可)风,往归之。师知为法器,留为侍者。”[17]673密藏深得紫柏器重并受其思想的影响,也大力倡导儒佛融通,这对促进普陀山佛儒会通事件意义重大。
憨山德清(1545-1623),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与紫柏真可是挚友,两者具有相近的性情与宗教情怀,是典型的以出世身做入世事业的禅门尊宿。万历十四年(1586),两大师在山东莱州牢山之脚相见,“予(德清)在长安闻之,亟促装归,兼程至即墨。师已出山,在脚院,诘朝将长发。是夜,一见大欢笑。明发,请还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师即以予为知言。”[16]975憨山德清明确提出:“三教圣人,本来一理。”[18]160他在总结前人三教合一的基础上,以一心统三教,以三乘分三教,倡导“三教一源论”,并指出:“学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庄而谓尽佛经,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庄意……余尝以三事自勉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18]160这后三句成为明代以后三教合一的经典言论。虽然憨山德清未曾朝圣普陀山,但心系普陀山写下了“普陀山诗词七首”,[19]68-71从诗词中可看出,与普陀山昱光等高僧关系非常密切。昱光,万历年间高僧,为白华庵首任住持、普陀寺主持(万历四十年[1612]任住持),昱光曾“刺血书经,上书阙廷,请敕建寺宇”。[4]466为此,憨山德清特地写了《寄普陀昱光禅人》:“白华山下久跏趺,水月光中一念孤。正使十方俱坐断,海枯石烂恰如无。”[19]71可见,两人甚为熟识,并对昱光的学识、为人评价很高,应有过来往并深受其影响。
普陀山造访名僧妙峰(1539-1612),与憨山德清是好友,为明万历年间护国大禅师,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李氏的师傅。妙峰早年“父母值凶岁,亡无殓具,荐席而已,”[16]1007这件事情对于妙峰来说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自己对父母没报恩尽孝道,是不孝子,至“万历元年癸酉也,师居常以二亲魂未妥,欲改葬山”,才完成自己的夙愿。[16]1008可见,妙峰虽出世在佛门,但知道百善孝为先,始终未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从小对其的影响。因此,对于妙峰来说,他把对父母的孝道扩及到对一切众生,在他个人身上体现得非常完美,这就是大孝、大敬,也是佛教的慈悲心。德清与妙峰,两者“名虽道友,其实心师之也。”[16]1010可见在真可、德清、妙峰三者之间,儒释融通的思想互为影响。妙峰为“遍参知识,至南海礼普陀”[16]1008,并多次朝拜、寓住,并与普陀山高僧宝峰同创餐霞庵于后山,由“眉公(陈继儒)陈徽君为题庵额。”[4]467从这里可以看出妙峰、宝峰(陈继儒的伯父)与陈继儒的关系非常密切。陈继儒(1558~1639)为晚明著名隐士,号眉公,少与董其昌同学。他博闻强识,对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释、道等书,无不研习,工诗善画。故其思想可谓融儒释道于一身,博杂而兼通。陈继儒的一生与佛结下不解之缘,每日必焚香宴座,与高僧来往密切,谈佛论禅。曾在万历十二年(1584),二十六岁的眉公致书紫柏真可,相与论禅问道。在普陀山,陈继儒又与白华庵先后两任住持师徒昱光如曜、朗彻性珠过从甚密,陈继儒还特为朗彻写了《普陀朗彻禅师修妙庄严路记》,其中记载:“安得大善知识如朗公辈布满人间,以平不平之心路乎?心路平,世路平。”[4]657可见他的言论与佛教思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可知陈继儒对儒佛之间一种融合的认识。
而明代普陀山白华庵(建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前),聚集了当时的高僧、隐士、山人、文人雅客,“山中精庐,惟此为冠。士大夫游山者,多住之。”[15]266因此,白华庵作为“山中精庐”,士大夫、隐士、山人与高僧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千丝万缕,其思想互为影响。正是他们之间的对话、亲和、融通,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佛教文化会通儒家文化,即明代石刻儒家《二十四孝》浮雕置放在普陀山法雨寺九龙观音殿月台前事件的产生。这一佛教文化会通儒家文化,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普陀山高僧以孝言慈,把佛教的慈悲同儒家的孝道融合起来,鼓励信徒把对父母的孝道扩及到一切众生,从而去领悟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无缘大慈,同体大悲。”⑤
注释:
①查阅普陀山《重修补陀山志》、《南海普陀山志》明清山志及《普陀洛迦新志》、《普陀山志》、《普陀洛迦山志》,法雨禅寺九龙殿前《二十四孝》浮雕为明代石刻。《普陀洛迦山志》记载法雨禅寺的规制:“明万历八年(1580),蜀僧大智首创法雨禅寺(初名海潮庵),为茅屋。明万历十五年(1587)扩建庵院,院内有楼。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增建殿宇,规模壮丽,改额海潮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北向广熙峰麓增建殿楼,赐额“护国永寿镇海禅寺”,进山门第一重天王殿,第二重藏经楼,第三重千佛阁,第四重圆通殿。……明万历四十年(1612)闰十一月十九日,寺尽毁。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住持了空重建斋堂、止阁等,后逐年恢复。”明崇祯十六年(1643),“大殿毁于火,(文元秀,明崇祯十三年[1640]任镇海禅寺住持)退居潮音洞庵。”(王连胜《普陀洛迦山志》)至清顺治三年(1646)才在圆通殿旧址建小殿五间。既然山志中明确《二十四孝》浮雕为明代石刻,那么由此看出,明万历八年(1580)至明万历十五年(1587)之前,这期间法雨禅寺为茅屋,雕刻《二十四孝》的可能性不大,故儒家《二十四孝》浮雕应刻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至明崇祯十六年(1643)之间,其中明万历十五年(1587)至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雕刻的可能性最大。
②明代以来的普陀山九本山志:《补陀山志》([明]侯继高辑)、《重修补陀山志》([明]周应宾辑)、《南海普陀山志》([清]裘琏辑)、《普陀山志》([清]朱瑾辑)、《重修南海普陀山志》([清]许琰辑)、《重修南海普陀山志》([清]秦耀曾辑)、《普陀洛迦新志》([民国]王亨彦编)、《普陀山志》(方长生)、《普陀洛迦山志》(王连胜)。
③明万历年间普陀山摩崖石刻,在梅公鼎岩处。落款:江东扶舆张可大题。
④普陀山正山门前楹联,香港陈守仁等十一人敬献,落款:丁丑年(1997)年春日郭仲选书。
⑤无缘大慈,佛观一切皆空,而不以特定之人为对象,故佛之慈悲特称无缘大慈,其慈心遍及一切众生,乃为慈悲中之最尊者。同体大悲(同体慈悲),观一切众生之身与己身同体一身,而起拔苦乐之心,谓之同体之慈悲。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八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九).中华大藏经[M].(唐)实叉难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清)裘琏.南海普陀山志[M].上海:上海图书馆藏本.
[3]方长生.普陀山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100.
[4]王连胜.普陀洛迦山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汉)许慎.说文解字[M].江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173.
[6]唐松波,耿葆贞.孝经·二十四孝注译[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8:7.
[7](唐)释法琳.辩正论.中华大藏经[M].北京:中华书局,1993:590.
[8](唐)伽梵达摩.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M]//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宏觉国师.梵音庵释迦佛真身舍利塔碑(轶碑)[M]//(清)秦耀曾编.重修南海普陀山志.清本道光刊本.
[10](姚秦)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M]//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姚秦)鸠摩罗什.大智度论(卷二十七释初品大慈大悲义第四十二)[M]//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7:556.
[12](鲁国)孟子.孟子卷四(离娄章句上)[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4.
[13](明)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十(三教论)[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8.
[1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9:687.
[15](民国)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M].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1990.
[16]憨山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M]//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94.
[17]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M]//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94.
[18]憨山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四十五:观老庄影响论)[M]//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94.
[19]王连胜.普陀山诗词全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