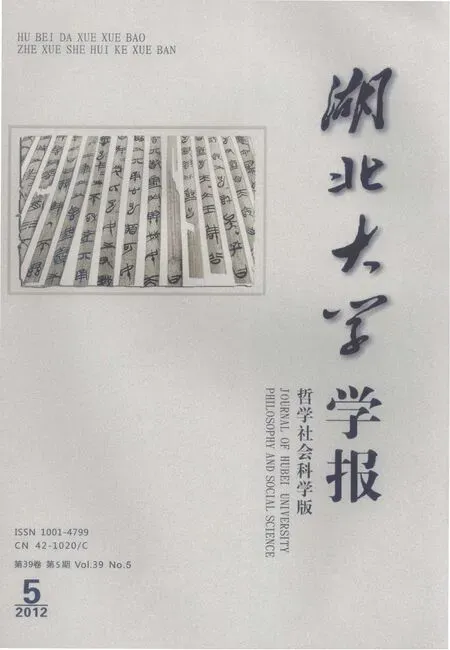语境创造论
2012-06-22廖美珍韩大伟
廖美珍,韩大伟
(1.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语境这个概念越来越为学者们重视。著名语言学学者T.Givon说:“如果说语用学整个学科有什么统一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的核心就是语境。”[1]1语境问题已有相当可观的研究[2,3]。然而,诚如Anita Fetzer所言,“语境这个概念尽管充斥于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话语分析学和常人方法论这些领域,但是至今仍然含糊不清,几乎无法把握”[4]3。语境研究的切入点很多,核心问题无外乎三个:(1)语境是什么?换言之,语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2)语境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3)语境是先在的,现成的,还是创造的?这三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不可分开的,也是互通的。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期研究的重点是回答第一个问题;20世纪末转向第二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持语境动态观——尽管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5];现在逐渐转向第三个问题。本文专门论述语境创造性问题,从言语行为理论和目的原则相结合的角度解释语境创造性。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1)语境是什么?(2)语境是如何创造的?(3)目的原则与语境创造。
一、语境是什么
1.本文语境观 我们认为,语境是由社会互动意义上的人,在一定目的的驱使下,实施一定的言语行为,从而引起的或者激活的、参与言语行为和意义生成、参与言语行为和意义理解的那些因素构成的。语境的这种定义有以下意义。第一,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人是语境的核心成分,第一位的要素。第二,说话人实施的言语行为既是语境最重要的构成成分,又是语境形成的主要因素。第三,人和人说的话语有一个根本的特征,就是目的性。人的言语行为是在目的驱使下实施的,因此目的是语境重要因素。第四,这种语境观是辩证的。在上面的定义里,我们避免了把所有世间万物——有形的、无形的——都纳入语境的泛语境观,只有那些参与言语行为和意义生成,参与言语行为和意义理解的因素,才构成语境要素。
2.两种语境说 从“说话者”角度出发,我们有“说话人语境”,由参与说话人话语和意义生成的因素构成。这些因素既有心理的,也有物理(质)的。从“听话人”角度出发,我们有“听话人语境”,由参与言语行为和意义理解或诠释的要素构成。这些东西包括心理的,也包括物质的。两种语境的关系大致有三种,分别是:(1)说话人语境与听话人语境吻合或者基本吻合,因此,我们就有沟通、理解、共识和和谐。(2)说话人语境与听话人语境不吻合或者基本不吻合,因此,我们就有误解、冲突、分歧、矛盾。(3)说话人语境和听话人语境部分(或者大部分)吻合,或者部分(或者大部分)不吻合。语境创造论很难苟同一些语境观中的认为“语境共享”这个概念。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往往比同一性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意义。个体差异性同样体现在语境和语境的处理上,以个体差异性为基础的两种语境说(观)是语境创造说的一个基础。可以说,没有个体差异性,便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创造。我们特别重视话语与语境的关系。话语包括:口头话语和书面话语;即席话语和有准备的话语;独白话语和互动话语。区分这些话语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的创造形式是不一样的。
二、语境创造说
1.何为创造 事实上,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语境是创造的,但是他们关于语境的一些描述,说明语境是创造的。例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特别是在一种原始文化里,说话不是告知,而是行事。”[6]9社会学重要学派“常人方法论”认为,行为具有三个重要特点,即“权宜性”、“局部性”和“情景性”。这“三性”实际上说的就是创造性。斯帕勃和威尔逊的认知语用学流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语境是一种心理建构。刘云泉在《修辞性适合语境创造》一文中主张通过言语表达者和言语接受者来共同创造语境,言语表达者要利用读者(接受者)的历史、文化、社会知识经验等等,来达到语言的表达效果,必要时可以通过语境来补充交际内容,增强言语接受者的理解能力[7]。林兴仁在《广播的模拟语境和广播的语体》一文中,针对广播语体的特点提出了模拟语境说这一理论,主张广播语体可以模拟人际的交谈,使说者和听话人处于一个虚拟的交谈环境中[7]。“模拟语境”说实际上也是一种语境创造说。但是这些学者要么没有明说语境创造,要么没有系统地提出语境创造的理论和模式。
我们认为,任何理智的人的每一个理智的言语行为都是一种创造,或者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创造是普遍的,绝对的。关于语言行为的创造性,洪堡特有过类似的论述:“无论在单个的词里,还是在连贯的言语中,语言都是一种精神行为,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创造活动;而在每一语言中,这种精神行为都具有独特性,它的作用方式是确定的,在所有方面都受到制约。”[8]249一般说来,创造有两种方式:
(1)从“无”到“有”。所谓“无”即人创造之前还不曾有过的东西。必须说明的是,这个“不曾有”是相对创造的结果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创造的质料而言的。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无”是不存在的。比如:“Who/Are you/Who is born/In the next room/So loud to my own/(Vision and prayer,Dylan Thomas).”
就诗歌形式而言,在Dylan Thomas创作这首诗之前,恐怕人们是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诗歌的。因此,创作这首诗就是创造。但是,创造诗歌的质料确实已经存在的。
(2)从“死”到“活”。现实的东西是存在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死”的,都是无价值的、无意义的,只有说话人针对它们实施有目的言语行为时才能变成“活”的,变成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语境是创造的。存在的东西只有被激活才有意义。但是,激活不是简单的原来的复制,不是简单地复活,而是再生。生于斯,又高于斯。
当我们说,任何话语都是创造的时候,并不等于说,创造都是一样的。创造的创新性有一个程度问题,有一个新颖度问题(其实还有一个价值度问题)。所以创造是一个连续体。创造因人而异。上面的两种创造方式都有一个连续体的问题:从“无”到“有”的创造有一个程度问题,从“死”(静)到“活”(动)的创造同样有一个程度问题。上面两种创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无”到“有”的创造包含从“死”到“活”的创造,而从“死”到“活”的创造包含从“无”到“有”的创造。
2.言语行为与语境创造 英国著名哲学家奥斯丁在《如何以言行事》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语言不只是用来描述和反映客观世界的,说话是做事。这种以说话的形式做的事情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世界。因此,任何说话和写作行为都是语境创造行为[9]。那么言语行为与语境创造的关系是什么呢?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和批判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基础上,按照言语行为的“言外意旨”和言语行为与世界的“适应方向”把言语行为归纳为五类:(1)表述言语行为;(2)指令性言语行为;(3)承诺性言语行为;(4)表情言语行为;(5)宣告行为[10]。语境是言语行为创造的。更准确地说,语境是这五种言语行为创造的。这五种创造的方式和创造的效果(对听话人、读者或世界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表述言语行为。表述性言语行为与世界的适应方向是从词语到世界。这种行为创造的是一种现实(状况)。因此,例如:
Sam smokes habitually.(Sam习惯性地抽烟。)
表述言语行为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11],因此,这里的创造有一个依据真实性的判断标准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另文研究),换言之,表述性行为具有真值问题,而真值又受说话人的目的意图支配。
(2)指令言语行为。指令性言语行为与表述性言语行为不同,其言外意旨是指使听话人做一件什么事情,其与世界的适应方向是从世界到词语,即世界因说话人的言语行为而变化,因此创造的是以往没有的,或者新的状态。例如:
Stand up!(站起来!)
在哈贝马斯那里,这种行为是“策略行为”、操纵行为,一种不是以共识为目的,而是以一己之利为目的的行为。指令性言语行为通常有明确的第二人称代词,所以其对语境的创造是不言而喻的。指令性言语行为是纯粹的行为,没有真值,无法用真假判断。但是指令性言语行为具有规范上的正确性问题。
(3)承诺言语行为。承诺性言语行为的言外意旨是承诺为听话人做一件对听话人有益的事情,创造的是一种未来事件、行为或状态,其与世界的适应方向是从世界到词语。例如:
We promise to clean the room afterwords.(我们许诺完事后清扫房间。)
承诺性言语行为创造的常常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者一种人际关系。
(4)表情言语行为。表情言语行为的言外意旨是表达情感,因此与世界之间不存在适应关系,创造的是一种情感语境。例如:
O,my God!(啊,我的上帝!)
在哈贝马斯那里,判断表情言语行为的标准是真诚性,没有真值,也不存在规范上的正确性问题。
(5)宣告言语行为。宣告言语行为的言外意旨是公布一种决定等等,其与世界的适应方向是从词到世界,又从世界到词。例如下面的法庭宣判:
Judge:Given all of that,it is the judgment of this Court that you be sentenced and committed to the custody of the Bureau of Prisons to serve a term of 120 months on Count 1 and Count 5 of the Case 05-225;that is,120 months on the conspiracy to communicate nat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to unauthorized persons,and Count 5,conspiracy to communicate classified information to an agent of a foreign government.2) As to those counts,it’s 120 months on each,but the sentences are to run concurrently. ——(United States v.Lawrence Anthony Franklin)
由于宣判言语行为影响并且改变现实,因此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创造。比如说,上述宣判之后,先前的被告人就成了犯人,这是一个性质不同的身份改变。
3.语境创造与听者和说者 任何言语交际都是一个包括说话者(作者)和听话人(读者)双方的活动,因此创造是双方的创造。但是,由于在言语交际互动中,互动对方(参与者)的角色等等因素的不同,因此对语境创造的方式、创造的程度、创造的效果、创造的主动性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上面说过,语境有说话人语境和听话人语境,而且说话人语境和听话人语境之间有三种不同的关系。这是语境创造说的一个重要依据和来源。三种不同的语境关系都需要创造形成,但是创造的力度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下面分别说明。
(1)说话人创造。语境创造首先是说话人的创造。在话语互动中,有先后关系。说话人是话语活动启动者,因此在语境创造方面具有启动的地位和优势。我们上面说过,创造是言语行为的创造,因此说话人的创造是上述五种言语行为的创造。说话人的语境创造有一个透明度、清晰度,或者可分析性和可理解性的程度问题。这种程度一方面受制于说话人(作者)的目的意图,一方面受制于说话人或作者的语言能力。在一般情况下,说话人(作者)追求的是语境的最大透明度、最佳清晰度、最可靠的可分析性和可理解性。而且,说话人一般会尽量利用他认为双方可能有的共享知识设定。但是,有时候,出于各自背景的不同,由于特殊的目的,说话人(作者)故意使语境晦涩艰深,模糊不清,难以捉摸。另一种情况是,说话人(作者)的语言能力影响语境创造的清晰程度。语言表达能力越弱,则语境创造清晰度和透明度越小。
(2)听话人创造。由于启动话语活动的先后关系,听话人相对于说话人来说,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说话人的话语首先对听话人形成了制约,因此听话人的创造受制于说话人和话语人话语。听话人的创造还要受制于其他的因素。但是听话人只是在先后关系上才是被动的,而且被动的程度有变化。听话人的语境创造首先是针对说话人上述五种言语行为的创造。对听话人来说,这个创造是在上述五种言语行为的理解过程中进行的。由于五种言语行为是不同的,因此对听者来说,语境的创造也是不一样的。听话人为什么也要进行语境创造呢?或者说,怎么理解听话人的语境创造呢?
我们首先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说明。上面说过,语境创造是上面五种言语行为的创造。这五种行为的实施,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是“能指”(signifier)对“所指”(signified)的一种物化过程,是一种目的意图活动,因此也是一种主观观念的物化过程。那么到了听话人(读者)这里,从最低级的程度上说,首先就存在“能指—→所指”还原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更重要的是,由于“能指”在作为接受主体的听话人(读者)的意向性结构中并不是以直接的形象化的客体形式呈现出来的,而常常是只呈现出客体形象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图示化的侧面,即只提供给听话人(读者)认识和想象客体形象的可能性条件。听话人(读者)为了在自己的意识中再现出说话人(作者)意欲在能指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等,就需要在客体的各个图示化的方面建立想象性关联,从而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把各个图示化的方面联系、组构起来。这是一种能动的目的指导下的意向性建构活动,作为接受主体的听话人(读者)可以调动自己既往的知识积存和当下的情感思考,以填补各个图示化的方面之间所存在的空白,并将那些不明确的地方具体化,最终把它们合成为一个有机的形象整体。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语境的创造过程。
对听话人来说,这里既有符号的还原和创造,更重要的是,还有对说话人(作者)的意图的还原和创造,这是一种基于前者但比前者更加重要的创造。前一种还原和创造是在后一种还原和创造指导下进行的。
同说话人(作者)的语境创造一样,听话人(读者)的语境创造也有一个程度问题。这个程度取决于上面所说的双方语境的关系:如果说话人话语创造的或者激活的、参与话语生成和话语理解的因素与听话人共享程度高,相吻合的程度大,并且说话人的话语明晰程度高,则听话人创造的程度低,为创造所付的成本和代价也低。如果参与说话人的言语行为生成和理解的因素不为听话人共享,或者发生冲突,而且话语明晰度低,则听话人的创造努力越大,成本越大,代价越高,创造的程度越大。一般说来,双方在场的互动的语境创造性,较之于一方在场一方不在场的互动的语境创造性,难度要小些。这里,我们不妨用王国维关于诗歌创作的境界说来解释这个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诗词创作的“境界”时,认为境界有“有隔”和“不隔”之分,“不隔”之境高于“有隔”之境。所谓境界,实质上是语境,或者语境的一部分。境界显而易见是创造出来的。相对来说,不隔的境界不只是艺术审美程度高,对于读者来说,意味着语境的共享成分多,因此听话人(读者)的创造的难度小一些。有隔的境界对于读者(听话人)来说,共享的成分和因素少,创造难度大一些。我们试以王国维提到的欧阳修的《少年游》为例:“栏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
王国维认为,上半阕“语语都在目前”,因而不隔;而下半阕语语均不在目前,故隔。上半阕以简练笔触,勾勒出一幅三月春色的美妙图画。作者意在咏草而着墨于人,写一少年(少妇),凭栏远眺,睛川历历,碧草连天,少年(少妇)的心也随之飞向天涯,思念远行的亲人。这里直接写草的虽然只有“暗碧”一句,但读者却从少年的思绪中感受到萋萋芳草、绿遍天涯了。像这样写无情草木映入少年(少妇)之眼,融进离人之情,就不仅境界广远,而且真切动人。下半阕还是紧扣春草来写,但连用了三个典故。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中,有一名句为“池塘生春草”,故“谢家池上”暗指春草;又因为江淹《别赋》里写到:“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所以“江淹浦畔”,也暗指春草;另外,《楚辞·招隐士》中又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词中“疏雨黄昏”、“更忆王孙”云云,便由此化来,说的还是春草。
王国维认为上阕胜过下阕,主要是从审美和审美效果角度来谈的。从读者的语境创造来说,显然上半阕的创造要容易些,也生动些,因为“语语都在目前”,不隔。而下半阕却要依作者和读者之间对参与语境建构和创造的共享成分的程度而定。知道春草典故出处的人,知道下阙事事都说春草;不知典故出处的人,读来便不知所云,因此创造难度很大,甚至单凭个人的努力还无法完成创造,姑且不说这三个涉及春草的典故所出的三篇作品,所写的生活境遇、思想情感各不相同,虽然同样描绘春草,但具体意蕴却差别很大,把它们堆砌在一起,既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也没有表达出真切的情感,除了感到由辞藻、声律带来的低度形式之美以外,很难与作者情感共鸣。不隔的境界需要读者和听话人创造(如前面符号学的解释),有隔的境界更需要读者和听话人的创造,后者创造的力度和难度要远远高于前者。
三、言语目的与语境创造
言语行为目的原则认为:任何理性(正常)的人的理性(正常)言语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或者说,任何理性(正常)的人的理性(正常)行为都带有目的的保证[12]。说到底,语境首先是由说话人的言语行为目的创造的。只有当我具有一定的目的时,我才决定(选择)实施言语行为。只有当我具有特定的目的并且决定实施这一目的行为时,相关的因素和成分才进入我的思维和大脑里,才与我的行为相关。而听话人为了理解说话人的话语,首先要理解(要创造)说话人的目的,要围绕说话人的言语行为的目的去创造和建构。因此,听话人语境也是目的创造的。我们上面说过,听话人的话语是在目的驱动下生成的,目的原则起着支配作用;言语行为的核心是言语行为的意图性(也即本文的目的性)。同样,在听话人的理解过程中,目的原则同样起着支配作用:听话人一方面要创造性地理解说话人的目的,另外一方面也要根据自己的目的与理解和创造说话人的语境。这是理解说话人的话语并保证交际成功的基础。如果能用一个图,或者需要一个图,来把整个创造过程简单地直观地表达一下的话,那么它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语境的核心是说话人,说话人的核心是目的性,是语境创造的源头,而语境本身则要用言语行为来创造,这种创造可以是从无到有,也可以是从静到动,从“死”到“活”。就在这种目的驱动下的说者和听者之间“静”与“动”、“死”与“活”的互动中,创造出了我们所谓的语境。莱文森有一段话非常能够表达他对语境的无可奈何的情绪:语境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如果说对一个话语加以解释需要一个语境的话,那么我们如何在解释之前从一个话语中提取一个语境呢?话语带有自己的语境,就像蜗牛随身带着自己的家一样,这个说法确实很奇怪——如果我们在给语境下定义时把信息内容排除在外(就像信息理论那样)。Givon,T也有一个很生动、很形象,但也是非常让人对语境失望的比喻:语境就像大蒜,剥了一层,又有一层,一层包着一层,没完没了。其实,只要我们抓住了目的这个关键,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因为说话人是根据目的来建构语境的,而听话人也是根据目的来建构语境的。
[1] Givon,T.Context as Other Minds:The Pragmatics Of Sociality,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5.
[2]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冯广艺.语境适应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4] Fetzer,Anita.Re-contextualizing Context:Grammaticality meets appropriateness[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
[5] 廖美珍.目的原则与语境动态性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6).
[6] Malinowski,B.The problems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M]//Supplement 1 to C.K.Ogden&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London:Kegan Paul,1923.
[7] 刘云泉.修辞形式和语境创造[M]//中国华东修辞学会.修辞学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8] 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论文集[M].姚小平,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9] 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10] Searle,J.Speech Act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1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2] 廖美珍.目的原则和目的分析:语用学新途径探索[J].修辞学习,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