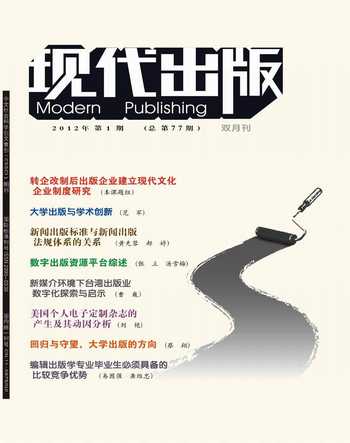“编辑力”
2012-04-29郑爽刘逸
郑爽 刘逸
摘要:日本出版人提出“编辑力”的概念,认为成熟的编辑应该是具有“完整人格”和非凡能力的人;不具备“编辑力”很难做好编辑工作。从中国近现代出版人的出版理念和实践中,可以提炼出有意义的、体现“编辑力”的精神。这种出版精神,对于编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编辑力;近现代出版人;实践
日本著名出版人鹫尾贤也曾在其著作《编辑力》一书中提出“编辑力”概念,从创意、策划到人际关系等方面说明“编辑力”的特点:编辑应该是整个出版流程的能手;应该是具备“完整的人格”和非凡能力的人。这里的“编辑”并不仅仅限于狭义的编辑的概念,而是指广义的编辑,主要是那些在出版史上卓有建树的出版人。在我国出版事业上作出重大贡献的近现代出版人,如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陈独秀等等,他们在出版经营的实践之路上,正是因为具备全面的“编辑力”,使他们在各自的机构岗位上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为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前进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从近现代出版人的理论和实践中,能够提炼出对编辑工作者有意义的、体现“编辑力”的精神。
以理想成就事业
毫无疑问,中国近现代出版人的出版活动是建立在他们的出版理想之上的,这是他们 “编辑力”最主要的基础。
这一点,在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张元济身上有深刻的体现。张元济曾有诗曰:“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正是有了“昌明教育”的理想,他才去从事出版业。原因何在?从他给蔡元培的信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在信中说,“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①他还想通过出版事业,创造一个“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的社会。
张元济对文化事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他九十寿辰之际,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茅盾先生的祝辞将他一生的事业概括得尤为精当,其中说道:张元济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业,将来的历史将记录他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茅盾称他为近代文化史上“开辟草莱的人”。
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像张元济这样因有了“昌明教育”的思想而去“开辟草莱”的出版人何止少数。回顾中国近现代出版史,那些出版大家,如梁启超、陆费逵、陈独秀、王云五、杜亚泉、胡适、茅盾等何尝不是如此。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执笔的《中华书局宣言书》开篇就说明:“立国根本,在乎教育。”②梁启超本人的出版活动主要体现在办报、办刊方面,他认为报刊是“开民智”“育人才”的重要手段。所以,他在办《新民晚报》的时候就有明确的宗旨:《新民晚报》取《大学》“新民”之意;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杜亚泉办《亚泉杂志》,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以至后来办《新青年》,都有他们“启蒙”与“醒世”的出版理想。
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张元济在1901年10月致盛宣怀的信中说是“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③这也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的很多出版家,同时也是教育家——这是由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更是由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所决定的。
其实,不论是身处哪一个时代,出版人都面对一个社会责任感的问题。正是由于责任感、由于理想,才铸造了中国近代现出版人的伟业;这是他们的“编辑力”得以体现的前提,也是对于今天的出版人具有启迪意义之处。
从社会活动中发现资源
“社会活动家”与“编辑”身份的融合,在中国近现代出版人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也是他们的“编辑力”的体现。
从大的方面讲,出版人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可以构建一个很好的出版平台,为出版单位营造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也可以网罗人才,为出版单位注入活力。从小的方面讲,策划编辑的社会活动可谓是选题的“源头活水”:他们可以从社会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地得到选题的资源。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人很少留下记录这方面的文字,但是,从他们出版活动的过程,可以看出社会活动能力对于出版工作、对于编辑的重要性。
以20世纪初著名出版家,先后任商务印书馆国文部部长、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的出版工作为例。起初,高梦旦给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投稿,文章的内容主要论废除拜跪之事。梁启超读后,大为叹服。可是后来两人见面,他们一个讲闽语,一个操粤语,没法交流,于是笔谈终日,自此结为莫逆之交。高梦旦的出版之路,也由此起步。后来高梦旦赴日本考察,深感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回国后,与张元济谈教育,志趣相投,于是应张元济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高梦旦在商务期间,除了与蔡元培、张元济合力推出商务的第一批近代新式教科书外,还极力邀请胡适入主商务的编译所;在胡适婉绝之后,他改请胡适推荐的王云五。这是明智之举,王云五后来把商务印书馆经营得有声有色,他本人也成为出版大家。
翻译家林纾的译著小说,如《茶花女》等在中国的风行,靠的也是高梦旦与林纾的私人友谊以及对他的译介工作的大力支持。
事实证明,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高梦旦是非常成功的,有梁启超、蔡元培、林纾、张元济、胡适、王云五等杰出人物的鼎力相助,就不难理解商务在中国出版史上的辉煌了。
毫无疑问,中国出版史上每一个有成就的出版家,都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现代出版人王任叔(巴人)认为编辑应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其中的“动”就是积极地介入社会活动。
总结前辈们的经验,那就是:要做一个合格的出版人、一个好编辑,就应该“走出去”。
用凝聚力团结同仁、作者、读者
凝聚力,当然应该是“编辑力”的重要内容。一个出版机构应凝聚的对象是同仁、作者、读者。在这方面,我国近现代出版人的理念和实践对于今天的编辑也具有启迪意义,他们在团结同事、培养作者队伍以及服务读者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今天的编辑来说,也是很值得借鉴的。
以张元济为例。在因为人事问题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的鲍咸昌有矛盾之后,张元济给他写信,信中说:“弟与吾兄订交二十余年矣。自入公司后,见吾兄实心办事、公正无私,知公司必能发达,故深愿竭其愚诚以为吾兄之助,而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④同事是共同创业的基础,但在工作中因为见解、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矛盾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工作中的矛盾。张元济的观点表明:事业是出版人共同的追求,在工作中产生的任何矛盾,都应该也能够化解,不能为一些矛盾而影响了共同创业的凝聚力。
作为编辑家的胡适也是善于在同仁之中铸造凝聚力的高手。当年他办周刊《独立评论》,因此团结了傅斯年、丁文江、蒋廷黻、陈衡哲、任鸿隽、罗尔纲、张奚若等人,组成优秀的编辑队伍,在当时的期刊界独领风骚,以致其中的蒋廷黻以骄傲的口吻说“《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
在对待作者方面,张元济、高梦旦等人也是编辑的楷模。当年,林纾翻译的小说销售很好,影响很大,是商务印书馆出书最多的译者。林纾的成功与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的支持资助是分不开的,他们为林纾的译作支付了高额稿酬。
邹韬奋对待作者的一个特点是“取稿凭质不凭名”。这不但有利于提高出版物质量,也很利于发现新作者。而邹韬奋本人对待读者的态度更已经成了出版行业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竭诚为读者服务。至今,三联书店还以此作为店训。
对于一个出版机构而言,同仁、作者、读者都是资源,如果缺少了对这些资源的凝聚力,事业就无从说起了。
借“计算”抓经营管理
王云五主持商务编译出版达25年,“擅长计算”是他在出版管理方面的一大特点。王云五晚年在总结其人生经历的《岫庐八十自述》中说到 “算学”对他事业的帮助:他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都要计算其利害得失,考虑其中的利害关系,以此作为判断的标准。他认为:“救济之道,舍从速采行科学管理方法,别无他途。……国家无预算,则财政紊乱,根本易致动摇;公司无预算,结果亦正相同。……统计对于一切事业,均有重大关系,其于实业亦然。”⑤
1930年2月,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甫一上任,他即出国考察,访问日本及欧美八个国家。期间,他多方调研,参观了40多家印刷厂,咨询了50多位出版管理专家。回国后,为推行“科学管理法”,他在商务发表了极具现代管理精神的长篇演讲《本馆采行科学管理计划》。“科学管理法”由《科学管理法计划》和《编译所工作报酬标准》组成,它对商务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科学管理法”在当时的实践难能可贵,它以新观念、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器材来加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为民营企业甚至官办企业之首创,对于提高生产力,促进企业尤其是出版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王云五是中国出版的科学管理之父,给后人以很有意义的启示。
现在,许多出版社不乏对图书成本管理很含糊的编辑。有的编辑甚至在一本图书推出并销售到一定册数之后,还不知道是否盈利。
综观王云五的出版经历,可以把他所说的“计算”的范围扩大一些。出版人的“计算”范围,除了图书的出版流程的各个方面之外,还有出版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说得再大一点,还应包括图书出版的外部环境等等。
“擅长计算”的能力是具体的管理能力,是一个出版人的“编辑力”的体现。作为一个出版者,如果不能在关涉图书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成本上“擅长计算”的话,那是很难做好出版的整体工作的。好的编辑并不仅仅是“做内容”的,他还应该是“做经营”的。
凭执著创新赢得竞争
执著是编辑赢得竞争必备的精神。陈独秀在做编辑过程中始终秉持执著的精神,使得一篇篇不同作者的佳作得以问世。鲁迅说他最初创作小说的动力在于《新青年》的编辑“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⑥陈独秀早年经常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寄奉《新青年》杂志,并不断地向胡适约稿。最终,胡适的名文,被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的《文学改良刍议》便在陈独秀的一再催促之下诞生了。
编辑的执著与耐心一方面可以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把作者的热情激发出来了,何愁没有出版资源?另一方面,对于竞争激烈的名家之作,也需要以执著的精神参与竞争。当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了争出梁启超的文集展开了竞争,最后双方各出一种。其实,双方的竞争过程何尝不是一种执著的“编辑力”的体现?
创新也是成功的编辑应当具备的“编辑力”。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创新”的竞争。以教科书的出版为例,在中华书局创办之前,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一统天下,几乎占尽了市场。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抓住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机,迎合新形势,推陈出新,适时出版新式的“中华教科书”,改变了商务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因其体例新、有突破而占据了更大市场。正是陆费逵的创新精神使他在竞争中争得先机。
时下,图书的跟风现象非常严重。一本书畅销之后,往往跟风成势:《谁动了我的奶酪》引出了很多“××奶酪”,《哈佛女孩刘亦婷》引出了诸如“北大女孩”“清华男孩”等等所谓素质教育方面的图书。这种形式的跟风是比较低劣的,不利于出版业的发展。
事实上,只要有创新精神,再讲求借鉴和移植的艺术,“跟风”也可以成为一种创造。如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图书竞争中,商务印书馆有《四部丛刊》,中华书局则推出《四部备要》;商务印书馆有《新字典》,中华书局则推出《中华大字典》;商务印书馆有《辞源》,中华书局则推出《辞海》;商务印书馆有《教育杂志》,中华书局则创办了《中华教育界》……其实中华书局对于商务印书馆的模仿并不是跟风,而是对商务印书馆的图书品种的移植和借鉴。以上所举例的书名相近的几种图书,体例有别,视角不同,同样具有文化上的积极意义。
王云五也是善于在借鉴中出新的出版家。他推出的《人人文库》,是从国外的鸿篇巨制《人人文库》得到启示的;国外有经典权威的《牛津大字典》,他便推出了《中山大辞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来创新是不排除借鉴的。
中国近现代出版人的“旧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在他们出版理念和实践中体现出的“编辑力”,还是能给人们带来有意义的启示的。
(郑爽系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三环子公司总经理、编辑;刘逸系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室主任、副编审)
注释:
①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61.
② 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集[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3.
③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4.
④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49.
⑤ 王云五著;王学哲编.岫庐八十自述(节录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8~89.
⑥ 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