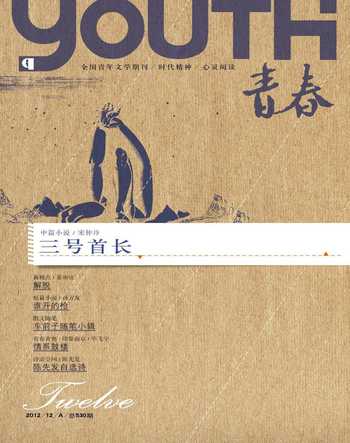返回金色村庄
2012-04-29苏宁
苏宁
葬亲之地
我将写的这个村庄,由一条河流的名字命名,它是辽河一个支流,如今早已干涸不在。前年清明,因为祖父去世,一心希望埋在那里的缘故,我们送他的灵柩回到那里安葬。
那是我离开那里多年之后第一次回去。再不是记忆里的样子了。我也再没有找到那条曾经的河流,连河床旧迹也已隐约难辨。这个以河流为名的村庄,我幼年时在此住过。曾经有着广阔无边的原野的美丽村落,因为比邻的城市的不断扩展,一点点被围进去,先是一些年轻的孩子,他们无法拒绝那些有时代感的东西,从内心向外无法抗拒时尚诱惑,在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在他们所接收的信息中,城市中心地带仿佛是人生梦想的所在之地,楼堂馆所,华裳美饰,一切气息,形态,声音,都有近于理想的年轻的味道。年老的人,或者被他们的孩子慢慢带进城里定居,或者因为年迈和疾病死去,成为树林空地中一堆一堆沉默无语的坟茔。房子破旧了,再无人翻新重建,在时光中颓败下去……好像终于完成了守护那一家几辈人白天休息、晚上安眠、不被风吹雨淋的重任。房子一间间空出来,因为没人住了,草也变得有勇气从房顶上墙垣上四处长出来,愣头愣脑,像没有管束的孩子,衣宽袖大,满世界疯长疯跑。
那一天,我走过一村的院落,也看到一些人,可已经没有人认得一个多年前在此住过的孩子了。我也是想上半天也记不起其中任何一个名姓。在村子正街前面的一条街上,我抓住一个正跑着追一只皮球的小孩,说:知不知道我也在这里拍过皮球?旁边咪着眼晒太阳的老人,也许一霎那隐约想起当年曾见过我这么一个小孩,也仿佛是自言自语,他对我说:还好,你回来赶上看它一眼了,这些房子全要拆掉了,这块地,早被人买走了,过不了几年,它就没有了,那些树,肯定也不要了,那些坟地,也要平掉,已经通知要不迁走,要不原地挖深深埋,人老归天,猫老归山,这个村子,也老了,人老了没样子,它也老得没样子了。
这个不曾在地图和地方志中出现过的村子,在那个下午使我无比悲伤。因为有我幼年的记忆。回来后,心意难平,我开始试图用文字把它在纸上做一点保存,希望它在文字中的存在使我的童年,还能有一点温度,有一个出处,也许它也是很多在那生活过的孩子共同的记忆。它曾经存在,但越来越像一个难以追索的梦。是多年后无法找到凭证的生命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很多这样的乡村,成为城市的伸延,使它做了它的一部分,却又是疏离的,两者若为母女,它得不到它待亲生骨肉地疼,若为夫妇,貌合神离却不分手,未来如何融合慢长而未知。
我的童年,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那段时间,关于这个时段的乡村生活景象和民风,还是朴素和纯净的,四处是春意盎然之象,它的生气和真诚可坦然相待于万物。关于这一时段的乡村生活景象,我所见记载亦不多,这也是我所以决定记下的另一个原因。我想,它应该还是我内心对文字的信仰的一次表达。对于记忆里的乡间风物气象,以及民众的精神情怀,呈现于纸上,不免要沾染个人理想情怀和精神意志的味道,况且,记忆这东西,是难以忠诚于光阴的,在不停流动向前的光阴中,记忆中的人事总会因光阴带来的个体成长而使它本来状态发生微妙变化。但我确信,一个孩子所看到的事物在时光中的样子,总是会过了很多年仍被这孩子记得清晰。希望这个记录能唤回它,像一个母亲在幼子成人之际再一次喊出乳儿之名。一切的记忆,都没有死去,它会活得比我们每个人都长久一些。
土地、童年、故乡,它们到底是我们生命中的什么?生活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将比前一天更灿烂和美好。在一些安静的黄昏,我希望有一个人,终于看到了我这些文字,他把它放在枕边,让它陪伴自己过一些长夜。在我们寂寞的成年时光中,那曾经存在但又消失的一条河流或者一个村庄,相信它们都会回来,只是可能换了一个名字。那存在过的一些事物,消失也就消失了,不必记得太深。
现在,当我写这些字的时候,写到这片我童年时代住过的土地的时候,我面前全是秋天的景象:成垛的金色的玉米、成垛的金色的麦子,成片的金色的稻田,一亩一亩地排过去,稻穗沉得快弯到地上了,孕期已深的母亲的样子,好像我的亲人都还才从那稻田里除草归来。
草木衷亲
开篇说过,我幼时所住过的拉马河村有一条笔直宽阔的大路贯通东西。这条路,我出生时便是这么虎虎生风地存在了,只是在我于此生活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忘了问一问谁,这条路是何时所修,且不知当地有否乡志并于其中记载。
若以今日之我估算,这条路长于我十年二十年总是有的。有一年开春,我大约总在五六岁,已经识字了,好像是才第一次真正跑到这条路上来,我一下惊住了,两旁高高的白杨树,所有枝杈正一齐拱出嫩而浅绿的叶芽,卷卷的,细细的,正要舒展,此时树干还是灰白枯裂的受了严冬敲打的样子,这齐展展的轻柔的悬在枝上逶迤远去的两队新绿仿佛一下子就把一个孩子的心教会了飞,仿佛才是第一次真正让一个小孩看到春天结队而来的样子,看到除了她出生的小村之外,还有同样的小村,绿色的春天,也要到达那里,要一直绿到最远方。
这些树既不大结果,也不大开花,绿叶展开到足够大就是真正的春天,然后结出一串串小穗子,孩子们可以用它做项链,绿色再深些,那小穗子就扬出絮子,飞得满天,天女单单散着一种花似的。虽说有些像花,但究终不是花,所以在我,这些树好像都是雄树,在我六七岁,也许是五六岁时,它们就已经长了有十年八年了,这些白杨静静分列在大路两边,列队远去,每边都种有三两行,偶尔见到一棵大杨树,很高很壮,似乎已经是一根檩子或一只大车辕的料了,刚被砍倒,那根就随之被挖出,在这原地,一棵小杨树苗连夜种了下去,就刚种进去的小杨树就像一个小孩子,被夹进了大人的队列里,在和大人一起吃饭干活、东张西望间,跟着一溜烟地长大着。
路边植杨,河边植柳,这规矩因何而来,从何时而来,我至今亦是不太明了,也许所谓约定俗成吧。这路与河都是人们生息的重要场地,也许因此,这人家的房前屋后也沾亲带故似的种着一些杨树柳树,杨树是雄树,可以看家护院,柳树多女子气,所以种了多半是为赏心悦目,能种在院里院外的还有榆树,这是很硬气的树,乡下人不大会转弯骂人,但若这人太笨到不可以教化,不开窍,即为“榆木脑袋”,我住过的村里历来也是有几个长着榆木脑袋的人,真是笨得不可浪费纸张细表。榆树之叶,我们呼之为榆钱,圆圆的,初上枝头最嫩时,色若新金小猫似的温柔可爱,久之老掉即沉重渐白。嫩时一嘟鲁一窜的,叶密密的挤在枝上,味道甜甜,是孩子的小点心也是水果,还可烧汤为菜,有如百任可当。榆树历来还被有些人看作招财聚宝之树,既然这样,真是不可不种,所以家家都要种上一棵。不过也不知为着什么,我们一村的人都把一棵榆树种在房子后面靠着墙院最边上,不知是何意,也许是家家如此,过日子吗,不便出格。后来去和绅家,他也种了一棵榆树,位置却是他家水塘的边上,看来他确实比我们村里的人更爱聚财。《齐民要术》中曾有“收榆之青荚,小葵曝晒,冬至而酿酒,滑香,宜养老”,只是村中如此多的榆树,年年生荚,老去,却无人用之酿酒,真是可惜得很。
柳树多是笨柳,没有我长大后在南方一些水边所见的那么婀娜,可那十分的婀娜在我看来不免有些娇情任性,不如村中幼年所见柳树的朴素。
家里打柜子打箱子做房梁的多是松柏木,坚韧有耐力,可这松柏多长在附近的小山坡上,地气好,又是空地,人人来种,十年二十年便是林子,林子中还有老人永久安息,所以,渐渐的,也是一块墓地了,此地风气,墓地前后,植几棵树,为着墓里的人也许寂寞,也许要凭着一棵树来辩知四季节气,松柏虽说是长青之树,但在乡下的人还是能在一枝松枝上看出日月轮回已到何处的。松树,柏树,这么好看的在漫漫严冬里唯一绿着的树,我一直很喜欢它。
这些树,年年月月的生息下来,陪着一个村子的人,也许只有这些树,它们会均匀地爱每一个人,怜惜一切它自己以外的众生,它不为单独的任何一个人而绿或枯老,它们为所有人所有事物心怀悲悯,它们也从不太走近我们本就已很寂寞的生活,只是远远的打量。保持尊严距离。
也许,一个心怀忧愁的人,他在田野或山坡中走,一棵一棵树木从他眼前移过,这些树,也许比他还要寂寞,还要老,或者它们比他还要年轻,但这些树总是朝气盎然的样子,让他一望之下,觉得自己的寂寞烦恼不过是天地之间最微小地最不值得为之一苦的,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心中另有所思,他走遍一百里的长堤,一百亩田野,就像在什么也没生长的大地上走着一样,那些树只是天地之间一组静物,他的目中有如空无一物。是的,他们是另一种人,可以不必在此时非得看到这些忠诚义气的树,只有我,现在想来,仍觉得那每一种每一棵仍如我的亲人,在苦痛时,独独可以抱着它们大哭一场。
跳大神
有些人生了病,虽经中医搭过脉,又在那村县的卫生所中打过针,还是百般不好,去不去城里的医院看看呢?一院子的琐碎事情,实在拿不定主意。
人生在世,生几次病是寻常事。可一些上年岁的人一心想知道病起何因。兼之历来的风俗逢年过节有病遭灾,都要找仙姑来看看才安心。
谓之仙姑,当然是位女仙,既为仙,一定是要漂亮的,长得不好不要紧,但要会打扮。头上一朵大红花,春天簪芍药,再迟些,石榴红的卷莲,称之为莲却是旱地里长的。西番莲开了,那西番莲花也是很美的,有紫有红,摘一朵戴在头发上。双朵的红牡丹,瓣重色艳,带了尤其好看。月季虽然小,别了总比没别强。秋天往后,园子里时兴的鲜花都谢的谢,败的败,那用红绸子做一朵花好了,同样红艳艳、水灵灵,而且能一直带着而不坏,这花只不过太完美,比西番莲壮实,比牡丹圆润,比芍药色更正。出神时簪上,不出神可能是不须簪的,天天出神时有着这样一朵花,也是底气,平时,可不能,她也要煮饭,要炒菜,想必煮烧时也是要像凡间女子那样在灶前弯下腰的。我住过的村子里早前也有仙姑,但后来据说没有了。我出生时,村中来的仙姑已为外请,她坐着马车一来,就已打扮好了,接仙姑多用马车,三匹马套着,若是冬天,那车上往往还铺着棉被,让仙姑坐在车上,用棉被盖住腿,仙姑那么端端正正一坐,手上往往还挑着一只大烟袋。
她穿着一张鲜艳的大裙子,是有着被面上的大花朵般的红花布裙,使人以为那就是一张被面,被面虽说多绣着鸳鸯戏水、龙凤呈祥,但那染着大牡丹、大芍药的被面子也是有处卖、有人买。
上身那斜襟袄的颜色也是鲜亮的,一个接一个的蒜瓣子大盘扣,比真正的蒜瓣子还要粗肥很多,虽说也是青布条盘的,但一望之下,尤如大蝴蝶一只一只从下颌的领部至腋下再至小腰斜落成排。
这一身打扮一望之下也是让人感觉仙气飘飘,心生敬畏。她的腋下,掖着花手绢,烟荷包不是灰黑色也是花布的,尤其她下了车,一走起来,也不知是腰里还是脚脖子上仿佛都系了小铃铛,叮当地响着。
夏天来村里唱戏的戏班子,有一出戏就叫《跳大神》,是一女一男两个人,一个是仙姑,那仙姑因为是神仙,所以叫大仙。大仙总要有跑腿的伙计,那男的虽说做着伙计的活,但因为毕竟和仙人在一起,所以,也封了一号,谓之二仙,北方的男人略笨一些,所以,即便为仙,也是二仙。
唱词中有好长一段是唱主人招待仙姑所备的食物,极尽华美,从酒到菜到肉到汤到烟,从天南到地北,所有物产未必都是家中所有,但要一一承报一番,为着什么?十分的敬和爱罢。如他对仙姑言:
要吃面更不难,我把面名报一番,有个伙计王老四,擀的面片赛雪片,拿刀一切一条线,下到锅里团团转,挑到碗里莲花瓣。
因这一出戏人人皆知的缘故,所以跳大神必是男女二仙共同起舞的场面亦是深入人心。可若只来了仙姑,而未带二神,大家心下虽然一疑,但一想,也许那二神另有公干(实际是忙着连日出马,玉米地早荒了,他要在家忙着铲二遍地),而这仙姑既然能自己来,想必也是胸有成竹的。
仙姑来到,先以好酒好菜招待,这仙姑酒量又好,五六十度的高梁烧亦觉得可口,她三杯两盏的一饮,愈发使人觉得她的可亲可敬,不高高在上,亦食人间烟火,如此的可亲近,那医病问卜的效果自然高上一层。她若在家是吃了饭而来,那自然不饿,所以亦是可免掉宴饮而直接跳神的。四平八稳的八仙桌,用一张红布蒙了而为香案,再杀一只大公鸡,就可以跳大神即谓之出仙了。
这跳大神的功能有:一可驱邪祈福,二来问病因,三是好多人还深信仙姑可帮着看病。
若二神没来,旁边要找一个经过事的帮着打鼓,鼓声一响,女仙即神色端穆,然后全身有韵律地摆动,那身体柔软至极,是真正的满族宗教仪式还是关东的民间舞蹈?或者是两者已默默无声地于时光流水中慢慢相融?一开始她是慢慢舞,慢慢摇,然后越旋转越快,她有时一只手还打着另一只小鼓,鼓点声越来越密,她舞得越来越快,是急急落下的夏天的一场雨。落雨声中,鼓声嘎然止住,她唱一声:仙童来呀哎(也许是仙姑或仙人)……听得不真切。这一声呼之后这仙姑便不是仙姑而是另一个人了,这个人也许是神仙,也许是那病人祖上的魂灵,这从她那说话的口气才可以知道。既而她表情更庄严,舞姿趋缓,开始唱曲,曲调婉转悠长,词意也能听得清,兼或停下问一声病人生辰八字或家乡年庚之类,唱词中兼有去年八月犯口舌,或报柴垛时不小心拆了黄鼠狼的窝之句。
谁家一请了来跳大神的,那一村子的人都放下正干着的活,来观看,看的人越多她越欢喜,小孩子往往一心看她跳舞,大人们往往边看边琢磨她所唱出的句子,并不停地点头,低头默想以印证,而那病人家里多跪伏在地,只耳朵竖起来听唱词,并在心下一一记着。
那舞蹈,是我小时候见过最诡异而美丽的舞蹈了,那女仙也许年纪大了,但在小孩子看来,仍是当年乡下最神密而好看的女人,加上出语成章俨如奥妙经文,真是一个通天地神古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子,安慰了人们普遍的对于生老病死十分的惧怕和无限的寂寞。有了她,仿佛那生病也不是可恐惧之事,仿佛有来自她或天地自然的力量帮着抵挡似的。兼之一些仙姑本来脾气就不大,且说话又能慢言慢语,则更为可爱可敬。哪怕最末,她说:这病恐怕来势汹涌,要去城里医院瞧瞧或一定要找人搭脉开药这样的话,也不觉得奇怪而只觉得更像亲人。
二人转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关东的小孩子都是听着二人转长大的。也听评戏、京剧、大鼓书,但也许因为是听得少,所以感情有些淡。评戏中,听来听去而不厌的,有《花为媒》、《茶瓶记》、《刘巧儿》,听戏,要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听,才解得况味。乡间年年都唱几次戏,盼看唱戏如盼过节,村中空地上有专门为做戏台而搭的土台子,土不经风雨,常常要修补,后来聪明的人想到用四台拖拉机的车斗一拼,四周镶上松柏枝子,可是最好不过的铁戏台。戏班子一到,那炒瓜子的、卖花生的、蘸糖葫芦的、卖雪糕的,也倾城而动,那花生、瓜子都是论茶杯而卖,大一点的一茶杯一毛,小一点的一杯五分,不用称量,盼看戏的小孩乐趣不在听戏而在吃。
唱二人转的一个戏班子顶多六七人,拉弦的一两个,演员三四个,有的班子才四五人,我自幼见过的最奢华的戏班子多不过十人,二人传,就是两个人一起唱戏。我幼小时亦曾在乡下看过赵本山的《瞎子观灯》和《摔三弦》。他在乡村戏台上演得远比在电视上好,那么放松,如鱼在水的感觉,他的每个笑,他眼睛微一眨,仿佛都是和一个人在秘密交流一件心照不宣的事,而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样的眼神,而他,有这样的力量,竟使每个人都觉得那一眼独独是和自己一个人之间的交流,而其它人却对此一无所知似的。《瞎子观灯》之好,竟使每个听过一遍的人都能唱起来。那《摔三弦》是个新戏,是为拉场戏,不是一男一女,而是一男二女(主要演员),我也非常之喜欢,到今天多少年过了,我想我仍能通篇将台词背诵如流,写这个本子的若不记错应是两个人,亦是此地前辈,李忠堂和崔凯,所以觉得如果不背一背,真是太辜负了。可惜对白多,这一个戏写的主题是计划生育。二人转男演员中声音最好听的我以为是韩志平,圆润绵甜,心平静气而且蓬蓬勃勃,他一出来,永远一幅书生打扮,在他之后,好像从没有人把《回杯记》、《楼台会》、《大西厢》唱到那样好,松驰,严正。
另一位演员安志彬我也是看过他的戏的,他也唱过《回杯记》、《楼台会》,但我觉得他的声音里有苍凉而不像韩志平那么溢年轻书生的朝气。两个人唱的《回杯记》是同一个本子,开头都是女演员先出来道白:
一只孤雁往南飞,
一阵凄凉一阵悲,
雁飞南北知寒暖,
二哥赶考不知归。
然后一声叹息,仿佛不是叹息,有压抑不住的喜气洋洋和调皮,让人听了欢喜。所以搭档很重要。《大西厢》这两个人也都唱过:(女)崔莺莺穿花越柳向前走,也不怕露水打湿(男)身上的鹦哥服,(女)也不怕花枝扎破(男)绣花衣裳。真是又绵远又凄凉,但后面唱到西厢观画中上一帘下一帘左一幅右一幅的对子时,历数今古,一问一答,应和如流,才情四溢,扇子飞似的扭来扭去真是美得眼花缭乱,让看的人每个人都为那唱的人提着一口气似的。还有很多演员,现在不大记得名字了,《梁赛鑫擀面》、《猪八戒拱地》、《水漫兰桥》、《包公陪情》、《马前泼水》等也很不错。《水漫兰桥》我不知作者,写得非常好,魏奎元半路喝水遇青梅竹马的兰瑞莲,两个人相认然后相约私奔,互留定情物:
男:我把小扇递过去。
女:我把小扇接手间
男:三更若有小扇在,烧火丫头我不嫌,三更若无小扇在,九天仙女我不攀。
…………
女:我把金钗递过去。
男:我把金钗接手间。
女:三更若有金钗在……
两人约定三更兰桥相见,可惜,夜里大雨,水漫兰桥,两人双双被洪流冲走。
《杨八姐游春》也是我喜欢的一出,最喜欢佘太君向包公要彩礼一段,包公代皇上向佘太君提亲娶杨八姐,佘太君张口应下,包公以为平时看错了佘太君,不禁目瞪口呆,以为佘太君也是攀龙附凤之流,佘太君应下亲事,却说女儿出嫁要为女儿按风俗要些彩礼,这戏的彩出来了,佘太君的礼单如下:
我要那一两星星,还有二两月;
三两轻风,四两白云;
五两泰山,六两气;
七两火苗;八两雷音;
张果老的毛驴我也要,我女儿骑它好回门;
何仙姑的笊篱我也要,我女儿捞饭待亲人;
曹国舅的葫芦我要它半拉(半个之意),我女儿用它装线针;
(男)吕洞宾的宝剑啊,我也要;
(女)我不要,
(男)为什么?
(女)老身我最恨贪花恋柳、恋柳舍花那路人
……
这出戏前面还要有小帽,可以是《放风筝》:
三三三月里,放呀放风筝,
桃红柳绿草儿又发青,姐妹二人来在郊外放风筝。
大姐姐放的是花蝴蝶,小妹妹放的是蜻蜓。
边扭边唱,这小帽多为润场之用。每出戏前都唱一段,因这二人转每出戏不管戏里多少人物,也只由这一男一女来唱,他们一会扮演男女主人公,一会又扮主仆其它人等,还可以边演边道白评判。男的多穿书生的长衫带着两条软纱翅的帽子,或肥纱裤,穿镶金边走银线的坎肩,一手执扇,扇子是纱的,或水红或翠绿,边上一转纱边,打开来一朵大荷花似的,一手执绣满花边的八角手绢,这手绢舞起来上下翻飞,左右摇摆,抛到半空也可以接回来,女的多穿绸缎的裙子,古代小姐的打扮,非常符合大家的审美也经得起所有观观众评判。不像现在所见一些二人传演员,那么不正经的打扮,二人传越来越没样子了,不像以前那么严肃,只是唱一个本子,从不靠其它戏外的东西华众取宠。
两人一上场,总是先唱小帽暖场,这经典的小帽除了《放风筝》、还有《游西湖》(是写白娘子和许仙的一段:徐郎夫啊,徐郎夫,那一年,你我二人搭船借伞、借伞搭船成夫妇……)还有《月牙五更》、《小拜年》(大年头一天啊,人人都把新衣服穿,也不管那男和女啊,也不管那老和少啊,都把新衣穿。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少给老拜年……初一到初八啊,新媳妇住妈家……)这些小帽中,亦可见乡俗民风。唱过小帽,两人要说说话,三言两语介绍自己或剧情,然后自报幕,戏归正传,从不罗嗦。
曾经很喜欢《月牙五更》,因为很多戏开场前都唱它,一来二去竟有了许多版本。一般都是一男一女两个演员唱,只是一个女的小姑娘、大婶不拘的唱则为单出头,单出头中有《红月娥做梦》,也有《月牙五更》:一更里呀月牙上窗棂,手扶栏杆呼唤梅香,银灯掌上……,单出头的曲目内容多为闺怨。
小帽、单出头、二人传和后来出现的拉场戏,戏文都质朴之极,多为关东方言俗语,简洁明白,内容多涉忠诚、义气、爱情,多截至历史传说中的一段,但皆有头有尾,使人听了不觉得有缺陷,那语言不仅生动,也是幽默的。演员们因爱而唱,端正虔敬勤勉,外人所谓台风不端、艺不入流之说只见于目下浮燥之时而非先时风气。
听一出二人转,而见北方民众性情之坚忍、忠义、幽默、豁达,并非虚言。而怎样广袤的土地历经多少年沧桑才哺育得出这样才情四溢的戏文?人生若戏,亦或戏若人生?一二十年过去,当年那一批批游走在草屋清巷,将二人传的至美漫天漫地不拘乡间街市恣意播洒的美青年们是否廉颇未老?也是否还有那么样多人喜欢他们,戏台搭起来,便三天五天彻夜无眠,四面八方不约而至,万人空巷?听者专注,唱者也不拘台下听者贫寒贵贱?
责任编辑⊙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