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笔下的印度
2012-04-29张瑞瑶
张瑞瑶
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家,外国人对它的兴趣永不会消失,不管是王子或贫民、学者或文盲、智者或傻子、富人或穷人、囚徒或自由人,概无例外。总之,这是一个人人都想看一看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一百年前,马克·吐温在他的长篇小说《赤道圈游记》中给出了心目中的答案:印度!他笃定地说:看过一回之后,即便是匆匆一瞥,也不愿去和世界其它各地的风光做交换!
《赤道圈游记》是马克·吐温在1895年环球旅行后写成的,于1897年出版,记述了他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非洲等地的见闻。在这本以游记为题材的书中,以对印度的描写最为具体和生动。作家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独特的眼光对印度的人文景观、风土人情作出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使人如身临其境、叹为观止,更让读者久久沉浸在印度所独有的厚重历史氛围中。
心荡神迷的色彩
最先触动马克·吐温的是印度的色彩,“一切都是色彩,是心荡神迷的色彩,是销魂夺魄的色彩——遍地都是——无处无之??”大街上全都挤满了衣着鲜艳的人群,他们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运动,在摆动,在游动,在转动,七彩十色,狂乱纷繁,明暗深浅,错落其间,雅致、秀丽、素淡、柔和、强烈、艳绝、活泼、灿烂,就像是一阵飓风扫过,刮起的一场香豌豆花风暴。不一会儿,在印度有着特殊象征意义的大象也为这支队伍增色,身罩华丽的节日象披摇摇摆摆穿过那一片五光十色的风暴。
在这条街上,马克 · 吐温缓缓地一路走过,置身其中,领略到了别样的异国情调。即将到了城里又不免朝那条街道望去,灿烂夺目的景象再次出现,只见它像在碾碎的草莓色调的火焰中燃烧一般。而道路两侧的阳台都缩入房子前面,仿佛是异想天开的鸟笼式安乐窝。一排排屋顶上全挤满了人,每一群人都迸发出光辉炫目的鲜艳色彩。
闹市的街道如此迷人,乡间小道的异域风味也毫不逊色。那儿从来都不会寂静无声,也从不会寂寥无人,印度总是在运动着的,棕色的人群总是川流不息。这一股跌跌撞撞、勤勤恳恳的人流,总是那样高高兴兴,吵吵嚷嚷,这是陌生的人类生活,看了使人着迷,令人满意。他们的衣服五光十色,仿佛是从彩虹处窃取来似的。
总之,对这些地方浓墨重彩的描写和渲染,使马克·吐温笔下的印度呈现出一副热闹、色彩流动、浪漫、瑰奇的气派,宛如一个富庶迷人、如梦似幻的东方福地。除了印度土著的服饰和人群散发出的令人难忘的情调外,印度土著特有的棕色皮肤也很让他着迷。他给我们设想了一个惊人的场面,当白人处于一大群棕色皮肤和黑色皮肤之中时,白色皮肤的人在映衬下更加显得苍白、无血色,有时简直惨白如鬼。
恭顺善良的土著
在勾勒出印度的人群之后,马克·吐温与他们有了更亲密的接触。他发现,大多数的印度土著温顺而善良,甚至让他怀疑印度暗杀帮的存在。在对印度的异域书写中,西方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鄙夷姿态来看待印度。比如,流传在西方的谚语:“印度人的话,如未证实是没有人相信的”、“在印度你所要做的事就是要提防你的邻居”等等。马克·吐温对这些说法不免有所耳闻。但当他亲历印度后发现,现实中的印度土著恭顺,懂礼貌,从前看的某些对印度的负面描写和道听途说的传闻仿佛不攻自破。
在他的笔下,印度是典型的礼仪之邦,印度土著温文尔雅,是一个温和、文雅的种族,举止中自有一种动人、可爱之处。比如说在一般的礼节方面,对于“粗野”的西方人来说,道上一声早安就够不错了。但对于文雅、重礼的东方来说,就显得太唐突了一点儿。在请安时做儿子的要毕恭毕敬地用一只顶端涂有朱砂印泥的小银器在父亲的额头上印一下,留下一个印记,做父亲的也要给儿子祝福作为答礼。雇佣的跟班也总是谦恭有度、彬彬有礼,在客人面前,他们总是低眉顺眼、尽职尽能。
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如马克·吐温所言,恒河本身和河中的每一滴水都是一座庙宇,从某种程度上说,信仰塑造了印度人温顺和善的性格,他们大都安于天命、老实本分、易于相处。
以杀人为乐的暗杀帮
马克·吐温坦言,当他还是个小孩子,住在当时还是偏僻而又人烟稀少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时候,就听到过一些模模糊糊的传闻和谣言:在印度有一个专干杀人勾当的神秘团体,被称之为暗杀帮。虽然这些传闻人人爱听,但都不相信,即便相信也是有保留的。可见他的态度很明确,虽然暗杀帮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他对传闻的可靠性很怀疑,而在《赤道圈游记》中,他却津津乐道地描述暗杀帮。尽管他仿佛在一开始就暗示读者,这部分对印度的书写充盈着幻想、想象臆测的成分。
暗杀帮的时代充满着偷袭、杀戮。在印度的大路上旅行,如果没有人保护,就休想活着通过。那些暗杀帮歹徒不管你是什么地位,什么职业,什么宗教,什么人,凡是没有携带武器用以自卫的人,只要让他们碰到,都一律杀无赦。每逢旅客到了村与村之间时,便成了最容易下手的猎物。暗杀帮歹徒都小心翼翼,通常都要被害人坐下来,因为这是最方便下手的姿势。暗号往往是几句极普通的话,譬如“拿烟来”这一类的话。接着一个老手能在瞬息之间将勒杀头巾绕在被害人脖子上,突然一绞,被害人的脑袋便会无声无息地向前垂落,眼睛从眼窝中突出,于是一场暗杀就此结束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暗杀逐渐演变成一种世袭的行当,父亲将暗杀伎俩传授给他的儿子,他儿子的儿子。男孩儿一满16岁便成为暗杀帮的正式成员,而一些老于此道的歹徒,到了70岁还在干。而暗杀帮在印度又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所以在马克·吐温的笔下,暗杀帮时代的印度笼罩在不安、惊恐之中,普通人个个噤若寒蝉,生存环境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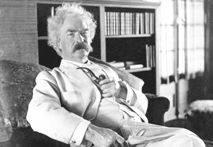
横行肆虐的鼠疫
在印度,不仅人与人过不去,连老鼠也不安生,“唯恐印度不乱”,马克·吐温以惊悚的笔调给我们讲述了一件事:那本来是一场婚礼,但眼下却没有那种景象,仿佛活在一座死城中。在那些静悄悄的、空荡荡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一点生的迹象,连乌鸦都不聒噪一声。这很像是为一部恐怖小说开了个头,他接着写道:在地上却到处躺着入睡的土著——竟有成百上千之多,他们挺直身子躺着,毯子紧紧地裹着身子,连脑袋都被裹住了,他们那种僵直的睡态活像个死人。任何一位读者读到这些文字都会毛骨悚然,但他总觉得这样的描写还不够刺激,随后又是一片深沉的寂静,窜来窜去的老鼠,地上到处直挺挺地躺着模糊难辨的人体,两旁那些敞开的摊位,恰似一座座墓穴,在守灵灯似的摇曳灯光中躺着一些一动不动,恰似尸骸般的人体……
情愿自焚的寡妇
假如说暗杀帮与鼠疫是外部势力带给人们的灾难,不幸的人身不由己而命丧黄泉,可就是有些人偏偏“乐意”选择自取灭亡,这就是印度的一大风俗——寡妇自焚。马克·吐温的解释是:“一个妇女在她丈夫死去时就自尽而死,便可以立刻和丈夫重新团聚,以后便永远和他愉快地生活在天堂里。”这种风俗更是有一种蛊惑人心的论调:她的家人就会为她立一块碑,或盖一座庙,对她表示敬意,永远纪念她,这位自我牺牲的妇女还会使她的子孙后代永享尊荣。相反,如果她选择忍辱偷生,她便会成为一个受人唾弃的人,她不能再嫁,她家里的人也都瞧不起她,同她脱离关系,她将成为一个无亲无友的丧家之犬,终生过着悲惨的生活。
而令人倍感惊异的是当时印度的寡妇选择自焚并不是出于舆论的压力,一年中竟有八百名寡妇心甘情愿,还确确实实高高兴兴地在死去的丈夫身上自焚而死。仿佛这种习俗开了头,就有了经久的魅力,马克·吐温更是用一种冷峻的、镇定的笔调详细描写了一个新寡的妇人自焚的前后经过,令人唏嘘不已。
繁华和荒凉的国土
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像印度这样对照鲜明的人居条件。一边是像皇宫一样的豪宅,高树围墙,佣人成班;一边是碎裂的泥墙,破败的茅舍,丑陋、肮脏。可以说印度人民总是处在富裕和贫穷的两极,要么给人的感觉是富可敌国,要么是一贫如洗,这是一个繁华和荒凉并存的国度。
印度的政府大厦除了卫队和奴役是土著外,别的一切都是欧洲式的,是一所私第和办公大厦的巧妙结合。它具有静谧的优雅、静谧的色调、静谧的韵味、静谧的庄重,仿佛都是现代教化的成果。同时,这座总督官邸代表着英国对印度的控制,英国的气势、英国的文明在这座大厦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英国人的居住区也是异常富裕,有宽阔的林荫道和长长的街道,秀丽、迷人,洋溢着舒适、悠闲和宁静的气氛。可是到了一处小镇,成片成片的建筑物显然都是些庞大的屋宇和历史遗迹,都那样倾圮、颓废,仿佛被肩负的年代重担压得那么疲惫、那么难以承担。在贝拿勒斯郊区,沿途的景观更是令人抑郁不欢,一眼望去尽是灰蒙蒙的不毛之地、倾圮的庙宇、塌败的坟冢,整个地区似乎由于衰朽和贫穷在痛苦地呻吟。当那些大象披上光彩夺目的宫廷象披悠闲地走过此地时,它们与周围那丑陋、肮脏的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
在欣赏完印度的景色之后,马克·吐温不禁对印度的游览经历回味一番,他突然抛出来一句话“你很快会觉得印度并不美”,这句话令读者很惊诧,不过他继续说:“但它还是有,一种令人消愁解闷、永不消退的魅力……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那是由于它的历史,而打动你的就是它的历史。”原来,印度最动人的还是它的历史!
众所周知,印度历史就是一段伤痕累累的殖民史,特别是在1880年英国实现了对它的完全占有,一个失去主权的国家是没有自尊可言的,所以这片土地“孤独凄凉、面貌丑陋”。可这个荒芜的国家并不能与当时同为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和格陵兰相提并论,那些不毛之地没有什么可申诉的,因为它们没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没有经历过眼云烟般的荣华富贵,更没有承受过人类所遭遇的种种灾难,因此,它们都没有什么东西足以使它们超凡脱俗。而印度的幽邃和苦难都是迷人的,它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是历史的母亲,是值得人们敬仰和爱戴的。
在他看来,印度申诉的声音是“心酸中含有讽刺,雄辩中带着忧伤”,这种讽刺何尝不是马克·吐温对西方殖民者的讽刺?这种忧伤何尝不是对印度受伤的文明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在这部分对印度的评说中,无形中传达出马克·吐温对殖民者的责难,而他是否也在暗示,印度当时正在经历的被殖民遭遇在它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将会风自轻来云自淡?也都会如过眼云烟般成为过去?
通过小说,马克·吐温为我们走进印度打开了一扇门,他的描写固然不能全面涵盖真实的印度,甚至有些地方跟现实中的印度存在或多或少的冲突、矛盾。但是在对印度形象的刻画中却体现出作家独特的见解和思辨性的考量,而且他对印度的感情也是真挚的、坦然的、美好的,值得人们珍视。

